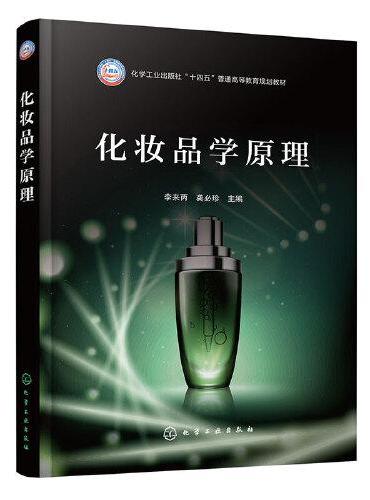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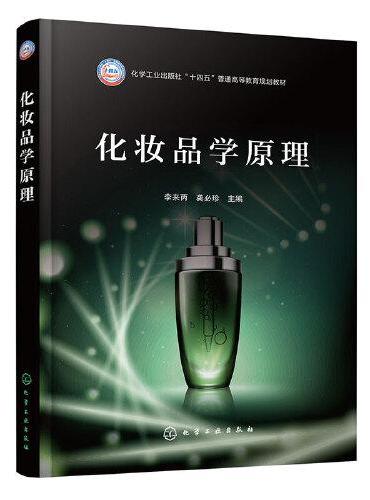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NT$
254.0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NT$
214.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NT$
254.0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NT$
254.0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NT$
500.0

《
拍电影的热知识:126部影片里的创作技巧(全彩插图版)
》
售價:NT$
500.0

《
大唐名城:长安风华冠天下
》
售價:NT$
398.0

《
情绪传染(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邵燕祥、贾平凹、阿来、舒婷、张新颖、梁鸿、祝勇、裘山山、王彬彬、林那北、孙小宁、彭学明、杨文丰、杨献平等14位名家联袂,百年一遇的作者阵容,打造史上巨强的中国散文读本。
◆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DI一大奖”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首次结集,呈现丰盛文化盛宴。
◆这是中国当代散文强音,代表当代散文发展的zui高水平。有你不曾读过的历史书写,有你不曾认知的鲜活现实。
◆集结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阿来《瞻对》、贾平凹《老生》等几部重量级作品的精彩片段,一本书读通多部名作。
|
| 內容簡介: |
|
《文人事》为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的作品选集,全书收录了邵燕祥、贾平凹、阿来、舒婷、张新颖、梁鸿、祝勇、裘山山、王彬彬、林那北、孙小宁、彭学明、杨文丰、杨献平等14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散文作品,其中集结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阿来《瞻对》、贾平凹《老生》等几部重量级作品的精彩片段。通过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有机融合的文本展示,力求呈现这个阶段汉语散文的zui优成果。透过这些作品,不仅可以窥见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审美本位和价值指向,也可洞悉在场主义的审美标尺和创作追求,昭示了在场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
| 關於作者: |
|
周闻道,本名周仲明,现供职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门。文学硕士,作家,经济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场》杂志主编。汉语写作di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di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发表作品500余万字,著有《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等文学专著13部,330余万字;财经评论专著3部,100余万字。主编“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丛书等多种。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多项文学奖,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大学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
| 目錄:
|
在场主义的批判精神引导文学走向(代序)丁帆
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节选)邵燕祥
附: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授奖词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节选)阿来
附:阿来《瞻对》授奖词
《沈从文的后半生》(节选)张新颖
附: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授奖词
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王彬彬
附:王彬彬《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授奖词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舒婷
附:舒婷《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授奖词
文渊阁:文人的骨头祝勇
附:祝勇《文渊阁:文人的骨头》授奖词
梁庄:归来与离去梁鸿
附:梁鸿《梁庄:归来与离去》授奖词
《老生》后记贾平凹
附:贾平凹《〈老生〉后记》授奖词
运动队林那北
附:林那北《运动队》授奖词
行走高原裘山山
附:裘山山《行走高原》授奖词
滇西笔记孙小宁
附:孙小宁《滇西笔记》授奖词
这样回到母亲河彭学明
附:彭学明《这样回到母亲河》授奖词
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杨文丰
附:杨文丰《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授奖词
南太行民间叙事杨献平
附:杨献平《南太行民间叙事》授奖词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
| 內容試閱:
|
1959年8月24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
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
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
把千言万语交付它
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
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
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
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
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
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
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
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
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
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
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19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19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
我在10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地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巴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
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
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
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〇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
那首诗中的“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从似乎缥缈空灵的云里雾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样,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
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
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听天由命了。
我在1959年重新进入办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找我们面谈,等于面试,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今天,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咱们这回一块儿工作了,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表演团体和唱片社。后来我多次想,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二十六岁的“摘帽右派”了?
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他说广院人手极缺,我回来正好,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他跟柳荫商量,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学院倒是来了就排进功课表,我半天在台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学院草创,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原是电台宿舍,我住过的——幸耶不幸?几年后“文革”开始,我又被关到这里,灰楼成了所谓的“牛棚”。那是后话。
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回来由我们判作业,讲评。我没参加听课,半年多的时间,只在什么场合,远远看过林焘一眼。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联大的。
我没读过文字、训诂之学,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语法自在其中。所读不多,却学语法,越学越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如主语、宾语的句子结构,好像一看就懂了。学英文时,有Diagram ,对句子进行图解。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这一些,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学养”根底了。
这时印尼排华,有大批侨生回国,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主要是改作文。这我倒是轻车熟路,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到“文革”,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
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像我这样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不再兼做辅导教师。左荧也表示理解,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邹晓青是“进城”老干部,20世纪50年代初大区撤销后,从《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1958年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一员。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他也受了处分。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温济泽调进来,又跟邹晓青共事了。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