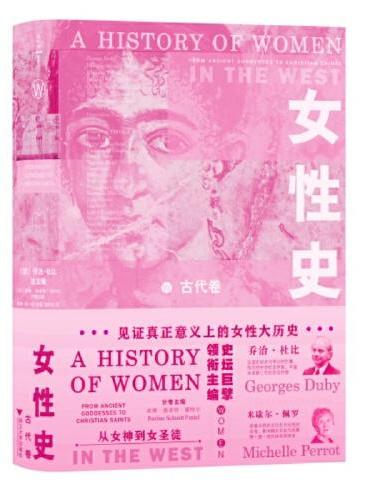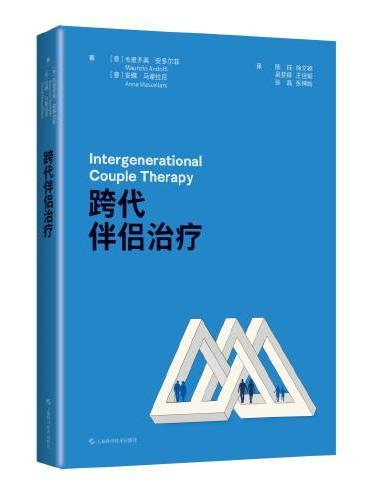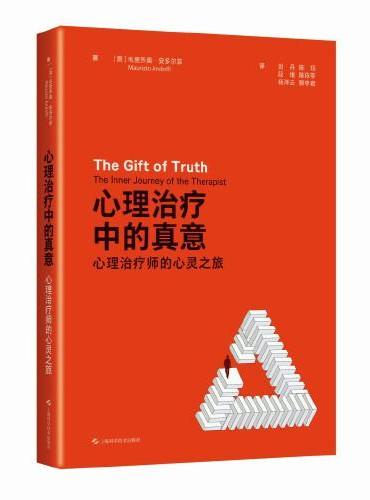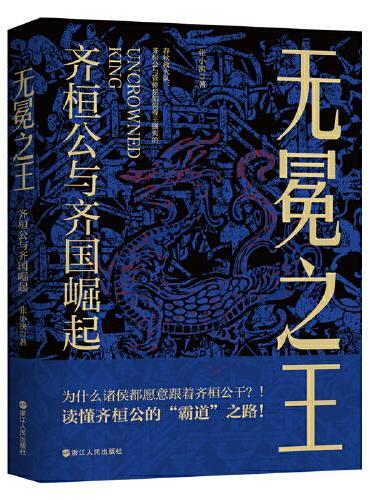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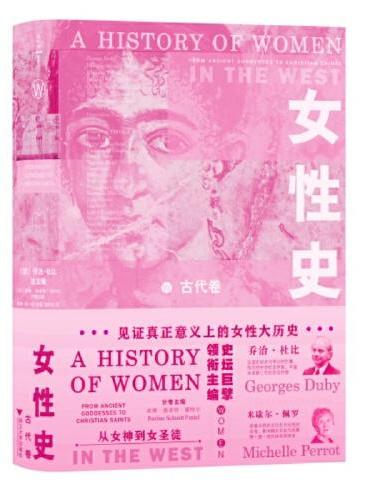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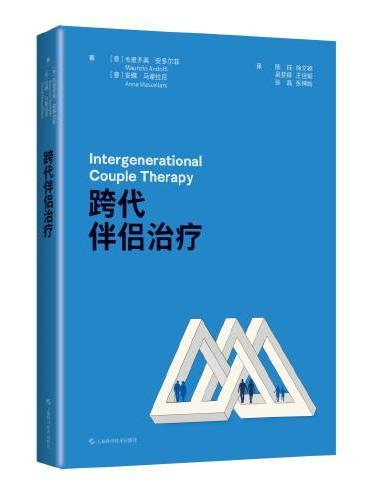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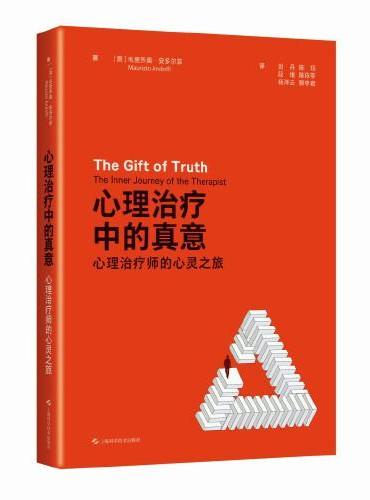
《
心理治疗中的真意:心理治疗师的心灵之旅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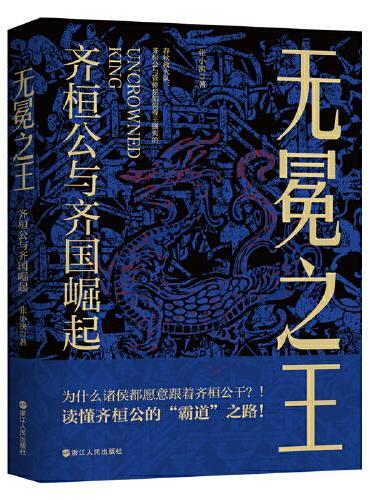
《
无冕之王:齐桓公与齐国崛起
》
售價:NT$
290.0
|
| 編輯推薦: |
|
作者大卫贝泽摩吉斯凭此作入选《纽约客》20位40岁以下优秀作家,获英联邦作家奖。七个漂泊异乡的成长故事,讲述边缘少年的彷徨与希望。
|
| 內容簡介: |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俄裔犹太人、波罗的海的贵族贝尔曼一家从前苏联移民到多伦多,他们不懂英文、没有钱和工作,只有对未来模糊不清的向往。《世界上第二强壮的人》以儿子马克的视角讲述了从孩童到青年七个主题各异的成长故事,马克遭遇的彷徨和挫折同时也折射出挣扎于社会边缘的父母所承受的打击与失望。《世界上第二强壮的人》是电影制片人大卫·贝泽摩吉斯的自传性短篇小说集、处女作,贝泽摩吉斯也凭此作在北美文坛一举成名。
|
| 關於作者: |
|
大卫·贝泽摩吉斯,加拿大作家、电影制片人。1973年生于拉脱维亚,6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作品首见于美国短篇小说圣殿《纽约客》《哈泼斯》和《西洋镜》,2004年结集出版处女作自传性短篇小说集《世界上第二强壮的人》,并凭此作一举成名,入选美国亚马逊年度十佳好书、纽约图书馆年度最值得记住的好书,获英联邦作家奖、《卫报》处女作奖提名。2010年,入选《纽约客》评选出的20位40岁以下优秀作家。此后陆续推出长篇小说《自由的世界》《背叛者》,两部作品均入围加拿大吉勒文学奖。
|
| 目錄:
|
达普卡
按摩师罗曼·贝尔曼
世界上第二强壮的人
以兽行纪念
娜塔莎
科恩斯基
法定人数
|
| 內容試閱:
|
世界上第二强壮的人
一九八四年冬天,母亲患了神经失常症,正在慢慢康复。父亲的生意时而濒临破产,时而略有起色。那个冬天,国际举重锦标赛在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一天晚上,父亲接到电
话,说要邀请他做大赛裁判员。尽管报酬极其微薄,父亲还是接受了这份象征着尊严的工作。当他再次穿上在国际举联工作时的运动衫,便不再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按摩师,也不再是巧克力厂辛苦劳作的工人。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哪怕只有几天。父亲从卧室里找出一本证件—上面有国际举联发给他的资质证书。证书上有父亲的照片,那时他还没有遭受这些年来移民生活的磨难。照片中,他脸上挂着苏联高级官员特有的那种超然的自信。这张照片我见过很多次,有时候还趁父亲不在家,偷偷拿出来仔细端详。想到照片上的人和父亲曾是同一个人,我心里觉得暖暖的。
接到电话几天后,我们收到国际举联寄来的正式文件。我和父母凑在餐桌前,浏览参赛者名单。苏联代表团的名单中,赫然印着谢尔盖·费德连科和格雷戈里·齐斯金的名字。母亲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见到他们了,是不是他们要看到我们家了。仅仅在一周前,医院的人来到家里,把母亲裹进一床橙色的毯子,绑到轮床上就送往布兰森医院。几个月来,母亲因患上瘫痪性焦虑症,浑身乏力,连最基本的家务也做不了。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靠煮鸡蛋和下立顿鸡汤面勉强填饱肚子,厨房的地板上已经积起一块块黏糊糊的脏东西,角落里也落满了灰尘。母亲说:“上帝啊,可不能让谢尔盖看到家里这个样子。”
我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从桌边一跃而起。我满屋子跳着,一边跳一边唱:“谢廖扎,谢廖扎,谢廖扎,谢廖扎要来啦!”
父亲叫我安静一下。
“谢廖扎,谢廖扎,谢廖扎!”
母亲站起来,把扫帚递给我。
“你要是坐不住,现在就扫地。”
“谢廖扎要来啦!”我对着扫帚唱道。
离开拉脱维亚的五年前,父亲在里加迪纳摩体育馆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业余健身班。那时他是迪纳摩的高级行政人员,负责翻阅文件、管理预算。之前父亲曾是优秀的大学校队运动员和VEFb 无线电厂出色的足球教练。尽管是犹太人,父亲却深得上级赏识。所以当他和同事格雷戈里·齐斯金(他也是犹太人)开始办健身班时,上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想,要是好的话,这个班有可能会发现举重人才,最不济也能捞点外快。
每周一、三、五晚上六点到九点,父亲和格雷戈里打开迪纳摩体育馆的后门,那帮热情高涨的学员就进去锻炼。学员主要是犹太大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员,大多想在尤尔马拉海滩上一展健壮的肌肉。他们算不上出色的运动员,但都能按时来上课,对训练结果也很满意。父亲和格雷戈里负责为他们制订训练计划并监督他们完成。平时,父亲不是忙着看没完没了的文件和冗长的报告,就是向迪纳摩的领导和来访要员做正式汇报。对他来说,这个健身班是个很好的调剂,可以让他暂时从苏联繁琐的行政职责中逃脱出来。而且办这个班收入也不错,除去给迪纳摩领导的那部分和给门房的几卢布,父亲和格雷戈里每人每个月可以多赚三十卢布,相当于我们三居室公寓房租的两倍还多。
这个班父亲和格雷戈里办了好几年,各方面一直都相安无事。领导拿到自己那份钱就什么也不说了,只要迪纳摩各队能拿到好名次,这么好的一件事,没人会来搅和。而那几
年,里加迪纳摩可谓顺风顺水:维克托·吉洪诺夫的曲棍球队屡创奇绩,后来他被提拔到莫斯科,又加入红军;伊万琴科成为总成绩达到五百公斤的首位中量级举重运动员;那时它的篮球队和排球队在欧洲也颇具威名。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注意父亲的健身班。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那时有些犹太人开始移民,父亲的一些学员也申请了以色列签证。由于迪纳摩代表克格勃,部里就开始有人猜疑了。他们向父亲的一个领导指出,在健身班学员和申请出国签证的犹太人之间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联系。这个领导请父亲和格雷戈里到他办公室,告诉他们这种怀疑。他说这会给他们所有人带来麻烦,里加迪纳摩体育馆要是发起反苏活动,那可不好。那个领导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盘问父亲。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但他们都知道,接下来,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现在健身班已经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为了避免被上级叫停,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它的官方职能,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换句话说,他们最好能发现举重天才。
那次和领导谈话后,父亲向格雷戈里提议,明智的做法其实是把健身班停掉。反正钱已经挣到了,当时我父母已经决定离开苏联,而这种事是会引起大麻烦的。格雷戈里虽然没有移民计划,却也没兴趣去西伯利亚,所以他也同意父亲的看法。两个人决定,月底前就把健身班停掉。
第二天,父亲发现了谢尔盖·费德连科。
发现谢尔盖·费德连科的那天晚上,他们比平时下课晚了一些。格雷戈里早走了一会儿,父亲留下来和五个学生继续训练。等父亲打开体育馆后门准备离开时,已经快十点了。他们走进巷子,发现巷子里有三个年轻的士兵,喝醉了酒在瞎唱,身材最矮小的那个正在往墙上撒尿。父亲转过身去没理会他们,可是有个学生却有些按捺不住,想试试身手。他指责那个小个子士兵行为不文明,骂他是条狗,还骂了他妈。
小个子士兵就像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撒尿,两个高个子却摩拳擦掌,看样子是要狠狠打一场了。
“来,还真是个难搞的犹太野种呢。”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道歉。”
父亲预感到要出事了,即便出现奇迹,他和学生们能侥幸保住性命,警察也会牵扯进来,而警察牵扯进来的后果可比挨一顿揍要严重得多。
学生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父亲就赶紧出来劝和。他向那几个士兵道歉,说这个学生在健身班训练,虽然下课了,还没清醒过来呢,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医生已经证明了,
肌肉一发达,头脑就萎缩。父亲说他不想惹麻烦,希望他们接受道歉,不要计较了。
父亲说话的时候,那个小个子士兵撒完尿,系好裤子。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不一样,始终镇定自若。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一小瓶伏特加。巷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莫斯科人牌轿车,另外一个士兵指着车对父亲说:
“听着,老东西,要是你学生里有人抬得起这辆莫斯科人,这事就算了。”
他们就这样说定了,从车后面抬,离地至少一米。虽然发动机在前面,车子后部还是很重。车架、车轮、轮胎,再加上后备厢里的东西,一共能有几百磅。三百?四百?反正055
这个赌是输定了。父亲没有一个学生能做到,试也白试,看来这顿羞辱是在劫难逃了。但在父亲看来,羞辱也强过挨打和接受警察的调查。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学生们都一声不吭,
任那两个士兵奚落嘲讽。他们一个个走到车后,下蹲至保险杠的位置。
“当心,别拉到裤子里。”
“为了俄国母亲,抬起来!”
“为了以色列,抬起来!”
不出所料,他们连让车离地都做不到。都试完后,一个士兵转向挑事的那个学生:
“不行了吧?”
“这根本就不可能。”
“对你当然不可能。”
“对你这样的笨蛋狗杂种也不可能。”
很奇怪,大个子没上去揍他,而是转向小个子。
“谢尔盖,告诉他什么是不可能。”
小个子把酒瓶放回口袋,朝那辆莫斯科人走去。
“看好了,你这笨蛋狗杂种。”
谢尔盖下蹲至保险杠处,深呼吸一口,将车抬离地面一米。
从我四岁那年开始,到两年后我们离开里加,谢尔盖经常去我们位于卡斯莫纳夫提卡斯的家里做客。每次参加完国际比赛回来,他都会来看我们。父亲发现谢尔盖两年后,他已经是国家队的队员,获得了“国际体育大师”这一备受尊敬的称号,在他所在的重量级保持着抓举、挺举、总成绩全部三项的世界纪录。父亲说谢尔盖是他见过的最伟大的举重天才,他的动作经济省力,对举重技巧也有很好的把握。这些都和天赋有关,他爱好举重就像别人钟情于毒品或巧克力那么自然。谢尔盖在一个集体农庄长大,从十二岁开始就干着成年人的活。对他来说,生活就是拉粪肥、把干草打成大包、收割蔓菁和拖笨重的农具。十八岁参军以前,他还从来没离开过农庄三十公里。一旦离开,他就再也不想回去了。他的父亲是酒鬼,母亲在一次事故中不幸去世,那时他只有三岁。是我父亲把他从军队和农庄里解救出来,所以他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无以复加。谢尔盖的地位越来越高,可是他对父亲的忠诚却始终像孩子对父母一样,丝毫未减。一九七九年我们离开里加的时候,他对父亲的感情依然如故。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大红大紫的体育明星,走在大街上都有陌生人和他打招呼。在拉脱维亚,他像电影明星一样,人人都认识他。很多国家的报纸称,把体重因素考虑在内,谢尔盖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在我四岁到六岁的记忆中,谢尔盖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对里加的记忆不多,也不连贯,不过是些小插曲和零零散散的印象,但其中很多都和谢尔盖有关。我对他的印象虽然
和父母的讲述分不开,我心里却自有属于我的谢尔盖。光谱穿过棱镜,折射回童年的一幕幕场景,逐渐生成他的形象。我仿佛看到了来卡斯莫纳夫提卡斯看我们的谢尔盖,他穿着最时尚的进口服装,从遥远的国度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礼物:菠萝、法国香水、瑞士巧克力和意大利太阳镜。他向我们讲起奇异的国家,在那里,所有东西都和我们这儿不一样—不一样的火车,不一样的房子,不一样的厕所,不一样的汽车。他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候带个漂亮姑娘来,那时他和好多姑娘约会。他每次来的时候,想取悦他的冲动都会让我浑身痉挛。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我像猴子一样吊在他的肱二头肌上,还在地毯上表演翻跟头。唯一能让我睡觉的办法就是让谢尔盖跟着母亲去我卧室,用他独特的方式和我说晚安。我们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序,我盖好被子躺好,他将我和我的小床一起搬起来。他搬得那么轻松,就好像我的床不过是一张报纸或是一个三明治。他把我的床058抬到胸口,就那么抬着不放,直到我说出谁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谢廖扎,谢廖扎·费德连科!”
父亲带我去苏联代表团入住的萨顿酒店。随团总会有一个克格勃特工,这次来的特工父亲认识。父亲曾随迪纳摩出访东欧,见过他几次。他见到父亲非常惊讶: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你怎么在这儿?我在飞机上没看到你啊。”
父亲说他没在飞机上,他现在住在这儿。父亲一挥胳膊,告诉他是“这儿”,把我也划了进来。我的夹克衫、运动鞋、李维斯牛仔裤都可以作证,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和儿子现在住这儿。克格勃特工用赞赏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过得不错?”
“还行。”
“这是个美丽的国家,有干净的城市,大片的森林,漂亮的汽车。听说你们还有很好的牙医。”
在酒店大厅,那个克格勃特工张开嘴给父亲看。在一颗磨牙的周围,他的牙龈肿得吓人。他说已经疼了好几周了,在莫斯科时拔了旁边那颗牙,结果伤口感染了。机舱内的气059
压让他觉得自己都快疯了,吃东西根本不可能,至少要喝一公斤伏特加才有可能睡着,而总是醉醺醺的又妨碍工作。他还听说这里的伏特加很贵。他现在需要的是牙医,要是父亲
能在多伦多帮他找一位,解除这份痛苦,他愿意为父亲赴汤蹈火。他已经疼得胡思乱想了,他的房间在二十八楼,站在窗边,他都想过要跳楼。
父亲用酒店的电话打给我们的牙医杜莎。杜莎在莫斯科时本来是顶级的牙医,只是现在还没有通过加拿大的考试。她暂时在晚上帮一位加拿大牙医做清洁,她和那位医生私下商量好,她可以用他的诊室给自己的病人看病,用现金悄悄结账,收入两人对半分。但他们也说好了,要是有麻烦,那个医生就说什么都不知道,风险由杜莎自己承担。幸运的是,这样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点麻烦都没有。每周有那么几次,杜莎把诊室打扫干净后就看自己形形色色的病人,都是些没有牙科保险的俄国移民。父亲将这些告诉那位克格勃官员,说如果他不反对凌晨一点看牙医,可以去找这位医生。
为了表示感谢,这个特工亲自陪我们上楼去找谢尔盖。他说只要谢尔盖按时参加比赛并和其他队员一起飞回莫斯科,其他一切都好说,我们怎么和他见面都行。他以自己孩
子的双眼发誓,绝对不会有问题。
我们来到谢尔盖门外,他啪啪地敲门:
“费德连科同志,有重要客人!”
门开了,谢尔盖穿着队里统一的灰色便裤,正在系衬衣扣子。看到我们,他愣了一下。克格勃特工拍了拍父亲的背,说每次看到老朋友重逢,他都会很感动。看到这里,谢尔盖
才开口说话。特工口袋里装着杜莎的地址,他转身走了。
谢尔盖在楼道里和父亲拥抱,并给他苏式的一吻。父亲身高5.6英尺,体重170磅,和谢尔盖在一起显得块头很大。虽然我像美国孩子记球队得分一样记着谢尔盖的比赛记录,知道他在五十二公斤级里也是体重最轻的,但真的看到他身材这么矮小,我还是感到意外。
“那浑蛋可吓死我了。”
“克格勃最会敲门。”
“尤其是那家伙,对苏联可真是死心塌地。”
谢尔盖朝那个克格勃特工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我和父亲也跟着他看了一眼,那人确实走了。
谢尔盖转过身来看着父亲,咧开嘴笑了。
“我刚才在洗手间,吓得差点尿裤子。我想要是幸运的话,只不过又是一次药检。”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药检了?”
“从来没怕过。”
“需要我提醒你要尊重药检吗?”
父亲在迪纳摩任职时曾负责运动员的类固醇服用。每周开始时,他把药片和特殊食品券一起发给所有举重运动员。人人都知道规矩:不吃药,就别吃饭。
“绝对不需要,让运动保持公平。”
“嗯。当然了,你是遵守规则的。”
“我是遵守规则的,举重队是遵守规则的,人人都是遵守规则的。”
“听到一切都没变,我真高兴。”
“一切都没变。”
谢尔盖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真是让我惊喜。”
来酒店的路上,我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谢尔盖了,兴奋得发狂。可是真的见到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站在父亲身后,等着谢尔盖和我打招呼。可是好像过了很久,他才注意到我。他终于看到我的时候,眼睛朝下看着,好像不认识我。
“这是谁?”
“不认识了?”
“有点面熟。”
“想想。”
“不好说。”
“猜。”
“好吧,要是非得猜,我想说有点像马克,可是他长得太小了。”
“太小?”
“马克长得大些,他能做十五个甚至二十个俯卧撑呢。
这孩子看起来连十个都做不了。”
“我能做二十五个呢!每天早上都做。”
“我不信。”
我趴到萨顿酒店红金两色的地毯上,开始做俯卧撑,谢尔盖帮我从一数到二十五。我气喘吁吁地站起来,等着他的反应。他笑着张开双臂说:
“来,伙计,跳!”
我跳起来,谢尔盖把我抱进房间。父亲往格雷戈里的房间打电话,我挂在谢尔盖的胳膊上不肯下来。离谢尔盖的比赛还有两天,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他先和我们待一段时间,等比赛结束后,再和格雷戈里一起去我们家吃晚饭。
我和父亲从酒店带回来好消息的时候,母亲正在家打扫卫生。她用力擦洗地板、烤箱、家具、窗户,一寸都不肯放过。她把好几袋垃圾丢给我和父亲,我们提到楼道里,扔进难闻的垃圾道。父亲说谢尔盖看起来很好,这五年好像一点都没变。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很好啊,现在像加拿大人了,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
“你要是年轻,我就是女学生了。”
“你本来就是女学生。”
“救护车一周一次来接女学生。”
第二天,父亲给中量级比赛做裁判,早上顺路带我去谢尔盖住的酒店。他那天没有比赛,所以我和父亲一起坐地铁去,我负责把他领回家,母亲再带他去购物。我们穿过大厅向电梯走去,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克格勃特工向我们走来。我比父亲先看到他,当时我就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走近些才发现,原来是他的脸肿得厉害。越近越明显,仿佛是那张肿肿的脸先到,人随后才到。远看还有胳膊、腿、躯干、头发,近看就只剩下一张脸了。父亲因为心里想着裁判的责任,又担心迟到,直到克格勃特工站在跟前,才认出他来。一看到他的脸,父亲就吓蒙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天哪!”父亲一边说一边往后拉我,自己站到我和那个人中间。
克格勃特工一拍手,像是咧嘴笑的样子,但嘴巴还歪着。他的嘴唇肿得几乎分不开,只能看到窄窄的一条缝,透过那条缝,可以看到他嘴里的白纱布。他说话的时候就那么不怀好意地笑着,好像下巴被铁丝箍住了一样。见他这副样子,父亲的手在我脖子上抓得更紧了。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她是我们家的牙医,我去她那儿,我的妻子、儿子都去,我发誓她一直都看得很好的。”
特工努力想合上嘴,下巴上的肌肉却还在不停地抽搐。
“看得好,看看我,不能再好了。她给我装了三个牙冠,搭了一个桥。”
“她很大方。”
“她知道怎么给男人治病,麻醉剂加一瓶伏特加,我凌晨四点才离开她那儿。很大方,还是个美女,真是美妙的一夜啊,你懂的。”
“很高兴你能满意。”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记住,你在莫斯科永远有个朋友,我随时都欢迎你。”
特工自己笑着,转身走了。我们继续向电梯走去,一直升到谢尔盖那层。电梯里,父亲倚着墙,终于放开我的脖子。他说:
“永远不要忘了,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苏联的,为了你永远都不用认识这种人。”
我们敲了敲门,听到里面有动静,但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才出来。他刚才在做俯卧撑,上身只穿着背心,胳膊上的肌肉、肌腱和血管都鼓鼓的。从俄国逃出来、来到加拿大之前,
我们曾有半年困在意大利。在那儿我见过一些雕像,胳膊就是这样。我想雕像是用来表现真人、真胳膊的,可是现实生活中除了谢尔盖,我还从来没见过谁有这样的胳膊。
父亲着急要走,把我留下就急忙去会议中心了,我等着谢尔盖穿衣服。
“今天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
“妈妈说去超市,她觉得你肯定会喜欢的。”
“超市?”
“好超市,什么吃的都有。”
“你知道怎么走吗?”
“知道,先坐地铁,再坐公交车。有地铁和公交车,差不多哪儿我都能去。”
“加利福尼亚能去吗?”
“地铁不到加利福尼亚。”
“也许我们应该坐飞机。”
谢尔盖说话的样子我听不出来是在开玩笑,直到他哈哈大笑我才明白。我也想笑,但不知道笑什么,他好像压根就没想让我听懂。我很伤心,因为我很想和他成为平等的朋友。我觉得他笑的是我,而不是他的玩笑。
谢尔盖看我不高兴了,赶紧顺着我,问我超市的事。
“我们有时候去另一个不太好的超市,电视广告里的东西那儿不一定都有,但好超市里什么都有。”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指给谢尔盖看我们新生活中的地标性建筑。为了弥补景观的无聊,我尽量介绍得有声有色。我感到自己肩负导游的重任,要让谢尔盖看到些有意思的东西。可是俄国移民大多住在城市的北部边缘,周围尽是些褐色的公寓楼和旧的路边商场,确实没什么可看的。所以对每件普通的东西,我都要强调它和我们之间的联系。这样,介绍就显得自然了。有个加拿大轮胎商店,我的自行车就是从那儿买的;有家俄国里维埃拉宴会厅,父亲在那儿过过生日;一家熟食店叫伏尔加,另一家叫敖德萨;还有我打电子游戏的便利店,我上学的学校、我的曲棍球场、我的足球场。谢尔盖一边看一边点头。我知道,我说的和他看到的其实很不一样,可我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
公交车在我家附近停下,我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不用再说了。谢尔盖跟着我进了大厅,我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进去。楼上,母亲在等着我们。几个月来,这是她第一次化妆,衣服也像是新的。餐厅里放了一只插满鲜花的花瓶,咖啡桌上,一只碗里盛着黄色的葡萄,旁边那只里面是各式各样的俄国夹心糖,有卡拉库姆、棕松鼠、笨笨熊等各种牌子。见到谢尔盖,母亲感到由衷的高兴,脸上也焕发出平日里少见的光彩。见到母亲这样,我却不由得移开目光。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我也奇怪自己竟会这样。一直祈祷她能好起来,可是她太高兴的时候我又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尴尬。曾经有一次,我偶然从门外瞥见她在医生的诊室里脱衣服,当时也是这种感觉。和那次一样,本能驱使我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
母亲开着我们家绿色的庞蒂亚克带谢尔盖去那个好超市,然后又去商场。谢尔盖在商场给自己买了条蓝色的牛仔裤,给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也买了一条。他还在我的建议下买了几件有Polo标志的衬衣,那在当时非常流行。又不顾母068亲的反对,坚持给我和父亲每人也买了一件。
“贝拉奇卡,别忘了,你早上醒来,开着车去商店,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可是在里加,人们为了能排上队,都得排半天队。”
母亲不再和他争了。我心里暗自高兴,因为我和母亲都明白,要不是谢尔盖给我们买,我们不可能穿得起五十块钱的衬衣。
那天晚上父亲从会议中心回来时,非常激动。他见证了两项世界纪录的诞生,其中一项还是他认识的一个苏联运动员创造的。父亲因如此接近以前的生活而备感振奋,他见到了一些老朋友,他们都还认识他。他和格雷戈里·齐斯金待了几个小时,两个人还在酒店的房间里喝了几杯。格雷戈里告诉他迪纳摩的消息,哪些同事升职了,哪些退休了,大家怎么对付领导,运动员有哪些后起之秀等等。格雷戈里很骄傲,包括谢尔盖在内,国家队有三名举重运动员都来自里加迪纳摩。有个叫克鲁托夫的,和谢尔盖是同一重量级的运动员。这个年轻人将来会大有前途,过去这一年一直跟在谢尔盖后面拿银牌。能培养出金牌、银牌运动员,对格雷戈里在部里的形象大有好处。他已经听到传言,说要把他调到莫斯科,并在红军中给他一个永久的职位。
父亲送给我一张苏联国家队签名的海报做纪念,这让我惊喜万分。我们也给他一个惊喜:他的Polo衬衣。我和父亲在客厅里穿上新衣服,父亲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穿得着,他的衬衣已经够多了。我的衬衣也不少,可是这一刻我却觉得只有这一件。
除了海报,父亲还替我和母亲要了第二天比赛的门票。母亲虽然很想看谢尔盖比赛,但又觉得不能去,她担心没有时间做饭。我没什么任务,比赛正好是周六,不用上学,也没有作业,什么也不能阻挡我去看谢尔盖表演。
会议中心里,他们将几十块木板连接起来,搭成一个台子。台子一端摆着一张长桌,是裁判席,父亲和另外两位裁判一会儿就坐在那里。每位裁判正前方都有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由电线连接到显示板。盒子上有两个按钮,一个代表成功,一个代表失败。比赛开始前,父亲让我坐在他的座位上玩按钮。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格雷戈里·齐斯金向我们走过来。我对格雷戈里的印象很模糊,他不像谢尔盖那样经常去我们家。他是父亲的朋友和生意伙伴,但他举止中有一种东西,强调着他的职业身份而不是这个人,他看上去永远都是那么焦躁不安。
在父亲的提议下,格雷戈里同意带我去后台看看,运动员正在那里做赛前准备活动。父亲在里加时就经常带我去后台,他一直喜欢准备活动室里充满活力的气氛。但他现在是裁判,不能给别人留下一点有失公平或是行为欠妥的印象。父亲留下来看文件,我跟着格雷戈里穿过厚厚的幕布向准备活动室走去,那里传来一片运动员用力的嗨哈声和器械碰撞的咣啷声。
我站在准备活动室的一侧,看着人们忙碌的身影,忽然意识到这一幕似曾相识。活动室很大,和一般的高中体育馆差不多。有些领队和教练在指导运动员,不同队穿着不同颜色的阿迪达斯训练服,所以很容易区分开。一些运动员还穿着运动服,另一些只穿着一件紧身衣。活动室的一角,教练帮运动员把膝盖包好、系紧。另一个角落里,一些教练已经把按摩桌放好。活动室中间是一大片胶合板地面,几副杠铃已经整整齐齐摆在那里,还有专门拿白垩粉的人。看着运动员把白垩粉擦在手上、胳膊上、肩上,我已经迷上这项运动了。能用这么好的白垩粉块,足以让人想成为举重运动员。
格雷戈里还有重要的事要办,他给我一个塑料的记者入场证,叫我不要惹事,说我可以待在这儿,多久都可以,只要没人赶我就行。说完他向苏联代表团走去,在那边,谢尔
盖正在做伸展活动,他旁边是一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年轻运动员。每个角落里都传来运动员用力的声音,金属相撞或金属碰撞木头的声音。我到处走来走去,没人注意我。最后我在
活动室中间停下来,看运动员举起很重的东西,他们这是在为举起更重的东西做准备。
比赛要进行好几个小时。父亲帮我在前排留了座位,免得大人们挡住我的视线。谢尔盖所在重量级的比赛安排在后面,在他出场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父亲。父亲和另外两位裁判坐在台上,这一刻,我好像又看到国际举联证件上那个他了。
谢尔盖所在重量级的比赛是在下午进行的。形势很快就清楚了,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角逐:谢尔盖和克鲁托夫,那个黄头发白皮肤的运动员。第一轮他们就领先其他对手几公斤,接下来的一次次试举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先是谢尔盖在抓举中打破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接着克鲁托夫也追上来。杠铃几乎是他们体重的两倍,但两个人的动作都优美流畅,一次成功。
进入挺举环节,谢尔盖放弃第一轮,亲眼看着克鲁托夫072成功逼近并追上他创下的世界纪录。要赶上克鲁托夫,谢尔盖有三次试举机会。他试举时,克鲁托夫就在大厅一侧静静地等着。我把手塞到屁股底下,看着谢尔盖第一次试举失败。几分钟后,第二次试举也失败了,两次都是举到胸部就不行了。直到谢尔盖最后一次试举之前,我从来都没想过他会输。
但看着他往手上擦白垩粉的时候,我不但想到他有可能输,而且知道他输定了。看看周围的人,我感觉他们也都知道了。谢尔盖自己好像也有预感,时间快到了才走上台。他身后有一个大钟,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就是为了继续比下去,他也需要举出自己曾经的世界纪录。可是他没有,杠铃举过了头顶,但没有稳住。当包括父亲在内的三位裁判都亮起红灯,我感到一阵恶心。看到谢尔盖拥抱克鲁托夫,克鲁托夫又拥抱格雷戈里,早上吃的鸡蛋一股脑儿全涌到嘴里,但我又强咽了回去。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跟着父亲去找谢尔盖。格雷戈里、克鲁托夫和苏联队的其他队员站在一起,谢尔盖站在一旁。看到我们,他勉强笑了。父亲祝贺他,他拿起银牌,从脖子
上摘下来,放在我手里。他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瞧,银牌,不是金牌,但我想在大街上也不好找。”073
谢尔盖朝格雷戈里那边看去,他正一只胳膊搂着克鲁托夫。
“别忘了祝贺齐斯金同志,这对迪纳摩又是伟大的一天,又一次金银全包。忽然第一变成第二、第二变成第一,这对他能有什么不同?”
母亲在家精心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沙拉、冷罗宋汤、熏狗鱼、熏白鲑、烤小牛肉、茶、蛋糕,还自制了冰激凌做餐后甜点。她摆好五个人的餐具,拿出水晶玻璃杯和精美的瓷盘。我穿着崭新的Polo衬衣,父亲讲了好多我们来加拿大的路上在意大利时的趣闻。他拉着格雷戈里一起回忆他们健身班上的学生,有的还在里加,有的来了多伦多,有的还会从纽约和以色列写信给他。母亲向格雷戈里问起她原来的一些女朋友,尽管格雷戈里和母亲差不多是两辈人,但那些住在同一个犹太社区的人他也应该认识。连我都说了一些学校里的情况,告诉他们我的犹太同学都有些什么车。唯一没说话的就是谢尔盖了,他听着大家说,自己一直在喝酒。父亲在桌上放了一瓶伏特加,敬完酒后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喝了。一瓶快喝完的时候,他突然冲格雷戈里发火,指责他暗中对他搞阴谋。他知道格雷戈里计划向上级提议,让自己离开国家队。
“他想把我弄到牧场,苏联牧场,想让我一生灰头土脸地放牧。想把我弄回去,没门!除非你用子弹打穿我的脑袋。”
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是不停地喝。
“罗曼,你是对的,你迅速逃离了坟墓,现在可以期待过真正的生活了。可是我们能期待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格雷戈里·达维多维奇?你这个克格勃的王八蛋!”
又一杯酒下肚,谢尔盖的头开始向盘子上耷拉。父亲扶他站起来,他的胳膊搭在父亲肩上,踉踉跄跄地去了我房间,躺在单人床上。父亲关上门,回到饭桌旁。他疲惫地坐下,身子沉沉的,又回到平时的样子了。
母亲给大家倒茶的时候,格雷戈里承认谢尔盖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但这种事父亲也不是不知道,举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也就是五年,最多七年。退役后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安置,在迪纳摩安排个职位或者去海关任职,那里收入会很高。有可能做教练,也可能做官员,审阅文件。谢尔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得到这些,他可以保留那套三居室的公寓,车库也会给他,而且永远都不用为工资发愁。至于俄国正在变成一个大粪堆,那是另外一回事。格雷戈里说,父亲选择离开无疑是天才之举。他把饼干往茶里蘸了蘸,承认他本来也应该抓住机会离开的,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父亲说话前看了母亲一眼。
“别傻了,格里沙,我常想着回去呢。”
“你疯了吗?看看你现在的生活,到外面去转转,大街上的乞丐都穿着李维斯牛仔裤和阿迪达斯跑鞋。”
“十天里有八天,我担心自己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行了,罗曼,我认识你三十年了,没必要和我撒谎。”
“我说的是真的,每天都在挣扎。”
“你瞧,我又不是看不见:你的车、你的房、你是如何奋斗的。相信我,你最难的日子也比我最好的日子好过。”
我离开父母和格雷戈里,沿着门厅往卧室走。虽然闭着眼睛都知道每一步怎么走,我还是等了一会儿,让眼睛慢慢适应黑暗。谢尔盖在我的单人床上四仰八叉,脚刚刚从床边耷拉下来。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倾听他的呼吸,透过衣服琢磨他的身体。我又一次感到吃惊,他的身材竟是这么小。我弯下身,仔细端详他的脸。我不介意他躺在我的床上,当然要是他不走,我也不知道自己睡哪儿。他忽然睁开眼,吓了我一跳。
“嘿,伙计,看什么呢?”
他坐起来看着我,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和胳膊,试试我的体格。
“能做多少个俯卧撑?”
“二十五个。”
“才二十五个?”
“嗯。”
“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做不到五十个都说不过去。”
他爬下床跪在地上,拍拍旁边的地面。
“来,过来。”
我正犹豫呢,他一把拎起我的新衬衣。我感觉到衣服被扯破了,两颗扣子掉到了地上。
“我们现在就做,你和我,五十个。”开始我还跟得上,不一会儿谢尔盖就快起来。我尽量让自己不落后,害怕他会对我怎么样。但他只管做他的,自己数着,根本没理我。他做完,我也停下了。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我点点头。
谢尔盖看了看我的闹钟,已经十点多了。
“看,都这么晚了,你是不是该睡觉了?”
“没事,有时候我十一点才睡呢。”
“在里加的时候,你可是九点整。还记得那时候你多喜欢我哄你睡觉吗?”
“记得。”
“好像就在眼前呢。”
“嗯。”
“来,上床躺下。”
“没事,我不用现在就睡。”
“躺下,躺下。”
他的语气没得商量,我踢掉鞋子,钻进被窝。
“好。”
谢尔盖在我床边跪下,握紧木床架。
“舒服吗?”
“嗯。”
他的脸紧绷着,腿一用力,站了起来。我的床不太配合,刮到了墙,不过还是起来了。一开始床不停地摇晃,我紧紧抓住床边,后来就稳住了。谢尔盖看着我,一脸胜利的微笑。这时他身后的门开了,我能听出来,是父亲的脚步声。后面还有别人,是母亲和格雷戈里。
“喂,伙计,说,谁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我看了一眼谢尔盖身后的父亲,想看看他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母亲正要过来,被父亲拦住了。
“喂,伙计,谁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谢廖扎,谢廖扎·费德连科。”
“错了,伙计,那是昨天的答案。”
他哈哈大笑,转过头去看着格雷戈里。
“是不是,格雷戈里·达维多维奇?”
“放下他,你这蠢货。”
谢廖扎哼了一声,像是咳嗽,又像是笑。他小心翼翼地把床放下,自己也顺势瘫倒在地上。格雷戈里和父亲过去搀他,但格雷戈里伸手去抓他的胳膊时,被他啪地甩开了。
“你这浑蛋,别碰我!”
格雷戈里退了回去。父亲轻轻托住谢尔盖腋下,扶他站起来。他没有反抗,两手搭在父亲肩上。
“罗曼,你是唯一关心我的人,可是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父亲架着谢尔盖,踉踉跄跄向门厅走去。我从床上下来,站在房间门口。格雷戈里跟着父亲和谢尔盖穿过门厅向前门走去。母亲过来站在我旁边。
父亲说开车送他们,要不就叫出租车。
格雷戈里摇了摇头,脸上是惯有的苏联式笑容:
“哪儿需要呢?你忘了吗?楼下总有车等着。”
谢尔盖还是紧抓着父亲不放,任由父亲架着,穿过走廊,走进电梯。格雷戈里和母亲说再见,母亲把门关上。我跑到卧室窗边等着,楼下的停车场里,有个人在一辆深色的轿车外抽烟。电梯下得比平时稍稍慢了一些,他们终于出现在停车场,谢尔盖还靠在父亲肩膀上,格雷戈里跟在他们后面。那个抽烟的人打开后车门,父亲轻轻把谢尔盖放进去。父亲和格雷戈里握手,也和那个人握手。父亲往回走时,那个人打开驾驶座那边的车门。那一刻,车里的光打在他肿肿的脸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