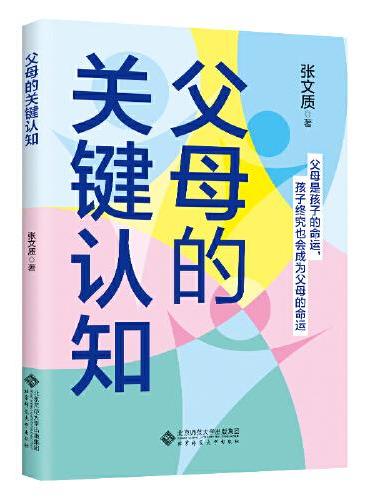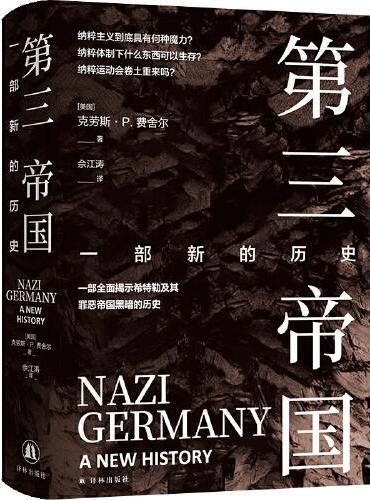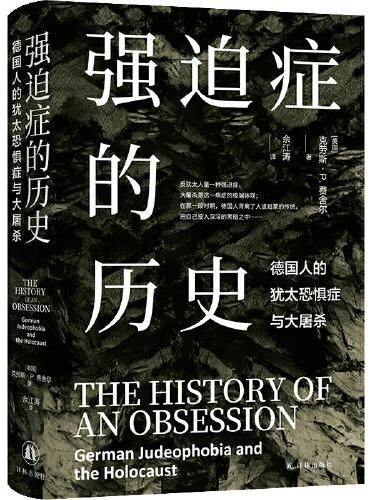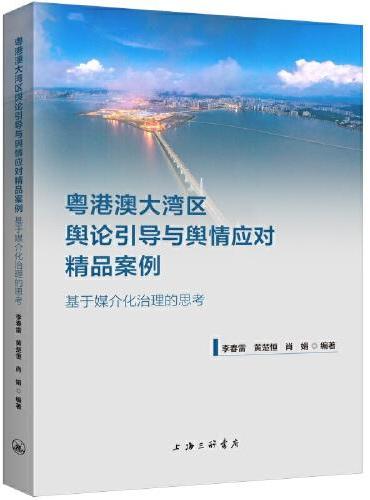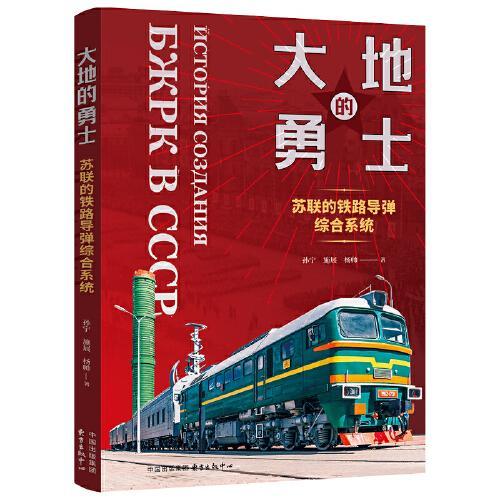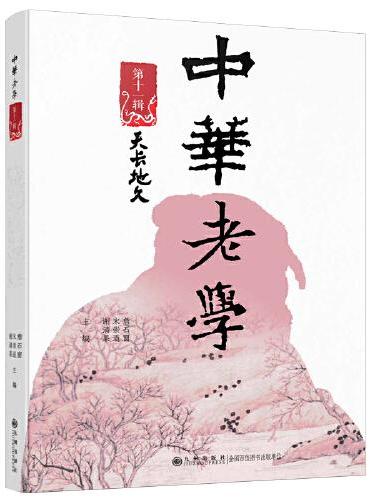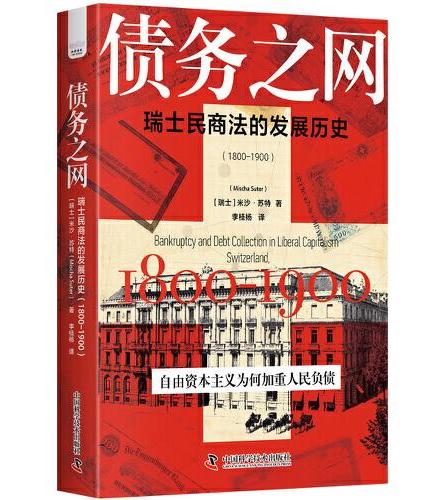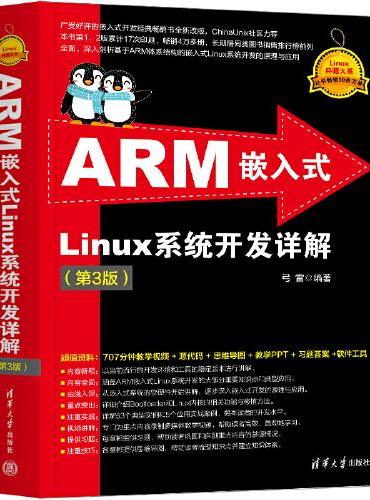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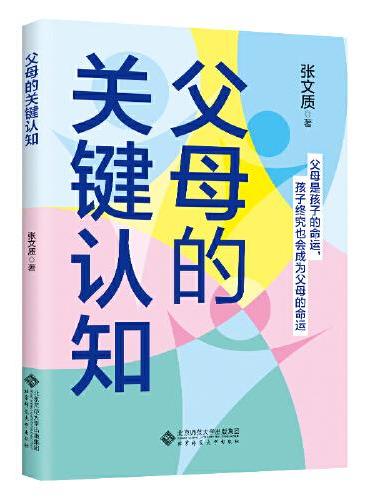
《
父母的关键认知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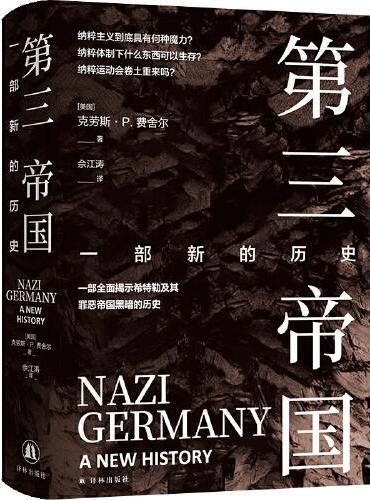
《
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纳粹主义具有何种魔力?纳粹运动会卷土重来吗?一部全面揭示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黑暗的历史)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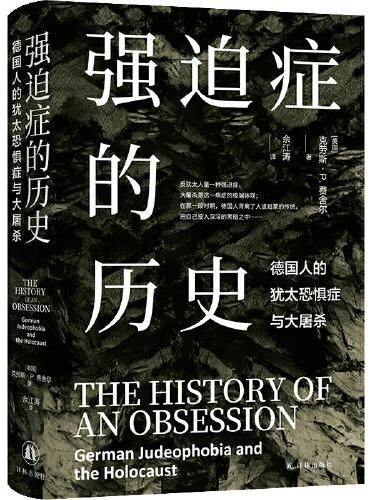
《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德国历史上的反犹文化源自哪里?如何演化为战争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德国历史研究专家克劳斯·费舍尔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典范之作)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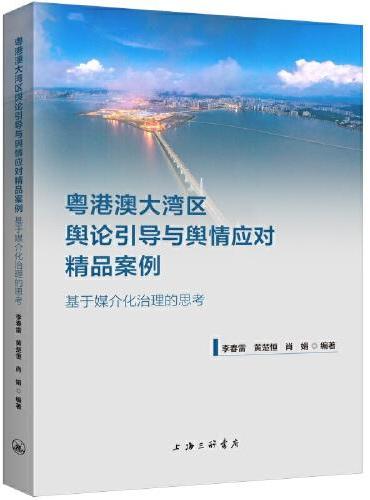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精品案例:基于媒介化治理的思考
》
售價:NT$
4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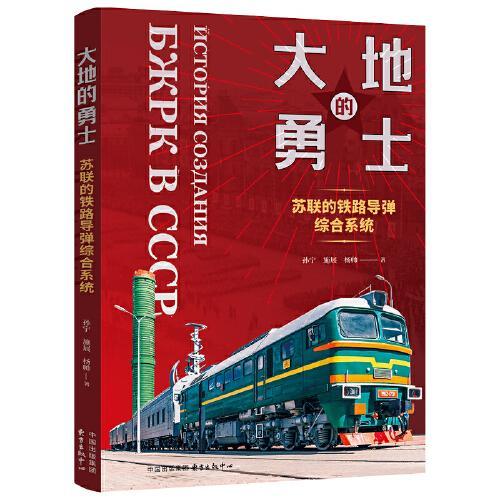
《
大地的勇士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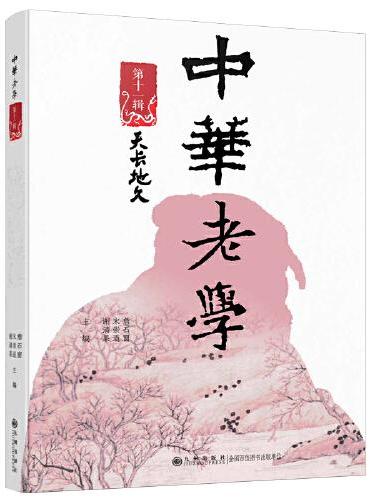
《
中华老学·第十一辑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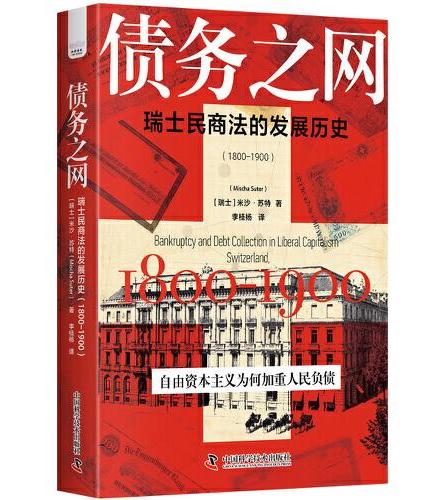
《
债务之网:瑞士民商法的发展历史(1800-1900)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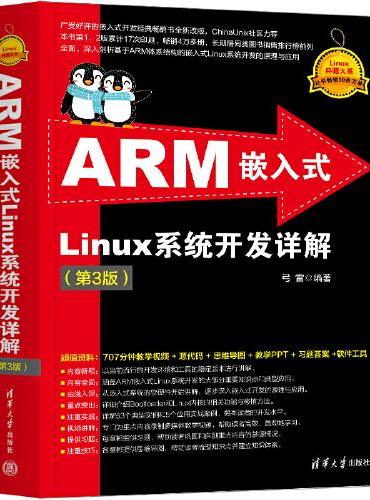
《
ARM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详解(第3版)
》
售價:NT$
595.0
|
| 編輯推薦: |
时光流逝,既会揭开鲜为人知的秘密,也会埋葬不为人知的事实。
口述历史,对日诉讼二十年。
对日索赔的纪实力作,让更多人了解“慰安妇”受害者、被強掳赴日劳工的历史真相,为战争受害者索回失落的尊严。
|
| 內容簡介: |
《索赔:亲历中国“慰安妇”及被强掳赴日劳工诉讼》系康健律师参与对日索赔近二十年诉讼历程的口述纪实。
全书分为上下篇,分别记述了康健律师从最初参与对日索赔案件的起因,对原“慰安妇”受害者和被强掳赴日劳工的实地调查、取证,记录了部分原“慰安妇”受害者和劳工当年受害的事实;通过作者亲历的多次赴日诉讼的过程与细节,以及与日本政府、有关日本公司在法庭内外斗争的经过,讲述了对日索赔案件中的种种艰辛;直至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有关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介绍了日本律师、日本民间支援团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团体在帮助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驳斥了日本政府和日本有关公司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为战争受害者索回正义与尊严。
|
| 關於作者: |
康健,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工作小组副主任,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执行主任,参与对日索赔案件最多的中方律师。
刘荣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文学所、历史所工作。
|
| 目錄:
|
上篇 原“慰安妇”受害者索赔诉讼
1 一个回应,走上索赔之路
2 山西“慰安妇”调查
3 海南“慰安妇”调查
4 中国“慰安妇”诉讼概况
5 与受害者第一次到日本出庭
6 数件“慰安妇”诉讼
7 “侵害女性的国际战犯法庭”审判
8 她们需要关怀
9 事实不容篡改
10 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
下篇 掳日劳工索赔诉讼
1 劳工索赔案的介入
2 被强掳赴日劳工的概况
3 劳工调查
4 出庭
5 与日本公司的交涉
6 与日本国会议员的沟通
7 八十人赴日本
8 诉讼中的成败
9 已有的和解是苦涩的和解
10 在中国国内起诉
索赔中的朋友们
未尽之言
|
| 內容試閱:
|
一个回应,走上索赔之路
1995 年9 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方面的会议牵头单位之一是全国妇联。为了更好地参加大会,全国妇联在会前几次召集参会的代表做会前的准备。根据会议分工,参会的律师主要是在会上谈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在会议开始前的一次准备会上,我们做了分工,我的发言主要是谈在离婚后对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执业律师有我和黄丹涵两位,另外还有我们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周纳新以及重庆律师协会的一位女性会长。我们四位是律师界的正式代表,其他也有旁听的律师,但不发言。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准备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一条纪律:会议期间可能有人要提出“慰安妇”问题(在当时,认为“慰安妇”是军妓),对此要求不做表态,不介入。在这个准备会上,我是第一次听说了“慰安妇”这个词,从此这个词也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为中国大陆“慰安妇”和被强掳赴日中国劳工的对日索赔倾注了大量心血。9 月份,世妇会正式召开。我们作为NGO(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大会,当时NGO 的主会场是在怀柔。世界各国的妇女代表都来了,在会场上发表各自的见解,气氛非常活跃。希拉里也参加了会议,她谈到了妇女权益的保护,但没有涉及“慰安妇”的问题。当然,会场中也贴出了韩国“慰安妇”问题的宣传资料,但由于事前不予介入的要求,我对这些也就没有更多的关注。会议期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了一个中日两国女律师代表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在全国律协办公地点附近举行的。会议由全国律协秘书长吴明德、国际部的宋芮作为召集人。中方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位女律师,周纳新会长也参加了;记得日本女律师参会的大概也是有五六位,与我方参会人员数量基本对等。翻译由中国法学会派人担任。会议确定的议题是在婚姻家庭中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我们的发言都是围绕着这个议题进行的。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在快结束的时候,参会的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突然提出了会议议题之外的话题,她说:日本有一些律师想帮着中国的“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但是作为外国律师在中国做有关调查十分不便,希望中国律师给予支持。她的话题一提出,中方代表相互看了一下,接着就是几十秒的停顿,这短暂的几十秒却使人感觉时间很长,没有任何人发言。我们都在认真遵守事先提出的工作纪律,一时不知怎样来回应日本律师的期望。停顿中我也在思考, 当时只是感觉到:对于一个法律问题,所有人都不回应是不合适的,最起码是不礼貌的。我就硬着头皮说:作为一个诉讼案件,我们中方律师给予协助不是不可以。我当时回应她主要考虑的是基本的道理和礼貌。日本律师听了后相互看了看,表情上都非常高兴。会后在送别日本律师时,大森典子律师特意到我面前,一边握手一边不断地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以为她是客气,也就礼节性地做了回应。会后, 我也向全国律协吴秘书长询问,刚才在会上这样表态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关系,说了也就说了。这次会议结束后没两天,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也结束了。我和大森典子律师也没有再见面,也没有联系。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多月后,大森律师按照我们交换名片上的信息给我发了个传真,大概意思是想专程到北京来和我商谈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看了传真,我感觉日本律师对这件事是认真的。我向北京律师协会会长周纳新做了汇报。周会长表态说,先谈一谈吧,接触一下也可以。这样,我就给大森典子律师做了回复,约她在10 月底左右到北京谈。
在这期间,我查找了一些关于“慰安妇”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查看,我初步感觉到所谓的“慰安妇”不是像我们参加世妇会时认知的军妓那样简单,二战中日军占领国中的“慰安妇”都是被日军强迫的受害者。这也是我对“慰安妇”的最初认识。
大森律师来了后,就在我们的事务所商谈(当时,我们的事务所叫北京市中元律师事务所,2000 年8 月我们所分立为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谈话中我也问了一下这个诉讼的起因以及起诉到了什么程度,大森律师介绍了一下有关情况,并告诉我,起诉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调查还不全面。我也向她询问了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日本律师,为什么你们要起诉日本政府?”大森律师说,主要是出于对人权保护的考虑,这样的问题应该予以解决。我接着提出要看看他们初步调查后的有关材料以及起诉书,她答应了。谈完后,大森律师提出要和我照张相。作为来访的律师留个纪念,这太平常了,我爽快答应,于是两人在书柜前留了张合影。
一年多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合作经历,大森律师告诉了我这张合影的“秘密”。在中日女律师座谈会上,虽然我回应了她的希望,但是没有照相。在初次谈话后,她要把我的形象带回去,让其他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的日本律师看看康健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日本律师看完后都觉得康健律师很可信。我笑了,大森律师是把我带回去让日本律师相了个面,但我也真实地感到,一年多的合作经历使他们感到我是可信任的,不然她也不会把这样一个“秘密”坦诚地告诉我。
与大森律师谈完之后,我向律协的周会长做了汇报。周会长说行,就先这样吧。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此事能真正进行。
又过了一段时间,约12 月份,大森律师发来传真:作为诉讼的律师团团长和干事长,他们一行五六位律师准备到北京和我做进一步商谈。作为律师的职业敏感,我知道到了双方都下决心的时候了。考虑到当时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时有关方面要求我们对“慰安妇”问题不介入,我又找周会长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若拒绝日本律师的提议,好像没有任何道理,中国律师在这之前也与外国律师有一些协作。对这样一起诉讼案件的协助都拒绝,说不过去;这也是一个人权保护的问题,人家在帮我们中国人做,我们自己还不做,人权保护从何谈起?周纳新会长说:“行,你就先做吧。有什么事及时汇报。”过后想起来,周会长还是很有眼光、很有魄力的,她这样的表态在那个时候也是顶着风险的。
这样,我就答应了大森律师与他们再次会谈。大概到了12 月中下旬的时候,他们来了三男三女六位律师。三位男律师分别是尾山宏、小野寺利孝、渡边春己。渡边律师当时参与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及无区别轰炸案件;三位女律师是野上佳世子、伊藤美莎子、大森典子。大森律师是“慰安妇”案件律师团的团长。交谈中我了解到,日本律师为了中国战争中受害人员的索赔,组成了“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辩护团”,尾山宏律师是这个律师团的团长,小野寺律师是律师团的干事长,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秘书长。后来尾山宏律师还作为唯一的外国人被评为我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03 年度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会谈是在北京贵友饭店进行的。这六位律师集体来和我谈,也让我感觉到他们对我参加这件事的认真态度和关注的分量。既然他们这样重视,我也就直率地问:“作为
支付了我们事务所几百元人民币的咨询费。当时我作为正常的咨询,公事公办,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在后来与这些日本律师的接触中,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所做的工作,所投入的精力,以及他们的良知深深打动了我,这几百元钱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我懊悔当时真不该收他们的钱,但要退回也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只有在后来的工作中加倍努力,在他们来中国时尽自己所能地接待与协助。
这次会谈主要是小野寺律师和渡边律师主谈,其他几位律师基本没有讲话,但都是认真地在做着笔记。会后在共进晚餐时,尾山宏律师谈起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为什么放弃战争赔偿?他感到不可理解。他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对于他谈的问题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想到一个日本律师对《中日联合声明》这么关注。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当时我还真没有认真研读过《中日联合声明》,具体的条款就更记不清楚了,但放弃了战争赔偿,还是有印象的。从律师的角度想,当时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的大局出发,放弃了赔偿。但我不认为是全面放弃,作为受害者个人还是有权主张的,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我就把自己对《中日联合声明》的初步理解向尾山宏律师做了回答。他说他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还谈到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些消极的做法,我当时感觉他像一位政治家。
回家后我认真研读了《中日联合声明》,该声明第五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我放心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到放弃中国国民个人有关战争赔偿的权利。后来我也听说,在这一年(1995 年)3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时,对一位代表的提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我的理解是对的。这次交谈后,我们确定了合作关系,日本律师给我发来了委托协议。我也就正式走上了这漫长的索赔历程。
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到,一个回应,竟影响了我此后二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也影响了我身边许许多多的人们。
日本律师,你们为什么要代理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你们有没有感到压力,这样做目的是什么?”谈话就以这样直率的问话开始了。当时小野寺律师是主谈,在这次谈话时,他的年纪也就五十多岁,应该是在二战后期出生的。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小野寺律师慢慢地从头道来。1994 年的时候,他带领一个司法考察团访问南京和北京,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南京时,他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令他十分震惊!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在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从来没有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事。
在北京,他又参观了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由于这次到中国是司法制度考察,对南京和北京两个纪念馆的参观只是匆匆掠过。就是这匆匆一看也使他非常吃惊。当时也有中国的民间人士找到他谈到劳工问题,也听到了“慰安妇”问题。那时韩国“慰安妇”已经在日本起诉了,但没有听说中国“慰安妇”的事。这次到中国后接触到这么多中国人在二战中的受害问题,对他触动非常大。回到日本后,他又专程到中国,再次到了抗日战争纪念馆,详细地看了展览,跟一些受害者见了面,内心再次引起了震动。他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些事情,日本人不会在亚洲得到其他国家国民的信任。许多日本人对这段历史都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想通过诉讼,把这段历史告诉日本国民。小野寺律师说:“作为律师,保护人权是应该的。”
小野寺律师的介绍,也深深触动了我。作为中国人,这些事情听来并不奇怪,日本鬼子到中国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我的头脑中,日本鬼子就是强盗、野兽。小野寺律师所言我觉得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我也十分不理解,像他们这样年纪的人怎么连这些事都不清楚,而且还那么吃惊?那日本的年轻人呢?他们能知道多少呢?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的态度,是造成日本在世人面前对历史问题有诸多奇怪表现的原因。
在谈到合作时,他们告诉我,代理中国受害者索赔这件事他们自己是免费做的,问我可不可以免费做这件事。我当时没有任何迟疑就说:“当然了!我们中国律师经常有法律援助(不收费)案件,对生活比较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正常的。”我当时也想:这件事我就是协助调查,在日本出庭也都是日本律师,外国律师不可能以律师的名义出庭,也就做一次调查就完了。不收费,没有什么奇怪。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几个律师相互看了看,眼神中似乎闪烁着不理解。也是在接触了一年多以后,小野寺律师、大森律师跟我说,在找我之前,他们也找过中国其他律师,那些律师提出要他们先付十万元代理费,他们觉得很难接受,这就给他们形成了一个看法——中国律师都是奔着钱去的,直到我爽快应允,他们才发现原来中国也有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我也就此明白了当时他们那不解的眼光,其实,我觉得他们对中国律师还是不了解,事情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中国律师也经常做法律援助,我分析之前要收代理费的
律师也可能是对他们的动机不了解,先以十万元预付让他们知难而退。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双方都是谨慎坦率地交换意见,他们也问我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我的回答是:既然要提起诉讼,又是中国的受害者,你们调查不方便,我作为中国律师帮助中国受害者,是责无旁贷的,没什么奇怪。他们一看我这样痛快地答应了,非常高兴。
渡边春己律师马上又向我提出了这个话题之外的问题,是关于细菌战的。那时他们已就731 部队在中国开展细菌战代理中国被活体实验受害者遗属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渡边律师还问我有关溥仪《我的后半生》在日本出书版权问题的律师咨询收费标准。我答复他们按涉外对待每小时200 美元。他又接着问:“那我咨询你这个问题要多少钱?”我回答:“按中国国内对待也不能低于每小时几百元人民币。”渡边律师便随即咨询了我国有关版权保护的规定,作为正常的律师业务,我向他做了说明,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