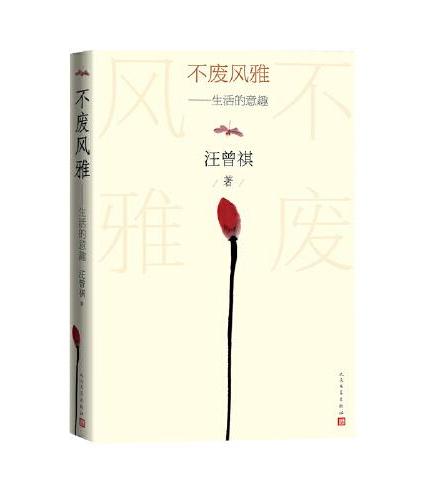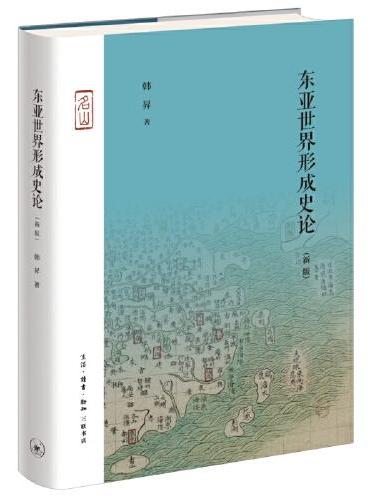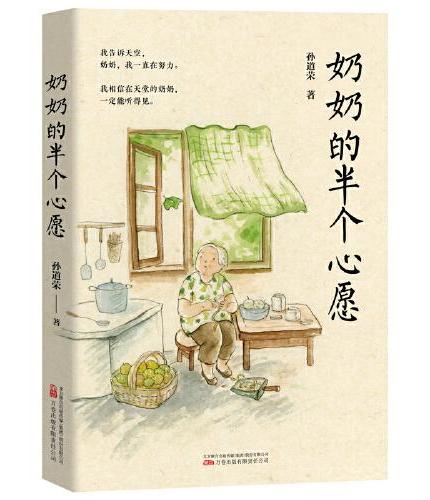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9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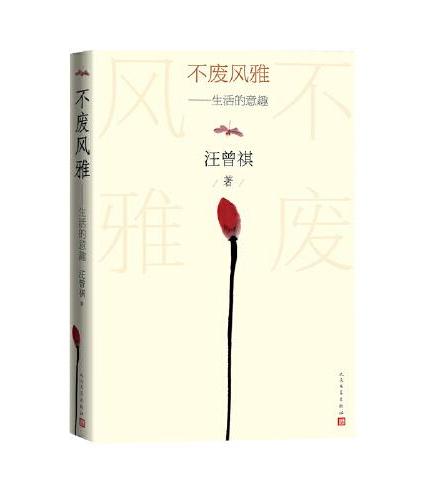
《
不废风雅 生活的意趣(汪曾祺风雅意趣妙文)
》
售價:NT$
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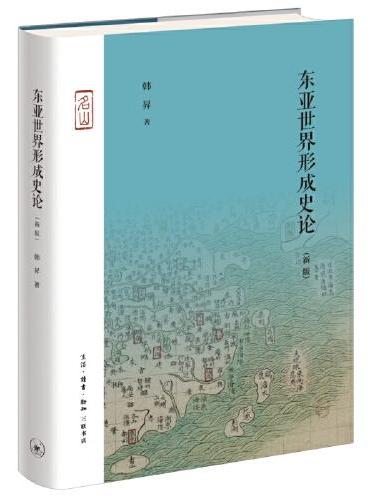
《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新版)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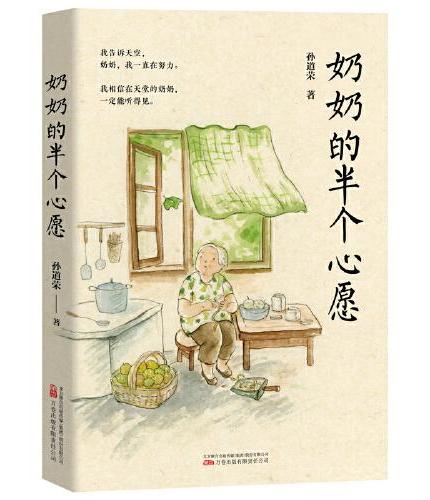
《
奶奶的半个心愿 “课本里的作家” 中考热点作家孙道荣2024年全新散文集
》
售價:NT$
19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 編輯推薦: |
▲贺雪峰、王小强、潘毅、梁鸿、祝东力、老田等知名学者诚挚推荐
▲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
▲一个基层媒体人的十年乡土观察实录。
▲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民族志。
▲同名纪录片即将上映。
|
| 內容簡介: |
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民族志。
一个基层媒体人的十年乡土观察实录。
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发生着裂变。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记录数十年来崖边人的命运史,打开乡愁之结,探讨和寻找还乡之途。
|
| 關於作者: |
|
阎海军,一九八二年出生于甘肃通渭。媒体人,独立纪录片导演,青年学者。现供职于某电视台。长期从事“三农”问题调查。
|
| 目錄:
|
引子:在崖边 ……1
困在田野上的人 ……17
秩序的裂变 ……45
困局 ……75
失落的教条 ……109
逃离的可能 ……135
迁徙 ……145
沦陷的土地 ……167
乡土的黄昏 ……241
尾声:何处还乡 ……285
|
| 內容試閱:
|
引子:在崖边
“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2008年清明节,我回到崖边时,80多岁的厉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十字路口给我这样感叹。
厉敬明没有经历过1929年的饥荒,但他的父母反复给他讲过1929年的灾难。厉敬明经历过1960年的饥荒,他像自己的父母那样,逢人就要不厌其烦、不由自主地讲述挨饿的痛苦。这既是传承历史,更是在告诫后人要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厉敬明对1929年和1960年的恐惧是整个村庄所有人共有的伤痕。
2008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1929年和1960年的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但当我听到厉敬明将村庄缺乏生机的现实生活与饿死人的历史时期相提并论,我震惊了。这促使我产生了认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乡土中国之忧的想法。返城后,厉敬明的话反复在我心里激荡着,它好似催促我进入认真思考村庄课堂的铃声。
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我的故乡——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
从310国道一路向西,在马营左拐翻山,一条县级柏油马路像一根动脉血管,在山包上蜿蜒盘旋。公路叫马(营)陇(西)公路。每隔三五百米,路边的山坳处就有一个岘口。岘口是公路上的驿站,把山湾里无数个灰蒙蒙、静悄悄的村庄连缀了起来。马陇公路35公里处的岘口叫井湾岘。从这里远眺,三公里开外的一座山格外显眼,因为山上有一个高大的古堡。山叫岳家山,堡叫岳家堡。崖边就在堡子那边的山脚下。
崖边村躺在岳家山的西面,坐东朝西,正视着前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渭河不起眼的小支流,从1990年代后期,已几近干涸。这预示着陇中黄土高原的旱情在不断加重。小河对岸是陇西县的村庄,崖边处在通渭县的西南边陲。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
童年的记忆中,十字路口一年四季总是有人活动。常年干旱,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与生产劳作的艰苦相比,活下来的人还有温暖人心的生存仪式,还有经久传承的道德操行。嵌入我童年记忆的内容,除了耕作大地的辛劳和贫瘠外,村庄还有和谐有度的生活内容:老人安享晚年,中青年躬耕农事,少年成群结队嬉戏打闹,村庄鸡鸣犬吠,人声接耳;进入年关岁尾,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上演,村庄会更加热闹。
离开故乡很久后,当我回到崖边时,十字路口已经很难碰到人,整个村庄死一般沉寂。夏天,绿意盎然的村庄缺少了人的踪迹而显得阴沉;冬天,萧杀的村庄因缺少了人而更显孤寂。
进城以来,故乡一直是令人惆怅的符号。在城市里怀念故乡,希望回到故乡。真正回到故乡时,故乡的贫瘠又会让人非常失落。与厉敬明在2008年的对话,让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惆怅者。
2008年之后,厉敬明再也无法出现在崖边十字路口,他病倒了。
十字路口没了厉敬明的守候,更加寂静。
经过十字路口进入我的家,我能碰见的第一个人经常是厉军红的母亲。农业合作社时期的马场就在十字路口,马场的拐角处建有一座高房,十字路口依着高房成型。高房的窗户正对入村道路,高房如同瞭望所。包产到户时,这个高房分给了厉军红家。所以,所有进入村庄的人总是被厉军红母亲第一时间发现。
“走,到我家去转转。”她每次都会这样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每次她邀请我,我都会问一句:“军红在不在家?”
她总是回答:“不在,打工挣钱去了。”
几乎每次还乡厉军红都不在家。厉军红和我同龄,要是他在家,我兴许会去他家看看。但想到厉军红不在家,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厉军红母亲的邀请。
2013年初冬,我回到崖边时,再次碰到了厉军红的母亲。她背着一捆柴,行走在村里新近硬化的村道上,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她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她照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无数次拒绝了她的邀请,这一次我跟着她到了她的家里。院落杂乱,鸡粪、柴草满地皆是。主屋里,粗糙的木桌上堆着厚厚的尘土。厉军红父亲的遗像格外显眼。北面的房屋是厉军红的婚房,大衣柜上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墙上还留着残缺的“喜”字。衣被、装饰画零星的红色早已被灰尘覆盖。显然,新婚时布置环境所憧憬的浪漫和美好早已被婚后的现实压力击得粉碎。
厉军红的母亲让我坐定,她翻箱倒柜用污浊的瓷盘端来了一片干硬如瓦片的馍馍,不停地招呼我吃。我象征性地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嚼起来有点费劲。
“军红去哪里打工?”
“不一定,有一阵子在兰州,有一阵子跑包头。”她一边回答一边从桌角拿起了一块黑乌乌的抹布。
“为啥要把老婆孩子也带走,那不是很有压力么?”
“人家媳妇子不愿意在家里待,两个人出去干活能多挣一点钱,家里的农活给我一个扔下,孩子带走了还好,要不然都得我管。”
“60多岁了,还能干动活吗?”
“干不动也得干,不能坐着等死。”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
1990年代,厉军红的父亲在什川乡集市上卖木料,他算是崖边为数不多的生意人。他常年做生意,家里的农活基本靠老婆孩子维持。在崖边,厉军红家的庄稼由于作务不好,常年长势欠佳。厉军红的父亲常年做生意,似乎也没能改变家里的面貌。他家和所有人一样,住着土房子,过着苦日子。
我和厉军红小时候一起长大,关系还算不错。他上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被开除,后来便去打工了,我和他便少了来往。2003年,他突患精神疾病,逢人便打。
由于他父亲做生意的缘故,小时候他手头的零花钱比较充足,花钱也大手大脚。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他用喝剩的白酒洗手,这个举动在贫瘠的陇中农民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但厉军红对此不以为然。厉军红花钱不受节制的习性在他走向成人之后,仅靠打工再难以为继。他是典型的“能力无法满足欲望”的新生代打工者,他的精神失常也多半源自于此。
厉军红的精神疾病康复后,不大和人来往了。2005年,厉军红的父亲身患气管炎离世,随后厉军红娶妻生子。
厉军红的母亲说,农忙时厉军红会回到崖边,将庄稼种好,然后自己去城里打工。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像个独鬼。”
“晚上一个人住,怕不怕?”
“习惯了,有时候还是害怕。”
崖边人迷信鬼神,所谓的害怕也就是怕传说中的鬼魂。
与厉军红母亲相比,出生于1940年代的宋福禄要潇洒得多,因为他的儿子宋辉在河北打工收入较好,他基本放弃了土地,不再操心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宋福禄的儿子宋辉1982年出生,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宋辉从16岁开始就在河北石家庄打工,结婚后妻子也被带到石家庄。从2007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母亲带到石家庄帮自己带孩子,但父亲依然留在家中。宋福禄一个人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把绝大多数土地都租给了村里有劳力的人,剩下离村较远、坡度过大的土地则撂荒。在崖边村,做饭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一般都不会做饭。但宋福禄一个人还要自己做饭,生一顿熟一顿,反正只能将就着吃。最要命的是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无人照应。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福禄对我说:“自己没办法,儿子宋辉也没有办法。儿子回家吧,外面的钱就挣不到了;跟着儿子到外面吧,儿子的压力会特别大。”
崖边人都以为宋辉可以留在城里,可以在城里把母亲养老送终。但2014年,宋辉的母亲得了重病,花了很多钱,依然返回了崖边。可见,宋辉依靠打工将父母接到城里是不现实的。很多打工的人,很难立足城市,一旦城里的工作有变故,崖边将是最后的老巢。故乡无疑是每一个农民最可靠的家园。
在崖边,1982年之前出生的人一般都有较多的兄弟,老大外出之后,还有老二老三等可以照顾老人。但1982年以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农村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换言之,一个农村家庭顶多有两个儿子,基本杜绝了一户弟兄好几个的情况。青壮年外出,老人留守家中都存在老无所养的问题。崖边81户人当中,很多老人和厉军红的母亲以及宋福禄一样,身边没有儿孙的陪伴,独自留守在家中,既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操持家中的几亩薄田。在中国,农民是无法退休的职业,与那些标榜自己鞠躬尽瘁的人相比,农民才是真正为职业而鞠躬尽瘁的人,很多农民会一直劳动直到死在岗位上。
全国老龄办测算,“十二五”时期,我国有4000万农村留守老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孙绕膝是富贵的象征。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曾是国人向往的理想状态。但外出打工的大迁徙开始后,每个家庭都不能人口完备,完整的家庭组合已经解体。
由于父亲去世早,厉军红是崖边80后青年中唯一沾染农事的人。崖边只有70后的壮年才会在家庭中选择“半工半耕”“子工父耕”的办法维持生活,而绝大多数80后青年都是全年在外打工,90后青年则基本不懂务农。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有的只身一人外出,有的带着妻子和孩子,有的只带着妻子而把孩子托付给父母亲。
留守妇女被称作“体制性寡妇”。据全国妇联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超过5000万人。“体制性寡妇”的诞生造成了农村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情感问题的增多引出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婚外情、离婚率增高等。
崖边张纪纲的老婆就因为丈夫常年外出,和外村男人产生了感情。张纪纲与妻子差点闹离婚,但为了孩子,张纪纲极力挽留了婚姻。不过张纪纲的遭遇几乎成了崖边人诟病的一大污点。由于老婆出轨的原因,张纪纲放弃了打工,但夫妻感情名存实亡,常年争吵不断,对孩子的成长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014年冬,在外打工的厉小虎回家,怀疑妻子和别人有婚外情,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喝了一瓶农药,幸好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随同老公一起外出,一些儿童只能与老弱病残的空巢老人厮守在一起。
佟富是崖边颇为成功的打工者,他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自学了贴瓷砖的手艺,坚持打工十余年,勤俭节约,有了丰厚的积蓄。2009年我见到佟富时,他正在崖边修盖房屋。此刻,他心中的家园显然在崖边。但到2013年时,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佟富已在银川购买了商品房,2009年新修的房屋也一直没有投用。尽管落户宁夏已成事实,佟富已将母亲接到银川,但佟富的儿子和佟富的父亲还是留守在崖边。
佟富的儿子在一本写字本上写阿拉伯数字,横不平竖不直,数字7总要擦掉两遍才能写好,一页纸从1写到9,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佟富的父亲佟进贤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用余光监督着孙子的作业工程。
“两个儿子都进城打工,挣得还行,我现在基本不种田了。”
正说着,佟进贤敏锐地发现旁边的孙子将9写得像个羽毛球拍子:“不好好写,今晚不要吃饭。”佟进贤厉声喝道。
佟进贤是文盲,除了1到10的阿拉伯数字比较熟悉外,他认识的汉字并不多。辅导孙子的作业显然是心有余力不足,好在接受我访问的2012年,佟进贤的孙子只在上小学一年级,写阿拉伯数字佟进贤显然还能应付得来,之后的学业再由文盲爷爷督导进行,肯定不大理想。
佟进贤出门取东西一刻钟时间,我和佟进贤8岁的孙子交流了一阵,孩子很腼腆,不大言语。问三句才能回答一句。我问他爱爷爷还是爱爸爸,他说爱爸爸,爷爷老是骂他。我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他不说话,但眼中已飘起了泪花。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全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因亲情缺失,留守儿童存在孤独、失落、焦虑等心理不健康因素,有的还会发展成社会偏差人员。留守儿童的学习由于缺乏父母亲的监督和指导,跟不上趟。
在崖边,每一个家庭的留守儿童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尽管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湖南卫视《变形记》节目中,贵州省一个叫梁训的留守儿童与四川成都的一位公子哥互换生活环境。梁训十四岁,一个人留守在家,自己背水、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睡觉,艰辛、孤独可想而知。面对镜头,他说自己通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害怕,他便用唱歌的方式驱散孤独和恐惧,唱着唱着就睡着了。他在自己完成一切生活学习的任务后,还要为家里喂养一头小猪。他年初送走爸爸妈妈时,小猪伴随他一起成长,到年关爸爸妈妈回家时,他在保持自己成长的同时,还要将小猪喂成大肥猪,以贴补家用。
梁训在成都新爸爸家里吃了一个鸡蛋,引发胃疼。医生说他平时吃得实在太差了,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好太多,连一个鸡蛋的营养都补充过剩。医生被他的经历感动,在他离开之前硬塞了几百块钱,让他买点好的吃。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栏目,通过城乡少年互换角色,不仅能影响参与节目的孩子们的成长,更能让全社会关注到城乡生存环境的巨大差距,关注到两极分化,关注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的问题,关注到人到底该如何全面发展的问题,确实是一档好节目。
2010年的冬天,崖边老人厉敬明去世。我回到崖边正好赶上他的葬礼。
婚丧嫁娶是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村庄的传统是:每出生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生;每迎娶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贺;每死亡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送别。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的几户人发展到如今的80多户人。
我记忆中,崖边所有的葬礼都是倾村出动,但厉敬明的葬礼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妇女儿童都在积极帮忙。呜咽的唢呐伴随着稀疏的送葬队伍,和我记忆中人们成群结对、熙熙攘攘的崖边葬礼相比,这场景更显凄凉。
看着包裹厉敬明身躯的棺材渐渐被乡亲们用黄土埋没,厉敬明一边捋着苍白胡须,一边给我感叹“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的神情再次浮现。厉敬明的葬礼直接检验了厉敬明的论断。
埋葬完厉敬明的第二天,村民厉永强来我家串门,他和阎海平继续谈论昨天的葬礼。
“到底是厉敬明的棺材太重,还是昨天抬棺材的人太少了,真把人累死了?”厉永强引出了话题。
“棺材都差不多,死老汉临死前瘦干了没重量,关键是人太少。以前咱们埋一个老汉都是十几个人换着抬,昨天咱们就八个人一共抬了十里路,还有上坡路,肯定感觉吃力。”阎海平分析说。
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像厉永强和阎海平这样的中年人成了包括葬礼在内的崖边集体劳动、公益劳动中的主力。他俩为人诚恳,常年难以外出,几乎村里的所有公益性劳动都会积极参与。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托人花钱只要能晋级士官就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部队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而出现的。农村被抽空了新鲜力量,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结婚时都在城市里举办婚礼,这样一则避免计划生育的追究,二则避免回村办婚礼的麻烦。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每一个老人死去,都要举行葬礼,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现在真的成了麻烦,年轻人走光了,死一个老汉埋的时候把人就挣死了。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了,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平继续感叹道。
和厉军红一样大的厉斌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自从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没见过面。2010年我专门去他家看看,只见大门紧锁,院落荒草凄凄。附近的邻居说厉斌的父亲得怪病死了,厉斌这些年从来没回来过。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给我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这是城市化的“功劳”。这十年时间崖边也更加萧条和凋敝了,但没有衰亡。它由厉敬明、宋福禄一样的老人和阎海平、厉永强一样的中年人守护着。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