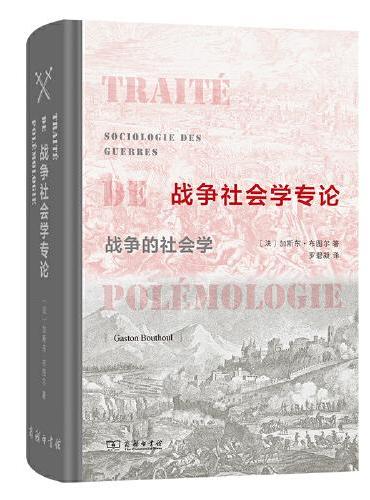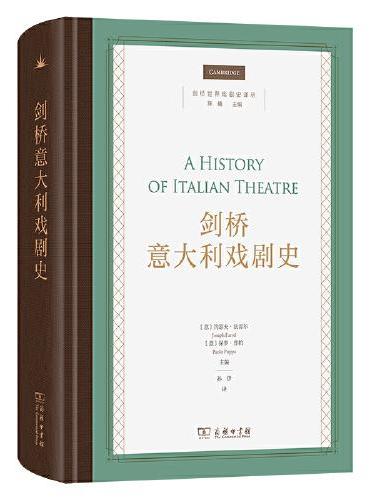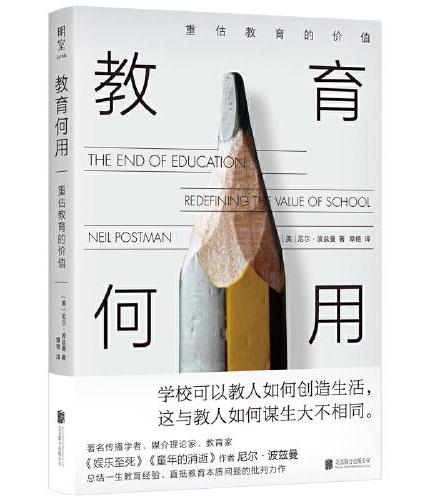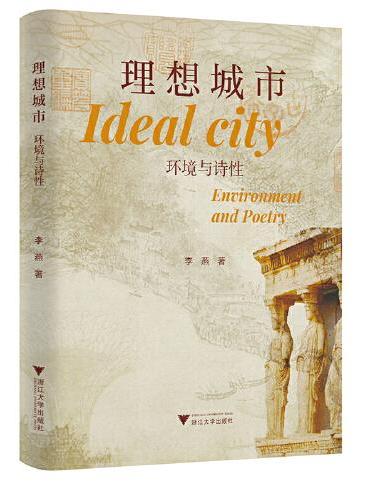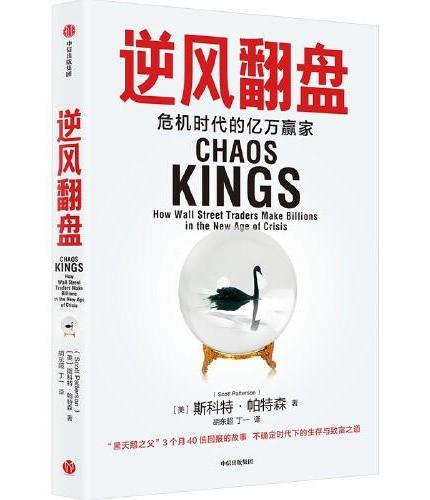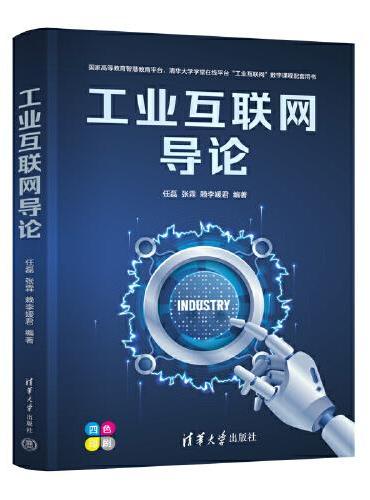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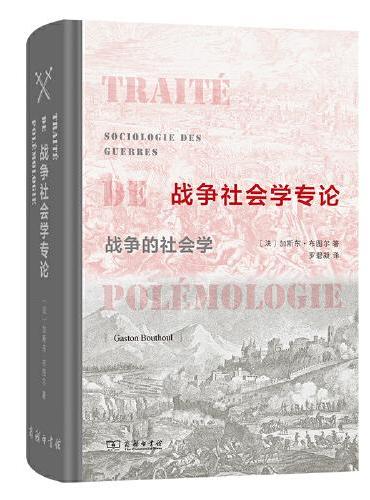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NT$
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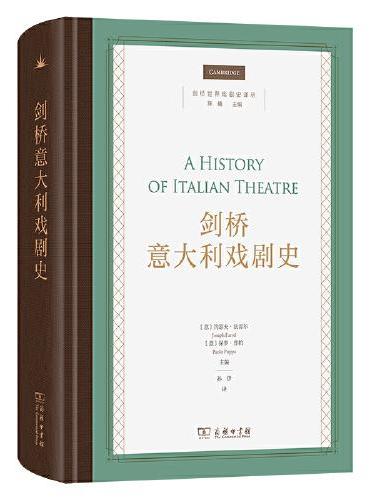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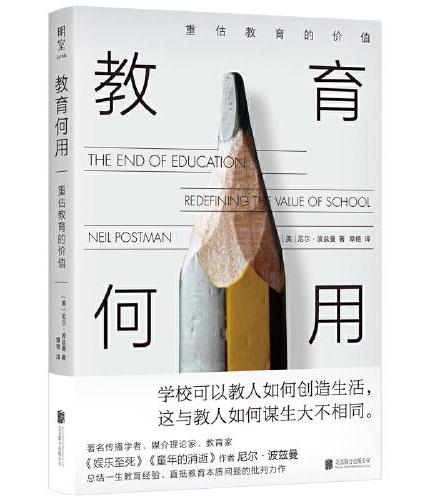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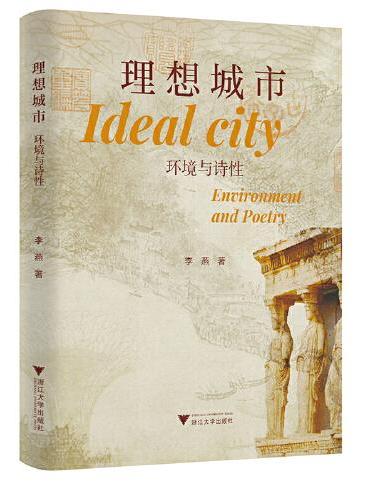
《
理想城市:环境与诗性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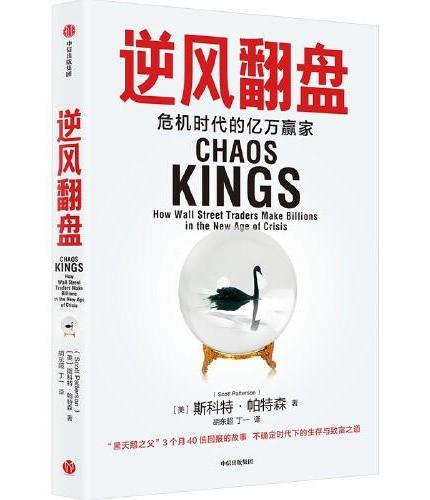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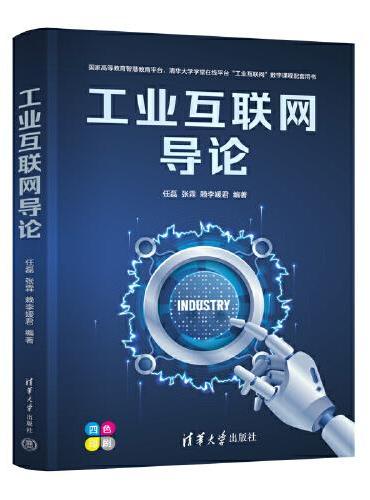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
《面包匠的狂欢节》中有随心所欲的性爱,有为所欲为的谵妄,却并不能激发起令人愉悦的兴奋,相反,这种放弃所有伦理与信仰约束,对放纵的任性演绎让人不寒而栗,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最不可见人的阴影,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在“恶”上无限的潜能。这一则离奇荒诞的寓言提出的是一个我们几乎无法回答的哲学问题:主导我们精神的到底是什么?为何在欲望面前,信仰的塌方如此猛烈,人的堕落会如此彻底?
|
| 內容簡介: |
意大利小镇巴切赖托的居民怀揣各自的欲望,不自知地过着荒唐而滑稽的生活:要为上帝照相的卢伊吉,用独腿跳舞的苉雅,色情暴虐的牧师,肥胖纵欲的面包匠……在伦理和堕落的对峙中日夜挣扎的人们终于在复活节与愚人节相遇的那一天借助面包匠吉安尼神奇的复活节面包彻底释放了内心的恶魔,在狂欢式的肆意交媾中放空了自我,洗涤了灵魂。
人类的信仰经得起怎样的考验?我们的伦理能承受怎样的试炼?直面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
| 關於作者: |
安德鲁·林赛
1955年生于悉尼,在充满乡野之趣的海边林区长大。从米切尔高等教育学院毕业后当过记者,后转投剧院从事编剧,导演与表演工作。1979年到1981年间赴巴黎求学,在著名的贾克·乐寇国际戏剧学校学习形体戏剧,并参加了乐寇的“动作研究实验室”,探索雕塑、建筑、音乐与形体之间的联系。回到悉尼后,创建“红色风暴”音乐剧团,专攻融讽刺、情色与幽默于一身的荒诞剧,社会反响热烈。其文学作品沿袭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充满了戏剧式的形象场景,人物情节荒诞离奇,立意深远而富有哲理。
|
| 目錄:
|
中文版序
声明
开场白:不过我离题了……
引子:关于那幅画
上帝的照片
第一章亲吻节
第二章她的童年即将结束
第三章不洁下等人的疗伤能力
第四章源自他裤裆的父权?
第五章面包匠的狂欢节
第六章狂欢节的殉道者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荣耀!
我不期望你们会相信,但这些事确确实实发生过。如果你们相信了,我也不会因此而小瞧你们。不管怎么说,有谁会相信生命这一事实?小时候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卵子里的精子这个概念搞清楚—难怪卷心菜要容易明白得多。让我来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其余的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卢伊吉·巴切莱蒂坐在他的摄影棚里,他想给上帝照张相。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给上帝照相,卢伊吉心想,这个可怜的杂种也许感到被人冷落了。
整个事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没人事先考虑过这张照片的实际尺寸、相框里需要放些什么,以及用什么来做相框等等这类的问题,至少卢伊吉没想过,所有这些以及某些其他事件将演变成一部传奇,而传奇的名字就叫“面包匠的狂欢节”。
面包匠名叫吉安尼·特里莫托,他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人。因为吃了很多黑麦食物的缘故,有人说他放的屁是全镇最响的,曾震开过马厩的大门,还有一些未经证实的其他传言。
他是个屁放得很响的男人,这点确凿无疑。他用放屁来加重自己说话的语气,就像别人用咳嗽或打喷嚏的方式一样。我这么说绝对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保持记录的准确性。你可以认为这是我对真相的一种承诺。很遗憾,诚实本身并不具备谦虚的特质,也不会让人觉得得体。我讲到哪儿了?
吉安尼·特里莫托嗜酒如命,他热衷于神圣和亵渎之间的界限,时不时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幽默感。他身体的一端是熏人的酒气,另一端则是热气腾腾的黑麦气流,幸亏这两股气体被分开了,不然的话,极可能引发一场剧烈的爆炸。
而那也许正是吉安尼死亡的原因—喝烈酒喝个烂醉,同时放了个屁,他即刻燃烧起来。这是个没有根据的推测,事情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更加让人担忧了。
吉安尼最大的心思是他唯一的孩子弗朗西斯卡,一个快速成长的十三岁女孩,她看上去像一枚就要初次绽放的无花果。她的初潮将至,他该对她说些什么呢?她母亲已经离开人世,这些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好,还是让他的女性朋友来说呢?他想去酒吧找好友阿马莱托参谋参谋。他放了一个屁,头脑清醒了一点,想去喝一杯,但面包还没有烤好呢。
弗朗西斯卡尚未意识到她体内将会发生多少场革命,她将被彻底改变。她的卵巢像两只暗藏的眼睛,凝视着对她来说还很陌生的世界。
很想说她变成了一棵圣树,但不太好意思。还是这么说吧,虽然那枚无花果尚未绽开,但她体内的水肯定已经流动起来了。
很难描述当她看到刚刚长出,并且越来越茂密的阴毛时那种被暴露的感觉。她刮掉阴毛,毛茬子刺疼了她,可毛很快又长了回来,而且比原先的更硬,更像电线。刮得越凶,长得越像电线,好像每刮一次,就有一些刀片上的碎金属钻进了阴毛里。没人警告过她毛茸茸的阴毛会冒出来。她觉得自己的一部分被人取走了,这很奇怪,因为实际上是有东西添加到了她的身体上。那种奇怪的感觉挥之不去,她的一部分被取走了,被拒绝了。没人向她谈起过童年之死。
塔兰图拉
吉安尼的面包房名叫“塔兰图拉”。面包房大门上方挂着一只毛茸茸的巨大黑蜘蛛,一只塔兰图拉狼蛛。她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攻击的架势,脚下的六枚蜘蛛蛋像一个个小面包,在毛茸茸的蜘蛛腿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小巧。塔兰图拉,神的绝妙之作。
她饱含毒液的一口是送你上西天的死亡之吻,一旦沾上她毒牙里流出的致命毒液,你若不想躺在地上抽搐而亡,就只能通过跳舞求生。塔兰图拉,这个长着八条腿的深黑色生物。
卢伊吉的父亲曾被这只塔兰图拉的母亲咬伤过,他坚信汗水可以排毒的民间传说,于是不得不通过跳舞来拯救自己的性命。
这种死法极其难看,喉咙肿得连水都咽不下去,你深信自己马上就要渴死了;因为无法呼吸,你感到窒息。如果不幸目睹过这种死法,你会知道受害者先是站在那儿抽搐,乱蹦乱跳,到了后来却只能躺在地上乱蹬,把尘土搅得遮云蔽日。被咬者的抽搐和晃动看上去极像一种舞蹈。人们普遍认为:塔兰图拉的致命一蜇是那个曾席卷了欧洲南部两百年,造成无数人死亡或者命系一弦,被称作“塔兰图拉综合征”的神经紊乱症的唯一病因。
也许是知道接下来的几分钟将是你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被咬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你反而显得出奇的平静,称之为宿命吧。据说你能感受到毒素沿着你的四肢传遍全身,当它开始燃烧时,你发誓它是从里向外烧的,你又能做什么呢?
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死亡之舞开始了。
死人和活人最大的差别(就被塔兰图拉咬到之后而言)是:活下来的绝不是那些坐在树桩上等死的人。这么做的人很快就会得到他们所等待的—对这个美好世界作最为惨烈的告别。能活下来的人什么都不等,他们抓住蜘蛛的毒牙,立刻跳起舞来。这种治疗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包括舞蹈本身,还有塔兰图拉,由于民间秘方的疗效,所有这一切都演变成了一个传奇。
挂在面包房外面的塔兰图拉是吉安尼·特里莫托亲手制作的招牌。当年遇见卢伊吉的父亲厄内斯托·巴切莱蒂的那一刻,他快要饿死了。
当时厄内斯托正躺在床上,做着一个艳梦,他妻子已经离世了。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塔兰图拉咬了他一口,把他疼醒了。
因为无处过夜,年轻的吉安尼就睡在附近树下的一个窝棚里。当他听到厄内斯托·巴切莱蒂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时,无法确定那是悲惨的呼叫声,还是一个单人的狂欢派对。精通民谣的巴切莱蒂先生知道只有立刻开始跳舞才能救自己一命,但卧室太小,热流已在他体内散开,感觉就像是在用手喝威士忌,饱含塔兰图拉毒液的威士忌需要空间。他冲到楼下的厨房,虽然空间还不够大,但他已经一边踢开挡道的椅子,一边跳起舞来,塔兰图拉的毒牙已把那玩意注入了他的血液,根本无法用嘴把毒汁吸出来,只能通过汗水才能把那个狗日的亲吻排出体外。多厉害的一副毒牙啊。
肚子饿得扁扁的吉安尼·特里莫托第一次见到厄内斯托·巴切莱蒂时,这个被咬的男人正一头冲出大门,当街跳起舞来,那是一支跳疯了的塔兰泰拉舞。
吉安尼·特里莫托看着卢伊吉的父亲纵情狂舞,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进去,为巴切莱蒂的性命跳起舞来。他们手拉着手,十指相扣,世界在两人的旋转里模糊了。他们当时就知道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对方的嘴脸和目光,更忘不了他们嘴里发出的疯狂尖叫。
他们不停地旋转,头、脖子和被咬的手臂都在疯狂地舞动,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跳着塔兰泰拉,奔跑着,用手击打着后背,哪怕一丝力气都没有了也不敢有一刻的停歇。
远处的天空露出了晨曦,两人摔倒时屁股先着地,跌倒后还在不停地大笑着。他们跌进一条长满荆棘的沟里,荆棘上全是灰,虽然他们跳了一整夜的舞,相互间却没有说过一句话。
厄内斯托·巴切莱蒂精疲力竭,但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行将就木的人了,死神虽然还没有离开,但已不再站在旁边俯视他了。骨瘦如柴的男孩率先掉进沟里,厄尼心里涌起一股爱意和感恩之情,他想知道这个男孩是谁。他俩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周围的世界还在旋转,但已经没那么快了,星星似乎也都已固定住了,他们的喘息也缓和了下来,心脏也不再像一条为了让美妙的鱼鳞与天光交汇而试图跃出水面的鱼那样跳个不停。他们躺在那里,平静了下来。
厄尼坐起身来,干咳两声,往草丛里吐了口痰,又躺下了。他肯定又睡着了,因为他接下来感觉到的是照在脸上的烈日,一只苍蝇在他的鼻尖上嗡嗡地飞着,弄醒了他。
还饿着肚子的男孩坐在一边,像吮吸吸管一样吮吸着一片草叶,想把里面的液体吸出来。随后他嚼了嚼叶子,品尝着叶子的甘甜,像是在吃一根胡萝卜。
他又揪下一片草叶,慢慢品尝着,当他揪下第三片草叶时,厄内斯托·巴切莱蒂站起身来说:该去吃点儿面包了!
坐在木餐桌对面的这个男孩看上去怪怪的。他瘦得脸都透明了,看上去就像死神本人,是死神比较安宁的一面。一个长着死神面孔的人让你感到震惊。得把他喂饱,厄尼心想。他不确定自己这辈子有没有见过看上去如此饥饿的人。年轻人一声不吭,他也几乎没说一句话。
他把面包、橄榄、奶酪和苹果放在桌上,等着水壶里的水开,好冲咖啡。他感到一阵强烈的饥饿,外加一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眼下他最关心的是早餐。坐在椅子上的男孩显得极其的不自在,他们在山坡上的泥潭里跋涉和掉进沟里时他的那种无拘无束不见了。那时他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而现在却像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水壶发出尖叫,厄尼拖着步子走到炉子跟前,拎起壶嘴锃亮的水壶,把开水倒进咖啡壶里。
男孩显得很僵硬,好像一到早晨他的骨头就变硬了。来块面包,厄尼说。
男孩看着厄内斯托,舔了舔嘴唇,拿起一个面包卷,捧在手里。他放下面包,用手挠着自己的胳膊,然后把面包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
男孩的这番动作引发了厄尼的好奇。他拿起一块面包,用手掰开,往嘴里塞了一小块。咀嚼的感觉真好。他发现自己的同伴还是没有吃面包,而是坐在那里盯着他看,看着这个大块头咀嚼。他感到一阵疲乏。
这个骨瘦如柴的男孩和他那双瘦骨伶仃的手。他觉得自己几乎能透过男孩的皮肤看到里面的骨头。这个男孩如此苍白消瘦,厄尼纳闷昨晚在跳那个救命舞蹈的时候,他的力气是从哪儿来的。
就这么定了:他要收留这个男孩,喂胖他,这棵幼苗需要养分。这不是他做出的唯一决定。在跳舞、睡去和醒来之间,一个想法形成了,在面对死神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将成为一个面包匠,而这个骨瘦如柴的男孩将是他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徒弟。万岁,“塔兰图拉”诞生了。
一位常客
神父派兹托索是“塔兰图拉”的常客。
他是坎诺利和克罗斯托利的狂热爱好者,也喜欢热乎乎的还淌着树莓酱的膀波罗尼。在对吉安尼杏仁面包的信任方面,他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贵族。比起自己在教堂发送的薄饼,他更喜欢前者,并愿意做个替换。也许克罗斯托利就可以了?耶稣本人,他确信,也长着一副喜欢甜食的牙齿。
总而言之,他发现“塔兰图拉”是一座“诱惑之殿”,经常身不由己地顺道拜访,并和吉安尼交换一些轻松的看法。如果吉安尼觉得有必要咨询一下他对刚出炉的糕点的看法,那么拒绝回答就显得太不礼貌了。
派兹托索从吉安尼·特里莫托身上得到的最大安慰是他的大肚皮。吉安尼狼吞虎咽的时候,大肚皮胀得鼓鼓的,当年的饿鬼形象早就消失殆尽了。
派兹托索常为自己肚子上的赘肉苦恼,在他看来,这不符合一个苦行僧的形象。不光是肚腩,还有遍布全身的一层名副其实的肥油,缠在四肢上,每根骨头和器官都被肥油包裹着。他不能算肥胖,只是被塞满了,而肚腩则是他肉体的终极礼赞。然而,吉安尼·特里莫托让艾米莱·派兹托索自我感觉很苗条,这就足以增进他对吉安尼的友情。
去做礼拜的路上,人们会在面包房停留片刻,买点儿吃的,在晨祷和祝福仪式之前,用一个坎诺利或一块膀波罗尼压压早晨喝下的咖啡。吉安尼·特里莫托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觉得填饱本教区信徒的肚皮是神工作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愿意喂饱那些不信教的。尽管长着一个不谦虚的肚皮,他其实是个很谦虚的人。
吉安尼的面包房就坐落在离教堂和广场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醉人的面包香味飘进礼拜天的教堂,让做礼拜的人口水直流,他们唱出的赞美歌重新注满激情,想到午餐,想到马上就能坐下来享用吉安尼炉里的面包,他们精神上的饥渴被激发了。
吉安尼和艾米莱·派兹托索谈得相当投机。“神父,”他会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我们解决的饥饿类型不同,但我确信在神的眼里,它们同样神圣!你提供精神上的食粮,我则为肚皮服务—填饱教徒们的肚皮。不管怎么说,想侍奉好上帝,没有充沛的体力是不行的!”
神父派兹托索发现这一类的谈话颇为有趣。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向吉安尼·特里莫托打听他侍奉的上帝的细节。
特里莫托的上帝
吉安尼的上帝是发酵面包之神。他坐在面包房里,看着面包缓缓膨胀起来。他内心深处的神迹与此有关,活在把生面团发酵成面包的世界里实在太奇妙了。
这是他的安宁,是从面包匠之神那里找寻到的安宁。
我是个异教徒,他寻思道,一个热爱生活的异教徒。
他决定去拜访一下他的情人西娃娜。是她最先告诉他“阿芙洛狄忒之唇”和鱼象征着什么的,但他的面包还没有烤好。
吉安尼看着桌上被拍打,搓揉,再摊开的面团,它很像一条精心撒上面粉的鱼,那是基督教的简单符号。有的时候,他的某些观点—称它为知识吧—能让可怜的艾米莱·派兹托索目瞪口呆。
“艾米莱,”他说,“你知道吗,象征耶稣的鱼以前是用来象征阿芙洛狄忒的,而且是没有鳍的。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吧,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鱼,它是阴户的美妙重现,是神粗糙多毛的嘴,基督徒借用它来代表神—我们的造物主有血有肉的嘴,后来他们加上鳍,把它变成鱼的样子,想让它体面一点,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它弄得干净一些。圣母马利亚鱼状的阴道口,带着鱼腥味的美味阴唇,有比它更干净,更得体的吗?把它变成一条鱼?哈,阿芙洛狄忒的阴户是万物中最圣洁的象征,它是上帝亲妈的嘴!生命之殿!”
派兹托索抿着嘴一言不发,像一条刚被那位至高无上的神扇了一巴掌的鱼,带着震惊的眼神频频点头。他往嘴里塞了一个膀波罗尼,牙齿咬下去时,红色的果酱流了出来。离开面包房时,他仍为鱼的演变感到困惑。
面包房里到处都是蜘蛛。柜台下面就住着一只,吉安尼不愿意杀死它。他母亲说过,千万不要杀死家里的蜘蛛,说这么做是要触霉头的。他甚至给那只蜘蛛起了个名字—罗拉。这只蜘蛛曾从它的皮里蜕出来,就像是从自已的身体里走了出去。他怀疑这就是蜘蛛成为神圣动物的原因,它能丢弃旧皮囊完成变形,却仍然保留自我。
西娃娜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母狼蛛在她伴侣射精的那一刹那刺中他。这一刺使他麻木,然后她把处于极乐状态下的他缓缓吞下,活活吃掉。他一点儿也感受不到疼痛,她的那一刺就像是一剂爱情吗啡,激发出一种终极的安乐。他的肉体将被用来饲养他的后代。雄蛛在他的伴侣吞吃他的过程中,虽然一直处于极乐状态,却始终是清醒的。不知是因为进化中形成的某种怪癖,还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她总是把他的头留到最后,突然一下子就没有光亮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死法。”
难相处的孩子
弗朗西斯卡亲眼目睹了她母亲的死亡,看着那双眼睛合上,知道它们再也不会睁开,这带给她某种终结的感觉。有些事情她无法与她父亲沟通。一说到她母亲他就坐立不安,在房间东张西望,像是要找条缝钻进去。她只好迅速改变话题,并飞也似的逃离那个充满面包匠排出的有害气体的蜘蛛王国。她待在阿马莱托的小店里,诧异自己怎么那么容易就推掉了父亲的家务事,却乐呵呵地替阿马莱托做同样的事情。
尽管年龄上存在差距,阿马莱托却是她父亲的好朋友。阿马莱托曾向弗朗西斯卡吐露:吉安尼比他父亲更像是父亲。弗朗西斯卡默默地点点头。看到父亲和阿马莱托一边喝酒一边热烈交谈的样子,她感到一丝嫉妒,眼红他俩之间的从容悠闲,以及在喝完第二杯,手里端着第三杯酒时达到的那种无拘无束。
弗朗西斯卡怀疑自己已经到了脱离父亲的年龄,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只要随便给他一个责备的眼神,他几乎就能哭出声来。想让他停下来太容易了,只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身体就一动也动不了,话也说不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实在没什么话要对他说。
她对面包和酵母的味道毫无兴趣,对面包没有一点胃口,她宁愿吃饼干或米饭。如果让她说实话,她对什么都没有胃口。“你不能靠空气过活。”她父亲曾对她这么说。她回答道:“有些东西可以!”说这话时,她想到的是树的气根,但她忘记了树的根是埋在泥土里的。她坚信空气里含有足够的养分。
大胖子吉安尼·特里莫托,这个老百姓的面包匠和“面包匠的狂欢节”之父,在处理自己女儿的问题上,可以说已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他害怕弗朗西斯卡,她显露出来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不值一文。她太像她母亲了。
一天早晨,当听说她要离开家搬到派兹托索那儿去住时,他松了一口气。但据吉安尼所知,派兹托索的厨房仍由漂亮的道恩统领。“不对,”他女儿更新了他的信息,“道恩已经离开镇子了,我和艾米莱说了,说我和你都觉得这么做很合适,我将取代道恩做他的管家。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今天下午就搬过去。”
吉安尼大吃一惊。他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女儿已慢慢控制住了他,他已无法与她抗衡。他觉得自己成了女儿生活中奇怪的附属物,诧异原来属于自己的生活是怎么了,好像父亲这个角色消磨掉了他的其他特征。他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不健康。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弗朗西斯卡需要学会自律,既然神父派兹托索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那就这么着吧。
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世界,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神。派兹托索看着打着结的鞭子,麻绳上的一个个死结和把手上缠着的皮条,寻思是否应该向弗朗西斯卡指出通向忏悔的道路—忏悔和领悟。
这是个神圣的使命。他要教她如何进行鞭打以及在鞭与鞭之间需要背诵的祷告词,警告她在实施过程中不要过于投入。
他认为:侍奉主的方式绝对不止一种。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她似乎生来就对此心领神会。她接过小鞭子,使劲儿抽了一下自己的后背,然后清晰地念出一句祷告词,鞭绳发出的声音像是一串标点符号,伴随她“阿门”的那一鞭,坚定准确,把她带到了句末。他不得不说她非常熟练,甚至可以肯定,她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或许是一种怪异的才能,但生活本来就充满了怪异。
弗朗西斯卡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才能?也许,简单地说,那是一种克制自已的才能。
艾米莱认为用塔兰图拉来做面包房的招牌不太合适,他常想就此和吉安尼交换一下意见,但每次走近面包房,他的决心就动摇了,好像大门上方的那只塔兰图拉正盯着他,迫使他放弃改名字的想法。
但他一直憋着没提改名字的事儿,原因是他一直想不出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来。“报复之吻”不行。“信徒的幸福”让他兴奋了一下午,但当他晚上搂着空酒瓶醉倒在床上发愣时,他认定信徒的幸福是酒而不是面包。这成了他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吉安尼面包房的新名字在躲避他,而他自身的饥渴却没有。“吉安尼的蛋糕洞穴”?不行。他昏睡了过去,醒来时,他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他头痛欲裂,无法再去想任何东西。
西娃娜
揉面的时候,只要想想西娃娜,他做出的面包就充满了情欲。
她的身体在他手里转动,把欲望带到他的嘴边。
有时候,他做出来的面包更像是乳房,面包卷做成了面包球,像是面做的睾丸挂在橱窗里,还有黑麦和黑面包做成的大鸡巴。
面包房唤起人们对健康生活的欲望。
亲吻她的花蕾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认为那是一种灵修,是他自己的圣礼和膜拜。阿芙洛狄忒的唇缘,宇宙万物温柔的嘴。当他的鼻子在通向世界的入口拱来拱去的时候,脑海里经常闪过一些这样的念头。
她的烤箱点燃了,闷闷地烧着,令人满足的温暖,他滚烫的面包卷像坎诺利一样喷射着奶油。一滴都不能浪费!她说,埋下头之前先舔了一下牙齿。那个滚烫的坎诺利就在她嘴里,啊,生活如此丰富甜蜜,他多么热爱面包匠的生活啊。
他对自己的热情感到很意外。虽然他还没到震惊的地步,但他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那种味道以及愿意那么做的,她对他的欲望让他兴奋。他俩都知道,这种欲望是相互的,他们都渴望对方。他们就像长着八条毛腿的蜘蛛,在面粉里放荡地翻腾着,多毛蜘蛛的嘴,在下着蛋,陷到对方的肉里。抬起头换口气,再把头埋下去。
他亲着她的肩头,小口小口地嘬变成了大口大口地咬。
“天哪,我真喜欢你高潮到来时的样子。你确定这样没事儿?我爽透了,真的,我不想说这个,一说我就还想再来,但我的鸡巴软没了。它去哪儿了?你把它咬掉了?哦,在这儿呢。”
她的嘴唇麻木瘀肿了。他的气味,他潮湿的胸毛,从他胸口流到肚皮并还在接着往下流的汗水,那种她喜欢的又甜又苦的气味,把头塞在他的腋窝里。天哪,美极了。
西娃娜第一次走进面包房时,吉安尼正在制作他最钟爱的“面包匠乳脂”—一种由马斯卡普尼软干酪、蛋白酥和拌了糖的蛋黄组成的混和物。他让她来试试,他在一旁看着她往蛋白里掺马斯卡普尼软干酪和蛋黄,被她迷住了。
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步骤。他从没见过有谁搅得这么好。他唯一想说的是:你真该当个面包匠。
他用手指在碗里蘸了蘸,拿出来舔了一下。“很好!”他说。
他又用手指在碗里蘸了蘸让她尝。她没有去尝他的手指,而是用自己的手指在碗里蘸了蘸,舔了舔奶油。“哦,真的,”她说,“太棒了!就这些?就这三样东西?”
“是的,”吉安尼回答道,“蛋黄、蛋白和马斯卡普尼软干酪。对我来说,这是面包匠的三位一体。当然,还要加点儿糖。”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好。难道他想给她留下一点好印象?
他跌跌撞撞地走过去,想看看面包发得怎么样了,他觉得可以把它们放进烤箱了。
他递给她一块没烤过的面团。房间里很热,生面团在她手里显得很柔顺。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这就像一个女人,吉安尼立刻知道他想要她,就在这里,就现在。
但她走掉了,他有点心荡神摇。我得喝一杯,他想,喝一杯阿马莱托定定神。但他先得把面包烤好。没一会儿功夫她又回来了。她又说了些什么呢?
她给他讲了一个阿芙洛狄忒的故事。
“古罗马的面包匠每年都要烤一个蛋糕向她表示敬意,这种蛋糕叫‘阿芙洛狄忒之唇’。他们每年都要吃一次这样的蛋糕。实际上,我没说对,应该叫‘维纳斯之唇’,希腊人才叫它‘阿芙洛狄忒之唇’,它是用熟透了的无花果做成的。吃这种蛋糕是隆重的纵欲狂欢的前奏曲。”
她解开那件绿褐相间的法兰绒衬衫的钮扣。她几乎从来不戴乳罩,衬衫解开后,她身上有点松垮的皮肉让他血脉偾张,不仅仅是血脉在偾张。那对带雀斑的奶子啊!
他让面粉从指缝里漏出,顺着她的乳房往下流,一边搓揉她一边开玩笑说想把她塞进烤箱,吃她的身体。
“天哪,你这个龌龊的下流胚。”她喜欢这么和他说话,称他为猥琐的杂种。
他感到自己被推上了波峰,又被摔入浪谷,一眨眼的工夫,俩人又干上了。面包在烤箱里慢慢烤着,他们在充满爱意的下午昏昏欲睡。
她想知道自己一生里有没有过这样的幸福,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