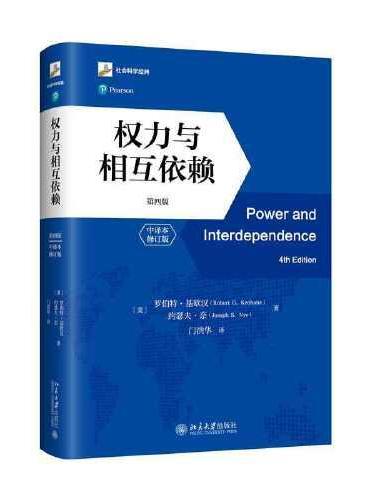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本)(经济学名著译丛)
》
售價:NT$
306.0

《
瘦肝
》
售價:NT$
454.0

《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
售價:NT$
254.0

《
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
》
售價:NT$
704.0

《
民法典1000问
》
售價:NT$
454.0

《
国术健身 易筋经
》
售價:NT$
152.0

《
古罗马800年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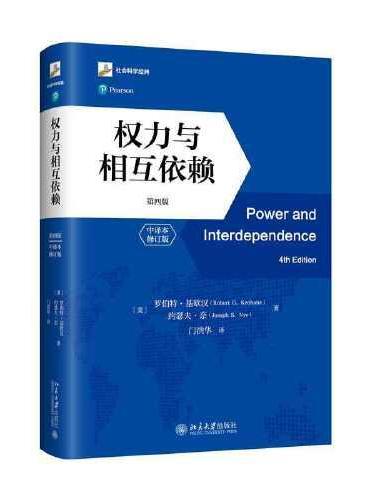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 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的中国乡愁
他的学问源于故纸,他的好友多是故人
庄子、李白、袁枚、金圣叹、林语堂是他的精神挚友
老舍、沈从文、卞之琳、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北岛是他的益友良朋
在一段斑驳的过往里贴地而行,与历史转捩点擦肩而过,结下六十年不解的中国缘
一切游子之思,都源于1948年夏天,一位瑞典青年的扬帆远行
随书附赠马悦然绝版多年性灵佳构《俳句一百首》最新增订版
|
| 內容簡介: |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
1948年7月,一位学习中文的瑞典青年,怀着一颗热爱中国文化的心,来到四川调查方言。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誉满全球的汉学家,用中文写下一部随笔集,诉说对第二故乡的浓浓乡愁。
马悦然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用轻松风趣的笔触记述了他在中国的往事、他与中国妻子的浪漫爱情,以及他与中国文人的友谊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在他的笔下,尘封于卷册之中人和事蓦然间鲜活起来,在我们眼前颦笑、流连,再渐行渐远,留下满卷幽思。
《俳句一百首》增订版
汉学大师马悦然笔下的俳句,巧思精构,又充满了天真与童趣。他不拘格律,运用日常口语,写燕子,写瓢虫,写雪人,跟李白对话,向蒲松龄提问,同金圣叹发感慨,活泼而风趣,以游戏式的幽默洒脱,引领读者进入尔汝群物、物我互置的美妙诗境。
《俳句一百首》原是作者发表于《联合报》副刊的百首俳句结集而成,本次增订,加入了三十多首新作及评论文章,亦可隐隐见出作者的创作轨迹。
作者说,读者阅读以后,如能明白写作俳句并不困难艰涩,进而也想写作这十七个音调的小诗,则于愿足矣。
|
| 關於作者: |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师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90年退休。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1982年、1986年—1988年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
主要研究兴趣着重于方言学、中国音韵学、古代和近代汉语语法及诗律学。1965年以来,共翻译四十余部中国古代、中古、近代和当代文学著作,包括大量汉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作品。现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
| 目錄:
|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
增订版序:怀有一颗谦谨的心 _陈文芬 1
初版序:心上的秋天 _李锐 7
第一辑 一九四九中国行
报国寺 13
小和尚们 16
我们上峨眉山去吧! 20
能海法师 25
仁慈的独裁者马步芳 29
塔尔寺二三事 33
1949岁末日记 37
解放军进城之后 42
旅途二三事 46
第二辑 动人的文字
为什么要调查中国方言 59
劳动号子的节奏与诗歌的格律 62
汉语的生命力 66
从“他”字谈起 70
《左传》中有口语吗 73
一个特殊的语法形式 76
汉语的被动式 79
金子般的先秦文学 83
为《切韵》1400周年干杯 86
《四库全书》小史 90
《水浒传》的瑞典文译本 94
翻译家的责任 97
第三辑 美的生活,生活的美
与中文结缘 105
我尊敬的老师高本汉 109
永恒的刹那 112
谈丢东西 116
一个厨子的道德观 119
四条腿的老朋友们 122
谈记愧、忏悔与其他 125
谈后悔 128
巨人都到哪里去了 133
林中空地的石头 137
我的妻子陈宁祖 139
一个真奇妙的事 145
我的岳父岳母 150
悼念宁祖 158
我心中的公主 165
第四辑 中国人与他们的诗意
康有为的《瑞典游记》 171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 175
学者的良知与名誉 178
中国建筑家梁思成 182
一位被遗忘的诗人 185
坐在同一块云上的诗人 189
冯至发现的一位诗人 192
香港的一位老诗人 198
一个奇特而真实的故事 203
“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207
沈从文乡巴佬作家与学者 210
寄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214
一部最精彩的中国戏剧 218
诗歌建筑家闻一多 223
谈北岛的两首诗 227
想念林语堂先生 231
真理是美丽的 247
附录三则
汉学渊茂,悦然从之 265
中国人的美感消失了吗 279
我的心在先秦 287
《俳句一百首》增订版
代序:我梦里做了个佳梦_陈文芬 001
俳句一百首 017
近作增补 119
附录二则
马悦然的俳句 _李长声 163
马悦然诗酒说汉学 _康正果 167
|
| 內容試閱:
|
增订版序:怀有一颗谦谨的心陈文芬
2012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
悦然说:“高兴。”
我又问:“为什么高兴?”
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8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国时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可汉”,那个“汉”字有追随老师高本汉的意思,日后他说到这个名字笑着摇头:“这名字简直不行!”四川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位优雅的学者闻宥教授为他取名“马悦然”,他的瑞典语名字就是“悦然”(Gran),相当于英语的“乔治”。这美丽的中文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马悦然1946年开始追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一生致力于汉语的研究与翻译,而他的中文写作却推迟到很晚,这是所有汉学家的处境。2000年,以中文写作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台湾报刊邀请马悦然撰写散文专栏一年,后集结成书,即《另一种乡愁》。我当时负责编辑联合文学出版的繁体字版,李锐将书稿交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还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品的台湾学者施淑女,赞叹马悦然一出手写散文就写出了30年代的民国优雅白话文体。过了十几年再读《另一种乡愁》,我更加喜爱。这本书尤为珍贵的意义是,悦然在写作过程中沉浸于对宁祖的毕生爱恋与怀念之中。2005年,悦然带着老二佩尔、儿媳卡琳与孙儿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宁祖的父母。儿媳与孙儿们都是老外,却如中国人一般磕头跪拜。一家人又陪悦然重登峨眉山,走进报国寺。2007年秋天,四川画家老友吴一峰百年冥诞画展,我随悦然回成都,也去拜访报国寺,寺庙大致维持了当年居住的模样。峨眉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乡愁就像还愿一样还完了。
马悦然的中文写作来得虽迟,他的创作力量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方位地爆发出来,明亮而有节奏。首先写作散文集《另一种乡愁》,接着创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写了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部接着一部,最后还翻译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诗作与散文的中文译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霍尔斯恩达尔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也发现马悦然有着运用汉语创作各种文类作品的才华。我认为,马悦然游走于各种文类写作都有着闪闪生辉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唤出往昔无限美好的记忆,传达出他的语言学涵养与经年累月研究汉语文学的哲思。
《另一种乡愁》呈现了一位汉学家研究中国音韵学、古文与现代中文作品的许多心得,马悦然用简朴的文字描述学术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汉代画像砖,当读者看过之后,连缀起来,就能了解当时的文化生活,理解为什么汉学家需要研究中国音韵学。在《劳动号子的节奏与诗歌的格律》一文中,马悦然用诗人曹辛之的笔名“杭约赫”三个字来记录他在四川听到的拉板板车的人哼唱劳动号子的节奏;几年之后,他发现两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节奏跟劳动号子的节奏完全相同;又过了一些年,他发现一个不识字但很有天赋的陕西诗人王老九写的叙事长诗也有相同的节奏,甚至一些弹词与数来宝也用这个节奏。马悦然写道:“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语相比。”
本书的一些文章将来会成为研究中文文学史未完的线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以一个学者的力量写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因为一个学者只有一个观点。1980~1982年、1986~1988年,马悦然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一次在德国召开的汉学会议上,大家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的汉学家有责任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其最大的意义是使许多被历史遗忘的中国作家通过这部文学史的出版而“复活”。
汉学家们通过投票,推举马悦然担任《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总编辑,这部书分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四卷,邀集一百名汉学家撰写导读书评,为作者立传,阐述作品精华。在这个过程中,总编辑必须跟撰写书评及担任各卷主编的汉学家们不断通信、讨论、辩论甚至争执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学史观点。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马悦然没有机会拜访中国。1979年4月,中国发给悦然、宁祖入境证。往后两三年,悦然回北京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的第一版。记得悦然曾在七月的大热天挥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馆一页一页影印了所有的小说诗集读本。后来,这批影印本送进了瑞典远东图书馆,作为他自己研究之用,以后也成为编选文学指南的参考依据。
80年代初,悦然遍访中国的学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学史料的意见。悦然的好友冯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遗忘的诗人韦丛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共140页的《君山》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长的情诗。韦丛芜生于1905年,写作《君山》时才19岁,一生只出版了两本诗集。悦然钦佩冯至先生的文学观点与研究态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的姿态对被遗忘的诗人施以偏见,能够秉持谦谨的公正之心看待不同作者的作品。1980年,马悦然推荐冯至先生选进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成为外国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诗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至今仍摆放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
马悦然几次提到“被遗忘的诗人”是研究文学史的非常严肃的命题。读者也许奇怪为什么他常能发掘别人所不知道的诗人如杨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说家如曹乃谦。悦然说:“那是我偶然发现的。”能使偶然变成必然,需要勤奋阅读,需要手到脚到地做足功课,更需要一颗像冯至那样的谦谨之心。
近年来学界兴起一股风潮,引用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来作为否定汉学家研究的一种依据。我认为“东方主义”是好的学说,但利用此说法来否定汉学家的观点,对真正优秀的汉学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说,要是因此加深了对汉学研究的误解,造成损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种象征。书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悦然发现,在高本汉的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到处都有学术巨人,现在却没有了。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添加了马悦然的三篇新作《林中空地的石头》、《想念林语堂先生》、《真理是美丽的》,附录三篇访问文章为编辑所选。
2015年5月4日
汉学渊茂,悦然从之
“一切都是假装!”白猫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北欧的老外假装做一个关于六言诗的演讲。假装听的人假装他讲的主题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你说笑人不笑人?”
在一篇两百余字的微型小说中,马悦然借小动物之口,幽了一默上次来沪演讲的经历。
那是2005年炎夏,这个八十多岁的瑞典老头儿,用“中古音韵”吟诵了李清照的《声声慢》但多数人并不关心他的汉学研究心得,只是抓紧一切时机、拐弯抹角地追问诺奖的事。
在瑞典闲聊时,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曾跟我提及这趟可怕的上海之行,“运气很不好,复旦在修路,学校里一塌糊涂,那天王安忆送我们出来时悦然就已开始发高烧,后来越来越热,他差点死了42度!陈丹燕就骂我,这个热度你还让他来?!”
是的,马悦然每次来都很“热”,但这个“热”却和他所做的冷门学问没什么关系。
10月中旬,马悦然携妻再次来沪,秋高气爽,却赶上了莫言获奖全国“发烧”的沸点:弄堂、剧院、高校、中学,他们夫妇俩遭遇了最热烈的围观其间,陈文芬曾给好友发过一条无奈的短信:“我明白我们跟中国之间就是这样了,中国作家没得奖,就怪悦然一个人,得奖了以后就莫名攻击得更加厉害。”
其实,马悦然此次中国行是早已计划好的,和诺奖刚颁给莫言并无关系。5月在斯德哥尔摩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就提及今秋会来沪分享翻译观,推介他自己翻译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奖得主)的作品《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
然而,10月21日下午的新书发布会上,三十多家媒体争相挤进了上海老弄堂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书吧。看见眼前小方桌上铺满几十支录音笔,88岁的马悦然似乎有些不适,他微微侧了侧身,旁边速记员正紧张地敲打着,“啪哒啪哒”的急促声响,伴随底下“莫言”、“诺奖”紧锣密鼓的提问,把他原本要分享的“特翁”给吓跑了。
关于莫言,“他们不应该乱开腔”
“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在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话。第二天他又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非常奇怪,人家起一大早到大学来,又马上就要回去,可是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九个大陆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就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沟通。第三次是2005年他参加(北京)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其实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
“(陈:你说莫言小说写得太长了。)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太长了,他04年在《上海文学》刊登了《小说九段》,非常短,只有两页,我觉得非常好,马上把它翻成瑞典文。(陈:你翻译了莫言哪些小说给瑞典学院看?)我开始翻译的时候,选的是在我看来莫言最好的一个中篇《透明的红萝卜》,另外一个是幽默感非常强的《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还有一些像《会唱歌的墙》和《姑娘翱翔》。(陈:讲一个麻子要娶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新婚夜姑娘跑了,飞起来停在树上不肯下来,村里人围在树底下等那新娘下来,悦然很喜欢这个故事。)
“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你读莫言会想到《水浒传》《西游记》《聊斋》的作者,莫言讲故事的能力就是从这些古代说书人那儿学来的。当然他也学过外国作家,他看了Faulkner(福克纳)和Marquez(马尔克斯)后非常惊讶,说,我们高密这样的故事很多,我比得上Faulkner。
“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说莫言是共产党员又是作协副主席,他还抄了《讲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奖?他们不喜欢。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一本书都没读过,他们不应该乱开枪,这让我非常生气(陈:悦然曾批评瑞典媒体,说他们都不读书,只凭外表评判作者,这是很可怕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懒惰)。还有,《讲话》是一个历史文件,在当时对发展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很强的,没有这个文件可能就没有赵树理等人,正因为有《讲话》才会有新的文学,只不过它以后的影响太坏了。”
“南坡居士”,在另一个世界游荡
马悦然说话,语速缓慢、调子沉稳,但他动起笔来则机敏活泼,十足老顽童。
“2004年拜读了老莫(即莫言)发表在《上海文学》的《小说九段》之后,我才明白微型小说到底是啥子。从那时起,要是没别的事做,我偶尔会写一两篇微型小说自娱。”他以“南坡居士”署名,用中文陆续写了60篇“微型小说”,合上“台湾小妖”(莫言对陈文芬的称呼,“她文笔快捷、精巧玲珑,与蒲松龄笔下人物好有一比,故赠此诨号与她,不想竟这样叫开了”)的40篇小品文,两人联袂推出了一部笔记体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
马悦然这位“洋居士”的微型小说别具一格,嘻嘻哈哈仿若酒后戏言。时而,他神游中国古代:骑着自行车回南北朝找寻子夜姑娘(《子夜歌》作者),让“李白那酒鬼”和讲究平仄的“杜老”来段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跟辛弃疾李清照他们对饮谈情发牢骚谈古论今“摆龙门阵”,他用的是夹杂“啥子”、“莫来头”的川话语体,还用起“日每日”、“做那个啥”这般劲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学曹乃谦写他们北温窑的村里人连老莫读后也叹服,赞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恶作剧,有圣哲般的睿言慧语,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掩卷沉思”。
2013年5月,记者曾至马悦然家中专访。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优斯宏”,这位世界闻名的汉学家过着素朴的书斋生活,他的经济来源依靠退休金(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和写作收入。老人并没有房产,长期租住在“燕鼻子住客之家”养老公寓。陈文芬介绍:“这里很受欢迎,许多人申请要等15年才能排到队,入住的全是年过65岁的老人。”走在前头的马悦然立马转身,向她温柔地纠正道:“但你是这里唯一的例外。”
自1998年入住以来,马悦然搬了几次家才换到现在位于二楼的风景更好的房间。那是暮春时节,屋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夫妇俩带我一路亲近自然:“白玉兰、迎春花、山毛榉,还有瑞典特有的柳树。”我们看到一株樱花,“它名字很特别,翻译过来是‘鸟的樱花’。”我半开玩笑:“听上去像骂人。”马悦然反应极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说到他的强项(中国方言和古汉语音韵研究)上了,老人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来。
马悦然的寓所不大,两室一厅不过70平方米,中间十来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他的书斋,屋内装饰简单,墙上几联湘绣书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陈宁祖的父亲)所赠,另有几幅老友高行健的画作。书柜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诸桥辙次编纂的多卷《大汉和辞典》,这是马悦然最常用的中文工具书。客厅正中长条大方桌上,放着各地寄来的样书、刊物和他的戴尔电脑。陈文芬笑道:“他也上网。每天都收到很多资料。我们家现在几乎是个广播台了。”
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它的光闪频率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这里的主人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他经年累月、孜孜矻矻地翻译了自上古至当代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
他爱《国风》里的“辣妹子”,读南北朝《子夜歌》会引动自己的情欲,钦羡“8世纪我的同胞们穿着熊皮在林中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在创作律诗和绝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
多年前马悦然以中文写成自传性文集《另一种乡愁》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为《在另一个世界游荡》。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都“在另一个世界游荡”。
“马可汉”中国行
1944年,遥远的北欧,那个姓马尔姆奎斯特(G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还在乌普萨拉大学修古典语文。“当时的人生目标是当个高中拉丁文和希腊文老师。”闲暇时,他读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艺术》。“林语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国学者还好!发现他对道教兴趣很深,于是我立马到图书馆借来《道德经》,但我发现英、法、德三种译本区别很大,就去请教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问他究竟哪个译文最好,他答:‘那些译本都一样糟。只有我译的是好的。’于是借给我那时还没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后我还去时,他就问我为何不直接学中文。我做了决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老师学中文了。”
当时欧洲的中文授课颇似中国古代私塾,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马悦然,以《左传》入门,比中国学生还古典地学了两年。“现在的读者会认为《左传》文体古老难懂,其实里头有很多当时的口语对话,很有戏剧性,精彩极了!”1947年,他偶然开始把中国文学作品翻成瑞典文。“我记得我所翻译的头两篇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欧阳修的《秋声赋》。196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后才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上古、中古、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
父亲曾任中学教师,马悦然从小跟着家人迁徙各地,习惯用耳朵记方言,也善说方言。1948年被高本汉派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时,他还说不了太多日常会话,但从上海到重庆,再到成都,他仅用两个月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内做了8个月的方言调查。
起初,寺里的小和尚都有点怕这个“马洋人”:“他鼻子好大!眼睛是绿的!摘了眼镜,眼睛是混的!好吓人哦!”当小和尚们发现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便视其为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一首内容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小和尚如果都还在世,现在也该是60岁的老人了,时间过得太快!阿弥陀佛!”
马悦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这个“中国洋女婿”最爱川菜麻婆豆腐:“为什么呢? 因为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怕不辣的人肯定会欣赏。”老人的口味到现在还是“辣”的。
1956年至1958年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从学术方面来看,那三年没什么收获,但我有机会跟一些作家见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齐放’,但1957年春天就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也不喜欢外交官的生活,非常无聊,每天有人要请你吃饭,应酬太多了。”
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
半个世纪以来,马悦然译成瑞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据说,20世纪50年代仍健在的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见过,并和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5月10日专访那天,恰逢沈从文祭日,马悦然回忆时有些伤感:“我们1981年、1982年时见过两三次面,记得我头一次去拜访,他的妻子张兆和就悄悄跟我说,‘千万不要问他古董的事,他一张嘴就讲不完了。’沈从文是个好人,问他关于丁玲的问题,他就说‘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说了。丁玲对他有很多攻击,但他不说人家的坏话。那时我在北京只有几天,要赶很多采访。我们11点多到沈从文家,还有汪曾祺陪着,在他家里,我就听到厨房咚咚咚地在准备,到1点钟我站起来说要走了,他们看起来很失望。(陈在旁安慰:外国人和中国人习惯不同,别太难过了。)”
谈及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马悦然说:“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我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槌),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
“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里,我把沈从文说成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