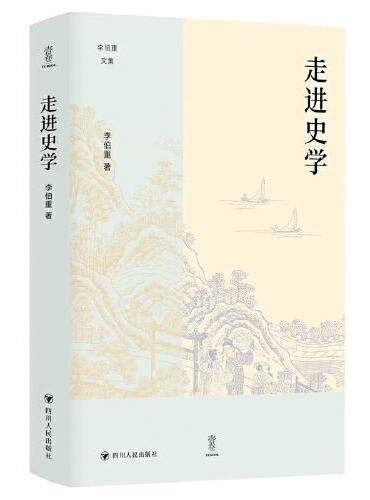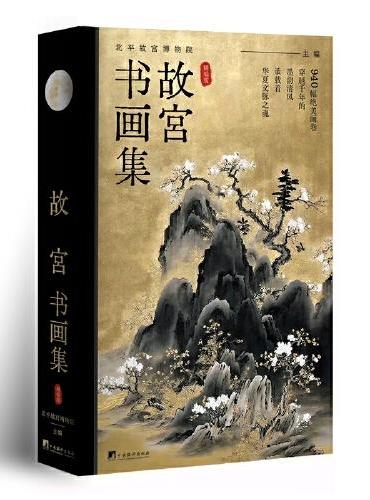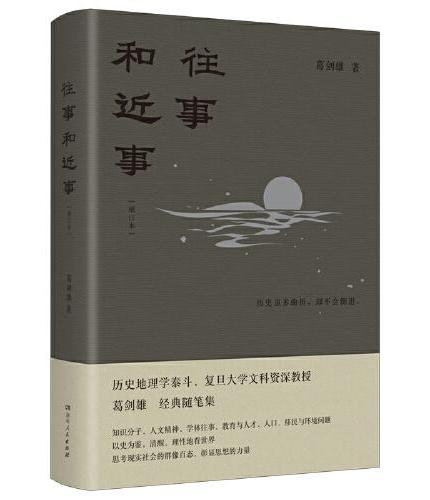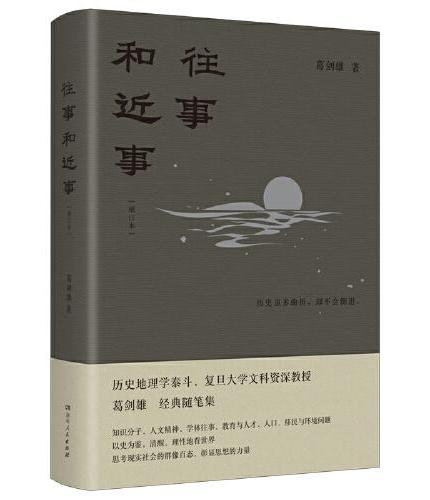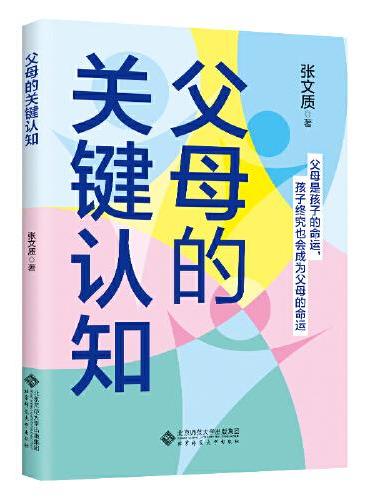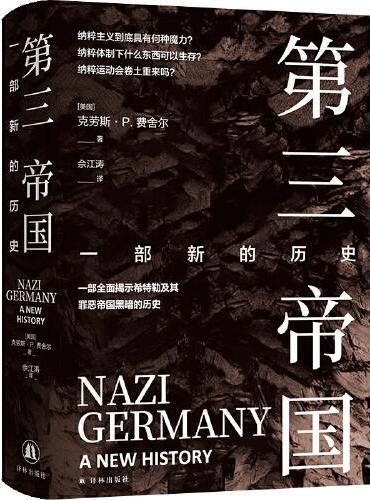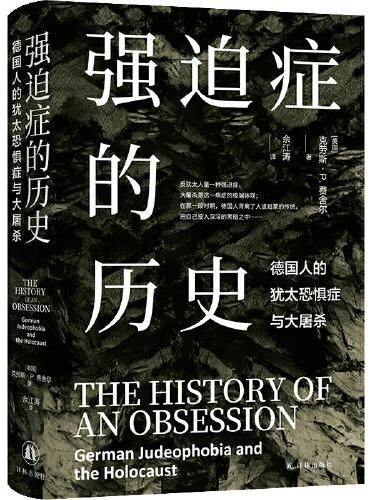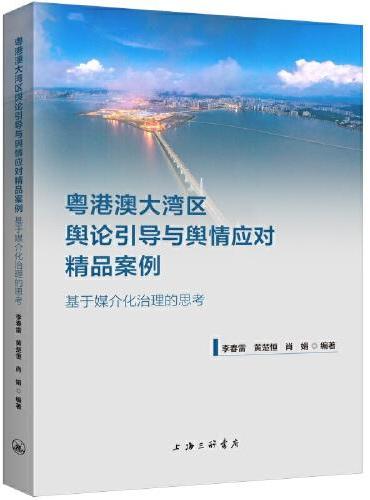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走进史学(壹卷李伯重文集:李伯重先生的学术印记与时代见证)
》 售價:NT$
360.0
《
故宫书画集(精编盒装)版传统文化收藏鉴赏艺术书法人物花鸟扇面雕刻探秘故宫书画简体中文注释解析
》 售價:NT$
1490.0
《
《往事和近事(增订本)》(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代表作,新增修订、全新推出。跨越三十多年的写作,多角度讲述中华文明)
》 售價:NT$
349.0
《
往事和近事:历史地理学泰斗、百家讲坛主讲葛剑雄经典文集
》 售價:NT$
349.0
《
父母的关键认知
》 售價:NT$
225.0
《
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纳粹主义具有何种魔力?纳粹运动会卷土重来吗?一部全面揭示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黑暗的历史)
》 售價:NT$
490.0
《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德国历史上的反犹文化源自哪里?如何演化为战争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德国历史研究专家克劳斯·费舍尔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典范之作)
》 售價:NT$
440.0
《
粤港澳大湾区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精品案例:基于媒介化治理的思考
》 售價:NT$
445.0
內容簡介: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關於作者:
Carol Benedict, 中文名班凯乐,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乔治城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表作是1.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鼠疫与社会变迁的专著;2.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讨论明清以来中国烟草消费史,本书获2011年费正清奖。
目錄
导言
內容試閱
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