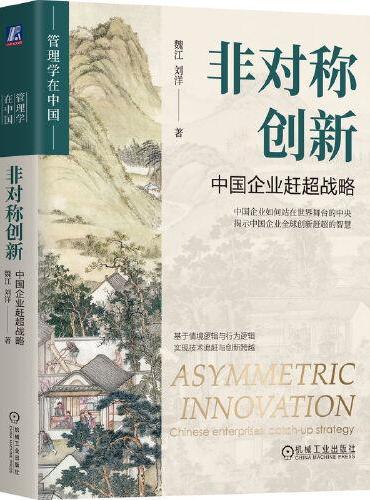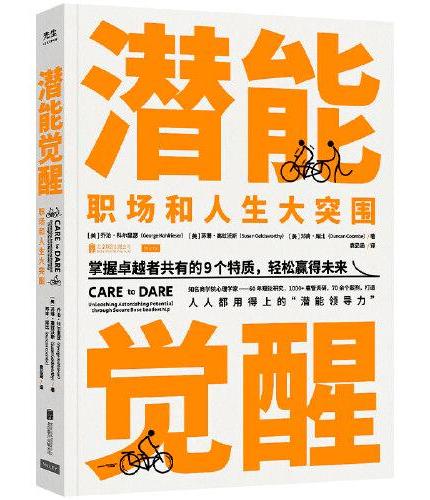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Androi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王玉芹
》
售價:NT$
495.0

《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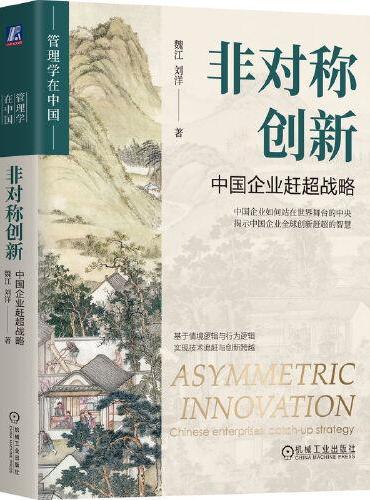
《
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赶超战略 魏江 刘洋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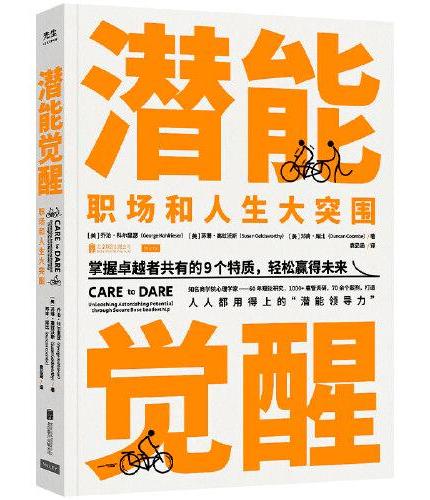
《
潜能觉醒
》
售價:NT$
395.0
|
| 編輯推薦: |
1、电影《一个勺子》原著小说!第51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获奖作品!
2、2015重磅话题,人生无奈,学好归来!
3、戏里戏外,这都不是一个傻子的故事,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荒诞命运。在这个精明的世界,能够做一个傻子,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
4、小说呈现更加震撼人心的故事原型:“犹如照妖镜,让社会中的人无从遁形。”
5、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善良而陷入荒诞的处境,但善良不是一种人格缺陷,即使会因此付出代价,也不要吝啬你的善意。
|
| 內容簡介: |
镇上一个讨饭的傻子跟着宋河回了家,赶不走,甩不掉。宋河想尽办法打发他,可福利院不收,公安局不管,他只好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不久,有人认领了傻子。
刚松一口气的宋河,并不知道,这才是他噩运的开始。傻子的“家人”接踵而至,纷纷上门问他要人。他这才意识到,傻子被冒领了!
明明做了一件好事,却陷入骗局,百口莫辩,难以证明清白,成了人们眼中的“傻子”。为这件好事吃尽了苦头。
一生谨小慎微的他,如同吞咽了钢钉,在喉咙里卡着,还要四处恭恭敬敬。
与其说这是一个傻子的故事,不如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荒诞命运。
当善良被看作一种人格缺陷,当被现实逼入绝境,当我们,突然不理解所谓的生活,
大概才会明白——
在这个精明的世界,能够做一个傻子,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
|
| 關於作者: |
胡学文,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私人档案》《红月亮》等四部长篇小说,《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我们为她做点什么吧》等六部中篇小说集。
曾获《小说选刊》“贞丰杯”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全国读者喜爱的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青年文学创作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2006年、2011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多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广受赞誉。其中,由《奔跑的月光》改编的电影《一个勺子》,获第51届金马奖五项提名,并最终斩获最佳新导演与最佳男主角两个奖项。
|
| 目錄:
|
奔跑的月光/001
被吴老三顶回来,宋河不死心,再次找到吴老三。吴老三依然客气,话里却夹着钢钉,你认为我有责任呢,就去告我,要是觉得和我没关系,别再跟我提这事。吞咽着钢钉,宋河还得恭恭敬敬的。他不占理。
婚姻穴位/047
陈红的眸子里有一层柔柔的、亮亮的东西,有一刹那,刘好觉得自己被化掉了。陈红娇啧,张嘴呀。刘好张开嘴,却连筷子一块咬住了。陈红抽了几下没抽出来,脸就红了。刘好觉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低下头。刘好暗想,陈红果真喜欢他吗?如果那样……刘好想把自己活蹦乱跳的念头摁下去,可越摁它蹦得越高。刘好没有什么鲁莽行为,在陈红面前他还是拘束的。
大风起兮/091
吴卫恨恨地骂娘。赶走一条狗,引来一条狼。吴卫摸摸头,湿漉漉的。他后悔得眼珠子都要放炮了,早知这样,贴几个钱也不能与这种人扯上关系。现在怎么办?吴卫想到报警,可又担心,报警未必能把秋子怎样,一旦秋子翻脸……吴卫想象不出那是什么结果。
飞翔的女人/137
宣判大爪那天,荷子最终没有挤近那辆卡车前,她在拥护的人群中,听见两个妇女的争执。一个说逮住这些人贩子的是一个外乡女人,她长得像俄罗斯人,还会武功。另一个女人说,听说那女人是公安局卧底,专门寻找人贩子的。
极地胭脂/187
唐英的男人没有如期而至。唐英有点魂不守舍,看人时的目光虚泛、空洞,没有内容。她的整个心思被男人挖走了。徐晃盯着唐英的背影想,爱情真他妈的有魔力,唐英这么刻板的女人也被烧得昏头。又想,两口子之间,何至于这样?不禁想起唐英骑驴的架势,心下嘀咕,真是烧的。
向阳坡/223
马达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脸,他怕脸上露出喜气,惹老板不高兴。他摆布着各种表情,终于从中选定一种。谁说马达粗?也有细的时候哩。马达越来越感到老板的重要,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福气是和老板连在一起的。
|
| 內容試閱:
|
1
回到村庄时,日头正往另一个地界缩。余晖被树梢摇落,如受伤的蝴蝶,虽竭力飞舞,终是隐散在寒风中。几天前下了一场雪,路已经变得瓷实光滑,但踩上去,仍怕疼似的咯咯吱吱叫。跟在宋河后面的人忽然挥舞胳膊,像驱赶什么,咻咻叫着往前猛冲。宋河正要提醒,他已仰面摔倒。一动不动,像冻硬的鱼。宋河疾走几步,俯下身。鼓凸的眼球卡住了似的,脏污的脸上却浸着笑。宋河生气了,猛抬起脚,却又缓下来,只是碰碰他。你个傻家伙,吓我一跳!
宋河走了没几步,那个人已追上来。他不说话,宋河更不想理他。两人穿过前街,后街,奔向村庄西北角。没碰见一个人,撞见两个活物,一条是吴老三家的狗,一只是流浪秃尾巴猫。
门敞着,白花花的气往外卷。宋河抽抽鼻子,黄花蒸的是他爱吃的酸菜包子。那个人学宋河皱皱鼻子,不同的是,他还咧开嘴巴。那样大,像一个洞。
那个人突然抢到宋河面前。宋河想拽,那个人一只脚已迈进门槛。黄花正将笼屉拎出锅,那个人几乎撞她身上。她呀一声,两手松脱,笼屉斜跌进冒着热气的锅里。那个人不看黄花,倾下腰,双手同时往锅里伸,迅速抓起两个包子。他被烫了,手腕抖了抖,包子掉到地上。黄花还未反应过来,他已蹲下去,再次抓起那两个烙上黑手印又沾了尘土的包子。左咬一口,右咬一口。他的下巴几乎变形,烫的缘故,脖子蛇一样扭动。宋河冲进来,那个人两手已经空了。宋河扯住他,他把宋河甩开。宋河再次拽他,另两个包子已到他手上。宋河和他争夺,被他拖得团团转。黄花目瞪口呆,直到宋河大叫,她才醒过神儿。两人奋力撕拽,终是将他摁到灶坑儿。他背对着他们,头埋在墙角,将包子塞进洞,方转过脸。黄花操起擀面杖,手却抖着。那个人没了刚才的疯样,鼓凸的眼球趴着横一条竖一条的恐惧。
宋河夺过擀面杖,冲他晃晃,老实点儿,小心把你的牙敲下来。那个人抬起胳膊,缓缓地却是紧紧地捂住嘴。手又大又黑,像破损的扇子。宋河瞪着他,会把你烫坏,烫坏你就不能吃东西了,晾凉才能吃,懂了?那个人不说话,可能是明白了,恐惧尚在,已淡去许多。
黄花问宋河怎么回事,宋河叹口气,先把包子拣出来吧。包子有一小半浸到水里,泡胀了。黄花翻出漏勺,捞上来。那个人窝在灶坑儿,悄无声息。
黄花盯着宋河,宋河看着包子。黄花急得跺脚,你倒是说话呀,咋不明不白领个疯子回来,你也疯了?宋河说,是个傻子,不疯。黄花说,傻也罢疯也罢,你不能往家里领呀。宋河辩解,不是我领,是他跟着我不放。黄花责备,四十大几的人了,连个傻子也对付不了?宋河抓起几个没泡水的包子,放进搪瓷盆,端给那个人。看个人看看宋河,又看看包子,有些胆怯地伸出手。宋河瞄黄花一下,怎样?他不疯,就是饿坏了。
宋河大略讲了经过,两人不约而同把目光甩过去。搪瓷盆已经空了。他害羞似的,把那个颜色灰暗的盆子扣在脸上,然后往侧面移移,露出一只眼睛。眼球显得更凸更大。黄花往宋河身边缩,宋河拍拍她的腰。盆子移向相反的方向,另一只眼凸出来。宋河伸出手,那个人乖乖把盆子交给宋河。没了遮掩,那个人似乎有点紧张,手臂交叉抱在胸前,脑袋缩着,突又仰起来,冲黄花叫声娘。
黄花惊叫,天神神,叫我娘!他看上去比宋河年龄大。那个人又叫,娘!脸上竟有几分欢喜。
黄花气呼呼的,不准你叫,听见没?我不是你娘。我有那么老吗?你叫我娘!见宋河咧着嘴,她狠狠瞪着宋河,他吃饱了,快把他打发走。宋河说冷冻寒天的,他非冻死不可。黄花拧着眉问,咋?还真让他住下?宋河说,反正就一夜,明早把他送到镇上,都叫你娘了,不能白叫啊。黄花拧宋河,宋河边躲边笑,别,别,他吃饱,我肚子还空着呢。
那晚,那个人就缩在灶坑儿。外屋没炉火,放一盆水,会冻出冰碴子。黄花不让那个人睡炕。那个人身板壮实,万一起了歹念,她和宋河加起来也不是对手。你不怕吃亏,就让他睡炕,黄花有些威胁的意思。宋河说着不会吧,心里也敲起鼓。那个人若抢包子一样和他抢女人,他真招架不住。灶坑儿就灶坑儿吧,总比野地强。宋河找出厚重的寒气打不透的白茬皮袄。没人再穿这个,都穿轻薄的羽绒服,宋河也是,但一直没舍得丢。白茬皮袄是父亲留下的。父亲唯一留下的东西,这就派上用场了嘛。那个人老老实实的,宋河让他闭眼,他当下就合上了。
尽管是个傻子,还睡在灶坑儿,毕竟是个大活人,两人说话的声音小了许多。不是怕他,也不是怕他听,不是怕什么,可终究有些担心。声音压低,便带出几分诡秘。他们说的不是那个人,是正事。宋河挺怕女人问,但这个关口逃不掉。黄花不凶不泼,有时嘴上咋呼一些,可跟他一样,是老实人。他们是一对老实夫妻。她早看出结果,但还是要问。每次无果,他都很难受,说出来反而轻松些,即便如此,也不愿意一遍遍说。一个人难受总比两个人难受强,不说呢,还会有另一种难受。
但,那是已往。那个人把这个晚上搅了。黄花自然要问,不同的是,她觉得宋河会说出与往常不同的话,他那么老远领个傻子回来,心情肯定不错么。可是,宋河说的话与之前没有任何不同,黄花就急了。往常,她也急,但只在心里急,因为那不是宋河的错,那个决定是他们共同做出的,她占的成分更大些。而今天,她似乎有资格急。宋河事没办成,反领个不相干人的回来,她能不急么?
宋河安慰她,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再藏,我住他家里。黄花说,你不是说他家多得是么?你找见他别的家么?你能同时住他几个家里?宋河也带出火气,你要我怎么办?就是拼命也得找见他吧?宋河发狠,黄花就闭了嘴。可是,她憋得难受。外屋多个外人,她不想哭出来,可……还是没憋住,先是抽泣,很快成了号啕。宋河没有制止,索性由着她吧。哭了好一阵儿,声音弱下去。宋河把毛巾给她,她问,不会惊着他吧?宋河责备,瞧你这相,不就几万块钱么?咱再挣。黄花也没好声调,单是钱,你还一趟趟跑什么?你又不是没受过骗,还不是自认倒霉?宋河就勾了头。黄花声音重,心反而不怎么憋了。她早就想哭,又怕给宋河添堵。这个不相干的人,似乎让她有理由无所顾忌。黄花不憋了,便有些气短,轻问,不会吓着他吧?宋河和她相视一眼,跳下地推开门。那个人仍在灶坑儿窝着,不知是睡着了,还是仅仅闭着眼。
两人仰躺着,像晒干的鱼。十五瓦的灯泡上沾着灰尘和苍蝇屎,灯光越发昏暗。儿子没出事的时候,黄花极为勤快,每季都要拧下擦拭,现在,她懒了许多。半晌,宋河说睡吧,黄花也说睡吧。宋河扯扯灯线,黑暗顿时挤满屋子。很快,宋河又爬起来。黄花问干什么,宋河说我忘了刚才插门没有。里屋门没有插销,宋河看的是外屋门。他没开灯,光着脚丫摸出去。
重新躺下,他说,那小子要是半夜跑出去,肯定冻死。
2
宋河领着那个人出了村,走出老远,村里的炊烟才东一绺西一绺甩出来。那个人一夜没动静,老老实实缩着。宋河拍他,他才睁开眼。他头发又浓又长,额前显然剪过,能看出是齐茬。黄花热了昨日的包子,那个人又是一顿海吃,挺规矩,没再抢夺,可吃得速度极快。宋河招呼他,他就跟在身后。
入了冬,宋河隔三差五往镇上跑。两年前,儿子坐了牢。六年,两千一百九十天。宋河听说只要花钱,可以少判几年。但花给谁呢?买紧俏东西总得和店掌柜说上话。宋河四处托关系四处碰壁,直到判决书下达,也没寻上帮忙的主儿,钱倒花出去许多。已经判了,宋河只好认命。今年夏天,宋河听吴老三说花钱可以减刑,又动了念头。宋河给吴老三重新打了炕,请吴老三喝了两顿酒,吴老三介绍宋河认识了他的远房亲戚吴多多。吴多多在镇上开着煤栈和油坊,听说县城还有别的生意。跑了三趟,吴多多答应帮忙,说按行情减一年五万块钱。家里有三万,宋河又借了两万。几个月过去,儿子没减一天刑。宋河催问,吴多多起先还有理由,后来就生气了。宋河想吴多多多半办不成了。宋河对吴多多说要是办不成,就把钱退回来吧。吴多多更加生气,说钱已经给了别人,追不回来。五万块钱可不是小数,没这五万,就不能再托别人。宋河一趟趟跑,快把脚跑烂了。
那个人,是宋河在吴多多煤栈门口撞上的。也不是撞,宋河根本不知他从哪儿冒出来的。宋河候了一上午,没见吴多多的影子。中午,坐在煤栈门口的石条上,就着寒风吃干粮。如果向吴多多女人讨口热水,想必也可。宋河不想张嘴,不想看她脸色。宋河一趟趟登门,她早就烦了。宋河宁愿就冷风,也有惩罚自己的意思。谁让他没能耐呢?没能耐还讲究什么?还喝什么热水?
宋河咬了几口,就看见那个人,距他不远。宋河没在意,继续啃自己的。可那个人一步步走过来,身子直直的,眼睛直直的。宋河挥挥手,让他走开。那个人没听见似的,死死盯着宋河手里的饼。宋河掏出一张,做个丢的架势。那个人一阵乱抓,仿佛烙饼已经在空中。宋河缓缓递过去。那个人不看宋河,所有注意力都在饼上。目光定牢靠,才颤颤地伸长胳膊,抓到饼,猛地撤回去。几下就把饼吞了。然后,小心翼翼地瞄一眼宋河手里的饼,又瞄一眼宋河。宋河把另外一张也给了他。吞掉,那个人仍站着不动。宋河说没了,为让他相信,还把帆布包翻开。听清了吗?宋河问。那个人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就那么站着。宋河不再理他。宋河在院里走几圈,在门口坐一会儿,然后又在院里走。宋河看着日头,掐着回家的点儿。
有那么一会儿,宋河没看见那个人,就把他忘了。差不多出了镇,宋河才发现他,他竟然在身后跟着。宋河再次说没吃的给他了,叫他不要跟。那个人听懂了,因为他点头了。宋河起步,他又跟着。宋河挥舞胳膊,大声叫着,总算把他吓得站住。宋河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再回回头,那个人站着没动。宋河松口气,不由加快步子。没多大工夫,那个人就追上来。宋河吓唬,他站住,宋河走,他就跟着。镇上好歹有个避寒的地方,在野外非冻死不可。这么一想,宋河又返回镇上,给那个人指指,让他留在那儿。宋河捡起一块石头,说再跟就砸他。那个人一点儿点儿退缩,贴到墙上。宋河走出不到一里地,他又跟上来。宋河火了,照他腿上屁股小腹一阵猛踹。他绊倒后,又照他胸口踢了两脚。那个人不躲也不还手,脸上满是泥水一样的恐惧和哀求。宋河累了,也心软了,蹲下去,搜了搜那个人的兜子,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宋河说,我不认识你,你跟我,我会把你丢在野地喂狼。宋河再走,那个人仍然尾随。宋河心想,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不再理他就是。看见村庄,宋河回头看看,改了主意。那个人不可能返回镇上,正是坝上最冷的时候,在野外半夜就得冻成冰棍。收留他一夜,就一夜。
往常,宋河上镇只一桩事,现在成了两桩。后一桩不算什么,宋河打定主意,到镇上就不再理他。
宋河使个心眼儿,没直接去煤栈,进了镇里最大的市场。市场是环形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中间的空地则是敞开的货摊,那儿人多,杂乱。宋河转了几圈,总算把那个人甩掉。
宋河推开门,一只脚刚迈进去,另一只脚还未抬起,吴多多女人就把话射出来,不在!宋河顿了一下,还是把另一只脚抽过门槛。吴多多女人声音冷硬,不是告诉你不在么?宋河说,吴老板说三两天回来。吴多多女人问,他给你保证了?宋河说,我给吴老板打过电话,要么,你给他打电话问问?吴多多女人说,手机没电,想打你出去打。她细长细长的,像一根榨菜,项链几乎有拇指粗。不知咋的,她金灿灿的项链总让宋河气短。宋河赔着小心说,我等一会儿吧。吴多多女人皱皱眉,没撵宋河走。宋河决定在屋里等,她甩脸色就甩脸色吧。没两分钟,她的手机就唱起来。她打麻将,宋河悄无声息地缩在沙发上。客厅大,宋河缩着,显得格外小。宋河忽然想起那个人缩在灶坑儿的样子。此刻,他和那个人没什么差别吧。
宋河在沙发上吃过干粮,换个姿势,没挪窝,直到她们散场。吴多多女人似乎猛然发现宋河,问,还没走?宋河胸口撞了撞,想说,我不走了,我要住下来。终是不敢,那样等于彻底撕破了脸。宋河无法预料会是什么结果。于是,他笑笑,问她能不能打个电话。她懒得回答,说要洗澡。然后,当着他的面脱下长裤。宋河从沙发上弹起来。
冷风吹过,宋河龇龇牙,骂了脏话。
宋河走得急,拐出院角,几乎和一个人撞上。竟然是那个人。宋河愣了愣,又骂了句脏话。
宋河到街上给吴多多打电话。家里有手机,儿子坐牢后,宋河不再交费,因为没什么用了。吴多多手机通着,但不接听。等了一会儿,宋河又拨,依然。宋河气呼呼地想,你不接,我天天来,不信撞不见你。
那个人在马路对面站着,显然在恭候宋河。宋河窝着一肚子气,大步过去,狠狠踹他一脚。还想吃干粮?还想跟我是不?那个人往后缩着,怯怯地看着宋河。见有人往这边瞅,宋河再次抬起的脚放下去。起风了,宋河一趔一趔的,那个人却直僵僵的,还有他的头发,裹了油污的缘故吧,竟然没乱。行了一段,宋河想,就这么走,根本甩不掉那个人。于是,他折返到十字街,打了一辆车。宋河没这么破费过。为甩掉这个麻烦,没别的办法。车从那个人身边驶过,宋河瞄他,暴凸眼瞪得特别大。
离村尚有一里地,宋河让司机停车,不想让人看见他打车。比昨天早了点儿,他没急着走,在雪地站了一会儿,直到夕阳坠落。街道很安静,天冷,没人愿意出来。走到后街,却碰上吴老三。两人冷冷地打过招呼,谁也没停留。宋河找过吴老三,想让吴老三和吴多多说说退钱的事。吴老三说这不能怪他,他只负责牵线,别的事与他无关。确实不怪吴老三,宋河也没怪他的意思,只是觉得吴老三说话,吴多多给面子。被吴老三顶回来,宋河不死心,再次找到吴老三。吴老三依然客气,话里却夹着钢钉,你认为我有责任呢,就去告我,要是觉得和我没关系,别再跟我提这事。吞咽着钢钉,宋河还得恭恭敬敬的。他不占理。
黄花直奔主题:咋样?她每次这样问,宋河的头皮都被电了似的。但他尽可能说得平静,轻松。黄花问明天还去?宋河说当然去。突然意识到,很有可能再撞见那个人,那就意味着,还得打车回来。不由一颤,接着是一个恶狠狠的喷嚏。
黄花打量他,冻着了?
宋河摇头,没事。
饭是蒸莜面,四周是宋河爱吃的土豆片。他没胃口,心不在焉。一天花三十,一个月就得九百。这样一算,胃口更差了。偏偏黄花问起那个人,宋河说到镇上就把他丢开了。黄花追问,你看清了,他没追你?宋河嘎嘎笑起来,表情夸张,不就个傻子嘛,还把你吓着了?黄花说,我真有些怕。宋河嘲弄,瞧瞧你这点儿胆子,把心好好放肚里吧。
睡前,黄花出去拎便盆,一个黑影突然从墙根站起。黄花惊叫一声,瘫下去。
宋河冲出屋,顺手扯扯门框一侧的灯线。昏黄的灯光下,那个人直直地戳着。
宋河把黄花扶起。黄花没好气,你不说甩掉了吗?宋河说当然甩掉了,你是我老婆,他是不相干的傻子,我会为不相干的傻子哄老婆?
那个人似乎明白吓到了黄花,怯怯地叫声娘。
黄花叫,滚,滚远远的,我才不是你娘呢。
宋河搀黄花进屋,那个人跟着。宋河甩过冷脸,那个人定住。
宋河插住门,又用杠子顶住。
黄花仍埋怨宋河,宋河只好讲了打车的事。黄花不哆嗦了,声音却跑了调儿,这就是说,他自己能寻到这儿?宋河安慰着黄花,心却往下沉。黄花问,他能找见咱家,咋就找不见自己家?宋河说谁知道呢,或许他根本没家,要么他家在老远的地方。黄花没长暴凸眼,且眼窝略凹陷,却也瞪得大大的。他怎么就到了镇上,偏偏撞见你?宋河苦笑,我怎么知道?黄花不言声了,神情分明在问,怎么办?宋河寻思一会儿,说把他赶出院子,他爱咋咋吧。黄花问,他要是冻死呢?宋河说,死就死呗,咱不操心。黄花说,昨个儿你怕他冻死,今儿就不怕了?宋河说留他一夜行,不能天天留,你想留他?黄花捣宋河一下,突然又抛出一个问题,要是他再爬进来,冻死在院里呢?一个人不明不白死在院里,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只能再留他一夜。宋河没直接说,反问,你说怎么办?黄花丧气地说,还能怎么办?你家祖传的皮袄派上用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