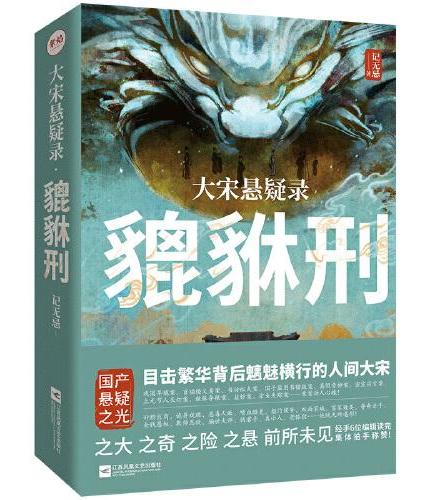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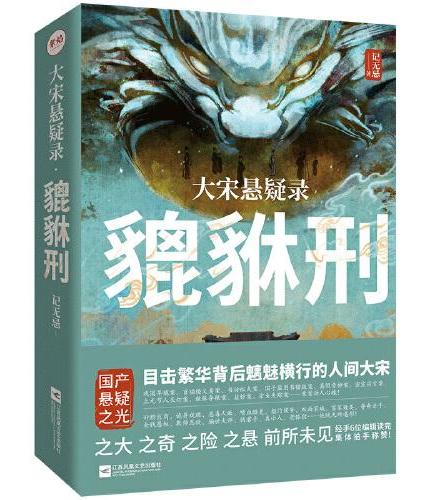
《
大宋悬疑录:貔貅刑
》
售價:NT$
340.0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NT$
490.0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NT$
295.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
| 編輯推薦: |
|
《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看大时代中“新青年”如何自觉而又有担当地救民族之危亡,图国家之强盛。
|
| 內容簡介: |
|
《新青年》是20世纪中国进入新时代创办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本杂志。它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赛先生”与“德先生”,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本书以《新青年》为线索,对陈独秀从办报到参与建党一路实践其对国家与社会的革新梦想进行了总体概览,记叙了《新青年》是如何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引发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叙述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瞿秋白等《新青年》同人相识相交的故事,力图还原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所作的人生抉择,展现他们对大时代背景下国家走向、社会进步、个人命运的思考和价值追求。
|
| 關於作者: |
|
张家康,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在《人物》《百年潮》《炎黄春秋》《纵横》《历史学家茶座》《团结报》《人民政协报》《党史信息报》等报刊发表诸多文章,其中有百余篇被《新华月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作家文摘》《马克思主义文摘》、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六十多种报刊转载。一篇获华东地区党史期刊优秀文章二等奖,两篇获华东地区党史期刊优秀文章三等奖。
|
| 目錄:
|
青年早尊他为领袖
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抗战中的陈独秀
艰难炼骨书生本色
陈独秀的朋友们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没世不渝的友谊
我得感谢我的慈母
"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
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
苦撑待变的"过河卒子"
一为"喇叭"一为"诤臣"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鼓吹学子一扫阴沉
书生领袖的困惑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春兰秋菊不同时
漫话周作人的毁誉是非
五四大潮中的康有为梁启超
最早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两个人
卫道忧时启迪今人的学问家
中共"一大"主持者的蜕变
周佛海一生的红与黑
一代怪杰辜鸿铭
|
| 內容試閱:
|
青年早尊他为领袖
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华民国的建立,可民主共和徒有虚名。皇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军阀政权,政治极其黑暗,思想异常混乱,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的思潮如沉渣泛起,十分活跃,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正是在前景堪忧,路途渺茫之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第一次全面、猛烈地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发起攻击,黑暗混沌中终于透现出曙光,这就是《新青年》所遵循一贯的宗旨——民主与科学。《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停刊于1926年7月,其间虽多有变故,但与陈独秀却如影随形,相随相傍。陈独秀与《新青年》已共同融为一个符号,存储于历史的记忆之中。
日夜梦想革新大业
陈独秀和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创办了许多报刊,旨在“改变人的思想”。1903年8月7日,他和章士钊在上海昌寿里的一间小阁楼上共同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可谓是他以报问政的开始。《国民日日报》吸取被查封的《苏报》的教训,文字迂回,论调舒缓,然而,其鼓吹排满革命的宗旨不变,在读者中影响极大,有“《苏报》第二”之称。
这样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自然要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上海知县布告,不准市民购买和零售。沿江省抚无不予以封杀查禁。1903年12月,《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年底,陈独秀又回到家乡安庆,与好友房秩五、吴守一等相商,创办一份别开生面的《安徽俗话报》。吴、房二人积极响应,并议定陈独秀主编,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守一负责小说栏。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从中联络资助经费,并将社址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这是份半个月发行一期的报纸。他说,这份报纸既要成本低,让“穷人买得起”,又要有丰富多样的信息和内容,以“通达学问,明白目标”。既然是份平民化的报纸,那么就不能“之乎者也矣焉哉”,而要贴近民众,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出来。《安徽俗话报》正是遵循这样的方针,所以才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有“最开风气”的赞誉。
《安徽俗话报》未办几期,房秩五就东渡日本,吴守一也回桐城教书去了,陈独秀一人依然坚持。十八年后,他在为《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撰写题词时,还余兴未减地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
1905年9月,《安徽俗话报》办到第23期便自动停刊。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躲避安徽军阀倪嗣冲的追捕,秘密潜往上海,住到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完成了《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两部著作。动乱的年代,这两本书很难出售。他给在东京的好友章士钊去信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他还向章士钊介绍了国事的黑暗与艰难。此时,章士钊正在日本创办《甲寅》,这是份旨在反对袁世凯的政论性月刊,它的政论性文章曾经轰动一时。次年6月10日,《甲寅》公布了陈独秀的信,还函约陈独秀来日本,共同编辑《甲寅》。
陈独秀接信后来到东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8月,《甲寅》第1卷第3号发表他的七首诗。11月10日,《甲寅》发表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四千多字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洗练,直面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大胆放言,无情批判,对当时的知识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有着很大的偏差,总是将国家“与社稷齐观”,认为国家便是历朝皇帝,“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于是,“忠君”便是爱国,爱国便是忠于皇上。西方人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家的天职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如此以民为本的“建设国家者”,在中国想都不能想。历代王朝只会疯狂地聚敛财富,即使是难得之“圣君贤相”,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旨以谋一姓之兴亡”。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如果对这样的所谓国家,还“过昵感情,侈言爱国”,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那就是缺乏自觉心的愚忠。
他说,一个理性的公民应该知道“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即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向外扩张时,公开号召“为皇帝为祖国而战”,其实质“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他说:“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人民如果盲目愚忠,势必为野心家所利用,那么“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他尤为强调,“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
中华民国虽已建立,可是,民主共和的理念,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遍视国中,法纪废弛,贪污横行,兵匪日盛,中国已“不能保国于今世”,此为何故?他的答案是:“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他怀疑以今日“国民之智力”,中国“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人民无权利、无福利,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果此时“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文章发表后,《甲寅》收到了十多封来信,信中诘问斥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时过半年,当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才从混沌中惊醒,认为卖国的中国现政府,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对陈独秀的文章,由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盲目愚忠的“爱国心”,也就“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
《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形成,是有一个嬗变跃进的心路历程。世纪之交,他身在闭塞的安庆城,也和莘莘学子一样,以为皇帝身系国家,忠君和爱国相连。1904年,他已经两次东渡日本,在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国家的理念后,便很快与封建的忠君保国的思想决裂,在他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对于国家已有了大胆的崭新的诠释:
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现在东西各强国,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叫做“主权”。……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
此时,他虽然还怀疑中国是否“算是一个国”,但是,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仍要人民不仅要“知道有家”,而且要“知道有国”;不仅要“知道天命”,而且要“知道尽人力”。十年后,袁世凯窃国篡权,国土破碎,主权丧失,国家已糜烂至极。他认为这样的国家,人民已“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
他在愤激哀叹之余,不免意气用事而走入极端。正如梁启超所说:“举国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耳,特不敢质言耳!”许多人心有此想,而未必敢言,陈独秀则不是这样,他是怎么想的,便要怎么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其实,他的本意是无可厚非的,“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他正是抱着如此偏激心情,采取正话反说的方式,以开启民智,树立民众的民主共和的国家观念。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良苦心情呢?历史再次召唤他开启思想启蒙的运动,不到一年,他便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又以思想巨人的风姿,高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巨涛狂飙。
文学革命取得胜利
1915年9月,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次年9月,因与上海一刊物同名,改名为《新青年》。每号(月)约一百页,六号为一卷。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因此停刊。从创刊到1917年8月,即第一卷第一号到第三卷第六号,总计十八号即十八期,都是陈独秀一人主撰。1918年1月,《新青年》在北京复刊,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六人相约《新青年》不谈政治,可当五四大潮涌来时,刊物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六人编辑也因此而名存实亡。如鲁迅所说:“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而被捕,《新青年》也因之停刊。1919年9月,陈独秀被释放。11月,《新青年》又在上海复刊。
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新青年》又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次年1月,上海法租界取缔《新青年》,陈独秀恰受陈炯明之聘,往广东任教育委员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广州。4月1日,《新青年》在广州复刊。1922年7月,《新青年》在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新青年》停刊。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全文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不敢提文学革命,他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陈独秀则不然,他的《文学革命论》很快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表明推行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和必胜信念。他说,中国文化界之所以“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推其原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
胡适的胆子却越发变小,给陈独秀写信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接信后,立即在《新青年》发表致胡适的信,公开表明他义无反顾、当仁不让的积极态度:
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多少年后,胡适在忆及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号。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1918年1月,《新青年》一月号破天荒地刊出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中国新文化史上第一批白话诗终于呱呱坠地,这些开天辟地的新诗,每字每句都浸透着创作者披荆斩棘的艰辛。他们那种敢于为“引车卖浆者流”写作的勇气,确有着一种目空古人,下开百代的悲壮,他们所表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精神,其本身就具有时代意义。
同年5月号《新青年》发表鲁迅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反动礼教作了锥骨敲髓的讽刺和鞭辟入里的批判。鲁迅出手不凡,确是一名健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除却《狂人日记》外,还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诗。自此,他以唐俟和鲁迅的笔名为《新青年》写文章。《新青年》开始白话文的时代。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白话文的《每周评论》,以作为《新青年》的补充和后援。北大学生积极响应,次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文学革命的生力军日益壮大。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主潮和期刊热,把文学革命推至高潮。这一年,全国至少有四百种白话报面世,著名的有《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开始刊载白话文。当时国内最大的几家杂志,如《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都尝试用白话写作。白话文已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和利用。
192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命令,小学校一、二年级教科书,从是年秋季改用白话。不久,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用白话教学。全国报刊也都相继改用白话文。从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算起,只有三年的时间,文学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青年早尊他为领袖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赞赏西方人的“年长而勿衰 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的生命哲学,讴歌鲜活、奋进的年轻生命,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是中国国民改造、社会进步的希望。“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青年何以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何以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呢?他提出了六条标准,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鼓吹人生应有“横厉无前”的美德,以去征服“恶社会”,“战胜恶社会”,“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他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即是民主,提倡个性的解放,屏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Democracy(民主)和Science(科学),五四那代人亲切称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
他在《新青年》的大多文章,几乎都是介绍和推崇西方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他研究了拿破仑、圣西门、傅立叶、卡耐基和马克思,从而形成了对他们的独特见解。在创刊号上,他介绍这些先哲的思想。他说,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拿破仑有言曰:‘难’,‘不能’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卡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他提倡的正是这种知难而进、义无反顾的战斗风格。他要将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明介绍于国民,以激励国民,树立独立自由的人格形象,使“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
在将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后,他大胆针砭国民的落后性和劣根性,指出国民的堕落品性:“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通病”“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等。他甚至找出国贫民穷的病因,是由于人口过多造成的,“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
他向国民敲响了警钟,“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他知道传统观念的改变,一定要遭遇传统的抵制和政治的压迫。可他却无所畏惧,视“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直指封建的纲常礼教,毫不妥协,“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
《新青年》一发行,便引起国人的关注,那些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崇论闳议,使深寂的古国从昏睡中骇然惊起。《新青年》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读者顾克刚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之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
从1915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四百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一百五十篇之多。这些文章可谓触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等,真是无所不谈。青年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详知他的独树一帜的思想、拔山盖世的气节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
《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北大同人精心协办这个杂志,使这个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由初办时的一千份增至一万五千份。据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顿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改老气横秋、陈旧腐败,而清新活泼、生意盎然起来。陈独秀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不仅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动起来,各地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报刊竟达四百余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那些割据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陈独秀认识到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说,早在建党前,革命青年就尊他为“我们的领袖”。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
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陈独秀认为,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积弱积贫的祸根,并将之概括为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1919年1月19日,他的《除三害》在《每周评论》发表,此时距五四运动只有三个多月。他呼吁:“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每周评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对国内政治问题坚决果敢、毫不妥协的态度。
五四运动前七天,他发表的《贫民的哭声》,乃是一篇政治煽情的杰作。文章说:“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贫苦百姓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就是因为政府“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平民百姓“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当权的文武官员却“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手里享用”。他警告说,如今的中国已如一个火药桶,“单是北京一处”,“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断言,这凄苦愤怒的哭声,早晚要产生巨大的震撼力量,撼动腐败、没落的北洋军阀政府,“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疼,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年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所提示的有“社会中坚分子”“挺身出头”的“相当的示威运动”成为事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并以磅礴之势向全国蔓延。
就是在5月4日,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孔教研究》《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公司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继续进行政治煽情。他说,上海的南北和会和巴黎的国际和会,都是分赃会议,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到来,“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他的“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号召力。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
五四运动刚刚发生时,市井民众非但不积极参与,还冷嘲热讽爱国的学生运动。陈独秀严厉批评这种冷漠的态度,“像这种全体国民的存亡大问题,可怜只有一小部分爱国的学生和政党出来热心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旁边不问,已经是放弃责任不成话说了。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是政客利用煽动,(全体国民那个不应该出来煽动?煽动国民爱国自卫,有什么错处?)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种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北京学生继续总罢课,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北洋军阀政府又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和4日,他们竟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释放陈独秀,不少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表示崇敬和声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