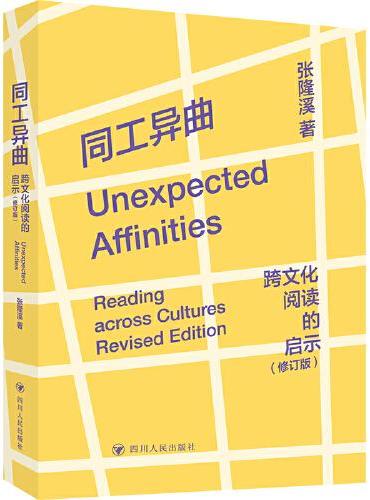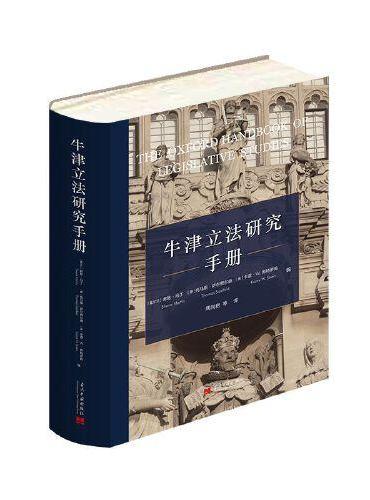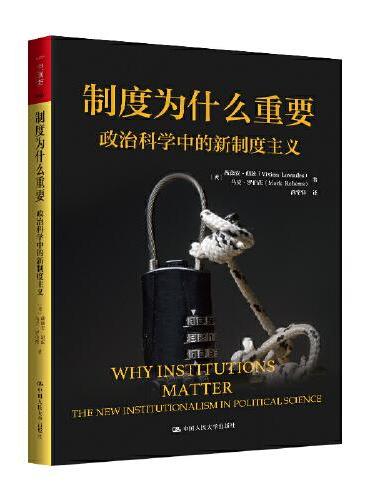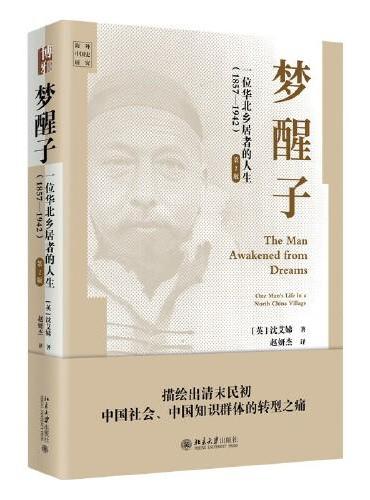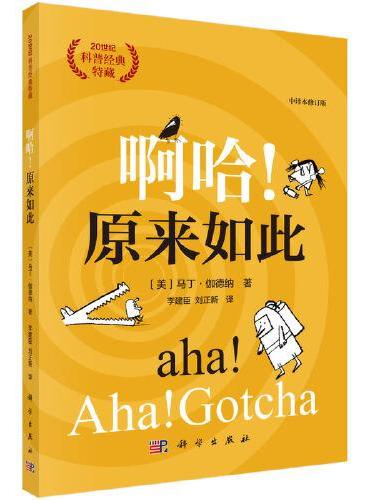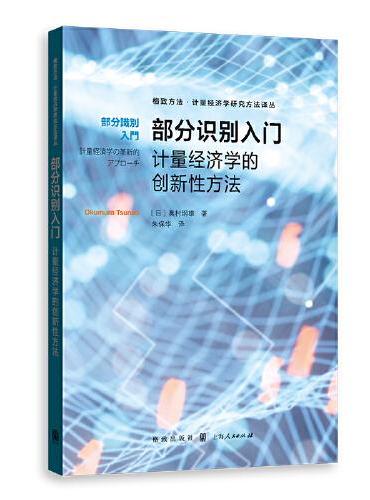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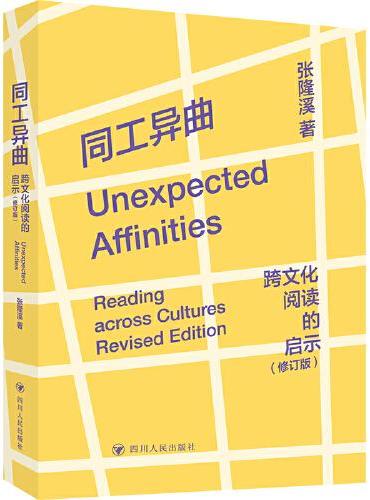
《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修订版)(师承钱锺书先生,比较文学入门,体量小但内容丰,案例文笔皆精彩)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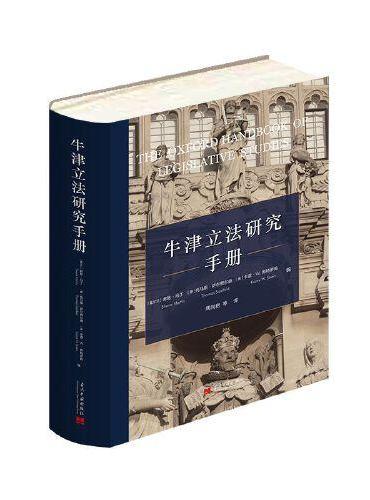
《
牛津立法研究手册
》
售價:NT$
1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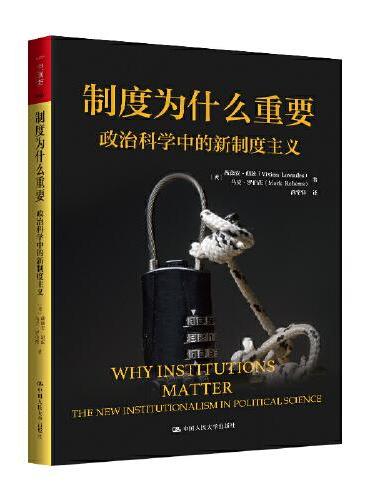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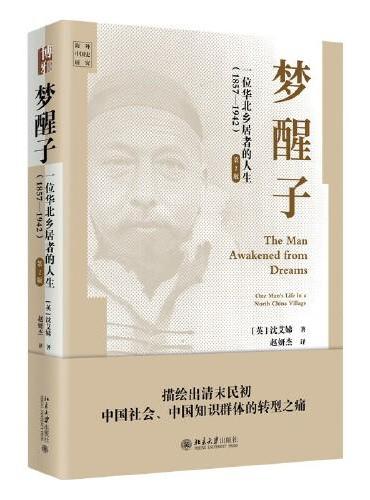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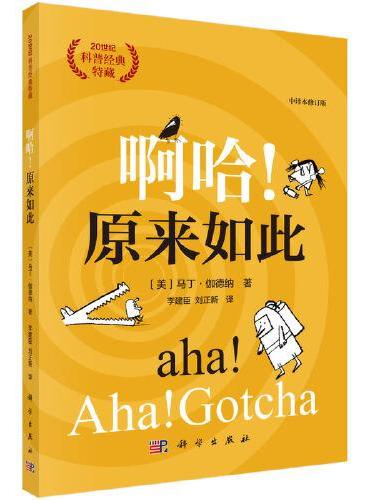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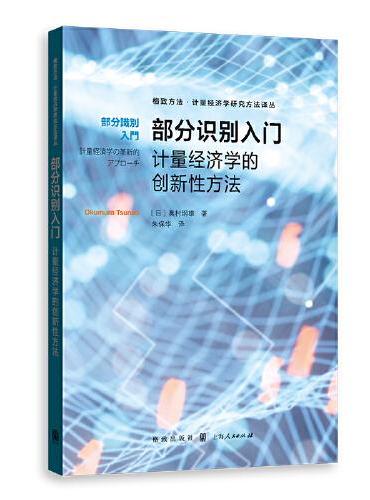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 編輯推薦: |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宪益舅舅百岁祭
我写了我眼中、我心里的舅舅。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们是实实在在的。
尘世中,他的不同凡响、他伟大而纯粹的人格常常会使我们自惭。
赵蘅笔下的杨宪益,自然地流露出一分大师的气质;一分老人的温柔;以及一分文字难以描绘的温暖。杨宪益大师伟大的人格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这套丛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女士,以及著名画家、作家、杨宪益先生的外甥女赵蘅女士主编,共分《魂兮归来》《宪益舅舅百岁祭》《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去日苦多》《五味人生——杨宪益传》《金丝小巷忘年交》六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并展现了杨宪益先生沧桑坎坷的一生:丛书除完整地收录了杨宪益先生生前的译余作品外,还从妹妹杨苡、外甥女赵蘅,以及好友范玮丽的视角出发,展现了杨宪益先生在公众视野之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书中还公开了大量展示杨宪益先生生平事迹的照片,以及图片资料,许多珍贵的手迹都是首度公开出版,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
《魂兮归来》
|
| 內容簡介: |
|
《宪益舅舅百岁祭》的作者赵蘅写了她的眼中与心里的杨宪益舅舅,展示了尘世中,不同凡响的杨宪益。宪益舅舅百岁祭的内容大部分来源于赵蘅的个人日记和追记、赵蘅的现场速写,以及赵蘅倾注画里的文字。赵蘅将内容真实完整地辑录成册,给读者呈现出她眼里的杨宪益舅舅,感人至深。
|
| 關於作者: |
|
赵蘅,女,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曾获冰心儿童图书新作佳作奖。现任国际女艺术家理事会理事暨中国分会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 目錄:
|
01YouRaiseMeUp
08断蓬白发亦平安
22蓦然回首
28和宪益舅舅仙逝前的对话
36生活因你离去而改变
60组稿手记
65宪益舅舅,挥之不去的身影!
81思念
84雪祭
88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98译写年华
110杨宪益有一说一
116而今往事成遗迹
137龙年种树记
152伦敦杨宪益周年祭纪念会发言
154《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后记
156一个馆和一个人
183附录:
183《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南京
卧龙湖研讨会选编
230后记
|
| 內容試閱:
|
断蓬白发亦平安
为我的宪益舅舅画像
“断蓬”是舅舅的一首无题诗中用的词。母亲说太棒了,瞩我用上。舅舅自己说“亦平安”前添上两个仄声念起来就好听了。我想起了舅舅已变得雪白的头发。
七言律诗写于今年的3月4日,这时他刚从五棵松外文局商品单元房搬到小金丝胡同6号。我的表妹、舅舅的小女儿杨炽夫妇翻盖了这幢足以成为这一带楷模的四和院
平房,它比邻前后海,过往银锭桥,地处尚能保留一些老北京风貌的区域。据说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学大家梁思成先生的女弟子,她将施工过程拍摄成册,怪不得常会
吸引洋人旅游者来叩门参观。
这是舅舅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诗的后四句是:“独身宛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莫怪巷深难觅迹,人生何处不相
逢。”虽然还流露出一点感伤,毕竟是回归了失去很久的天伦生活。也让所有惦记他的亲友们,从此不用再担心他的安危,像他独居五棵松一年时那样的状况。至于
对这条胡同的形容,他一点不夸张。我第一次骑车来探访,就七拐八拐走了弯路。回家也诌了一首五言古诗抒发印象。自知古文底薄,请教敏如姨妈修正了一下。有
四句我颇为得意:“钟鼓楼远望,邻家鸽飞翔。”“国母多寂寞,阿舅解愁肠。”
舅舅在小金丝胡同新居一连写了五六首诗。越写他的情绪越积极乐观,他写诗从来是信手拈来又直面现实。总是他的大妹妹,我的姨妈为第一位收藏者,然后再转告已翘首待看的小妹妹。住在南京的我母亲又总爱传送友人,她把舅舅的自传放在枕边,这是她的一份骄傲。
我的舅母戴乃迭于1999年秋天去世,生前她有长达十年的从忧郁到衰竭的煎熬。而我的舅舅也苦守了病妻十年。这对他们这样的荣辱患难半个多世纪、仍恩爱如初
的夫妻,无疑是非常残酷的折磨。如果再记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活趋于安定祥和、译著迭出,频频出访,更不必说国家给予的各种荣衔。对比他们
曾有这一段不算短的好日子,我更感到反差强烈地难以接受。那时两人对饮是从每天的傍晚开始,这意味着书房里的打字机为主人服务了一天,可以暂时歇歇了。常
会加入好酒好文的朋友们,男主人越喝越幽默,女主人越喝越直率得令人汗颜。百万庄宿舍那不大的客厅里笑声不断,舅舅更是妙语成珠。有一次他讲起在日本学茶
道的经历,说着说着竟下跪到地毯上模仿起来。而我作为晚辈亲戚只会在一旁傻乐。现在重新回味,悟出那是他们一起度过劫难后,难得的一段精神释放的快乐时
光。自从舅母病后,舅舅先是劝阻她少喝,后来他偷偷往酒里兑凉开水,越兑越多。舅母喝出不是酒“抗议”过,却经不住丈夫的爱护。渐渐这客厅里完全变成舅舅
一个人独饮了。舅母照旧坐在他的对面,但已不再会风趣谈笑,她终究对自己在中国所受到的苦难能够表达了,用她的方式。偶尔吐出几句英文,或对来看她的人张
冠李戴。舅舅只得在一旁默默苦笑。
搬到友谊宾馆后,我和舅舅单独聊天的次数变得多起来。我就住在对街,保姆走了,我有时会多陪舅舅坐一会儿。我知
道他并不喜欢这里,像与世隔绝似的。他写过四首迁居诗作自嘲过。我也知道白天他多操劳,主外又主内,要服侍病人,还得时时刻刻留神,生怕舅母有个什么闪
失。有一回客人问他在做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很快回答:“做家务。”有几次我看见他在叠舅母的晾干的衣物,虽然叠的不大像样。早年那么喜爱旅行的舅舅已变得
“畏远行”了。他辞谢了几乎所有的出访邀请,即使1994年到香港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都心不踏实,写下了:“家有仙妻常卧病,身无神术起沉疴。”的诗句。
这会儿舅母已早早被搀进屋睡下,舅舅总可以喘口气了吧。冬天这宾馆式的公寓里弥漫着热烘烘的暖气,夏天窗外那浓密深色的树叶会在晚风里发出沙
沙声响,一切是那么的宁静,使人暂时忘掉不幸。我们什么都谈,但他从来不吐露自己的内心有多惆怅。他的思绪依然很广阔,我讲的各种新闻其实他都知道。他依
然好忧国忧民,从青年时代就这样。他不属于那种“穷则思变”,他是富家子弟,却真正要爱国!这辈子惹出了多少麻烦也终不悔。而我在舅舅面前,没有当晚辈的
怯懦,因为他丝毫没有说教的口吻,他从来是平等的、和善的,有时还重复我突然冒出来的什么词儿,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我最爱和他谈保护古迹,一起谴责眼下越
来越盛行的拆风怪象,比如南京的砍树。他说北京已不像北京了,外国朋友觉得北京不再好玩儿。他还谈文学前辈的生平轶事,记性好极了。一次他非常公允地把自
己和同辈大家比较长短。还有一次他把自己写钱钟书的手稿给我看,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舅舅的手稿。他的文章总是一遍写完,令向来写作迟缓的我羡慕不已。有时
我们也谈艺术,我发现他好像更喜欢现代写意的风格。当我跟他谈自己打算要做的这事那事时,他耐心听着,吸烟或呷一口酒,有问必答。我写的、我画的东西到了
舅舅手里,他都是马上看完,还直率地指出其中的毛病。每次和他聊天真是受益匪浅,我都有回家写追记的冲动。可惜我总是忙忙碌碌,很想为舅舅、舅母画幅油画
肖像,都没能如愿。现在我很后悔在舅舅最需要帮助之时,自己没有腾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他过街散散步,或是多做几个好菜。
舅母走后当天,单位来人与舅舅商量办后事。舅舅明确表示:“乃迭不在了,我不能再住在宾馆里,这是她的待遇。后事从简,不要骨灰,不开会,这也是乃迭的意思。”我在外屋听了眼泪直往外涌。不由得想起20世纪60年代头几年的情景。
1960
年我报考中央美院附中,就住在舅舅刚搬来的宅院里。一天下午我从考场出来,在胡同里迷了路,夜里才找到家,他就站在院门口等我。事后我母亲告诉我,他看我
已回来,就小声说:“不要责怪她。”后来也是舅舅亲自从北京拍来电报通知我考上的消息。我想,在舅舅的眼里,我这个他小妹妹的老二、小名叫小采的女孩就是
爱画画,和她妈一样。附中住校期间差不多每个周末我都来舅舅家,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尽管舅舅他们有二等供应,但他视之为“特权”并不喜欢。饭桌上出现了窝
头,舅母要求减薪,一周只见到一次红烧肉。有一天,舅舅领着我和表哥、表妹们一起去看第二十六届乒乓球赛。不记得是谁跟谁打的了,反正中国乒乓队员个个打
得特别出色,第一次赢得全部冠军,大家也从未有过的这样投入热情。我们坐在东郊体育馆的看台上,赛场间隙时,舅舅发给每个孩子一份夹黄油的面包片。多少年
过去了我仍记得它诱人的香味。
最近才听表妹说她所以选择老式宅院安家,是想给小儿一个能够刨土挖坑、上房玩耍的童年生活环境。我们都讨厌如今城市
里布满洋灰大厦。她怀念自己小时候在八宝坑船板胡同度过的幸福时光,和那两棵槐树,一棵枣树。而我的记忆里是满院子的地砖,冬天晾出刚洗过的衣服,立刻会
冻得硬邦邦像盔甲似的铁片。这个幽静的四和院里,常会听见年轻的舅母从南厢房里发出“嗒嗒嗒……”的打字声。现在才了解舅舅和她在那一时期共同翻译了《奥
德修纪》《罗兰之歌》。1964年还完成了《红楼梦》译本中一百回的草稿。那时我已毕业了,而舅舅一家只住两三年又搬回外文局宿舍,这般折腾的缘由我到今
天读了舅舅的新近出版的自传才弄明白。这只是他一生所受到的种种猜疑诬告的一小段插曲罢了。
“文革”中我在乡下自顾不暇,很长时间没有舅舅、舅母
的消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遭受过牢狱之苦,我的表哥、表妹们也发落南北。这些还是事后父亲写信告诉我的呢。1972年舅舅先于舅母出狱,我也很快由东北
干校获准来京探亲,这是“文革”以来我第一次见到舅舅。半百挂零的他已变得憔悴苍老,头发不仅花白,还因发质太缺营养,新长出来的头发直愣愣的像怒发冲冠
似的。那些日子我住在他家,一天,我用一张小纸片给他勾了张半素描式的速写,画里的舅舅穿着半旧的白色短袖老头衫,光着脖子昂着头,足以表现那个特殊年
代。他很喜欢这张画,还说画得多像谢富治。保留了很长时间,一搬家就难讲还有没有了。现在我真想再看到它,因为那毕竟是舅舅中年时期,又是出狱后唯一的画
像啊!
1996年我应邀去巴黎国际艺术城,临出国前舅舅一再问我需不需要钱,他说他有,没有问题。我的脸顿时红了。长这么大从没拿过舅舅的钱,我
知道他和舅母多年搞翻译并不拿稿费,他没有什么家底,过去的那个富室望族早已破产了。但他真的为我有机会出国而高兴,他想帮助我,那么恳切。
同年的一个深秋早晨,我在伦敦国家画廊门前,终于一次拨通了舅舅的北京电话,“喂?”是熟悉的舅舅声音,隔着千山万水还这么清晰。我激动极了,赶紧接上说:
“我是小采,我在伦敦,你和舅母近来好吗?”“我们挺好。”他回答,语气跟在北京时一样平缓。他不会奇怪我走了这么远,对于历经人生磨难的舅舅来说,这世
界发生什么翻江倒海的事,他都依然泰然处之。即便我告诉他,我马上可以看到他年轻时见过的大师原作,他也只是说:“那好,那好。”也许我提起他送给母亲的
印象派画册的事,他都会这样说:“有这回事。很久了,我不大记得了。”他不知道这四大本封皮已破损的画册早已传给了我。母亲说那是舅舅留学时,在欧洲旅行
中特地买来邮寄到天津的,为了鼓励她学画。母亲在中西女校毕业时,舅舅又遥购了五十朵白玫瑰来祝贺,那一年母亲十九岁。她那张被鲜花簇拥的美丽相片,长年
悬挂在南京住宅的客厅里,令所有见过的人赞叹不绝。印象派画册是1936年的版本,不知是否算得上将印象画派引入中国的早期记录。
我外公去世很早。我的外婆眼高志远,使舅舅和他的两个妹妹有幸在少年时代受到第一流的中西文化启蒙。舅舅与生俱来的天赋得以保护发展。所以当他一走进牛津校园,就以品
学兼优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他作为中国学会主席,也迷倒了一个剑桥大学圣安妮学院的女生格莱迪斯,这个出生在中国的美貌优雅的英格兰姑娘,后来在中国最危
难的时候成了我的舅母。一天,我为自己的一篇文章去拜访舅舅,想问问当萧乾伯伯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在英国采访伦敦大轰炸时,他在哪儿?我这才了解到,原来
他携未婚妻幸亏刚离开。坏消息是他们登船第一天下午通过收音机得知的。这次谈话他还讲了那次回国的路线为什么要绕到大西洋,为什么要从加拿大乘船等等。回
家我找来地图认真查看他们的航线。那时我还没读到舅舅的自传,不知道他真的遭遇到日本兵的野蛮盘查。如此惊心动魄的险情在他的一生里遇到许许多多,然而你
在他的书中只看到轻松诙谐的笔调。你想紧张又不感到累,想难过又觉得可笑。这就是我舅舅的性格魅力。
写到这里,我该向读者说说舅舅最近生病的事了。
这么多年几乎没听说舅舅生过病。他的长寿秘诀:“抽烟、喝酒、不运动”成了一句最具幽默的妙语。所以当敏如姨妈打来电话告诉我,舅舅早上吐了的消息,我吃了一惊。姨妈很客气,她知道我忙。然而我已经意识到这回舅舅病得不轻。
我
又一次当了“救火员”。但不同以往,只是传递点东西,顶多去探视住院的舅母。这回我得去找医生,因为高龄的舅舅头晕腿软已无法出门了。可到哪儿去找能够出
诊的大夫呢?感谢114服务帮我寻到了积水潭医院的社医保健科,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三位白衣天使蹬门行医,又有李主任亲自挂帅,舅舅有救了!
这天瞧病他非常顺从,不再那么满不在乎总让姨妈惦念不已。我守着他,因为需要连续挂两瓶水。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们俩,从高高的本色木板房梁上垂下一盏“宜家”的大灯。北墙上悬挂着王世襄先生的两行赠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