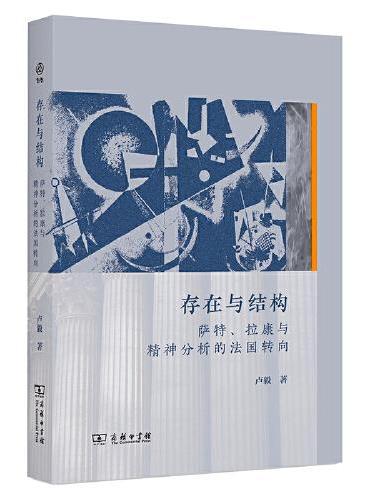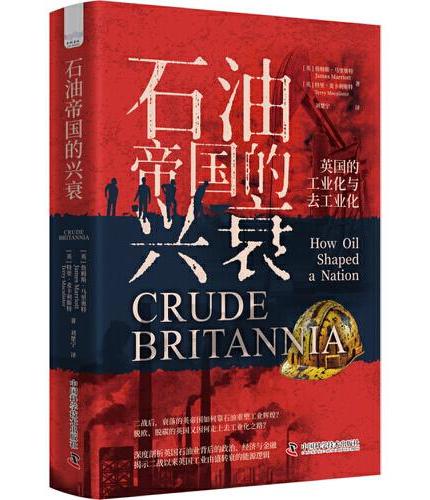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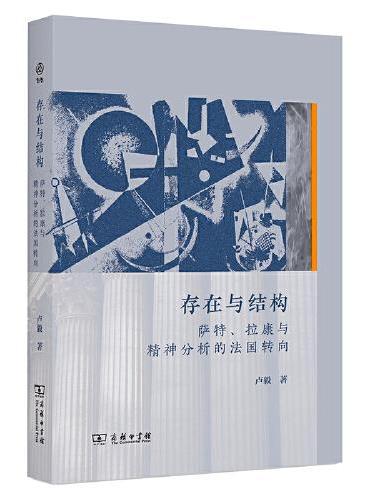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NT$
240.0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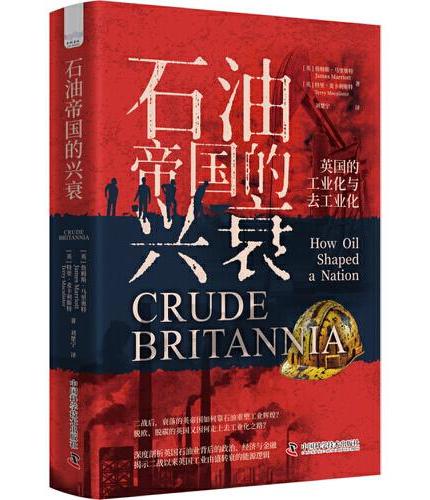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NT$
445.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学(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50.0
|
| 編輯推薦: |
脚步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线索,
不断缝补被时空割裂的一切神迹,一切文明、信仰与日常生活。
旅行,从不应只是看景、观光;
旅行,是生活方式的思考与转换,是地域景观背后的文明脉搏的触碰与体验。
《Across穿越》人文旅行杂志封面故事首次结集出版,
穿越阿尔及利亚、南非、古巴、爪哇、不丹、印度、墨西哥、缅甸八国,追寻地域奇观背后的文明脉络。
|
| 內容簡介: |
《神的孩子都旅行》
————————————————
寻找被时空割裂的文明印痕,以脚步丈量人性与神性的距离。
《Across穿越》杂志人文旅行丛书,撷取八篇敏锐而充满情感力量的文化游记,让精神跟上你的脚步。杂志每一期都派出本刊记者与摄影师历时数周深入不同国家进行体验、采访、考察,最终奉献给读者与众不同的、极具人文色彩的旅行记录。
“整个民族在水边沉思,千万个孤独从人群中升起。”
《神的孩子都旅行》是关于信仰的。这些地方留给我们的强烈印象归根结底来自一种坚韧的性格,它调和了贫穷与富足、痛苦与欢乐、混乱与和谐,使更高的图景屹立于纷繁冗乱的俗世之上。培植这种性格的土壤即是信仰,无论它归于政治或是宗教。
|
| 關於作者: |
|
《Across穿越》是《南方人物周刊》旗下的人文地理杂志,创刊近四年,强调精神内涵的传达,旨在推广具有人文深度的旅行。“穿越”所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生活方式的思考与转换,希望通过这种行走的串联切入地域景观背后的文明脉搏。
|
| 目錄:
|
序
※※※一人一世界※※※
※【阿尔及利亚】知天命之年
头巾的漩涡
不祥的礼物
枯萎的废墟
乖男孩的微笑
微醺的夜晚
※【南非】好望角的凝望
内城冒险
种族藩篱
殖民面具
开普敦牢笼
好望角灯塔
※【古巴】缓缓而至的革命黄昏
哈瓦那的客厅马拉贡
“为了革命胜利,向首都进军!”
“古巴制造,美国进口”
底特律的怀旧博物馆
供出租的“雪佛莱芭蕾小姐”
“你干得很好,菲德尔”
菜单由海峡对岸决定的餐厅
“文化体验”
哈瓦那的最后一个黄昏
※【爪哇】遗忘在爪哇国
雅加达,斋月前夜
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
探底硫磺火山
处处有神迹
【不丹】如果幸福是一个国度
不丹没有“百姓”
简单才是最不简单的
不入虎穴,焉得仁波切?
“疯僧”引发的不丹四大怪
Hello,不丹“中南海”
至圣之地
【印度】车轮上的国度
“百年纪念”特快:新德里(NewDelhi)—阿姆利则(Amritsar)
8104号快车:瓦拉纳西(Varanasi)—格雅(Gaya)
登山火车:大吉岭(Darjeeling)—古姆(Ghum)
“首都”特快:新德里(NewDelhi)—孟买(Mumbai)
【伊朗】越禁忌,越美丽
序幕:头巾
王朝的背影
倒车,请注意
“半个天下”的甜梦
酒精与爱情
天堂
夜莺的占卜
海角天涯
尾声
【缅甸】阴与晴
多重仰光
曼德勒混响
|
| 內容試閱:
|
【哈瓦那的最后一个黄昏】
这是我在哈瓦那的最后一个黄昏。穿着初夏的衣裳,我从总统饭店出来,向12月的马拉贡大道北行而去。马拉贡大道和G街交界处那幢玻璃好像随时准备稀里哗啦掉落下来的大楼,是古巴外交部。门口没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只有一个腆着大肚子,一直在看手机的草绿军装大叔寂寥地守在门口。那些在建设时设想的喷泉或小池子,现在变成了一个个盛放垃圾的大型容器。
我对外交部对面的何塞·马蒂体育场(EstadioJoséMartí)异常感兴趣,每天长日将近时,总会去那里转一转。这座当时想给人带来强硬未来感的苏联共产主义风格体育场,现在就像一个被早已奔往外星球的飞船永久遗弃的港口。顶篷颇具科幻气息的看台早已进入风烛残年,周边墙上用油漆刷着“摇摇欲坠”的字样,提醒人们慎入。然而,一个年轻人一溜烟钻进看台下的一个破洞,他们把它作了更衣室,里面有粪便的气味。青年迅速更完衣,加入足球场上的战团。
此时,何塞·马蒂体育场的近处弥漫着儿童学骑自行车的叮咚铃声,拳击手出击的砰砰声,女孩们捉迷藏的欢叫声,男孩们挥棒击球的梆梆声;稍远处,是小伙子们在足球场的奔跑呼喊声;再远处,就是来自佛罗里达海峡的浪花越过防汛墙,在人行道上摔得粉碎的痛呼声。而那些孤独地绕着足球场的长跑者是沉默的,他们以近乎一致的间隔时间,一次又一次打你身边经过。大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并不需要观众鼓掌或喝彩,看台上也的确没法坐人,就好像这个国家一般,在加勒比海这个舞台上孤独地表演着。再过十来分钟,我在古巴的最后一抹夕阳就会永久消逝。
我珍惜此刻的哈瓦那,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乐园。它不仅仅是一个20度就像到了冬天,人民每天排队买面包,波浪平均高过防汛堤三倍,年轻男子想着乘慢船偷渡,漂亮女孩难免要被当作是妓女的城市。
胡安这样的年轻一辈都觉得古巴需要一个像邓小平一样的领导者,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带领古巴进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时代。他们通常就把话说到这里,但我知道,这个领导者不会是劳尔。果然,2013年2月,劳尔宣布自己将在2018年退休。其继任者目前看来可能不是卡斯特罗家族成员,这也意味着美国和古巴走回修好的谈判桌指日可待,因为美国取消古巴禁运的前提,就是古巴不在卡斯特罗家族治下。如果真是这样,古巴就有可能重新成为美国的后院。马拉贡大道是否将成为又一条迈阿密的海洋大道?马拉贡旁那些几乎可以听得到墙粉剥落的面海老宅,是否将成为一座座豪华酒店或高级住宅?巴拉德罗海滩是否就此一如终日沸沸扬扬的迈阿密南海滩,海龟也不会再回到古巴下蛋?
我拦下了一辆正好从我身边经过的Cocotaxi,和马拉贡平行着,我们最后一次向哈瓦那老城进发。我戴上耳机,找到“美景俱乐部”那些老枪们的歌,是的,这是此刻我最需要的告别曲——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经济改革,不论过去,亦不谈将来。我要去老歌手依伯拉海姆·费热(IbrahimFerrer)曾挽着太太徜徉过的那条哈瓦那老街:镂空拉花的铁门,粉蓝斑驳的外墙,不知所措的流浪狗,坐着或站在门口的邻人……
依伯拉海姆唱着:“送你两朵栀子花,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仰慕你,我的爱人,把爱心给它们吧,我俩心心相印……”我的视野就这样无可挽回地从凋零的街景转向了流金的舞台。
【枯萎的废墟】
1878年,法国的葡萄园因虫害而趋于凋零,阿尔及利亚成了替补,开始大量种植葡萄。而在近两千年前,罗马人曾命令这里的土地长出燕麦和橄榄树。
殖民地的历史总是一个悲剧连着另一个悲剧。在罗马人之前是迦太基人的统治,在罗马人之后,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的铁蹄又接踵而来——“阿尔及尔这个海盗出没的都市,在紧紧束缚着它的高大城墙里乱哄哄地生活着”。15世纪时,西班牙人在阿尔及尔城外建造了许多用于瞭望和炮击的小型堡垒,阿尔及利亚人没有能力摧毁他们,一度把四个来自咸海之滨的土耳其海盗当作救星,其中的首领阿鲁杰想要凭借自己的海上实力成为阿尔及尔的苏丹,最终在陆战中受挫,想要从奥兰(Oran)逃回大海,却殒命沙场。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复杂的战场,南部是沙漠,北部是海,如今各有各的浪漫。在海和沙漠之间,是路边无尽的旷野,这个国家满是褶皱沟坎的肉体——村庄、麦田、草地、牛羊、赤裸的岩石、弯曲狭窄的路、高低起伏的雪山——各种排列组合,一点都不诗意。在十字路口等车的男人,向来往的车辆吹响口哨,偶有两个少年,在午后撑开店铺的门面。
争夺阿尔及利亚的血腥故事,多数就这样没入生活的灰烬,或者成为当地人郊游的地点。比如法国城和土耳其行宫,总统将阿尔及尔郊外的那一大片殖民遗迹改建成公园、网球场、宾馆和洗浴中心,沙滩开放,游艇进驻,鸽子飞来,用以忘记法兰西。
古罗马的废墟表面上得到了最大的礼遇,被辟为文物保护地,其实却人迹罕至。在杰米拉(Djemila)和提姆加德(Timgad),漫山都是石头垒砌的城邦和冬季的枯树相依为命,就连天上也只有寥寥几缕白云,到中午才多了起来。枯萎的不知疲倦的草和风干的蒲公英还探着头,有力地摇曳,矮一点的植物也活着,比如黄色、紫色的小花,以及另一种盛开着四瓣白叶的花朵,仿佛一片十字架,听着阿訇的声音从旁边的市镇飘来。
殊不知在杰米拉,古罗马喷泉和市场里用作度量衡的桌子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现存实物。方圆几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人,司机突然来了表演欲,把围巾往后一拨,冲我们喊道:“嘿,客官要来点土豆吗?”
只有少数本地人在这里打发时间,坐在废墟上发呆、看报、谈情说爱。这些僻静的地方倒是情侣们的好去处,他们挽着胳膊,并不避嫌。我终于看到有姑娘扎着活泼的马尾,撒娇地喊着前面的恋人。
海边的蒂巴萨(Tipasa)保存不及前两者,人气却更旺,距离阿尔及尔只有70千米。因为海浪的侵蚀,石头上到处是坑洞和从洞里长出的草。加缪曾经最喜欢在此散步——如今的人气恐怕并不是因为他,阿尔及利亚人把法国人赶走之际,也赶走了加缪的幽灵。
“春天,蒂巴萨住满了神衹,它们说着话儿,在阳光和苦艾的气味中,在披挂着银甲的大海上,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在铺满了鲜花的废墟上,在沸滚于乱石堆里的光亮中。”加缪正是在这里酝酿了被萨特称作“地中海式”的理想主义,这也埋下了两人日后争论的伏笔——萨特是哲学家,他的存在主义是沉浸到时代当中,以“荒谬”为起点,追问人类如何从野蛮抵达意义,他后期坚持认为,暴力和共产主义是通往实质性变革的必经之路;而加缪是艺术家,他坚持道德原则,“无节制地爱”,难以认同任何重要的变革力量,在他这里,“荒谬”是无法超越的生命经验,是人类的全部生活,“并非所有人都能与历史一致”。
加缪与萨特的分歧是20世纪知识界的一段传奇故事。至今,人类思想的进展依然停留在两人分手的路口,并未走得更远。
驶离这些废墟,往山上去。前一阵才下过大雪,我们决定去高处寻它。有的地表已经露出裸石,有的雪却还紧紧凑在一起,出汗一样往外沁出极细的水珠,在别处流出细水,汇到路边,沿着大路一路向前。阳光掉在里面,反射出银色的光,跟着车子的速度狂奔如梭。几道水流一经汇合,便有了水势,混着泥巴,变得混浊,遇到山涧,就跳下去。直到成为小河,才又重新平缓、清澈起来。这些山上来水的流向正是罗马古城,流进那里的厕所,供人们洗手;流进那里的澡堂,供人们桑拿。或者也会流进昔日保卫故土的战士们的嘴里——中部的阿特拉斯山区是柏柏尔人的大本营,他们无数次从山上冲杀下来,对抗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法国人,令对手十分头痛。
如今的柏柏尔人依然惯于穿着沙漠色的长袍,脸如尘土,背影佝偻,把身体埋进斗篷。他们是最沉默的路人,低头走过,几乎很少见到他们交谈。最初法国人看到他们,也十分鄙夷,称他们是“赶骆驼的怪人,喝骆驼的奶,吃骆驼肉干,既不知道谷物,也不知道水果,更不知道蔬菜或鱼”。
我是一个糟糕的搭讪者,这些沉默而威严的人才是这里最初的主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