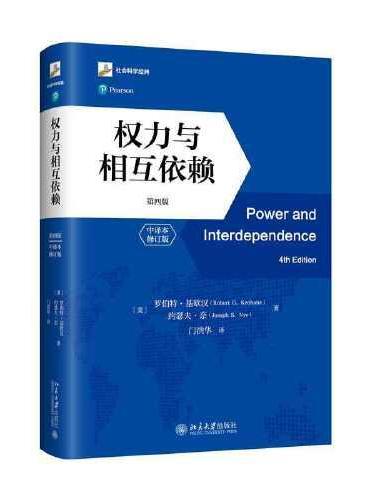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民法典1000问
》
售價:NT$
454.0

《
国术健身 易筋经
》
售價:NT$
152.0

《
古罗马800年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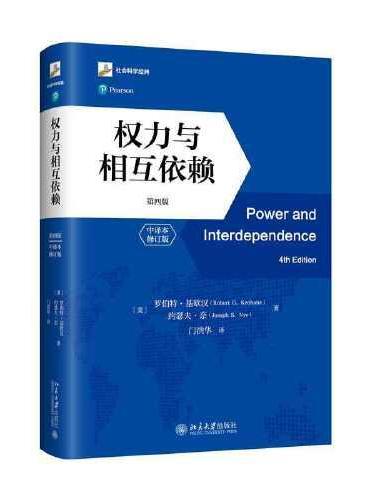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控制权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管理与传承
》
售價:NT$
398.0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
》
售價:NT$
762.0

《
利他主义的生意:偏爱“非理性”的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推荐读物!)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我们居住的城市是从何时起变得如此平凡庸俗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座座大城市里是雷同的水泥盒子;就连偏远的古镇和山村,也免不了“过度开发”的媚俗。而这些,都集中在一个我们非常熟悉,却从来没有想要去了解过的名词上——建筑。
建筑,既不是图纸上冷冰冰的线条和数据,也不是市场上昂贵无比的商品。它是城市文化最直白的体现,它和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也是你最该读懂的东西。读懂建筑,你会了解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理性与感性的融合;读懂建筑史,你会感受到植根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性格如何体现,如何影响着历史的源流。
中国建筑学、建筑史学知名学者王贵祥以今喻古,畅谈所有你不知道而又想知道的,建筑的那些事儿。
|
| 內容簡介: |
“鵩上承尘才一日,鹤归华表已千年。”
到今天为止,中国建筑走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历程:自上古时代开始,我们就拥有一代代辉煌灿烂的建筑遗产;到了近代,一批批建筑家、建筑学人又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但如今,“建筑”这个词似乎只与节节攀升的房价和丑不可言的“地标楼”联系在一起。而它的真意,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重新了解建筑,了解它如何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源流变化,体现出民族性格的的发展变迁。读懂建筑,读懂建筑史,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本书收录中国建筑学、建筑史学知名学者王贵祥自世纪之交以来,有关建筑理论、文物保护、建筑历史研究的随笔与感悟。在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哲们致以敬意的同时,亦对当下有志投身建筑事业的年轻人寄予殷切的期望。
|
| 關於作者: |
|
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1981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建筑学院分委会主席,并兼任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古建园林分会副会长、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出版大量专著和译著,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
| 目錄:
|
卷一 中国建筑
卷一之一 中国人的建筑十灯
卷一之二 宁波保国寺大殿礼赞
卷一之三 房屋与城市
卷二 学界先驱
卷二之一 建筑学专业早期中国留美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教育
卷二之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早期中国建筑留学生的几件史料
卷二之三(上篇) 驳《新京报》记者谬评
卷二之三(下篇) 再驳《新京报》记者谬评
卷三 建筑史学
卷三之一 关于中国建筑史研究分期的几点拙见
卷三之二 关于建筑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卷三之三 中国建筑史研究仍然有相当广阔的拓展空间
卷四 遗产保护
卷四之一 明清北京紫禁城的保护历史与现状
卷四之二 关于文物古建筑保护的几点思考
卷四之三 历史建筑保护三议
卷五 建筑评论
卷五之一 世纪之交——两难中的北京新建筑
卷五之二 中国建筑的传统及现代意味
卷五之三 风水观念的非理性层面剖析
卷六 理论探讨
卷六之一 建筑理论: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卷六之二 建筑美的哲学思辨
卷六之三 建筑理论、建筑史与维特鲁威《建筑十书》
卷七 无病闲吟
卷七之一 问学四箴
卷七之二 闲来有吟
卷七之三 晋游小记
后记
|
| 內容試閱:
|
世纪之交——两难中的北京新建筑(节选)
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再来看看在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建筑思想发展的历史好像画了一个圆圈。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与一个世纪之前同样的困惑与徘徊的境地。人们对新世纪的新的建筑的种种机遇与可能翘首以盼,人们又对世纪之交的建筑现状充满疑惑与忧虑。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建筑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境况一样,中国以及北京建筑的发展,同样处于一种“地方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与尴尬的两难境地。像19世纪末时人们的心态一样,人们争辩,人们探索,人们也顿足捶胸,痛心疾首。‘
事实上,对80年代以来兴建的北京新建筑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其中既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创新与探索,又有许多使人无以言对的无奈与悲哀。一方面,北京在发展,北京的城市面貌与建筑形象日新月异,使许多渴望“现代化”的人们兴奋不已;另一方面,作为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城的历史价值与传统建筑与城市风貌却在无可抗拒的“现代化”的浪潮下日益消失,而人们所孜孜以求的能够代表我们这一伟大时代的,与北京这样一座伟大国家的历史古都的地位相称的“时代风格”的经典性建筑或建筑组群,却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也使许多有识之士扼腕而叹。
80年代以来,确实是北京建设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是建筑师们施展身手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在林林总总的新建筑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设计独到的作品,如80年代以来陆续建造的北京国际饭店建筑、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建筑及亚运村体育场馆建筑等;以及一些富于探索性的作品,如菊儿胡同改造工程与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等。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由国外或港台建筑师设计的富于特色的建筑,如香山饭店、建国饭店等,都使当时的北京人耳目为之一新。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近20年的北京建筑发展,确实存在许多令建筑界的有识同仁们不敢苟同之处。甚至,在许多方面,令大多数关注建筑理论与建筑发展的人们除了叹息而外,几乎无言以对。
首先,在总体的城市发展战略上,或者说在实际操作上,让人们一直感觉不到有一个思路清晰的目标与步骤,而在实际的设计与建设中,更缺乏现代城市设计的概念。一方面,经过了近20年的大规模建设,我们仍然很难见到几处规模较大的能够代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与北京特色的新建筑街区或新城市片断。新建筑是散置的,遍地开花的,如摊煎饼一样向四处漫延的。虽然,偶尔不乏有个别出彩之作,但是却被淹没在参差不齐的大量平庸粗陋之作的海洋之中,形不成一个可以令人驻足或留连的街区或城市片断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利益或其他因素的驱动,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旧城区的改造显得过于急迫而缺乏远见。应该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北京是一个屹立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首都;另一方面则在于北京的悠久历史与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北京作为一个古老都城的保存与保护,是一个久已被世人所瞩目的大课题。因此,需要多花费一些时日,进行严肃缜密的研究与探索。而从建筑科学的角度讲,一座古城的保存与保护,不仅仅在于对其中个别重要古建筑的保护,而且在于对整个城市的空间特征、街道肌理、局部环境甚至民俗文化等等的保存与保护。
例如,一般北京人对于王府井或东单、西单这样一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商业街道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许多老北京人把到这些老街购物作为假日休闲的享受之一。离开北京多年的人,也以到这些老街一走,而聊补岁月流逝造成的心灵缺憾。保留这些著名历史商业街的基本空间尺度与街道形态,就是保存了一段活的北京历史,也保存了普通北京人可以徜徉回味的一个去处。然而,近些年的大规模改建,特别是街道的拓宽、建筑体量与室内空间的加大,尤其是新建的具有超大体量与规模的东方广场建筑组团的落成,使原本修长狭促的老街,一夜之间,竟变得开阔、宏伟而短促,使人惶然置身于一个现代化的崭新城市,虽然不乏新鲜与方便之处,但对于大多数曾经光顾过这些街区的人们来说,除了陌生、疏远的感觉之外,那庞大压抑的建筑体量与宽展宏阔的街道空间,只会使光顾其间的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
试想,置身于这样一个几乎在任何大都市中都可以见到的现代化街区中,即使人流如旧,其外在的环境却早已恍若隔世,熟悉它的人们还能够期待重新寻找到老北京商业街区特有的那种树老楼低、人流熙攘、万头攒动、擦肩摩踵的拥挤、繁闹而亲切的场面吗?而那种几乎在每座现代大商厦都可以见到的大型而摩登的室内外空间,真的能够取代往日王府井大街特有的那种适度狭促而富于传统意韵的老街与店铺对人们所构成的心理吸引与购物享受吗?
记得笔者初次在新开的王府井大街上漫步时,恰好听到一位擦肩而过的不知姓名的中年男士自言自语地轻声叹道:“唉,老北京没了”,不由引起笔者的同感。我想这叹惋,一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个绵延了百余年的繁华老街,何以就不能够继续述说它的市井故事呢?据说,最近刚刚在上海落成了一条按照本世纪初的面貌建造的低矮而风格传统的老式街道,以满足人们怀旧的心境。是不是将来哪一天,人们又会在北京城外的什么地方,照着老照片的样子,再造一条老式的王府井大街呢?若果真会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其实,在许多现代都市中,都往往有意识地保留一些具有历史遗韵的老街。伦敦的soho、巴黎的拉丁区都是这类既有悠久历史,又有市井意韵的老街区。直到今日,在巴黎拉丁区的老式小咖啡馆中消磨时光,以体验巴尔扎克的灵感源泉,仍然是法国文学青年的一大乐事。日本东京在现代化的新宿区附近,仍然保留了一个成片的低矮而狭促的老街,而实际上,在老街上停留的购物人流密度要远比附近大商厦内的人流密度大,就十分形象地印证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我们要保存与保护的是历史文化、民俗传统与城市空间形态的记忆与延续。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街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而将一个古老的街区在基本保持原有空间风貌与历史韵味的基础上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到建筑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的方面,需要加以审慎的对待。
试想,如果我们将旧城改造的步伐放慢一些,把主要建设资金首先投放到北京旧城以外的新街区的建设与发展上,尽量通过将旧城中的人口吸引到经过认真规划与设计的,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着丰富而便捷的商业、交通及教育、服务条件的新区,用同样的甚至较少的资金,在旧城以外的什么地方,重新设计建造一个比新王府井大街更宽阔、更现代、更便捷、交通也更通畅方便的,或者也可以揉入更多一些民族风韵的大型步行街,而将旧城的整体改造再推延几十年,到那个时候,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与人民教育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相信会有更为恰当而合理的旧城改造思路与方案出现。而在城市发展急需资金的今天,我们能用同样的资金,既保存了旧城与旧街,又建造了一个真正的新城与新街,使北京多一些不同风味的购物休闲的去处,岂不是更为明智。而到许多年以后,保存与保护古都历史风貌与城市现代化的矛盾,就远没有现在这样尖锐,到那个时候,人们对旧城改造的思考与实践会从容与审慎得多。
其二,北京的许多新建筑,缺乏整体环境艺术的考虑。有时,就某一座单体建筑而言,其造型、材料、色彩还使人觉得略可搪塞,但将之与周围其他一些新造建筑放在一起来观察,就会使人有杂乱不堪、索然无味的感觉。每一座建筑似乎都是目中无人、桀骜不驯的样子,根本不考虑其所处的街区及周围建筑的空间、尺度与色彩环境。如位于东长安街上的交通部大楼与全国妇联及妇女活动中心大厦一组建筑,相互之间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细部尺度处理与色彩关系上,都使人有啼笑皆非的感觉。位于复兴门附近的相互毗邻的百盛购物中心与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大楼及原有的长途电话大楼,彼此之间也如心存芥蒂,相互傲视,互无关联。类似的例子几乎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起的建筑,都是以孤高自傲的单体出现的,很难见到一片能够相互联系成为一个体形与环境整体的建筑组群。如位于西二环上的金融街,原来是可以设计成为一组富于城市设计特色的完整而相互联系的建筑群,以形成一个较有特色的城市片断的。而实际的情形却是,每一座建筑各为一个独立不羁的完整个体,犹如一个个摆在小商摊上,呈一线排列的其形各异的矮敦敦的印章。这正如一位英国建筑师在对笔者谈起其对北京建筑的印象时所说的,中国人用的是方块字,所以建筑与建筑之间彼此独立,毫无关联;而西方人用的是字母拼音,建筑往往相互连贯成为一个个完整的富于空间与造型内涵的组团,并进而形成一些较完整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片断。虽然,他的结论有失偏颇,但现代中国人,似乎早已将古代中国艺术中“毫微向背”的理念扔到爪哇国去了。试想,如果一位中国书法家,将“故”字写成“古文”,将“掰”字写成“手分手”,或将“辩”字写成“辛言辛”,我们该作何感想呢?
其三,也许是出于建筑探索的原因,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具有象征性的新建筑。其实,就建筑学的本义而言,赋予建筑物以某种象征性内涵,使建筑内蕴有某种“意义”,本是十分正常的设计理念追求。许多优秀的现代建筑,就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勒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或贝聿铭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甚至解构主义建筑师彼得艾森曼的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象征性的创造,应该是自然而含蓄的,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然而,我们的一些新建筑,却总喜欢玩一些象征的手法,例如:西客站和海关大楼,代表了城市与国家的大门,就要不惜代价地造一个凌空飞架的门洞,上面还要加上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大屋顶或小亭子之类的东西,以标志出这是中国的或北京的“门户”。至于银行造成元宝的形式、通讯社造成笔头的形式,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有益的探索与恰到的推敲,但却总使人觉得太直白了一些。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交通中心建筑中,已经将火车站、地铁站、长途汽车站、城市电汽车总站等交通系统,与餐饮、娱乐、住宿、零售商店等服务功能,综合而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整体,建筑的外观已经不再重要,而建筑作为城市门户的象征性特征,也很难在这样的建筑中表达出来。可以说这些交通中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复合型的几乎无外部立面、无外观体量的空间综合体,却从根本上满足了交通中心建筑所特有的错综复杂的功能与空间需求。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对火车站这样的功能性建筑在象征性上的刻意追求,在建筑理念上,似乎已经比这些发达国家落后了许多年。
其四,在北京的建设史上,像一个幽灵一样徘徊了数十年的所谓“民族形式”问题,在近20年的建筑中,也曾以新的方式鼓噪一时。如果说,在50年代时,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与自信,对传统中国建筑形式与现代结构体系的结合,作了一些十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这在当时的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然而,在改革浪潮汹涌,国门洞开的80年代与90年代,各种新的建筑理念与建筑技术目不暇给,北京的建筑师们却无暇去探索符合时代精神与民族意蕴的现代建筑,而被人为地拖入了一个所谓“夺回古都风貌”的涡流之中。于是,一些素与传统建筑无缘的建筑师,忽然间关心起种种传统中国式的“亭子”与“帽子”来,甚或还为自己冠之以“后现代主义”的美称。在这些折衷主义与复古主义的大合唱中,如果说有些作品,如王府饭店,还略可归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探索,并且也有较缜密的造型推敲之外,大多数类似的作品却颇有一些“东拼西凑”的味道,如新大都饭店、台湾饭店等,在一个高耸而庞大的体量上,画蛇添足地加上一些造型琐碎、尺度狭小的各样亭子,实在有损传统中国建筑的伟大与深邃。
其五,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一些没有多少教育背景与民族自尊心的业主,在思想上的殖民地奴性特征又开始萌芽,而一些建筑师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也心甘情愿地以折衷主义的态度,去迎合业主的种种趣好,因而使一些具有“文化殖民主义”特征的粗制滥造的所谓“欧陆风情”的建筑应运而生。如果说,在这一类建筑中,还不乏有设计独到、推敲细密者,如东长安街上的恒基大厦、东二环路上的富华大厦等,其效果尚可以说差强人意。但大量模仿欧式传统风格的建筑,如某些在外立面上生硬地贴上一些欧洲传统柱式,或冠以穹顶、嵌以拱窗的作法,其粗制滥造的设计水平,几乎连19世纪欧洲折衷主义建筑的皮毛也没有学到。何况,其中既没有“现代”的气息,更没有“时代”的风韵,甚至连一点民族的自尊也丧失尽了。在理念上,这些建筑师连100年前的欧洲建筑师们还不如。19世纪末叶的那些提倡建筑应该体现“现代”风格,应该表现“时代精神”的欧洲建筑师们,如果知道在一个世纪之后,还会有人在异土他乡循着折衷主义建筑师们的脚印亦步亦趋,甚至比他们的前辈在设计技巧上拙劣得多,在九泉之下也会气歪了鼻子。
在此世纪之交的时候,笔者还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北京正在建设一座硕大无比的“世纪坛”,虽然,时下还无缘一睹这座世纪之坛的芳影,但可以想见创意者与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不过,使笔者感到有趣的是,这座具有世纪之交象征意义的建筑,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北京新建筑矛盾与尴尬的两难处境。其实,谁都知道,“坛庙”这种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典型形式,是一种与传统儒家的自然崇拜密切关联的礼仪、礼拜性建筑,是一种古代文化的历史遗存。北京有天、地、日、月、先蚕、先农等数坛之多,其中一些已亟待修缮保护,可惜因为资金匮乏而无从开展,却要斥巨资去建造一座无根、无脉,无所礼拜仪典依托的新坛。历史乎?现代乎?保护乎?创新乎?其中的矛盾与尴尬可以想见。
其实,北京新建筑的创作问题,归根结蒂仍然是一个建筑理念与建筑实践的关系问题。在建筑理念上,要兼顾古城保护与建筑创新两者的关系,要尽可能少地改造旧城以内的已有街区,并且,尽可能多地保存与保护古城北京固有的空间轮廓与街道肌理。在建筑实践中,既不能沉湎于所谓“民族风格”或“欧陆风情”之类的陈旧小把戏,也不能简单地追求什么“现代化”或“时代精神”。而是应当在立足于我们时代的与民族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力求有一些创造性的设计作品问世。
应该提倡建筑师在创作中要有一点文化的追求与体现,这包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淳厚深沉的北京地方文化的现代追求与体现;要追求一种真正的“现代”意蕴,这种现代感,不是简单地模仿或重复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建筑,更不是对传统中国建筑作简单的模仿与标贴,而是一种基于深厚的建筑设计功力基础上的某种崭新的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内涵文化底蕴的创造。
要强调有一点环境的意识,将建筑、建筑群、建筑周围的外部环境、城市片断,乃至整座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要引入生态建筑与生态城市的概念,使整座城市,使城市中建筑的室内与室外增加更多的绿色;同时,还要创造更好的城市周边环境,使城市周围的山水更清秀,有更多的林木,更多的水面,更多的花鸟,更为清新的大气环境与自然环境。
更重要的是,要用一个21世纪国际性大都市的标准来建设北京,要在整体解决城市交通、城市环境的基础上,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单体建筑,富有崭新的地方与时代气息,使建筑在造型与空间上有尽可能多的新意。同时,要通过城市设计,创造一些成片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使人能够赏心悦目的建筑组团、商业街区、居住小区或新的城市片断。
19世纪的欧洲建筑师在世纪末的困惑与焦虑中,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们为20世纪建筑的发展既奠定了基础,也构想了蓝图。其实,细想起来,20世纪的建筑师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实践了19世纪的建筑师们对于未来建筑的一些猜测与设想。在建筑理念上,20世纪的建筑师们还不敢说有多少前无古人的创造。现在,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我们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困惑与焦虑,我们也同样充满着对新世纪的向往与希冀,如何使我们的建筑,尽快地从目前的矛盾与尴尬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以一种充满希望与信心的心境去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到来,是每一个建筑师都十分关注的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东方的世纪,21世纪北京的城市与建筑发展,将会面临一个富于机遇与挑战的时代,21世纪的中国建筑师,尤其是北京建筑师,将会有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这些都应该加以十分珍惜。
作者简介:
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1981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建筑学院分委会主席,并兼任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古建园林分会副会长、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出版大量专著和译著,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