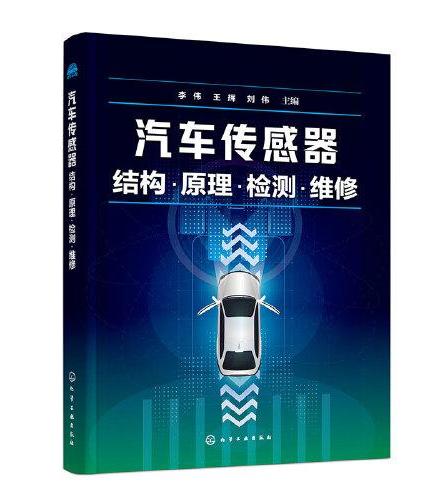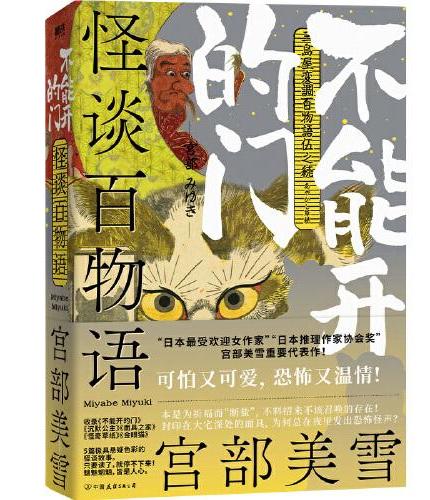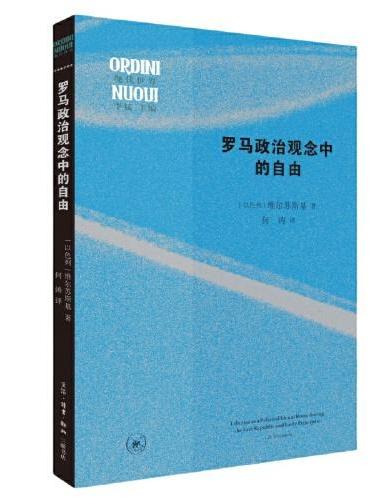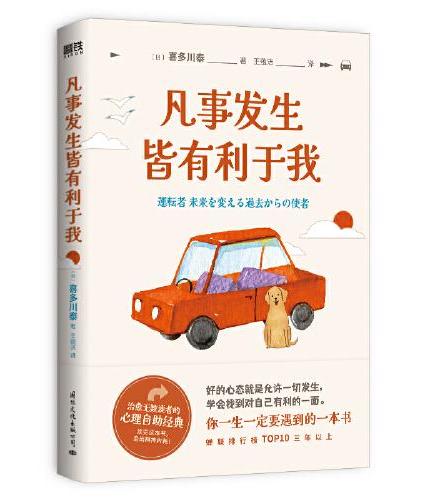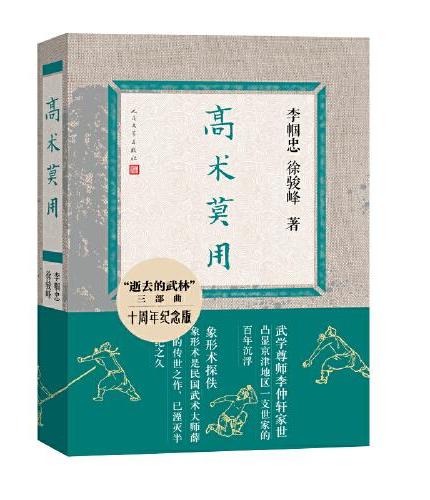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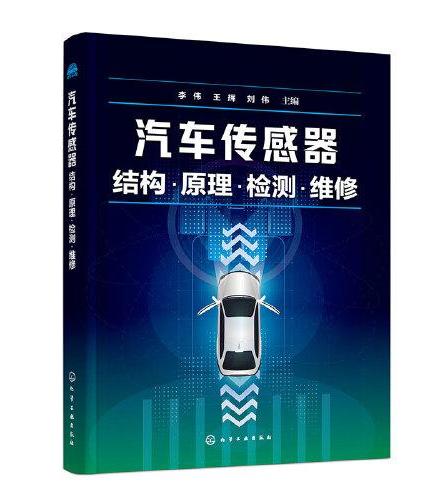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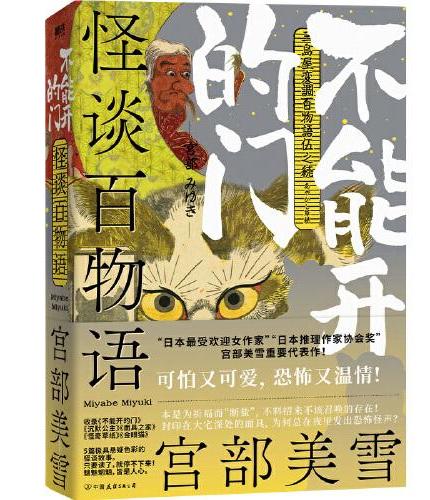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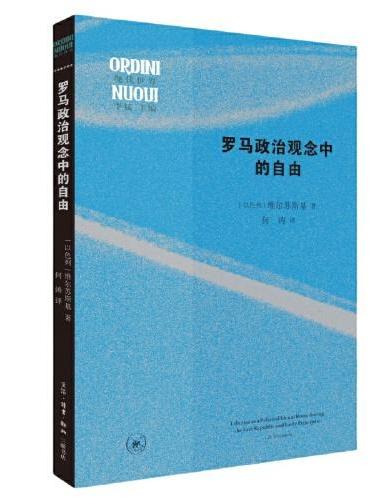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NT$
230.0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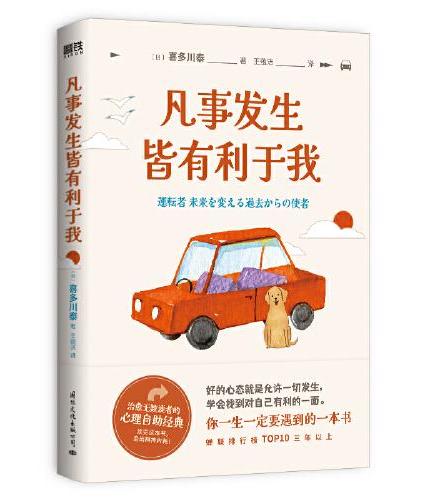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NT$
203.0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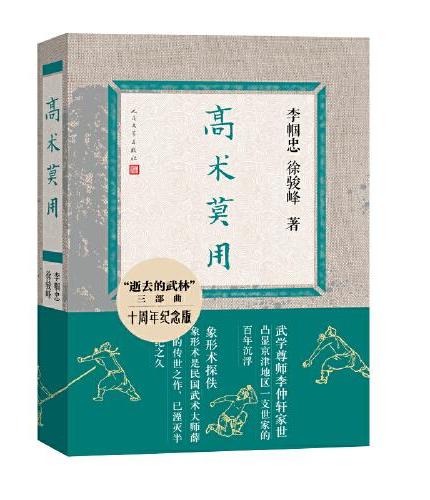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NT$
250.0
|
| 編輯推薦: |
|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
| 內容簡介: |
|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
| 目錄:
|
序冯岩1
小说
酸把梨马自祥3
冬花马自祥14
撒拉拉吾,我的月光宝镜马自祥27
马老大汪玉祥39
命途了一容46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了一容54
一只滩羊的风波汪玉祥64
索菲娅马自东83
沙沟行了一容98
口唤钟翔108
立木了一容125
与幸福约会延枫135
散文
太阳宝镜冯军149
牡丹遐思冯军150
我是洮河的女儿陈玉芳153
我爱石子赵存禄158
东乡秋雨马自祥160
锁南坝——古松的清芬马自祥163
梦牵情萦孔雀河冯岩166
美丽的太阳城——锁南坝马如基170
“花儿”故乡花儿美冯岩174
陇上杏花村——唐汪川马如基182
驾着摩托去“探幽”马福荣186
临夏的水马效忠188
啊!神奇的郎木寺马效忠191
我西海固的兄弟姊妹了一容195
阿娜马效忠200
不朽的沙漠“恋人”冯岩203
乡村里的路钟翔208
广通河奇石赞马福荣211
凤凰岭马福荣213
蜜蜂钟翔216
岁寒民风暖冯岩221
恰西的雪了一容229
白塔山随想汪小平233
怀念我的老师汪生凯236
温馨的村庄钟翔241
家乡的土炕陈玉芳247
为母亲祈祷马自东252
梦想之旅汪小平259
寂静的火石寨了一容261
阿姑姐汪生凯264
诗歌
米拉尕黑(节选)汪玉良273
尕马拉回来,台湾赵存禄277
滩上人的歌赵存禄280
七月的歌马自祥284
采撷阳光的手汪玉良286
冰花汪玉良288
高原出平湖马如基290
山路的变迁赵存禄292
大山在呼唤汪玉良294
献给十月的歌汪玉良300
锁南坝情思(组诗)马颖308
筚筚与花儿马自祥317
写在春天的阡陌里马自祥320
祖国呵,我们骄傲的祖国马自祥322
崖上榆树马如基324
姑娘·车站·雨艾布326
旧信(外一首)钟翔327
飞翔(外一首)钟翔329
那是一个月夜(外二首)艾布331
南疆艾布336
离别艾布338
尘埃钟翔340
马兰花艾布342
改革开放三十年(新编花儿)陈有俊346
实现个“中国梦”做贡献(新编花儿)陈有俊348
报告文学
厚土情马自祥353
苦难中孕育的壮美民族史诗冯岩363
拯救马志勇375
漂流在岁月长河中的红色记忆延枫401
东乡民族的鼓手汪生凯411
太子山下的“金唢呐”冯岩419
长篇作品存目426
后记427
|
| 內容試閱:
|
酸把梨
马自祥
“看你这个死老头子,成天疯疯癫癫,哼哼唧唧的老不正经,在家里也胡哼开了。”
酸老汉刚从槽里牵出一头灰色叫驴,鞴上了鞍鞯。“铁青骡子,马呀溜溜儿三呀。”一句唱词还未哼唧完,老伴就骂骂咧咧地朝他直嘟囔。老汉立时缄了口,白了一眼老伴,把叫驴牵到洋芋口袋跟前。刚从洋芋窖里钻出来的老伴,双手扶着差不离跟她一般高装满洋芋的麻线口袋,可能是说话分心的缘故,那口袋东倒西歪地晃荡起来。老伴急忙鼓着全身的劲双手死死地抱住口袋,脸憋成酱紫色,那模样挺滑稽挺狼狈的。
“嘿嘿,连个口袋也扶不住,还嘟囔个屁。”老汉忍俊不禁,失声笑了起来。而后,一个侧背身拿右手把口袋倒拔起来,左手麻利地朝底一扶,口袋码上了驮子,不偏不倚,稳稳当当。
“咳咳,老黄牛的尿多,老婆娘的话多。嘚儿驾!”灰叫驴撒开蹄子,嘚嘚嘚一奔子出了门。老汉悠然自得,迈起步子。没想到老伴在他身后倒提笤帚疙瘩,冷不防在他屁股蛋上猛给了一下子。
“哎咦,这是咋了?”
“看你再骂人,老不死的,还想占便宜。”
恰巧一个年轻媳妇空着手从巷道里走过来,见状,拿手捂住嘴,哧哧地笑。
“笑啥哩,我后裆里沾了些土,叫老婆子扫一扫哩。”老汉又回头说了一句,“把羊赶上山。”便急慌慌上了路。
他今天有个尕因干(事情),心急火燎地想浪一趟河州城。这因干只有老汉自己清楚。因老伴不大情愿替他挡羊,他便给老伴撒了一个屁谎,“城里洋芋涨了价,二毛五一斤,赶紧卖一口袋,给你扯一件褂子。”
略施小计,老伴上当了。一大早钻进洋芋窑,揽出四五背篼洋芋,装满大口袋。嘿嘿,照老汉自己的话说,个家的婆娘好哄弄。
拐过山梁梁,老汉轻轻嘘了一口,喉咙里痒酥酥的,他猛咳了一声,吐了一口黄痰。在弯弯山道的另一头,也有一头毛驴颠儿颠儿地扬着蹄子迎面蹦跶过来。毛驴上骑着一个上下绿、中间红的年轻媳妇,那红衫儿、绿盖头随风飘拂着,后面却没有和往常那样赶驴的新郎官。
“这新媳妇回娘家,女婿不知上哪儿拾狼粪去了。”老汉的喉结楚楚蠕动着,小曲子早已淌开了:
咕噜雁单飞了没有伴,
尕心里煮了个泼烦;
成双成对是算好看,
单帮子活的是落怜。
一曲刚完了,尕毛驴颠儿颠儿已奔到跟前来了。
“阿达,这么高兴的,到哪里去哩?”
冷丁一声,抬头一看老汉愣住了。这不是自己的小儿媳妇嘛。顿时他臊得满脸酱紫,口里“嗯啊”不止,显得特别忸怩。
儿媳妇早已麻利地从驴背上跳下来,把缰绳牵在手里,想给公公端上殷殷的问候语。刚结婚两个月,新女婿就跟上乡上的淘金队,到新疆阿勒泰去了,一年多没回来。她这次回娘家,一住两个多月,心里正有点那个。想必刚才唱的野曲词儿,儿媳妇未曾注意听还是故意没理这个茬儿,笑憨憨地,不羞不臊。公公此时正陷入觅个地缝子想钻进去的尴尬之境,还哪顾得抱怨呢,“你先回家吧,我还有个要紧事,进城去哩。”说完,低着头往前直窥。
“真是个酸把梨,别人没有叫错,没大没小的,给儿媳妇也胡唱开了。”老汉自言自语,肚里真像咽了一口还未熟透的酸把梨,又酸又涩。
唉,这老汉一大把年纪了,爱哼哼个花儿,时常闹出些笑话来,叫村里人低看一眼,叫他“酸把梨”。
这酸把梨是这一带的特产。大西山一带,靠近太子山,算二阴地区,气候湿润,特别适宜生长这种果树。一到秋天,满山满山的拳头大的酸把梨结满枝头,风一吹,满坡噼里啪啦,落满一地。别看这酸把梨,黄生生的,像冬果梨一样,又大又好看,可一咬,酸汁汁能把你的牙给倒掉。除了怀上娃娃的大肚子婆和馋嘴的小孩儿,男人们是不想逗它的。只有把它捡起来,背到家里,藏在地窖或是大板柜里,拿麦草捂严,放上两个多月,到了冬天,酸把梨全成黑亮亮的,而后,你再像剥炕洞里烧熟的洋芋一样,慢条斯理地剥掉一层薄薄果皮,吃起来,啧啧,那滋味,赛过奶油面包,老人、病人什么的特别喜欢,可以当饭,因此人们也叫它为“哑面包”。可眼下这糟老头子,怎么却也叫“酸把梨”,问起来还有点尕尕的意思哩。
这“酸把梨”老汉,别看村里人瞧他窝囊,可方圆几十里,却是个有名的唱把式。花儿里一百多种调,没人能唱得全,唯独这酸老汉口张曲来,一样不缺,各种亢声柔情的山调调、野曲曲,都给你哼个有板有眼。这还不算一回事,他最拿手的是,见什么编什么,编的词儿,照他听众的话来说:听了叫人的心动弹哩。花儿中有些奇妙的调儿,也是他从这支曲那首令里串套在一起,由他唱出去,成了一种绝“曲”。俗话说,村里卖不出村里的货,不仅卖不出,还嫌他老老不亢、没大没小的乱哼哼,不像话。地窑里吹哔哔,名声在外哩。省、州、县一些搞民间文艺和上面一些大歌舞团的编导、作曲、演员以及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时不时降尊移贵地跑到酸老汉住的小山沟里来采风。一位乡村戴帽中学的民办教员说过一句话:这酸老汉被蒙在鼓里,有那么几个专家歌手,在巧妙地吃老头儿。他列举了几个“气度不凡”者,因从酸把梨老汉口边搜集民歌,编成集子,凑成论文,或是灌成唱片,或是排成民间舞蹈,或稍稍变换一下,谱成曲子被评上职称,或被批准吸收为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的会员。这些事,这个民办教员大概始终没有捅咕给酸老汉,所以,老汉也无从知道。即使是捅给了,老汉也不懂。
酸老汉依然是一个太子山下普普通通的拎铁锨把的山民,干完地里活,就拿起鞭杆儿上山挡羊。饿了,捡几枝枯树枝,烧它一窝地锅锅,山芋烧熟了,连吹带拍,吃得有滋有味;渴了,喝一口太子山晶莹的泉水;寂了,漫起开心的花儿。至今他连个什么“员”也不是。不过也有一次,州群艺馆给酸老汉寄了一张表,州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要他加入。乡政府把表捎给村民委员会,村主任拿着表,找见酸把梨老汉,“我看怕是叫你当脱产干部哩,赶紧把这个表填上,不过你先得宰个羊,把我们村干部请一顿哩,我们得贺一贺哩。”
吃完了嫩闪闪的羊羔肉,村主任嘿嘿一笑,把嘴一抹,走了,把填表的事也给忘了。
过了几天,村主任见着酸把梨老汉,咧嘴嘿嘿干笑,“上一回不是那么回事,我打听清楚了,不是白吃碗菜当脱产的好差,是个什么什么唱把式会,一出门倒贴饭钱的买卖,人家也嫌你大字不识一个,人老毽子了,我看算了吧。我让那个咱村的民办老师顶替了。”
顶替就顶替,酸把梨老汉也没大在意。他的老伴后来知道了,还对村主任千恩万谢的,说他办了一件好事,老不痴痴的,人跟前胡子一扎一扎地唱“尕妹妹的大门上”,丢人现眼地遭罪哩。
那位为酸老汉打抱不平的民办教员,从州府开完文代会回来,给酸老汉尖声尖气地说:“亏你没有去。去了没啥劲道,咳,人家一个个牛皮烘烘的,把咱瞅成个啥不是。”
说毕,民办老师还特意嘱咐了一句:“以后那些撇油花的人来了,甭搭理。看究竟啥是啦不是。”
本不该开会去的人,在老汉跟前乱拉风闸。瞎马揽露水。酸把梨老汉莫名其妙地把村长和顶替人的“不是”揽在自己心里了,一句愤愤之词脱口而出:“咋个是啥不是啥,组长们下来,该叫爷的时候,照样叫爷。”
这一带的山民,把凡是吃官饭的干部统称组长。以前的年成,下乡的工作组多春去秋来多如牛毛,工作组的干部,群众都叫组长,约定俗成,相沿成习,经久不改,不管你是搞文艺的还是行政干部。诚如那年月四个兜的千篇一律的干部服一样,灰不溜秋的,有啥识别头。
“民间老艺人,您老给我们好好唱几首,我们是专程向您求教来的。”穿着整齐的组长们打开本本子,恭恭敬敬。
“老师,老大爷,您把最精彩的花儿唱给我们听听,哎,就是那些最原始,最带有人性味,最够味,最带有乡土气息的。”还有那些如花似玉水灵活现的大姑娘,一口一声“老师、老大爷”,把酸老汉叫得舒坦坦的。
这时候,每当这时候,正是老汉感到最惬意的时候。支书,或是生产队乃至后来的村委会主任,派人四处喊山,把手筒成喇叭状:“喂酸把梨阿伯……酸把梨……工作组来找你,快回家吧!”听到山谷回应的呼唤声,老汉心里不知有几多慰藉,几多欣喜。此时,也只有在此时,老汉并不急忙应声,也不吭声,总是磨磨蹭蹭地,不急不慢地,悄悄地踱步回去。
有些坏小子,派他们喊山的时候,听不见老汉的应答声,便怪腔怪调地给你胡喊:
“喂,酸爸,来了几棵嫩白菜,快些弹来啊。”一听这些不恭敬的微词,老汉便气不打一处来:“这些驴日的坏小子,下三烂。”其实这倒也怪不得几个小青年。这也是有因而来,有感而发的。一次省城艺校来了一位女教师,带着两个粉嘟嘟喷香香的女学生,到这山沟里来学“山味”的。据说学美声唱法的改唱花儿没有花儿味儿。她们是准备参加西北民歌荟萃大奖赛的。看着两个漂亮小妞儿粉嘟嘟的脸蛋,老汉口里却冒出了两句白牡丹令:
尕妹妹活像是嫩白菜,
一指头弹出个水来。
满院子的人哄堂大笑。酸老汉的老伴正在给客人们烧火做饭,在厨房里侧着耳朵细听,见笑声暴涨,便挥着擀杖,骂骂咧咧地:“老东西,没个正经。”那两个女演员倒毫不介意,一个用手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一个毛瞰瞰大眼睛里笑出了一滴晶莹的泪。
嘚儿驾!酸老汉赶着毛驴,驴蹄子把路面敲得尘土扑扑迎面,几辆摩托车呼啸而来。擦身闪过的当儿,戴头盔的主儿,故意把嘟嘟嘟的响声弄得山响,惊得灰叫驴,在路边的埂垄上直扑腾,要不是老汉眼疾手快,死死攥住驴缰绳,差点把驮子的洋芋口袋也掀翻了。更气恼的是,摩托车后坐上一个仰脖子喝啤酒戴墨镜、披肩发的时髦女郎,一个猿舒长臂,把空酒瓶扔在离老汉不远的路当中。砰的一声,碎片四溅,留下一阵阵浪笑,进太子山赏秋去了。看样子,他们不是冒了尖的山户,而是城里发了财的“嬉皮士”们。老汉想立马编上一句花儿骂上几句,又一想,摩托车早已扬长而去,骂给谁听,算了。
“龟孙子们,牛个×哩。”愤愤了一句,眼睛里却刺芒芒的,那些碎了的绿玻璃碴儿直闪亮儿:“说不准,这些玻璃碴儿把庄稼人的架子车胎给扎破哩。”酸老汉便俯拾着,把那些碎玻璃碴儿从山路上拾起来扔进小沟里。又一想,弃物害原主,摩托车回来,玻璃碴把轮胎给扎了,这前不着店、后不挨村的,上哪里修补去?
毛撒啦细雨里抓蚂蚱,
我看你蹦里么跳哩。
轻轻唱了一句,又觉得有点悔意,似乎不该拾那些玻璃碴儿。“城里的大爷,孽障没惜头。”这使他又想起来气的事儿:大前年,他到兰州去看望在一家农民建筑工程队当民工的大儿子。大白天,民工们干活,老汉在大街上转了几天,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人下乡采风时,曾给他留下一张纸条,写着单位、住址、姓名。老汉第一次进省城,怕遇着个什么事儿,防备着,把纸条也带在兜里。光在街上转悠也没啥意思,找这个人谝会闲传去。于是东寻西觅,拿上纸条打问,找上门了。那人戴着厚厚的两片眼镜坨子,瞪了半天,说:“你不是刚拿二十个鸡蛋换走我的几件旧衣服吗?怎么又来拾便宜来了,去去去,看我忙成啥样儿。”
老汉心里凉了半截,这个眼镜坨子,在我家吃住半个月,给他还唱了一肚子两肋巴的歌,怎么现在拿出这一副嘴脸来,把我当成“倒蛋”的二爷。老汉把纸条往那人怀里一塞:“谁稀罕你,到我家里嘴甜成蜜罐罐,一口一声‘爷’,现在装开‘尕拉鸡’来了。”
眼镜坨子看着纸条,莫名其妙。大概他几十年下乡采风的人认识得太多了,一时想不起来,这个萎靡的采风者,等他猛醒过来,奔出门外,人已经不知去向了。
自那以后,老汉家里来了采风的艺术家,他一照面就说:“你们城里人,说不成……”闹得人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气归气,进门就是客,酸把梨老汉依然给他们唱那些各种各样的乡调调、野曲曲,不过那以后,他开始耍开“奸”,使开“滑”了,萌生了捉弄一下的念头。
一次,老汉对面坐着一个也戴着眼镜的采风者。
老汉眯缝着眼,瞧了半天,不开尊口。好,给他胡哼哼几句没令没调,摸不着门道的。
于是老汉信口胡拐。采风者手下书写不停,一边也哼哼嘀嘀地摇头晃脑,把老汉胡拐的调原模原样用简谱记下来,高兴得直拍大腿:“太好了,这首花儿令我就从来没听过,可能是一首蒙尘已久的古歌,到底让我给发掘抢救出来了,太谢谢了。”年轻的采风者紧握着老汉的手,激动地问他是哪一带流传的。老汉信口开河,老实说,也确被采风者突发的激情所感染,随意侃侃,把音乐学院刚毕业的音乐学士听得鸡啄小米直点头。
本想是捉弄人的,倒成了绝唱,老汉唱过也就忘了,那学士改头换面,谱成一首新曲子刊登在《西部歌曲》杂志上,又被好几个走红的西部歌星传唱。这个,酸老汉自然也是不知晓的。
“酸爸,上哪里酸去哩?”昨个傍晚,老汉挡完羊回来,吃罢饭,正想去村口的闲话台上散散心。猛刹里巷道里冒出个尖声气儿,细细一打量,原来是乡政府的民政干事,原来的民办教员。这家伙路子广教员一转正,就不想当娃娃头了。
语气间明显带着揶揄味,老汉十分的不高兴。把头扭到一边,故意装作没听见。
“哎,酸爸,你先甭拿架子啥。”大嘴曼苏姆一见老汉便龇牙咧嘴地笑,话匣子一开,瓦缸里倒核桃,“酸爸,绝了,前个子我到城里去,那些小摊小铺上,收录机音量放得大大的,你猜录音机里唱的是啥?咳,唱的是你,酸把梨,都是些你老汉家唱过的酸把梨令,歪啦啦调。哪个摊子上唱的声音大,哪个摊子上挤的人就多,小媳妇大姑娘,青皮光棍胡碴子汉,还有脸上长满骚疙瘩的尕小伙,一个劲挤着听,邪了,见了个阵势,满街道的酸把梨。”
老汉迷瞪着眼,斜眦眦瞅着大嘴。
“不信了,你个人看去,阿个哄你是这个。”大嘴曼苏姆把伸出的小拇指跷得老高老高。
“这是咋回事,他人在这搭,声音怎么会跑到河州城去了呢?”民政干部装傻卖瓜的那尖声气一冒,老汉的主意反而倒定了,他决意去一趟河州城,也瞧瞧那阵势去。
嘚儿驾!脚底下一块土坷垃一绊,老汉打了趔趄,差点绊倒了。
野雀儿登枝的登空了,
白杨的树枝上卧了;
平地里走路者绊倒了,
人老是老已久了。
老汉即兴作歌,不禁黯然神伤!唉,记忆之弦,随着年龄的嬗娣,倒变得越来越脆弱,也越来越清晰,这一辈子跟花儿搅拌汤,曾有过神来之运吗?
哦,有过,当然有过。十七岁那年,跟上堂哥走脚户。晚夕里在一家小店打尖,久久地,听见破格子窗扇灯光昏暗,有个女子嘤嘤哭泣。堂哥是老出门人,烫了脚先睡了。他倒一整夜毫无睡意,起夜起了好几回,提着裤子,在半截子拦马墙头边呆若木鸡,望着那个小窗,屏神细听着那悲切切的哭诉,渐渐地,他听明白了。原来,那年轻女子的丈夫被国民党的马家队伍抓了壮丁,一个逃回来的连手说,她丈夫在逃跑的时候,被当官的发现,给一枪崩了……起夜回来,尕脚户哥狠劲摇醒了堂哥,迷迷糊糊中,堂哥一骨碌爬起来,往外跑,以为出了啥事情,一会儿回来,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几脚:“驴日的狗松货,睡梦里日的啥鬼。”尕脚户哥却说:“阿哥,你甭骂,我给你唱一段花儿。”“不听,驴日的,半夜三更的,你勾子痒了吧。”堂哥蒙头就睡,可这一折腾,二回里却怎么也睡不着,便辗转起身,抱住膝盖:“哎,尕兄弟,唱就唱吧,唱一个寒碜些的。”堂哥也被夜的悲凉的某种氛围所感染。于是尕脚户哥从头到尾把个麻五阿哥唱了个溪水跌坡,对面那个小窗户的女人不再哭了。
尕脚户哥歌兴方酣,又换了一个调:
酸把梨嘛就酸地来者哟,
小六连哎呀哎嗨没入了味,
没入了味呀就,
尕酸果嫩呀哎嗨,
咋这么嫩了;
一颗颗么就泪泡来者哟,
小六连哎呀哎嗨揪肝肺,
揪肝了肺呀就,
苦命人苦呀哎嗨,
咋这么苦了。
尕脚户哥唱的这段令调,其震撼人心处,还不在于它的歌词上,而在于它七滑八颤的曲儿上,他把这首“花儿”唱得撕心裂肺,唱得鬼泣神惊。
第二天,尕脚户哥与他的堂兄又上了路。远远的一个手提包袱的尕媳妇在后面跟着。堂兄在尕脚户的后背上捣了一拳头:“驴日的,你唱着把麻达闯下了。”
尕脚户却又唱起来:
骑上个尕驴赶上个牛,
身后头跟的是尕联手;
有人的地方你自家走,
没人了我把你捎在驴背后。
那个女人三脚两步跟上来了来到跟前看,憨敦敦的那么年轻。她怯生生地,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唱酸把梨的阿哥,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后来她便成了他的婆娘。
哦,酸把梨。原来第一声称他为酸把梨的,竟然是他的婆娘。
嗨,不知不觉,怎么就到了繁华的团结路。心里想事脚步快。酸老汉醒过神儿来,忙牵起灰叫驴的缰绳,横贯街中心的一条大马路。虽然名字就叫马路,可是决不让牲口走过去的,就是那些大小机动车辆,走走停停,都得听洋灰杆上横架的红绿灯指挥。城里人就是道道子多,你有啥法儿。他得从一条小巷道,绕过农贸市场。洋芋口袋一卸驮子,敞开袋口,买主马上蜂拥而至,大西山的洋芋又大又绵,名声早叫响着哩。
“多少钱一斤?”
酸老汉想打听打听今天的行市,已经来不及了。
“两、两毛。”老汉把毛字拖得很长,毛字的后面想拖出个五来,拖了一阵,终究没有拖出声来
“两毛钱,这一口袋我全要了,走,驮到我家里。”秋后,正是城里人贮备冬菜的当儿,从那干脆的口气上,老汉就知道,这个买主拾了便宜。
“拾了拾子,一个人要,也图个省心我还办要紧因干哩。”
四张大团结和几张毛毛子一卷,塞到夹衣下面的兜兜里。赶着毛驴,径直往摊铺如云的三道桥方向走。
一家小卖部里,十几个青年男女在柜台外面拥挤着,不知在抢购什么热门货。录音机正播放着“花儿”音乐,一段音乐没完,一阵紧鼓敲得哟,好像把一帮驴赶上了平房顶,“咚咚儿咚,咚咚儿咚”,直震得你心惊肉跳,半天,才憋出一声响遏行云、柔如琴弦的唱腔:
酸把梨么就酸呀来者哟,
小六连哎呀哎嗨没入了味。
酸老汉的脚掌如像钉了铁钉,他一动不动。
小店铺里叽叽喳喳地吵成一片:
“这酸把梨调,干散者尺码没有。”
“去去去,主要是迪斯科伴奏的效果好。”
“马赛仲,这小子也成了走红的歌星了,西部华声音响出版公司也居然给他出版磁带。”
“马赛仲是我的铁哥儿们。眼下正夜夜在芳蕾舞厅伴唱。怎么,想认识一下吗?”
“这小子一场伴唱,能捞多少钱?什么,才三十,太掉价了,人家全国的名歌星一场好几千呢。”
“音响出版公司才给他七百多稿费。一场舞会伴唱三十块,不少了,够我一个小职工十来天的工资。”
…………
“哎哎哎,你们究竟买不买磁带。”
“买买买,七块就七块,现在什么都涨价,物价委员会不知是干什么吃的。一盘花儿磁带也给你漫天要价,你们这些个体户够歪的了。”
酸老汉站着,站着,在乱嚷嚷的吵吵声中仔细捕捉住每一首“花儿”的灵魂。这一句句歌、一节节音符,在他的声带上不知流泻、洗练了多少次,如今却让一年轻人传遍了很多地方,老汉的心震颤了。他情不自禁也挤了上去,买了一盘。他注视着封面上身穿西装、头戴白帽的英俊小伙,慨然赞叹了两句:“对,马赛仲,这娃,攒劲!”
马赛仲,是一个县文工队的声乐演员。年初,他从民族学院音乐系进修回来以后,曾带着冰糖、桂圆、细茶,到他酸老汉那里学过歌。老汉上山,他帮着挡羊;老汉犁地,他帮着吆牛,一住二十多天,老汉把一肚子两肋巴的歌全叫这小伙子的赤诚抖搂尽了。临走的时候,老汉对这位年轻人恋恋不舍。如今,他继花儿王苏平、朱仲禄以后,第三个出版了个人专辑磁带,而又畅销“花儿之乡”,当然够攒劲得了。突然,老汉想见见马赛仲,跟他好好听一听,可不知他在哪里,听说他在这座小城的一家迪斯科舞厅里伴唱,在万头攒动的大街上能碰到他吗?
老汉牵着毛驴在寻觅着。
大嘴曼苏姆说得一点儿不错,“花儿之乡”首府的这大街小巷里,摊摊铺铺的录音机里都漫着酸把梨调,老汉适才连吃了三碗甜麦子,听说这甜麦子水水里也含有酒精,老汉的确有点醉了。
“酸把梨汁,酸把梨汁!”
一个小青年站在一只大白箱上,手里提着几瓶黄水水,在大声兜揽生意:“这是我们饮食服务公司最新产品,经科学鉴定,它比沙棘汁还要营养丰富,酸甜适度,解渴消暑,提神健脑,赏心悦目,味美价廉,可口可乐……”
这小青年嘴巴真够利索,四个字一套,一口气说了一大串串。
“多少钱一瓶?”有人抿着干嘴唇,着急地问。
“一块四一瓶,来迟的不得了。”
盈盈的笑中,顾客们纷纷掏钱尝鲜。
酸老汉也微微感到有点口渴,当他想到满山满山熟落的酸把梨,铺满自家挡羊的小山沟时,却不愿意掏一块四毛钱。
“咳,没想到这山沟里的酸把梨,如今也值开钱了。”
老汉笑憨憨地,把毛驴拴在一个木桩上,踏进了城外一家小茶馆。茶摊铺为了招揽生意,家家都备有录音机。
酸把梨么梨就酸呀来者哟……
原载于《民族文学》1989年第9期
作者简介:马自祥(1949—),笔名舍·尤素夫,甘肃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