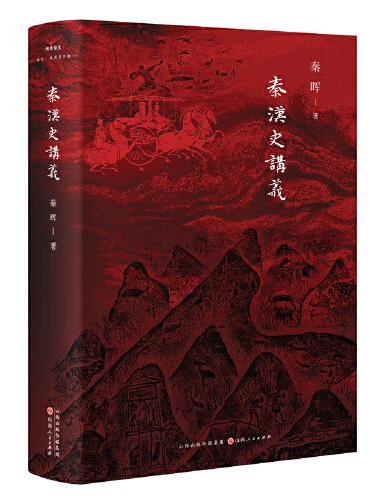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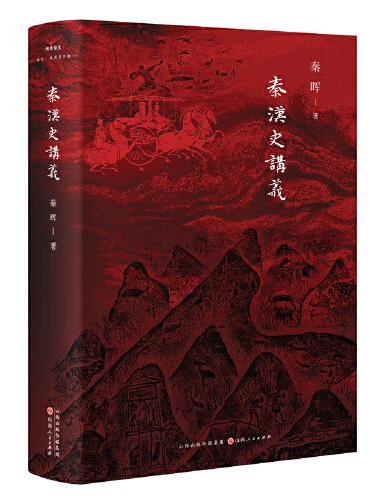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NT$
690.0

《
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售價:NT$
475.0

《
荷马:伊利亚特(英文)-西方人文经典影印21
》
售價:NT$
490.0

《
我的心理医生是只猫
》
售價:NT$
225.0

《
股权控制战略:如何实现公司控制和有效激励(第2版)
》
售價:NT$
449.0

《
汉译名著·哲学经典十种
》
售價:NT$
3460.0

《
成吉思汗传:看历代帝王将相谋略 修炼安身成事之根本
》
售價:NT$
280.0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
| 編輯推薦: |
|
作品用诙谐的笔触展现了刘炳和的心理演变史及其在各阶层的广泛表现,对其产生的诸多现象进行深层思考,唤起人们应持重和珍视的价值。
|
| 內容簡介: |
江南底层农民刘炳和原屡屡受气遭压,作有限的抗争又总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常常被人骂作“肉头”。因见人快速致富而心动,舍弃种粮和祖传做豆制品的“绝技”,将农田改种花木,外出推销,由卑微的穷苦农民变为村里首富再成为村支书,从保守到开放,从谨慎到大胆直至冒险,从勤俭节约到为面子不惜大把消费,从反对干部生活腐化到有两个情妇……
传统吴地农耕文化、近百年来自上海辐射的外来文化、涌进的西方“现代文明”,在刘炳和身上既有冲突,也有交糅。作品展现了刘炳和的心理演变史及其在各阶层的广泛表现,对其产生的诸多现象进行深层思考,唤起人们应持重和珍视的价值。
|
| 關於作者: |
|
陆涛声 江苏常州人。早年从事书画专业工作,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发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二百多万字,短篇小说《再见千岛湖》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并编入全国高等职业学校语文读本。作品和论文被多种选刊转载,并入选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等选本。己出版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专著九种。书法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等多家收藏,曾应邀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个人书展,出版书法集和书法丛帖共五种。现为研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知识产权局特聘“中国知识产权文化大使”。
|
| 目錄:
|
一、投票 001
二、恩怨 017
三、老话 038
四、志愿 089
五、天堂 106
六、输赢 153
七、新话 173
八、虔诚 244
九、出洋 298
十、祸福 319
|
| 內容試閱:
|
【 投票 】
苏南滆湖和长荡湖相隔三十里,中间有一条运河连通着,半月湖又有河道通过城市连着长江。两湖间在离滆湖四五里处,有条河港与运河相通,形成了一个河湾,湾里村就窝在这河湾里,属于碧溪乡。它原本只是个自然村,成立人民公社时,五个大小自然村建大队,其中湾里村有近百户人家,是最大的一个,又有小学,便定为大队部所在地,就叫湾里大队。近年公社撤销改为乡,大队改为行政村,村委会依然驻在这里,叫湾里村民委员会。
湾里村本村有个外号“肉头”的村民,本名叫刘炳和。他四十岁时,分得了承包责任田,由社员变回了村民,在这块土地上,迈开了新的脚步,开始了他奇特的后半生……
一
刘炳和被人背后叫“肉头”,这缘于他遇事总有点不三不四肉里肉气。
一天半夜三更,他起身挑水做豆腐,眼看到村支书兼村主任金小龙往人家老婆房里钻,一不当场去捉双,二不到上级去反映,偏又在背后叽叽咕咕泛泡泡,秘密地告诉了好朋友。秘密新闻秘密地传来传去,传到金小龙耳朵里。金小龙追“谣”追到他头上,一记耳光打落了他左边两颗盘牙。他气得面孔铁青,要上乡里去告状。他老婆硬把他按捺在家提醒他:你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乡里去不见得能占上风,翻千个跟头都难出金小龙手掌心。他只好长叹一声,左边两颗盘牙吐出口,一口鲜血咽进肚。
满以为事已了结。金小龙心头却还挂着一笔账。
刘炳和家里还是土改时分到的两间旧瓦屋,旁边搭了一间屋是半砖半墙毛竹梁椽麦草盖顶,在村里已显得极寒酸,他连做梦都想也造两间新楼。他有父亲传给他的做豆腐、百页手艺,原先政策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只能以到生产队田里干活挣工分为主,带着帮人家加工豆制品赚点加工费,不敢自家买黄豆做成品拿出去卖了赚钱。这两年,说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了,大家好发家致富了,土地又分给大家承包,江南乡村人人都在钻天打洞寻财路挣钱。刘炳和也心痒痒的,一半工夫花在承包田里,一半工夫花在做豆腐、百页上,夜里磨豆煮浆点卤做货,第二天一早挑担穿村走巷叫卖,使足劲点点滴滴攒钱,拾散芝麻凑斗满,三个五个月聚到一笔,就随手想法买进一点建房材料。
一天黄昏,运河里开来一只装黄豆的安徽船,在他家门口码头边停靠过夜,打算第二天一早开往城里把豆批发卸给贸易市场。刘炳和做豆腐、百页用的黄豆,本来都是到城里贸易市场买的,每斤八角。安徽船上的黄豆批发价是六角,有四千斤。刘炳和肚皮里盘算,若是全部端下,自己做豆腐用,也转卖给人,都可以多得七八百元,这可是一笔小财呀,可以买三个立方木头,足够做木窗、家具。他心一横,决定全都吃进。安徽人也图个省时间少赶路程少花用,乐得脱手。刘炳和家里钱不够,连夜向木匠根宝借来一千元,又向半秀才士俊借六百。他想,今后若是能经常这样批发进点黄豆来转手卖,倒是多条省劲的财路,就和安徽人讲好,下回再装黄豆来江南,依旧先到这里。这样便有了一条源源不断的财路。
四千斤黄豆堆在家,不满半个月就转卖掉两千多斤,归还了木匠根宝的钱。正当如意算盘才拨了头个子,村党支书兼村主任金小龙派村委会会计周玉林找上门来,说他刘炳和以做豆腐做幌子搞非法经营,必须罚款一千元,还要写张检查书保证今后不犯。还说,三天内不交罚款和检查,处理就要加严。
刘炳和可不服:“如今改革开放,人家都在做生意了,怎么偏偏我是非法经营?”
周会计说:“你别跟我争辩,粮食、油料可是国家统管的,你是倒卖油料,是违法的。人家做的买卖可不违法。是金主任说的。”
碰巧捡到一只肥烧鸡才啃了一口,就让骨头卡了喉咙,又气又急又恨,等周玉林一走就发起牢骚:“操他娘,如今这年头,像老子这样买回料兼自己用又带转让的,从公家单位到私人,有门路的没有一个不做,有的靠这一套赚到的钱都好当垫被铺床了,几时有人大惊小怪过?老子不过是小打小敲,才开头偏就有鬼上门来寻事!哼,分明是金小龙这狗日的存心找茬儿报复!老子就偏不理他,不信他有长锅子把我煮熟了吃!”
他舍不得从心头割那么大一块肉!可一时又想不出对策,只能先拖着,不交罚款不写检查书,想看看风头再说,心悬着。
第三天中午,周会计又来了,警告说:今天到天黑不交,明天就要通知乡里,叫工商所、税务所来罚款、罚税,叫粮管所来按国家计划价强行收购余下的黄豆。
刘炳和心里慌乱,嘴上却还硬着说不怕,竟忍不住冲着周会计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周会计也别这么跟着欺人。”
“金主任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过是传个话而已。这可不关我事。”周会计不悦地说,“你要是不服,去找金主任说。别乱怪到我头上。”
亲自去找金主任说?刘炳和浑身一震,舌头马上舔到了左边那被打掉两颗牙的缺口,身子打了个冷战,大脑冻结了。
周会计走后,老婆劝刘炳和说:“别再强拗啦,如今就是这样嘛,脱轨的事大家都做,市面再大,只要不冒犯城隍、土地,就太平无事;你做的市面再小,冲撞了哪路神道,就要被抓小辫子倒大霉。公事公办对条文,你终究犯了规矩嘛,不该揪?这点道理你还不明白?”
倒也是。刘炳和冷静一掂量,金小龙心里已经恨他,他越顶会越倒霉,怕闹不好反而又要多脱几块皮,只好认了晦气,决定交罚款。他进的黄豆将近一半还没出手,还凑不出交罚款的钱,只好再去向木匠根宝借。
二
他随即赶到根宝家去。
这天是阴的,空气湿湿的,东北风很大。刘炳和感觉到,这江南早春,阴湿的天空暗得像口大锅似乎要压下来把他罩住,带水汽的东北风特别冷,刮到他脸上,就像刀片,在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削去……
他到根宝家,一开口,根宝竟说:“你先别交,等几天再说。村委会马上要换届选举了。”
“村委会换届选举跟我罚款搭嗲界?”
“看你这脑子,咋这么笨!这回要是大家把金小龙村主任选下了台,支书的位置也就坐不牢了,谁还罚你这么重!你现在去交不是做肉头吗!”
“到底我肉头还是你肉头?”刘炳和不服,“选村委会又不是头回。你想想,金小龙当年上任,是你我选出来的吗?”
“过去是过去,这回不一样。这届村委群众意见大,新来的高乡长听到反映了,也有看法,不会再硬保他们过关,下决心由群众选信得过的人。”
“说是这么说,这种只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的事还少吗?”刘炳和巴望根宝说的能实现,却又不敢相信,总觉得根宝太天真。
“这回可不再是那样了,沟南村前天已经先选了,那邪神村主任王锁贵就被选下了台。”
“真的假的?”刘炳和眼前闪过一道亮光。
“你不信,到沟南村去问问。”
刘炳和心里似出现一线亮光:“如果是真的,倒是谢天谢地。”
根宝说:“我们也得想法把金小龙选下去。”
“有可能吗?”刘炳和强烈向往,却又觉得太难。
“好些人找我通过气了,约定选吴春山。本来就想去找你的。”
村农技员吴春山!这年轻人在刘炳和眼里,既有文化,能干,为人也正派,确是头挑的人选,“要是他真能选上当村主任,我炳和情愿白做一天豆腐,花钱买挂五百响的鞭炮和八个大爆竹在村头放——根宝,我也算跟你通过气。我家也一定投春山的票!”
刘炳和沿运河边的村道回家了,把借钱交罚款的事丢到了脑后。他浑身已轻松了许多。扑面的东北风吹来也不觉得阴冷了,阴霪的天也似乎亮堂了许多,铺满麦苗儿的田野也变得格外平坦广阔,运河河面似乎比平时宽了许多,三五成群的鸭子正在水面自在地悠游……
他回到家,把根宝传的消息告诉了老婆。她却给他泼冷水:“就算根宝说的是实情,眼下还没有选举,你有把握说金小龙一定会下台?”
他一想,倒也是,活到四十二岁了,遇事可不能单顾一头,罚款暂且拖着,还是该先去烧把香,让金小龙把心里那点气消了,留点后路好进好退,以防万一。他赶到镇上,买了一条沪产的带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这上海产的香烟店里凭票供应,他是从烟贩子手里买的,黑市价,花了三十元钱,用报纸包着。另外买了一包带在身上,赶到金小龙门上。金小龙人不在家,他把整条烟交给了金小龙的老婆。
回家的路上,见金小龙站在运河上的水泥拱桥桥头,跟刘炳和所在村民组的组长生法谈着话。他壮壮胆走过去,恭恭敬敬给两人各递了一支烟:“金主任,那罚款我一定交,决不赖。只是家里一时实在凑不出这么多钱,买豆还借根宝一千元呢。这两天我天天在找人借钱,还没有着落。求你宽延几天,让我有辰光想法子把钱凑齐。”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就过几天再说吧。”金小龙态度很温和。
刘炳和心里放松了些:看来,金小龙是因为要改选有顾忌,态度软了。改选的事,果真刚见点风就来雨。刘炳和松了口气,也又暗暗得意:嘿,老子不过是缓兵之计,过几天要是你被选下台,还“再说”个屁!
三
当天黄昏,各村民组就分别开了村民会让大家提名推荐候选人。刘炳和宁愿耽误磨黄豆,也要准时去参加。他刘炳和家夫妻俩和三个孩子共有五口人,三个孩子,老大女儿菊菊已满十八岁,按理已经有选举权了,在省城念中专,户口三年前就迁到了学校,不能回来投票,真可惜;老二儿子阿新在读高中一年级,小儿子阿华正读初二,都还没满十八岁。他们家只有他和老婆有资格投票。他要老婆跟他同去开会参加候选人推荐,她却不肯去,还叫他也别去,防着再得罪金小龙。她还说,马上去娘家向她哥借钱去交罚款。
刘炳和等她走后,还是熬不住去参加了村民小组会。
他们这个村民组开会,推荐人最多的是吴春山,只有个别人提了金小龙。刘炳和心花又绽开了几分。
他回家不久,老婆也从娘家回来,说她兄弟手头没有这么多钱,答应尽快帮忙想办法凑齐送来。也真是妇道人家,胆子小,心眼死!多此一举!
金小龙说话还算作数,第二天已过了交罚款的期限,真没有派人来寻麻烦。
又过了两天的中午,刘炳和卖完豆腐挑着空担回家,在村口运河桥桥头遇到木匠根宝。根宝又告诉他,乡里来人综合了各组推荐的名单,商定了七名村委委员候选人,吴春山、金小龙、生法都在内,实行差额选举,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投票选出五名村委委员,然后从五名村委委员中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再由全体村民从两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一名村委会主任。已经在印选票,晚上就要在小书场开村民大会投票正式选举。刘炳和心头先是一热,随后又一凉:“金小龙还是候选人嘛!”
“还不是他金家门里人和一些马屁精提的!不过提也白搭,正式投票选票数不会有吴春山的一半。”
“你能肯定?”
“金小龙要是不落选,我在村头倒爬三转。”
刘炳和又吃了颗定心丸。吃午饭时,兴致勃勃跟老婆谈起了选举,大有诸葛亮料事如神的把握。
他老婆偏还要打拦头板:你不要光顺自己的心愿想,俗话说,百姓、百姓,有百条心。选村主任不是光看我们这个组。十个组三百多户人家呢,他根宝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吗?能把几百人的心思都摸透?……
刘炳和一愣:这话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还是该仔细周到些。他放下饭碗,就赶紧出门到别的村民组,走东家串西家打听行情。他找了半秀才士俊,又找了寡妇兰花……一连走了七个组二十来户人家,搭讪闲聊,转弯抹角,一一探明态度。十有七八的人都说只选吴春山,只有少数人家支支吾吾不肯明说,没有一个明确说要选金小龙的。倒是有人对他刘炳和信不过:“只怕你到节骨眼上像你做的豆腐,硬不了!”
刘炳和已经铁下心:“我要再选金小龙就是乌龟王八蛋!”
他搞了“抽样调查”,完全定心。回到家,天已黑,灯已亮,老婆和两个儿子已吃过夜饭。阿新娘气他丢下活儿在外头瞎撞,骂他“神经不正常”,不理睬他,只顾守着电动小钢磨磨黄豆。两个儿子正在做作业,阿新放下笔给爹盛来一碗泡饭,接着就到房里拿出一沓钞票:“一千元,放晚学我拐到舅舅家去拿来的。娘说你还是明天去把罚款交掉。”
刘炳和把放在面前台上的钞票一推:“我还来做肉头!”他想到晚上就要选举,心里热乎乎痒嗖嗖,拼命猜想着选票的模样,把端到手的泡饭放下,从儿子的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拿过圆珠笔想象着试画起选票来。
阿新娘忍不住怨骂:“你中了什么邪,夜饭还不吃,画什么鬼符?”
“鬼符?”刘炳和憨笑笑,摹拟画好一张选票,把吴春山的名字写在头格,金小龙写在第二格,拿起来一扬,“老子今朝就是画的鬼符,要送金小龙这恶鬼到东南方向三十六步!”随后,在吴春山名字下画个三角。在金小龙名字下使劲画了个大杠。他真痛快,不由从酒缸里舀了一碗自家酿的米酒,就用下泡饭的咸菜和香葱炒豆渣做下酒菜,轻松地独酌起来。他本来酒量很小,一碗米酒喝完,柿饼面孔也就红到耳根,开裂核桃似的两眼暴满了血丝。他觉得自己腰板已变粗变硬,身子也已变高变大,手里捏的似乎不是“选票”,而是堂前画轴上钟馗手里的斩妖剑。他眼前虚虚幻幻出现了金小龙的人影。这个略显肥胖壮实十分威严的邪神,渐渐变得又矮小又猥琐……刘炳和胸中积压的怨恨终于毫无顾忌喷出口:“娘的你姓金的本来有什么了不起!造三间三层光鲜楼房,买电视机、录音机、共鸣箱,三天两头上酒席,猪头似的脸喝得红通通、吃得油光光,一年到头常吸高档香烟,又轧姘头又赌钱,还硬沾村办电镀厂搞外交的光,逛北京、上海、广州……你凭啥,还不是凭有顶小乌纱帽吗!老子不当官还会做豆腐、百页呢,你不当干部就狗屁不如……”他越说越出性子,声音也越响。
阿新娘吓得面孔脱色,忍不住过来捂住他的嘴怨道:“你这张夜壶嘴还乱倒,苦头还没吃够!还非要……”
刘炳和已是英雄虎胆,无所畏惧,推开老婆手,嗓门更大:“我还怕个屁!他金小龙马上就要变成烂死蛇!到时候看我指他鼻子骂个狗血喷头!”话音刚落,门被“呀”地推开,响进一个熟悉的嗓音:
“老刘,会快开了,还不动身?”
门口出现的正是金小龙。他依旧壮实肥胖得像尊佛。也不知怎的,刘炳和的心一下蹦到喉咙口;嘴巴竟不争气,变得非常客气:“呃……金主任,你吃过夜饭了吧?……去开会啦?呃……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金小龙先走了。
刘炳和定了定神,忽然留意到台上的一沓钞票,连忙一把抓在手:“他,看到这钱没有?”
“哪个知道?!”阿新娘没好气地说。
刘炳和愣了愣,像对老婆又像对自己说:“不过他对我还蛮客气的。喊我‘老刘’哪——这还是第一回。”他把钱放到房里出来,再望望“选票”。心想:你金小龙今朝为啥换了副面孔对我?还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头上的乌纱成了癞痢的辫子……他捺捺左边面颊,摸摸掉了一两颗盘牙的缺塘,胸口一股火焰直往上蹿,手掌一拍那“选票”:“哼,你狗日的,对老子客气已经晚啦!”
四
时间不早,刘炳和匆匆吃完那碗泡饭,要去参加选举。阿新娘以往并不把这类事放在心上,这回竟也要去,说是不放心,怕他头发昏闯出纰漏。他感到讨厌:“我要你女娘家保驾?不是活得倒缩了?别白费工夫,在家把豆磨完!”
“我也有一票的权嘛。”女人另有理由。
“素来是由我代投票的。”
“今天我就要自己去选。”女人偏拗着气,“我选哪个我做主。”
这个家庭只有两人有选举资格,鬼女人要自己选,难料会出什么花头。要紧当口一票可推扳不起!刘炳和又气又火:“我是一家之主,这两票选哪个全该由我做主!”
女人就是不服:“你我一起到会上去让人家评评理!”
刘炳和气得核桃眼直翻:“你……你是存心要拆散这个家!好,散就散!”他喘着大气乱投乱撞找到一把锄头,抡起来要砸浸着黄豆的缸。两个儿子都急忙放开作业本拉住了他手。女人也被吓呆。
两个儿子两边劝说了一会儿,一个不再说要去,一个也就乘机落篷丢开锄头。
刘炳和保住了掌握两张选票的大权,带上儿子的圆珠笔,去当“判官”了。一路上,他昂头挺胸,反剪双手,踏着官步,大有武二爷上景阳冈的神气。不过,他也不无遗憾:娘的,阿新这细赤佬只差一岁,没有选的资格;女儿菊菊满了选举年纪,偏又考在外地念中专,要不老子一家好有四张选票呢……
选举会场在湾里小学的礼堂里。这里原本是座庙,供奉的是白龙娘娘,解放初先在这儿办扫盲班和冬学,接着搬掉了泥塑菩萨,办了小学,他刘炳和就是这小学第一批学生。学校由初小到高小,不断发展扩大,白龙庙的其他房子都被改造了,还扩建了校舍,只有这间大殿一直没拆掉改建,依旧留着做礼堂。搭了个两张乒乓台大的小小舞台,安放了许多长条木凳,还另外开了个门通外边,晚上经常接纳锡剧清唱组和苏州评话艺人演出。礼堂前有棵自古留下的银杏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方圆十里独高,从镇上回来,三里路外就能见到它鹤立鸡群的雄姿。
刘炳和到礼堂外时,迎面就是古银杏树,抬头望望高高耸入夜空的树冠,仿佛自己也跟着雄伟起来。
屋里早挤满人,两盏二百支光电灯亮得耀眼。刘炳和进屋时,头轮选村委早已开始,唱票人已在唱票。刘炳和真恼恨:都是那鬼女人胡搅蛮缠,害老子迟到……他急忙挤到台前,要求补领选票,乡里来主持选举的干部说多余选票已经撕掉,不能补领了。错失头一轮让金小龙在村委员中落选出一份力的机会,失掉了两票权利,他心猛一沉,浑身顷刻渗出一层汗来,头一眩,差点儿晕倒。他更恨老婆拖误他辰光,浑浑然回到会场后边,找了个空位置坐下,等着这一轮选举公布结果。结果终于公布:投票有点散,除了原定七个委员候选人,“另选他人”冒出了十来个,五个当选人,吴春山最高,生法也当选,可金小龙也过半数只多一票,勉强当选委员,并没彻底垮台。刘炳和心里很不满足。
主持人宣布,让大家暂时休息一会儿,当选的新一届村委委员要开个小会,协商提名两位主任候选人。
对了,关键还是谁当村主任。刘炳和心里又一亮,盼着第二轮推荐的两位候选人中第一个就是吴春山,巴望不再有金小龙。
五
乡领导与五位新当选委员协商的小会散了,并没有马上开大会公布候选人名单;又等了好一会儿,会计周玉林拿着在小学办公室临时用钢板铁笔蜡纸刻写油印的选票,急匆匆赶来会场,主持人才招呼开会,向大家宣布,两个村主任候选人,是吴春山和金小龙,接着就分发选票,叫大家酝酿一下。
金小龙在五名当选的村委委员中,得票数是第四,怎么还会被推荐为村主任候选人之一呢?真是怪了!心又一凉,刘炳和拿到选票一看,票上的两人名字,竟是金小龙排在前,选委员时他金小龙可比吴春山少了二十四票呀,吴春山怎么排在后边了呢?肯定是乡里来的人捣鬼硬包庇!说不定金小龙还能再当选……刘炳和眼前变得暗淡起来——真不甘心啊!他愣了片刻,忽然又认为不会,金小龙与吴春山票数相差这么多,还得大家投票,要想超过不大可能。他心里终于定了铁案,在他大脑里翻江倒海之际,大家都已纷纷填好选票往票箱里送了,他得赶紧填选票,随即找个地方挤一挤。屁股搁到一点板凳头,把选票摊在膝头上,取出圆珠笔,在吴春山的名字上边画了个圈,在金小龙名字上边画了个大杠——哼,金小龙,今天你这村主任下台,老子要推你一把!
鲁提辖终于要拳打镇关西了。刘炳和雄赳赳气昂昂要往台前票箱去投他与老婆的两张票,头一抬,突然发现,候选人都坐在主席台的一侧,高乡长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场,也和两个候选人坐在一起,金小龙还拿出牡丹香烟给了高乡长一支,凑近高乡长谈着话,样子十分亲近,不时自在地笑着。刘炳和怔住:难道真……不对,刘炳和真为难,两脚来了个急刹车,忙转向投过票的人堆里想找木匠根宝商量商量。
他忙转身在人群里找到根宝,嘴朝台上努努,轻声问:“这是怎么回事?”
根宝没回答,一把拉着刘炳和挤出会场门:“你该看出苖头。”
“你们家的票是不是投给吴春山的?”
根宝苦笑说:“你们家没有改投?”
刘炳和一听话音不对:“啊,你投的是……?”
根宝“嗯”了一声。
刘炳和气得发抖:“王八蛋,说话是放屁!”
根宝抱屈地说:“不能怨我。刚才一阵风刮来,不少人转向。”
“什么风?”
根宝丧气地说:“还不是人来风……”
会议开始前,高乡长从镇上赶来,把金小龙叫到屋外古银杏树下谈了好一会儿。先到会的人对这都十分用心。有人装着要出去撒尿搞“侦察”,依稀听到高乡长说:“……你工作上的成绩,用不着你说,组织上会有正确估价,乡里领导对你还是会负责的……”
“这不是明摆着还要金小龙再当?这风一吹进金家门里人耳朵,马上就张着一只只耳朵刮遍全场。”根宝头朝门里探了探又说,“刚才,金小龙掏出香烟敬高乡长,高乡长还用打火机给他点火的。两人关系很亲近。你说,大家能不转舵?”
倒是,既然上头内定了,铁炮都难轰得掉。当年金小龙上台,头回选举得票没过半数,来坐镇的老乡长就让大家再酝酿重选,还逐个找人谈话动员,有几个投反对票的露了底,后来都多少吃了点辣糊酱,刘炳和想不通:“乡里知道他名声不好,怎么还护着他?”
“还不是念他办了两个厂,产值不低!”
刘炳和后悔不已。他本有先见之明,料到金小龙这尊菩萨很难扳得倒,只怪自己的耳朵根软心太活,信了根宝……
“我也不是存心害你,刚到会场时,金小龙的堂弟还特地私下把我拉到外边谈话,……我还能怎样?”
“还呆啥,不快点想法把票送上去!”阿新娘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刘炳和捺捺左边面颊掉了盘牙的缺塘,再想想一千元罚款,教训实在深。这两张选票倘若依旧选吴春山,不仅白费,与金小龙的仇还会结得更加深,霉会倒得更大……他暗暗庆幸选票还在手。杉木扁担,不弯会断,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会大拐弯,我刘炳和也不是肉头,也会向后转!
他马上拔出圆珠笔要改选票。凑近门口灯光,糟糕,原在金小龙名字下用圆珠笔打过大杠,用指头蘸唾液擦,怎么也擦不掉。回头看看,人家都投完票了,计票人都在开票箱了,他急得浑身一阵潮热,满头满脑汗直冒。
根宝劝他:“算了,你还是干脆弃权吧,省得露马脚。”
弃权?为这两票的权利,他刘炳和不知费了多少心机,能甘心?想天法都要让派上用场,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两票即使当两支香烟,也可以敬一敬金小龙,说不定今后流年还好顺些……他刘炳和这时竟变得特别聪明,灵机一动,把那大杠改成个五角星,又加画个圈,把吴春山名字下的圈涂掉,另画了个大杠。
刘炳和改好两张选票,计票人已从票箱里取出选票清点,他急火火从座位间过道向台前冲去,把选票朝前一扬。大声喊道:“慢点,我家的票还要投!”他不顾一切向台前挤去,心急脚不稳,不防被一张长凳头一绊,“啪”地跌了个“吻土地”,碰得鼻子酸痛到眼泪出。他爬起身又朝前闯,鼻孔滴血都没在意。一到讲台前,把选票往唱票人手里一塞,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家两票……都赞成……金主任!”他还怕金小龙没听明白,又拉大嗓门说,“我家两票全投给金主任!”
哪知选票上滴了滴鼻血,计票人一接捏了一拇指红,忙又丢给他:“这五颜六色的选票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回去镶在镜框里好当年画挂呢!”
刘炳和浑身汗珠直冒,核桃眼瞪圆:“你这算啥话?想压制民主,剥夺我选举权吗?”多亏高乡长开了口,叫记票人接下他两票,他终于舒了口气,用棉袄衣袖揩了揩鼻子下的血,笑了。
选举结果,金小龙超过半数一票,于是当选;吴春山比半数少一票,于是当副主任。
怎么会这样?刘炳和的心又如被人抛上高空又突然落到地上:真该死,要是自己两票不改主意,吴春山就会比金小龙多两票,结局就完全相反。他极后悔,恨不得用拳头敲自己头。
再一转念,心又一亮:嘿,他金小龙在危急关头,我两票威力等于两百票呢。帮了他大忙,决定了他的命运,可以说他这村主任是我给他当的,他绝不会心里没数,定会感激我一辈子。一千元罚款,肯定不会再提。说不定他的佛光还会长照着我……刘炳和越想越开心,连高乡长最后讲了哪些话和宣布散会都没听清。
回家路上,刘炳和高兴得心头像有毛毛虫直往上爬,爬得喉头痒嗖嗖,老想跟人搭话,想找根宝,根宝却不知怎的不见。同路人却都不理他,他老婆暗示他别多说话,拉着他连走带跑往家冲,有人还在背后低声骂他“肉头”。刘炳和窘得面孔热辣辣,心里可不服气:嘿,骂我肉头!如今有几个人腰杆是硬的!我不相信你们就没有半点肉气!
六
刘炳和满以为,金小龙主动会上门来说几句贴心话,表示点感恩的意思。等了两天,没见,忍不住嘀咕起来:“他老金也是,白天怕人看见生议论,还有天黑的时候嘛。再说,你当干部到群众家里走走也名正言顺,怕什么呢?”
“你这想得就不对。”阿新娘通情达理,“你也不是真心要投他票。人家又不是头回当选村主任,哪会为你丢掉架子来服小当矮子,认不认你情还不一定呢。我看还是该我们先上门去拜望他。说到底,今后还要靠他呢。”
刘炳和想想有道理,晚饭后,避开人眼走进了金家围着院墙的小洋楼。
金小龙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眼一瞥他,又转向屏幕,似笑非笑地问:“送罚款来啦?”
“呃……”刘炳和摸不清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不是欠我私人的钱。你明天送到村委办公室去吧。”
刘炳和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看看金小龙那神情,不像是笑话。他像一头撞到了石墙上,蒙了。缓了缓神,恨不得破口大骂一场。满肚狠话冲到嘴边,鬼差神使化成一句带讨好的说明:“金主任,那天我家投你两票,就是想到这五六百户家人家没有你当家不行哩。”
金小龙微微一怔,笑笑说:“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就更应该坚持原则做好工作,要是放弃原则讲私情,就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你嘛。你说呢?”
刘炳和浑身发软了,不由带着哭音说:“金……主任,我一家选你可是真心诚意的呀!”
金小龙依然微笑着:“我心里一清二楚。”
刘炳和脑髓一下子结了冻。他浑浑噩噩,不知是怎么离开金家回到家的。当夜他躺在床上,两眼眼皮久久合不拢。他娘的,他金小龙怎么一点都不认情?看来,他是知道了我改票的底细——对了,他那“我心里一清二楚”,不正是话里有话!……上回嘴巴不紧兜了他的丑,赔了两颗盘牙,贩了点黄豆要罚款一千元;这回选票不讨巧又种下祸根,往后不知又要遭多少罪……刘炳和想得心惊肉跳,浑身发寒。唉,那两票改得真冤枉,我确实是肉头!……
下半夜起身烧浆做豆腐,他还是六神不安,放石膏点花竟没个数,把一缸豆浆点坏。他心里在熬猪油,偏偏阿新娘还盯住他咕噜不完。他恨不得投河上吊。操他娘,真是乡下人挑粪——前后都是死(屎 )。既然被逼到这地步,寻死还不如闯祸,干脆豁出去跟他姓金的拼个鱼死网破!老子要到乡政府去喊冤,要收回我两票加给吴春山!不成,就上县里、省里……
七
天蒙蒙亮,刘炳和就赶到镇上,等到乡政府秘书办公室一开门,就进去对秘书喊起了冤枉。
高乡长进来了。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乡长站旁边静静听了一会儿,拍拍刘炳和肩头招呼他,领他到另一个办公室。他想加重反映意见的分量,竟假借是木匠根宝、半秀才士俊、寡妇兰花等十来家人集体的名义到乡里来的。
“那你和那么多人又为啥要投票选他?”年轻的乡长没好气地问。
刘炳和先是一阵尴尬,接着低下头嘟哝说:“是你们乡里内定还要他当,我们都怕不选他会倒霉!”
“哪个说我们内定的?”高乡长莫名其妙。
“都说是你……”刘炳和结结巴巴把选举时根宝传的“风”摊了出来。
“你们这帮人啊!”高乡长苦笑着摇了摇头,“我那天找他谈话,是做他思想工作,叫他有落选的思想准备,告诉他乡里会给他另行安排。你们竟会……唉!”
原来是这样!刘炳和又懊悔不及,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看来,乡长是个明镜高悬的父母官,还有巴望。他乘机要求说:“你就下个命令,把他调走吧。”
高乡长为难地说:“不管怎样,他是你们大家投票选上的,乡里怎能不尊重大家的权利!可没理由马上把他调走。”
“也是为大家好嘛,有什么关碍。”
高乡长在屋里踱了两个来回,大有感慨地说:“上头搞考察先定个初步方案,确实常生偏差,搞包办代替,你们反映不让大家做主;放手让你们自己选,又出这么多花样;闹到头来,又要叫乡里做主,真叫人哭笑不得。唉,你们这些人真是……”
“也是,也是。”刘炳和感到羞惭。然而,他决不放过金小龙,“现在想想,还是领导做主好,这回无论如何要请乡里做主。”
高乡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先回去。等我们再到你们村里征求征求群众意见,乡党委领导班子集体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妥善的办法。”
刘炳和心宽了许多。他回到家,满怀信心对老婆说:“高乡长是个公正的清官,会帮我们说话。他肯定会有好办法。”随后,他又出门去找被他借名的人一一打招呼,免得乡里来调查时他们说没让他代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