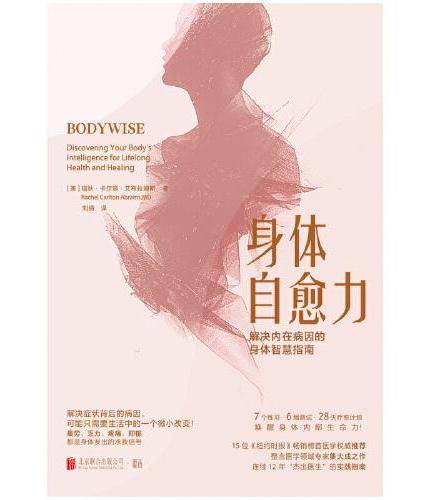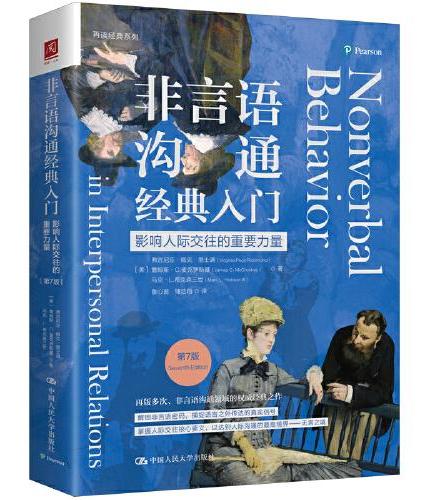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直观的经营:哲学视野下的动态管理
》
售價:NT$
407.0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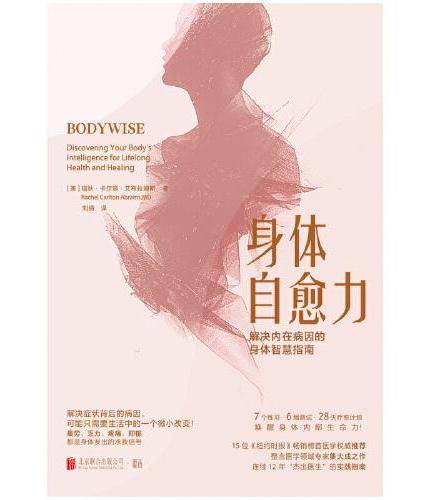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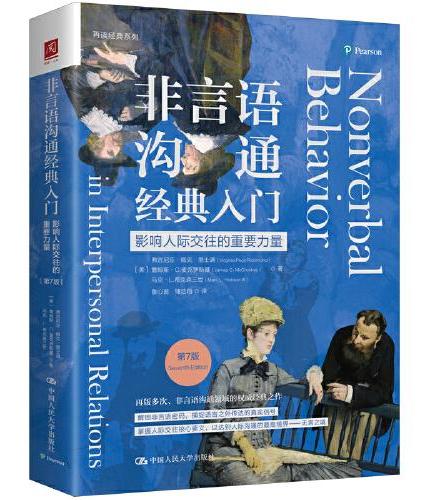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0.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NT$
4998.0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NT$
254.0
|
| 編輯推薦: |
《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王蒙是政客中的文人,那么王小波便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正如他自己所言:“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中国人的尊严》:
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真正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一切尊严都从整体上定义,唯独缺失了个人的位置。然而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同样需要体面地活着。
《你为什么活着》: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活着就好,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
但面对王小波的文字,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沉思:许多年以后,站在时光的分岔口,要如何证明自己来过这个世界呢?
|
| 內容簡介: |
《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是当代作家王小波创作的杂文随笔集,收录了作者的杂文名篇。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时政、经济、人文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主题之下根植着作者的思想内核——始终如一的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
《中国人的尊严》:
本书是当代作家王小波的杂文精选集,收录了《个人尊严》《居住环境与尊严》《我的精神家园》《苏东坡与东坡肉》《奸近杀》等经典杂文。作者以深刻甚至带着调侃的笔调针砭时事,对“个人尊严”“媚雅”“格调”等问题进行了有趣而深刻的分析。
《你为什么活着》:
本书是当代作家王小波创作的散文随笔集,收录了作者的经典杂文。作者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探索与思考了身在其中的个体的生活价值与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阐述观点时的逻辑相当缜密,而笔触又不乏生动有趣,忍俊不禁甚至有些可爱的语言中透露出引人深思的独到见解,对每一个渴望自由与幸福的人而言,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
| 關於作者: |
王小波,当代著名学者、作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云南插队,后转插队到山东,做过民办教师。1974年以后在北京街道当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198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92年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主要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等。
|
| 目錄:
|
沉默的大多数:
序言
沉默的大多数
思维的乐趣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知识分子的不幸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积极的结论
跳出手掌心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论战与道德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我看文化热
文化之争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极端体验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对待知识的态度
有与无
我看国学
智慧与国学
理想国与哲人王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关天圆地方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思想和害臊
皇帝做习题
拒绝恭维
关于崇高
高考经历
盛装舞步
迷信与邪门书
科学与邪道
科学的美好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掩卷:《鱼王》读后
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
《血统》序
《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
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中国人的尊严:
个人尊严
君子的尊严
居住环境与尊严
饮食卫生与尊严
我的精神家园
洋鬼子与辜鸿铭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百姓·洋人·官
椰子树与平等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长虫·草帽·细高挑
卡拉OK和驴鸣镇
从Internet说起
奸近杀
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电影·韭菜·旧报纸
商业片与艺术片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
电脑特技与异化
旧片重温
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欣赏经典
好人电影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有关爱情片
《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
《他们的世界》序
《他们的世界》跋
《红拂夜奔》序
《黄金时代》后记
《未来世界》自序
《寻找无双》序
《怀疑三部曲》序
《怀疑三部曲》后记
《思维的乐趣》自序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关于文体
关于格调
关于幽闭型小说
文明与反讽
关于“媚雅”
有关贫穷
有关“伟大一族”
有关“给点气氛”
生活和小说
我看老三届
苏东坡与东坡肉
驴和人的新寓言
愚人节有感
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
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
你为什么活着:
代序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孤独的灵魂多么寂寞啊
我是一只骆驼
人为什么活着
我厌恶模式化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写作
我的师承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我对小说的看法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盖茨的紧身衣
摆脱童稚状态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关于同性恋问题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虚伪与毫不利己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人性的逆转
工作与人生
体验生活
有关“错误的故事”
承认的勇气
谦卑学习班
优越感种种
肚子里的战争
明星与癫狂
另一种文化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电视与电脑病毒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诚实与浮嚣
拷问社会学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门前空地
卖唱的人们
打工经历
工作·使命·信心
生命科学与骗术
与人交流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北京风情
文化的园地
环境问题
域外杂谈·衣
域外杂谈·食
域外杂谈·住
域外杂谈·行
域外杂谈·盗贼
域外杂谈·农场
域外杂谈·中国餐馆
|
| 內容試閱:
|
《沉默的大多数》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
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一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儿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茨),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儿。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儿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作“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作“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中国人的尊严》
个人尊严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好像都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的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合,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我们就不必细说“文革”中、“文革”前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一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挤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
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假如外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都是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虽然一句话说不清,但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唉!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嘛!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分,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失,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一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当然,现在我把这作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个好处,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
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或则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笔者自己曾在外国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的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也有其二的成分,而且归根结底,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
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地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觉。
君子的尊严
笔者是个学究,待人也算谦和有礼,自以为算个君子——当然,实际上是不是,还要别人来评判。总的来说,君子是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是士人或称知识分子。按照中国的传统,君子是做人的典范。君子不言利。君子忍让不争。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独善其身。这都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时至今日,以君子自居的人还是如此行事。我是宁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我还是以为,君子身上有些缺点,不配作为人的典范,因为他太文弱、太窝囊、太受人欺。
君子既不肯与人争利,就要安于清贫。但有时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前些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北京的一位人大代表发言,说儿童医院的挂号费是一毛钱,公厕的收费是两毛钱。很显然,这样的收费标准有损医务工作的尊严。当然,发言的结尾是呼吁有关领导注意这个问题,有关领导也点点头说:“是呀是呀,这个问题要重视。”我总觉得这位代表太君子,没把话讲清楚——直截了当的说法是:我们要收两块钱。别人要是觉得太贵,那你就还个价来——这样三下五除二就切入了正题。这样说话比较能解决问题。
君子不与人争,就要受气。举例来说,我乘地铁时排队购票,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前面加塞。说实在的,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排队,你为什么不排队?你忙,难道我就没有事?但是碍于君子的规范,讲不出口来。话憋在肚子里,难免要生气。有时气不过,就嚷嚷几句:“排队,排队啊。”这种表达方式不够清晰,人家也不知道是在说他。正确的方式是:指住加塞者的鼻子,口齿清楚地说道:“先生,大家都在排队,请你也排队。”但这样一来,就陷入与人争论的境地,肯定不是君子了。
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流氓横行不法,围观者如堵,无人上前制止。我敢断定,围观的都是君子,也很想制止,但怎么制止呢?难道上前和他打架吗?须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知道英国有句俗话:绅士动拳头,小人动刀子。假如在场的是英国绅士,就可以上前用拳头打流氓了。既然扯到了绅士,就可以多说几句。从前有个英国人到澳大利亚去旅行,过海关时,当地官员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答道:“我是一个绅士。”因为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人不喜欢这句话,尤其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从一个英国人嘴里说出来。那官员又问:“我问你的职业是什么?”英国人答道:“职业就是绅士。难道你们这里没有绅士吗?”这下澳大利亚人可火了,差点儿揍他,幸亏有人拉开了。在英美,说某人不是绅士,就是一句骂人的话。
当然,在我们这里说谁不是君子,等于说他是小人,也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君子和绅士不是一个概念。从字面上看,绅士(gentleman)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如此。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坦白地说,他们有点狂傲自大。但也有一种好处:真正的绅士绝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大战期间,英国绅士大批开赴前线为国捐躯,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君子的标准里就不包括这一条。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不可压缩的空间,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捍卫的意思是指敢争、敢打官司、敢动手(勇斗歹徒)。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尊严的好,假如个人连一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就无法为人做事,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了。
《你为什么活着》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除了这只猪,我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对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斗鸡,后者像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响,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们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儿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动了真格,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人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一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虽然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工作与人生
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
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系副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
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吧。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