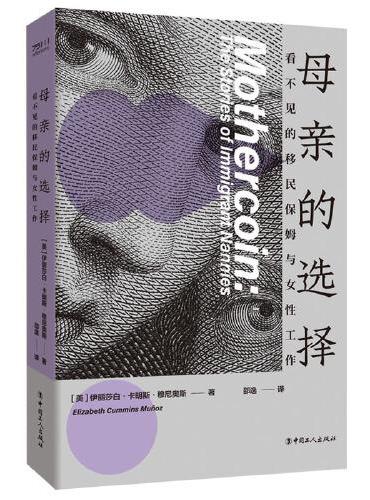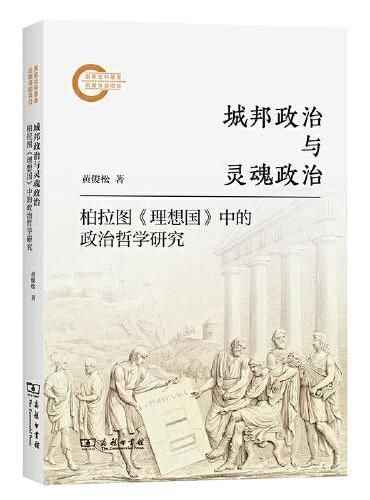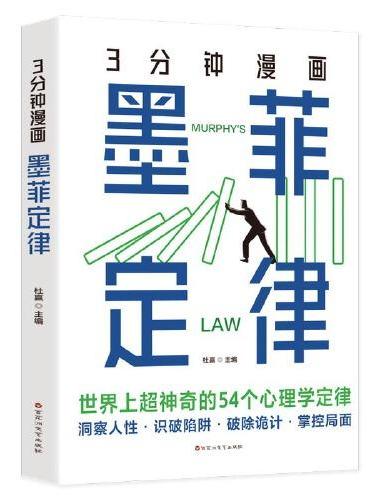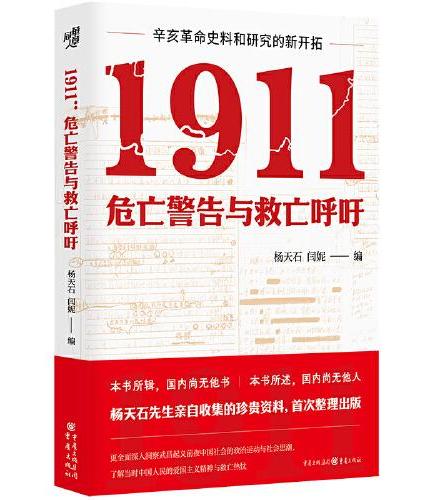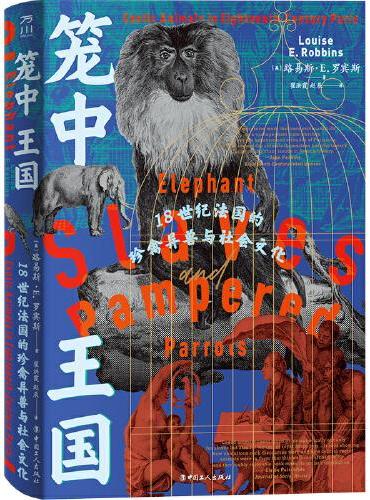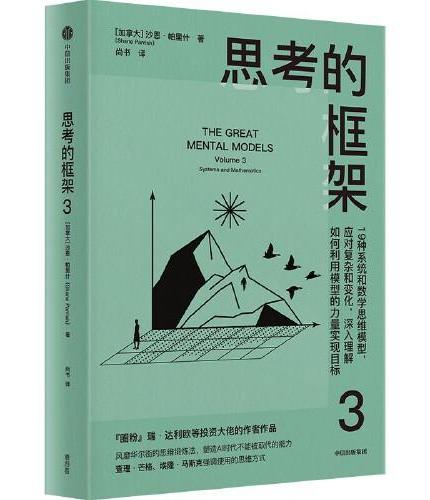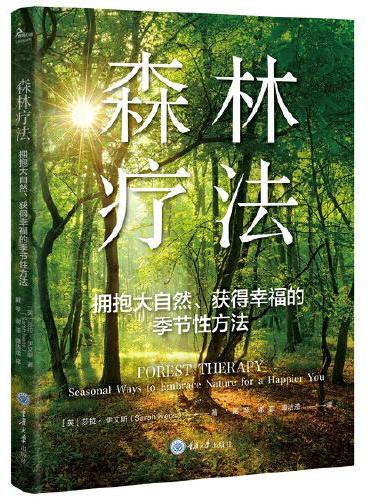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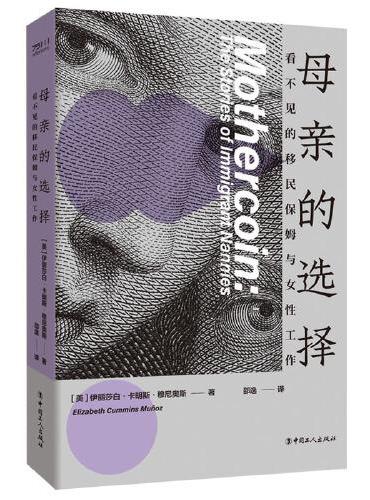
《
母亲的选择:看不见的移民保姆与女性工作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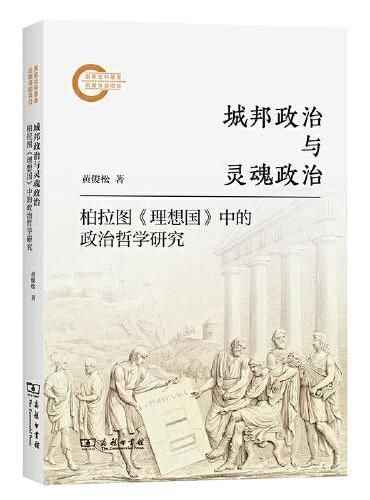
《
城邦政治与灵魂政治——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
售價:NT$
5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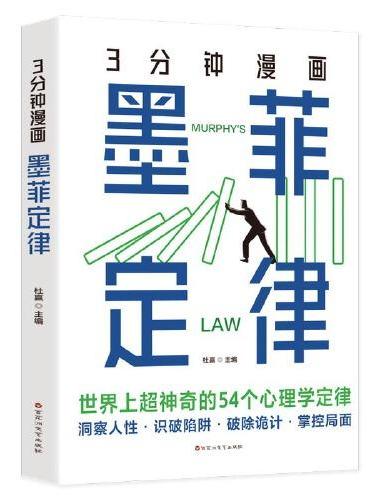
《
3分钟漫画墨菲定律:十万个为什么科普百科思维方式心理学 胜天半子人定胜天做事与成事的权衡博弈之道
》
售價:NT$
2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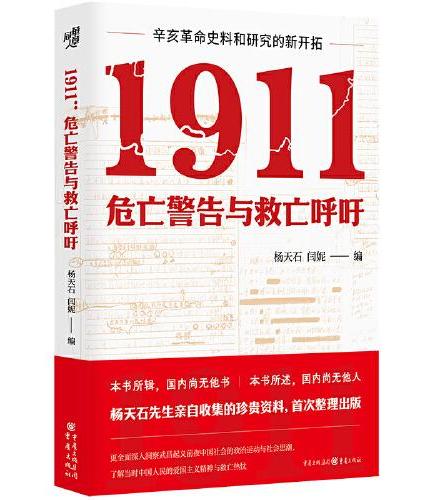
《
1911:危亡警告与救亡呼吁
》
售價:NT$
349.0

《
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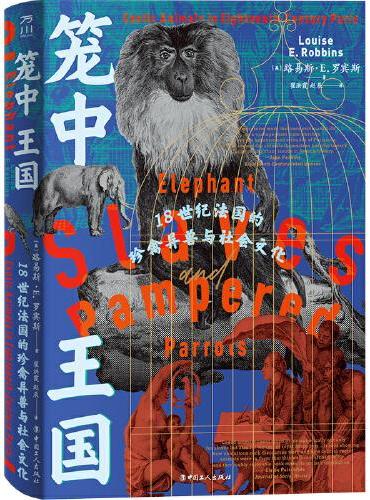
《
笼中王国 : 18世纪法国的珍禽异兽与社会文化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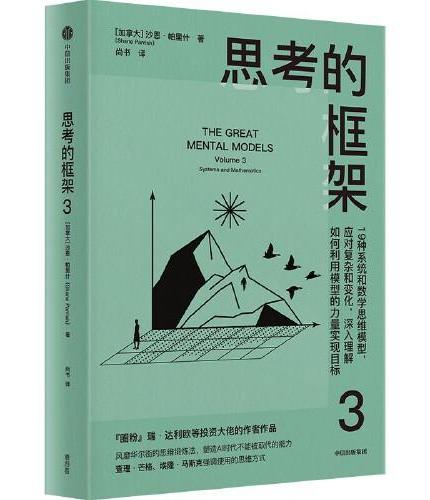
《
思考的框架3 巴菲特芒格马斯克推崇的思维方式 风靡华尔街的思维训练法 沙恩·帕里什 著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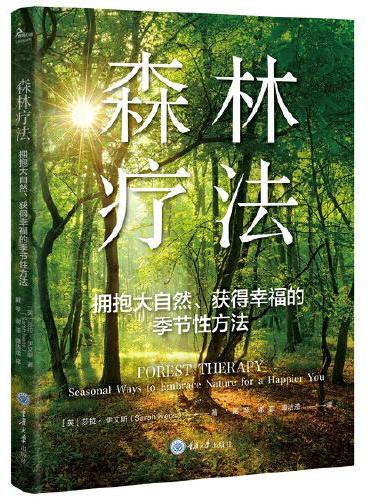
《
森林疗法:拥抱大自然、获得幸福的季节性方法
》
售價:NT$
340.0
|
| 編輯推薦: |
世间再没有一个女子,如她这般爱得寂寞。
向年度巨制电影《黄金时代》致敬之作!许鞍华导演多次表示,拍摄萧红是她四十年的心愿。
最受争议的民国才女萧红流星般耀眼而短暂的一生,和文坛恋人之间曲折心碎的情感纠葛
文字会告诉你,为什么世人对她的故事念念不忘。
|
| 內容簡介: |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她的一生都向往着自由、温暖、爱和尊重,却英年早逝,只留下空灵的文字惊艳了文坛,多舛的爱情和命运打湿了后世人的眼光。
她的一生,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一个弱女子拼尽全力的抗争,在封建的男权社会里,怎会为自己寻得一丝光明和安稳?她的每次抉择,又充满无奈和矛盾,因此一直饱受争议。她是女权主义者,却始终无法摆脱对男性的附属和依赖;她对劳苦大众有着深切的悲悯,却放弃了自己初生的孩子;她视爱情为生命的救赎,却终是没有嫁给此生最爱的人。
好在,她是个作家啊,她是个文字的天才。命运薄待她的,爱情亏欠她的,她在文字里得到了慰藉和补偿。“民国文学洛神”的声名,她也许是不看重的,然而在颠沛的乱世里,人情的疏离间,这个内心敏感的才女,终于在写作中找到了她生命最重要的价值——“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向着人类的愚昧!”
31岁,香消玉殒,任时光再温柔也无法抚平世人的怜惜和遗憾。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个有着美丽灵魂的女子曾写给恋人的信笺:“这不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
| 關於作者: |
|
月小妆,原名张佳。寄居尘世的灵魂柔软的小女子。尘世如酒,不可满饮,纵使寂寞缠绵生花,亦不纵容自己的感情,浅浅爱,缓缓收。迷恋古典的一切,沉迷于古典歌舞琴艺、作诗填词之中,并略通一二。常缈缈而不知今夕何夕,曾被许多人称为,不食人间烟火。文字散见于《爱人》《幸福》《女人坊》等各类期刊杂志。因喜桃花开时烂漫,柔而不弱,曾用笔名桃花如是。已出版作品《遇见最真的自己,唤醒灵性那朵花》《放下爱,超越爱》《剪一段时光,遇见宋词里的忧伤》《明年花好,知与谁同——宋代词人的流年心事》等。
|
| 目錄:
|
序 寂寞,是她一生的爱人
第一卷 梦想是一株开花的树
花曾开过
光阴的油纸伞
蝴蝶晾晒双翼
花朵忘记芬芳
悬崖的冷花
雪瓣,是花瓣的眠床
心若无根
第二卷 月明花满,遗她一身孤清
逃离,是一种宿命
烟锁楼阁
月辞楼,花辞树
焚爱为生
孤岛旅馆
前世今生
第三卷 相逢的终究会相逢
爱是沉沦
因为爱情
满饮暖爱
爱的行囊
太薄弱,是爱情遗留的美
你是,唯一可循的光
月明花满,不如情暖一场
第四卷 生命是一场迁徙
天空不曾留下痕迹
灿若莲花,心若菩提
爱到阑珊
跋涉,一朵流年
光阴生苔
海边筑巢
第五卷 我以灵魂的微光照亮苍穹
灵魂的皈依
上海旧事
珠玉般的时光
灵魂火焰
皈依爱,即使悲凉
第六卷 爱情是含笑饮毒
雨落花台
逃离,到你心灵的客栈
与一座城的诀别
孤独,是逆风的船
第七卷 满载时光,与爱
断肠的旅程
幸福,一扇迟来的天窗
情系呼兰
香消玉殒
|
| 內容試閱:
|
第一卷 梦想是一株开花的树
花曾开过
一束清菊,几支素香,墓碑前松柏掩映,苍翠如初。恍若你将醒未醒的前世。枝叶滴落阳光,光影吞没了喧嚣。你的墓前人来人往,花影扶疏,恰似你容颜不老的今生。一帧小照,四行碑文,写尽你三十一载的韶华。千里之外,那条因你而熠熠生辉的呼兰河,带着童年祖父草帽上的一衔天色,奔涌着,没入这些为你而生的文字。
也许生命的前行,不是为描摹盛世浮华,而是为此心有所皈依。你从呼兰河的冰天雪地里走来,襟袖里兜满冷风,肩膀上悬挂清雪。也许生命的终点,不是寂灭,而是重生。你最终完成了心愿,葬在风景很美的南方。在那里,再也没有蚀骨的寒冷,如刀的冰霜,只有数不清的热带植物,开不败的鲜花。你终于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扫墓的人说,萧红生前寂寞,死后却热闹。她是个多么爱热闹的孩子,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墓碑上镌刻着简简单单的字样:“一九一一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九四二年卒於香港,原葬香港淺水灣,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遷骨灰安葬於銀河公墓。”寥寥五十个字,你的一生。你来了,你走了。是谁在耳边悄吟:“花曾开过,我曾来过。”
故乡是什么?从生到死,每个人都在思索这个简单的问题,却始终未有圆满答案。有时,灵性之门骤然开启,一切好像近了,近了。但当你伸手去捞,答案就像破碎在水中的月亮一样,散了,淡了。渐渐地,我们发现,走得越远,心离着故乡越近。当萧红背对着呼兰河水渐行渐远时,她的灵魂深处生出几许迫切,几多期许。前面,再走几步,或许就是故乡了吧!
就这样,她怀着近乎虔诚的信仰,走过冰封的冷,抱过爱情的暖,握着苍凉的风,拨开漠漠的雨,一直走到生命的深处。她从生走到了死,又从死走到了生。萧红的一生,同三毛一样,背对着故乡渐行渐远,从北走到南。然而,她并无三毛的率性无畏,也并不是以流浪对抗俗世的冰冷。她只是有你我一样的心肠。她想家,但是她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家。那是我们都曾寻找过的答案。只期望宿命终怀着慈悲和善意,让我们的灵魂归于温暖的巢穴,让我们此生不再漂泊无依。
终究,是命运薄待了这个女子,许她以颠沛流离,半生辛劳。而她,以文字为宴,灵性为酒,款待命运以丰盛。她像用尽全力寂寂绽放在山涧的野花,即使无人欣赏,也要美到极致。
或许,她并不美,也没有许多人去探索她的文字里蕴藏着多么美的灵魂。俗世的心肠啊,终究辜负了她。然而,她不悲不喜,不忧不惧。这个曾被誉为“文字洛神”的女子,这个曾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与张爱玲比肩的女子,未曾获得如林徽因般众星捧月的关注,亦无张爱玲炫目的个性、犀利的才情,她的文字是空灵而俏皮的,她的爱是清浅而温润的,她的美是没有侵略感的。她如同星光弥漫于长天,无论俗世眼光,她自有她的闪耀。
1911年,是个多事之秋。辛亥革命爆发,局势动荡不安,黑云压境,湍急的呼兰河,翻卷着,呼啸着,与这墨黑的天际互相厮杀。四处都是压抑的气息,到处都流窜着不安分的因子。那是1911年6月1日,适时,正值阴历五月的端午,屈原殉国的一天。恍若宿命的感召,这一天,萧红来了。她的到来令家人忧喜参半。喜的是20年不曾听闻婴儿啼哭,忧的却是陈规陋习,须得有儿子传承家业。母亲蹙起了眉,父亲冷了脸,只有祖父的笑容照亮了小小婴儿的天。他们给她取了漂亮的名字,张乃莹。她的出生,如一束光,照耀着呼兰河上的天空。
多年之后,《呼兰河传》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语,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后花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但是又发现了这储藏室。这里面无穷无尽的什么都有,这里边保藏的都是我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
不知你可曾相信宿命的缘。我们的一生中,总铭刻着一些人深情的目光,不问缘由,就是喜欢。而一些人却是怎么努力,都无法取悦,无法融入的。萧红与祖父之间,就有这么一段善缘。他是小小萧红所有的光、暖和希望,是她生命伊始那一树一树的花开。从此,在日渐逼近的世态炎凉里,在阅历深重的苦难里,她始终汲取着祖父爱的能量,以爱来对抗世事的冷漠,人情的凉薄。
她的童年并不幸运,倒也不凄苦。呼兰张家是名门望族。虽说到她祖父张维祯那里,开始渐次衰落,然而大家的气数还是在的,托得起她幼小的灵魂。在外人眼里,她是富家小姐,哪里懂得世态炎凉!然而在家族里,她并不是个讨喜的小孩,她是个有争议的孩子。爱她的人,十足溺爱她。不喜她的人,十足冷淡她。于是,世界在她幼小的头脑里分裂成两个,一半火焰,一半冰山,正如她所隐隐抗拒的宅府,与无限向往的后花园,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样。小小的她开始思索,到底是该爱呢,还是该恨?
祖父张维祯原是个读书人,清高淡泊,并不以俗物为念。这些读书人的散淡疏离的性子,却令祖母冷眼相看。在她眼里,一个反反复复擦一套锡器的老人,是那么寒酸而不合时宜。幸也不幸,他那些清高,竟然被萧红悉数继承了去。然而在萧红眼里,祖父简直是神。“祖父是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他总是笑着,笑容温润而遥远,如头顶上狭窄却明亮的天。祖父的爱是流淌的月光,是迢递的垂柳,是扶疏的花影,是濡软的江南。后来,才知道,江南并不在远方,而在心里。若这一生无缘得见江南,那么温润爱你的人,就是你的江南。
她的母亲是严厉的,她不喜欢,只是让她待在母亲这个名词里。她期待时光能赋予她智慧,终有一天,她会明白。
祖母是一件黑斗篷,她也不喜欢,因为祖母曾用针刺伤过她的手指。这倒是有一段典故的。幼时的萧红十分顽皮,尤喜用手指捅破窗户纸,嘶嘶拉拉的声音,每每让她开怀大笑。祖母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终于有一天,当萧红再次伸出顽皮的手指,等待她的不是裂帛般的声音,而是钻心的疼痛。原来,祖母拿着针等在另一端。想来,对于一个三岁的儿童,大人是有法子让她得到点教训。可偏偏萧红是个早慧的孩子,她记住了,而且记仇了,一记就是一辈子。后来,亲友说,祖母也是很溺爱她的。然而她的灵魂太孱弱,需要完完全全的包容,捧在掌心小心呵护,容不下一点点伤害。
父亲是什么?她想了一辈子也没想明白。大约是凝聚在琥珀里的不知名的幼虫吧。历史悠久,却不知来历。
唯有祖父是她童年所有欢笑的来源。祖父的爱,如同江南的春光。若非如此,当命运的粗砂袭来,她又怎能抱守柔情,庇佑童心,此心不改呢?他用爱,守护了爱,打捞了她半生的柔情,漾开她文字里清澈的深情。
她的文字是柔软的、空灵的、跳脱的。你我都曾惊艳于诗词歌赋的华美典丽,却不想另有一种质朴天真,亦能动摇人的心襟。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飞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说话似的。一切都得活了,都有无限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哪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童心童眼,却换不来童话般的世界。这个空灵细腻的女孩,却独自饮下上天赐予的悲伤。那悲伤有一个名字,叫宿命。
看不破的镜花水月,走不完的沧海桑田。每个人都有独自的宿命,每种宿命都是花开花落的完成。也许真有一本命册,上面用鎏金的小楷将你的一生娓娓道来。于是,再深的缘分,也只能隔岸相望,而无法彼此搭救。她像一朵随水旋流的萍花,纵使你我都想在墨色的字迹里将她打捞,却终究只能看她独自挣扎,不问沉浮。风很急,夜很长,我们只能就此别过,从此山长水远,各自安好。
光阴的油纸伞
始终相信,我们来到世间,并非为独自的完成,而是寻找一种生命的融入。你的光阴,我的光阴,你的菩提,我的世界,枝枝蔓蔓地交叠在一起。于是她的爱恋,亦是你的慈悲。你的疼痛,亦是她的执迷。杭州、呼兰,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几乎同时孕育出山川日月的精华。林徽因、萧红,一样蕙质兰心的才女,却因了际遇不同,造就了她们截然不同的命运。假使她们彼此相识,会否围炉夜话,讲一讲开花的树,讲一讲跌入云端的鸟儿,讲一讲雾霭和云烟,讲一讲人间的四月天?
当林徽因在老宅光阴里,推开窗,见一帘空濛的烟云,一拢多情春光,萧红却在遥远的冰雪之地燃起生命的烛光。她的灵魂是轻盈薄透的,一直以为,这样的女子必生于江南。可是命运偏爱捉弄人,她托生在苦寒之地呼兰。那是哈尔滨的一个边陲小境,那里的天是锁住的,地是冻裂的,冬是一座座翻不完的雪山。她被以冰雪喂养,反生出一段琉璃心肠。而那心是脆硬的,带着一抹东北女孩特有的倔强和刚烈。
可,为何光阴对林徽因始终是静好的慈悲,而对于萧红,却吝啬于那一点一滴的柔情?对于林徽因是捧在手心的供养,对于萧红却是踩踏入泥土的扼腕?于是相信,是有造化这回事的。有的事,有的人,纵使你拿命来争取,都未必能复你想要的答案。只得面向菩提,还生命以至纯,以勘破红尘的痴,不怨不怼,用今生的苦,照亮来世的路。
对于萧红而言,也许只有童年的光阴是慈悲的。虽然童年是那永远蒙着黑的堂屋;是父亲阴晴不定的脸,和深沉冷峻的目光;是祖母威严的黑斗篷;是母亲扯着嗓子敲的锣。然而,毕竟还有后花园。那是她和祖父的“避难所”。当他们被家人排挤时,就手拉手,一起躲进后花园。一个是清癯飘逸的老人,一个是天真娇憨的女童,亦步亦趋,侍弄花花草草,共享天伦之乐。后花园是她的第三时间。在这里,时光漫漫,可以濯足,光阴无限,可以挥霍。
后花园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堂。祖父侍弄瓜果,萧红“拈花惹草”,时而在祖父浇水时,突然抢过水瓢浇散上天空:“下雨啦,下雨啦!”祖父播下新鲜的种子,萧红则随着蝴蝶好奇地追来跑去。她的世界与别人不同,她的早慧,让她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她的眼里,不仅花鸟虫鱼,连土墙都是有生命的。她会淘气地拍打土墙,把土墙的每一个回应,当做沟通仔细聆听。“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她的世界是静态的,时光是凝滞的,各种生命哪怕最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纵情地跑着笑着,她如同生机勃勃的向日葵,沐浴着阳光,自如生长。
泰戈尔说:“你若爱她,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她,并且给她自由。”这恰是萧红一生孜孜以求的爱。然而,只有两个人给予了她,一个是祖父,一个是鲁迅。那天使般明亮通透的爱,原本就是尘世里不多的琼浆玉液。她要的不多,只求绛珠草上的那滴甘露,那已是最极致的奢华。人世间风沙太大,欲望太脏,哪里容得下清清白白的女儿心?
孩提时代的萧红是淘气异常的。后花园有棵果树被祖母的羊破坏殆尽,玫瑰树倒是长得繁盛,她便打起了玫瑰花的主意。这一次,她没有踢飞菜籽,而是趁祖父弯腰的时候,把玫瑰花插在他的帽檐上。祖父感慨道:“今年的雨水真大呀,咱这些玫瑰开得这么香,只怕是二里路也闻得到。”小小的萧红笑得几乎哆嗦起来。待到祖父回了屋子,祖母、父母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祖父才知道个中缘由。从此,萧红与祖父有了共同的“秘密”。只要她说一句:“爷爷……今年春天的雨水大呀!”爷孙两就笑做一团。
也曾有那样的旧时光,心中不染尘埃,快乐俯拾皆是。那时,我们有好多好多能力,比如取悦自己,比如深爱他人。那须臾的快乐,比白驹更为急遽匆忙,风迷住了眼,阳光颤巍巍地跌落花枝,只是霎那间,沧海变成了桑田。我们已无法将自己识别,恍若身体里,住着别人的灵魂。生命变成一座空城,你我各自怅惘,却终了无凭据。我们紧紧攫取着贪欲,却不相信幸福是摊开掌心就能铺满的阳光。或许人生再也没有哪一个阶段,能令我们缅怀一如生命的最初。又或者,我们念念不忘的,不是旧时光里的旧人旧事,而是那个纯白如初,目光澄澈的自己。
后来,萧红曾不吝笔墨,用至美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后花园:“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过来。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心底的明亮折射外界的光明。这个时候,她的世界是完全打开的,无遮无掩,纤尘不染。也许,我们只有用最初的童心去面对最真的自然,才能除下面具,卸下心防,此心从此光明,不问沧桑。
进了堂屋,也未必就是黑暗。有了一颗无暇的童心和澄澈的双眼,在哪里发现不了光明呢?光明藏在祖母的衣橱里。光明是帽筒里柔软华美的孔雀翎,光明是祖母躺箱上姿态各异的古装小人,光明是老式的洋钟,里面住着黄头发眼珠乱转的小洋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珍稀古玩?还有箱子柜子筐子篓子、花丝线、绸子条、烟荷包、搭腰、祖母绿的戒指、美轮美奂的耳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幼年的她,眼睛里住着好奇,脑袋里住着精灵。她时时冒着被洁癖祖母骂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将手冒冒失失伸向这些玩意儿,用抓过泥巴的小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还有一把宝贝小锯子,锯不下桌子角,可以用来锯馒头吃。她还发现了一盏灯笼,吵着闹着让爷爷点上,提着东屋西屋兴奋地跑,直到把灯笼摔成碎片。碎片也是好看的,怎么看都看不够。生命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再后来,她翻找出的只有时间。祖母挨个跟她讲:她拿了大姑的扇子,又点了二姑的灯笼,这双绣花鞋是三姑的……然后,她看到了祖母的哀伤。二姑她,好多年没着家了。好多年?年幼的女孩盯着祖母寂寥的眼,她读不懂哀伤,却依然微觉凉意。时光是什么呢?是那条一去不回头的呼兰河,是带着疼痛找寻的路,还是揣着泪触摸不及的伤?原来,时光只是一把油纸伞,雨下在童年的天,却浇湿了成年的心。
蝴蝶终于飞过了墙。她跑过墙去,世界延伸在她的脚底。她看见了呼兰河多得数不胜数的民间活动。在那个萨满教盛行的区域,贫穷的人们多期望借助神灵的力量,庇佑生活的安稳。跳大神的鼓声,让敏感细腻的小萧红生出了“人生何如”的叹息。盂兰节放的漂亮河灯,笙、管、笛、箫的和鸣,像香气四溢的油墨,将萧红的生命浸染出自由和多情的底色。
最令她难过的,是那些贫民、她家的房客身不由己的挣扎,以及鲜明的贫富两极分化。善良如祖父,也曾劈面打过一个好心送迷路的萧红回家的车夫,仅仅是因为淘气的萧红不小心滚落下来。萧红不解,祖父说:“有钱人家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那些交不起钱的房客齐齐在父亲、祖父面前下跪,他们愿意租“下雨会走”的房子,仅仅为了廉价的房租。民间疾苦如同一鼓重锤,打在了萧红心里。后来,左翼文学的路,当是她一早做出的抉择。她要做人民艺术家,写普通人的故事,哪怕凄怆或者挣扎。
愿以文字烹煮哀伤,这世界再无饥寒与困苦。或许,作为一个女子,终究是不能有男子那般作为。然而我以我精灵般的存在,让你相信这世界一切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虚构。
她是这样一个女子,苦难带给她的并非沉重,而是轻盈。她的文字里看不见挣扎,只有淡淡的光。不侵不扰,却给了你在困苦中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也许是为了午夜梦回时,那株花,那棵树,那座淹没在时光洪荒中不曾老去的后花园。
蝴蝶晾晒双翼
太薄弱,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当白昼已经过完,依然可期待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夜深长,却有比深长更隽永的芬芳。昙花凋零,自有一室为之储藏清香。清香散尽,还有回忆锁住。所以,即使走到生命尽头,又谁敢说真的过完了一生?诗人会把逝去世界的繁荣带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字字留香;生命消亡,亦可化为不灭的精神之光,前行的路途熠熠生辉。
祖母死了,接着,母亲也死了。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人离她而去。然而,对于亲人,人们往往有太多太复杂太纠葛的情感。你信与不信,亲情也是一种缘。有的缘无限亲近,如同前世就是至亲。比如小萧红与爷爷。有的缘纵使心里亲笃眷念着,面上却总是淡着,仿佛隔着什么。有许多许多的话,还没出口,就被融化在火中,破碎在风里。那个人呵,亲也亲不得,疏也疏不得,想放,却又放不下。有多爱着,就有多怨着。可怨着怨着,却忍不住噙满泪水。他是我们生命里无药可医的伤痛。
当一向严苛的母亲即将离世时,萧红已经懂事了。那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火迅速蔓延开来。这一把火,蔓延到了张家。萧红的母亲姜玉兰,是与萧红截然不同的人。她简直是王熙凤这样的人,是世人眼里精明干练的好媳妇。呼兰张家,虽说世袭繁华,到如今早已呈衰颓之相。之所以还能支撑,全靠姜玉兰的治家本领。这一年,萧红的二姑家韩家,家财被大火焚烧殆尽,齐齐投奔张家。张家日子本已只是表皮光鲜,偏偏韩家人好吃懒做,只知抽大烟。姜玉兰眼见自己半生的努力,都要付之一炬,又碍着三从四德的规矩不便抱怨,急火攻心,居然病重不治。
萧红在《情感碎片》中记录了母亲去世的场景:
“许多医生来过了……他用银针在母亲腿上刺了一下,他说:‘血流则生,不流则亡。’
“我确确实实看到那个针孔没有流血……我站着。
“‘母亲要没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在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里取出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
“‘小洋刀丢了从此就没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也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那是孩子的时候。”
生离死别,未免会有真情的流露。然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再也没有比小洋刀更重要的事物,因为那把小洋刀,装载着厚重的母爱。那母爱,是我们生命的最初所有的财富。尽管母亲有时无暇眷顾,在俗世事物中分给孩子的爱太少。然而,爱终归是爱。即使后来的继母对萧红,甚至比母亲更为宽容、忍让,然而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打断骨头连着筋,是怎么扯也扯不断的。
经年之后,她或许一边写着:“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是母亲。”一边满怀遗憾,当初为何不紧紧抱着母亲痛哭一场,用眼泪化解怨怼,用最深的爱,照亮母亲来世的路。水里的游鱼兀自沉默,飞鸟与浮云相亲相爱。或许,一切怒放都是凋零的先奏,而一切相聚早已预演着别离。人的一生,有的人能够相伴走一段路,有的人却可以相携走完一辈子的路。对于亲人,再不想割舍,也只能放手。
姜氏是一个极其入世的人,她的世界里不仅仅有萧红。她要将精力照拂整个家族。她并非文化人,亦非闲人,所以分给萧红的爱,自然所剩不多。而脆弱敏感如萧红,所需的爱,却是祖父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关注。祖母死后,萧红吵闹着要搬去跟祖父住。闲来无事,爷孙两人开始读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每次读到“春眠不觉晓”,小萧红就高兴地拍着巴掌说,这声音真好听。“重重叠叠上小楼,几度呼童扫不开。”萧红声音朗朗地念着,激动之时,竟大喊大叫起来。爷爷说:“房盖都要被你掀走了。”母亲说:“再喊,揍你!”萧红安静了一会,淘气劲儿又上来了,拼命大喊大叫。萧红是好奇的,爱思考的。当读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爷爷讲了一遍,她依然蹙眉问:“桃树开花不就结了桃子了吗?桃子不是很好吃吗?爷爷,咱门前的樱桃树开花不开花?”幼时的启蒙,让小萧红对于音韵和色彩均有了清晰的认知。她读诗,意思倒是囫囵吞枣,然而却为其中声韵之美,画面之绚烂深深震撼。她心灵的艺术之门,早在这时已经渐渐开启。
四季有交叠,白昼有交替,落叶归根是生命永恒的主题。然而,最悲凉的人生是,望乡而思,却终身不得回归。回去做什么呢?竹林疏箫处,花影扶疏里,旧的年华轰然倒塌,新的繁华纷纷伫立。回了乡,或者触目所及依然是熟悉,然而却已换了天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亦是我们童年读过的诗,当时不觉得,一别经年,倒成了心底不能碰触的痛。萧红问爷爷:“爷爷,我也要离家吗?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也不认得我了吗?”童言无忌,却似乎冥冥中有预感。客死他乡的宿命,也许在那时就一语成谶了。
后来萧红以乡土作家的身份进入文坛,与那时的环境当是分不开的。那是她最早乡土意识的启蒙。人世的苍凉,世态的炎凉,总能触动萧红那颗天然的,对生命对人性的悲悯之心。虽然出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然而萧红的封建根苗却是早已被剔除的。周遭邻居的生活,野蛮的婚俗制度,贫苦线上挣扎着的房客,还有她所依恋却被家族所讥讽取笑的有二伯。伴随着夕阳暮色、胡琴幽怨、秦腔嘹亮,萧红的世界里竟骤然充满了这么多有灵性的“物件”。荒凉的、悲悯的、喧嚣的,每一个都渲染和勾勒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夜是寂寥的,庭院是荒凉的,人们是艰辛却又快乐的,因思想是无边无垠的。多年之后,当我看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时忘言。她的世界竟然有这样多的东西!虽然她重章叠唱地说“我家院子是荒凉的”,可我,却透过荒凉看到了一幅车马喧嚣,繁华垂注的清明上河图。原来人的内心容得下数万亿恒河沙,而一粒沙里竟有大千世界。她的可贵当是心若琉璃,所以没有边际。
人生在世,只有少数人是拥有梦想的,而大部分人为三餐所迫,被名利所擒,跌跌撞撞地走,赎不出自由。生命便由最初的华丽,逐渐布满虫眼,最终渐渐腐烂。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最初的梦想。“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的感得到寒冷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冷,因此而来了悲哀。”
夜色寂寥,天际间疏落几点星子,却照亮了人们的眼眸。再小的光芒,也是光芒。即使不能燃尽九州所有的不公,最少,能够温暖饱经沧桑的心。萧红以生活为书,不断品读,渐渐初尝到人生百味。她发现,蒙昧的思想,并没有浇灭人本性中对于光明和自由的渴求。众生尽管麻木,不懂得孜孜以求,然而,那颗心却是温润如玉的。她润了润笔,看墨色在青莲磨洗中微微漾开,如同马蹄踏碎的夜色。她提笔写道:
“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并不是繁华的,也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者希望光明,这样都不是。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到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萧红一生所求,是自由与光明。她在外界里找,在书中找,在命运里找,在爱情里找,在生里找,在死里找。她似一个不断问路,却永不言弃的人。她把生活这本书翻到生命的终点,然后,我们再来翻她。却发现,怎么也翻不完。
她的童年却翻完了。
花朵忘记芬芳
花朵眠于冬季,却忘记了芬芳。初醒的梦想,必然比蝴蝶的翅膀更为薄弱。是年,当少女林徽因在老宅光阴里手握书卷,托腮凝思时,少女陆小曼风情万种地拿起画笔,倾身研墨时,此刻,9岁的萧红获得了上学的权利。曾想,这些出生在民国交界的美人或才女,她们可否会在某个时刻心有灵犀,意识到世界上总有一个角落,总有那么几个人,虽然永无机会谋面,却与自己的灵魂惺惺相惜?
世界的另一端总有一个我,以不同的生命形式,一起看这风云日月的变幻莫测,一起听这高山流水的悠扬深长,一起赏这轻云蔽月、流风回雪的凄美婉转,一起享这烟柳亭台、花开花落的琉璃心肠。所以,遇见未遇见,相识不相识,早已不再重要。只求你安好,我便是晴天。当林徽因在康桥芳心萌动,诗性湍飞,小曼或许已经初嫁为妇,而萧红也实现了她一生最大的夙愿——读书。生命向她们露出最动人的模样。
我们都渴望在动荡的岁月里,彼此安好,却最终只能看到掌心里破碎的星光。生命是吝啬的,也是凄美的。生命最深的伤痛在于,它想让你失去什么,就会让你尽情地得到过什么。暮春时节,花朵总会美得窒息炫目,正因如此,凋零的时候才会更加惹人伤心。怒放,从来就是生命有关幸福的谎言。像烟花,璀璨在歌舞升平的夜,遗落在虚无的天空。惟其怒放过,才会尝尽生命的悲苦。可是作为一朵花,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于是,只求生命淡若流水,轻若云烟,不悲不喜,有所皈依。只求一场痴心,慢慢点染,徐徐求取,不要竭力争夺,才能日久天长。只求相爱的人,缓缓用情,缓缓用爱,然后才能偎依着慢慢到老。
这场痴心,对于陆小曼是情劫,而对于萧红则是书恋。一直以为,情未必是对人,对物也是一样。古时有女子恋琴,有男子痴画,琴亡画毁,他们亦不贪生,其情不可谓不深,其心不可谓不痴。萧红一生的悲剧,是命运的薄待,亦是痴心所至。太痴的心,必然无法与世俗相融。太痴的情,终究容易被辜负。
果真是命运的安排,五四运动说来就来了。吹过帝都是一粒石掀起千层浪,吹到遥远的北国边陲小镇呼兰,却是风暖入怀。新文化的兴起带来了女学的兴盛。懵懂的萧红,尚不懂什么是反封建礼教,只知道自己可以有一间教室,躺得下灵魂放得下心。
她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不眠不休地汲取着知识,即使放了学,眼睛也粘在书上,家人唤她吃饭她总不应。只觉得光阴太短太短了,经不起挥霍。泛黄的窗纸渗漏的灯光,夜比一匹马的鬃毛更为光滑厚软。灵感却也像一匹野马,总也驯服不了。她试图抓住什么,它却甩甩尾巴扬尘而去。于是,她愈加迷恋,不能自拔。她用旧了光阴,换取这韶华的盛宴。很多年后,在《呼兰河传》里依稀流淌着当年的心情,她记得那间校舍的砖瓦红墙,一草一木。
那时,她生母过世,祖父老迈无法照拂她,父亲待她严苛而继母又冷淡,然而,幸之又幸,父亲因了在教育局工作的缘故,非常顺应潮流,赞同女孩读书。他说:“谁能出人才,我就供他读书,女孩子有本事更要抬举,在我们张家不讲男尊女卑。”父亲的开明,算是萧红狭小窗子里渗透进的一点阳光。但这一点光,已是足够。
她异常用功读书,家里的藏书阁已经放不下她野马般的心。也许,这个聪慧心肠的女孩意识到,在这一生中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光,已是不多不多了。可她依然希望,光阴再过得慢点,让她好在看清人世沧桑前,享用生命给予她的最后一点温柔。
她的居室简洁素雅,除了几样简单必须的家具,没任何多余的摆设。而她的灵魂却是一间宽敞的客栈,古往今来的圣贤、文人墨客、才子帝王都可以进来坐坐。她的心亦如童年的后花园,洋溢着天真的喜悦。她时常捧着《宋词》手不释卷,她的心有着雕梁画栋的精致,她迷上了画画,常常为邻居描花样,设计衣服的纹样。翻阅她之后的作品,虽然遍及民间疾苦,恍若扎根于俗世,灵魂却是轻盈跳脱不染尘埃的。她从尘世的疾苦打马而过,长袍掠过灰蒙蒙的天,却瞬息潜入光明的末端。她抚摸过尘世沧桑的脸,却肌肤通透一如初生。她是苦难的看客也是过客。对于苦难与责任,她虽身之所系,心却不曾蒙尘。
古往今来,才女大多有比较优渥的家境。而才子却有许多生来落拓。女子是朵娇柔的花,精华之气如花蕊里的光,需被小心捧起,细细呵护,与男子的粗粝自然不能一般对待。才气和灵性是一个女子最宝贵的东西。
三毛曾说,小时候家境优渥,一向不知物质匮乏为何物。而张爱玲是李鸿章之后,家世鼎盛自然非常人可比,尽管没落了,然而书香门第的气息还在,足以滋养她的浩瀚文墨,玲珑心肠。林徽因、陆小曼莫不如此。正因早年不为外物所累,才会比寻常人更孜孜以求精神的殷实,才会有比寻常人更敏感纤细的心思。然而,这也是造成才女多不幸的根源所在。为物质所苦的人,灵魂是麻布,经得起风沙,蹉跎得了岁月。才女的心却是一袭华美的锦帛,日晒了不行,虫蛀了不行,稍有不慎,即会破碎如冰裂。可见物质匮乏也不是坏事,无暇顾及灵魂,自不会将生命向更深的苦中蔓延。
求外物不得,是人生一苦。求精神之不得,则是苦上加苦。物质尚有形,精神却是无形。比如,世人心心念念的精神之爱,究竟生了何种模样?是化蝶的哀婉,垓下之围的凄迷,秦淮河的桃花扇,牡丹亭里的情深不知所起,故一往而情深?抑或是古书典籍里的惊鸿一瞥?只是惊鸿一瞥,故而口口相传。可,这点至纯至美的精华,偏偏是才女梦寐以求的。求取,求取,终是求而不得。伤在发肤可见得,伤在灵魂无药可医。所以,才女的灵魂莫不是千疮百孔。
此刻的萧红,是呼兰张家的阔小姐,出入自有马车和车夫接送。然而她却不要这些,跟同学一起走路上学。她生性淡漠,无视权势,亦懂得惜福。有人说,萧红一生性子太纵了些,自由过度,而责任不顾。我想,她是一脚在红尘,一脚在槛外。人在红尘,却不为红尘俗物所拘。权势门第于她不过如浮云,起初,她只想做在岁月里看淡烟云的女子,埋首书卷,不问世事。懂她的,大约只有庭前的花开花落了罢。
她想与世事无碍,现世却偏不给她安稳。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萧红带领一帮女学生募捐,公演。她演出的《傲霜枝》展示了其在文艺方面过人的天赋。萧红第一次汇入民族抗争的大潮,她带头剪掉辫子,并且帮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剪掉辫子。这一下,张廷举坐不住了。封建官场变幻莫测,其中压力不可谓不大,萧红此举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仕途。然而,他所在的教育部门又处于潮流前端。于是张廷举百般纠结,虽未拿萧红治罪,父女两的隔膜也是日渐加深。
萧红天生一颗济世的心,于是她的文字亦是关联着苍生的疾苦。当一场暴雨袭击了呼兰,导致贫苦农民家破人亡,萧红动情地写了一篇《大雨记》,轰动了全校。于是才女之名散播开来。
萧红从不趋炎附势,也深恶痛绝不公正的事情。高小毕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萧红终生难忘的事儿。那一天,公布成绩的红榜迟迟没有贴出来,直到毕业典礼前10分钟才贴出来,萧红的名字赫然在榜首。第一名!这个令人激动的名次,却让萧红耳根发热,头都不敢抬起来。她平时只能得前10的名次,这个结果明显不是真实的。果然,她得知她的父亲张廷举要来观礼,此时,张廷举处在教育局比较重要的部门,校长为了讨好他,将萧红列在第一。
萧红尴尬极了,她似乎能感觉到同学的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有几句话不经意地飘入她的耳朵:“你看,张乃莹和张廷举长得多像啊,那脸盘,那鼻子。”敏感若萧红,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捱的日子。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一步一步挪上舞台,代表学生做了演讲,也不知道毕业歌都唱了些什么。倒是张廷举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从那一刻开始,一个呼之欲出的念头就在她胸中涌动:离开小镇,离开呼兰!到一个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平等的乐园去!出去、逃离,也许意味着艰险,也许意味着重生。
她的灵魂是公正的。这是才女中不多见的品性。与张爱玲沉浸于小资情爱中的精明和冷漠不同,萧红的一生有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慈悲:愿天下苍生不再有愁苦,愿每一个灵魂都被平等相待。可惜,这个愿望太过奢华。
她是误入红尘的天使,本该与尘世两不相干,安然度日,却偏偏忍不住挣扎抗争,逃离再逃离。她以微弱的反抗,去呵护生命的烛光。她以天堂的眼,慰红尘的心。最终收获的,却是满心的伤。她锁住了自己的光阴,想用爱来解除尘世的苦,却独独赎不出自己的自由。
光阴过不够啊,鹅黄柳绿,碧瓦红墙,多少韶华转瞬间没入时光洪荒。那些才女、情事、愁绪,纷纷被吞没,直到渐渐不闻。然而,对光和暖的渴望,却劈开时空,纷至沓来。于是我们铭记她们,一如铭记我们生命里所有最初的美好。
一朵花,渐渐开得从容,惊醒了时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