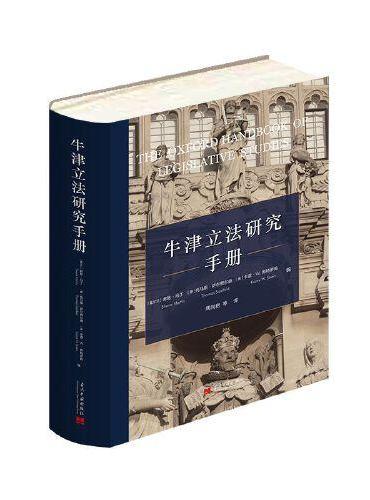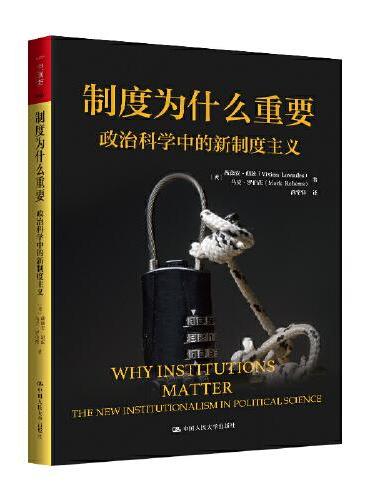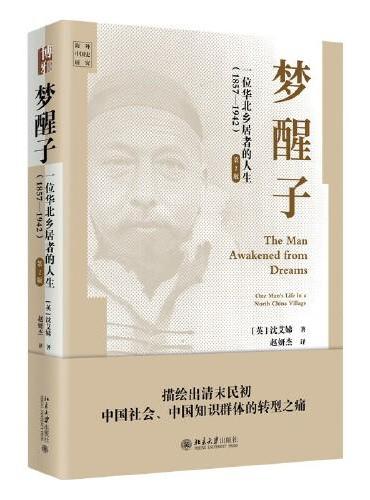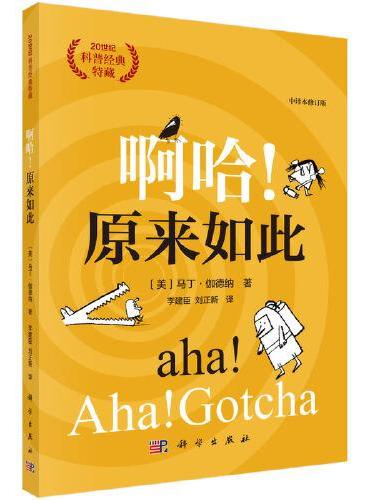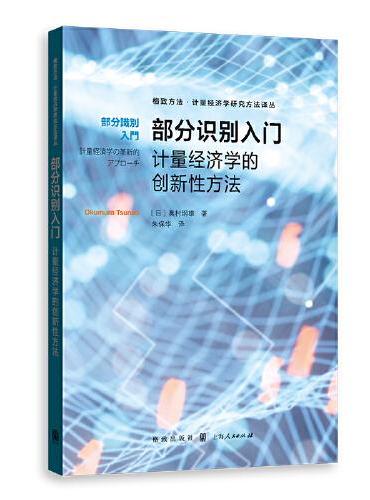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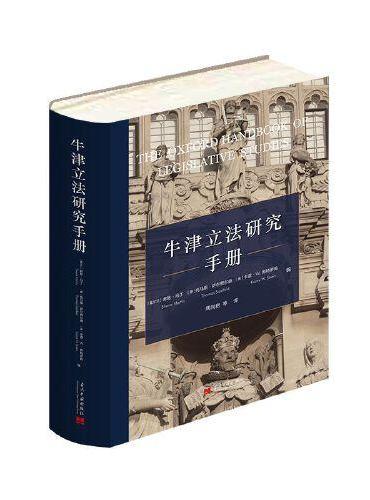
《
牛津立法研究手册
》
售價:NT$
1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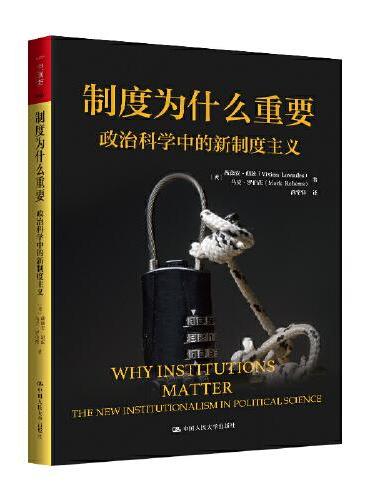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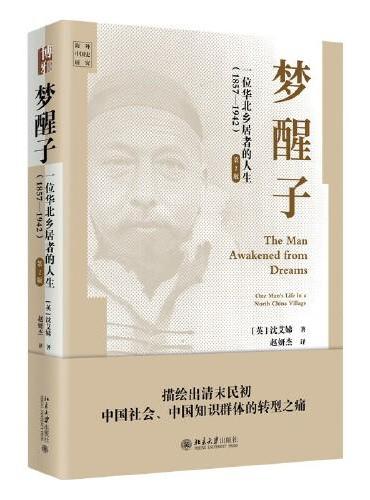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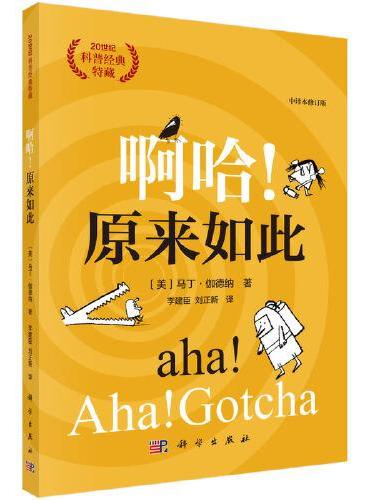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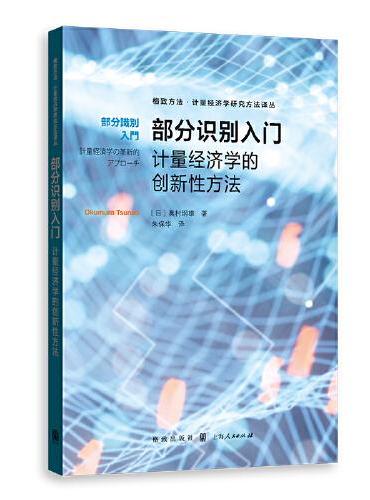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NT$
225.0
|
| 編輯推薦: |
|
正宗学院风格,得到诗人雷平阳首肯的研究性著作。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部研究诗人雷平阳诗歌创作的学术性著作,作者主要探讨了雷平阳的意义及昭通经验与雷平阳写作的关系,分别从雷平阳创作中的空间构建、地理性--心理性写作、时间塑形、生命关怀、经验呈现、语言努力、叙事探险和意象的生命痛感品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
|
| 關於作者: |
|
杨昭:彝族,47岁,云南昭通学院教师,曾获得首届云南青年诗歌大赛优秀奖、2007年度滇池文学奖、第二届高黎贡文学奖等奖项。
|
| 目錄:
|
一、引论:雷平阳的意义及昭通经验与雷平阳写作的关系
二、“针尖上的蜂蜜”——雷平阳作品的空间构建
(一)土地——雷平阳写作的先行条件
(二)“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这逐渐爆炸、膨胀的过程
(三)城市——与乡土对立的怪兽式存在
(四)雷平阳的地理性——心理性写作
三、“从阅历中来”——雷平阳作品的时间塑形
(一)“用我一生的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雷平阳写作的时态置换术
(二)“巫趣”沛然——雷平阳写作的返源旅行
(三)与传统文化命脉的对接——雷平阳作品中时间的深度
四、向死而生、以生克死——雷平阳作品中的生命关怀
(一)对现实破相——雷平阳作品为生命开路的基本形式
(二)大象国王的胜利——雷平阳作品中生命的悲凉与尊严
(三)人需要先杀了自己,才能完成杀狗的过程——生命的罪性与生命的不幸
(四)精神的上升或肉体的下沉——人的生命活动的两种方向
五、“纸上有片旷野”——雷平阳作品的经验呈现
(一)“把铁箭变成了一只多余的脚”——雷平阳眼中的世界本相
(二)记忆是另一种现实——雷平阳作品追忆的“故乡”和“故事”
(三)“写诗就是说人话”——雷平阳的语言努力
(四)“刀尖直抵心脏或骨头”——雷平阳意象的生命痛感品质
(五)在两个世界之间滑动——雷平阳的叙事探险
六、结语
|
| 內容試閱:
|
让我们拂去当下文坛浮躁、迷乱的功利尘埃,从无数狼藉的写者中,拾起一个珍贵、厚重的名字,一个“汉语言的劳动模范”(诗人老六语)的名字——雷平阳。
雷平阳惯以凌厉而又节制、直率而又厚道、决绝而又隐忍的笔触去抒写他正反同体的经验世界。这个一眼看上去似乎有些木讷的写者,他笔下的世界却何其的鲜活灵动、繁复多姿、情深义重、夺人心魄:他极其注重语言艺术的精纯度,从不以抽象的思想和观念去简约现实,并借此去吓唬、折磨、搅扰读者,而是用及物的、有力道的、有心性和有质感的诉说,用顽石崩裂、火星飞溅般强劲而又出人意料的意象,用饱满、丰沛、贴身的感性细节,去表达他那强烈、诚挚,极为精细而又复杂、矛盾、痛苦的生命体验,并使众多读者的感性生命体验也因之而被激活;他的形象世界情感沉郁、想象奇崛,看似略显光感幽暗、气氛神秘,内里却深蕴着让人心安的祥和、踏实、明亮与温暖;他精心安排他的个人经验与普泛的人生经验邂逅相遇,将它们并置或重叠在一起,小中见大,平中见奇,旧中翻新,粗砺雄浑,浩荡宽阔,古今辉映,既具有开源性传统的来头,又具有现代性视角的观照,重量感十足,纵深感凸显。他低调、诚恳而又大气磅礴: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总是饱含着切肤的疼痛感,他的疼痛始终是新鲜的、当下的、在场的、现在进行时态的、撕心裂肺的;另一方面,他的文字方阵又总是富有体温的,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当他自述他的沉郁与纠结时,其实是在替无数被世界与生活逼近绝境的生命表达他们共有的痛楚与悲怆,是在为他们舔伤口,替他们呻吟和嘶喊;当他细察自然或者浮生时,其灵魂始终是仰望着、惊叹着、疼惜着和敬畏着的。阅读雷平阳的作品,不仅让人感觉到他的文字间弥漫着泰戈尔式的谦卑、挚爱与托尔斯泰式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更让人感觉到它们还充满着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宗教精神的深沉的注目和悲悯的长太息。
三十年来,雷平阳一直在默默而坚韧地经营、训练、指挥、调度着他的文字方阵,浇铸着他黄钟大吕的语言故乡,徒劳而又顽强地试图为他自己的心灵,也为广大读者的心灵寻找或构筑一个值得信赖的栖居之所。他的内心深处十分清楚:由于时间的提速和人心的沉沦、朽坏,在现实的世界里失乐园的悲剧早已成了定局,这个栖居之所只有在用灵魂供奉着的特定的语境中才可能存在。因此,他对语言的谨严执守到了呕心沥血和“偏执”、“愚顽”的地步,为了校准语言使其通向存在,他甚至不无书生气地坚持每一篇作品都用钢笔或毛笔写成,在文坛上传为佳话,或者笑话。而其实,他是力图用古老的书写方式来滋养文字,来献上自己“敬惜字纸”的那一份谦卑与虔诚。他的文字是活的、灵动的、元气充沛个性饱满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三十年来在语言上的惨淡经营,使他的文字有着令人吃惊的内聚力与爆发力,他在诗歌、散文、小说、田野考察等领域的创作硕果累累,异彩纷呈,齐头并进,互相增益。他的写作捉牢了“存在物”,并通过个体性与主体性对“存在物”的注入,成功地显现了“存在”。这位痛苦和矛盾的写者把他的整场人生都当成了一次修炼,他强忍着内心分裂、冲突所引起的剧痛,不断地将自己撕开,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自己,始终坚持着经典性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一股强劲的创造活力,每有力作问世,辄引起文坛及众多喜爱他的作品的读者的一片欢呼。凭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诗歌与散文所作出的实质性贡献,毋庸置疑,雷平阳是属于中国的,他是当今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作家。
把他辽阔、丰富、独特、壮丽的文学创作硬塞进“昭通文学现象”、“昭通作家群”、“昭通经验对雷平阳写作的意义”的框架里来考察,仅仅出于包括本文在内的整个“昭通文学现象调查”课题研究与行文的需要。从这一视角来管窥雷平阳的文学世界,会使本文的撰写不可避免地留下诸多的疏漏、缺憾与谬误。但笔者又确信这种考察的角度和方法也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首先,时空的具体性及作为个体的写者置身于其间的早期人生经验,以一种宿命般的力量,以一种不由分说的方式,强有力地设计、塑造、影响了该写者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表达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到了他书写的质感。诚如雷平阳所言:
“……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来昆明,我曾问他:‘在你的艺术世界的背后,是否藏着一个村庄?’……其实我想说的是,也许每一个艺术家的身后都存在着一个艺术的源头,犹如生命之于母体。之所以问谷川,是因为我的写作全围绕着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具体地点来展开,目前我正写作的诗歌和小说,无一例外。”(《天空中捉鸟?另附》,见于雷平阳著《云南黄昏的秩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28页)
雷平阳的“犹如生命之于母体”的“艺术的源头”不在别处,正在于他恶狠狠地爱着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土——云南昭通,那正是他领取到人之初的生命胎记以及他个人的语言指纹的地方。雷平阳视野辽阔,涉猎深广,精神海拔高远,其书写活动却始终抗拒过故土云南昭通的遥控。美国文艺理论家艾伦?塔特对与此相类似的写作现象有着十分精当的见解,他说:
“一个人要是想概括整个大陆,想包罗万象,他便一无所有。归根结底,能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都已经扎根或决定扎根的某一条街、某一个社区。只有空间、运动、广袤千里是不会产生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H?R?斯通贝克选目并作序、《世界文学》编辑部编:《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1版,第11—12页)
雷平阳曾经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犹如生命之于母体”的“艺术的源头”对创作的重要性。对此现象,我的解读是他急欲寻找一个为他自己所独有的,同时又深藏着旧时代精神的坚固可感的物化对象。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一切文学都视为作者的一种隐蔽的自传。认识,不管它有多么辽阔,多么深远,其最隐秘的目的却在于自我认识。对于写者来说更是如此。“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我国的许多小区保安对来访者常用的这一连串追问,常常让我们惊悚地想起我们在认识世界时,又何尝不是在认识我们自己?是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当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摹写这个或表现那个时,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借被摹写、被表现之物来摹写和表现我们自己,从而支支吾吾、勉为其难地回答大神般的小区保安向我们发出的当头棒喝?对于写者来说,他的真正的历史就是他的心灵史,而心灵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心灵最理想不过的安放之处,莫过于曾经给写者的人之初喂过初乳的故土。一个人长大后无论去到哪里,故土与故土情结的消失都总是一场社会的、道德的与艺术的大灾难。
其次,是否清醒、自觉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冲动并将其付诸行动——沿着生命历程所经由过的轨迹去回溯、重温、确认、强化、升华生命经验,在情感上、文化上乃至血缘上主动后退、寻根、认同并皈依这种不断累积着、增殖着的经验,常常正是决定一个写者能否向前走得更快、更稳、更高、更远的后劲所在。莱布尼兹常常说:“后退才能跳得更高。”我心叹服!在《雷平阳诗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的封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
雷平阳文字中到处弥漫着的这份挥之不去的乡愁,正是在故土、在往昔经验中确立他自己有根据的、可持续发展的写作方式的明证。在许多个场合,雷平阳都曾多次嘲笑或者自嘲过“那个抱着地球仪写诗的家伙”:
“胸怀天下地写作,满眼都是艺术、哲学、爱情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想着背负青天朝下看,把世界尽收眼底,可慢慢觉得凡大而无当者,犹如蚂蚁承受不了雷霆。是的,一切都是逐渐缩小的,自己也便跟着小,比小还小。大与小之间的关系,犹如置身草原,爱上成吉思汗很容易却徒生绝望,爱上一只蚂蚁谈何容易却心生感恩。”(见《在神示之前,一切都只是尽人事——朱彩梅、安阿凤对话雷平阳》,《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09年第11期。)
昭通仅仅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其它地方,才是昭通;雷平阳仅仅因为他不是任何一个其他人,才是雷平阳。作为个体的写者,雷平阳既是某种特定的文化的一个因子,是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分子,同时又是不可被其他人重复、替代的他自己。如此,昭通经验之于他的写作的意义才得以显现出来。写者要想建立独特的、意义丰沛的文本,必先建立独特的、意义丰沛的自己。只有成为一名个人化的写者,向广大读者奉献出个人化的经验,写作活动才能避免同质化,才能获得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曾经生活、正在生活和将要生活。所有人的生活都有一个毫无例外的同时又是极为无趣的共同之处:降生,存活,然后死去。作为读者,我们想知道的不是这个老早就已经知道了的常识,我们感兴趣的是仿佛仅仅只为写者所独有,对于我们来说却显得很陌生很有吸引力的完全个人化的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唯一者的经验。这就好比说我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我自己的家,要是我想旅游了,我绝不会想到在自己家的各个角落转着圈圈“旅游”,我想到远方去,到那些能够让我激动的地方去。写者最令我们读者激动的地方,就是他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与我们很相似,内里却注满了他自己专有的经验汁液之处。
要想让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显示出唯一性的特征,就需要回顾这个人的生活史。外在的生活史大家都彼此相似、大同小异,内心的生活史即经验史则彼此间有着天壤之别。从整体上来把握雷平阳的作品,便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有着十分鲜明的向他自己生命的来处回望、后退、反刍的特点,他那粗黑有力的文字,套牢了个体生命史在往昔一个个阶段、一个个点滴细节中所蕴含着,并在他心灵深处不断发酵着的况味。这种回望、后退、反刍的姿势的意义在于:虽然写者自己在早年的那副尊容,以及他曾经做过的或梦想过的一切都早已经过去了,有的甚至死去了,但只要他对自己的从前始终保持着回望、后退、反刍的深情姿势,现在的他的形象便是一副活着的遗体的形象,同时又是一副领悟者、感恩者、新生者、复活者的形象。此外,因为回溯往昔,使他明白了未来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他还是一副前程未可限量的朝气蓬勃的初生者的形象。当雷平阳沉入对往昔的回望、后退、反刍时,要想完全摆脱他在故土云南昭通所获得的经验是不可能的。
云南昭通是雷平阳的个体性、主体性精神觉醒、萌芽并开始生长之处。其实雷平阳近期作品的诸多特点,早在他多年前生活于昭通时所创作的诗文中就已有了雏形和端倪。那些在云南昭通获得的、窖藏在心底的经验,历久弥香,随着个体性、主体性精神的不断成熟、稳定和厚积,雷平阳对它们的表达也越来越体现出深加工、精加工的趋势。这些被不断反刍着的云南昭通经验,对雷平阳而言绝不仅只具有写作资源的价值,更是他的精神世界的构成要件,它们在雷平阳的文字里默默呈现着存在与命运的种种意味,在性格上早已跟身心绞痛着的雷平阳同构,在实质上早已成了雷平阳的一个个替身,它们都姓雷。
尽管早已身居异地昆明并常常在省内外、国内外各处游荡、考察、行吟,但因这位忍痛的写者和不懈的行者始终梦魂萦系着故土云南昭通,故而将“昭通文学现象”中最富典型性和“昭通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作家之一的雷平阳纳入本文划定的框架范围来考察,也似无大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昭通”之于雷平阳写作的意义与“昭通经验”之于雷平阳写作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昭通”只是对雷平阳肉体生命早期成长的一个具体可感的时空设定,它只为雷平阳的生命感受提供了一种条件、对象与可能,它之于雷平阳写作的意义更多地在题材方面表现出来,而无法完全限定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与写作历程。生命的意义主要凝聚于精神而非肉身,而这个灵性的生命从一个地方所领受到的滋养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是昭通人,同样是“昭通经验”,在我这里是浅尝即止,在雷平阳那里则是贪得无厌;我得到了一小瓢,而雷平阳得到的却是一片汪洋;我的“昭通经验”深度约为十八厘米,雷平阳的深度则有可能是十八公里。必须看到雷平阳个体性、主体性精神在形成“昭通经验”时独有的渗入方式和他的艰辛努力,而不能硬拿“昭通”这双小鞋去套在雷平阳的那双“昭通经验”的大脚上。雷平阳的“昭通经验”是成长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是不断更新、升级和扩张的,是现在进行时而非过去完成时的。批评界有些人借“昭通”、“云南”之类的地名以及雷平阳在诗文中频繁出现的大地上的种种事物,就硬要“盛情”地将雷平阳写作的意义打入“地方主义写作”、“地域性写作”、“草根写作”、“乡土写作”的死牢,我猜不透是他们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呢,还是有着什么不便明说的用意。雷平阳在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的对话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现代性眼光对他的地域性经验的穿透:
“对‘地域性’写作,我们必须审查写作者的视域、幅面和经验,同时还应该关注其指向和开放度。众所周知,诗歌书写的语境和旨趣已经远离了中国古代诗人所持有的天人感应的世界,传统诗意早已荡然无存,在此背景下,一种在场的、基于当下的、拔地而起或掘地三尺的写作,也就成了必然,如果我们仍然无视泊来之物和边界拓展,总是沿用陶渊明等古代诗人的符号谱系,地域势必会成为一座过时的美学古堡。我的认识,这是个走神的时代,从浩浩荡荡的大城到群山背后的村庄,很多东西都魂不附体了,为此,‘兽’与‘鹰’、‘走进’与‘走出’的关系,我只能用‘灵魂出窍’来与之对应,我总是让自己的灵魂在进与出、天与地的双向航线上不停的往返,以此回避‘夜郎自大’和‘锦衣夜行’…… 如果必须说‘地域性’,我觉得处理它与‘现代性’的最佳办法,只要你以‘现代性’的眼光去体认地域文化,你就会发现,地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往往更具‘现代性’,所以这貌似敌对的两个邻居,其实是肢体相连的兄弟。(《宁静的力量》,见雷平阳的新浪博客,由朋友替雷平阳建立并管理。)
在《答安琪十二问》(见雷平阳新浪博客)中,雷平阳又说:
“我心安处是吾乡。其实,我真正写作故乡昭通市土城乡的文字并不多,而是有些事件、念头,写作愿望,我只能将其放到“土城乡”之上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在土城乡我生活了十八年,对世界、生命、大自然的原初认识大都形成于此,少小经验可以说就是一口永不枯竭的井。需要风景,故乡的风景写起来肯定情真意切;需要河流,故乡的河流就是自己的血管,写它,怎么也不会轻易打滑;需要人物,父老乡亲最动自己的肝肠,写起来自然最贴心。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写作,我才能获得写作的不可遏制的动力,而写作本身也就合理地拒斥了一些悬浮感。由此说,土城乡在我的写作中,类似于一个永恒的母体。再说,在思想、欲望、美学都“大一统”的今天,任何地名都是可以置换的,“昭通市”可以换成中国的任何一个“市”,关键是所谓的地域性是否因巨大的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土城乡又是我写作过程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阅读雷平阳关涉到昭通经验的作品,怎么读我都觉得有一种悼词的性质在它们里面。在致悼词的时候,巨大的悲痛与深深的感恩混杂在一起,对逝者生前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一刹那间都涌上了心头,却又往往不知从何说起。逝者生前对致悼词者的千般恩情与万般欺凌,都被空前深情的记忆潮水浸泡得肿胀无比。致悼词者一边颤栗着、哽咽着,一边又在心底里意识到这个永远离开了我们的逝者,必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未来心灵的成长。而生者在未来活出一份精彩来,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那被雷平阳诸多作品深切追悼的逝者,就是“村庄”。
一方面,在雷平阳的艺术世界背后,确实藏着一个岁月与路途无法遮挡住的 “村庄”,一个艺术的源头,这使他的文字在发力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坚实、可靠的支点;另一方面,这个“村庄”又只是雷平阳的一种心绪、态度、情感和回望的姿势。与其说它是昭通市土城乡欧家营那真实存在着的一亩菜地、两座瓦房、三条沟渠、四块田畴、五棵老树、六个乡邻,不如说是雷平阳一直在用灵魂与文字供养着的安心之所。说到底,诗人最可靠的写作资源是他的灵魂的容貌和变化,而不是外在的时空的构成,更不是这种具体、确定的时空对他的限定。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灵魂在碰到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时的遭遇、反应以及显现。有的初学写作的写者以为文学就是用“优美”的语言和花里胡哨的技法描写一下事物,反映一下生活,抒发一下感情,殊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地硬将还算是过得去的作文误当成了文学作品。他们的写作只触及到了外在事物的表层和“认识”、“感情”的浅层,离灵魂的层面还差得很远。如果把写作比作游泳,把对“村庄”的灵魂痛苦体验比作大海,那么你穿着小短裤套着救生圈蹦蹦跳跳地扑向大海,跟你扔掉救生圈一口气向下潜入三米、三十米、三百米……真的不骗你,你所能领教到的大海的滋味是有很大区别的。越是优秀的写者,越是敢于在自己灵魂的深海里往下潜沉的人。“这是个走神的时代”,现实的“村庄”、“家园”早已被异化甚至早已被铲除,但是,拒绝迎面而来的履带,始终保持着对“村庄”的诚挚怀想,始终保持着对“家园”的执着追寻,明知回不去偏偏就忘不了要回去,这一忠贞不渝的情感与绝望而激愤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村庄”与“家园”!如今,地理意义上的那个村庄早已被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糟蹋得不成样子,而在雷平阳的内心深处,任何力量也无法污染、拆迁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村庄”。她是一个雷平阳不忍在浊世中说出的词,是他在炎凉世态中突然忆起的一抹暖意。她会在他的守望中成长,会“女大十八变”。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回眸中,她将永远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她是那么的小,小到雷平阳走到哪里都一直随身将她携带,但她是一个世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