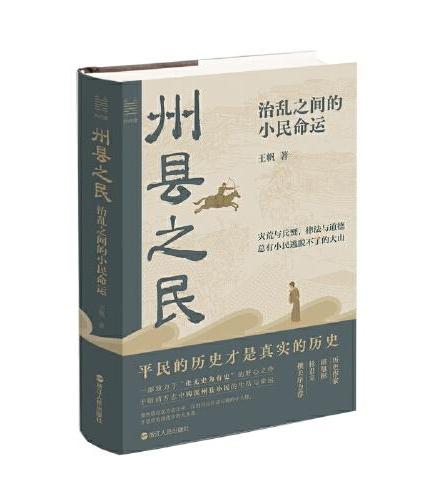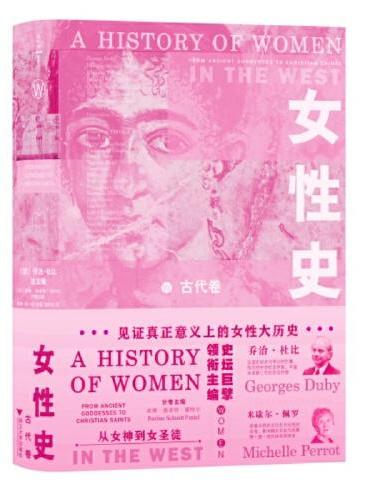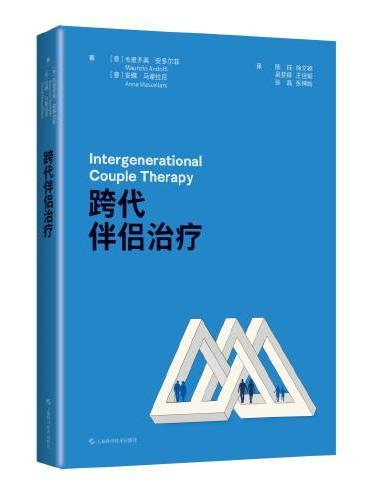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NT$
440.0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NT$
440.0
《
精华类化妆品配方与制备手册
》 售價:NT$
990.0
編輯推薦:
这本书刚刚完稿时,曾因多重阻力未能出版。作者只能印制百余本在老友间传阅。今天,我们非常欣慰地是,这样一本关于“文革”记忆的真实故事终于可以呈现给广大读者。
內容簡介:
这本书向我们透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历史。带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重演一段曾发生的 “荒谬”历史,体会在大环境下人性的改变、扭曲;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不溢美,不隐恶的立体式回忆录,向人们讲述个人坎坷的生涯,剖析自己曲折的心路。是成功的,供人家借鉴;是缺点,任别人批判。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一点他们这些耄耋老人走过的路、蹚过的河、爬过的坡、跌过的跟头。倘真能如此,也就够了。
關於作者:
叶笃义生于1912年,944年加入中国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起协助民盟主席张澜工作。他曾参与了民盟创立与发展的许多重要活动,与司徒雷登、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过从甚密。他的经历是以救国、兴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缩影。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以“特嫌”罪名被关押四年之久;1978年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以后曾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目錄
前言1
內容試閱
我的四个朋友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