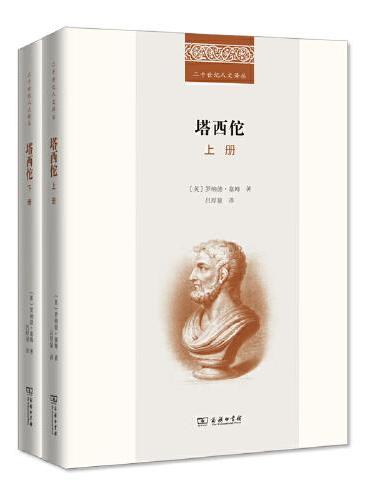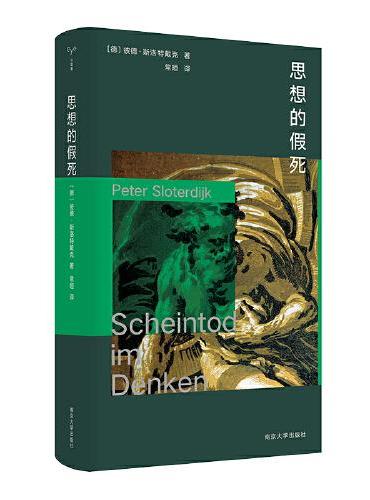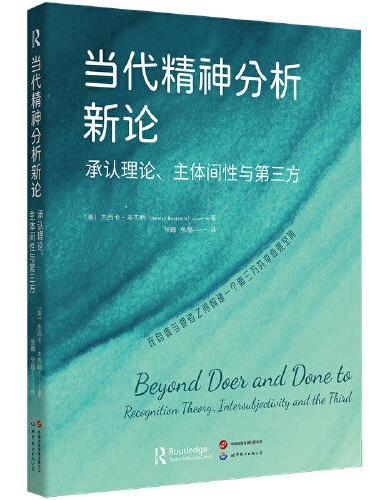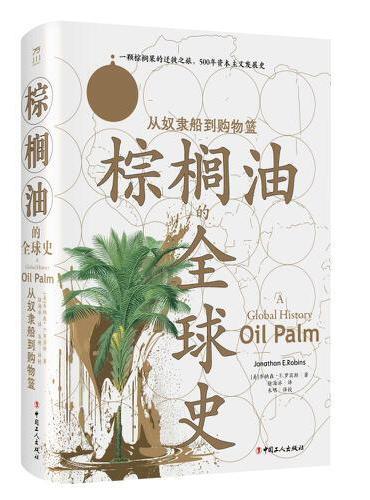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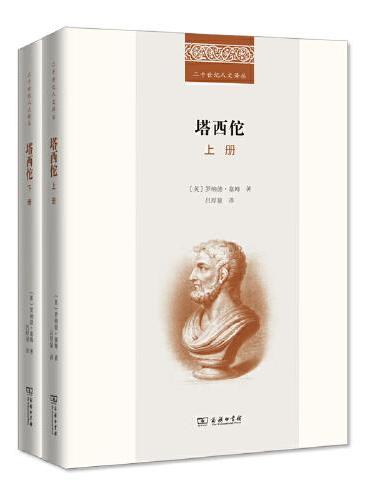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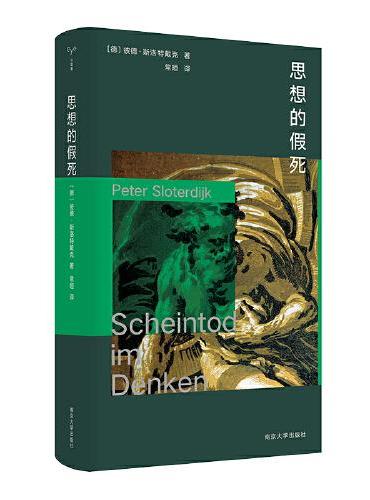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思想的假死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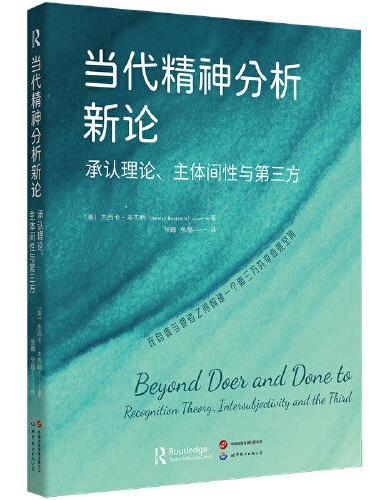
《
当代精神分析新论
》
售價:NT$
43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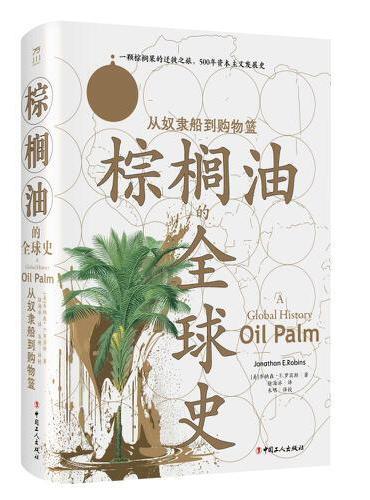
《
棕榈油的全球史 : 从奴隶船到购物篮
》
售價:NT$
440.0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1400.0

《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950.0
|
| 編輯推薦: |
本书是“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的传奇老奶奶姜淑梅2014年最新作品。
姜淑梅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曾入选“新浪2013年度三十大好书”“豆瓣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得到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专题推荐,《新周刊》《南方周末》《读者》专题报道,以及王小妮、梁文道、许戈辉等名家鼎力推荐。
《苦菜花,甘蔗芽》延续了《乱时候,穷时候》的风格,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平民史。
|
| 內容簡介: |
《苦菜花,甘蔗芽》是姜淑梅的第二部作品,是《乱时候,穷时候》的姊妹篇。本书分为《老家女人》《老家男人》《百时屯》《在东北》四部分,延续了第一部的写作风格,语言通俗凝练,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记录了作者亲身与闻的中国老百姓的故事。
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来以后,在北京开了个读者见面会。
有个女孩想问俺啥,她叫了声奶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说的啥俺没听清。
她这么难过,俺觉得对不起她,就说:“孩子,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本书来。”
俺这辈子跟弹花锤子似的,两头粗,中间细,经历的事太多了。
——姜淑梅
|
| 關於作者: |
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二十多年家属工。早年读过几天书,忘得差不多了。1997年学写字,2012年学写作。2013年4月起,部分文字刊于《读库》。
作者阅历丰富,历经战乱、饥荒年代,笔下故事篇篇精彩传神,每个字都“钉”在之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部分文字面世后,好评如潮,感动了众多读者和网友,为老人赢得了众多“姜丝”。
2013年10月,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得到中央电视台“读书”、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梁文道“开卷八分钟”等专题推荐,《新周刊》、《南方周末》、《读者》等专题报道,并入选新浪好书榜2013年度三十大好书、豆瓣读书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
2014年8月,出版第二部作品《苦菜花,甘蔗芽》。
|
| 目錄:
|
序
俺的故事接着讲 姜淑梅 001
老家女人
女老缺 003
爱莲 006
小妹 016
干绝户 025
三嫂 030
百时屯的媳妇 036
赔钱货 039
傻闺女 044
洗头 048
月亮地里讲故事 051
王门李氏 055
三样饭 061
戏迷婆婆 063
大姥娘为啥挤眼睛 074
黄明珠 077
老家男人
家族长 089
被胡子绑架的“亲戚” 093
明白人 097
亲爹找上门 100
穷得担不起自己的名字 104
继卜 107
恨乎 112
士平 114
白果树庄的傻子 118
四大爷还愿 121
三哥 124
爷公公卖牛 131
百时屯
上黄水子 137
时家场里 141
百时屯的井 145
百时屯的庙 148
庙台子 151
郭寺 154
锅屋 157
热死人 159
外扒户子 161
瞎子家 164
小时候咋玩 168
打架 173
穿戴 176
老辈子留下的规矩 179
赶会 190
种牛痘 193
吃苹果 196
逮鹌鹑 198
于家正骨 201
唱扬琴的 204
冯家家庙 206
傅家茶炉子 210
在东北
逃荒 217
刚到东北 221
第一次盖房 230
拉帮套的 234
五十多年前的狼 237
丁家和狼 240
忆苦思甜会 243
提洪林 246
孙家人 249
郭八 253
大病 256
车祸 259
|
| 內容試閱:
|
【序】俺的故事接着讲
姜淑梅
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来以后,在北京开了个读者见面会。
有个女孩想问俺啥,她叫了声奶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说的啥俺没听清。
她这么难过,俺觉得对不起她,就说:“孩子,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本书来。”
俺这辈子跟弹花槌子似的,两头粗,中间细,经历的事太多了。
俺上面有仨哥,大哥比俺大十七岁,二哥比俺大十四岁,三哥比俺大五岁。俺爹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闺女,仨哥他都没抱过,就抱过俺。
俺奶名叫小四,都叫俺四妮儿。听大嫂说,有一天,爹从城里回家,抱俺出去玩。爹是干净人,这是他头一回抱孩子。把孩子抱出去一会儿,他一个人回家了。
娘问:“你抱的孩子呢?”
爹说:“在场里玩呢,那里有很多小孩。”
“四妮儿不会走,她咋玩?”
“四妮儿开始不会走,走两步坐下了,自己爬起来再走。现在走得可好了,喜得哈哈的。”
娘不信:“四妮儿会走了?”
爹说:“你看看去。”
娘到场里一看,真的会走了。那时候,俺一周岁多,从这个怀里到那个怀里,没大下过地,会走了,都还不知道呢。
从俺家出门,走十步,左边是大井,右边往东十米是大水坑。娘就怕一眼看不到,俺掉坑里、井里。后来,二哥教学,在百时屯庙里办小学,娘让二哥把俺领学校去,就是给她看孩子。
二哥给俺一块石板、一盒石笔。去得晚,书都发下去了,人家都两本书,俺就一本语文。
学校离家近,俺家在道南,学校在道北。学校天天有早课,上算术,上体育,上完课回家吃早饭。他们都去,俺不去。吃完早饭,俺再跟二哥去学校。
学校不收学费,有三十多个学生,有十四五岁的,还有结完婚去上学的,就俺一个小闺女。没谁跟俺玩,也没啥玩的,俺玩语文书。时间不长,书皮就没了,这里掉个角,那里掉一块。
二哥看见俺的书,要打俺手板,没打就把俺吓哭了。
二哥说:“你看看同学的书,谁像你?不知道爱惜书!”
俺怕二哥。
俺不爱学写字,爱念书歌子,第一本语文前几课,俺跟着他们背会了。
二哥考俺:“你背语文。”
俺高高兴兴给他背:
天亮了。
弟弟妹妹快起来。
姊姊说:“太阳升起来了。”
妹妹唱:“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明光光。”
二哥笑了,说:“行了。”
背是背会了,拿出来哪个字写黑板上,俺都不认得。
二哥说:“以后念书,用手指着念,比着书上的字写。”
第二回发书,二哥给俺四本书:语文、算术、常识、修身。
这回俺知道学,不祸害书了,还是跟不上趟。
第二册书没学完,俺家搬到城里。把家安排好了,二哥把俺送到女子学校,叫俺上二年级。教俺的女老师一个姓宋,一个姓商。俺没书,还啥都不会,天天挨手板,有时候打得手肿起来好高。
有个同学叫姚桂兰,她比俺大两岁,上三年级。看见俺天天挨打,她把二年级课本送给俺了。有书比没书好多了,但还是跟不上趟。
俺是收了麦子去城里的,到了秋天就说有情况了,八路军要打巨野城,老师学生都逃走,到农村亲戚家去了。从那以后,俺再没上过学。
六十岁那年,老伴死了。大闺女让俺学字,她想叫俺消愁解闷。她爸刚死,俺学不进去。当时她在北京读书,俺知道她心里难过,心想:要是俺会写信多好,能安慰她,逗她开心。再想:闺女叫俺学字,那俺就学着给她写信吧。
那时候,俺住在秦皇岛的旅店里,等着处理车祸的事。店里的服务员没事了,俺说一句话,叫她们帮俺写个字样,俺比着写。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好了,再往信纸上写。就这样,一次一次求人写字样,一次一次比着写,一封信几行字,俺写半个月,邮走了。
那年,俺给她写了两封信,就停下不学了。
俺胆小。老伴死了,俺就怕黑天,一夜一夜睡不着觉,睡着了就觉得老伴在俺身边躺着呢。还不敢说害怕,怕吓着孩子。两个侄子在大庆开饭店,承包食堂,俺去帮忙,白天干活累,晚上睡得可香了。
老伴去世三年以后,小闺女要生孩子,把俺接走了。给她看孩子的时候,大闺女又让俺学字,俺又捡起来学。
咋能学字快点儿呢?俺想了个办法,自己编快板,让大外孙女给俺写出来。
孩子小,她睡了,俺就比着写;她醒了,俺就抱着她念。自己编的快板,一遍一遍念,就认识了;一遍一遍写,俺就会写这个字了,轻易忘不了。
有一个快板,编完写了很多遍,俺还记得:
打竹板,响连环,听我把老人的心愿谈一谈。
老太太进花园,手拉花枝想当年。
花开花落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年。
老婆观罢花园景,转身回到家里边。
老婆沙发上坐,孝顺的儿女听我言:
娘死了,买张席子三道缠,深深的坑,埋得严。
亲戚朋友不给信,不叫他们多花钱。
儿媳妇听了这些话,拉拉板凳坐跟前,
伸手拉住婆婆的手:娘啊娘,你说这话俺心酸。
现在老人都长寿,你老也能活到一百三。
等到你老去了世,俺扎金山扎银山,扎童女扎童男。
扎个黄牛肥又大,雇上一帮好喇叭。
大车小车排成队,俺们披麻戴孝送灵前。
安达卖健身器材的地方都有体验中心,免费做体验,俺也去。排队等着的人多了,那儿的老师就让大家上台演节目。
上台表演那天,俺给这个快板加了几句话:
老婆听了哈哈笑,不要不要我不要。
好儿女心疼娘,给我买张大锗床。
俺逗笑的话,小闺女当真事了,花一万八千八百元,给俺买了个最好的锗石床。
那时候,俺也自己编歌,让大外孙女写出来,俺学写学唱。唱熟了,俺也到台上唱。
这样用功不到一年,就泄劲了:俺又不考大学,学写字有啥用啊?以后,就放松了,光认字,不写字了。光看书,也有长进,越认越多,孩子的小人书都能看了。
过去平平常常的事,打仗啊、挨饿啊、批斗啊,现在都成了好故事。第一本书出来以后,俺跟辣椒似的,老了老了还红了。
有个记者问:“奶奶,你的梦想是啥?”
俺说:“俺不知道啥叫梦想,俺知道啥叫做梦。写作,出书,是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这回成真的了。”
为了写好第二本书,俺跟大闺女回了一趟山东。那半个月里,俺娘儿俩天天忙“上货”,上回来不少新鲜货。
俺有个打算: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也不用多厚,一本书十多万字就行。
以后,俺还得接着上货,接着讲故事。
女老缺
百时屯的人都知道,来云他娘是女老缺。
老缺,就是胡子。
她爹就是老缺,家住孙官屯,出去弄钱,让人在东湖里弄死了。东湖里在巨野东边,听说就是现在的微山湖那片,湖很多。
那年,来云他娘十八岁,大辫子过腿弯。听说爹让人弄死了,她把大辫子往头上缠了几道,骑着马就去了东湖里,给爹报仇。
咋报的仇,百时屯人不知道,她也不说。
在百时屯,来云他娘跟俺娘最好,她比娘大十多岁,但得叫娘二奶奶。两个人经常一边抽烟,一边说话。百时屯的女人里,就她俩抽烟。
她问:“二奶奶,人家女人都不吸烟,你咋学会吸烟的?”
娘说:“二儿子小时候,俺家摊上官司,把俺愁得学会吸烟。”
娘问:“你咋学会的?”
她说:“俺爹叫人杀了,俺总想给俺爹报仇,想不出好办法,愁啊。报完仇,这烟戒不了了。”
来云他娘也裹脚了,裹出来的是大脚,也就意思意思吧。人家都是小脚女人,她这两只大脚往那儿一站,一看就像个母夜叉,说话也粗声粗气的。
她说:“二奶奶,你可不知道,给俺爹报完仇,好人家没谁敢要俺。二十二岁那年,才嫁到百时屯,当后娘,家还穷,没办法。”
嫁到百时屯以后,她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第一个儿子叫宝仓,生了宝仓,百时屯人都叫她“宝仓他娘”。二儿子叫来云,这个儿子十六岁那年,让她打出去了,十年以后回到百时屯。来云是个穷八路,来云他娘着急了,她给来云说了个媳妇是二婚头。两人结婚三年,没生孩子。一打听,在原来的婆家就不生,人家才休了她。来云想离婚,来云他娘拦着不让,说“休了前妻没饭吃”。
来云那时候已经是章缝区副区长,百时屯人不再叫她“宝仓他娘”,都叫“来云他娘”了。
有一次开会,来云正在会上讲话,来云他娘拄着拐杖进来了,举起拐杖就打来云。事后,她学给俺娘听:“俺不管开会不开会,娘个×,不听俺的俺就打!”
打也没拦住来云离婚,来云后娶的媳妇是他自己找的,新媳妇躲着婆婆不敢见,怕挨打。原来那个媳妇嫁到百时屯的西头时家,两年后生了个儿子。听说,这媳妇死的时候,棺材还是来云给买的。
俺记事的时候,来云娘快六十岁了,爱打抱不平,好骂人,不怕得罪人。土改的时候,也不知咋得罪了农民会会长,要开她的会,斗她。
几个民兵去她家,叫她去开会,她去了。她一走到,民兵就叫她站到中间。她大声说:“叫俺开会,这是要开俺的会呀!奶奶个×,开吧!”
那些人都喊口号:“打倒恶霸!”
她喊:“你屙犁子!屙大牛!”
那些人再喊:“打倒恶霸!”
她喊:“你屙耙!屙犁子!屙大牛!屙大马!”
农民会会长叫儿童团的孩子去尿她,她说:“俺看哪个王八羔子敢尿俺?俺把你的小鸡巴揪下来!”
那些孩子谁也不敢靠前。
农民会会长一看,整不服她,就散会了。
从那以后,她骂会长更起劲了。她儿子来云在章缝当官,谁能咋着她?会长干脆躲着她。
日本人在巨野的时候,爹在县里当过文书。八路军解放巨野以后,章缝区贴出布告,要枪毙他。听说了这事,很多老头老太太去了区政府,要保俺爹,那些人跪在区政府门口。来云他娘领着爱莲她娘、大黑孩他娘,进去找区长说理。
听说,来云他娘拍着桌子、瞪着眼睛跟区长说话,不叫区长走。来云知道了,过来劝他娘,衣服袖子让他娘一把扯烂了。
后来区长出来表态说,明天枪毙的没有姜清车,那些老头老太太才起来走了。
三年困难时期,百时屯家家挨饿。来云他娘七十多岁了,没挨过去,一九五九年三月死了。听说,来云他娘死的时候,大辫子还老长呢。
爱莲
爱莲比俺大一岁,姓姜,按辈分,她叫俺姑奶奶。
六岁那年,俺去找她玩,爱莲说:“俺家枣没咋丢,俺天天看着。你家枣树这么多,也没人看,都快叫人家偷完了,咱去看枣呗。”
俺说:“行。”
俺两家枣园离得近,俺俩拉着手去枣园看枣。走到枣园,爱莲说:“咱两家没有妈妈枣,坠家1有,俺去够坠家的妈妈枣。”
妈妈枣个头不小,又甜又脆,下面有个小圆头,像乳头似的。爱莲爬树快,一会儿就摘了二十多个枣回来。那时候,小孩子也穿带大襟衣裳,她用大襟兜着枣回来,说:“吃吧,姑奶奶。”
俺就是白吃。俺爬树也快,就是不敢偷。
中午回家吃完饭,俺俩又去看枣。爱莲说:“垛家的梨熟了,离老远都能闻见香味,咱俩去偷梨吧。俺上树,用脚跺梨树枝子,你在下边捡,熟的往下掉,生的不掉。”
俺说:“俺不敢去。”
爱莲生气走了,吓得俺躲在炮楼里不敢出来,比偷梨的还害怕哩。
时间不长,爱莲用大襟兜回来十多个梨,又香又面。
爱莲说:“俺在梨树枝子上跺两脚,梨掉下来不少,没捡完,俺就跑回来了。俺看见看梨的四奶奶,四奶奶没看见俺。”
梨没吃完,又不敢往家拿。俺想了个办法,用大麻子叶2包上,用土埋上,啥时候想吃,扒出来就吃。十个梨得用十个大麻子叶,俺俩从一棵麻子上往下掐叶,把一棵麻子掐得光秃秃的。包好梨刚埋上,爱莲娘来了。
她娘问:“你掐麻子叶干啥?这棵子不完了吗?”
吓得爱莲离她娘好远,怕她娘打她。
她娘打了点儿枣走了。
爱莲说:“吓死俺了,要是俺娘看见俺偷的梨,少不了一顿打。”
跟俺常在一起玩的,还有菊个,她跟俺同岁,比俺生日大。夏天,菊个天天去瓜园,不能跟俺们玩了,她让俺们去瓜地玩。中午该吃饭了,菊个爹来了,换菊个回家吃饭。路上看见一个浅水坑,爱莲说:“这天热死人,咱去水坑洗洗再走呗,走到家衣裳也干了。”
俺仨穿着衣裳下了水坑。那年爱莲七岁,俺和菊个六岁,坑里的水到膝盖上边,俺仨来回蹚水玩。坑里边有个土井子,菊个掉井里了。爱莲去救她,也掉里面了。
俺得救她俩,看了一圈没人,她俩的小头发辫在水上漂着。俺把左脚使劲往泥里扎,右腿往前,伸过去一只手,摸着爱莲的手,用力一拽,她俩都上来了。上来以后,她俩咯喽吐一口水,咯喽吐一口水,吐了很长时间,回家谁也不敢说,说了就得挨打。
冬天,俺和爱莲、菊个去找二妮儿,二妮儿十三岁。
二妮儿说:“俺从姐姐家拿来一瓶梳头油,俺给你们梳头呗。”
俺仨高兴坏了,都说:“给俺先梳,给俺先梳。”
二妮儿说:“先给小的梳。”
俺比她俩小,二妮儿先给俺梳。她把俺前边的头发剪得齐齐的,抹上梳头油,梳得一绺一绺的。给俺抹完了,俺一照镜子,感觉可美了。
俺四个长这么大,都是第一次梳油头。
第二天,俺四个头脸都肿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
娘问俺:“从哪里整的梳头油呀?”
俺说:“二妮儿家。”
俺娘到二妮儿家拿回来梳头油,叫二哥看,二哥说是巴豆油。
那时候,也没什么药,娘煮了蒜瓣水,叫俺把头洗了。过了几天,俺们脸上都褪了一层皮。
爱莲家常住地下党,她爹在单县大孟庄待着的时候,就跟地下党接上头了。后来,八路军和中央军在百时屯拉锯,她爹暗地里帮八路军从各庄敛上来吃的,再偷着送出去。那时候干这样的事,全家人的脑袋都在柳树梢上挂着呢,说不上啥时候掉下来。要是中央军知道了,一家人都得杀光。
有一回中央军撤退,用百时屯的驴驮子弹箱子。爱莲跟着她家的驴走出去老远,再走怕摸不回来,她偷着用柳枝捅驴屁股,驴一会儿就疯了,乱踢乱蹦。中央军生气了,赶紧打发她回家,驴也跟着回家了。
那时候八路军穷,百时屯人编了一套嗑:
八路军,不吃香,
破袜子破鞋破军装。
哑巴火,白打枪,
子弹辫子3装格挡。
把高粱秸掰断,一截一截的,俺那儿就叫“格挡”。八路军子弹少,有时候把格挡装进子弹辫子。要是探子过来打听情况,一看八路军的子弹辫子鼓溜溜的,就以为他们不缺子弹呢。
有个八路军连长叫李汉杰,有一阵子他们四个人藏在后小洼。后小洼离百时屯三四里地,都是爱莲送饭,一天两次。
那时候,百时屯还有海子墙和海子门,海子墙两米多高,外边是海子壕,水很深,海子门有中央军站岗。爱莲那年虚岁十一,还是小闺女,她从海子门进进出出,谁也不注意。
有一回,爱莲家实在没啥送的了。爱莲娘下地,整回来一捆高粱穗子,地上铺个床单,再用席子圈上。她左手拿个高粱穗,右手拿个二尺多长的青秫秸,使劲抽。高粱穗子还没红,咋抽也不爱下粮食粒,抽下来的粮食粒里一包水。爱莲娘用石头囤窑子4砸碎,做了七个小锅饼。
这回送吃的,爱莲没走海子门,她翻过海子墙,脱下褂子把干粮包上。她会浮水,先跳进海子壕。站岗的中央军往这边看,爱莲赶紧往身上撩水,假装洗澡。中央军回头检查别人,她抱起褂子跑进高粱地。
爱莲想:四个大男人,七个小锅饼,不够吃的。她去了自家地瓜地,地瓜还没长好,她专找大个的扒。
中央军的飞机过来了,看见庄稼地里有人,就往下打机关枪,吓得爱莲抓起地瓜秧盖到身上,躺到奶奶的坟上。
飞机飞走了,爱莲用马莲扎上袖口,装上地瓜,还捡了九个子弹壳。地瓜和锅饼给了李汉杰,子弹壳她自己留下了。
听说中央军看见大脚板女人就抓,说她们不是八路军就是洋学生。爱莲不是八路军,不是洋学生,却是大脚板,愁坏了娘。爱莲自己做了一双尖鞋,用裹脚布把脚包上,蒙混过去了。
爱莲听见娘问爹:“咱闺女大脚板,能找着婆家不?”
爹说:“别愁,有一屋就有一主。”
八路军把中央军打跑了,兴姊妹团,爱莲当上姊妹团团长。她领着姊妹团排着队唱革命歌曲,宣传毛主席的政策,叫女人放脚,吓得那些小脚女人没处躲、没处藏。
姊妹团看见小脚女人就摁倒,把裹脚布抖搂开拿走,女人都骂爱莲。
爱莲说:“现在你就骂吧,以后你的脚不疼了,你就不骂俺了。”
爱莲能干,好几年都是模范团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汉杰到菏泽工作,他特意来接爱莲,想让爱莲跟他去菏泽上技校,把她培养出来。爹身体不好,种地离不了爱莲;娘孩子多,离了爱莲也不行,两个人都不放她走。李汉杰没办法,找到百时屯的老红军姜来云,让他去讲情,讲爱莲上学的好处。说了半天,爹娘还是不放人。
据说李汉杰当过菏泽的专员,爱莲没找过他。李汉杰退休以后,爱莲看过他一回。
爱莲十八岁的时候,妇女主任姜桂荣给她介绍对象,是百时屯工作组的,叫李庆招。李庆招的爹是共产党,在金乡县当过区长。中央军打进来,他爹撤退了。家中老娘病了,他爹回家看老娘,让中央军抓住,活埋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家是光荣烈属。这门亲事,一说就成了。
爱莲和庆招要结婚,工作组找到爱莲和她爹娘,想让他们带个头,在百时屯办新式婚礼,也宣传一下《婚姻法》。说了几次,爱莲爹娘同意了。
一九五三年底,百时屯搭了一米多高的台子。结婚这天,十里八里、三里五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俺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进,那天也去了。
一上午就听那些干部讲话了,一个人手里拿几张纸,说的啥也听不懂。都讲完话,姜爱莲和李庆招才从后台出来。那时候,百时屯女人都穿大襟的家织布衣裳。那天,爱莲穿的是天蓝色对襟洋布衣裳,庆招穿深蓝色中山装。他俩胸前戴着绿叶大红花,是用红绿纸做的。
一对新人站在台上,台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那个主事的人喊:“一对新人向后转,给毛主席三鞠躬!”
他后来又喊:“给介绍人三鞠躬!给在座领导三鞠躬!给台下群众三鞠躬!”
鞠完躬就完了,人就散了。
结婚以后,爱莲住在工作组的院里。那儿原来是姓时的地主家大院,药房东屋有个小套间,他们住一间,里边就一张床、两套被。
过了一段时间,爱莲到俺屋里,说要给俺介绍对象,也是工作组的。俺那时候傻,啥都不知道,这还是第一次提亲,脸发烧,害臊得不行。
爱莲说:“那个男人有文化,工作干得好。”
俺说:“那个男人好,你就要了吧。”说完就跑了。
这事就俺俩知道,爱莲没跟俺娘提,就过去了。
当时,工作组有个组长姓郭,入党的事他说了算。有一天,没有外人,郭组长往爱莲的脸上摸了一把,爱莲回手使劲打了他一耳刮子。这一耳刮子,耽误了爱莲。
百时屯管烧香信佛的人叫“会道门”,爱莲爹信佛,经常烧香。开会的时候,郭组长说:“姜爱莲历史问题不清,没资格入党。”
爱莲急了,说:“新中国成立前,俺家私藏过四个地下党。俺一天两顿给他们送饭,都是从海子壕浮水过去,一天穿两次湿衣裳,这是小事。要是中央军知道俺家窝藏地下党,一家人都活不了。一家人的命,还换不来俺的入党资格吗?”
村干部说:“你爹是会道门头子。”
爱莲问:“他是谁的头子?你倒给俺说说!”
他们说不出来啥,可爱莲到了没入上党。二〇一三年秋天,俺回巨野看爱莲,提起入党的事,她还生气呢。
郭组长有媳妇,他看上百时屯小学老师云英,整天追云英,吓得云英看见他就跑。云英没娘,住在百时屯姥娘家,经常下了课跟俺学织布。她有文化,长得俊,说话也好听。
郭组长胡整,上面不光撤了他的组长,还把他开除了。
后来,李庆招到章缝工作,爱莲搬到章缝。李庆招到巨野工作,爱莲跟到城里。国家号召支援农业,她又回到百时屯当农民。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李庆招是巨野县工商局长,成了当权派,经常挨斗,吓疯了,回家住着。
有一回,城里造反派要斗庆招,爱莲抱着三儿子跟来了。夜里,她把三儿子哄睡,就出门了。
找到开会的地方,她看见庆招在前面撅着,听见里边人批斗他,说他“耳根子软”“驴耳朵”“听人家话”。她一脚踹开门,拾起砖头就砸过去,那个人躲闪一下,没砸着。
爱莲直接问那个人:“你们这是革命还是整人?你走的是谁的路线?俺家门上有牌子,俺是革命家庭。你们把他整成这样不算完,还想咋整?国民党没把他整死,你们想把他整死吗?你们要是把李庆招整死,俺也不活了。”
她拉起丈夫,说:“走,咱回百时屯。谁要是敢再找你,俺用抓钩5刨死他!刨死一个够本,刨死两个挣一个!”
全场的人都傻了,没谁敢拦着。
第二天早晨,他们回到百时屯。县城这边都知道,庆招家的是半吊子,没人再招惹。
庆招回到百时屯,百时屯也搭台子,要斗老红军姜来云,把李庆招、姜来运、李素英也整上台,一起斗。
批斗大会刚开始,爱莲几下翻上台,问大队干部:“‘文化大革命’,你革的是谁的命?俺看你革的是共产党的命!没开除李庆招党籍,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姜来云、姜来运、李素英谁不是?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的时候,你们都干啥去了?他们打下江山,天下太平了,你们收拾他们,你们到底想干啥?”
大队干部没一个搭话的,待了一会儿,有人喊:“散会,散会。”
准备好几天、费了不少劲的批斗会就散了。
说起过去的事,她跟俺说:“姑奶奶,人家屙到头上,咱扒拉扒拉。实在不中了,就得拼它一家伙。”
这几年,有人问爱莲:“你现在还有那劲不?”
爱莲说:“蹦不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李庆招的病也没治好,七十四岁那年死了。爱莲的六个孩子都有本事,大孙子李锐是书法家,在巨野很有名。
爱莲的三儿子在上海做生意,他给爱莲在巨野县城买了高层。房子装修好了,三儿媳妇找好保姆,让她搬去住。
爱莲问:“是人家伺候俺,还是俺伺候人家?”
儿媳妇说:“人家伺候你呗。”
爱莲说:“那不中,俺就干活儿的命,待着难受。”
爱莲的地还在百时屯,种庄稼、收庄稼她都回去。她住在县城的老房子里,院里有棵柿子树,笼子里养着鸡和兔子。她经常骑着三轮车给兔子割草,弄吃的。鸡和兔子养到过年,杀了,分给儿女。
爱莲衣裳多,孩子们给买的,貂皮都有。她问:“穿上这衣服,俺咋走路?”
孩子说:“用脚走呗,不能用头走。”
爱莲的好衣裳都在包袱里,平常穿的,总是那几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