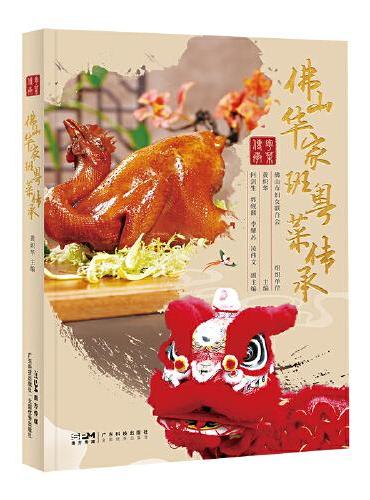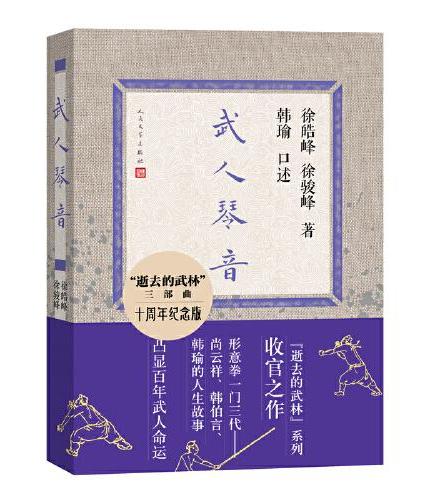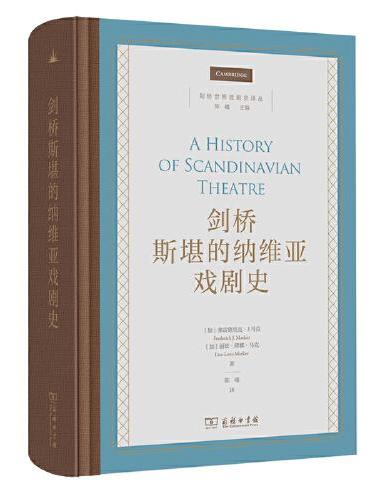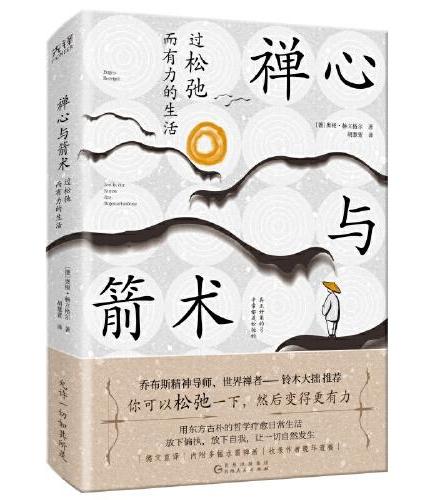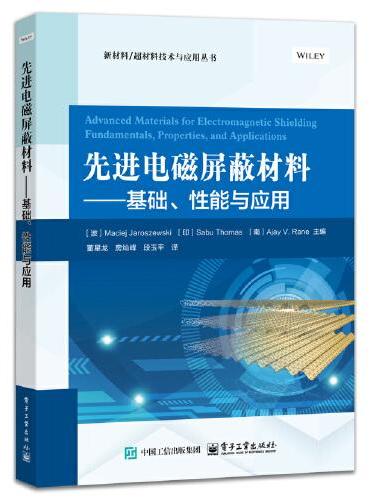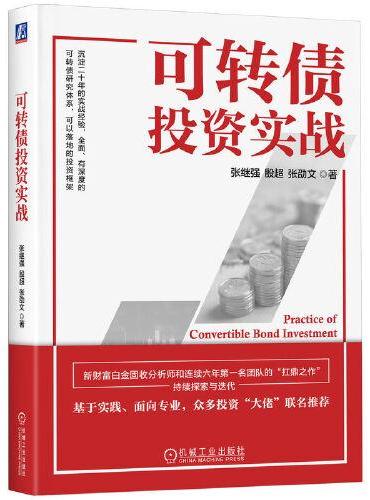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NT$
806.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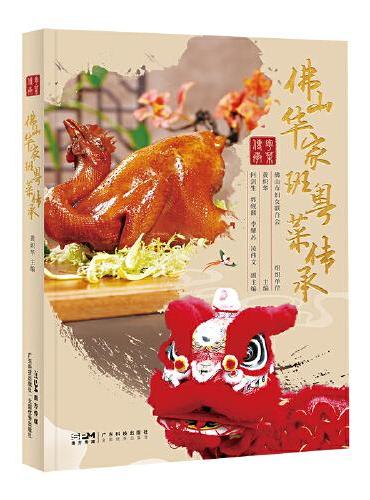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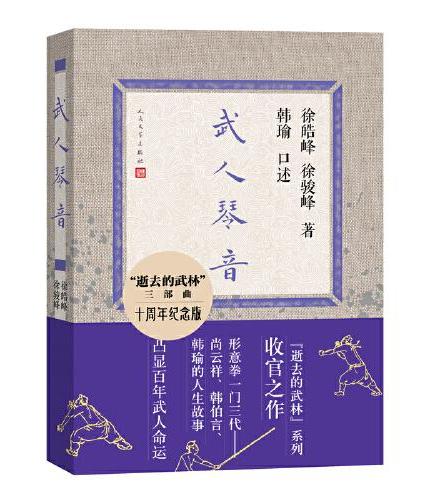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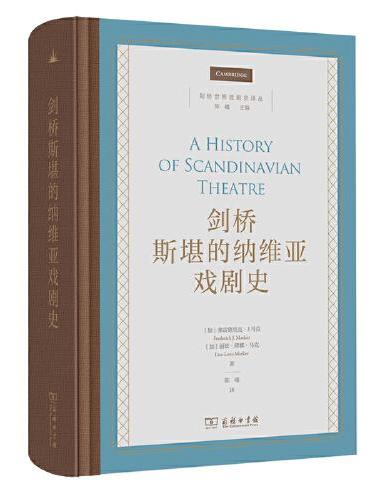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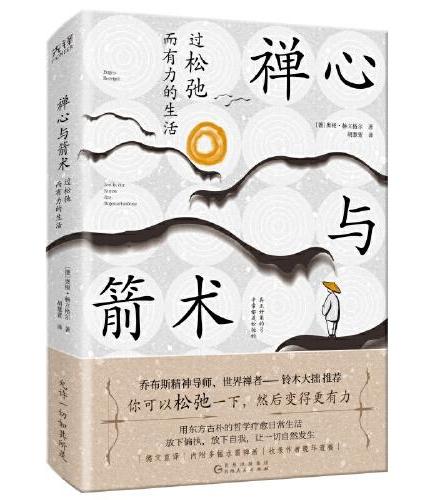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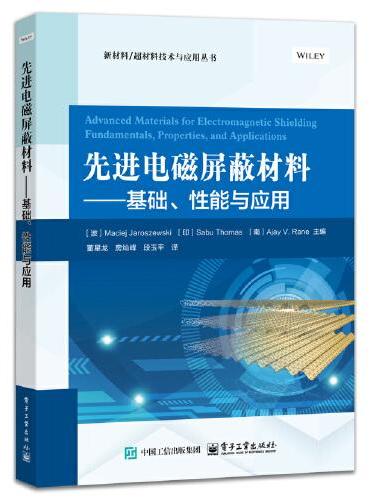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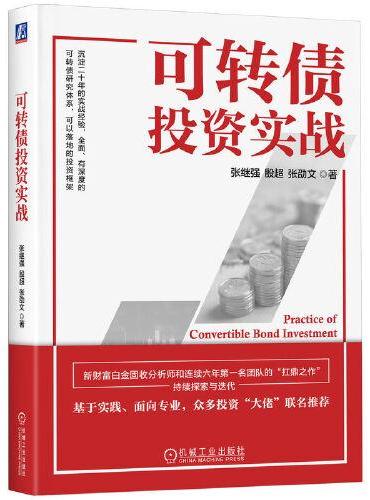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NT$
454.0
|
| 內容簡介: |
|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
| 關於作者: |
|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患尿毒症至今。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命若琴
|
| 內容試閱:
|
一
去年我竟作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象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茆、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呆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茬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唧唧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嘛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过了一会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定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迫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二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作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象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象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哭了一个,一会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像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道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这)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像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干)嘛它(插)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象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像。”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划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三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象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象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不怕呀?干嘛?”
“不干嘛。问问。”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
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
“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费话,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
“废话。”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磨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象,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象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臂在站台上瞎蹓跶,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再邪乎点。所谓惟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捡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揣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楞,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