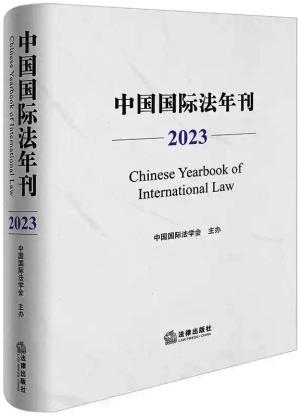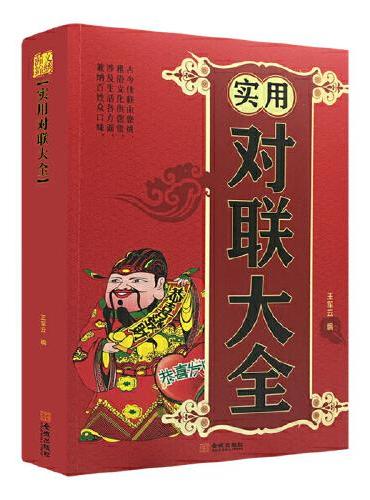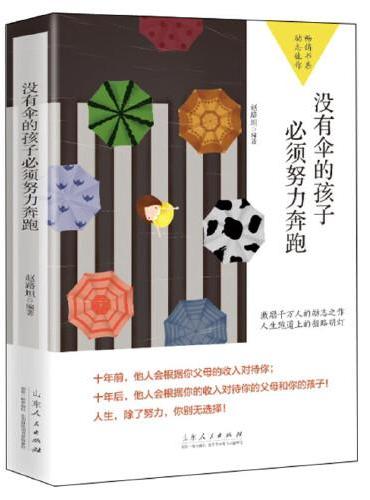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法国汉学经典译丛)
》
售價:NT$
380.0

《
花外集斠箋
》
售價:NT$
704.0

《
有兽焉.8
》
售價:NT$
305.0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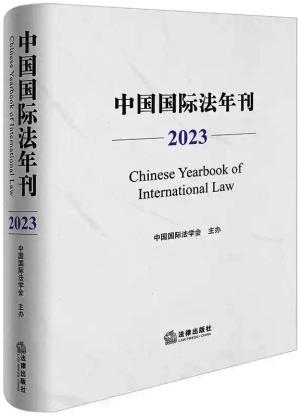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NT$
5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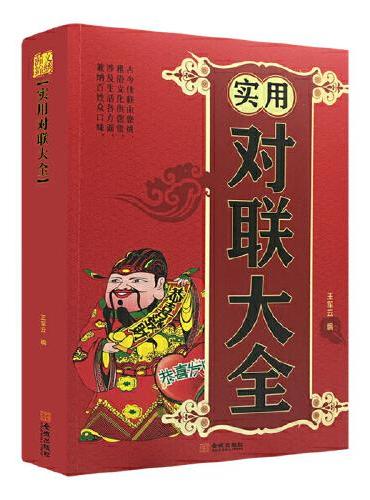
《
实用对联大全
》
售價:NT$
225.0

《
想象欧洲丛书(7册)欧洲史
》
售價:NT$
18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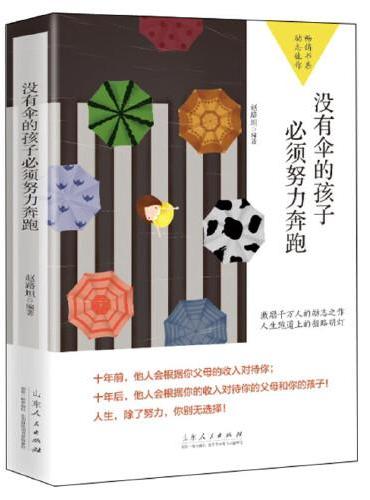
《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
售價:NT$
149.0
|
| 內容簡介: |
|
《纳博科夫文集:黑暗中的笑声》仿效二三十年代电影中盛行的那种廉价三角恋爱故事,一开始就以电影为题,引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男主角欧比纳斯对影院引座员玛戈一见钟情,“着了魔似的爱看电影”的玛戈一心梦想当影星,当她确信他属于能为她“登上舞台和银幕提供条件”的阶层时,便决定与他来往。欧比纳斯为招待明星而举办的宴会,则为玛戈与昔日情人雷克斯重逢创造了机会,由此构成三角关系,直到小说以悲剧结束。
|
| 關於作者: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1899年4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1919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
| 內容試閱:
|
她叫玛戈·彼德斯。她父亲是个看门人,在战争中被炮弹震坏了脑子,长着满头银发的脑袋不停地颤动,似乎总在以此证明他的怨愤与忧愁。谁若说了一句稍微不中听的话,他就会怒气冲天地发作一通。她母亲还很年轻,但已被生活磨蚀成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她的手掌通红,是经常揍人的见证;头发总用一块帕子扎住,以防干活时落上尘土。但是,在每星期六大清扫之后一这活计主要依靠巧妙地连结在电梯上的一架真空吸尘器来完成一她便穿戴起来,出门会亲访友。房客们都不喜欢她,因为她态度蛮横,总是粗鲁地命令他们在门口的垫子上把鞋底蹭干净。她一生最崇拜的偶像就是楼梯,并不是她把楼梯看成是上升天国的象征,而是把它看成必须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物件。所以,她做的最可怕的噩梦(在吃了太多土豆和泡菜之后),就是一段洁白的楼梯被人从头到尾左一脚右一脚地踩出一长串黑色脚印。她是个贫苦妇人,这没什么可以取笑的。
玛戈的哥哥叫奥托,比她大三岁,在一家自行车厂工作。他看不起父亲不死不活的共和派观点,常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唾沫横飞地大谈政治。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人生头等大事就是填饱肚子。”这是他的基本准则——也的确是一条明智的原则。
玛戈小时候上过学,在学校挨耳光的次数比家里少得多。小猫最常见的动作是突然而连续的轻跳,她的习惯动作则是猛地抬起左手护住脸颊。尽管如此,她还是长成了一个伶俐活泼的姑娘。
刚到八岁的时候她就兴奋地和男孩们一道又嚷又闹地在街上踢柑橘般大小的橡皮球。十岁时她学会了骑她哥哥的自行车。她光着胳膊,骑着车飞快地在马路上兜来兜去,一双黑辫子飞在身后;她会突然刹车,伸出一只脚踏在人行道上,沉思起来。十二岁时她变得文静了一些。
她最大的爱好是站在大门口和运煤工的女儿絮絮叨叨议论前来拜访某位住户的那些女客,或是评论过往行人戴的帽子。有一次她在楼梯上拾到一个破旧的手提包,里边装着一小块杏仁香皂,上面粘着一根卷曲的细毛,提包里还有六七张古怪的照片。又有一次,做游戏时老爱捉弄她的一个红发男孩亲吻了她的颈背。后来,有天晚上,她发了一阵歇斯底里。他们朝她身上浇了一盆冷水,又把她痛打了一顿。
一年后她已经出落得相当俏丽,常穿一件红色短袖紧身衫,着了魔似的爱看电影。每当回想起这段时期,她总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那明亮、温暖、宁静的黄昏;入夜前商店的插门声;父亲叉开腿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母亲双手叉着腰;丁香树藤悬垂在栅栏上方,冯·布洛克夫人上街回来,用一只网兜提着买来的东西;女仆玛莎带着一头灵提狗和两头硬毛狗正要过马路……天渐渐暗了下来。她哥哥会带来两个壮实的伙伴,他们会跑过来推挤着逗她,拽她的一双光胳膊。哥哥的两个伙伴中有一个长着影星维德那样的眼睛。楼房的上部仍然沐浴着金色的夕阳,街道却已经寂静下来,只是在街对面的阳台上有两个秃顶的男子在玩牌。他们敲打桌子和说笑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刚满十六岁时,她结识了附近一家文具店里一个站柜台的姑娘。那姑娘的妹妹已经开始挣钱养活自己,她在给画家当模特儿。于是玛戈也梦想当模特儿,然后再当电影明星。她把从模特儿到影星的过渡看得相当简单——一旦上了天空,她这颗星星就会发亮。
就在那时她学会了跳舞,常和那女售货员一道去“天堂”舞厅,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男子毫不客气地过来邀她随着忽而轰响、忽而呜咽的爵士乐跳舞。
一天,她正站在街道拐角处,一个骑一辆红摩托车的人忽然停下车来邀她一道去兜风。这人她以前曾见过一两次。他的亚麻色头发朝后梳着,衬衫的后背在飘舞,停车之后仍被风兜起胀得鼓了起来。她笑一笑,上车坐在他背后,整理了一下裙子。摩托车飞快地开动了,他的领带飘起来碰着她的脸。他把她带到城外,停了车。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蚊虫成群飞舞,织补着一小块天空。到处一片寂静一四周是静悄悄的松树和石楠。他下了车,挨着她坐在一条小沟旁。
他告诉她,去年他就这样把车一直开到了西班牙。他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开始放肆地狂吻乱摸。她感到很不舒服,难受得直犯恶心。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哭了。
“可以让你亲吻,”她抽泣着说,“可请你不要乱来。”
小伙子耸耸肩,发动了引擎。车子开动,跳了一跳,忽地急转弯,一溜烟开走了,留下她独自一人坐在一块路碑上。她步行回了家。奥托曾看见她离家。
他朝她脖颈上打了一拳,又熟练地踢了她一脚。她摔到缝纫机上,撞伤了。
第二年冬天,那女售货员的妹妹引她去见了列万多夫斯基太太。那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生得挺匀称,举止也挺斯文,美中不足的是嗓门粗了点,脸上还有巴掌大的一块紫斑。她常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她母亲怀她时叫一场火灾吓着了。玛戈搬进太太公寓里一间仆人住的小房。她父母巴不得她早点搬出去,自然感到庆幸。他们认为,任何邪恶的职业都会因为赚来金钱而变得圣洁起来。这样一想他们就更心安理得了。她哥哥喜欢用威吓的口吻谈论资本家如何收买穷人家的闺女,幸运的是他出门到布雷斯劳做工去了。
玛戈起初在一家女子学校的教室里当模特儿,后来她到了一个真正的画室。画她的既有女人,也有男人——多数都相当年轻。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一小块地毯上,柔润的黑发修剪得很美,双腿蜷曲着,头倚在白得显出青筋的胳膊上,苗条的脊背微朝前倾(秀美的双肩当中有一层细细的汗毛,一个肩膀抬起来托着红润的腮),正作出一副忧愁、倦怠的姿态。她斜睨着一会儿抬眼一会儿低头的学生们,听着炭笔勾勒线条的沙沙声。
为了解闷她常会挑选一个最好看的男子,等他张着嘴、皱着眉抬起头来,她就含情脉脉地送去一个秋波。她丝毫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为此她大为恼火。先前她满以为像这样独自坐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供人欣赏一定非常有趣,结果坐在这儿只能累得她浑身发僵,毫无半点趣味。为了找点乐趣,她在去画室前搽上脂粉,在燥热的唇上涂唇膏,把本已很黑的睫毛描得更黑。有一次她居然把乳头也抹上了口红,结果招来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一顿臭骂。
于是,时光一天天流逝,玛戈自己也说不清她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尽管她总在梦想有一天成为影星,穿着体面的皮衣,一位体面的旅馆侍者撑着一把大伞把她扶出一辆体面的轿车。她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铺着陈旧地毯的画室一步跨入那富丽堂皇的世界。就在此时,列万多夫斯基太太第一次向她提起外省来的那个害单相思病的年轻人。
“你得交一个男朋友,”那位太太一边喝咖啡,一边不经意地说。“像你这样精力充沛的姑娘哪能没个伴儿?这小伙子挺老实,咱们城里的风气太坏,他想找一个纯洁的好姑娘。”
玛戈正把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肥胖的黄猎狗抱在膝上,捏起它丝绸般柔滑的两只耳朵,让两个耳尖在它小巧的头顶碰在一起(耳朵孔里面像是用旧了的深粉红色吸墨纸)。她头也不抬地说:
“呃,现在还用不着。我不是才十六岁吗?找朋友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吗?我可见识过那些家伙。”
“傻姑娘,”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不紧不慢地说。
“我说的不是那种二流子。这是个大方的少爷,他在街上看见你,就做起相思梦来了。”
“一定是个老病鬼吧?”玛戈吻着猎狗脸上的肉疙瘩。
“傻丫头,”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又说。“他才三十岁,脸刮得光光的,很有身份,打着丝领带,叼着金烟嘴。”P15-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