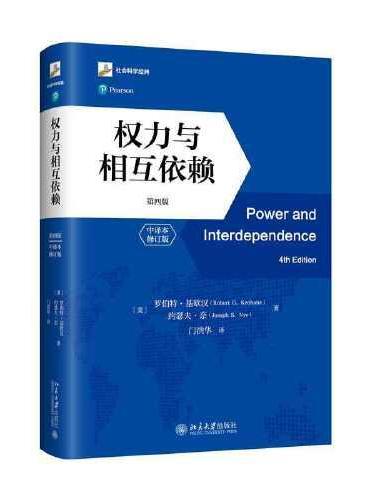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
》
售價:NT$
704.0

《
民法典1000问
》
售價:NT$
454.0

《
国术健身 易筋经
》
售價:NT$
152.0

《
古罗马800年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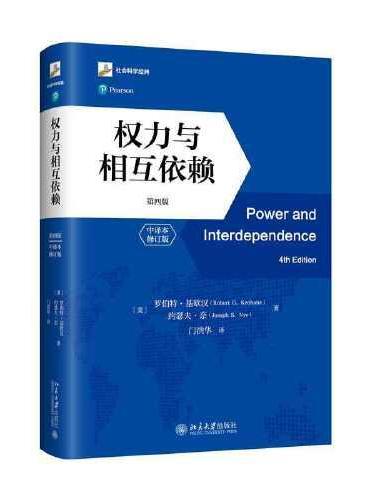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控制权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管理与传承
》
售價:NT$
398.0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
》
售價:NT$
762.0
|
| 內容簡介: |
|
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河北赞皇跳扇鼓的池素英,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浙江衢州打纸簾的程宵春,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本书以他们四个人的日常生活来呈现本真质朴的“中国人”。
|
| 關於作者: |
雷建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纪录片研究、电视节目策划与制作、电视新闻。2006年创建清影工作室,2009年创建清影放映,主编了《清影纪录中国》系列丛书,2009年拍摄纪录片《2008纪》入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竞赛单元。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焦瑞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
| 目錄:
|
吕崇德
001
程宵春
053
高喜业
119
池素英
181
后 记
244
|
| 內容試閱:
|
前
言
今天,“中国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名字。
网络上的中国人光怪陆离。
电视上的中国人不食人间烟火。
生活中的中国人,要么经常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管你是否怀孕,是否有心脏病;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是否还流着唐诗宋词中那些有情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们是否还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的后裔?我们是否还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抑或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想象,中国只是一个地名而非文化名称,因为自从孔子痛心疾首地说礼崩乐坏之后,礼乐再也没能恢复,如同秦晖教授用尽半辈子实证研究而无奈地笑着说,那种士绅与农民温情脉脉的乡土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
2007年开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这期间我们在陕西华县遇见了演皮影的吕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见了打纸簾的程宵春,在陕西榆林遇见了唱红白的高喜业,在河北赞皇遇见了跳扇鼓的池素英。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
演皮影的吕师,从地主娃到皮影艺人,一生命运多舛,但弹起月琴,就如泣如诉地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拿起锄头就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城里塬上两头跑,日子紧紧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
打纸簾的宵春,上班在化肥厂装尿素,下班回自己家织簾子,传承千年的宣纸仿佛只在他一个人心中,对工业化的鄙视与屈服都在他的声声叹息与滴滴眼泪之中。手闲了练字,心闲了吹箫,身闲了捉鱼,琴棋书画只是生活中的玩意儿。
唱酸曲的喜业,一生走南闯北,落叶归根,做起了“下贱人”,在大俗的红白喜事上靠作践自己搏名搏利,但在夕阳下放羊时一首首酸曲从心底涌出,那是一个拥有无限温暖的精神世界,单纯而悠远。
跳扇鼓的素英,在穷山沟里乐活着,一闲下来就打扇鼓。农村人有说不出的美感,吴冠中说,他在乡间作画,画得好的农民便说,这张画美;画得不好了,农民们说,这画很漂亮。农民在心里知道“漂亮”和“美”的区别,素英也是如此。
是什么赋予了这四个人,四个普通中国人,当代社会梦寐以求的自律与快乐,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相对的单纯与宁静?我们试着用镜头、用特写来关注他们,用参与式的观察来审视他们,用长时段的沉淀来思考他们。
我们发现,传承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机制。皮影戏的师徒传承、打纸簾的父子传承、二人台的江湖传承、扇鼓乐的同伴传承,总之在一点一滴中,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有传承的目标,戒律被无形中树立,文化被无形中继承,人被无形中塑造。这种机制与现行的社会教育体系不同,它没有批量生产,它没有急功近利,它没有锦标竞赛,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这些是以前在社会教育不发达的状况下,每个中国家庭都有的。
我们发现,“有闲”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条件。传统农村生活中,忙闲有时,忙闲有度,春忙夏种秋收冬闲,大可以玩个尽兴。工业生产、商业活动透支了人们的闲暇时间,人们更习惯将碎片化的时间花在媒介上,人们更习惯媒介化的交流而不是真实的生活,殊不知媒介使人焦躁。闲是和欲望成反比的,这四个人都不算富裕,但欲望有限,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闲和闲出来的情趣,有情趣则不焦虑。
我们发现,市场化可能是泯灭他们的催化剂。市场对规模的追求,对速度的追求,对成本的追求,归结成一句话对利润的追求,可以彻底颠覆一对一的传承模式,同时也可以用便捷低廉的方式俘获卷入市场的民众,所以传统文化生活先从城市淡去,然后再从农村淡去。这不仅关乎文化,也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的心性,老一代有文化没知识,而新一代有知识没文化。这种趋势也许无法阻挡,也许没必要阻挡,但我们可以在市场的洪流中,看到多元的存在,向历史习得更好的精神生活。
四个中国人,简单而有趣的微观生活,可以有宏观的升华,但还要回到微观,从四个回到更多人的微观世界,让更好的精神生活在微观、在日常生根发芽。
吕崇德
1949年的清明节,吕塬村村外不远处的吕氏宗族墓地上正在举行每年一次的祭祖活动。这一年吕崇德6岁,祭祀完毕后,他抱了他这房分得的10个烧饼馍一路小跑,回到家中。他的家庭本是殷实的地主之家,不过民国十七年关中地区的匪患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吕崇德的正值壮年的爷爷被土匪打死在家中,家中正房也被烧毁,只有一间门房和门楼、砖墙幸免于难,那年吕崇德的父亲才十几岁。随着爷爷的死去,家道直线没落,解放前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男丁。然而,解放后土改的时候,虽然家中有50多亩地,但因为只有三口人,按照人均占有土地的规模,被划为地主。除了吕崇德家,吕塬村还有其他两个刘姓的地主。这次意外的身份划分,让吕崇德从少年时代起就与皮影戏结缘,并把这种缘分延续了一辈子。
1949年清明节之后一个月,华县和渭南得到解放。解放军进城后在渭南创建了军政大学,为新的国家培养基层干部。
开学的那天,21岁的郭树俊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了这里。郭树俊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给商铺当伙计,常常往来于山陕之间,贩卖大宗货物。后来解放战争打响,战火烧到山陕地区,郭树俊才停止生意回到家中。1949年夏末,郭树俊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从军政大学毕业。当他穿着军装参加毕业活动的时候,郭树俊以为是要送他去当兵打仗,于是悄悄逃回华县。60年后的今天,郭树俊回忆起这件事情依然后悔不已:“当年我要是留下了,肯定也是个不小的干部。”
在华县县城里,郭树俊的整洁军装和精干外表引起了当地工商业者刘云峰的注意,他拉着郭树俊的手说:“我有个戏箱,你愿不愿意给我跑外交?”郭树俊答应下来,这一跑就是40年;不但给刘云峰跑过,还给其他人跑,其中时间最长的是潘京乐和吕崇德师徒。潘京乐在关中地区驰名几十年,与郭树俊的干练是分不开的。生产队时期,经常能在乡间小路上看见郭树俊的身影,他骑着二八大号自行车,前面车把上插着一面红旗,迎风飘展,后座捆着一个大喇叭,威风凛凛,被人称为“华县红”。当时所有的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他都认识,他能拉来最多的演戏营生,他的戏班生意总是最好的。
可以说,1949年的“解放”,在关中地区的皮影戏艺人眼中不过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戏里戏外见惯了兴亡成败、世道变迁,他们知道如何趋利避害地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他们也确信,无论哪个时代,都少不了看戏听曲找乐的,天底下唱戏卖艺的仍然是凭本事吃饭。艺人雷全印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江湖人就是个混嘴,我给你唱戏,你给我饭吃。”不过,他们眼中的“江湖”在解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吕崇德在他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适应着这变化的江湖。
吕塬自然村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的华县境内,隶属于大明镇刘塬行政村。当地人称刘塬村周围一直延伸到南山的这片塬区为“影戏的老窝子”,华县影戏艺人以此地为多,水平也较高。这片台塬名叫太平塬,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条塬区,平均比川道高出60~80米。太平塬南侧坡底是大明镇政府所在地,北侧坡底是国道和陇海线铁路,东西两侧坡底川道各有一条公路。太平塬区分布着九个自然村,刘塬行政村下辖九个自然村中的四个,从北到南分别是刘塬村、吕塬村、苏塬村和颜塬村,其中吕塬村分为吕东和吕西两个村民小组,其他各自然村自为一个村民小组。关中台塬地区的传统作物是小米和小麦,一年两种;解放后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小米改为玉米。
根据吕塬行政村会计的统计数据,1994年最后一次分地时,自然村分地人口为457人,土地总面积近900亩。
根据访谈和家谱等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吕塬自然村的简史。太平塬地区最早的村落位于交通和水源较为便利的川道底下,随着人口的增长带来对粮食生产的压力,土地开垦情况逐渐由川道向塬区上扩展,村民居住于川道的村落,在塬上进行耕作。清朝初年,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耕作的便利,位于太平塬东侧川道的吕楼村的一户吕姓人家在塬上定居,是为吕塬自然村最早的居民。康熙年间,十公里外圣山行政村刘家堡自然村的刘汉义与吕塬村吕姓女子结婚,并定居在吕塬村,是为吕塬自然村刘姓村民的祖先。最迟清代末年开始,吕塬自然村的宗族构成是吕、刘、颜三家,由于没有确切的田野证据,无法考证颜家进入吕塬村的历史。目前,三个宗族的人口大致相当。
如同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文化一样,皮影戏的起源也被追溯到很早的年代。姓名可考的第一位皮影戏的观众和资助人据说是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刘彻,这场皮影戏演出的主角是他死去的爱妃李夫人,从《史记》开始的一系列古籍中都记述了这个故事。根据史料推断,当时的皮影戏表演是一种利用光学物理原理的“弄影术”,与现代意义上的皮影戏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成熟的皮影戏表演见诸史籍于宋代,当时商品经济发达,都市文化生活丰富,不但有专门的影戏表演艺人和戏班,甚至还有雕刻皮影的作坊。
宋代之后,由于北剧南曲的发展和成熟,相对于优伶表演的大戏,皮影戏作为小戏,因其表演时间(一般必须晚间借助油灯表演)和表演规模(皮影尺寸较小,观看距离较远后无法欣赏)的有限性,逐渐在都市文化生活中落到了边缘的位置。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观众规模不大,支付能力不高,交通运输不便,皮影戏反而能够借助自身轻便易行、花费较小的特点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皮影戏逐渐融入到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中,显示了作为文化和媒介形态的重要价值。
20世纪上半叶的关中农村被认为是解放前皮影戏演出最为兴盛的年代,根据县志记载,全县共有戏班三四十家,不但在华县的大小农村中不断演出,有些班社的演出范围还包括了整个关中平原东部地区,北至铜川,南至秦岭。不过,现在仍然在世的经历过这段辉煌的艺人已经屈指可数。1928年,吕崇德的师父潘京乐出生在华县大明乡潘家塬村,这个村落位于太平塬的边缘,离吕塬村步行大概半个小时的样子。潘京乐的舅舅也是一名皮影前声,但技术一般,于是在他的推荐下,14岁的潘京乐来到三十多里外的下庙镇,和著名影戏艺人刘德娃学习前声,半年之后出师。赵家村位于太平塬北面川道,从吕塬村北面下塬,穿过一片平整的农田,绿树环绕的村落就是。此地的影戏艺人赵振才比潘京乐大一岁,但学戏反倒晚了一年。魏振业生于1931年,他的二哥魏振杰是给赵振才拉板胡的,因为这个关系,魏振业在13岁的时候开始和赵振才学艺,14岁学成,开始自己搭班子演戏。潘京乐、赵振才和魏振业,是目前华县仅存的三位从解放前就开始演戏的关中东路皮影戏的前声。
华县地区的碗碗腔皮影戏属于陕西东路皮影的一支,故老相传。其得名原因有二:一种说法是来自于节奏乐器铜碗,敲击时声音悦耳;另一种说法来自于主要的拨弦乐器阮咸,原本称为“阮儿腔”,后来由于发音相近,流传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碗碗腔”。晚清民国时期,碗碗腔在关中东府地区得到广泛流传,被称为“时腔”。吕崇德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沉浸在这细腻的碗碗腔中。夜幕降临之后,黢黑的关中平原上,昏暗的油灯照亮了一面白布,随着月琴、板胡咿咿呀呀的音乐,前声亮起了嗓门,签手舞动着皮影。吕崇德和他的乡党们不仅观看在自己村庄表演的皮影戏,只要步行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们都会结伴而去,午夜结束了再结伴而归。
吕崇德尤其喜欢一村之隔的潘京乐的唱腔,吕崇德童年听戏的时候潘京乐已经唱出了名头,尤其是哭腔,堪称华县一绝。因为头顶的头发因病脱落,观众就以“秃子娃”这样一个略显滑稽的绰号称呼潘京乐。现在,八十多岁的潘京乐只要外出,必定戴着藏蓝色的旧帽子来遮掩一下头顶的不雅观,只有在夏天极热的时候到家中拜访,才有可能亲眼见到他唱红之后绰号的来历。
解放后最开始的几年,潘京乐们的演出并没有受太大政策影响,但由于当时的经济困难,演戏的机会逐渐减少,落到了仅仅能维持生活的境地。无奈之下不少班社从之前的包戏转而卖戏,到集镇人多的地方打上广告,入夜之后支起戏台进行表演,按人头收费。不过,这种从城市里学来的方式仍然不太管用,在华县的赤水镇,潘京乐的戏班卖了十来天就做不下去了。
就在潘京乐们正经历短暂困难的时候,新的国家政权通过大城市积累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戏曲改革的工作。在诸如“爱护和尊重”、“团结和教育”、“争取和改造”等宣传口号的指引下,政府机关、戏改工作者和戏曲艺人之间在不断的冲突与磨合中开始了真正“史无前例”的协作与互动。
华县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并进行了艺人座谈会和短期的培训;同时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新剧本进行了一次选择性收集,并择优报送省文教厅。1955-1958年,陕西省陆续开展了各个戏种的登记工作,唱戏人由“戏子”变成了“文艺工作者”,并且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1956年秋,为了选拔年底参加省会演的剧团,华县举行了头一次皮影戏会演,时间从当年的10月17日持续到21日,共有3个皮影班社22人参加,另外还有民间艺人9人和剧作者2人。此时,潘京乐的戏班子已经登记为华县光艺皮影社,与另外三个较为有名的前声艺人的戏班子一同,被人称为华县皮影的“四大班社”。华县的汇演结束后一个月,也就是1956年11月25日,历时17天的陕西省第一届皮影木偶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全省参加演出的有21个皮影社,7个木偶社,演出代表291人,观摩代表26人,共演出56个剧目,总计大会演出89场,观众达39850人次。罗马尼亚木偶剧院院长、中国木偶艺术剧团、上海电影制片厂、山西省文化局等都来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闭幕式上,潘京乐获个人表演二等奖,皮影艺人“秃子娃”的名头更加响亮了。
正宗的华县碗碗腔皮影表演由五人组成。潘京乐的角色前声是最重要的,要用自己一个人不同的嗓音负责所有角色的唱腔,主要乐器是月琴,古称阮咸,另外还操作手鼓和手锣,通过不同的起乐方式来指挥整个团队的伴奏和表演。一般的皮影戏剧本并不表明唱段的音乐,前声在给剧本配乐的方式上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不同前声因此往往有不同的风格。因为前声在表演中担任指挥和首脑的角色,前声又被称为前首。
剧团中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角色是签手,也叫“挑线的”,负责所有的皮影操作工作。在大场面中,往往每只手都要操作两个甚至更多的皮影角色,当然表演较为粗糙,以形式取胜,在一般的场面中,往往两只手共同操作一个皮影角色,表演细腻,举手投足无不惟妙惟肖。
1956年之后,受省皮影戏会演的鼓舞,以及农村集体化带来的演出市场的稳定,以四大班社为首的华县皮影戏班子在经历了解放后的短暂低谷之后,重新走向繁荣。春种秋收之外的农闲时间里,就由生产队出面,用公共费用邀请戏班,给农忙之后的社员们唱上两夜的皮影戏,既是调剂,也算农村文化活动。正是在50年代后半段的这些个年头里,正在接受初小和高小教育的吕崇德,在农闲的夜晚常常沉浸在碗碗腔柔软细腻的音乐和纵横古今的故事中。他真正开始感受到生活带来的压力,要等到1961年高小毕业之后。作为地主家的孩子,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毕业后不得不回乡务农。不仅如此,农业社不时提供给年轻村民的招工和升学的机会,对他也一概不予考虑。受到同等待遇的还有刘姓地主家的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刘正宏和刘正娃。他们的家人不得不为年轻后辈寻找一条能够糊口的出路。吕崇德和刘家的两个兄弟都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碗碗腔皮影戏。华县四大班社的红火让他们生出了学戏、演戏的念头。
对关中农村的孩子们来说,学习皮影戏表演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由于影戏演出的普及,大多数的关中农民对皮影戏的基本原理和演出方式已经比较了解。在皮影演出的过程中,常常能看到十来个孩子们挤在戏台的下方,猫着腰,把头伸到戏台里,看里头的五个人是如何操作和配合的。这些调皮的男孩有的时候甚至爬进去坐在艺人身边的条凳上,只要他们不进行破坏演出的活动,艺人们也懒得理。而且,这些孩子们不仅在本村看戏,还经常呼朋引伴,步行十多里地,到较远的地方看戏。以每个村庄最少每年两次的演出频率计算,乘以半径七公里内的村庄个数(这个距离意味着步行一个半小时内可以到达,对传统关中农民来说是休闲性步行距离的上限),每个喜爱影戏的关中孩子每年至少可以有二三十次的观看机会。这样的频率使得一个喜爱影戏的少年在正式拜师之前基本上对影戏的故事、音乐、操作都能够具有相当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