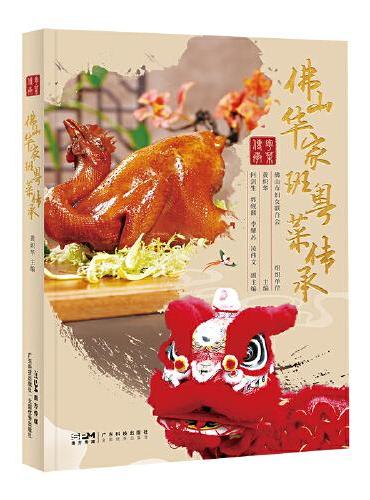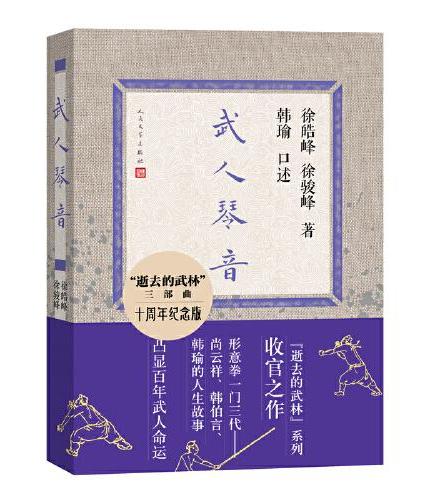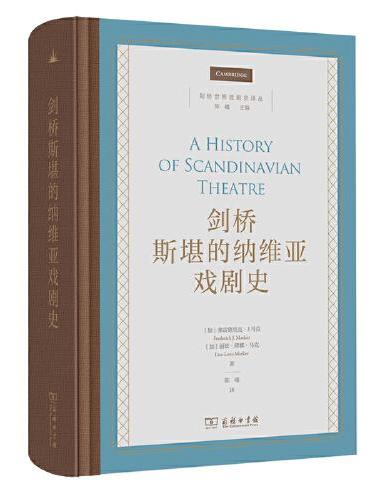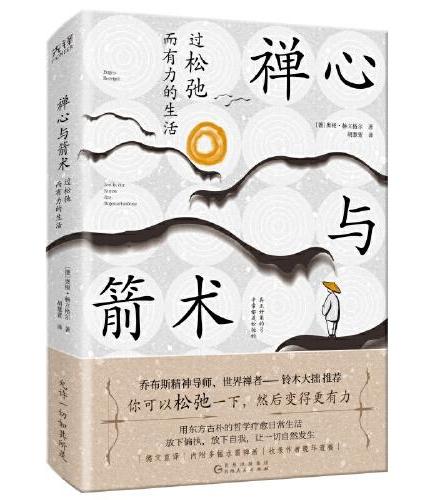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甲骨文丛书·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
售價:NT$
454.0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套装全4册):从未见过的王朝内争编著史
》
售價:NT$
1112.0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NT$
806.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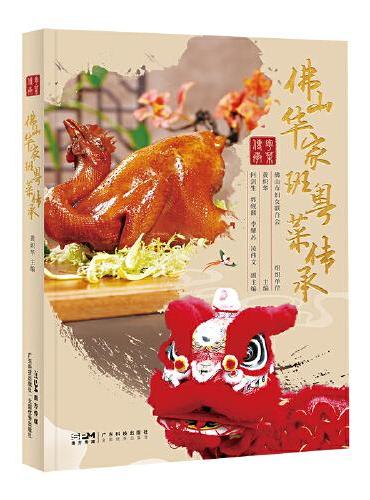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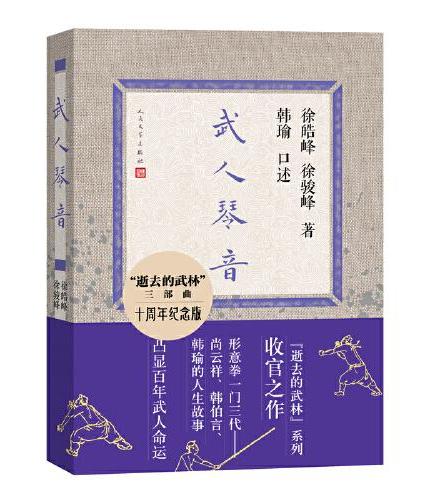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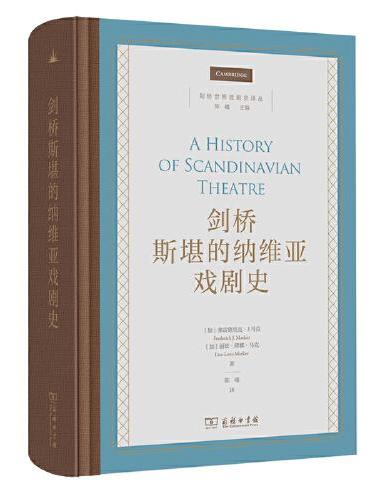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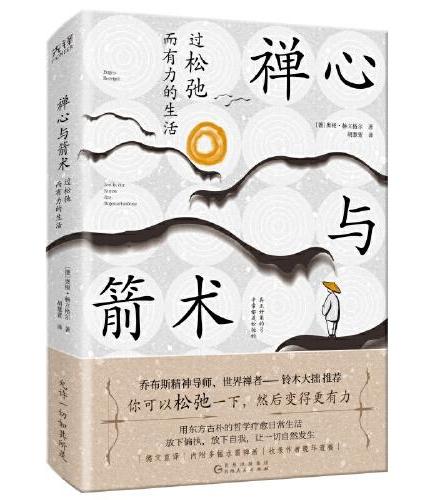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NT$
301.0
|
| 編輯推薦: |
刘亮程长篇小说处女作
倾听一个村庄的百年孤独!
内地、香港大中小学生必读作家!
《亚洲周刊》2010年度十大长篇小说!!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强力入围作品!!
刘亮程创作三十年唯一自选集 精装珍藏版
|
| 內容簡介: |
|
《凿空》是刘亮程长篇小说处女作,荣获《亚洲周刊》2010年度十大长篇小说奖,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强力入围作品。全书以魔幻现实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古老村庄里一系列看似荒诞又真实的故事。在迅速崛起的现代城市和石油井架的包围下,大规模的工业挖掘和村民们的地下挖掘,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即将被彻底凿空的村庄。
|
| 關於作者: |
|
1962年生,新疆沙湾县人。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十多年农机管理员,现任新疆作协副主席,被誉为“乡村哲学家”和“20世纪中国最后的散文家”,是继沈从文、汪曾祺之后,当代作品最经典,最常销的乡土文学作家。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及长篇散文《虚土》,长篇小说《凿空》等。《鸟叫》《我改变的事物》《对一朵花微笑》《寒风吹彻》《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作品入选内地和香港小学、中学、大学教材。
|
| 目錄:
|
序
红色1出事2村子没腿了4驴叫4
第一章
“腾”9宝贝11土里的人12洞14房子16诵经18
第二章
相好20地下驴叫23地被捣疼了25
驴的身体是一座桥25大巴扎27木头的声音27粮食巷28
清真寺29“西气东输”29卡瓦(葫芦)30
第三章
公路的声音33水泥块里的钢筋35挖出好东西36倾听37
有人也在挖洞39
第四章
铁匠铺40柏油路41坎土曼工程44
拖拉机把铁匠铺救活了46车祸48原油49车斗49
第五章
亚生村长52黄母狗54要发生事情了55美容院58
石油井架58
第六章
坎土曼62女主人64铁锨是坎土曼变的66等活66
坎土曼是铁锨变的67磨损的铁锨69
龟兹佛窟是坎土曼挖出来的71佛像73
第七章
艾疆76驴怎么想78一个活法80嫁接81
第八章
通气口86咳嗽88哭声传进洞里89路90
第九章
库半92起风93解放牌汽车93狗叫95阴森96
夜晚的味道97一只羊占两个人位子99比肚子更饿的地方100
第十章
玉素甫102打架103一疙瘩铜钱105生土的味道107
第十一章
狗知道109村庄的气味都不一样110铁勺铲锅底的声音111
轰隆隆113出大事114
第十二章
地下村子116向导118工程队120坎土曼老板121
一个人的洞123艾布125黑汉126
第十三章
挖掘声128王兰兰129洞那头131种子132房子133
头顶的驴车135土里的走路声136
第十四章
漆黑138空洞的睡眠141等树叶飘落141巷子143
夜晚144
第十五章
白杨树梢的哗哗声148库房149集体保管种子150
副村长151致富152一窝老鼠154会挖洞了157
第十六章
墓位159麻扎是最安全的地方161六百年历史163家族166
第十七章
毛驴协会167午饭169驴头数171驴档案172黑母驴173
阿赫姆说驴175鸡师傅古丽莎176狗师傅艾布177
羊师傅是阿不拉江177驴师傅阿赫姆178驴睡觉吗178
驴干的活179
第十八章
老鼠药181听懂驴叫183灭鼠184外来老鼠185
浩浩荡荡186老鼠上吊187
第十九章
铁190铁匠铺造的农机具192拖拉机的秘密193铁驴车195
一堆烂铁响197铁东西多起来198
第二十章
五保户埃希提201坎土曼的声音203割礼205
头里的打铁声207危险的事208艾布210黑汉212
第二十一章
十三代铁匠214印记215变形216命220兵器223
坎土曼的挖痕224各说各226钉驴掌227坎土曼是啥228
第二十二章
调查队来了230地窖231中午饭233漏洞235艾布的洞236
驴不怕警车237隐瞒238阿訇的话240“就这样吧”241
第二十三章
拉着心的那头驴乏了244错误246失踪248土里的脚步249
适应黑252钥匙253一个人的洞254
第二十四章
老村长额什丁257脚印259狗和驴都知道261一茬子人262
狗认得谁是村长264驴开会265嘴严267驴是人骑的268
第二十五章
棉花开了270洗头房271文化广场274石油井架277
开挖281
第二十六章
大驴头283文件285三轮摩托287铁牲口288
村庄的一半是驴的290驴和拖拉机291羊和拖拉机293
狗和拖拉机295人和拖拉机298
第二十七章
驴教授来信300坏话302驴报告303驴中间的人师傅305
祖先用过的毛驴306
第二十八章
驴车路309万驴齐鸣310这辈子没见过的事312
驴疯了314驴在叫啥314完蛋了316调查319保密文件321
第二十九章
枪声324追驴326天光328逃脱330黄胡子331
第三十章
张旺才的洞334铁锨和坎土曼335探子338坎土曼学340
第三十一章
玉素甫的洞342埋掉的村庄343春天照旧来了345
坎土曼的活又来了346谣言349
第三十二章
定数352大号坎土曼353驴自己跑来钉掌354叮叮354
第三十三章
说给驴听358驴政策359红头文件359
驴叫声里谈买卖360驴脾气361驴为坎土曼操心361
驴喜欢歪东西363驴不叫天会塌下来363
一种叫等的生活364硬骨头365荒谬366掉下去368
第三十四章
张旺才370头顶上的家372测量373挨打374抓获376
那些年377挖一个洞走回来378通了381
第三十五章
回家382古兰经385声音386爆爆米花389凿空391
声音的故事396
跋
张金399耳朵402
我喜欢写被我视若平常的事物407
|
| 內容試閱:
|
【序】
红色
驴叫是红色的。全村的驴齐鸣时村子覆盖在声音的红色拱顶里。驴叫把鸡鸣压在草垛下,把狗吠压在树荫下,把人声和牛哞压在屋檐下。狗吠是黑色的,狗在夜里对月亮长吠,声音悠远飘忽,仿佛月亮在叫。羊咩是绿色,在羊绵长的叫声里,草木忍不住生发出翠绿嫩芽。鸡鸣是白色,鸡把天叫亮后,便静悄悄了。
也有人说黑驴的叫声是黑色,灰驴的叫声是灰色。都是胡说。驴叫刚出口时,是紫红色,白杨树干一样直戳天空,到空中爆炸成红色蘑菇云,向四面八方覆盖下来。驴叫时人的耳朵和心里都充满血,仿佛自己的另一个喉咙在叫。人没有另一个喉咙,叫不出驴叫。人的声音低哑地混杂在拖拉机、汽车和各种动物的叫声中。
拖拉机的叫声没有颜色,它是铁东西,它的皮是红色,也有绿皮的,冒出的烟是黑色,跑起来好像有生命,停下就变成一堆死铁。拖拉机到底有没有生命狗一直没弄清楚,驴也一直没弄清楚,驴跟拖拉机比叫声,比了几十年,还在比。
驴顶风鸣叫。驴叫能把风顶回去五里。刮西风时阿不旦全村的驴顶风鸣叫,风就刮不过村子。
驴是阿不旦声音世界里的王。
天上云一聚堆,驴就仰头鸣叫。驴叫把云冲散,把云块顶翻。云一翻动,就悠悠晃晃地走散。驴不喜欢下雨。毛驴子多的地方都没有雨。民间谚语也这么说:“若要天下雨,驴嘴早闭住。”
往远处走,村庄的声音一声声丢失。鸡鸣五更天,狗吠十里地。二里外听不见羊咩,三里外听不见牛哞,人声在七里外消失,剩下狗吠驴鸣。在远处听,村庄是狗和驴的,没有人的一丝声息。更远处听,狗吠也消失了,村庄是驴的。在村外河岸边张旺才家的房顶上听,村庄所有的声音都在。张旺才家离村子二里地,村里的鸡鸣狗吠驴叫和人声,还有开门关门的声音都在他的耳朵里。他家的狗吠人声也在村里人的耳朵里。
出事
我走到阿不旦村边时突然听到驴叫。我好久听不到声音,我的耳朵被炮震聋了。昨天,在矿区吃午饭时,我看见一个工友在喊我,朝我大张嘴说话,挥手招呼,我走到跟前才隐约听见他在喊:“阿不旦、阿不旦,广播里在说你们阿不旦村出事了。”他把收音机贴到我的耳朵上,我听着里面就像蚊子叫一样。
“你们阿不旦村出事了。”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喊,声音远远的,像在半里外。
我从矿山赶到县城,我母亲住在县城医院的妹妹家。我问母亲阿不旦到底出啥事了,我看见母亲对着我说话,我说:“妈你大声点儿,我听不清。”母亲瞪大眼睛望着我,她的儿子出去打了两年工,变成一个聋子回来,她着急地对着我的耳朵喊,我听着她的喊声仿佛远在童年。她让我赶紧到医院去治:“你妹妹就在医院,给你找个好医生看看。”
我说去过医院了,医生让我没事就回想脑子里以前的声音。“医生说,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我的听觉。”我喊着对母亲说。我听见我的喊声远远的,仿佛我在另外的地方。
母亲不让我回村子,她说村子都戒严了。我说,我还是回去看看我爸。母亲说,那你千万要小心,在家呆着,别去村子里转。我啊啊地答应着。
我从县城坐中巴车到乡上,改乘去村里的三轮摩托。以前从乡里到村里的路上都是驴车,现在也有驴车在跑,但坐驴车的人少了,驴车太慢。
三轮车斗里坐着五个人,都是阿不旦村人,我向他们打招呼,问好。坐在我身边的买买提大叔看着我说了几句话,我只听清楚“巴郎子”三个字。是在说我这个巴郎子回来了,还是说,这个巴郎子长大了,还是别的。我装着听清了,对他笑笑。早年我父亲张旺才听村里人跟他说话,第一个表情也是张嘴笑笑,父亲不聋,但村里人说的话他多半听不懂,就对人家笑,不管好话坏话他都傻笑。我什么话都能听懂,父亲张旺才的河南话,母亲王兰兰的甘肃武威话,村里人说的龟兹方言,我都懂。母亲说我出生后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汉语是龟兹语。我不光能听懂人说的话,还能听懂驴叫牛哞鸡鸣狗吠。现在我啥都听不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聋了,别人出去打工都是挣钱回来,我钱没挣上,变成一个聋子回来。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车上人挤得很紧,我夹在买买提和一个胖阿姨中间,他们身上的味道把我夹得更紧。我从小在这种味道里长大,以前我身上也有和他们一样的味道,现在好像淡了,我闻不到。可能别人还能闻到,别处的人还会凭嗅觉知道我是从哪来的。没办法,一个人的气味里带着他从小吃的粮食、喝的水、吸的空气,还有身边的人、牲畜、果木以及全村子的味道,这是洗不掉的。三轮车左右晃动时,夹着我的气味也在晃动,我的头有点晕,耳朵里寂寂静静的,车上的人、三轮车、车外熟悉的村庄田野,都没有一点声音。
村子没腿了
到村头,我跳下车,向他们笑了笑,算打招呼。我站在路边朝村子里望,看见村中间柏油路上停着一辆警车,警灯闪着。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驴车,也不见毛驴,也没驴叫。往年这季节正是驴撒野的时候,庄稼收光了,拴了大半年的驴都撒开,聚成一群一群。那些拉车的驴、驮人的驴,都解开缰绳回到驴群里,巷子和马路成了驴撒欢儿的地方,村外大麦场成了驴聚会的场所,摘完棉花的地里到处是找草吃的毛驴。驴从来不安心吃草,眼睛盯着路,见人走过来就偏着头看。我经常遇见偏着头看我的驴,一直看着我走过去,再盯着我的背影看。我能感到驴的目光落在后背上,一种鬼鬼的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注视。我不回头,我等着驴叫,我知道驴会叫。驴叫时我的心会一起上升,驴叫多高我的心升多高。
今年的毛驴呢?驴都到哪儿去了?村庄没有驴看着不对劲,好像没腿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庄是一个长着几千条驴腿的东西,人坐在驴车上,骑在驴背上,好多东西装在驴车上,驮在驴背上,千百条驴腿在村庄下面动,村子就跟着动起来,房子、树、路跟着动起来,天上的云一起动起来。没有驴的阿不旦村一下变成另外的样子,它没腿了,卧倒在土里。
驴叫
我母亲说我是驴叫出来的,给我接生的古丽阿娜也这样说,母亲生我时难产,都看见头顶了,就是不出来,古丽阿娜着急得没办法,让我妈使劲。我妈早喊叫得没有力气了,去县上医院已经来不及,眼看着我就要憋死在里面。这时候,院子里的驴叫开了,“昂—叽昂叽昂叽”—古丽阿娜这样给我学驴叫。一头一叫,邻居家的驴也叫开了,全村的驴都叫起来。我在一片驴叫声里降生。
“驴不叫,你不出来。”古丽阿娜说。
我出生在买买提家的房子里,阿依古丽给我接生,她剪断我的脐带,她是我的脐母,我叫她阿娜(阿姨)。我在阿娜家住到三岁,她把我当她的孩子,教我说龟兹语,给我馕吃,给我葡萄干。那时我父亲张旺才正盖房子,我看见村里好多人帮我们家盖房子。我记住夯打地基的声音,“腾、腾”,那些声音朝地下沉,沉到一个很深的地方,停住。地基打好了,开始垒墙,我记得他们往墙上扔土块和泥巴,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墙头,一个人在墙下往上扔土块,扔的时候喊一声,喊声和土块一起飞上天。抹墙时我听见往墙上甩泥巴的声音,“叭、叭”,一坨一坨的泥巴甩在裸墙上又被抹平。声音没法被抹平,声音有形状和颜色。
我小时候听见的所有声音都有颜色,鸡叫是白色,羊咩声绿油油,是那种春天最嫩的青草的颜色,老鼠叫声是土灰色,蚂蚁的叫声是土黄色,母亲的喊声是米饭和白面馍馍的颜色,她黄昏时站在河岸上叫我。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出村子住在了河岸,我放学在村里玩忘了时间,她喊我回家吃饭。我听见了就往家走,河边小路是我一个人走出来的,我有一条自己的小路。我几天不去村里学校,小路上就踏满驴蹄印。我喜欢驴蹄印,喜欢跟在驴后面走,看它扭动屁股,调皮地甩打尾巴,只要它不对我放屁。
我的耳朵里突然响起驴叫,像从很远处,驴鸣叫着跑过来,叫声越来越大。先是一头驴在叫,接着好多驴一起叫。驴叫是红色的,一道一道声音的虹从田野村庄升起来。我四处望,望见红色驴鸣声里的阿不旦村,望见河岸上我们家孤零零的烟囱,没有一头驴。我不知道阿不旦的驴真的叫了,还是,我耳朵里以前的驴叫声。
我听了母亲的话没有进村。从河边小路走到家,就一会儿工夫。我们家菜地没人,屋门朝里顶着,我推了几下,推开一条缝,手伸进去移开顶门棍,我知道父亲在他的地洞里,我走进里屋,掀开盖在洞口的纸箱壳,嘴对着下面喊了一声。我听不见我的声音,也听不见喊声在洞里的回响。我知道父亲会听见,听见了他会出来。
我坐在门口看河,河依旧流淌着,却没有了声音,河边的阿不旦村也没有一丝声音,这个村庄几天前出了件大事,它一下变得不一样。也许是我变得不一样,我的耳朵聋了。
耳聋后我瞒着母亲和妹妹去过两次医院,前一个医生让我住院治疗,我摇摇头,说我没钱。后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个不花钱的方子,让我没事就回想:“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你的听觉。”我望着医生,直摇头,脑子里空空的啥声音都没有。
“那你回想小时候村子里的声音。”他不问都知道我是村子里出来的人。
往村里走的一路上,我都在回想这个村庄的声音,我以为那些声音都死掉了。刚才在村边听到驴叫我有多高兴,我知道它们还在。我坐在河岸上,想着村子里所有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个由声音回想起来的村庄,离现实的阿不旦村有多远,就像我耳聋以后,身边的声音变远,那些早已远去的声音背后的故事却逐渐地清晰起来。这是一个聋子耳朵里的声音世界,我闭住眼睛回想时,我听到了毛驴的鸣叫,听到铁匠铺的打铁声,听到这一村庄人平常安静的龟兹话语,听到狗吠羊咩和拖拉机汽车的轰隆声,再就是我父亲挖洞的声音。他挖了二十多年洞,耳聋之后我才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
他该出来了吧。
【我喜欢写被我视若平常的事物】
符二访谈刘亮程
第一天(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符二:谈谈最近的写作动向。
刘亮程:在写一部跟新疆历史有关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那个节点正好是新疆伊斯兰教和佛教交锋最激烈的时期。
符二:那是在北宋时期。
刘亮程:是。那是新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于阗佛国和喀喇汗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宗教战争,最终伊斯兰教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冲突,但战争和冲突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声音和语言。
这本小说名叫《捎话》。讲的是一个懂得几十种语言的捎话人的故事。因为战争,书信往来困难,只有动用民间的这种捎话人,把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的话,长途跋涉捎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给别人。
符二:捎的过程中会不会像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一样,最后传得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
刘亮程:会的。因为语言在捎的过程中都会变。语言是最不可靠的。写成书面的东西可能相对可靠一点,但是靠口传是绝对不可靠的。语言在走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方式。在向别人转述的时候,因为语词的关系,还牵扯到翻译的问题,可能将一种东西变为另外一种东西。我们汉语有一句话,叫作“话经三张嘴,长虫也长腿”,这就是传话过程中语言的走形。传到远处的话大都面目全非。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预计得两年时间能写完吧。
符二:动笔了吗?
刘亮程:已经写了一部分了。感觉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次长途捎话,从遥远的先人那里把话接过来,捎给现在和以后的人。只是不知道那些接话的人都是谁。
符二:现在透露,难道不担心两年后还没完成,却已被他人抢先拿去写了吗?
刘亮程:没关系。也不可能。我就是把故事全部告诉别人,别人写出来也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作家是一种最不老实的捎话人,他不安分于现实。同一句话在一百个作家那里有一百种说法。同一个故事自然会被写成一百个故事。
符二:从一开始,您就在气定神闲地书写村庄,书写新疆大地上所有发生的一切,最后赢取了声名和读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于新疆的题材比较讨巧吗?
刘亮程:我从来不写新疆的传奇,从来不猎奇式地写新疆题材。新疆是我的家乡。家乡无传奇,看啥都是视若平常。我喜欢写已经被我视若平常的事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事物我才是熟悉的,我才能够把握和呈现它。当我书写时,那些被我看旧的事物又是多么的新鲜如初。
符二:刚才说到新的写作方向,您是否想要突破和颠覆此前的自己?
刘亮程: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自己,颠覆自己。问题是你超越自己要干什么。我超越别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超越自己?
符二:但很多作家都在为读者改变。
刘亮程:但很多作家改来改去多是在原地转圈。只是在变花样。
我们应该相信个人超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作家只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但是读者往往对作家的完善视而不见。读者不欣赏你的成熟。读者欣赏的是你最初的那种冲动,你最初展示给他的那种内心的盲目的、茫然的、不知所措的冲动。作家茫然不觉时已经把最好的作品给了读者。读者还想要更好的。有时候作家和读者是相互偏离的。作家常常想要把活儿越干越好,每一部作品都打造成一个精品,而读者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在这个玉雕作品上再多动一刀,少动一刀,读者对这个视而不见。他要的可能还是你最初给他的那些。但你没有了。或者变化了。
符二:这也不能责怪读者。
刘亮程:不是。它是两种愿望和追求,不一样。读者的阅读愿望和作家的写作愿望是两回事,所以可以互不理睬。读者可以不理睬作家,你写得再好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选择去读别的新作家。作家也一样,他也在选择读者。
符二:那您认为写作的过程包不包括读者的阅读?
刘亮程:不包括。写作独立于阅读之外。阅读是跟一部作品的相遇。
符二:我想知道,当初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您知道它是好的东西吗?
刘亮程:我当然知道它是好东西。写的时候就觉得好得不得了。
符二:那如果没有读者的回应与认可呢?
刘亮程:那也没关系。你要相信,好的东西,即便再放多少年,它依然会被人看到。当然一部作品被这么广泛地阅读之后,它可能会被更多的人挖掘出更多的意义来,这部分是靠阅读完成的。
但是首先这部作品要能经得起读者的阅读。其实一部好作品,它面对的不是一代人的阅读。一代人把它看熟悉了,下一代人来看仍然是新鲜的。就像《一个人的村庄》,我相信就是再过两三代人,他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仍然认为这些文字是新鲜的。他不会因为他的爷爷已经读烦了,他会觉得烦。
作家不需要过多地为读者着想。当然你要写一部畅销书,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读者群,你的读者是谁,你在为谁而写作。但我不考虑这些。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谁,我就是想为我的读者去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就不想它。《一个人的村庄》就是在漫长的十年时间里,一篇一篇去写完的。在写的过程中,也没考虑什么读者群,只是把它写完而已。我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我的书就卖几万本。当然《一个人的村庄》卖到了几十万本,我不知道这几十万的读者都是谁,是些什么人群。我的写作一直是一种盲目的写作,不知道自己能写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一旦我开了头,那个文字里的世界会自己动,会自己完成。
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在一种茫然的醒悟中开始,同样在一种茫然的醒悟中结束。
符二:那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刘亮程:我本来就喜欢这样一种混沌的状态。
符二:如果这次写作不成功,您现在在做着什么?
刘亮程:可以干别的呀。我小时候学过许多手艺,编制、木工、种地,随便干一件都活得好好的。
符二:感到满足吗?
刘亮程: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嘛。一个种地的刘亮程和一个写书的刘亮程,我都可以满足。
符二:再成功的作品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极致的完美,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自己的作品缺陷在哪儿?
刘亮程:缺陷很多。我记得刚开始文学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写作者。我看那些优秀的文学,觉得我这辈子可能永远都写不了这么好。所以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多么出色的作家,一篇一篇去写。只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把好多自己的缺点规避了。
符二:比如说?
刘亮程:这我说不清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缺点或者软肋,他只是不把这个示给别人。文学就是美饰。“文”就是花纹嘛,作家靠自己的花纹可以把自己的缺陷掩盖起来。或者他天然就懂得去绕开自己的缺点,呈现自己的所长。再或者说,他有办法让缺点成为特点。我的许多缺点其实都变成特点了。你不觉得我的文字很有特点吗?
符二:把不好的隐藏起来。
刘亮程:不用隐藏,他只呈现他能够呈现的。他不去碰他碰不动的东西。他不用鸡蛋去碰石头,他用石头去碰鸡蛋。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天然知道选择去做自己能做好的事。什么叫好?就是干了自己能干好的事就叫好,而不是干了自己干不好的事情,那样好事情也干坏。
符二:传统的小说是有情节有故事的,线性的,指向明确的。但是您的两部小说,仿佛只能完整地存在于小说本身之中,不可转述,无法概括。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小说?
刘亮程:也有读者读《凿空》以后,觉得不知道顺着哪个线索去读,觉得很难读下去。但是也有读进去的人,就说这部小说好得不得了。不是有两种读者吗?那这部书就是写给能读下去的那些读者的。
符二:您是否有一种野心,想要成为新疆的马尔克斯,或者退一步,成为新疆的代言人?
刘亮程:我是一个闲人,不操心去成为什么。我觉得像我这样,一旦进入写作的状态,感觉来了的时候,我是完全自信的,无论我写到哪个地方,都能石头开花。
我们常说作家写作要有灵感。作家是把写作灵感变成常态的人。一旦他坐在那儿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就会进入这种写作状态,要不然一个人一天天坐在那儿等灵感,等到何时才能写出一部作品?
符二:现在是您写作最好的时候吗?
刘亮程:不是。我写作状态最好是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那时候更纯粹。《一个人的村庄》大家认可的文学价值可能也更高。因为《一个人的村庄》太完整。尽管是由一篇一篇散文构造的,但是我塑造的刘二这个人物非常成功。一个乡间闲人。它是我青年时期的成熟作品。我在乡下思考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年的诗歌,有这样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到城市来,远远地眺望自己的家乡,完成了一个人对家乡的回望。它是我的处女作,是我的元气之作。一个人的元气之作里有很强的那种灵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到现在,有人说我无法超越《一个人的村庄》。我说对的,我不需要超越它。但我会绕过它,写出另外一部书。
符二: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读者总是期待那些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
刘亮程:一般都是早晨或下午抽点时间写写东西,有时候不写,就是打开电脑看一看那些文字,还在那儿躺着。就是时刻关照它,跟它不要断了联系。有时候好久不写,也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那些写了一半的文字。我是一个写作很慢的人,“慢”也是闲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时间都是被慢人拖延住的。
符二:人们将您誉为“乡村哲学家”,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刘亮程:什么乡村哲学家,乡村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到村里面去,那些老头偶尔说一两句话,你会觉得像是天人语。人家琢磨了一辈子,说几句话,当然够你琢磨一阵子。我记得小时候,我很懒,我一不干活,一闲着,我后父就说:“人站一站也老呢,你为啥不动一动呢?”说我为啥不干活,站在那儿闲着也会老的,为啥不去干干活?最后我把这句话写到书里面了。写到书里面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既然人动一动也会老,我为啥不站着?忙着也会老,我为啥不闲着?既然都是这样,那选择闲肯定更好嘛。
符二:同一般人比较起来,觉得自己观察事物的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刘亮程:我关注生活,其实我是在关注时间。人在时间中的衰老和年轻,希望和失望,痛苦和快乐。人在时光中的无边流浪。
符二:您很痴迷于这个东西。
刘亮程:是很痴迷。我在《一个人的村庄》里面写到,一根木头在时光中开裂,一根木头经过几十年的岁月在某个墙角慢慢地腐朽掉。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焦点。伴随时间的这些人和事物,反而成了配角。
符二:每次下笔,就算面对的是一头驴、一棵草,您都从不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否出于天然的对事物的理解?
刘亮程:你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理解,它是一种沟通。任何事物,包括一个土块、一个石头,你只要安静下来,有跟它沟通的愿望的时候,它就能沟通。
这种沟通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物理上的那种沟通,作家本身从事的是一种精神事业,他在书写人类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其他事物的精神相遇。我把它称之为“相遇”。当我告诉你我能都看懂一棵树的时候,你可能不相信。我看到路边的一棵树,跟它对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看懂它,我能知道它为什么长成这样,我能知道树的某一根枝条为什么在这里发生了弯曲,它的树干为什么朝这边斜了。我完全知道一棵树在什么样的生活中活成了这样。而且,我也能看到树在看我。相互看。
符二:这难道不是常识或知识所致?
刘亮程:这不是,是交流。你会感动。有时候看到树的某个地方突然弯了一下,你会感动,就像看到一个人受了挫折一样。这种感动就是一种交流。
我崇尚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萨满认为,每一个事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事物,都是有灵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宗教。在作家眼里,所有事物都应该是有灵的。我们不跟它交流或者说我们不能跟它交流,是因为我们光有“心”没有“灵”。
符二:怎么讲?
刘亮程:我们所说的心灵,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肉身的“心”,一部分是精神的“灵”,这个“心”必须是有灵的,才叫“心灵”。很多人是光有“心”而没有“灵”,这个就不能叫“心灵”,只能叫“心”。
作家是那种有心灵的人。有心灵的人,他的“灵”就可以跟其他事物的“灵”去相遇、去交流、去对话。可以感知彼此的存在。什么叫文学?最好的文学就是靠作家的心灵,让你的文字在事物中自由穿行。你的文字到达一根木头的时候,这根木头是有灵的;到达一片树叶的时候,这片树叶是有灵的。你的文字所到之处,整个世界,灵光闪闪。在作家写作过程中,不是一片死寂。没有死的东西。在作家眼里,那些死东西,作家靠自己的“灵”,可以把它激活,让它变成活的。写作就是一个作家激活事物的能力。在你的作品中,这个东西你写得活灵活现,你把它的神写出来了,证明你就跟它的“灵”产生交流了。或者它原本的“灵”被你激活了,发现了,它跟你交流了。
符二:我注意到您的作品,用词颇为精准,句型很是简明。对语言有什么追求?
刘亮程:我对语言的感觉非常好,非常敏感,就像一个天才的音乐人对音符的感觉一样,有一点点不好都听不下去。我的阅读和写作也是这样。我读过一些作家的东西,别人说这个小说很好,但我接受不了他的语言。那种粗的语言,不讲究,砖头一样硬邦邦地在堆砌故事,在生造事物,我受不了。写作也是这样,我觉得某个字不合适,我都没法写下去。
符二:所以写下的每一句话,都那么感性却又明晰。
刘亮程:我们古汉语中,语言自身的逻辑非常清晰,不需要那么多的成分,疙疙瘩瘩挤在一起。
你看明清笔记,多简洁呀。他们叙述一个事物的时候,无论场景复原,还是情态的描述,都一句话就能到位。现在的翻译语言,漫长的句式,一个句子读完以后不知道中心在哪儿。我发现好多小说作家,都是受翻译语言的影响,他们的句子很长,句子中塞入了过多的内容。相对而言,我的语言还是短的。接近古汉语。我对词语的这种要求,对语言的这种苛刻,再加上我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经历,还有在西北地区受当地口语的影响—西北人说话都是短句,语言中缺少成分,说半句话—你在民间话语中很少听到一句完整的话,好多人只说半句话。说半句话就懂了,为什么要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写作也是这样。半句话说完的,就没必要说一句。最好的句子是半句。半句说完一个事。
符二:但是有些作家会担心读者看不懂他们写什么。
刘亮程:不自信的作家都是怕别人不懂。自信的作家都是自言自语,不管别人懂不懂。自言自语就是一种最好的状态。眼睛朝天,说地上的事情。整个《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符二:身为作家,觉得自己的最好品质是什么?
刘亮程:不知道。还有待于你来发现,告诉我。
第二天(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符二:谈一下您所理解的文学。
刘亮程:有些作家把文学当成了讲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去讲。有些作家把文学当成了说道理。还有一些作家,像农民一样在写作,面朝土地,像农民刨土一样去刨土地上的那些故事。这些笨重的作家。文学需要这样去做吗?
符二:文学需要怎样去做?
刘亮程:文学需要引领我们从沉重的生活中抬起头来,朝上仰望。我发现许多作家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在讲述一个大地上的故事时,心和目光都是向着大地的,没有一种朝天上仰望的自觉。所以他们的故事从土地中刨出来,最后再还到土地中。
文学是引领我们朝天空飞翔的。在大地上获得翅膀,朝天上飞翔。
符二:您的作品做到了吗?
刘亮程:我觉得我的作品是这样。我喜欢那些有灵性的文字,三言两语中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语言抬起头来,朝上引领,朝一个不知道的存在去引领,它是有灵的,飞起来了。它用现实中的一点点材料,或者用生活中一个小故事做助跑,就可以朝天飞翔。我欣赏这样的文字。
一些作家是耗费了大地上那么多的材料,最终却没有飞起来,让一个沉重的故事沉重地砸在大地上。当然,这也是文学,爬行动物的文学。
我个人喜欢那种飞翔的文字,喜欢精灵古怪的、长翅膀的文字。从厚实的土地上,带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带着人的梦想、失望与希望、痛苦与快乐,带着人世间所有所有的一切,朝天空飞翔。我梦想的是这样的一种文字。它应该承载大地上的一切,但是朝着一个最高存在去飞升。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朝上飞升的能力。我喜欢的是一种梦一样的文学。如果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变成了一个梦,存在于文字中,我觉得它是成功的。
第三天(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上午)
符二:好了,可以开始了。
刘亮程:我刚才说什么了?
符二:您说知识如果不是让人变得世故,就会让人变得智慧。
刘亮程:对。一个作家需要突破知识障碍。什么是知识障碍你知道吗?知识在障碍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事物。
符二:知识难道不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事物?
刘亮程:不是,它是障碍而不是帮助。因为人类的知道是局限于知识层面的。在古代,我们的科学知识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就是用心灵感受、感应。后来有了科学知识,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手段了解事物,比如我们对大自然中最常见的风、雨、雷、电等都有了这样一种科学的分析和定性。比如一棵草,我们通过书本上的知识可以知道,这棵草是属于什么科,它是一年生还是两年生,它的种子是怎么传播的,它的花期、生长期,等等。我们通过这些知识就可以认识一棵草,但是恰好是这部分知识,使我们见到真草的时候不认识它。我们认识的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草,但草是有生命的。当你放下知识,放下通过知识描述的这棵草,用你的眼睛去看这棵草,用你的耳朵去听这棵草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超越知识层面的生命。如果我们仅限于知识告诉我们的这棵草,那我们跟一棵草其实就已经错过了。
作家在体验任何事物的时候,都应该把这个事物原先的知识和经验放下,去重新感受它,感验它,让它全新地出现在你的文字中。
符二:您一直是这样吗?
刘亮程:我会在经验中看到未经验的东西。我对事物的这种注视总是处在一种欢喜状态。这种欢喜它就像初次见面的感觉。一棵草,我认识它、知道它的名字,从小它就在我的家园旁边生长,但是这个秋天我再次遇到它的时候,我仍然欢喜地看着它,仿佛初次见面,其实已认识多年,草和人都到了秋天,籽粒满满的,枝干壮壮的,草看我亦如初,能不欢喜吗?
符二:这真是特别好的说法。不过,您是不是有选择性地关注乡村中那些诗意的、美好的事物,从而回避了那些庸常的、粗俗的方面?
刘亮程:我关注的是乡村时间中那些不变的东西,我不关心变的东西。我没有写到改革开放,没有写到新农村建设,没有写到城镇化。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投入过一点笔墨,我不关注这些东西。因为相对于漫长的时间和历史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短的、瞬间的。
在人类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我关注的是这些乡村事物中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在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我们的心灵那个轴心部分,它一直没有变。我们这一块心灵没有参与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参与“土改”,没有参与“三反五反”,没有参与“文革”,也没有参与改革开放。它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跟我们祖先的心灵保持着某种一致性。不要以为任何大的政治运动,都可以触及人心灵的最深处,不会的。人心灵最深处的那一点点东西是不动的,它没有变化,我关注的恰好是这一点点不动的东西。它构成了永恒。它让我们人在历经多少磨难之后,在历经许多不可抗拒的天灾和人为灾难之后,仍然能够保持人的原貌,仍然能够恢复人的尊严,仍然能够去过一种正常的、平常的、地久天长的生活,就是这一点点心灵在起作用。
符二:怎么看待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书斋型作家?
刘亮程:博尔赫斯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但我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家。他对自己世界的构建还是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或者说处在一种敞开的状态。
什么叫文学的完成?我个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论长与短,它只要完成了一种精神故乡意义,这部作品就算完成了。
符二:像福克纳那样吗,一生都在写他的小镇?
刘亮程:不单单指这样写一个小镇、一个小村庄。这样的作品太多了。就是读者在阅读他的时候,感觉他建立起来了一种完整的精神谱系,让读者的心灵可以安放其中。哪怕空间很小,哪怕这样的书写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甚至是一片树叶。
符二:您建立起来了吗?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建立起来了,它有一种故乡意义。
从故乡意义来说,那“锄禾日当午”当然也是有故乡意义的,“明月出天山”也是有故乡意义的。建立起故乡意义的文学作品,无论在中国文学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其实都不是太多。
符二:承认您的作品中有隐喻吗?
刘亮程:我不知道什么叫作隐喻。有一个评论家,把我作品当中的许多词,“月亮”“星星”“梦”,全都抽离出来,分析它的隐喻。
符二:您不认可?
刘亮程:我不认识隐喻。
符二:到处都是隐喻。文学就是隐喻。您的写作怎么能脱离开隐喻?
刘亮程:我呈现的是事物本身。我写草的时候,这棵草就是自然界的一棵草,经过我的心灵感受之后呈现给大家的。
符二:既是途经心灵,您如何还能还原它?
刘亮程:我觉得我们对自然的书写,从《诗经》、唐宋诗词到现在,一直是利用式的,自然是我们的象征物,或者说自然是我们的隐喻体,我们通过对自然的隐喻来书写我们的内心,抒发我们的内心。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文字中,自然也应该是自然本身。
至少在我的《一个人的村庄》中,我努力使这些自然之物还原本真。也可以这样说,我通过我的书写,把这些自然之物从我们的隐喻系统、象征体系中解救出来,让草木还原到草木中,还原到土地上。草木就是草木,它不需要为我们的情感去做隐喻体,做象征体。它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欢喜,有自己的风姿,有自己的生命过程。
读者在这样的一棵草上会发现更多。我的心灵是单独的、干净的,跟一棵草在对话。我看到的草就是草,不是隐喻体系中的草,不是一个象征物。
符二:但是经过了文字的书写,要知道,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辞。
刘亮程:写作是一种修辞。但是写作者更多的是要把修辞忘记。
符二:所以您的写作更不是寓言化的写作。
刘亮程:当然,你用这样的思维去呈现出来的一个自然世界,它更有隐喻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寓言性。因为事物有它的外延意义。
符二:如此看来,说您的写作质朴就不准确。就像陶渊明一样,我们说他的诗文平和冲淡,实际上,我认为他的文字非常华丽绚烂。
刘亮程:当我书写一件事物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句子,都有无限的外延性。
符二:这种延展是平面的,发散的,还是向上或纵深的?
刘亮程:它同时是向上、向下、向四面八方的。你要仔细读一读我的《虚土》,你会发现我所有句子的指向都是多向的。我不喜欢指向明确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有无数个远方,读者阅读的时候会迷茫和欢喜:它像花开一样,芬芳四溢。有一缕花香到了天上,有一缕到了地下,其他的朝四面八方扩散。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朵花的花开。
我写过十年的诗歌。诗歌追求语言的弹性,追求词语的外延意义。这种文字在《虚土》中达到了一种极致。《虚土》写作是我个人语言的一次盛开。
符二:所以你是很华丽的写作。不,也许又不能这么说。
刘亮程:朴素又华丽。
符二:安静地、从容地、缓慢地爆发出来的能量,同时又是最大的。
刘亮程:我不喜欢“爆发”这个词,太硬了,太强暴。我喜欢缓慢地进入。让事物感觉不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事物。
第三天(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下午)
符二:我有一个问题,您的两部小说,写法上跟我们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情节都不同。西方有“诗体小说”的命名,您的小说是否可以给它一个新的说法,比如叫它“散文体小说”?
刘亮程:暂时还不能。它就是长篇。或者你把它叫作长散文也可以。
符二:说它是长散文,反过来又会颠覆我们“散文”的概念。
刘亮程:其实我的《虚土》就是一部长散文。当时我没有想把它当成小说去发表。出版社说这应该归到小说里面去,我也没提异议。大家按照散文去阅读,可能效果更好。因为你把它当成小说的时候,小说经验就在起作用。
符二:我们当作散文去阅读,散文经验同样也在起作用。
刘亮程:当你把它当成散文的时候,你的心境就慢下来了,你不会去追求故事了。你的阅读就是另外的一种心态。
符二:我知道有一些作家,写了多年的散文或诗歌之后转向小说创作,因为小说比散文或诗更具读者市场,而您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刘亮程:很自然而然吧。《一个人的村庄》之后我写了第一部小说《虚土》,当时也没打算要把《虚土》写成小说,或者说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故事,按照我原先的创意,它应该是一个场面比较宏大的移民小说,因为我的家族在六十年代闹饥荒的时候就从甘肃酒泉逃荒到新疆,又从新疆乌鲁木齐到一个县上,然后到一个村庄,最终扎根在准噶尔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上,到那个小村庄其实已经走到天尽头了。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准噶尔沙漠,后面是很稀落的几个小村庄,县城都在百里之外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村庄,无路可走地停下,开始了生活。我父亲以前是教书匠,然后带着我们全家,把我们变成农民,开始了一种农民的生活。
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新疆非常之多,我就想写这样的一个移民故事。但是写着写着,我对这样的故事一点没兴趣了。我写《虚土》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人生中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样的阶段对男人来说,是一个很惶恐的年龄段,因为接下来就是步入老年,回头是青年,有人生的那种空茫感,悬空的感觉。假如人生是一个坡的话,你的生命差不多就已经到坡顶上了。《虚土》整个是以一个五岁孩子的视觉来写作,但它写的又是一个人进入中年的这种惶恐、空茫、恍惚,尤其是这样的感觉你把它设置在新疆这样的一个荒天野地之中,设置在一种渺无边际的自然之中,它可能又沾染了新疆的味道、新疆的气息。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虚土》这部书。
一开始当小说写,后来写着写着,不像小说,像散文,也不像散文,它是诗。我写《虚土》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了一个诗人的写作激情。因为我早年写诗,一直觉得没有一个机会,让我畅快淋漓地去写一首长诗。我在沙湾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两万行的长诗,写到一半我辞掉工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去了。后来这部诗,一段一段被我写进散文中,变成了《一个人的村庄》的片段。但是写《虚土》,我又回到了我的诗歌时代,那种对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感知,那种一个人蹲在某个角落里对时间、时空和人世间的这种想象。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一个诗人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小说家或者散文家的状态。所以《虚土》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我的一部长诗,是对我个人的生命有纪念意义的一部长诗。
符二:我想知道,您写《凿空》之前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因为《凿空》是一个发生在地底下的故事,是在黑暗中、摸索中、未知中的挖凿。我想换作是我,我肯定画一张精细的地图,像地下迷宫一样,将张旺才和玉素甫在什么地方相遇,将地道的走势,诸如此类,标示得清清楚楚。
刘亮程:我对那个村庄清清楚楚。这个洞要挖到哪儿,挖到第几排房子,这个村庄有一条主线穿过巷子,有哪几条巷子,我清清楚楚。写的时候,它不会跑乱。在挖的时候人物有他的方向,我也有方向。我不能把他指错了。
符二:有没有想过这部小说因为节奏太慢,或许会让读者产生难以为继之感?
刘亮程:是慢。《凿空》是散点式结构。它符合乡村生活的散漫,适合散漫地去看。我不喜欢写极端的东西,我不喜欢把人物的命运,放在一个自己勾画的严丝合缝的故事中,去压榨人性。我认为所有极端的描写都是压榨人性,他把人性放在一个他设置的叙述机器当中,靠节奏,靠故事的推动操控人物的命运,压榨人性。我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把人物放在一个相对松散、自然的环境中,让人性缓慢去盛开。这是我的一种写作原则。我认为人性在常态下的盛开可能才是最真实的。
符二:您的写作属于第四类写作吗?也即我们常说的“非虚构”?
刘亮程:文学的本质就是虚构。
符二:散文呢?
刘亮程:散文也一样。
符二:我们说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没说散文也是虚构。
刘亮程:你既然认为散文是文学,那它就是虚构的。《一个人的村庄》是虚构的。任何一种写作,哪怕它是写自己的真人真事,它也是虚构的,它首先要把自己的第一人称虚构出来。当我开始写散文时,文章中的第一人称“我”,其实已经脱离开了自己,整个状态已经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写作是一种状态,它不同于生活状态。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学人物。那种情绪已经是文学化的。尽管里面有一些故事是现实的,是真实的,但是它被这种情绪推动的时候,整个故事是虚构的,是飘起来的。像神仙一样。神仙看起来是地上的人,但是把他放到云上,他就成了虚构的人,变成神仙了。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
符二:“非虚构”是一个伪命题吗?
刘亮程:非虚构是文学向新闻通讯的投靠。作家丧失了虚构能力之后,他会向非虚构投靠,他认为现实的力量更强大。他认为我去找一个现实的题材,我去书写现实更有震撼力、更真实。这恰好是作家犯的一个错误。作家丧失了虚构的能力,失去了对世界的想象。你去看《南方周末》,每一篇文章都是非虚构。每一个事件都非常震撼人。这不是作家干的活,这是记者干的活。作家干什么?作家是从现实事件结束处开始写作。
符二:我们引入这一概念,认为真实的写作就是“非虚构”,但是我们越来越忽略了:第四类写作最本质的特征是强调写作行为的独立,强调不依附任何写作因素之外的写作。我想,或许我们的评论家们在这个理解上有些问题。
刘亮程:文学是虚构的,但不是虚无缥缈的,它跟大地,跟自己的血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高的虚构必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大地在支撑,是大地上的花开,大地上的云来云往、风起风落。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虚幻的东西太多了,提出这样的一个“非虚构”理念,也是在矫正这些东西。
符二:最后我想问一个黑暗的问题:如何看待死亡?
刘亮程:死是生的一部分。生的时候人已经在死,死亡并不是最后发生的,人一出生的时候死亡就已经发生了。
符二:在时间中最后发生的是什么?
刘亮程:最后发生的只是我们跟死亡的一次完整见面。
(符二,一九八二年生。写作小说和诗。出版小说集《在他身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