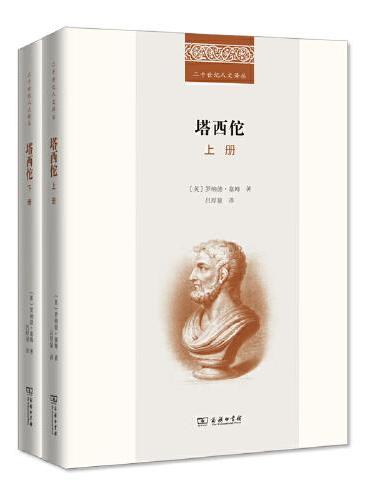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NT$
450.0

《
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NT$
345.0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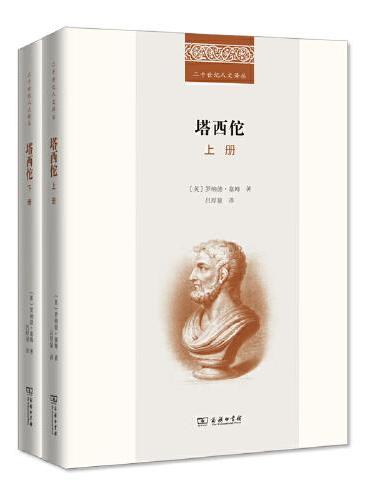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1400.0
|
| 編輯推薦: |
|
这部小说把人物置身于香港商场背景,细腻地描绘人物心理,对人物的多重性格下了很多笔力;揭示社会对人的生存信仰、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磨损.小说采用多角度自白的艺术结构,将各自人物的内心隐秘揭示出来,面对高度商业社会的利益和情感纠葛,深层地表现人性底蕴,真实、生动、亲切、可信,让读者倾听一首灵魂的变奏曲.
|
| 內容簡介: |
|
这部小说把人物置身于香港商场背景,细腻地描绘人物心理,对人物的多重性格下了很多笔力;揭示社会对人的生存信仰、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磨损.小说采用多角度自白的艺术结构,将各自人物的内心隐秘揭示出来,面对高度商业社会的利益和情感纠葛,深层地表现人性底蕴,真实、生动、亲切、可信,让读者倾听一首灵魂的变奏曲.
|
| 關於作者: |
陶然,本名涂乃贤,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尼万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年秋天移居香港。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选《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陶然中短篇小说选》;小说集《岁月如歌》;微型小说集《密码168》;散文集《回音壁》、《十四朵玫瑰》、《街角咖啡馆》;散文诗集《生命流程》等近四十本作品,分别在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出版。主编“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四辑共十六卷,主编香港三联版《香港散文选(2000~2001)》、主编《香港作家作品合集?散文卷》上下两册,由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屋联合出版。有关其作品的评论选集《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曹惠民编)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陶然作品评论集》(蔡益怀编)由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出版。
曾任青年文学獎、
香港“大学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等之小说、散文评审委员,澳门文学奖、马来西亚冰心儿童文学奖、加拿大“第一届加华文学奖”小说组评审。
现为《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顾问、香港艺发局文学组审批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级别评定委员会常任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
|
| 內容試閱:
|
从这总经理室隔窗望下去,维多利亚海港静静地躺在那里。冬阳下的海水依然蔚蓝,海面上不时滑过渡轮,让我想起许许多多道听途说的海上故事。
毕竟是四十八楼,果然居高临下,有一种大气魄。
“也不一定只是气魄吧,最重要的是风水。”瑞兴笑嘻嘻地轻摇着他的“大班椅”,整个身子都缩在那柔软高大的椅背上,“风水不好,财从何处来?”
我不懂风水,但那天美若也说过:“你看看我们家,背靠着山,面向着海,风水一流,一路发呢——这可不是我说的,是风水先生批的,你信不信?”
风水先生说的,我未必怎么信,但有你们做活广告,我焉能不信?
“我们看过铁板神算,批得非常准。”美若又说,“不容得我们不相信。”
“很贵吧?”我随口问了一句。
“一个人两万块。”瑞兴答道,“我们还托了一点关系,要不,排队也要排在半年之后。”
这么厉害?
“信不信由你。”他说。
看一次要两万,那也真是有钱的玩意儿了。我也占过卦,算过命,但也只是捐点香油钱而已,也许“级数”不同,算的也不同吧?
“真的很灵呀!连我们的子女什么时候生的,也算得很准!”美若一面剥着瓜子,一面说,“他又不认识我们。”
“许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释。”瑞兴从鼻孔中喷出白烟,“就像当年我怎么会心血来潮转行,至今也说不清楚,好像鬼使神差。也许财神爷就这样看上我,也说不定?”
其实,假如他那时不抓紧机会,凭他当时在泰国有些财势的大姐夫的关系,逃出餐厅跳到银行的话,也许也就没有今天的陈瑞兴了。
那个时候他在银行当文员,我在报馆当编辑,大家也差不多。我也还没成家,没事就往他家跑,吃饭睡觉,也都很随便。那个周末下午,我们跑到“明珠”电影院去看阿伦狄龙主演的《
独行杀手 》后,回到他家,恹恹地斜躺在沙发上,谁都不出声。
这电影够凄美的吧?也许杀手的下场都是如此,只不过当阿伦狄龙中暗枪倒下,影片戛然结束时,仍不免令人有些抑郁。他追逐别人的生命,殊不知别人也在追逐他的生命,这是永远没有完结的战斗,直至死亡才能解脱。我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
瑞兴好像也从深思中惊醒过来,欠起了身子,道:“杀手孤独寂寞,别看他表面威风,内心其实也胆战心惊。反而追逐金钱没有那么危险。”
不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杀手说到底不也就是为了钱?有钱就可以收买人命。
他仰头呆望着天花板,沉吟了一会儿,才答:“赚钱就要赚大钱,小钱没有用的。有了大钱……”
大钱?别臭美了,我现在连小钱也没有呢!
“正因为没有,才要拼命去找。”他微微一笑。
你要找就一定能找到了?
“不一定,但我不放弃。”他愣了一会儿,才说:“假如我找了,却一直没法找到,那我认命。但如果根本没有去找,那便是我自己白痴!”
见我没再搭腔,他忽然一掌打在我的肩膀上,笑道:“那么严肃干什么?发发白日梦而已。我当杀手不行,你看我都有点发福了,当杀手必须身手灵活,而且枪法要准。我只能打鸟枪。”
鸟枪?我笑。他的鸟枪也不大高明。
那时他在追求美若,情绪却低落。他提着一支鸟枪,要我陪他到学校后园去。坐在树荫下,他告诉我说,美若的哥哥持反对态度,说:“要做我们高家的女婿,必须出色,他怎么行?”
看到他愤愤然的样子,我有点担心他会用鸟枪对付美若的哥哥。我唯有好言相劝:“你别傻气了,天底下也不是只有一个美若,天涯何处无芳草?美若不行,你就再找英若啦,德若啦,法若啦,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对不对?”
“大丈夫何患无妻?”他抬头问我。
“正是。”我把心一狠。
“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呀,”我硬着心肠说,“既然美若说了,必须她哥哥同意才行,你又过不了这一关,你说怎么办?还是正视现实啦!”
他忽地站起来,举枪瞄向一棵树。他说:“就以这一枪为准,倘若我追得到,那麻雀会给我射中;假如追不到……嗯,追不到就不说了!”
枪声微响,麻雀高飞。他气得把鸟枪撂在地上,喃喃地说:“没理由呀,我平时枪法不赖呀!”
不相信也不行,射不中就是射不中。只不过美若终于还是嫁给他了。
但是他的鸟枪枪法……
不过,在人的一生中,鸟枪枪法大概也算不得什么,倒是阿伦狄龙忧郁的蓝眼睛教人有些分心。
冷面,紧皱的眉头,男性魅力无穷。
“但他不能笑,他一笑就不好看了。”瑞兴说。
我怎么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冷面漂亮过笑脸。人都会有一个最佳角度,可能这也是阿伦狄龙的“最佳角度”,别人是模仿不来的。
“唉!独行杀手也好,城市牛郎也好,都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商场强人,这才实际些。”他说。
当时我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人往高处走嘛,即使我,明知不可能捞得风生水起,但有时随心所欲地幻想一下,也很过瘾。假如一个人连一点幻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太悲哀了吗?生活本来就够沉重的了,人总得要会排解一下自己,没有宣泄的渠道,还怎么度日?
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也不知道他是否心里藏着一个目标,只见他一步步地攀向高峰,好像攀得越来越好。
我至今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身家,也从来没有打听过。他没有主动提过,我也不问。人人心底大约都有或大或小的秘密,关系再怎么密切,也要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一方领地,交往才会舒适随意些。以前,每到年底,他都会笑着对我说:“明年圣诞吧,明年圣诞应该鸟枪换炮了!”我并不太在意,只不过附和几句:“好哇!明年该如何庆祝?”“随你!”他说:“我老弟发达了,你老哥也有好处嘛,这还用说?”但是一年又一年,他老是说:“明年圣诞吧……”每次也都引起我的憧憬,虽然并不是把自己的前景交托在他的运程上,但我既明知自己不会发达,私心也就不免暗暗期望这个哥儿们到时扶我一把。也不知道我这想法是不是没出息?不过,人一旦给经济的担子压垮了,志气还有什么用?生活本身是严酷的,住的吃的穿的用的,少一分钱都不行。志气太抽象,钱最实际。可是我自己又苦于没有本事做生意,连讨价还价都拉不下面子,叫我去追账岂非要了我的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重要的是自己要找出适合于自己发挥能力的位置,明知自己不行,却勉为其难,哪里会快活?
不管怎样,他的环境越来越好,倒是显然的。我刚来港时,他和美若还是租住美孚新村一个六十平方尺三房一厅的房子,其中两间房分租给别人,后来他准备退却到新界,我还极力反对,说:“你一到新界,就很难返回市区了!”其实心里却自私地盘算着,他搬得那么远,我岂不是没有什么可以过从的老朋友了?他对我笑了一笑:“管不了那么多了,那边房租便宜,在乡村嘛!我准备筹点钱,开个山寨厂织毛衣,旧的手摇机器也不太贵。在那里进可攻退可守,等到条件成熟,我再杀回来!”我心里不舍,叹了一口气:“谈何容易!”不料他真的回来了,重住美孚新村时,已经是一百六十平方尺的自置房子,再转两转,便转到中环半山区了,简直就像是在变魔术一样。
只是他重回市区后,来往倒不如他还在新界时那样多了。我只觉得他似乎很忙,打电话也常找不到,我甚至不太知道他的生意伙伴是谁。在新界时,他那小小的山寨厂雇用了二十来个少女,我几乎都认识。那里地方大,也没有汽车,家家的孩子都随处乱走。美若学医,因为是大陆大学文凭,在香港无法挂牌行医,只好做其无牌医生,收费低,医术又好,村民们渐渐便成了熟客。有她做后盾,瑞兴也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生意上动脑筋。
那回我去他家睡了一晚,次日是星期天,他说:“走吧!村长给他家老人做寿,我们去吃酒!”我想推辞,美若却说:“村子里很随便,而且主人家喜欢热闹,人越多越好。你看看乡村摆酒也好。”
去就去吧。
饭桌摆在屋外,只见露天下尽是一圈又一圈的宾客,密密麻麻。碗筷声。碰杯声。谈笑声。春天暖暖的阳光洒了下来,“生力”啤酒在琉璃杯里冒泡。几个妇女穿梭传菜,来客吃饱了便走,新来的代替那空位。莫非这叫“流水宴”?一切都显得那么随意,我虽然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感到拘束。旁边的村民与瑞兴热烈地招呼后,转头问我:“市区来的吧?莫嫌我们乡下……”
那时我内心里也有一种优越感,想的是,这般吃法,倘若夏天,阳光酷热,怎生吃得下?晒都晒死了,何况还有些苍蝇,飞来飞去。还是我们市里好,酒楼干净,侍者招呼周到,有排场;这里?这里连寿星公也看不见,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乡村自有乡村的纯朴人情味,没有都市的疏离感,人人似乎都在高度戒备,人情冷漠。难道这是因为人的相对独立,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有太多的合作而造成的?或是因为社会的渐趋复杂化,令人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因为人人都忙得无暇他顾,哪里还有闲情去聊天叙旧,无益又无建设性?比方瑞兴,现在我也难得一见,在我看来,他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即使昔日如何死党,但到了今天,我再老去约他,不免有些不识趣,甚至可能让人误以为我别有所图。他来约我就不同了。想来想去,怎么一下子便会有这样的芥蒂?本来他发财是他的事情,朋友依然是平等的,那又何必分彼此?莫非我的自重,骨子里是因为自卑在作怪?
许多有钱人家都喜欢摆派头,也有自身的交际范围,大概这也是身份的象征,何时见过亿万富翁与一个低级的吃薪阶级人士称兄道弟?但瑞兴不同,他并不大在乎这种观念。那回,说起他姐夫阿超对他的蜚短流长,他显得有些激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承澜,你说说看,我怎样对待我那些亲戚?他们要来,我随时都欢迎。不是我说什么,你看我周围的人家,来客都是什么身份?只有我这一家,什么样的客人都有。连楼下的看更都知道。”
阿超我也相熟,昨天在中环闹市碰到他,就在街边聊了几句。他笑着问我:“怎么少见你到瑞兴家了?你要常常走动才行呀!他周围那么多人,他又很忙,你不常出现,他怎么会想到你?说真的,只要从他手上漏一滴给我们,那就够我们受用的了。你是他穷时的好朋友,他不会不关照你的。”
我笑。关照我?当然求之不得啦。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