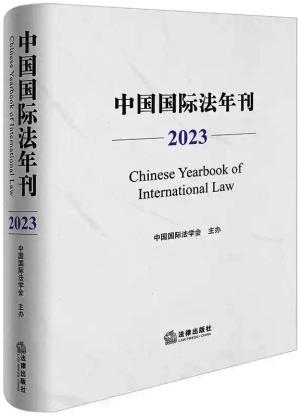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法国汉学经典译丛)
》
售價:NT$
380.0

《
花外集斠箋
》
售價:NT$
704.0

《
有兽焉.8
》
售價:NT$
305.0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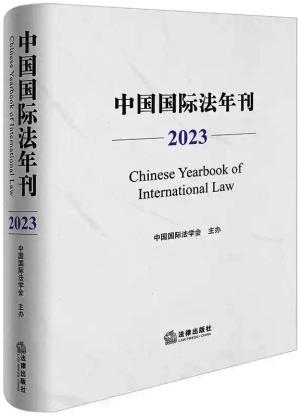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NT$
539.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
》
售價:NT$
760.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 編輯推薦: |
★
儿童若能将他们自己的直觉抒写出来,一定是无上的美。曾经听有人说过,文艺家有个未开拓的世界而又是最奇妙的世界,就是童心。儿童不能自为抒写,文艺家观察其内在的生命而表现之,或者文艺家自己永葆赤子之心,都可以开拓这个最美妙的世界。
—— 叶圣陶
随着近几年《开明国语课本》的大行其道,“民国教育理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民国时期涌现教育先驱的探索和尝试也越来越被人重视,其中叶圣陶是民国教育专家中最知名的一位。叶圣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教育专家,还是一位优秀的童话作家、小说家。他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倡导着儿童教育的理念,不仅创作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燕子》等大量优秀的童话,还写作了一系列儿童教育题材的小说,用这些来呼吁对儿童关爱的重要性,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稻草人》一书集中梳理和展现了叶圣陶用文学作品而儿童进行教育的理念,分“童话”和“小说”两部分,用代表性的情景和人物,向我们探索了儿童教育的可能性,比《开明国语课本》系统性、可读性、趣味性都要强,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不少教育孩子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
★第一次全面而集中地展现中国童话奠基者和著名儿童教育专家的叶圣陶先生
|
| 內容簡介: |
|
随着近几年持续火爆的《开明国语课本》不断受到家长们的追捧,“民国教育理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教育孩子?我们应该用何种理念培养下一代?一个名字又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他就是《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者、儿童教育先驱叶圣陶。叶圣陶可谓我国童话的奠基人,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童话作品,众所周知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燕子》等问世之初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除了童话创作,叶圣陶还有好多优秀的儿童教育小说,用生动的故事,优美的语言展现了自己儿童教育的理念,如反映孩子顽皮天性的《一课》、《义儿》、《新的表》,主张家庭教育和父母关爱重要性的《阿菊》,对落后的育儿方式进行抨击的《祖母的心》、《阿凤》等。这些优秀的儿童教育小说铜叶圣陶的童话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儿童教育专家、儿童文学大家的叶圣陶的画像。
|
| 關於作者: |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
叶圣陶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倪焕之》、《隔膜》、《潘先生在难中》、《火灾》等,奠定了他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其中《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叶圣陶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尤其是童话领域具有突出贡献。他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另一部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也是中国童话史上的重要作品。叶圣陶还撰写过《儿童之观念》等多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作为一名优秀的出版家和教育家,叶圣陶曾亲自编写过当时初等小学的国语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可谓对中国儿童的成长和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
| 目錄:
|
童话
《小白船》
《燕子》
《一粒种子》
《芳儿的梦》
《梧桐子》
《旅行家》
《富翁》
《眼泪》
《跛乞丐》
《稻草人》
《古代英雄的石像》
《书的夜话》
《熊夫人幼稚园》
《含羞草》
小说
《阿菊》
《阿凤》
《一课》
《义儿》
《花园之外》
《祖母的心》
《小蚬的回家》
《马铃瓜》
《老牛的晚年》
《新的表》
《半年》
《寒假的一天》
|
| 內容試閱:
|
一课
上课的钟声叫他随着许多同学走进教室里,这个他是习惯了,不用思虑,纯由两条腿做主宰。他是个活动的孩子,两颗乌黑的眼珠流转不停,表示他在那里不绝地想他爱想的念头。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烟卷的小匣子,里面有几张嫩绿的桑叶,有许多细小而灰白色的蚕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将匣子摆在书桌上,两个膝盖便是他的第二张桌子。他开了匣盖,眼睛极自然地俯视,心魂便随着眼睛加入小蚕的群里,仿佛他也是一条小蚕:他踏在光洁鲜绿的地毯上,尝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的快乐啊!那些同伴极和气的样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种婉娈优美的舞蹈,何等的可亲啊!
许多同学,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里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语,忘形而发出大声的;也有离了座位,起来徘徊眺望的。总之,全室的儿童没有一个不动,没有一个不专注心灵在某一件事。倘若有大绘画家、大音乐家、大文学家,或用彩色,或用声音,或用文字,把他们此刻的心灵表现出来,没有不成绝妙的艺术,而且可以通用一个题目,叫做“动的生命”。然而他哪里觉察环绕他的是这么一种现象,而自己也是动的生命的一个呢?他自己是变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条小蚕。
冷峻的面容,沉重的脚步声,一阵历乱的脚声,触着桌椅声,身躯轻轻地移动声——忽然全归于寂静,这使他由小蚕回复到自己。他看见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来了,才极随便地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完整洁白的理科教科书,摊在书桌上。那个储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现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屉没关上,便极敏捷地将匣子放在里面。这等动作,他有积年的经验,所以绝不会使别人觉察。
他手里不拿什么东西了,他连绵的、深沉的思考却开始了。他预算摘到的嫩桑叶可以供给那些小蚕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去采,同王复一块儿去采。”他立时想起了卢元,他的最亲爱的小友,和王复一样,平时他们三个一同出进、一同玩耍,连一歌一笑都互相应和。他想:“那位陆先生为什么定要卢元买这本英文书?他和我合用一本书,而且考问的时候他都能答出来,那就好了。”
一种又重又高的语音振动着室内的空气,传散开来,“天空的星,分做两种:位置固定,并且能够发光的,叫做恒星;旋转不定,又不能发光的,叫做行星……”
这语音虽然高,送到他的耳朵里便化而为低——距离非常远呢。只有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几个声音“星……恒星……光……行星”他可以听见。他也不想听明白那些,只继续他的沉思。“先生越要他买,他只是答应,略微点一点头,偏偏不买。我也曾劝他:‘你买了罢,省得陆先生天天寻着你发怒。’他也只点一点头。那一天,陆先生的话真使我不懂,什么叫‘没有书求什么学’?什么叫‘不配’?我从没见卢元动过怒,他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却怒了。他的面庞红得像醉汉,发鬓的近旁青筋涨了起来,眼睛里淌下泪来。他挺直了身躯,很响地说:‘我没有书,不配在这里求学,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是要求学,世界上总有一个容许我求学的地方!’当时大家都呆了,陆先生也呆了。”
“……轨道……不会差错……周而复始……地球……”那些语音又轻轻地激动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实行了他的话。第二天他就没来,一连几天没来。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他母亲说他跟了一个亲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肯离开他母亲。”他这么想,回头望卢元的书桌,上面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还有几个纸团儿、几张干枯的小桑叶,是别的同学随手丢在那里的。
他又从干桑叶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来,看了王复,采了桑,畅畅地游玩一会儿,然后到校,大约还不至于烦级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个符号。但是哪里去采呢?乱砖墙旁桑树上的叶小而薄,不好。还是眠羊泾旁的桑叶好。我们一准儿到那里去采。那条眠羊泾真可爱呀!”
“……热的泉源……动植物……生活……没有他……试想……怎样?”方先生讲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庞现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样”两字说得何等地摇曳尽致。停了一会儿,有几个学生发出不经意的游戏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它是我们的大火炉!”语音杂乱,室内的空气微觉激荡,不稳定。
他才四顾室内,知先生在那里发问,就跟着他人随便说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条眠羊泾。“一条小船,在泾上慢慢地划着,这一定是神仙的乐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条没人的小船停泊在那里,我们跳上船去,撑动篙子,碧绿的两岸就摇摇地后移动,我们都拍手欢呼。我看见船舷旁一群小鱼钻来钻去,活动得像梭子一船,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鱼儿不知哪里去了。卢元也学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溅得我满脸的水。这个引大家都笑起来,说我是个冒雨的失败的渔夫。最不幸的是在这个当儿,看见级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来!他赶到我们船旁,勉强露出笑容,叫我们好好儿上岸罢。我们全身的,从头发以至脚趾里的兴致都消散了,就移船近岸,一个一个跨上去。不好了!我们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变了。他责备我们不该把生命看得这么轻;又责备我们不懂危险,竟和危险去亲近。我们……”
“……北极……南极……轴……”梦幻似的声音,有时他约略听见。忽然有繁杂的细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看许多同学都望着右面的窗,轻轻地指点告语。他跟着他们望去,见一个白的蝴蝶飞舞窗外,两翅鼓动得极快,全身几乎成为圆形。一会儿,那蝴蝶扑到玻璃上,似乎要飞进来的样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体向后倒退,还落了些翅上的白鳞粉。他就想:“那蝴蝶飞不进来了!这一间宽大冷静的屋子里,倘若放许多蝴蝶进来,白的、黄的、斑斓的都有,飞满一屋,倒也好玩,坐在这里才觉得有趣。我们何不开了窗放它进来。”他这么想,嘴里不知不觉地说出“开窗!”两个字来。就有几个同学和他唱同调,也极自然地吐露出“开窗!”两个字。
方先生梦幻似的声音忽然全灭,严厉的面容对着全室的学生,居然聚集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放弃了那蝴蝶。方先生才斥责道:“一个蝴蝶,有什么好看!让它在那里飞就是了。我们且讲那经度……距离……多少度。”
以下的话,他又听不清楚了。他俯首假作看书,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哪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时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道哪里去了?倘若飞到小桥旁的田里,那里有刚开的深紫的豆花,发出清美的香气,可以陪伴它在风里飞舞。它倘若沿着眠羊泾再往前飞,一棵临溪的杨树下正开着一丛野蔷薇,在那里可以得到甘甜的蜜。不知道它还回到这里来望我吗?”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归来的蝴蝶。梦幻似的声音,一室内的人物,于他都无所觉。时间的脚步本来是沉默的,不断如流地过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辨知。
窗外的树经风力吹着,似乎点头、似乎招手地舞动,那种鲜绿的舞衣、优美的姿势,竟转移了他心的深处的相思。那些树还似乎正唱一种甜美的催眠歌,使他全身软软的,感到不可说的舒适。他更听得小鸟复音的合唱,蜂儿沉着而低微的祈祷。忽然一种怀疑——人类普遍的、玄秘的怀疑——侵入他的心里,“空气传声音,先生讲过了,但是声音是什么?空气传了声音来,我的耳朵又何以能听见?”
他便想到一个大玻璃球,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钟。“陈列室里那个东西,先生说是试验空气传声的道理的:用抽气机把里面的空气抽去了,即将球摇动,使钟杵动荡,也不会听见小钟的声音。不知道可真是这样?抽气机我也看见,两片圆玻璃装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曾见它怎样抽空气。先生总对我们说:‘一切仪器不要将手去触着,只许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耳朵,看出声音的道理来?”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听窗外自然的音乐,那种醉心的快感,决不是平时听到风琴发出滞重单调的声音的时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常常走到田野里领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纠结得很牢固了,那人为的风琴哪有这等吸引力去解开他们的纠结呢?
“……”他没有一切思虑,情绪……他的境界不可说。
室内动的生命重又表现出外显的活动来,豪放快活的歌声告诉他已退了课。他急急开抽屉,取出那小匣子来,看他的伴侣。小蚕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然和自然牢固地纠结着。
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义儿
义儿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纸和笔了:不论是练习英文的富士纸,印画地图的拷贝纸,写大楷的八都纸,乃至一张撕下的日历,一页剩余的文格;不论是钢笔、蜡笔、毛笔、铅笔,乃至课室内用残的颜色粉笔,一到他手里,他就如获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笔杆,左手五指张开,按着铺在桌上的纸,描绘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鸟。他的头总是侧着,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舌尖露出在上下唇之间,似乎要禁止呼吸的样子。他能画成侧形的鲤鱼,俯视形的菊花,从正面几笔,或加上一部分。有时加得高兴了,鲤鱼的鳞片都给画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尽量加多,以致整朵花凑不成个圆形;从烟囱喷出的烟越涂越多,所占纸面比屋子还大。他看看这不像一幅画了,就在上面打一个大“×”,或者撕成两半,叠起来再撕,如是屡屡,以至于粉碎。他留着的画稿都折得很小很小,积存在一个旧的布书包里。
他当然同别的孩子一样,喜欢奔跑,喜欢无意识地叫喊,喜欢看不经见
的东西,喜欢附和着人家胡闹。但是他不喜欢学校里的功课。他在课室里难得静心,除了他觉得先生演讲的态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语声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时候。若是被考问时,他总能够回答,可是只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懒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几位先生的心里成立了。就是那位图画先生,也说他不要好,只知道乱涂,画的简直不成东西。这是的确的,他逢到画图的功课,随随便便临了黑板上先生画的一幅画,缴给先生就算了,从没用过一点儿心,希望它好。
他的父亲早死了,母亲养护着他,总希望他背书像流水一般的快,更读通一点儿英文,将来好成家立业。但是实际所得的只是失望和悲伤。义儿今年十二岁了,高等小学的二年级生了,赞美他的声息一丝也听不到,却时时听得些愚笨、懒惰、欢喜捣乱等对于他的考语。她很相信这些考语是确实的,不然,何以义儿回了家总不肯自己拿出书来读,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总是一字一顿地读,从不曾熟诵如流水呢?他只喜欢捉虫子,钓鱼儿,涂些怕人的东西在纸上,这不是捣乱吗?而且有什么用处呢?她想到这等情形时,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旧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现在给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对义儿这么说。义儿听了,也不辨这句话何等伤心,只觉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脑子里。因此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将积蓄着的母亲给他的钱,买了两匣纸烟匣内的画片儿;有两次他跑到河边,蹲在露出河面的石头上钓鱼;再有几次,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亲的恼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说伤心的话绝对没有效果,但是总希望得到一点儿效果,便换了个似乎较有把握的办法,就是打。她的细瘦惨白的手握着一把量衣的尺,颤颤地在他身上乱抽,因为怨恨极了,用了好大的力气。可是他一声都不响,沉静的面孔,时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断断续续地问:“可知道你的错处吗?下次还敢这样吗?”他只当没有这回事,并且偏转他的头。她没有法子了,余怒里却萌生一丝智慧,就说:“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饶恕了你这一次。”这时候他的头或者微微一摇,或者轻轻一点,或者只有摇或点的意思,都被认为悔过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咽下去了。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义儿是个难得教好的孩子,想起的时候就默默流泪,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更伤悼丈夫的早死。
母亲终究是母亲,虽然觉得今后的失望是注定的了。义儿上学校去的时候,她总要问他穿的衣服够不够,肚子吃饱了没有;有时买了一点儿吃的东西,或是人家送了什么饼饵糖果来,她总把最好的留着给他吃。他是难得教好的,他是引起她的失望和悲伤的,她却全然不想到了。
义儿还有两位叔叔,也是时常斥责他的。不知为什么,他对于那位三叔特别害怕,一看见周身就不自由起来,好像被束缚住的样子。对于他的劣迹,三叔发现得最少,因为三叔看见他时,他总是很安定、很规矩的。人家发现了义儿的错处,就去告诉三叔,靠三叔来达到训诫他的目的——就是义儿的母亲也常常如此。三叔训诫义儿的时候,义儿的面孔就红了,不敢现出沉静的神态了,头也不敢转了。三叔教他以后不要再这个样子,他就很可怜地答应一声“知道了”。胜利每每操在三叔手里,三叔就发明了处置义儿的秘诀。三叔向义儿的母亲和旁人这么说,“处置义儿惟一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将好颜脸对他。我就这样做,所以他还能听我的话。”义儿的母亲对于这句话非常信服,可是她熬不住,不能不问暖问饱,留最好的东西给他吃。
一张山水画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绿的丛树、突兀的山石、蓝碧的云天、纡曲曳白的迴泉,义儿从一个同学手里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宛如得了宝贝,心想临绘一张。不干不净的颜色盒,是他每天携带的,他取了出来,立刻开始工作。一张桌子不过一方尺有余的面积,实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砚台、颜色盒、明信片、画图纸、两条手臂,等等东西。然而一个课室里要布置五六十张桌子,预备五六十个学生做功课呢,怎能顾得各人过分的安适?好在义儿已经习惯了,局促的小天地里他自能优游如意。此刻他将墨水瓶摆在砚台上面,明信片倚靠着瓶口,就仿佛帖架托着画帖。左手拿着颜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
平铺画纸了。他画得非常专心,竟忘了周围的和自己的一切,没有思虑、没有情绪,只有脑和手联合的、简单的运动,就是作画。同学的喧声和沉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过他旁边的暂时止步而看他一看,对于他只起很淡很淡的感觉,差不多春夜的梦一般,迷离而杳渺。功课又开始了,同学都上了他们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进了课室了,他周围的空气全变,而他如无所觉,还是临他的画。
竖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加上义儿那坐着作画的姿势,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点儿恼怒:“他在那里作画,连课本都不拿出来,分明不愿意上我的功课!”他这么想,洪大而严正的呵斥声就从他喉间涌出:“沈义,你做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的课本哪里去了?你不爱上我的功课,尽管出去,你在课室外画一辈子的图我不来管你,在我的课室里却容不得你这样懒惰捣乱的学生!”同学们听了,有的望着义儿,看他怎么下场;有的故意看书,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向着英文先生红涨的怒容只是微笑。课室内暂时静默。
义儿被唤醒了,还有几株小树没画上,他感觉不舒快,像睡眠未足的样子。他知道不能再画了,便将明信片、画幅、颜色盒放入抽屉里,顺便拣出读本来,慢慢地翻到将要诵习的一课。他并不看先生一眼,脸容紧张,现出懊丧的神态。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说过了,若是不愿意,就不必勉强上我的课!你恼怒什么?难道我错怪了你?上课不拿出课本来,是不是懒惰?因你而妨害同学的学习,是不是捣乱?我错怪了你吗?”
“是的,没有错怪,”义儿随口地说,却含有冷峻的意味。“现在课本已拿出来了,请教下去罢,时间去得快呢。”同学们不料义儿有这样英雄的气概,听着就大表同情,齐发出胜利的笑声来。刚才的静默的反响就是此刻的骚动了,室内不仅是笑声,许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桌椅被震摇而发出的叽叽格格的声音,英文先生把书扔在桌上并且击桌的声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觉得这太难堪,非叫义儿立刻退出课室,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威严。他就很决断地说:“你竟敢同我斗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课!”其实英文先生并没仔细地想,说这句话很危险的,假若义儿不听话,不立刻退出课室,岂不更损了威严?果然,义儿听到驱逐令,只将身体坐后一点儿,以为这样就非常稳固了,——他绝对没有出去的意思。同学们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败将怎样挽救,义儿的抵抗将怎样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上演的戏文。他们望望先生,又望望义儿,身躯频频转侧,还轻轻地有所议论,室内的空气更显得不稳定。
英文先生脸已红了,他斜睨义儿,见他不动,又见许多学生都好像露出讥讽的颜色。这是何等的侮辱啊!他的血管涨得粗了,头脑涔涔地响了;一种不可名的力驱策着他奔下讲台,一把抓住义儿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来。义儿有桌子做保障,他两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动;他的脸色微青,坚毅的神色仿佛勇士拒敌的样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只将义儿的左臂震摇,桌子便移动了位置,并且发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齿酸麻之感的声音。义儿终于支持不住,半个身体已离开桌子了。桌子受压不平均,忽然向左倾侧。一霎的想念在英文先生的脑际涌现,他想桌子倒时一定发出重大的声音,这似乎不像个样子。他就放了手,义儿的身躯重复移正,桌子便稳定了。于是课室内的战事暂时休止。
同学们观战,早已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有的奋一点儿无所着力的力,同情于义儿的拒敌;有的只觉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长一刻;有的觉得这是个机会,便取出心爱的玩意儿来玩弄,或是谈有趣味的话。总之,在课室之内,上功课的事是没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惊奇的目光又集中在先生脸上。
英文先生把手放了,忽然觉得这个动作太没意思,况且许多学生正看着自己的脸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觉包围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围诸人。他只喃喃地说:“你不出去也好,我总不承认你留在这里。刚才的事退了课再同你讲。现在且上功课,你不爱上,同学们要上呢。”他很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讲台。
学校里从此起风波了:英文先生将义儿的事告诉了级任先生,说以后一定不要义儿上他的课。级任先生口里虽不说什么,心里却异常踌躇,不要他上课就是不肯教他,哪有学校里不肯教学生之理?并且在英文课的时间叫他做什么呢?若是还叫他上英文课,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么顾全?说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动怒,又生出另外的枝节来。级任先生宛如受了过大的激刺,觉得满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诉了义儿的三叔,他们俩本是天天在茶馆里会见的茶友。许多同学呢,他们将义儿的事作为新闻,一散课就告诉别级的同学,像讲述踢球的胜利那么有味,——于是别级的同学流动不居的心里又换了个新的对象了。他们怀着好奇的心在那里观望:课已退了,英文先生将怎样办理这一件事呢?义儿仍旧取出抽屉里的东西,完成他的画幅,可是心里总觉不安定,有点儿惊怯,以后将有什么事临头,模糊而不能预料。一块小石的投掷可以激动全世界的水,虽然我们不尽能看见波纹: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三叔听了级任先生的诉说,当然痛恨义儿的顽劣,一方面想法解决这件事。他说:“由我训诫他,已经不知几回了!当着面他总是很能领受的态度,自称情愿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个过失就来了。他母亲打他骂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课,更没有什么用处,当时他就不肯说一个改字。我们须得换一个方法才行。”
“是呀,须得换一个方法,”级任先生连连点着头说,“他在课室内这样捣乱,非但同学们和授课的先生受他的累,连我也觉得难以措置。总要使他知所畏惧,以后不敢再这样,才得大家安静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赔罪。为他的话的威信起见,不妨令义儿暂时不上英文课。到哪一天,说‘你确能改过,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后再叫他上课。”
“你这办法,解除了我的为难了!”级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压在他肩上的无形的重负似乎轻了好多。“就这么办罢。可是怎能使你家义儿确能改过呢?”
三叔轻轻击一下桌子,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然后说:“就是你所说的那句话,要他知所畏惧。我想他这么浮动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触而来的。若是叫他住在学校里,和外间一切隔离,过严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动的心情渐渐定了,一方面尝到严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觉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么坏的行为做出来吧。”
“这确是一个办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间里好了。但是,你先要给他一个暗示,重重地训斥他一顿,使他没搬进学校就觉得懔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都照三叔的计划进行,义儿搬进学校里住了。他本来很羡慕住校的同学。他常常想晚上的学校里不知怎么个情形,课室里点了灯,许多同学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吗?可是他并不曾向母亲要求过要在校内寄宿,因为他不能设想这事的可能。现在母亲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里,实在是梦想不到的。这就是他往日的学校呀,但在他觉得新鲜。晚饭的铃声,课室里点了火的煤油灯,住校的同学的随意谈笑,夜色笼罩下的操场上的赛跑,都是他从来不曾经历的。他听着、看着、谈着、玩着,恍恍惚惚如在梦里,悠久而又变化多端。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张《洛川神女之图》,到末了画那条衣带,墨色沸了开来,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觉舒适。母亲的唠叨现在是非常之远,好似在她怀抱里的时候的事;画完一幅画,居然没听见“又在那里涂怕人的东西了”的责骂。更可希望的,一个同学约他明天一早去捉栖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哪里去取竹竿,怎么涂上了膏,预备怎样一个笼子,怎样伸手……渐渐地模糊,不能想了。
两三天内,级任先生暗里观察,希望看见义儿愁苦怯惧的面容。可是事实竟相反,义儿还是往日的义儿,而且更高兴了一点儿。
当级任先生到茶馆时,三叔就问他:“义儿可又闹了什么事?”
“暂时没有。”级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态,语言间带着冷然的调子。
“他住在校内觉得怕吗?”
“怕?”级任先生斜睨着三叔,“哪有这回事!他还是往日的模样,而且更为高兴。”
“他竟不怕吗?”三叔怅然愕视。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