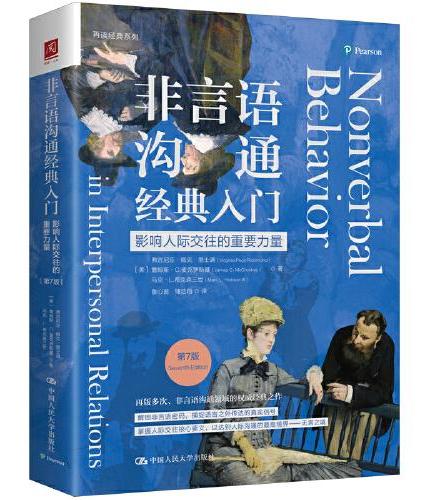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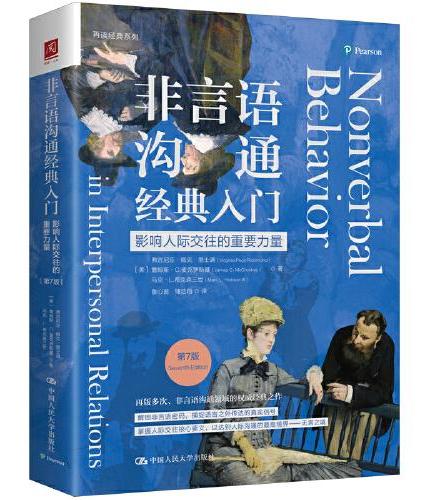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0.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NT$
4998.0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NT$
254.0

《
自由,不是放纵
》
售價:NT$
250.0

《
甲骨文丛书·消逝的光明:欧洲国际史,1919—1933年(套装全2册)
》
售價:NT$
1265.0

《
剑桥日本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918.0
|
| 編輯推薦: |
1. 孟京辉 史航 牟森 “愿效犬马之劳”的大师
2. 以极简之笔追索母亲的悲剧人生,她只是被时代和社会吞噬的无数人中的一个
3. 作者是当代德语文学大师,屡获毕希纳奖、卡夫卡奖等重要文学奖。
4.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说,汉德克是“活着的经典”,比她更有资格获奖。
5. 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斯评价汉德克:彼得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当代作家中,唯有他的作品,让我感到最亲近,最理解,最爱读。
6. 戏剧导演孟京辉一直将汉德克引为偶像,二十年前其代表作《我爱XXX》正是深受汉德克《骂观众》的影响。
|
| 內容簡介: |
《无欲的悲歌》本书由两部小说组成,包括《无欲的悲歌》和《大黄蜂》。
《无欲的悲歌》是以一位51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
作者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
|
| 關於作者: |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
),奥地利著名先锋剧作家,小说家。他创作的《卡斯帕》,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相提并论,被誉为创造“说话剧”与反语言规训的大师。他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重现》《无欲的悲歌》等渗透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他用最简单的笔调状出具有丰富内蕴的作品。汉德克是20世纪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几位作家之一,被称为“活着的经典”,他于1973年获毕希纳文学奖,2009年获弗朗茨?卡夫卡奖。在文学创作之外,汉德克参与编剧的《柏林苍穹下》成为电影史经典,他本人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电影《左撇子女人》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主编简介
韩瑞祥,陕西礼泉人,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年来主要从事德语文学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40余篇、文学译著13部、教材1部,主编文学名著3套。
|
| 內容試閱:
|
克恩滕州《人民报》周日版的“综合新闻”一栏里有这样一条消息:“星期五深夜,A 地(G 县)一名51
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个星期了,我想趁着葬礼时那股强烈的想要写写她的欲望还没有变回当初接到自杀消息时的麻木无语让自己开始工作。没错,是让自己开始工作,因为写写母亲的欲望尽管有的时候突如其来,但同时又极飘忽,以至于工作时必须很努力,才不会随兴所至地用打字机在纸上不断敲击同一个字母。单纯的运动疗法对我没有用处,只能让我更加消极和漠然,否则我也完全可以出门去,而且在路上,在旅途中,头脑一片空白地打盹或者无所事事也不会太让人难以忍受。
几个星期以来,我比平常更易怒,杂乱、寒冷或者寂静更是能让我跟人连话也说不得,并且只要看到地板上有细毛或面包屑就弯腰去捡。想到母亲自杀的事,我的感官就会突然变得木然,有时就连我自己都诧异手里拿的东西竟没有早就掉落。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渴望那样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麻木的感觉不再,头脑一片清明。那是能让我释然的惊骇:终于不再无聊,身体任凭摆布,没有费力地疏远,时间的流逝也不再让我痛苦。
在这样的时候,最让人恼火的似乎莫过于旁人的关心,用一个眼神甚至一句话。我要么马上移开目光,要么截断别人的话头,因为我需要的感觉是:自己正经历的这些是不能理解、无法言语的,只有如此,方能让人感到那惊骇是有意义的、真实的,一旦有人提起,就马上会感到无趣,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重归空虚。然而我偶尔还是会毫无来由地向别人说起母亲自杀的事,若他们胆敢评论,我又气恼,情愿他们马上岔开话题,或是嘲弄我,不管因为什么。
就像在上一部的“007”电影里,有人问起邦德刚才被他从楼梯扶手上扔下的那个对手是不是死了,他说:“但愿如此吧!”当时我就忍不住轻松地笑了起来。关于死和亡故的玩笑非但根本不会使我不快,甚至能让我感到愉悦。
惊恐的瞬间总是很短暂,更多的是不真实的感觉,一切都在瞬间过后重新隐匿,如果这时旁边有人在,我马上就会更加把心思用在对方身上,仿佛刚才冒犯了他们一样。
而且自从动笔,这样的状态,也许恰恰是因为我想要尽量准确地描述它们,结果它们反倒离我而去了,消失了。因为要描述,我开始了对它们的回忆,如同回忆生命中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艰难的回忆和表述弄得我无暇他顾,竟使我对过去几个星期里那些短暂的白日梦境产生了距离感。我之前会不时出现的“状态”是:日复一日的那些想法只是一些不断机械反复的、存在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原初想法而已。如今它们四散,意识因为一下子变得空空如也而疼痛。
现在这些都结束了,我不再处于这种状态。写作的时候,总是无法避免地写到从前,写起已经经历过的那些事,至少写作时是如此。我做的工作是文学的,它显现于表面并且具体成一台回忆和表达的机器,不如此又能怎样。而我写母亲的故事,一则是认为自己对她以及她如何走上死亡之路比那些不相干的记者知道得更多,虽然后者借助宗教的、个体心理学的或者社会学的释梦模式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释这个有趣的自杀事件;再者就是为着自己,因为有事情可做,我就能振作起来;最后是因为我恰恰和任何不相干的记者一样,也想把自愿死亡这事看作一个案例。
当然,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过是随手拈来,可以用同样是随手拈来的另一些解释代替。只是一些彻底失语的瞬间和想要表述这些瞬间的欲望而已,与向来写作的动机没两样。
去参加葬礼时,我在母亲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编号432的邮局收据。星期五晚上,她在回家服药之前还用挂号信往法兰克福寄了一份遗嘱的副本。(又是为什么要用快件呢?)我星期一就在同一家邮局打电话,那是她死后两天半,我看到放在邮局工作人员面前的一卷黄色的挂号信标签:这期间有九封挂号信寄出,现在显示的下一个号码是442,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想要把这些事讲出来的愿望让我真正开怀。那天是多么晴朗;雪;我们吃的是肝泥丸子汤。“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如果这样开讲的话,一切都会像是杜撰出来的,我不想胁迫听众或读者对我个人表示同情,只是要给他们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的母亲五十多年前就出生在她后来去世的地方。那个地方但凡有点用的东西,当时都归教堂或者贵族地主所有,其中一部分租给百姓,这些人主要是工匠或者下层农民。贫困的状况之普遍,以至于少量占有土地的情况都还很少见。事实上,当时依然维持着1848
年以前的状况,只不过农奴制度正式取消了。我的外祖父——他还健在,如今已经八十六岁了——是个木工,此外还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种了几片地,还有草场,每年交一次地租。他祖上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当时大多数下层农民的孩子一样是私生子。这种人即便早已经性成熟,却是既没钱结婚,也没有地方过婚姻生活。他的母亲至少是个家境相当殷实的农家的女儿,他的父亲当时在这家当长工。这个父亲对他而言不再只是“制造者”。不管怎样,他的母亲借此得到了购置一小片田产的钱。
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洗礼证明填得残缺不全,在他人屋檐下出生又死去,身后几乎没有什么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从外祖父开始,成长的环境才终于让人真正有家的感觉,不再是通过每天的劳动勉强换来的栖身之所。为了捍卫西方世界的基本经济准则,一家报纸不久前在经济专栏内称财产是物化的自由。对于外祖父这样,历经数代没有财产因而也没有权势的家族里出现的首批有产者(至少是在不动产方面)而言,这种说法倒是有其道理:意识到自己拥有财产而产生的自由感,让人在世世代代任人摆布之后突然第一次有了意愿,那就是要更加自由。这其实只是说:扩大自己的财产,当然鉴于祖父当时所处的状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财产却少得要倾尽心力才能勉强保住,所以抱负远大的小业主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积攒。
于是,我的外祖父就一直积攒,直到在二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丢掉了所有积蓄。接着他又重新开始积攒,不是把省下的钱堆积在一处就算了,而是采用了压抑个人欲求的方式,同时还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而他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反正是从一落地就连做梦也不曾想过要有什么不一样。
他继续积攒,要一直积攒到子女们需要资金结婚或者工作为止,像把积蓄提前用在子女,特别是女儿们的教育上的这种念头,他则顺利成章地想都没想过。就连在他的儿子们身上,处处寄人篱下做穷光蛋的噩梦依然根深蒂固。儿子中的一个在中学里得到了免费学习的机会(这更多的是因为巧合而不是提前计划好的),不过才几天,他就因为忍受不了陌生的环境,半夜里步行四十公里从州府走回了家。到达自家屋前,正好是星期六,那通常是打扫房舍的日子,他二话不说就动手扫起了院子,晨曦中,他的扫帚发出的声音足以说明一切了。据说他当了木匠后倒是很勤勉,而且很满足。
他和他的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就丢了性命。这期间,外祖父继续积攒,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失业大潮中再次失去了所有积蓄。他积攒,这就是说:他不喝酒,不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惟一允许自己参与的娱乐就是星期天的牌局,就算是打牌时赢的钱(他牌打得非常冷静,这让他几乎永远是赢家)也要攒起来,他充其量会从里面拈出一小枚铜子儿给孩子们。战后他又开始积攒,直到今天成了拿国家退休金的人,他也没有停下来过。
那个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手下毕竟雇着二十个工人,用不着再积攒了。他开始投资,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喝酒、娱乐,这甚至是他分内的事。和自己沉默了一辈子、什么都不敢享受的父亲不同,他至少凭这个找到了一种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只是他作为乡镇代表,并且代表一个痴迷地用伟大的过去谈论伟大的将来、忘却现实的小党派时才用得到。
身为一个女人,出生在这种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是致命的,当然这件事也可以让人宽心地来看待:至少不用对未来感到恐惧。节日时在教堂前集市上给人看相的女人从来只给男孩儿看手相占卜未来,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毫无机会,一切都注定了:男人小打小闹的调情,吃吃地一笑,短暂的目瞪口呆,然后是第一次陌生和克制的表情,随之又开始忙里忙外,一个个孩子出世,忙完厨房的活儿后再跟家人待一会儿,从一开始说的话就没人听,自己也越来越不听人说话,自言自语,然后是腿脚的不灵便,静脉曲张,只剩睡觉时的一声嘟囔,下身的癌症,最后,注定的一切随着死亡而圆满。就连当地女孩儿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也是这样:累了
倦了 病了 病重了死了。
我母亲是五个孩子里的倒数第二个。她在学校里被认为是个聪明孩子,老师们给她最好的成绩,尤其欣赏她工整的书写。随后学也就上完了。学习不过是小孩儿的游戏而已。等完成了义务教育,年龄大了,也就没有必要了。女人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家里演习将来的家务事。
没有恐惧,除了对黑暗和暴风雨本能的害怕;只有冷与热、潮湿与干燥、快乐与不快的交替。
时光就伴随着教堂的节日,伴随着偷偷进舞池而挨耳光,伴随着对兄弟的羡慕和参加合唱团演唱的愉快流逝。至于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就都不清楚了。除了教区的星期日报之外,报纸是不看的,就算是在那份报里能够看到的也只有小说连载而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