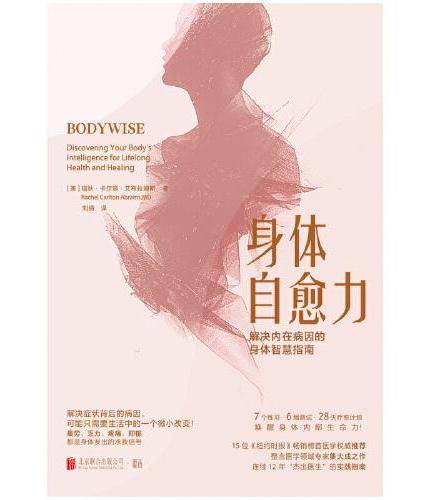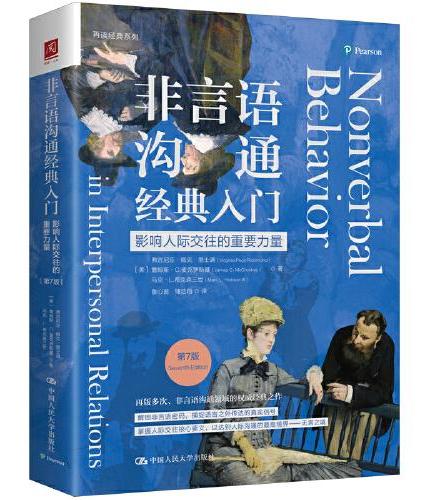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NT$
214.0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0.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NT$
4998.0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NT$
254.0
《
自由,不是放纵
》 售價:NT$
250.0
編輯推薦:
虹影的作品总像重磅炸弹引发种种议论。在虚构和真实生活之间,所有的议论是因为虹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争议——非婚女身份、私生女的身份。私生女和别人不同,因为私生女不是婚姻的结果,而是绝对的爱情结晶,对情与性到了狂热的程度。这也注定了虹影作品的独特气质。
內容簡介:
“有一本书写着一个人的过去,那太完美的过去,总难与今生相连。我在茫茫的夜里,把一个个梦留给那本书,闭上眼睛,想象我的身影如猫一样在夜里来回走,仿佛在象棋格里穿越,没有惊动任何人。”——虹影在《53种离别》前写道。
關於作者:
虹影,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等。现居北京。
目錄
之 一 忠县
內容試閱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