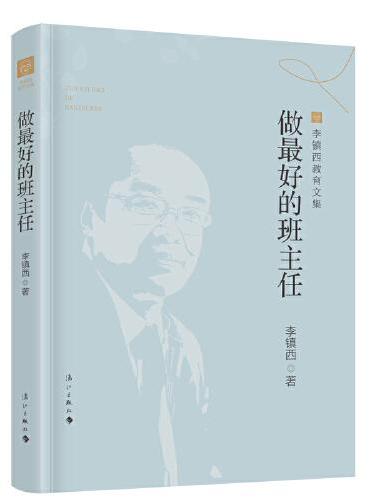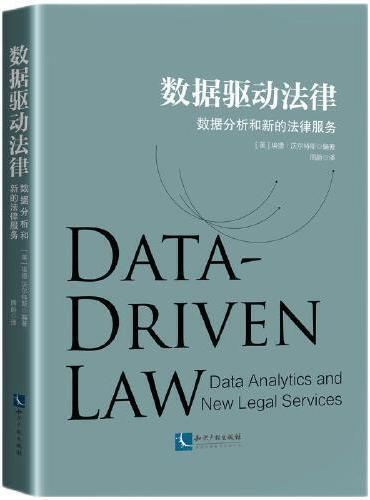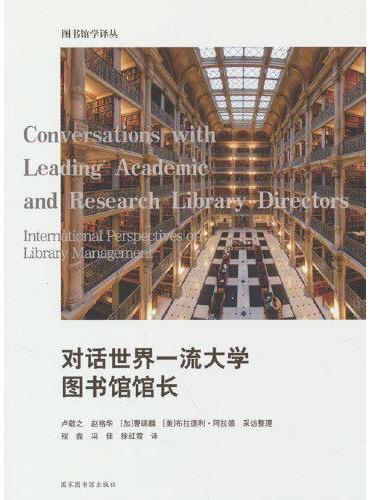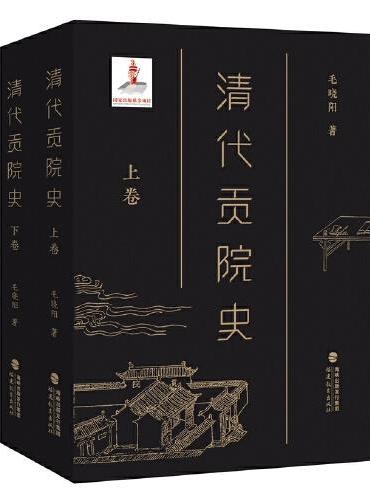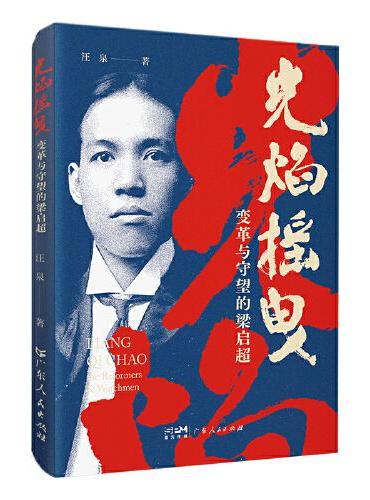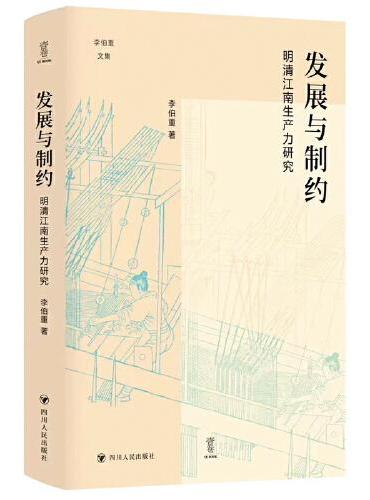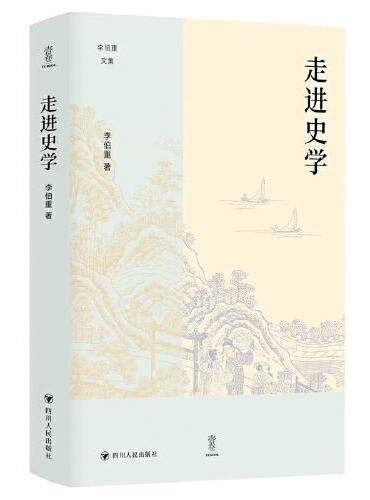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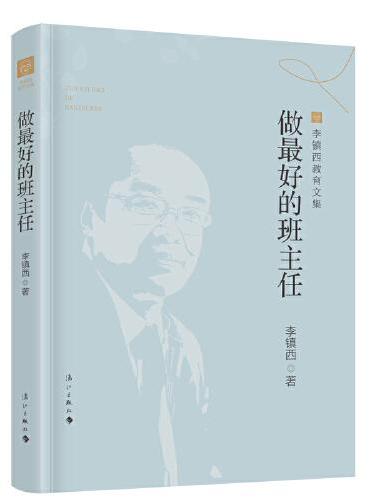
《
做最好的班主任(李镇西教育文集版)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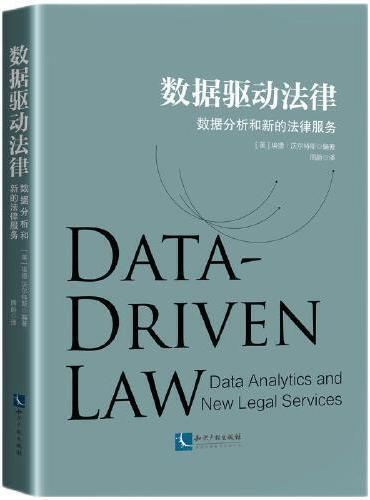
《
数据驱动法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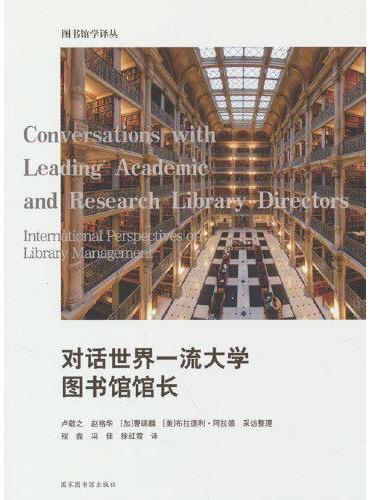
《
对话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馆长
》
售價:NT$
995.0

《
揭秘立体翻翻书--我们的国宝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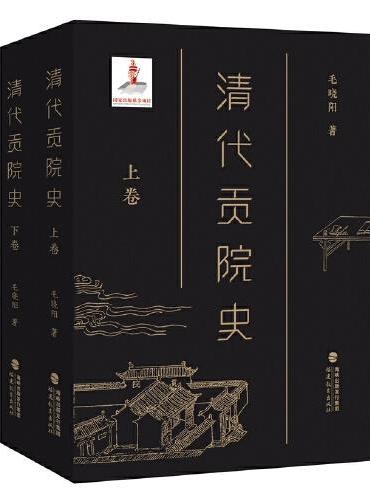
《
清代贡院史
》
售價:NT$
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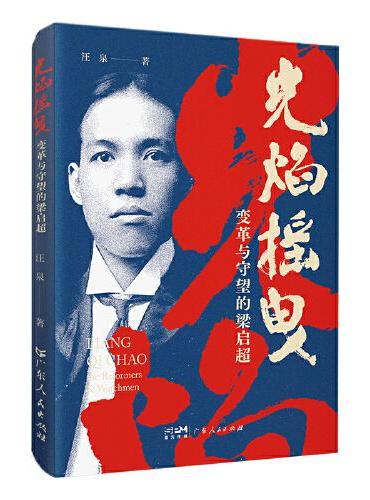
《
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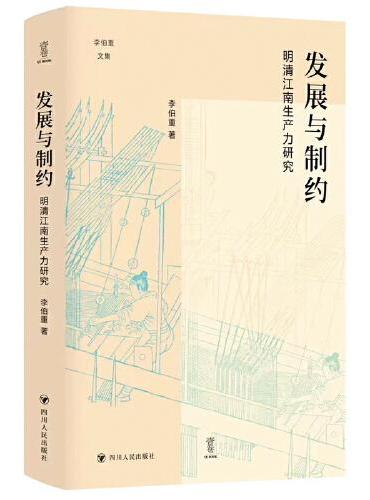
《
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壹卷李伯重文集:江南水乡,经济兴衰,一本书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
》
售價:NT$
4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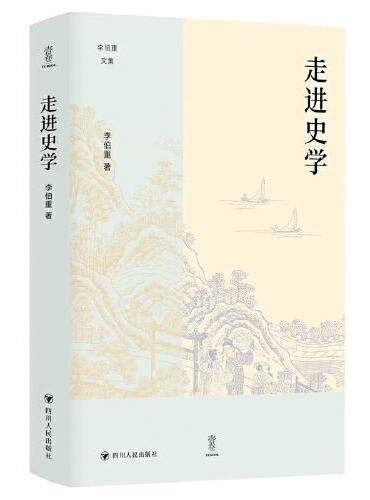
《
走进史学(壹卷李伯重文集:李伯重先生的学术印记与时代见证)
》
售價:NT$
360.0
|
| 內容簡介: |
《菩萨蛮》(长篇小说)是一个发生在南方一个平民家中的故事,是一个传统的一家人的故事,只是所有的叙述通过亡父华金斗的幽灵来完成。故事发生时间: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叙述人华金斗是个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的幽灵,这个人已经死去,做一个飘荡的幽灵,不用吃饭,省了口粮,不用穿衣,省了布线,这一点他很满意,但他既然已经死去,就管不了家里人的闲事,这使他在天上仍然怒火满腔。死人不愿安息,注定是一个痛苦而孤独的幽灵。大姑是活着的,如此她就要照顾哥嫂遗留下来的五个子女。大姑对孩子们的爱是一锅粘稠的粥,看不见清晰的内容,但正是这种粥型之爱喂饱了孩子们,使他们长大成人,大姑在漫长的岁月中顽强地责备整个世界,呵护华家的孩子,因为太忙太累她来不及思考,所以她并不知道她的孤独,在我看来,大姑这样的女性,不懂孤独便是她的孤独。说到华家的孩子们,除了二女儿新梅,几乎个个让华金斗很铁不成钢,可是新梅却让一个浑小子骗大了肚子,红颜早逝,剩下的三女一男、他们从小就跟父亲的亡灵对着干,虽然结结巴巴地长大成了人,但又算什么玩意儿?尤其是华家的唯一的儿子,他竟然不能为华家传继血脉,整天跟男人在一起鬼混。用港台流行的说法,他是一个可恶的“基佬”。
我写了一个痛哭的幽灵,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此磨难,后来他就不想管人间的什么闲事了,他想接去了地狱,把更大的孤独留给别人,留给我,留给我们大家。我一直想在一部小说中尽情地描摹我所目睹过的一种平民生活,我一直为那种生活中人所展示的质量唏嘘感叹,我一直觉得有一类人将苦难和不幸看作他们的命运,就是这些人且爱且恨地生活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上,他们唾弃旁人,也被旁人唾弃,我一直想表现这一种孤独,是平民的孤独,不是哲学家或者其它人的孤独。
因此我写了《菩萨蛮》。
|
| 關於作者: |
|
苏童,1963年1月出生于苏州市。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苏童文集》等。主要作品有《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米》、《蛇为什么会飞》等。
|
| 內容試閱:
|
秋天的阳光照耀着我的家,阳光在中午时分还是暖热的黄色,到了午后它们看上去几乎就是白色的了。阳光是活的,它们像一群鱼,从窗外的河水里纷纷跳到我家的窗台上、门板上,跳到孩子们的床上,跳到脸盆里,跳到锅里。多少次我在家中无人的时候降临,看见的就是那些像鱼一样游动的阳光。午后两点,有线广播里准时响起说书艺人自说自话的声音,说来说去就是什么包公呀,李娘娘呀,陈琳呀,寇珠呀,说来说去说的都是古人的事,还不一定是真的。我是不信那些东西的,可大姑她不一样,她坐在广播下面拣蚕豆,恨不得把两只耳朵变成两只嘴吞下那些个故事。她听得泪汪汪的,哪儿分得清好蚕豆和坏蚕豆呢,我看见她拣了半天,最后好蚕豆和坏蚕豆全都混到一起去了。我看见她为那个忠心的宫女寇珠哭红了眼睛,她竖起巴掌拍打着墙,口口声声地说,寇珠,寇珠,你这是何苦呀,寇珠,寇珠,你太可怜了。
那只有线广播挂在西墙上,西墙是我家所有墙壁中最平整最干净的墙面,因此我们家该挂的东西全挂在西墙上。西墙上挂着我双亲的画像,可怜我的双亲大人,他们辛苦一辈子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是我请了中学里的美术老师替他们画了像,也不知道那老师是怎么回事;他不听我的描绘,只顾把他们画得浓眉大眼的,看上去石点也不像我爹我娘,倒是很像样板戏里的两个英雄人物。西墙上挂着我和凤凰的所有奖状,还有孩子们的奖状。我们夫妻的当然都是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什么的,孩子们中间就数新兰得的奖状多,她当学生每年不是三好就是五好,她当知识青年不是个积极分子就是青年标兵,你看看我的儿女们给我带回了多少奖状!差不多快把半面墙盖住了,那都是荣誉的标志,那些奖状都是向看不起我华家的人脸上打去的耳光呀。
只有儿子不争气,你别指望在西墙上找到他的名字。我记得他上一年级的时候曾经带回来一张奖状,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奖状往西墙上贴,老师就追来了,老师对我们说,刚刚有同学报告说华独虎在他课桌洞里小便,既然有这种行为,那奖状就只好收回了。我问老师,是哪个孩子打这种小报告的,我觉得我这句话问得也没什么大错,可那个女老师却大惊小怪地瞪着我,好像我喊了一句反动口号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女老师的表情呢,她瞪着我说,你这种家长,真少见!
你可能已经猜到我在西墙上还会看到什么。我在西墙上还
看见了我自己,那是摄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我的脸上也是一种大跃进的乐观豪迈的笑容。那时候我还只有三十来岁,那时候还没有新竹新菊,还没有独虎呢,少三张嘴吃饭,人就容易笑一些。我在西墙上看见了凤凰,照片上的凤凰比我更年轻,那张照片是她生新梅那年在昌隆照相馆照的,摄影师有一套,他把凤凰照得像桃花一样美丽而灿烂,比电影明星还美呀。那时候的凤凰哪儿像后来那样整天愁眉苦脸呢,记得我们小夫妻一起上街,总有一些人用不三不四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他们的目光加在一起大概就是那种意思:鲜花插在牛粪上嘛。你能想到我是多么讨厌那种下流的目光,它们就像剪刀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伸过来干什么?想剪凤凰的衣服呀。你要是见过那些下流胚的目光,你就会明白我年轻时候为什么总在大街上跟陌生人干仗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有办法把凤凰变成一朵花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把她装在口袋里,不让那些家伙看见她。年轻的时候我是把凤凰当花那样小心呵护的,可是孩子越生越多,家务越来越重,她这朵花就渐渐枯萎了。再后来她自己离开了枝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