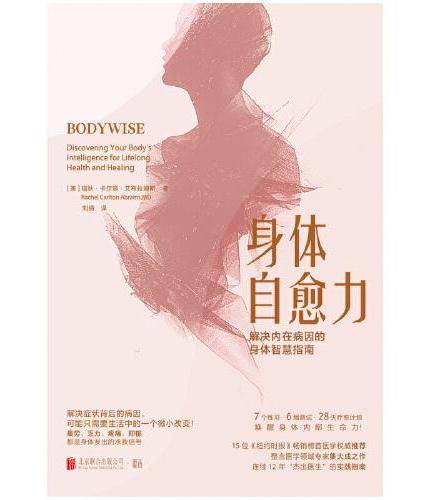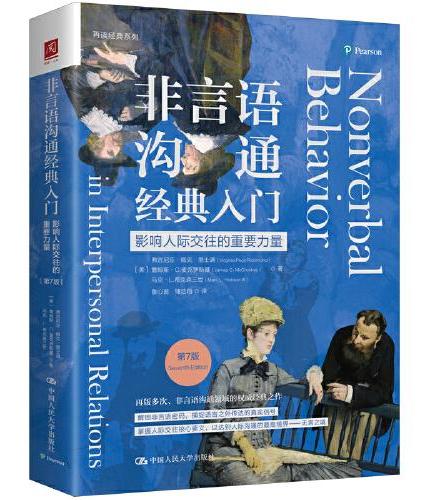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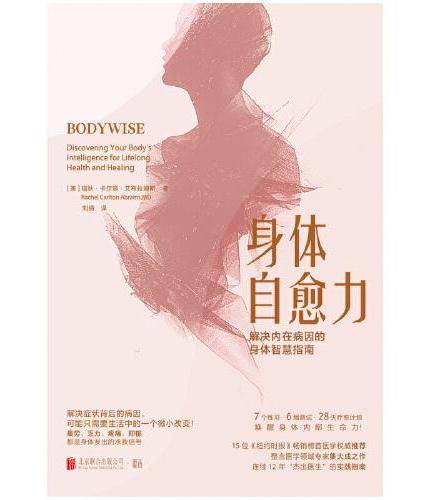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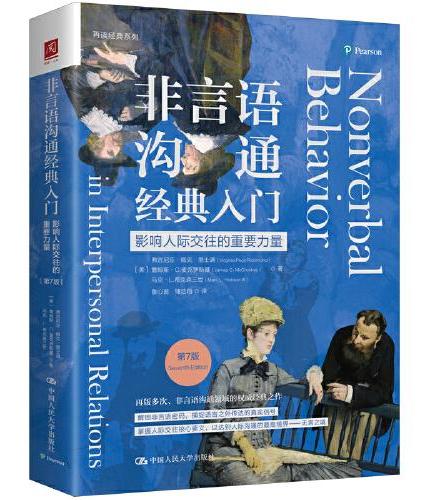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1.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NT$
4998.0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NT$
254.0

《
自由,不是放纵
》
售價:NT$
250.0

《
甲骨文丛书·消逝的光明:欧洲国际史,1919—1933年(套装全2册)
》
售價:NT$
1265.0
|
| 編輯推薦: |
|
他总觉得饥饿、空虚、孤独,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不朽他被誉为美国精神的化身,他的死让整个国家悲泣硬汉子既是他笔下的人物,也是现实中的自己在你陷入人生的低谷时,他是上天指给你的转机
|
| 內容簡介: |
|
他笔下有刚强灵魂,也有柔情万种他精通于叙事艺术,作品影响着自他以后的创作。海明威习惯站着写作,他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精致简洁的行文,他笔下的每一个单词都承担着确定的叙事任务。
|
| 關於作者: |
|
海明威,他于1899年在伊利诺州的奥克帕克出生,并于1961年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自杀身亡。约翰?肯尼迪总统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以文学硬汉著称。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留下两百多处伤痕和抹不去的战争记忆。他有过四次婚姻,私生活极为放荡不羁,风流韵事不断,唯独对好莱坞女星玛琳?黛德丽始终保持着纯洁如一的爱。虽拥有一切却选择自杀,海明威血液里燃烧着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自杀欲望,他的一生都在与这种自杀冲动做斗争。他赞同尼采的观点:“适时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巅者最光荣。”
|
| 目錄:
|
非洲的青山
第一部 追猎与对话
第二部 记忆中的追猎
第三部 追猎与失败
第四部 以追猎为乐
流动的盛宴
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不错的咖啡馆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迷惘的一代”
莎士比亚书店
塞纳河畔的人们
虚假的春天
一项副业的终结
饥饿是很好的锻炼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信徒
一个新学派的诞生
和帕斯金在圆顶咖啡馆
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才子
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局
一个带着死亡征兆的人
丁香园咖啡馆的埃文?希普曼
魔鬼的化身
巴黎用不完结
|
| 內容試閱:
|
第一部
追猎与对话
第一章
我们正躲在旺德罗博 猎人用树枝在舔盐地
边建造的遮蔽物的后面,这时传来一阵貌似卡车驶来的声音。起先它离得很远,谁也分不清那是什么声音,接着声音消失了。我们祈祷着刚才不是汽车的声音,祈祷那仅仅是风吹声。可那声音又慢慢地逼近了,这下没错了,的确是汽车。声音越来越响,汽车在一连串响亮的不规则的爆裂声中挣扎前进,从我们的背后擦过后沿着道路向前驶了过去。两个追猎人中有个按耐不住站了起来。
“这下没戏了。”他说。
我以手掩嘴,示意他坐下。
“这下没戏了。”他又重复道,并将双臂摊的很开。
我向来不喜欢这家伙,这下更不喜欢他了。
“再等会。”我轻声说。麦考拉摇了摇头。他留着黝黑的光头,他把脸向我这边歪了一下,我看到了他嘴角上稀拉拉的中国式胡子。
“没用的。”他说
“再稍微等会儿吧。”我告诉他。于是他把头又低了下来,这样就不会暴露在枯枝上面。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洞口里,天渐渐暗了下来,枪口上的准星已近看不清了,但还是没什么猎物出现。刚才那位按耐不住的追猎者又开始失去耐心,变得坐立不安起来。
天空中最后的光亮马上就要消失了,他轻声告诉麦考拉天色太暗,没法射击。
“你闭嘴,”麦考拉对他说。“即使天色看不见了,老板 也能射的中。”
另外一个受过教育的追猎手,在他腿上乌黑的皮肤上划着自己的名字——阿卜杜拉,这一举动又一次证明了他的确受过教育。我看着他,脸上毫无艳羡之情。麦考拉看着他写出的名字,脸上也是没有一丝表情。过了一会那个追猎手将名字划掉了。
最后我借着余光进行了最后一次瞄准,发现即使把瞄准器上的孔径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了。
麦考拉在一旁看着我。
“不行了。”我说。
“是的,”他用斯瓦西里语附和道。“回营地吗?”
“是的。”
我们起身走出藏身处,穿过了树林,踩着沙质的土地,在树丛之间摸索着回去的路。我们的车停在一英里开外的地方。当我们接近汽车时,司机卡马乌打开了车灯。
那辆卡车的噪音破坏了我们的狩猎计划。那天下午我们将车停在路边后,小心翼翼地向舔盐地靠近。前一天下过小雨,但雨量不大,没有把舔盐地淹没。这块舔盐地其实就是一块林中空地,由于动物长期来此处舔食泥土来摄入盐,所以这里就形成了一块圆形的边缘呈凹槽状的区域。我们前一天晚上在附近发现了四只体型较大的公条纹羚留下的长长的、心形的新鲜脚印,还有一些更小的羚羊不久前留下的脚印。还有一头犀牛,从脚印和粪便判断,这只犀牛每晚必来这里。
打猎用的遮蔽物建在离舔盐地一箭之遥的地方。我们身体后倾,双膝高抬,脑袋放低,坐在一半是灰尘,一半是泥土的坑里。透过干枯的树叶和细细的树枝,我看到一只较小的公条纹羚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来到舔盐地边缘的时候站住了。这只羚羊脖子粗壮,一身灰色的皮毛英俊潇洒,两只盘旋的犄角映衬着阳光。我瞄准了它的胸脯,但没有开枪,因为我知道黄昏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条纹羚会来到这边,我不想吓跑它们。但羚羊们先于我们听到了卡车声,都跑到了树丛里。还有其他的一切朝舔盐地行进的动物,躲在灌木里的,平地上的,从小山上穿过树林下来的,听到那哐啷哐啷的声音都被吓跑了。它们晚一点的时候还会回来,但那时天就黑了,一切都太迟了。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放弃。汽车在沙土路上行驶,路边鸟儿的眼睛在车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直到车辆靠近时,它们才会感到一丝惊慌,拍动着翅膀飞走了。我们驶过了白天西行的旅人留下的篝火,将这片饥荒的土地抛到身后。
我坐在车里,枪托靠着脚跟,枪管倚在左臂弯里,一瓶威士忌夹在双膝间。我倒了一杯酒,在黑暗中掠过我的肩膀递给了麦考拉,让他从水壶里把水倒进酒杯兑着喝。这是我今天喝的第一杯酒,也是最好的一杯。昏暗中看着浓密的灌木丛从身边飞过,吹着夜晚袭人的凉风,嗅着非洲醉人的气息,我已经感到无比幸福。
接着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团大火,当我们的车靠近并驶过时,我看到路边停着一辆卡车。我告诉卡马乌停车并往回开。当我们开进火光时,我看到一个矮矮的,有点罗圈腿的人。他带着蒂罗尔帽,穿着一条皮短裤和一件开衫,跟一群当地人站在卡车打开的引擎盖旁。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我问他。
“我看够呛,”他说。“除非你是机修工。这引擎不喜欢我,所有引擎都不喜欢我。”
“你说会不会是发火定时器坏了?你从我们边上开过时听上去好像有定时器的爆裂声。”
“我想情况要糟糕很多。听上去像是很严重的故障。”
“你要是愿意过来的话,我们那倒是有位机修工。”
“有多远?”
“大约二十英里。”
“要是上午的话我兴许会去试试。现在这东西发出这催命的声音,我可不敢继续开了。这东不喜欢我,所以想拉上我一起死。我也不喜欢它。但如果我要死的话我可不想拉上它。”
“要来点酒吗?”我拿出酒壶。“我叫海明威。”
“康迪斯基,”他边说边鞠了个躬。“海明威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在哪儿听过呢?哪里来着?哦,对,有个诗人叫海明威。你听过诗人海明威吗?”
“你在哪里读到过他的诗?”
“在《横断面》里读过。”
“彼海明威正是此海明威。”我高兴地说。《横断面》是德国的一本杂志,那时我写的东西在美国根本没市场,我曾为那本杂志写过几首不怎么样的诗,还发表了一篇长篇故事。
“这事真奇怪,”带着蒂罗尔帽的人说。“说说看,你觉得林格尔纳茨 怎么样?”
“他很出色。”
“哦,你喜欢林格尔纳茨。不错。那亨利希?曼 呢?”
“他不怎么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