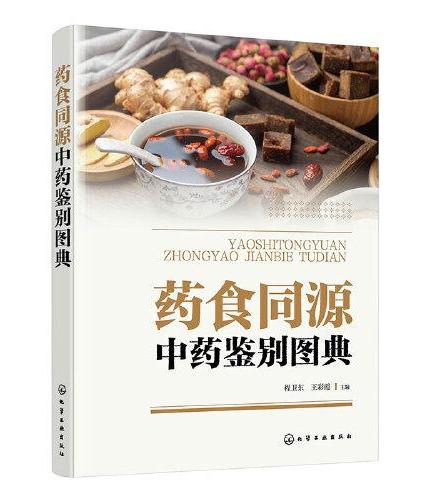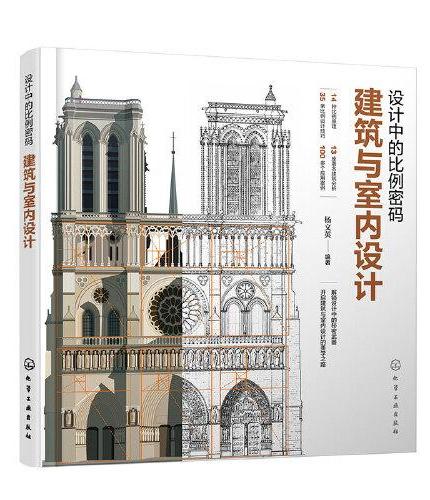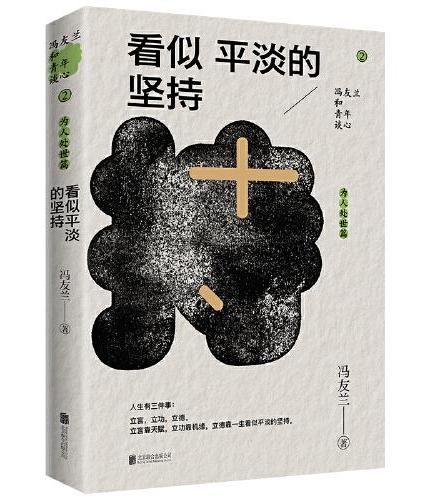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NT$
500.0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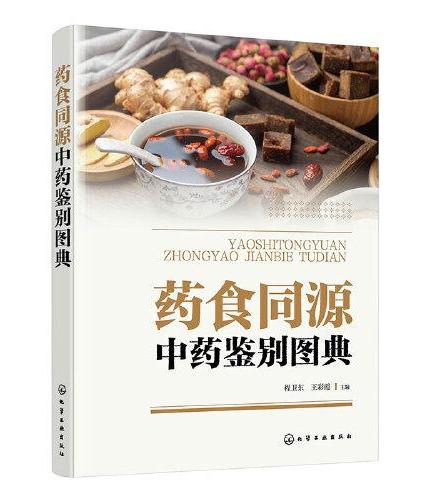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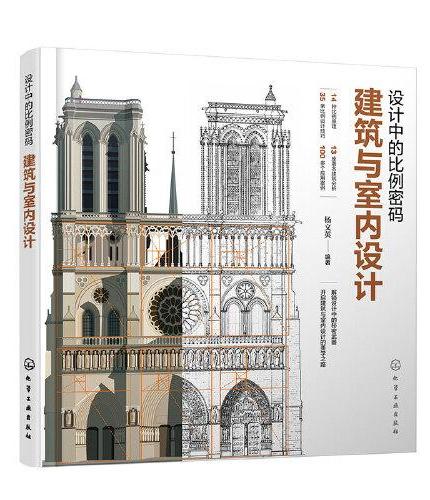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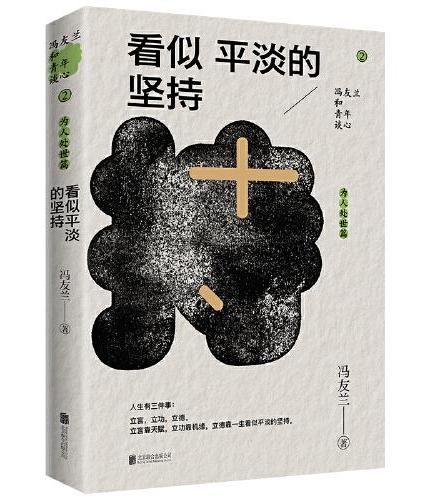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NT$
254.0

《
汉字理论与汉字阐释概要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作者李守奎新作
》
售價:NT$
347.0

《
汗青堂丛书144·决战地中海
》
售價:NT$
765.0

《
逝去的武林(十周年纪念版 武学宗师 口述亲历 李仲轩亲历一九三零年代武人言行录)
》
售價:NT$
250.0
|
| 內容簡介: |
相较于大多数旅行者,作家洛艺嘉更像古老时候的游吟诗人,她所到之处,总有故事伴随左右,有些是她讲的故事,有些是她参与的故事,有些则是别人希望她带走的故事。这些故事像窗口,使她在旅途中面对的不仅是异国风景,更有别人的真实生活。本书,是洛艺嘉在行走过程中所遇到的爱的故事。
本哈都单身夜晚
这世上,不知身在何处的一个人,会和你那么相近,你和那个人,那么相近,那么相近,却在这大世界里自行其路,永不相见。即使遇见了,交谈过几句,也不问过往,流水般无意地经过了。
塞内加尔,偶遇一个女孩的梦想
那个人,虽然他脸上布满尘土,神情也开始疲惫了。但是,他的一切,那么深地装在我心中。
时光流转卡萨布兰卡
“我猜卡萨布兰卡一定有很多破碎的心,你知道我从未真正地去过那里。”
非洲,失去的乐园
远方,其实没有我们要的生活,我们却停不下追寻的脚步。因为年轻,我们就要出发。年轻,出发。
图西少年布特拉
我也流泪了,把他抱在怀里。我也是爱他的。真的,这种爱,就像吉瑞姆对哈碧玛娜的爱吧,深爱狂恨,就像白天和黑夜交替着、夹裹着,涌进生活这条昏暗乏味的长河里。
异国的情侣们
世界之大,我只爱他一个
|
| 關於作者: |
|
洛艺嘉:作家,旅行者。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传统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其文章入选《当代名家小说快递》《当代名家散文快递》等多种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同居的男人要离开》《中国病人》《资本爱情现在时》后,突然放弃优裕舒闲的生活,开始一个人的世界游。9年时间,游遍五大洲101国。是国内以自助游身份走遍非洲的第一人。是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周游世界的第一人。著有旅行文学《一个人的非洲》《遗失象牙的海岸》《马德里美人帮》《慢游地中海》。
|
| 目錄:
|
目 录 Contents
本哈都单身夜晚
那男孩在等谁
单身男子
塞内加尔,偶遇一个女孩的梦想
带你去新鲜的地方
她心中的大漠英雄
布宜诺斯艾利斯,荒芜的花园
时光流转卡萨布兰卡
时光流转
白色宫殿
我的卡萨寄居生活
谁在卡萨心碎
阿联酋梦想
皇宫酒店侍者的眺望
一个律师的中产阶级生活
布城,沿着故事的轨迹
来自世界各地的怀念
听埃维塔老婆婆讲贝隆夫人
激情探戈
沿着“春光乍泄”的路
非洲,失去的乐园
图西少年布特拉
英俊少年
“你不是高吗?我就砍你的脚!”
一个少年的逃亡
最深的爱与恨
北伦敦之夜
五月到荷兰看花田
你到 LISSE 看过郁金香花田吗?
因你的注视而幸福
桑吉巴尔,石头城中再迷醉
芒,雨夜狂奔去金矿
雨夜惊雷
陈翻
神医
热内波
这孩子,是你的了
异国的情侣们
阿妲和约翰
布查与菲拉姿
井上与伊莎贝拉
|
| 內容試閱:
|
本哈都单身夜晚
那男孩在等谁?
暮色初染,这些连绵的赫色山峦仿佛将赴黄昏约的美人,将自己换上姹紫的晚装。紫色的,蓝紫色的,红紫色的,更有那形容不出的神秘颜色。在这些山的后面,飘浮灰蓝色的云,橙黄色的云,色彩神迷的云。夕阳有时会从云中钻出来。晶亮璀璨,一分钟便消失了。再早一些时候的阴霭下午,太阳也会穿透厚厚的灰色云层,散下金丝般的万丈光芒。那是神出现时会有的光芒,西方绘画中天堂的光芒。
再往南走,道路会越来越崎岖,遍布石头。然后,就是变幻莫测,浩瀚无垠的撒哈拉沙漠了。
这无垠天地中美醉欲死的景色,这在我眼里惊为神祉的景色,在拉森,在卡摩拉,虽也“很美”,但也因为日常而平常了。
夕阳散尽,空气开始凉爽起来。有着灰绿色叶子的橄榄树,从白日的昏沉中清醒过来。隔条马路,能看到对面的一家家客栈。它们的小院子里停着安息下来的旅行车。客栈后面,是阿伊特.本哈都村的民居。它们迥然于北方的“白色群落”,它们是南方high
atlas的赫色小屋。high
atlas,北非最高的山脉。隔一条现在看不到的玛拉河,再远再高处,倚山而筑的,就是那卡斯巴。这些同是土赫色的黏土房子,平时就和脚下的山难分彼此,现在,更是色形皆隐了。不过因为太熟悉,拉森、卡摩拉会识得它们的轮廓。还有那点缀在房舍中老实敦厚的棕榈树,高高俊俏的白鲁树。
久远世纪前就已在这里的卡斯巴,是电影导演们崇爱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又译《沙漠枭雄》拍摄于此。那是这村子的黄金时代。在玛拉河岸,紧临着原来的卡斯巴,英国人用赫色的黏土建起了仿旧的城门。这使得卡斯巴更像一个坚固的城堡。村里许多人参加了影片的拍摄。平时骑悠闲毛驴的他们,陡然变成了猎猎战马上英武的骑士。彼得.奥图尔,也似乎真从那个散漫的英国中尉,变成了阿拉伯人眼中的“圣人”劳伦斯。他性格复杂,却有天生的军事才能。卓而不群,在浩瀚沙漠中大显身手。尤其是黄昏初临之时,夕阳西去,天地间一片壮丽。沙漠历险、战争、史诗,那是男人的一生中,怎么也会梦想过一次的悲情壮美。开始,其实是结束的倒计时。只是,我们太过欣然于开始的布展,沉湎其中,欣欣然,而不觉为结束的到来,嗟然。电影拍完,剧组撤走了。本哈都的村民自然地失落。他们不再能拿工资了。也终究从壮怀梦想跌回平淡的现实。外面世界的人,欢喜这影片并不差于他们。取材于真实的这大型画卷般的史诗性巨片,196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摄影等7项大奖。本哈都开始声名远播。隔着一层想像的迷雾,世人眼里的沙漠、卡斯巴,更壮美绝伦。“观众全神贯注盯住纯净的金子般的沙子熔化的闪光,盯住空旷、灿烂的无限苍茫,就好像盯住上帝的眼睛一样”。拜访它的人,从世界各地来了。1987年,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望着这山谷暮色的我,拉森,卡摩拉,我们在本哈都卡斯阿旅店的二层露台上。这旅店刚刚开张。我是它的第二位客人,这几天唯一的客人。拉森是替旅店老板经营的管家,卡摩拉是他手下的伙计。拉森经常穿休闲西装。卡摩拉则穿柏柏尔牧羊人穿的那种长袍“吉哈巴”。
“哈森刚把那中国男孩领进屋时,我们便发现他颇异常。惊喜、好奇、失望、陌生,反正一个游人身上该有的,他都没有。他进了这屋子,就像进自己家一样平常,没有感觉。领他看完房间后,我们问他是否在这里就餐。如果就餐,那么一天110块钱。也没有讲价,也没有爽快地说行,那男孩只是淡漠地说‘随便’。然后我问他希望晚餐何时吃,吃什么。他还是冷淡地说‘随便’”。卡摩拉看了眼拉森说,“虽然拉森认识一些中国人,知道你们喜欢说随便,但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卡摩拉和拉森商量了一下,决定9点半开饭。这是旅店的第一位客人,所以他们准备的晚餐很丰盛。可这客人皱着眉头,动了两下便放下刀叉。拉森的理想是经营人性化的旅店,住过的旅客忘不掉的地方。见中国男孩这样,他谦和地过去,关心地问:“你不高兴吗?”男孩看也没看他一眼,道,“我高不高兴,关你什么事?”
“这话把我噎的。我发誓再不问客人这些了。可我没有记性。”拉森看我一眼,“当你坐下吃饭时,我又问你了。”
“是啊。”我笑了一下,“第一天,当谷斯谷斯上来的时候,我记得你是第4次说‘欢迎’,第3次问‘你开心吗?’”
柏柏尔人上茶要上3遍。客人拒绝,视为不礼貌。可是,那男孩,刚喝了一口茶,就告诉拉森和卡摩拉:“我自己呆着,你们出去吧。”卡摩拉怀疑那是个厌世,准备自杀的人,说旅店刚开业就碰上这事真是太晦气。拉森说要是那样的话,更得救他了。不好张望,他们就在外面逡巡,谛听里面的动静。没闻听有何异样的他们,半小时后借故进餐厅去。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男孩不在屋里了。卡摩拉听拉森讲过中国的灵异故事,开始觉得男孩是鬼,顿时惊骇万分。男孩如此无声便没了踪影是颇令人惊疑,但拉森还是马上返身去他房间。房门大敞四开,男孩不在屋里。正准备叫村里的小伙子四下搜寻时,他们在连接餐厅和客房的小院子里,发现了静望天空的男孩。这个方形院落有天然的穹顶画幕。白天,是蓝得逼人的天,白得惊人的云。夜晚的天空同样是蓝的,星光繁盛。男孩回房间时,拉森跟过去。不善言辞的他,想和这男孩靠近,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就只能问“这房间还好吧?”男孩同样看也没看他一眼说“好不好对我都无所谓。”第二天,哈森想带他去卡斯巴时,男孩拒绝了。“那我就奇怪了,昨天他是怎么跟你来这里的?”拉森问哈森。哈森笑了“是他径直往这里走,我跟来的。”
我倒确实是哈森带到这里的。在暮色已经笼罩了村子,几盏灯在混沌中次第亮起来时,哈森从墙边阴影里,他靠着的土坯房上起身,向我走来,“我能带你去不错的旅店。”
第二天晚上,中国男孩也是吃了几口东西,跟谁也不打招呼便回房间睡觉了。然而,第三天早上,卡摩拉进厨房准备早餐时,竟发现那男孩在里面烧咖啡。“你们早餐吃什么?”他问卡摩拉,好像他是这旅店的主人似的。然后,一上午,他就在这个露台上,望着云影下变换色彩的山谷,奇怪地意兴盎然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初次的恋爱是17岁那年的夏季。在微微晃动的巴士上,他手上的调频立体声把他最喜欢的《山鹰的飞逝》播放出来。这突然来到的歌,是那么令他激动。他想找个分享的人,就摘下一个耳机,把它插到身边女孩的耳朵里。这动作是那么突然,使得那女孩,虽然是完全陌生的女孩,都没有拒绝的机会。也许是那曲音实在美妙,女孩没有把耳机摘下,就那么听着。周围的人,是否注意到他们是陌生人?多年后他想。当时的他,完全忘我了。他忘了自己是如何把耳机从女孩的耳朵上摘下的。多年后,他还心惊地记得自己下车后,一转身,看到女孩也下车了。同样在等换车。夏季的暴雨不期而至。想起自己车上不经意的勇敢,他鼓足勇气,走过两步,对同样也没带伞的女孩说“咱们去看电影吧。”女孩几乎没有犹豫,“好。”那是4路车西单站,离首都影院咫尺之遥。他们走出影院时,雨还在淅沥着。散了一会儿步后,他问“我能做你的男朋友吗?”女孩问他的年纪,然后说比他大两岁。大好啊,知道疼我,他说。女孩笑了,没说什么。雨又大起来,女孩从背包里拿出大夹子给他挡雨。一本书从里面落了出来。他看到了扉页上某大学图书馆的图章。夜晚分手之时,他把自己的初吻给了这女孩。温暖的雨夜,女孩的长发上有丁香的清幽。在女孩别致小巧的通讯录上,他把自己的电话写在姓名之后。女孩没说自己的姓名,她说,明天中午我给你电话。第二天中午,他没去吃饭,一直守在电话旁。他有事不得不出去。回来后,别人告诉他:刚才有个女孩打电话找你。该是昨夜让他交付初次爱情的女孩吧。可为什么,她再不来电话了?为什么?为什么呢?他永远不知道了。在那个雨季的午后,她出现在他青春的天空下,惊鸿一瞥,却再也不肯重现。他去那所他觉得她该在里面的大学等过她,一次次。他知道了什么叫人海茫茫。为什么不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贴启示找她?在他为自己的不彻底而后悔,而终于有主意时,更是无法寻她了。4年过去,她毕业了。或许早就毕业了。人海更加茫茫。或许,或许她根本就不是那所大学的?
男孩的第二个女友有名有姓。也不是浪漫的路遇,是在某会上认识的。本该叫乔红菲的这个女孩,给自己改名乔鸿飞。短发的她,不喜欢柔美,倒爱男性化的壮丽。会吹好听的口哨。看《阿拉伯的劳伦斯》时,更是和他一起投入。看到影片中劳伦斯让风把自己的长袍鼓起来,想学鹰般飞翔时,他想起《山鹰的飞逝》,想起多年前那个夏季。那个神秘女孩,只在他生命中出现过半天,却将他永远改变了。
鸿飞很喜欢这影片。他们一起看了3遍。还不过瘾,她又找来劳伦斯的自传《智慧的七根柱》。看到劳伦斯写给他永远的爱人,他的同性恋人阿拉伯青年达洪的那首诗时,不多愁善感的她流下泪来。
我爱你
所以我把千军万马召入掌中
让夜空的繁星写出我的意愿
……
“如果我也是男人,你还爱我吗?”鸿飞问。他没有给她满意的答案,她便兀自说,“我要是男人,你也得爱我。你要是女人,我也爱你。”
他们那么相爱。每个黄昏,她都要过他那里去。他们读书,听音乐,看影碟。他们相约要到那故事的发生地,那沙浪驼影,那大漠孤烟的摩洛哥去。去穿越那沙漠的灼人热浪,那神秘的死亡之谷。他为此做了不乏艰苦的努力。可是,就在他即将把梦想交给她时,他找不到她了。他知道她的姓名,电话,单位。可他找不到她了。她的单位都不知她去了哪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似那么自立的她,难道被人供养着?亦或,那么求灵魂纯净的她,却不在乎肉体的堕落,根本就是个“卖的”?或者,她清秀的外表原本是人工所为?或者,她根本就是个男人?或者,外表坚韧的她,心思太过细腻,发现了他不敢提及的从前,不能原谅?是隐情难言,还是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只是他青春的梦想?是照亮他的一束光,让他对万象迷惑,而又断然而解人生的残破?他想起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想起她用那么动听的口哨吹给他《山鹰的飞逝》时,他第一次流下的眼泪。人是多么不解自己。这泪水,是流给鸿飞,流给那不曾知晓姓名的女孩,还是流给他自己?或许都有吧,人生是那么复杂难辨。
他一遍遍地看《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把大卫.里恩导演的《桂河大桥》和《日瓦戈医生》也一起看了。仍旧没有等来鸿飞。仍旧什么也不知晓。
他还是决定去摩洛哥。“梦想实现了。可是,一起做梦的那个人不在了。”就在两周前,就在这里,他望着这壮美的山峦,这沙漠上的绿洲,问:“你们说,也有那最美的可能吗?她会在这里等我?”
不知何时开始,拉森和卡摩拉都直盯盯地望着我。半晌,拉森打破沉默:“那男孩要找的女孩,是你吗?”
我看着他们笑了,没有回答。
“来这里的中国人极少。独行的,我看到的还真只有你和他。而且,你们都没有去那旅客众多的客栈,而是投宿在我这刚开张的小店。”
“既然孤身行走,当然不愿凑那份热闹。”我说,“最主要的,还是村口替你们拉客的哈森,把我带来了这里。”
“你在这里真可能有所等待。因为一般的客人,只是在去瓦尔扎扎特城时在这里停一站。过夜的并不多。像你就这么住下来的,除了那男孩,还真没有别人。”拉森说,“你别等了,那男孩走了。”
“我不等什么。我只是习惯于一个地方住上那么一阵。这样,体会才不会是匆忙的,飘梦般的,才会是现实些的。真实的,不那么片面的。”
“还有个理由可能是那男孩不曾想到的。”我接着说,“他的心思转变得太快。一会儿狂喜,一会儿深愁。太出色的个性不适合现实生活。太特立独行对自己是洒脱的无羁,对亲近的人却可能是伤害。也许,是现实世界的分秒必新,使得他有太过迅捷的变化。”
“你真的比别人都懂他。”卡摩拉说,“而且,我发现你们身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真的?而这男孩,会是我在马拉喀什遇到的那个吗?那是在皇宫附近,一群外国老太太从一辆大旅行车上下来。碰巧站在我身边的他说:“老头们都死了,出来玩的都是老太太。”
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话,并非他的东方面孔。而是那时候,看着花花绿绿的老太婆从旅行车上下来,我想的也是:呵,出来玩的全是老太太。
我虽也常有感于这人世的弹指之顷,无常幻灭。但那么年轻的人,离安息太早,总还是该安乐的,我说:“什么都死了?老头们都在安定门地铁下棋呢。”真的,不论阴雨晴风,安定门地铁东北出口,总有那么多老头下棋,那么多老头围看。每次经过我总想:和家人该说的话都说尽了,他们只有出来。在北非,看着遍布的咖啡馆里那众多的老头;看着他们很多并不和别人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深夜了,他们还坐在那里,我想,男人和女人,真的不需要那么靠近吧?
“你北京的吧?我也是。”隔了有一会儿,那男孩说,“老头们是都死了。”
“什么死了?人家都在那里下棋呢。”
“他们都死了。”那男孩无比确信,“是新一批男人老了。在那里下棋。”
这世界对男人或许真是残忍。他们不能像女人一样在家做做饭,看看孩子,收拾收拾屋子,从平常的生活里便能找到快乐。他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心和女人不同。但是,他们中,又有几人能创功建业呢?芸芸众生,基本不是在浑噩中迎来世寿之尽?
我曾在佛罗伦萨的街头,一天之内,4次遇到同一个人。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同为旅人,又同为国人,我们的足迹是相像的:教堂,广场,中餐馆,麦当劳。而那个偏得让老头死去的男孩,我们说过几句话,也便各走各路了。自己准备的安宁,有时是怕别人惊扰的。
“其实有一点,就可以确信我不是鸿飞。”我说,“你们看过我的护照。”
“既然那么轻易就消失了,又怎能保证她鸿飞的名字,”拉森笑了,“或你的名字,不是假的呢?”
“我不是鸿飞。却是那个他不知姓名的女孩。”我假装正经。
他们更惊诧地瞪着我。
“他不是和那女孩在首都影院看过一场电影吗?他们坐哪里,看的又是什么?他没说吧。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坐在最后一排,看的是《霸王别姬》。”
卡摩拉惊愕得都转身了。他又转回来:“是最后一排,是《霸王别姬》。他说了,他说了。只是我们忘了告诉你。”
“你真是那个他不知晓姓名的女孩吗?”拉森认真地问。
我笑了:“不知道。”
“是不是呢?”拉森更认真了。
“开玩笑呢。”
“那怎么会说得那么准?”
“恋人当然愿坐最后一排了。而那影片,是从前的一个流行片子。我顺嘴瞎说的。”
“真的,你们太像了。”卡摩拉又说,“喝咖啡都不加糖。喜欢长久地望着某处。会看和路途没有关系的书。对草木有特别的兴致……”
这世上,不知身在何处的一个人,会和你那么相近。你和那个人,那么相近,那么相近,却在这大世界里自行其路,永不相见。即使遇见了,交谈过几句,也不问过往,流水般无意地经过了。是的,太多的相同,又能怎样呢?又能保证在一起便不散吗?浩瀚世界,不见不散。萍水相逢,飘零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