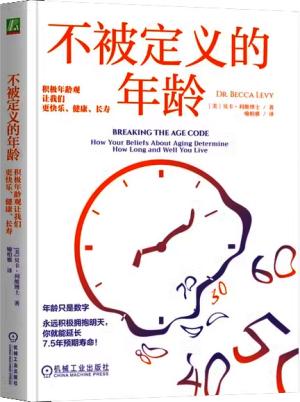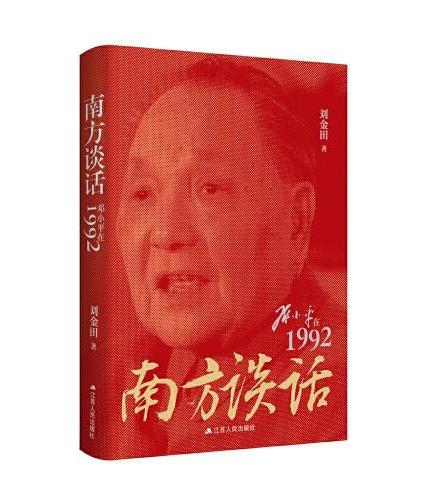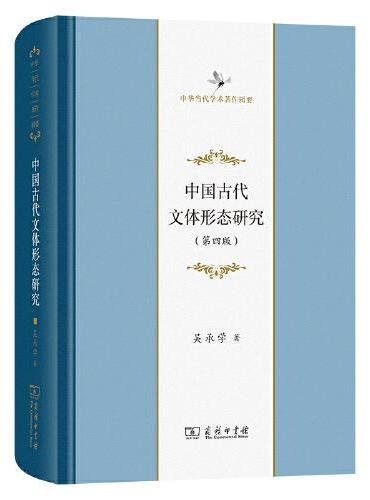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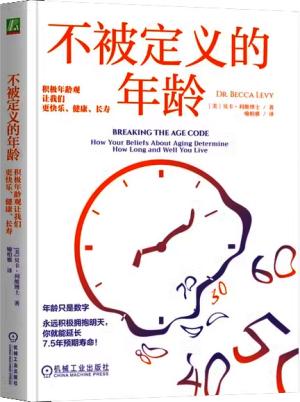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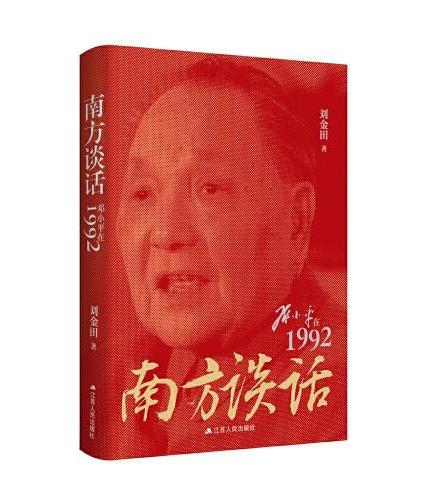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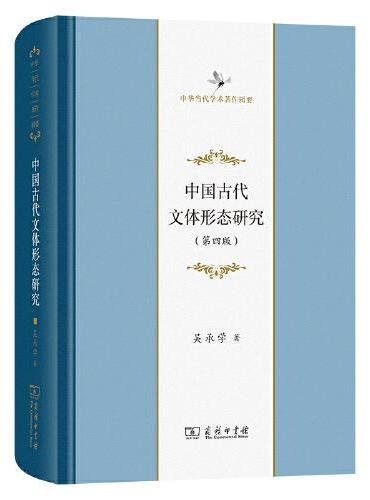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NT$
765.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NT$
403.0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NT$
286.0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NT$
245.0
|
| 編輯推薦: |
90后文坛新生力量汪立早首部青春疼痛推理小说
父辈情仇、友情救赎、亲情的捆绑、成长的蜕变……
十五年前一出《霸王别姬》酿造的血案,
十五年后三个少年在戏剧的真与幻中步步追踪,
水落石出的一天,年少的灵魂,是否也会破茧成蝶?
|
| 內容簡介: |
十五年前,一宗谋杀案给两个家庭烙下痛苦的烙印,十五年后,他们的女儿却阴差阳错在青城戏曲学院附中成为彼此唯一的好友。
一位是老师同学眼中才貌双全的“花旦”,一位是受尽白眼天资平庸的杀人犯女儿,条件的差异、关系的特殊,加上豆蔻年华的微妙心事——那位笑容永远明亮温暖的少年,让两个女孩的友情在进退之间摆荡。
在一次次友情的嫌隙与修补中,她们不约而同地将焦点对准了当年那个疑点重重的案件,却发觉,事情并不似大家认知的那样简单。
比巧合更可怕的是人性,比结局更可怕的是真相。
十五年前,一出《霸王别姬》酿成惨烈血案;十五年后,同一个剧院、同一出戏,当曲折的推断遭遇人性暗面,谜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然而,冥冥中似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他们前行,三位少年各自发现的碎片,拼凑成一个让人窒息的真相……
黎明到来之前,他们的命运将会发生怎样的颠覆?
|
| 關於作者: |
汪立早。1997年5月出生于青岛。11岁短篇小说获冰心作文奖。如今站在十几岁的路口半梦半醒,相信并期待着童话,同时睁大双眼,试图看清周围。
笃信文字和音乐是最干净、安宁的城,因而希望在其中躲藏,
也以此铭刻某段时光,或着,认识自己。
|
| 目錄:
|
引子
第一章 6点整
第二章 6点半
第三章 7点一刻
第四章 7点20
第五章 差5分8点
第六章 8点40
第七章 差5分9点
第八章 10点10分
尾声
|
| 內容試閱:
|
屏幕上是一张秀美的女孩儿面孔。眉蹙青山,双瞳剪水,乌黑的发丝被北风吹得贴在白皙的面颊上。
“拉远。”指挥员命令说。
播放员按动按钮,视野变得宽阔许多。
是一片坟地。
旧坟低矮,无规律散落在空地四处如晚上的星星散落夜空般,传说每一颗星星都是地上一个灵魂的归宿,而坟墓是肉体的归宿。灵魂闪亮时,肉体漆黑一片,当肉体光明,灵魂便暗淡无光。
女孩儿站在离坟头有些距离的地方,身着白色单衣,身后残阳如血。坟头上跪着一个男人,枯瘦得恍如坟中人。
男人嘴唇在动。
“声音。”指挥员说。
播放员旋开一个圆形旋钮,声音即从四周的音响中泻出,苍老、地方口音明显。
“爹,儿子来看您了。爹,您在下头好受不?缺什么不?儿子给您送。这儿是二锅头,这儿是哈德门,这儿是钱票子,都给您带过来了。去年那副麻将您用着顺手不?不顺啊明儿再捎一副新的来。”
“爹,儿子不孝啊!这么些年了,我一直没能给您添个孙子,叫咱们老谢家绝了后了,儿子不孝……”
男人只是对着那坟重复着,薄嘴唇在枯瘦的脸盘上颤动,就像秋天垂死的虫子在营养不良的梧桐叶上慢慢蠕动。他的头上,几根弯曲的黑发像蚯蚓卧在湿润的泥土中一样,卧在他油亮的头皮上。男人的一双手骨节突出,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无法伸直。
男人终于吐完了一肚子话,他往后退了退,跪下,磕头。脖子上油渍渍的红绳拴着的送子平安符和一把小金钥匙从衣领中露出来。
“再拉远。”
女孩儿、男人和坟头渐渐变成屏幕上的黑点,一座轮廓清晰的小城随着镜头的不断拉远而逐渐呈现出来。
不靠山,不挨水,一座小城完完全全躺在周遭城市的臂弯里,不设一点防备。道路规规矩矩,像小学生的田字格一样把小城分成规整的形状,又把一个个格子连得紧紧密密。建筑都不算高,板楼、塔楼大多是灰色屋顶,低矮的平房屋顶却多为暗红色,又被长年累月的雨淋成了不规则的脏兮兮的红色与黑色相间的油画。
“不对。”指挥员提出疑问,“我们今天要看的主人公应该是未成年的男性啊?”
“没有错,主人公的确是未成年的男性,但是跟踪器开头的试播显示就是这样。”
指挥官点点头,他看了看腕上的表。我们大家都已经坐好,我也看了一眼手腕内植入的生物表,5点55分。
五分钟过后,灯灭了,播放员终止了试播画面,按动了椭圆形的正式播放按钮。
第一章 6点整
也许每个人的初衷都只有一个简单的追求,或期待一场温润的春雨,或盼望一株茉莉花开,或等待一个远行的归人。我们在属于自己的那座城里筑梦,不求闻达于世,但终究还是希望可以留下些什么,仅仅为了被某个人偶然地记起。
—— 白落梅《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1
傍晚的阳光聚拢着一日的余晖,慵懒却也欢喜,斜照进青城戏剧学院附中位于四楼高一教室的窗户。窗台上面是一盆略显歪斜的仙人掌,本来坚硬的绿色枝干上面爬满皱纹,边缘泛着枯黄色,枝干上面顶着的原本鲜红的花球萎缩了,针刺正在变软。
窗台不远处,讲台上的地理老师自顾自地在黑板上写画,掩不住心不在焉,粉笔总跑向不该去的地方。写完潦草的板书,他转过身,面对着下面坐着的学生,眼睛却不知道在看向哪里,他仿佛没有看见讲台下的学生——东倒西歪、姿势各异,如凡尔登战役后的残兵。
何离秋坐在放着仙人掌的窗台旁,双手托着微微泛红的腮帮,任凭自己的思绪游走在地理老师所口若悬河,而自己不能懂得的东南西北、江河山川之外。
“何离秋,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没有经历过。你不会在睡梦中梦见自己的妈妈面孔惨白,身体没有一丝温度;你也不会在梦里感觉自己身体中温热的血液被一柄剑的寒气攻克,一点点冷却凝固。你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知道我的恐惧?你走吧,离秋,让我一个人待着。你不知道我看到你更害怕,你知道这些都是为什么!何离秋,你自己知道……”
何离秋的脑海中,谢彦昨天说话的声音还在盘旋萦绕。傍晚的太阳光在教室的地面上形成了灰黄的光斑,何离秋仿佛看见光斑中间浮现出一张秀美的女孩儿面孔,眉蹙青山,双瞳剪水,发丝乌黑。何离秋的心一如昨天那样快速地跳动着,口中也与昨天一样有着许多急于表达出的解释,还有解释之后安慰的话语。但是,也和昨日一样,舌根下那些话语的刑期还没有到,何离秋无论如何无法将它们释放。
何离秋摇摇脑袋,想让耳边萦绕不休的、谢彦昨天站在走廊尽头冲自己喊出来的那些句子离开。但是只能是徒劳,谢彦那张秀美的滑落无数泪水的面孔仍旧在光斑中间,她一直在诉说十多年前的那场变故带给她的日夜相随的痛苦,那一把锋利凛冽的剑,寒光霜刃,如何一寸一寸刺破华服,刺进鲜活的血肉,刺进舞台后的生活。
何离秋仿佛看见地面上在漫延着鲜血,暗红的颜色如同窗外的夕阳,何离秋亦在自己的错觉中感觉到恐惧和一种莫名的罪孽,她知道循着血泊走到尽头,就是她无法置身于外的恩怨,也是数段年岁正好的生命的最后终结,想到这里,何离秋打了一个寒战。
同时,何离秋感觉到后脖颈处传来一阵强烈的刺痛。
讲台上,老师扔下刚刚擦过黑板的粉笔擦,粉笔擦掉到讲台上的瞬间,白色的粉尘从粉笔擦上升起来,好像热茶上方的袅袅蒸汽,向着讲台四周飘散而去。
疼痛似乎就来自于何离秋曾经想象过无数次的那柄剑,她仿佛在这转瞬即逝的疼痛中看见自己血流满地的样子,恐惧和疼痛让她忍不住惊叫出声。
“是谁?”地理老师终于将视线投向讲台下的学生。看着移动的白色烟尘,他皱起了眉头,这一声几乎与他扔下粉笔擦同时响起来的声音,带着抱怨和吃惊。
教室中有睡梦正酣的学生轻微的鼾声,何离秋的表情凝固在刚才惊叫过后的样子上,仿佛时间停止了。
地理老师想要的答案就写在何离秋的脸上。
看到地理老师投来的冷峻目光,何离秋缓过神来,将张着的嘴合拢,用上牙咬住了下唇。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笔袋,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
地理老师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还有几分钟就要下课了,他清清嗓子,将快要滑落到鼻尖的金丝边儿眼镜向上推了推,然后开口。
“何离秋,起立。”
何离秋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同时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塌鼻子。
“你,刚才嚷嚷什么劲儿?”
“我……”
“解释不了,那就没理由。弄点儿粉笔灰又怎么了?老师我都闻了三十年了,你娇生惯养,闻不来?”
“我……他……”
“哦,忘了,你可不是特殊吗!你可不是被照顾对象吗?你有资格娇生惯养吗……”
何离秋红着脸,塌鼻子中是屈辱的酸楚,星星点点的泪珠被眼眶狠狠束住,才没有爬上脸颊。
教室里原来熟睡的学生被地理老师高八度的音调吵醒,看了一眼站立着的何离秋,像被注射了鸡血般,揉亮眼睛,打起十二分精神,随着地理老师的话发出阵阵笑声。
何离秋把头埋得很低,她想有一种魔法,让自己听不见耳边的一切。她竭尽全力去幻想,自己在一个偌大的、布景异常华丽的舞台上,满头珠翠,身上是绣工精美的贵妃戏服。梦幻般的灯光打在自己身上,莲步微移,朱唇轻启,婉转悠扬的声音从自己口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宛若一条惊艳的小溪,在台下众人心中流过,溅起迷醉的水花。众人高声喝彩,掌声、呼喊声和京胡月琴的声音融在一起,奏响出令人陶醉的美艳音乐。醉卧花丛,化了妆的脸看上去十分妖娆,自己折过腰身,头上的凤冠摇摇晃晃,台下人们的喝彩声浪鼎沸。
在何离秋已经要为掌声轻轻勾起嘴角的时候,那个魔法舞台在何离秋的目光不经意掠过旁边女生的面孔时轰然倒塌,燃起红色的火焰,最后连灰烬也不剩。她听清了,耳边是嘲笑谩骂和侮辱讽刺,而非热闹的喝彩。
讥讽和笑声好像是世界锦标赛双人花样滑冰冠军组合脚上的那两双昂贵冰鞋的冰刀刃,锋利无比。两者又配合得极为默契,一方在何离秋的心上狠狠划过时,另一方则不时跃起,偶尔用力踏进何离秋的心脏。四把利刃在何离秋的心上灵巧地旋转,划出一道道血弧;又轻盈跳跃,制造出不规则的血色花纹;飞速前行,满不在乎地把何离秋的心割出长长的口子。
她低头沉默,而讽刺挖苦嘲笑更加汹涌,何离秋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溺水的小孩子,丢失了救生圈,咸涩的海水一点点灌进她的口腔、胸腔、心房心室。她浮在海浪中间,孤身一人,像是在等待着最终的下沉。
但她没沉下去。
拯救她的是下课铃。
地理老师一句话只说了一半,把讲台上摊开的书合起来,夹在手臂和身体中间,便眼也不抬地走出了教室。
何离秋不知道老师是否看见后座的男生用圆规尖扎她的脖子,男生总说是在模仿何离秋的杀人犯父亲。何离秋想,也许老师看到了,只是这个校董家里的男孩,才是真正被照顾的对象。
何离秋默默地坐下,直起刚才默默垂着的脖颈。
用手摸一下脖颈后面,没有血。
为什么没有血?
桌边经过的一个男孩儿停住了,何离秋抬起头,看见一双清亮温和的眼睛,男孩扬扬嘴角,递给何离秋一个熟悉温暖的笑容后走开了。
何离秋看他走远,掏出了一个小本,在里面的格子里又打了一个小勾,标上日期。
“九百六十四。”她在心里默念。海浪退去,冰刀遁形,疼痛飘散在热闹拥挤的空气中。
楼外,残红一片。
何离秋顺着空无一人的楼梯迅速跑下去,嗒嗒的脚步声在挑高的空间中回荡。她看看手腕上的表,还不晚,谢彦应该还没有吃完饭,于是她迅速冲向食堂。
一条两旁种着梧桐树的小道是去往食堂的必经之路。这条小道是几位当红戏曲名家在一起怀旧时总要提及的风景,因而许多有戏曲禀赋的少年被送到这里,希望数年之后其中的某某能够成为戏曲界的名角、新秀。
黄昏里,法国梧桐的树叶静止不动,影子投射在灰红和灰黄两色的地砖上。何离秋迈着大步,用力踩在梧桐树的叶影上,仿佛想要将它们踏成碎片。
到了食堂,地上有积年残余的油垢,时不时粘住何离秋的鞋底,她迈着尽量大的步子,眼睛搜寻着那个身影。
谢彦就坐在她们两人常坐的地方,身形瘦弱,动作优美,孤零零的影子映在身后带着不规则污渍的白色墙壁上。
“这么晚才来,还吃吗?”谢彦听见粗粗的喘气声,知道是何离秋来了,便说,那双漂亮的细长眼睛却没有瞧何离秋一眼。她没有给何离秋回答的时间,就伸出细长的指头轻轻指一指何离秋身后,“帮忙盛碗汤吧。”
两碗紫菜蛋花汤,何离秋把鸡蛋多的那一碗推到谢彦面前,谢彦说了一声谢谢,还是没有看何离秋。
“彦儿,昨天的事情……”何离秋怯怯地问。
谢彦抬起眼睛看着何离秋,然后摆手说:“没事了。”
何离秋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汤,有些凉了。
何离秋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种情景回忆初逢有些莫名其妙,不合时宜,可是回忆这件事总是无可避免地自由来去着,从蛋花汤里钻出来了,何离秋就再不知道怎么把它塞回蛋花汤里去。
2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夕阳挂在梧桐树梢上的时间,何离秋刚刚告别了高一。
何离秋的高一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高一。
孤立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孤立了世界;另一种是世界孤立了你。
何离秋知道自己绝不属于前者。
在何离秋踏入校门之前,何妈妈就已经让足够多的人知道了何离秋杀人犯爸爸的故事。何妈妈以一种近似疯狂的状态给不同的人讲述何离秋的爸爸——何阔贤的故事,她似乎认为当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何阔贤就能复活。
因而无可避免,当何离秋像所有高一新生一样走进校园,她发现身边异样的目光和小学、初中时的情形没有区别。她身世的悲剧带给她的是一成不变的鄙视和嘲讽,而人们的冷酷似乎也随着年月的增长而变得坚不可摧。
但还是有件事值得何离秋庆幸。她遇见的专业老师省略了对她身世的讥讽,反而聚焦于她的专业素养。她也很努力,终于成为无数舞台聚光灯下的主角,能够在台上演绎勇敢的人生,能够偶尔地抬起下巴。
那天何离秋坐在本班的桌子边,她的旁边是三个旁若无人般大聊校园八卦的女生。何离秋迅速地将饭送进嘴里,以便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何离秋刚将一块土豆送进嘴里,就听见头顶上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你好,你是何离秋吗?”
她急忙咽下口中的土豆,抬起头来,眼前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少女穿着白色棉布的衬衣式及膝裙子,皮肤白净,五官精致,头发随意地扎成一束,两手放在身前,唇间含着若有若无的微笑。
何离秋感觉脸颊发烫,不禁用牙齿咬住嘴唇。
她记得自己那天穿了一条宽松的牛仔裤,一件粉色长袖体恤,紧身的,更显得下半身臃肿。
“我是何离秋,”她说,“你是?”
“谢彦,今年的高一新生。我想我应该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吃饭吧?”
“啊?好啊。”何离秋说,两只手背在身后,紧张地互搓着,说完这三个字后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谢彦的目光从何离秋的身上转向四周,长条桌边已坐满,只剩一个三条腿的残疾板凳。她瞟了一眼喋喋不休的三个女生,示意何离秋端起饭盘。
她们找到一个角落处空着的桌子面对面坐下,并且一直坐那个座位坐到现在。谢彦背对着墙面,墙面上有深浅、形状不一,时间久远的菜汤污渍,何离秋的目光越过谢彦精致的脸看着墙上的污块,想起医院老大夫手背上的老年斑。
何离秋看着“老年斑”有些恍惚。
“在哪里可以打汤?”谢彦问对面不知所措的何离秋,语气动作都比何离秋自然大方许多。
“我去给你打吧。”
两碗紫菜蛋花汤,何离秋把蛋多的那碗推到谢彦面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动作将要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上演。
“汤还不算太凉。”谢彦喝过一口后说。
何离秋以为她迎来了等待了数年的友情。
最初的一个月,和所有美妙的友谊、单纯的朋友一样,她们之间像草莓味的哈根达斯,纯粹而甜美,尽管亦含神秘。
清晨,宿舍老师狂野的敲门声响过不久,谢彦寝室门上方的小玻璃中便映出何离秋的一张圆脸。高二了,但她仍喜欢像孩童一样,把她的塌鼻子贴在玻璃上压得更扁,看鼻孔下方出现一幅哈气绘成的对称画。谢彦见了总要笑,说这个时候的何离秋和猪八戒可谓郎才女貌,何离秋便佯怒地打几下她的手臂。
她们一起去专业课教室练习基本功,她们幸运地由同一个专业老师教导。
清晨6点多的天空,云层厚重,拖着暗青色的阳光,同是暗青色的风旋转着吹过,吹起两个少女长而飘逸的头发。谢彦的头发乌黑,丝绸般柔顺,平日里极有垂感地坠在身后,自由的发梢及至腰间。何离秋的头发也是乌黑的,有些蓬松,偶尔会有些奓。风将两人的头发缠绕在一起,如人参的小根须一样盘结纠缠,好像两个生命的灵性就由这些细细长长的导线相互传递。
路边的叶子上挂着露珠,晶莹灵动。唱了一夜的秋虫仿佛未晓白昼的登场,依旧用不会喑哑的嗓子歌颂着它并不十分明了的什么事物,它只是需要去崇拜,因此歌颂。土壤温润,残留着夜间月亮温柔呼吸所吐纳的湿润的伤感,也保存着月亮身边无数星星轻轻闪耀给土地带来的明媚慰藉。两个少女轻轻踏过草间的石板路,露珠滑落,落进了秋虫的歌声里,落进了月亮的眼眸里,落进了星星熟睡的梦乡里。
正午最后一堂课后,在何离秋所在班级的门旁,谢彦穿着干净的白色衣裙静静地等待着,她等待着总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何离秋,等待何离秋暗淡了一上午的眼睛在看到自己的一瞬间倏地变明亮。她静静地看着何离秋班上的人独自或者结伴走出,静静地躲避着男孩子炽热的目光和女孩子冰冷的白眼。她等着何离秋的手拉上自己的手,然后慢慢下楼。
食堂内的空气黏稠得不会流动,秋老虎来临的正午时走进去,感觉整个肺中装着一壶滚热的黏稠的油,烧灼得难受。两人迅速解决掉面前的饭菜,然后逃离食堂中黏稠的热浪,站在屋子外面,面朝火红的太阳吞吐干燥的空气,感觉好了很多。而后相视一笑,到小卖部买两个小豆冰棒,谢彦吃绿豆棒,何离秋吃红豆棒,两人在校园里慢慢溜达,让嘴里吮吸的冰棒慢慢融化,冰凉的甜丝丝的味道从舌尖上蔓延。
3
“何离秋!又在愣什么神?我吃好了,走吧。”
“啊?哦,好,走吧。”何离秋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撞着了身边的椅子腿,弄得椅子发出不小的声响,惹来很多抱怨的目光,她顾不得理会,快步追上走远的谢彦。
有人曾说何离秋是一条鱼。
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也就是说,每七秒钟它的记忆会更新一次,不再记得刚才发生过的事。
这样,一条鱼一辈子活在巴掌大的一缸水里,却每七秒钟都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如此,它才能活过一生而不是中途因为绝望而死去。如此,它认识不到自身的悲哀,它才不流泪,仍能盼望未来。
何离秋听着那人的评价,不置可否地默不作声。
她怎么会只有七秒钟记忆?
她都记得。
她记得那些睥睨的目光,那些视她为不洁之物的厌弃,那些讥笑和嘲讽。他们似乎看不见她的努力,她试着热情,然而被称为谄媚,试着善良,然而被说成虚伪。她记得自己做过的一切努力,也无法忘记所有的伤害。因为她记得,所以她的世界每一刻都是陈旧异常的,每一刻都充斥着悲哀。而她看似不在乎,看似将一切都忘记了,是因为她找到了走入另一个世界的魔法,那里存着她所有的幻想,还有从一旁走过的那个男孩儿的笑脸,谢彦在教室外边安静地等候,专业老师的赞许目光,让她觉得这世界仍有一部分是崭新而值得期待的。
三节晚自习之后,何离秋和谢彦一道回宿舍楼,两人年级不同,宿舍楼层也不同。何离秋上到自己这一层时整个楼道还都空荡荡的,宿舍老师听到脚步声打开了门,看到何离秋小声嘟囔了一句:“又是你第一个回来。”随后把胳膊抱到胸前,盯着何离秋进了她自己的寝室。
何离秋打开灯,屋里有一只蛾子,受惊飞起。
她坐到自己的床上,床头有本刚买的连城纪三彦的《一朵桔梗花》,她找到昨夜夹的书签读起来。
“呦,这么早回来,是一直在你自己床上坐着吗?”室友回来了,瞟了一眼何离秋。
这是一位电话女士,最近新换了一部手机和男友聊得更加起劲儿了。旧的那部手机就是在寝室里丢的,所以这段时间在寝室里说话明着暗着从来没离开
“谁是小偷”这一话题。
“嘭”的一声,厕所的老木门关上了,电话女准时坐上马桶盖,拨通了男友的号码。
“喂,嗯……想我了没……”
八卦女静悄悄地走进寝室,对何离秋夸张地做了一个“别出声”手势,把耳朵紧紧贴在厕所的木门上,眼睛眨巴眨巴,时不时地坏笑。
“哟!八卦同志,别挡路!女神归来!”马屁精咋咋呼呼的声音传进来,她用手拨拉开了八卦女。她身后是她的“女神”,十根指头上戴着五枚不同牌子的戒指,穿着学校屡次禁止的高跟鞋,昂首挺胸,真像个女王似的走进来,眼睛环视四周,随口吐出一句脏话,然后坐在自己的床上开始摆弄昂贵的手表。马屁精在她的床旁边蹲着,一个劲儿称赞她的表。
穿越女最后回到了寝室:“哎呀!今天我试了昨天查的那个用历史书穿越的办法,根本不管用嘛,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到四爷身边呢?我都想好了,我就当一个……”
“拜托闭下嘴,你看寝室里有人听你说话吗?”马屁精冷冷地说。
“我说话你管啊!我自己听,自己高兴……”
寝室中是一片混乱,各执说辞的众人将拌嘴当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何离秋无法在时刻传来的争执吵闹声中安静地读书,于是下床来穿过争吵的战场,从柜子里取出一袋牛奶,准备到床上慢慢喝下牛奶,权当打发时间,等她们安静下来。
“哎,给我一袋你的牛奶。”马屁精的女神还在玩手表,盯着那里面的齿轮说话。何离秋反应了五秒钟才明白,那一个“哎”是给自己的。
何离秋没说什么,默默地拿了一袋奶给她。
“再拿一袋给小乙(马屁精)。”她依旧没有称呼地命令着。
何离秋又拿了一袋奶,递到马屁精手上,马屁精也一样没说声谢谢。
“咦?这是什么牌子?没听说过,不行,我一喝杂牌就想吐,算了,八卦女,赏你,接着。”女神接过何离秋的牛奶,瞅了一眼商标就把牛奶往八卦女的方向扔去。因为完全没当回事,那袋牛奶像发射失败的导弹一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提前在穿越女的床下坠落了,炸开一地白花。
没有人停止玩手机,穿越女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床下发生了爆炸。
一片手机的嘀嘀按键声中,女神说:“何离秋,你愣着干什么?你牛奶洒了,还不赶紧擦?”
何离秋拿着自己那一袋牛奶,呆呆地看看地上那一大朵白花,又看看女神聚精会神调表的脸。她像刚才再拿出两袋奶时一样,默默地走出了寝室门,找来一把墩布。
那朵白花美丽极了。硕大的花瓣均匀地铺开在地面上,白色因着厚重显得十分妖艳。墩布上青色的布条扫过去,划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涟漪,晕开了花蕊,使花瓣更加舒展,白花更是与地贴得紧密了。整个墩布粘在白花上,青色渐渐吸收了白花的营养,白花一点点枯萎,青色焗上了一层白。
白花消失了,依旧没有人停止手上的动作。
何离秋放回墩布,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床上。
“何离秋!把你的手机电池给我用一下。”厕所里的电话女士高声喊着。
“哦。”何离秋答应一声,递进自己的电池。
“何离秋,一会儿熄灯以后给我你台灯啊!”八卦女挥着手里的娱乐杂志说。
在凶杀案里,凶手一般是主动的吧。
父亲在之前是主动的,而且过分主动,把女儿的主动权都用完了。那么女儿在如今只能是被动的,而且尽力被动,把父亲欠下的、占用的全部偿还。
何离秋总是以此自我安慰、释怀。
可是十五年前那一场扑朔迷离的凶杀案中,父亲果真是主动的?果真是凶手吗?
4
“哇呀呀!妃子不可以啊!”
谢彦听见莫柏在几步远的地方用他一贯的浑厚唱腔唱出这最后一句唱词,同时也感觉自己手中那把道具剑的剑刃轻轻划过了自己的喉咙,带来极其轻微的灼热感。剑光滑的表面反射着这间一号排练室屋顶若干60W节能灯的白色灯光,形成无数射向台下的光束。
有一束光晃到了在台下用牙齿咬着嘴唇的何离秋,于是她用手背揉揉细长的眼睛。等她的目光再次聚在舞台上时,谢彦和莫柏已经保持了五秒钟的结束姿势。
那顶金灿灿的虞姬冠上的垂坠随着谢彦的呼吸有规律地摆动着,湖蓝色的虎头鱼鳞甲因为有黄绸缎彩绣古装上衣和明黄绣金凤戏牡丹镶边长斗篷的衬托,愈显得颜色清澈。那柄假剑在地上,谢彦因无力而垂下的手中仍握着剑柄。莫柏有力的手臂负担着谢彦的重量,他穿着黑色厚底靴,靴底完全贴在地面上。
一种叫人不敢呼吸的悲伤从舞台上蔓延到各处,安静得如同绿色植物的藤蔓包裹住整个排练室。
何离秋的思绪还在戏的悲伤气氛中,专业老师老骆的大嗓门却已经响起来:“好!像个样子!行了,今天练到这儿。对了,前些天我说过的八校联演现在有确切消息了,就是三个月以后,大家都好好准备,两星期之后我要确定演出剧目和人员。我们青城戏剧学院附中在两年一次的八校联演上最次也是第二名,你们可不能让我丢脸啊!行了,下课。”
老骆迈着老人独有的鸭子步穿过排练室的门,身后的人一拥而出。何离秋想该等等谢彦,好问问她要不要去食堂。于是她找到化妆室外的一个角落等着,看着窗外的阳光俯角越来越小。小化妆室里有轻声的说话声,是谢彦和莫柏。
集体排练结束的傍晚,青城戏剧学院附中黑色的铁栏杆被云层中麻雀的翅膀所剪开的太阳余晖镀上了一层金色。暗红色的教学楼静静伫立,楼体拐弯处形成的逼仄的小空间里,有一株矮小的玉兰树孤独地立着。校园的小路边种着成排的梧桐树,初秋,树叶还没有落尽,叶子在傍晚的凉风中享受着晚年的清闲,跳着益寿迪斯科。而梧桐树下的人呢,同每次上文化课放学时不同,不仅有情侣,还有一人独行或者三人成伙的。何离秋想起一句不知在哪里读到的话:“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三个人怕孤立。”她对这话倒并没有什么认同感,一个人的她很好,她迁就孤独,所以孤独并不恼她;两个人时,她迁就对方,也就从不怕对方辜负。何离秋不喜欢黄昏,每次黄昏她总堵不住记忆的堤口,不小心就让过去了的夏花冬雪、春雨秋叶决堤般倾泻而出,重新左右她当下的喜怒哀乐。何离秋试着重启自己的大脑,不去回忆讨厌的黄昏。
重启成功。何离秋站起身,二十分钟了,她该让谢彦知道她在等她。她轻轻走到化妆室门口,“谢彦?”她大声喊。
“离秋,你怎么在这儿?”谢彦小心地掀开蓝灰色布帘,只露出一张已经卸了妆的脸,“你怎么没去食堂?”
“我……”何离秋吐出一个字,又咬住了嘴唇。
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莫柏出了化妆间,直接拉开了帘子,两个人明明都已经换下了戏装,卸过了妆。
“何离秋等你呢,那你快去吧,咱们改日再聊。”莫柏看着谢彦笑着说。
“哦,那好,改日见。”谢彦走出化妆间,伸手拽住了何离秋的袖口。
“那,拜拜。何离秋,怎么等到了谢彦连个招呼也不和我打就走?”莫柏看着两个女孩儿的背影说。
“哦,拜拜。”何离秋想回头看一眼莫柏的脸,好确认他的脸上是否有那熟悉的笑容,好知道那个小本上是否应再添一个小勾,但是谢彦拽着她的衣袖径直向往前走去。
出了教学楼的门,谢彦松开何离秋的衣袖快步往前走。何离秋追上谢彦,扯住了她的衣角不放手。
“好彦儿,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你没让我等我就不等你了,行吗?今天就别生我气了!都是我这个姐姐不好,我以后不自作主张关心你了行吗?”
谢彦的脚步缓了。
“好彦儿?”
“行,以后等我这类事情你先问问我,记着了。”
何离秋小心地挽上谢彦的手臂,和她肩并肩行走成为两人结伴的风景,何离秋想起来刚才想到的“两个人怕辜负”,笑了笑,秋风吹进她的齿缝里。
“离秋,明天早上你先走吧,不用等我了。”谢彦说。
5
不用等谢彦,何离秋是第一个到排练室的人。排练室在一条长走廊的尽头,楼道两面的墙上爱迪生和梅兰芳被面对面挂在一起,两双杰出的眼睛似乎都正盯着何离秋,何离秋一恍惚,不禁心一颤,赶紧低下头不去看那两幅画像。
“离秋!这么早就到了。”是老骆,气喘吁吁但是依旧响度巨强的声音。
“老师好。”何离秋退到门边上,等待老骆打开排练室的门。
老骆边往这边迈着鸭步边说:“何离秋啊,你最近有进步,戏剧中感情处理一直是你的大难点,最近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那个八校联演你是怎么考虑的?”
“嗯,也没什么打算,看看再说。”
“这种事啊你得努力争取。我带的学生除了谢彦也就是你了,虽然悟性略差了些,但还是蛮不错的,多练练。谢彦还小,你已经高三了,我会酌情考虑的。”
“好,老师,我知道了。”
“对了,”老骆打开了门,“这一次选演员校长打算试着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候选人由老师定,你要考虑这方面,我听说你的人缘儿可不是很好。这次比赛可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知道了,老师。”
老骆打开了门,自己迈着鸭子步去走廊另一边的洗手间了,何离秋一个人进了排练室。
排练室里空荡荡的,四周的墙上有更多看着何离秋的杰出眼睛。何离秋走到单杠前头,提前开始压腿。
“争取机会,争取机会。”她在嘴里轻声念叨着,“多下工夫,多下工夫。民主选举,民主选举?”
何离秋停住了,心中充斥着失望,但是,也还有一点点兴奋。
开始有人陆陆续续进入排练室了,说话的声音、吊嗓子的声音很快塞满这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老骆进来了,看看有十五六人的教室,拿出点名册。
“何离秋?何离秋来了吗?”
“到,老师,在这儿。”何离秋疑惑老骆为什么问自己是否来了,难道老骆不记得刚刚和自己的那一番对话吗?
点名继续。
“谢彦,谢彦?何离秋,谢彦在哪?”老骆的声音音调像坐着电梯,越来越高。何离秋正犹犹豫豫不知怎么回答,门口传来了声音。
“老师,在这里。”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门口。
黑色长发披了下来,整齐地垂在腰间。像牛奶一样白净的皮肤上嵌着艺术品似的五官——这都是大家常见的。令大家惊讶的是谢彦身着一条莲花般的白色长裙,七分袖口上缀着同色丝绸质地的蝴蝶结,裙摆飘逸,使谢彦款款走进来的时候宛如仙女一样飘逸脱俗、纯净完美。
教室里没有说话声了,老骆看着谢彦,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何离秋回过头,看见莫柏的目光亦同所有男生一样,望着门口的谢彦,轻声叹了口气,低头看看自己的手。
看来有人早知道了这次是民主选举。
“进来吧,谢彦。”老骆说,大嗓门把大家的目光扯了回来,“我们继续点名……”
谢彦轻轻走进来,还有男生时不时偷偷地瞟一眼她。她走到何离秋身边站定,等待老骆念完最后的三个名字。何离秋侧过脸,凑到谢彦耳边说了一句漂亮,谢彦也轻声回了一句谢谢。
下课后两人一起吃早餐,坐在长桌的一头,老地方,老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