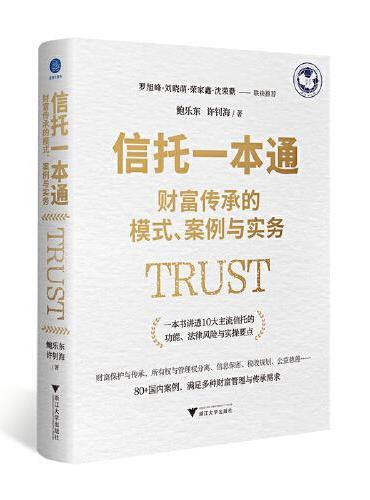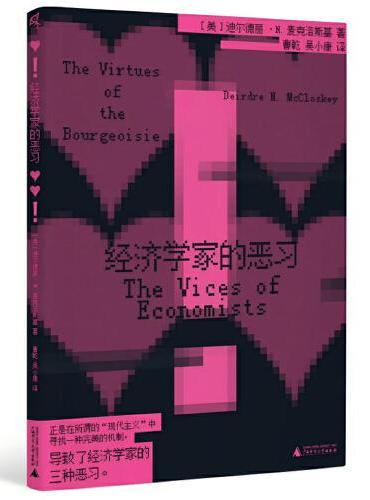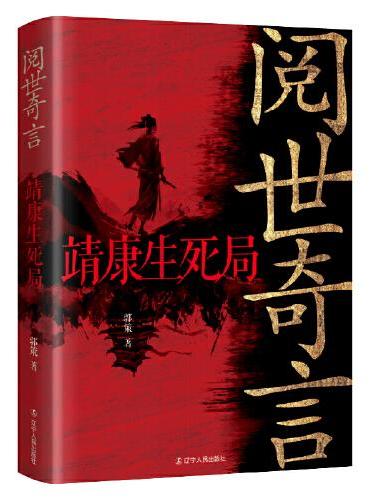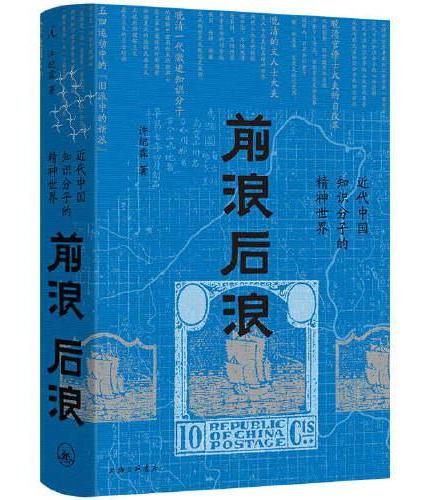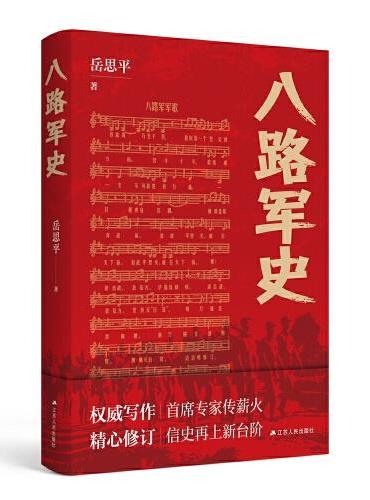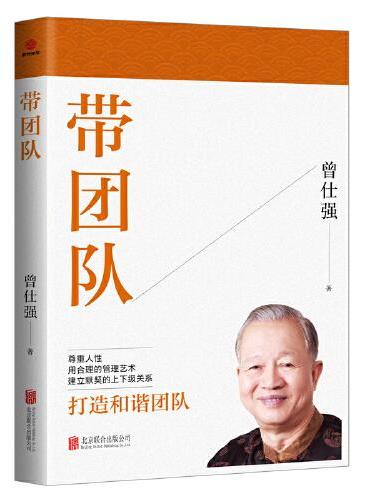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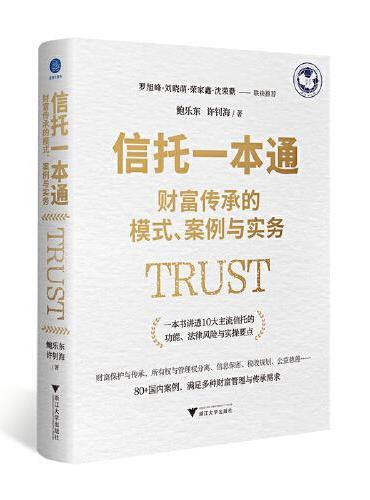
《
信托一本通:财富传承的模式、案例与实务(丰富案例+专业解读,讲透10大信托业务功能、法律风险与实操)
》
售價:NT$
500.0

《
AI绘画:技术、创意与商业应用全解析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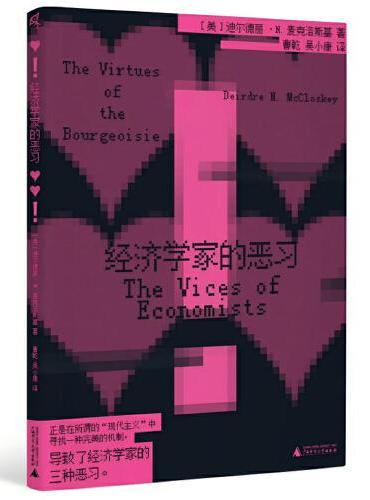
《
新民说·经济学家的恶习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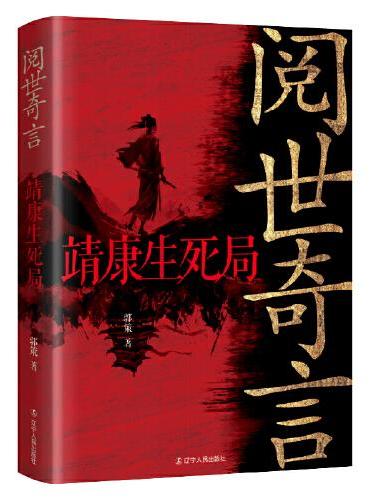
《
阅世奇言:靖康生死局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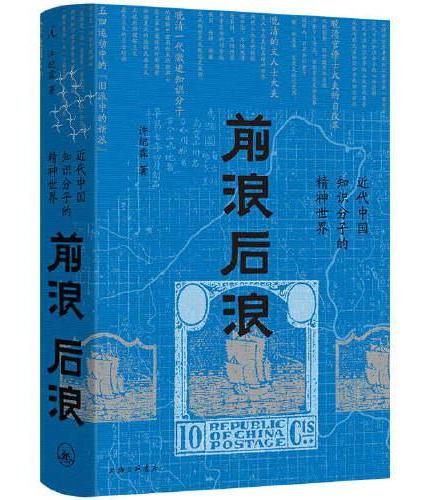
《
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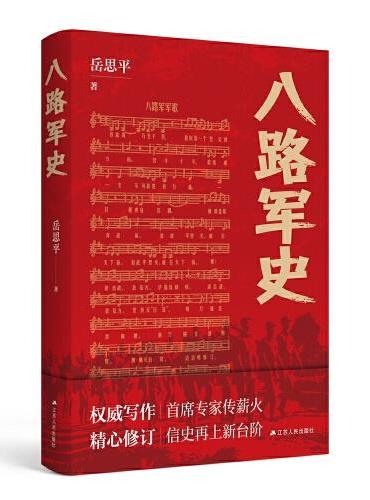
《
八路军史
》
售價:NT$
500.0

《
美味简史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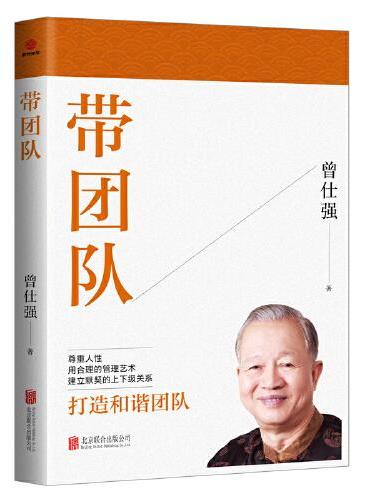
《
带团队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铁伊是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作家之一被誉为“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 八部长篇,部部经典
她的作品在CWA票选百部经典侦探小说中排名第一
在MWA票选百部经典侦探小说中排名第四朱天文,朱天心,詹宏志,唐诺,止庵,小宝推崇的侦探小说大师
|
| 內容簡介: |
|
长着一张俊美的脸的莱斯利?瑟尔突然出现在平静的英国小镇圣玛丽,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不同寻常的感觉,也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瑟尔的蓦然失踪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就连老练的格兰特探长也如坠五里雾中,找不到案件的任何线索……
|
| 關於作者: |
约瑟芬·铁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侦探小说史上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和她齐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都是产量惊人的作家,铁伊却穷尽一生之力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八部水准齐一的好小说。她写作没有推理公式可循,每一部小说都有其各自独特的风貌。她的笔法妙趣横生,文风冷静优雅。被誉为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
铁伊的代表作《时间的女儿》,是推理小说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被称为历史推理小说之最,正面攻打一则几乎不可撼动达四百年的历史定论,比绝大多数的正统历史著作更加严谨磊落,在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史上百大推理小说中名列榜首,在美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的百大推理小说中位列第四,而前三名分别是《福尔摩斯全集》、《马尔他黑鹰》和《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除《时间的女儿》外,铁伊另有两部作品入选,分别是《法兰柴思事件》和《博来特·法拉先生》。
|
| 內容試閱:
|
1
格兰特一脚停在最底层的台阶上,听着上方门内传来的尖叫。此外,还有阵阵低沉的大笑,以及像森林失火或洪水暴涨般的巨响。他双腿不情愿地往上抬,不由暗想:聚会果然很成功。
他不是来参加聚会的。文学聚会,即便是那些声名远扬的,都不是他的所好。他来接玛尔塔·哈拉德小姐去共进晚餐。的确,警察不常跟海马基特和老维克剧院的当红女星共赴餐会,就算身为苏格兰场的探长也不例外。格兰特能享此殊荣,可以说有三个理由,对此他心知肚明:其一,他是个撑得起门面的护花使者;其二,他上得起劳伦特这种餐厅;其三,哈拉德小姐发现找护花使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男人们怯于她的地位和美貌,总是有些望而生畏。于是,当格兰特——一个纯粹的警探,因一起珠宝失窃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她便觉得不能让他再完全消隐。而格兰特也乐得如此。如果说格兰特在玛尔塔有需要的时候适于充当护花使者,那玛尔塔则更适于作为格兰特观察世界的窗口。警察拥有的“窗口”越多,干起工作来就越得心应手,而玛尔塔正是格兰特在文艺圈“难得的眼线”。
聚会的欢腾声从敞开的门内奔涌而出。格兰特停在门厅,看着吵吵嚷嚷的宾客,琢磨着该如何把玛尔塔直接找出来,这些人将乔治王风格的长形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
就在门内,立着一个神情茫然的年轻人,很明显被眼前高谈阔论、开怀畅饮的局面弄糊涂了。帽子还在手中,看来他也刚刚来。
“有麻烦吗?”格兰特看着对方,问道。
“我忘记带扩音器来了。”年轻人回答。
他声音温温吞吞,没有刻意扯着嗓子压过周遭的嘈杂,这种音调的差异,反而让他的话清晰可闻,远强于大喊大叫。格兰特又瞥了他一眼,颇为欣赏。说到引人注目,这年轻人确实相貌英俊。看那一头惹眼的金发,不太像个地道的英国人。挪威人,或许?
或者美国人。他说“忘记”这个词的时候,带点儿美国腔。
初春的傍晚,暮色微笼,灯火已亮。透过烟雾,格兰特看见了屋内远处的玛尔塔,她正在听剧作家塔利斯谈论版税收入。格兰特不用听,也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除了版税他就不会聊别的。塔利斯会告诉你——漫不经心地——一九三八年的复活节周一,在黑泽,上演他的作品《三人晚餐》为第二公司带来了什么效应。玛尔塔甚至都不愿做样子假装在听了,耷拉下嘴角。格兰特心想,如果那位女爵士再不快点现身解围,玛尔塔一味沮丧,就需要做脸部除皱了。他决定待在原地,等着她发现自己——他们俩都很高,足以越过攒动的人头看到对方。
出于警察的职业习惯,格兰特扫视了一遍周遭的面孔,但没发现什么感兴趣的情况。这不过是个寻常的聚会,经营有道的罗斯与克罗默蒂出版社正在庆贺拉维尼亚·菲奇第二十一部作品的面世。出版社的兴旺主要归功于拉维尼亚,正因为如此,聚会上酒水丰足,宾客也都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不同凡响的衣饰和知名度。可是,这些贵宾出席,并不是为了庆贺《莫琳的情人》的出版,也不是为了来喝罗斯先生和克罗默蒂先生的雪利酒。即使是玛尔塔这位贵妇人,她来这里也只因为自己是拉维尼亚在乡间的邻居。玛尔塔,多亏了她那时髦的黑白装扮和不悦的表情,成了满屋子里真正与超凡脱俗最沾边的人。
当然,除非他不认识的这个年轻人为聚会奉上的不仅仅是出众的相貌。他琢磨着这陌生人是做哪一行的。演员?可演员不至于在热闹的场合显得茫然无措。还有,他刚才说“扩音器”的含蓄语气,以及打量环境的疏离表情,都有些蹊跷,将他与周遭的环境区隔开来。格兰特想,他说不定是个股票经纪人,只是浪费了那副俊俏的容貌?又或者他在白天看来根本没这么英俊,只是出版社柔和的灯光美化了那英挺的鼻子和直顺的金发?
“或许你能告诉我——”年轻人说话依然不急不躁,“哪一位是拉维尼亚·菲奇小姐?”
拉维尼亚·菲奇就是中间窗户旁那位沙色头发的娇小女士。她为今天这个场合买了顶时髦的帽子,可是没花心思作搭配,因此帽子戴在她那如鸟窝般的沙色头发上,就仿佛是她沿街走过,它从上面的窗户掉下来正好落在她头上一样。她没有化妆,如往常一样显出欣悦的迷茫之态。
格兰特把拉维尼亚指给年轻人看。
“刚到镇上?”他借用了西部片中常用的一句问话。“拉维尼亚小姐”这种礼貌用语只能出自美国人之口。
“我其实是想找菲奇小姐的外甥。我查了地址簿,没找到他的名字,希望在这里可以碰上。或许你认识他,对了,你是……”
“格兰特。”
“格兰特先生?”
“我能认出他,但他不在这里。沃尔特·惠特莫尔,你说的是他吧?”
“正是。惠特莫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很想见他,因为我们有——我是说,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他应该在这儿。你确定他不在?毕竟,这是个热闹的聚会。”
“他不在这屋子里。他和我一样高,我能确定。不过,他或许就在附近。瞧,你最好先去问问菲奇小姐。我们下个狠心,就能穿过这人墙了。”
“你带路,我跟着。”年轻人说,暗指他们各自的体形。两人被众人的胳膊肘和肩膀紧紧夹着,中途缓口气时,他说:“真是谢谢你,格兰特先生。”然后仰头朝动弹不得的格兰特揶揄一笑。格兰特顿觉窘迫,赶紧转身,继续在人群中奋力开路,朝中间窗户边拉维尼亚小姐所站的空处挤去。
“菲奇小姐,”他说,“有个年轻人想见你。他正在找你的外甥。”
“找沃尔特?”拉维尼亚说。她尖尖的小脸上,惯常那亲切的茫然神情一扫而光,露出好奇的神色。
“我叫瑟尔,菲奇小姐,从美国来,正在度假。我想找沃尔特是因为我们都是库尼·威金的朋友。”
“库尼!你是库尼的朋友?哦,沃尔特一定会很开心,亲爱的,他会高兴坏了!哦,真是个惊喜,在今天这个——我是说,太让人意外了。沃尔特会乐坏的。你说你叫瑟尔?”
“是的,莱斯利·瑟尔。我在地址簿里找不到沃尔特的名字——”
“哦,他在这里的住处是临时的。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住在萨尔科特圣玛丽镇。你知道,他在那里有个农场,就是他宣传的那个农场。其实那是我的农场,他替我经营和推广——今天下午他又得上电台,所以没来这里。可是,你一定要来住一住。就这个周末吧。今天下午直接跟我们一起回去。”
“可你知道沃尔特是否——”
“你这个周末没有别的安排,对吧?”
“是的,是的,没有,不过——”
“那就没问题了。沃尔特会直接从播音室回家,你就跟莉兹①和我一起坐我们的车回家,给他一个惊喜。莉兹!莉兹,亲爱的,你在哪儿?瑟尔先生,你现在住哪里?”
“威斯特摩兰。”
“哦,那很近。莉兹!莉兹在哪儿?”
“这里,拉维尼亚姨妈。”
“莉兹,亲爱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莱斯利·瑟尔先生,会和我们一起过周末。他要找沃尔特,他们俩都是库尼的朋友。今天正好是星期五,我们本来就要去萨尔科特镇过周末缓缓劲儿,我们已经被这儿——去过一个清静安宁的周末,反正一切都会很美好。这样吧,莉兹,你开车载他回威斯特摩兰拿行李,再过来接我,好吗?到时,这——这聚会应该结束了,你接上我,我们一起回萨尔科特镇,给沃尔特一个惊喜。”
格兰特发现,年轻人看着莉兹·盖洛比的时候脸露兴味,不禁有些纳闷。莉兹是个相貌平平、脸色发黄的娇小女孩。没错,她长着一双迷人的眼睛,婆婆纳草的那种蓝,令人惊诧;她那种面容,也是男人可能会想长期相处的。莉兹,好女孩。可她并不是普通小伙子一眼就能看上的那种女孩。或许,瑟尔听到了她的订婚传言,这会儿正在估摸她可能就是沃尔特·惠特莫尔的未婚妻。
他注意到玛尔塔发现了自己,便没什么兴趣再琢磨菲奇家的家务事了。他示意在门口和她会合,然后又一次扎进令人窒息的人群中。玛尔塔可比他勇猛多了,隔的距离虽然远一倍,用的时间却只有他的一半,早就在门口等他了。
“那位漂亮的年轻人是谁啊?”走向门口的台阶时,她还边回头边问格兰特。
“他来找沃尔特·惠特莫尔,他说他是库尼·威金的朋友。”
“他说?”玛尔塔重复道,语带讥讽,但针对的是格兰特,而不是那位年轻人。
“职业习惯。”格兰特讪讪地说。
“好吧,库尼·威金又是什么人物?”
“库尼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新闻摄影家,一年或两年前在巴尔干半岛的一次冲突中拍摄照片时遇难。”
“你真是无所不知,对吧。”
格兰特差点脱口而出:“全天下大概只有你这个女演员不知道这事吧。”但他喜欢她,说出口的却是:“我想,他要去萨尔科特镇度周末。”
“那位漂亮的年轻人?哦,好吧,希望拉维尼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带他回去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但他们似乎在拿自己的运气冒险。”
“运气?”
“他们的生活好不容易才算如愿,不是吗?沃尔特从玛格丽特·梅里亚姆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安下心要和莉兹结婚,一家人在老农场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再和美不过了。依我看,这时候可不适合带这么一个美得让人不安的年轻男人回家。”
“不安?”格兰特咕哝着,又开始琢磨刚才瑟尔为什么会让自己不自在。不可能纯粹因为俊美的外表。警察不会单凭相貌好看就疑神疑鬼。
“我敢打赌,埃玛只要瞧他一眼,就会在星期一的早餐后把他赶走。”玛尔塔说,“她的宝贝女儿莉兹马上就要嫁给沃尔特了,她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诸事顺利。”
“我看莉兹·盖洛比不是个容易动摇心意的人,盖洛比太太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当然这么看。可我站在二十码外,不到半分钟的工夫就被那年轻人吸引住了,我还是公认的难以动情之人呢。况且,我从来都不觉得莉兹真的爱上了那家伙,她只是想修整他那颗破碎的心。”
“他很伤心吗?”
“应该说,伤得很重。很自然的事情。”
“你和玛格丽特·梅里亚姆同台演出过吗?”
“哦,是的,不止一次。我们曾为《漫步黑暗中》合作过很长时间。出租车来了。”
“出租车!你觉得她这人怎么样?”
“玛格丽特?哦,她根本就是个疯子。”
“怎么个疯法?”
“彻底的疯。”
“哪一方面?”
“你是指她哪里不对劲吗?为了抓住眼前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可以不顾一切!”
“那不叫发疯,那是一种潜在的犯罪心理。”
“哦,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或许她真的是个潜在的犯罪者。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她疯得像个制帽工;就算是沃尔特,我也不希望他因娶她而坠入厄运。”
“这个大家公认出色的英国年轻人,就这么不招你喜欢?”
“亲爱的,我讨厌他抒情的方式。他向往着爱琴海小山丘上的百里香,同时子弹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这实在够糟了——他从不放过让我们听子弹声的机会,我一直怀疑他在不停地挥鞭子制造出那声音——”
“玛尔塔,你吓着我了。”
“才没有,亲爱的,一点也没有。你和我一样清楚!当我们都有中弹的危险时,他可是小心安稳地待在地下五十英尺闷热的办公室里。等到又一次可以孤身涉险以显得与众不同时,他就从那安全的小办公室里跳出来,坐在百里香山丘上,手拿麦克风,用鞭子制造子弹声。”
“我看总有一天我得把你从监狱里保释出来。”
“因为谋杀罪?”
“不,是恶意诽谤。”
“你确定要保释?我原以为,你只会因为那些体面的事被传唤到法庭。”
格兰特暗想,真是拿玛尔塔的鲁莽没办法。
“或许还是谋杀罪吧。”玛尔塔若有所思地柔声说,用的是她在舞台上的标志性嗓音,“尽管我还能忍受百里香和子弹,可是他永远占着广播台聊什么春玉米、啄木鸟这类东西,根本就是公众危害嘛!”
“那你干吗听他的广播?”
“嗯,你知道,那是一种可怕的魔力。你会想:没错,广播糟糕极了,不可能再糟了。但是,下个星期你还是会收听,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更糟。这是个陷阱,很恐怖,你根本无法抽身。你着迷地等着下次、再下次更糟的表现,而当他的声音消失时,你居然还愣在那里。”
“不可能吧,怎么会,玛尔塔,这只是同行相轻吧?”
“你说那家伙是我的同行?”玛尔塔问道,声音漂亮地降了五度,恰如其分地微微带颤,显出怀旧意味:上演轮演剧目的岁月,外省的寄宿房间,周日的列车,又冷又暗的剧院里枯燥的试演。
“不,我是说他算得上是个演员,一个自然而然、率性而为的演员。这些年他根本没有刻意经营,却几乎变得家喻户晓。你不喜欢他倒没什么,玛格丽特到底迷上了他哪一点呢?”
“我可以告诉你,是他的忠诚。玛格丽特喜欢撕掉飞虫的翅膀,沃尔特则心甘情愿让她撕成几片,还会回来求她继续。”
“可最终他再也不回来了。”
“没错。”
“最后一次矛盾因什么而起,你知道吗?”
“我看没什么矛盾。他只是告诉她不想再那样下去了,至少他在接受问讯时是这样说的。对了,你看过她的讣告吗?”
“当时应该看过,但记得不是很清楚。”
“如果她能多活十年,就可以在报纸的后页广告栏中占据一小块相匹配的版面,证明她比杜丝更受关注。‘天才的陨落,世界的损失’、‘轻盈如起舞的叶片,优雅如摇曳的垂柳’,诸如此类。大家都很惊讶报上竟然没有黑边,而这种哀悼本该是国家级的。”
“经历了那些,再和莉兹·盖洛比牵手,这中间的差异可大了。”
“哦,好女孩莉兹。如果说玛格丽特·梅里亚姆就算配沃尔特·惠特莫尔也差了一大截,那莉兹配沃尔特·惠特莫尔就多出一大截。配他绰绰有余。那位漂亮的年轻人真要从他眼前把莉兹抢走,我真该高兴。”
“怎么说呢,我看不出你那位‘漂亮的年轻人’会是个好丈夫,但沃尔特却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我的好人儿,沃尔特会到处嚷嚷的。有关他们孩子的一切,他在餐室里摆设的架子,娇小妻子隆起的肚子,育婴室窗户上的霜花……相反,她则会安稳多了,要是跟——你说那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瑟尔,莱斯利·瑟尔。”他心不在焉地看着越来越近的劳伦特餐厅淡黄色的霓虹灯招牌,“我可不觉得‘安稳’是个适合形容瑟尔的词。”他若有所思地说。但从这一刻起,他就把莱斯利·瑟尔的一切抛到了脑后,直到有一天接获任务去萨尔科特圣玛丽镇搜寻这个年轻人的尸体。
2
“瞧这天气!”莉兹说着走到人行道上,“好晴朗!”她惬意地吸了口傍晚的空气,“车子停在广场的拐角处。你对伦敦熟吗,瑟尔——先生?”
“我常来英国度假,算是熟了。只是这么早的季节倒是不常来。”
“如果没在春天来过英国,就不算真正到过英国。”
“听说过。”
“坐飞机来的?”
“刚从巴黎飞过来,美国人一般都这样。巴黎的春天也很美。”
“听说过。”她回了句——同样的话,同样的语气。然后,发现他那双慑人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看,她又说:“你是个记者?在工作中结识库尼·威金的?”
“不是,我跟库尼只是同行。”
“新闻摄影师?”
“和新闻无关,就是个摄影师。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西海岸,拍人物。”
“西海岸?”
“加利福尼亚。这是我固定的经济来源。另外半年我四处旅行,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听起来是不错的生活方式。”莉兹说着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的确很不错。”
车子是双人座的劳斯莱斯,就这个品牌而言款式有点过时了,可是经久耐用。莉兹把车开出广场驶入傍晚的车流时,还解释了一番。
“拉维尼亚姨妈赚了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条貂皮披肩,她一直认为貂皮披肩是最美的服饰。她想要的第二件东西就是劳斯莱斯轿车,在出版第二本书时实现了心愿。可她一次也没用过那条披肩,说身上成天吊着个东西实在心烦。不过劳斯莱斯轿车倒是买对了,我们到现在还开着。”
“那条貂皮披肩怎样了?”
“她拿去换了一套安妮王后时代的椅子和一台割草机。”
车子在旅馆门口停下,莉兹说:“他们不会让我把车停在这儿等人的,我去那边的停车场等你吧。”
“你不上去帮我收拾行李吗?”
“帮你收拾?当然不了。”
“可你姨妈是这么说的。”
“那只是客套话而已。”
“我可不这么想。无论怎样你也上去瞧瞧吧,看着我收拾就行了。指点指点,给些心理安慰。美妙的心理安慰。”
事实上,最后还是莉兹帮他收拾好两个行李箱,他只是从抽屉里把衣物拿出来往她手上一塞。她注意到衣服都很昂贵,应该是用一流的质料量身定做的。
“你很有钱,或者纯粹就是好奢侈?”她问。
“这么说吧,只是比较挑剔。”
他们离开旅馆的时候,街灯已经亮起来了,和暮色交相辉映。
“我觉得这时的灯光最美,”莉兹说,“衬着傍晚的天色。晕晕黄黄的,真迷人。等到天真的黑了,灯光就会变得惨白,显得平常了。”
他们开车回到布鲁姆斯伯里,却发现菲奇小姐已经走了。出版社的罗斯先生累得瘫软在椅子上,一边默默思索着聚会的效果。他站起身,勉强摆出职业人的友好态度,告诉他们菲奇小姐已经去了沃尔特的播音室找他,她觉得可以在他结束播音后搭他的车回去,而盖洛比小姐和瑟尔先生可以随后开车回萨尔科特圣玛丽镇。
他们离开伦敦市区的一路上,瑟尔都没怎么说话。以免干扰驾驶,莉兹暗想,由此对他生出几分好感。直到绿野在车窗两边展开,他才开口聊起沃尔特的事。看来,库尼没少想起沃尔特。
“你那时候没和库尼·威金一起待在巴尔干吧?”
“没有。我和库尼是早先在美国认识的,但他在信里经常提起你表哥。”
“他真好。不过你误会了,沃尔特并不是我表哥。”
“不是?可菲奇小姐明明是你的姨妈,对吧?”
“不是,我和他们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在我很小的时候,拉维尼亚的姐姐——埃玛——嫁给了我父亲。就这么回事。老实说,我母亲——就是埃玛,把我父亲给‘困住’了。他别无选择。你知道,埃玛一手带大了拉维尼亚,拉维尼亚长大后却有了自己的生活,这对她真是个可怕的打击——尤其拉维尼亚还这么古怪,偏偏成了畅销作家。她放眼四周,看看有什么别的事能插上手好转移情感,结果就遇上了我父亲,他还被一个幼小的女儿牵绊着,只等着就范。因此她就成了埃玛·盖洛比太太,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把她当继母看,因为我对我的生母一点印象都没有。父亲去世后,她就带着我到崔明斯庄园跟拉维尼亚姨妈一起生活。我毕业后接过了她的秘书工作。就这样,我才会出现在这里为你收拾行李。”
“那沃尔特呢?他又是什么身份?”
“他是她们姐姐的儿子。他的父母在印度去世了,拉维尼亚姨妈从那时起就开始照顾他,大概十五岁的时候吧。”
他沉默了好一阵,显然是在消化这一连串信息。
莉兹不禁纳闷,她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她为什么要跟他提到她母亲的占有欲?即便她说得很清楚,她母亲是出于爱意才那样的。是她太紧张了吗?可她从来不会紧张,从来不会方寸大乱。况且有什么好紧张的?面对英俊的异性,她绝对不会不自在的。不管是作为莉兹自己还是身为拉维尼亚的秘书,她遇到过不少长相好看的年轻人,不过还没对谁有过特别的印象(就她记忆所及)。
车子从黑色的柏油主干道转到一条岔道上,最后一抹城区的开发痕迹消失在身后,现在他们已完全置身乡间。一条条小路弯弯曲曲、纵横交错,既没标路牌又看不分明。莉兹娴熟地把握着方向。
“你怎么知道该走哪条路?”瑟尔问,“这些土路看起来都差不多。”
“看起来是差不多,可这条路我走得太多了,闭上眼睛都知道该怎么走,就像手一摸打字机就知道该如何按键。我总不能先想一下哪个键在哪儿,事实上手指自己就能找到正确的位置。你知道这儿吗?”
“不知道,新鲜的地方。”
“真是很乏味的乡村,毫无特色可言。沃尔特说这里就是七根‘柱子’的一连串变换排列:六棵树加一个干草堆。事实上,他说这里的部队在行军时还会唱上一句,相当平白:六棵树和一个干草——堆。”她唱给他听了,“你看到路上那个隆起的地方了吗,那边就是奥福德郡,看着就舒服多了。”
果然,奥福德郡铺陈出一片赏心悦目的乡野。随着暮色渐浓,它的轮廓线流动着,交融出一幅幅如梦似幻的美景。此刻,他们停在一个小山谷边,俯望着村里黑糊糊的屋顶和点点灯火。
“萨尔科特圣玛丽镇,”莉兹介绍道,“一个曾经美丽的英国小镇,现在却成了占领区。”
“被谁占领?”
“被当地人口中所谓的‘那帮艺术人士’占领。对那些可怜的人来说,这事可真悲哀。他们把拉维尼亚姨妈算作了自己人,因为她占着那幢‘大房子’,而且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她在这里住了那么久,几乎算得上是个本地人了。近百年来,大房子并不算是村庄的一部分,因此谁住里面都无关紧要。这地方的衰败是从那幢磨坊屋的不景气开始的,有家公司打算把它买下来盖工厂——就是改造成工厂。后来玛尔塔·哈拉德听说了这事,就在好些律师的鼻子底下,把它买下来住了进去。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被拯救了。他们并不是很乐意让一个女演员住到磨坊屋来,可这总好过让一个工厂进驻他们美丽的村庄吧。可怜的人们,他们要是能预见这些事就好了。”
她开着汽车缓缓驶下斜坡,沿着村庄边缘前行。
“我猜当初不出六个月,从伦敦到这里就踩出了一条小路。”瑟尔说。
“你怎么知道的?”
“这种事情我在西海岸见多了。只要有人发现一个清净的地方,他们还没来得及装设水管安顿下来,就得要投票选市长了。”
“是啊,这里每三户之中就有一户是外地人。有钱的或没钱的,什么经济条件的都有,比如托比·塔利斯——那个剧作家,你知道,在村里的中央大街上有幢非常迷人的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别墅,而舞蹈家瑟奇·莱托夫就只能住在改造过的马厩里。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比如迪尼·帕丁顿家每个周末出现的客人都是新面孔,那个可怜的老亚特兰大·霍普跟巴特·霍巴特一直都在同居,愿上帝保佑他们。当然也有各种才华横溢的高人,比如赛拉斯·威克利,他写那种以乡间生活为主题的恐怖小说,什么热气腾腾的粪肥啊,狂暴的雨啊,还有伊斯顿-迪克森小姐,她每年都为圣诞节写本童话故事。”
“听起来很有趣。”
“很恶心呢。”莉兹说,语气之激烈让她自己都吃惊,继而又纳闷这个傍晚自己为何会如此情绪失控。“提到这些恶心的事,”她收回心神,继续说道,“我想天已经太黑,你没法好好看看崔明斯了,不过明天欣赏它的风韵也不迟,天光大亮的时候可以看个清楚。”
年轻人看着夜色中的尖塔雕饰和垛口,莉兹等着。“这里的特色珍宝是那座哥特式艺术学校,可惜天色太暗看不清楚。”
“菲奇小姐为什么会选择这里?”瑟尔不解地问。
“因为她觉得这里有气派。”莉兹柔和地说,声音里透着爱意,“她是在教士住宅区长大的,你知道,就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盖的那种房子,所以她一直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即使到现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她即使知道别人在取笑她,也根本不在乎,事实上她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她第一次带科马克·罗斯——她的出版商——来这里的时候,他恭维她房子的名字取得贴切,她却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唔,我没有那个意思,就算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也没什么意见。”年轻人说,“菲奇小姐真是太热情了,事先都不打探一下我的来历,就邀请我来这里。不知怎么的,在美国,大家都认为英国人比较谨小慎微。”
“这和英国人的疑心无关,而是关乎家庭开支。拉维尼亚姨妈没多想就请你来做客,是因为她根本不用操心这类家务事。她知道家里吃的住的都没问题,还有足够的人手把客人伺候得舒舒服服,因此根本没什么好顾虑的。我们直接绕到车库那里停车,然后从边门把你的行李拿进去,你不介意吧?从前门进的话,得走上大半天才能到内屋,因为中间很不幸地隔着那个宽阔的大厅。”
“这是谁建的?又为了什么?”汽车绕着房子行驶的时候,瑟尔盯着这庞大的建筑问道。
“布拉德福德的一个家伙,我听说的。这里以前是一幢很美的乔治时代的房子,枪械室里还留存有当时的一张照片呢,可他觉得很丑,就把它拆了。”
最终,瑟尔拎着行李走进一个过道,阴暗逼仄;莉兹说这过道总让她想起寄宿学校。
“就把东西放那儿吧,”她指了指一道小楼梯,“一会儿有人会拿上去的。现在要进入文明世界了,喝点东西暖暖身子,见见沃尔特。”
她推开一扇绒面门,带他进入房子的前部。
“你溜冰吗?”穿过空旷的大厅时,瑟尔问她。
莉兹说她从没想过溜冰这回事,不过这地方倒是挺适合跳舞。“本地猎人每年都会使用一回这个场地,但你可能想不到,这里其实比威克姆的谷物交易所还不通风。”
她打开一扇门,两人终于脱离奥福德郡灰蒙蒙的旷野、屋内黑糊糊的过道,融入了客厅内的温暖、火光与亲和当中。屋内摆满经久耐用的家具,弥漫着原木的燃烧味和水仙的清香。拉维尼亚沉陷在椅子里,小巧的双脚搁在铁炉架上,蓬松的头发从发夹里滑出散在椅背上。她对面的沃尔特·惠特莫尔,一只胳膊肘撑着壁炉台,一只脚搁在壁炉架上,非常惬意的样子。莉兹看到她,心里顿时涌起爱意,同时也松了口气。
为什么会觉得松了口气?她听着他们彼此寒暄,暗暗问自己。她本来就知道沃尔特在这里,为什么会觉得松了口气呢?
就因为她现在可以把这个应酬的负担交给沃尔特吗?
可是社交应酬就是她的日常工作,她处理起来总是游刃有余。而且瑟尔也称不上是什么负担。她还很少遇到像他这样相处轻松、善解人意的人。那见到沃尔特的这份高兴算怎么回事?这种荒谬的安心感觉是为什么?就像小孩从陌生的世界回到了熟悉的环境。
她凝视着沃尔特,他正对瑟尔表示欢迎,一脸欣喜。她爱他。他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不够完美,脸上有了皱纹,两鬓的发际线也开始往后退——可他是沃尔特,真实的沃尔特,而不是那些美得虚幻,某天早晨就有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从此远离我们记忆的事物。
她还高兴地暗自比较:和高大的沃尔特面对面站着,新访客几乎显得矮小。还有他脚上的鞋子,除了昂贵,就英国人的眼光来看实在糟糕。
“毕竟,他也只是个摄影师。”她想,觉得自己真是荒唐。
她难道是被瑟尔吸引住了,所以才需要不断提高戒心?绝不可能!
北方民族中出现美若晨光的人,并不算稀奇;你由此想到海豹人①的传说以及他们的怪异的话,也没什么好惊奇的。这个年轻人只不过是个长相好看的北欧-美国人,会摆弄几下镜头,穿鞋的品位糟糕。她根本没必要神经兮兮,对他戒心重重。
即便如此,她母亲在餐桌上问起他在英国有没有亲人的时候,她心里还是隐隐一惊——她从没想过他还应该拥有亲戚关系这种世俗的东西!
他有个表姐在这里,他回答,就这一个。
“我们对对方都没什么好感。她是画画的。”
“画画不好吗?”沃尔特问。
“哦,我非常喜欢她的作品——凡是我看过的。可我们总惹对方生气,所以就谁都不烦谁了。”
拉维尼亚问她画些什么。是人物肖像吗?
莉兹听着他们闲聊,又开始走神:她画过他的表兄吗?拿着画笔和颜料盒,随自己的心意和兴致,画下一个不为自己拥有的美好人物,那感觉一定很奇妙。保存好画作,想看一眼就拿出来瞅瞅,就这样直到自己死去。
“伊丽莎白·盖洛比!”她警告自己,“一会儿你是不是就要挂上男影星的照片了!”
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跟喜爱、欣赏一件普拉克西特列斯①的作品一样没什么可指责的。假如普拉克西特列斯曾经想过创造一个不朽的跨栏选手形象,那他就应该是莱斯利·瑟尔这样的。她一定要找个时间问问他在哪里上的学,有没有参加过跨栏运动。
她看得出来母亲不喜欢瑟尔,有些失落。当然,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可是莉兹太了解她了,任何场合下都能把她心底的想法猜个八九不离十。她现在就知道,母亲温和的表情下,疑虑和不安已经开了锅,就像宁静的维苏威山坡下岩浆正在沸腾一般。
当然,她猜得一点都没错。事实上,一等沃尔特带客人去他的房间,莉兹也去洗手准备吃晚餐了,盖洛比太太就赶紧盘问她妹妹怎么会带个不知根底的陌生人回家。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库尼·威金的朋友?”她问。
“如果不是,沃尔特很快就会发现。”拉维尼亚理所当然地说,“别烦我了,埃玛,我很累。聚会真糟糕,所有人都闹哄哄的。”
“如果他是来偷东西的呢?等到沃尔特明早起来发现他根本不是库尼的朋友,就为时已晚了。谁都可以说他认识库尼。说到这个,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库尼的朋友,然后捞上一票溜之大吉。事实上,库尼的事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我想不出你为什么对他疑心重重。我们常常临时请些来历不明的人来做客——”
“的确是这样。”埃玛冷冷地说。
“一直以来也没有人欺骗过我们,你为什么单挑瑟尔先生怀疑呢?”
“他的气度太好了,让人不舒服。”
埃玛总是这样,羞于说出“漂亮”这个词,于是选用了含蓄一点的“气度太好了”。
拉维尼亚解释说瑟尔先生只会住到星期一,因此他能制造的威胁不会太大。
“如果你担心的是失窃,那他把整个崔明斯庄园搜一遍后,可能会失望了。和威克姆相比,我一时还真的想不起这里有什么东西值得偷。”
“那些银器啊。”
“不管怎样,我实在无法相信,有人会费尽周折跑到科马克·罗斯举办的聚会上,假装成库尼的朋友说要找沃尔特,居然就只是为了到我们家来偷那些银叉、银勺、银托盘。你干脆就把它们锁上一晚吧。”
盖洛比太太还是不放心。
“如果你想侵入别人家,用死人做幌子是再方便不过了。”
“得了,埃玛!”拉维尼亚忍不住大笑起来,既是笑这句话,也是笑话语中透出的情绪。
因此,盖洛比太太坐在那里依然焦躁难安,表面却还是温文不惊。她自然不是在担心崔明斯庄园里的银器。她忧虑的是她口中那个年轻人的“气度”。她就是信不过这一点,讨厌它给这个家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