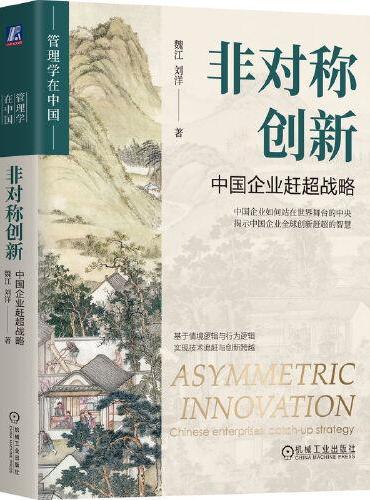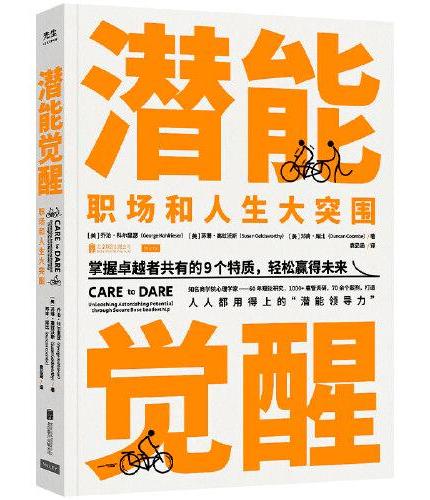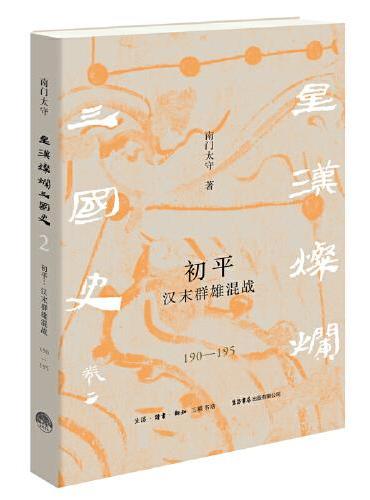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Androi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王玉芹
》
售價:NT$
495.0

《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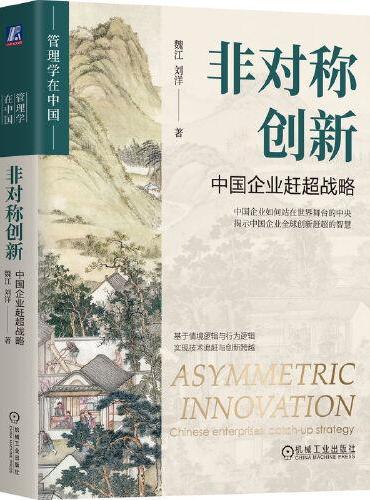
《
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赶超战略 魏江 刘洋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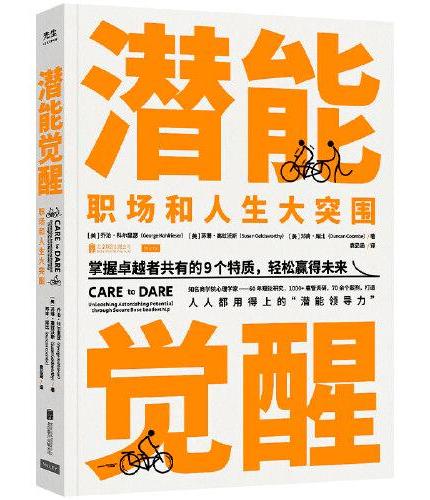
《
潜能觉醒
》
售價:NT$
3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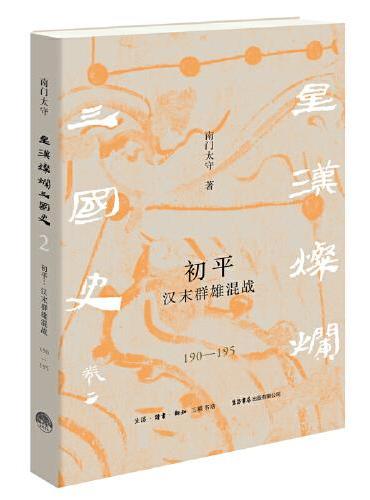
《
初平:汉末群雄混战(190—195)
》
售價:NT$
245.0
|
| 編輯推薦: |
|
从“文学之新”新人选拔大赛开始,包晓琳就以她无限的潜力,和永不出错的创作稳定性,被郭敬明赞誉为“十项全能的作者”。对叙述节奏的控制能力,塑造刻画人物的真实能力和细节之处的处理能力,都是她的强项。《阴阳》作为包晓琳的处女长篇作,是她在自己优点之上的一次创新和挑战,在《最小说》连载期间引起了大批读者的讨论和追捧,精妙的桥段、精准的人物塑造,和文中“案件侦查”“基因实验”等热点元素的呈现,将又一次展现她的永不出错的稳定的创作。
|
| 內容簡介: |
|
主人公乔唯到康复中心去接双胞胎弟弟乔奕,兄弟俩一起回到了家里的老房子居住,打算开始新的生活,却意外地发现庭院里藏有一具掩埋了十年的尸体,作为专门侦破“特殊案件”的刑警司徒南和蓝鸽接手了这桩无人看好的案子,在调查中,女刑警蓝鸽惊讶地发现这对双胞胎竟和多年前受到热议的一个基因优化计划有关,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人”,但如今,弟弟成了孤僻自闭的“雨人”,而哥哥却被卷入了这桩谋杀案,到底完美人的人生遭遇了何等的不完美?
|
| 目錄:
|
乔唯之章
Chapter1
一棵秋天的树
Chapter3
LOVE BANK?SAVE LOVE.
Chapter5
只有想活下去的人,活下去才对
Chapter7
看啊,强而有力的心跳
Chapter9
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
Chapter11
归来的他,远去的他
蓝鸽之章
Chapter2
重返视线的完美人
Chapter4
Elliott和他的E.T.
Chapter6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Chapter8
一件一件,慢慢浮上来
Chapter10
穿卡其色风衣的神秘女人
Chapter12
空瘪的爱意,饱满的恨意
尾声
2012年12月21日
|
| 內容試閱:
|
Chapter1乔唯之章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那场意外发生之后,我总在做一些怪诞的梦。
比如说,我曾无数次在梦中回到了老房子--从这座城市的滨海路一路向北,一片环海而建的复式住宅之中,有我以前住过的房子--有时,我会幽灵般的在整栋房子里游荡,或者钻进其中一个房间,试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虽然梦的内容多少会有些不同,但一直以来都相同的是:我再也没有在自己的梦里遇见过我的家人--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还有与我性格迥异的弟弟,他们就像蒸发一般从我的梦境里消失了,又或者说,根本从未出现过。
在我的意识还能用“清醒”二字来形容的几小时前,我仍待在那家叫“魔王”的夜店里,手里端着一个玻璃酒杯,从嘈杂的音浪和狂躁的人潮中穿行而过,那种漂浮感像乘着一辆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车轮咣当咣当敲击着枕木,我伫立车头,检阅着轨道两侧一张张陌生的脸,那些人脸交替着拉长又变窄,感觉是从哈哈镜里映出来的。我的身体似乎被注入了某种节奏,如同一台上足了发条的玩偶,有笑声从牙缝里迸出,可听上去却异常遥远。
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头,回头一看,竟是一张熟人的脸,熟人的嘴巴一张一翕地爆了几句粗口,又和我推搡了几下,空气里便弹起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酒精在胃袋里烧灼,我不过是吐了口气,天花板上就有火星落了下来,砸在那人脸上,他的脸碎了一地,和周遭的一切融化成了一团火,整个空间都被拉扯成诡异的形状,顷刻间,又归于一片沉寂。
短暂的意识断档之后,我在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之中爬行,一扇门阻挡了我的去路,但光就在门的另一面,它从门缝下面透出来,吸引着我把那扇门推开。就在推开门的一刹那,耀眼的白光晃得我的双眼刺痛,几秒钟之后,我才得以放下遮挡双眼的手臂,分辨自己身在何处。整个空间如同一个白光织成的蛹,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到了天堂,但我转念一想,天堂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天堂里不应该只有一张床,而且像我这种人也上不了天堂。没错,我是看到了一张床,它被雪白的床单覆盖着,但傻瓜都看得出那床单下面有东西,是一具人形的轮廓躺在那里,鼻尖将床单高高顶起,鲜明的五官线条像是庞贝古城留下的遗迹,深深的恐惧攫住了我,我想快点逃离这儿,满脑子充斥着拔腿就跑的念头,但身体却不受控制,该死的双脚一步一步向那张床挪过去,我在心里大叫着:嘿!拜托!别……
可是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我那不受控制的双手已经伸向雪白的床单,像变魔术似的缓慢地掀起床单的一角,我听到心脏怦怦乱响,像两伙持枪者交锋时在打一场巷战。接下来,枪声一般的心跳声戛然而止--假如这场戏是吴宇森导演的,这时就该有白鸽振翅飞起,在翅膀的扇动之中,某个慢动作倒下的大英雄砰砰砰砰血浆四溅--然而,我只看到了自己,而且是自己的死相,在我以往的人生中,曾经无数次从镜子里照见过,无数次从相片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张脸:松弛的皮肤苍白却光洁,眼睛虽是闭着,但无法让人忽视,无论是眼睛、鼻子还是嘴巴,都继承了我父母的优点,不自夸地说,还算得上是一张英俊的面孔,起码审美观正常的人不会说难看,女人缘嘛,也是不错的。
第一次以俯视的角度去盯着自己的尸体看,我竟想起了那部叫《入殓师》的电影。但话说回来,我是不喜欢自己的容貌的,更不喜欢照镜子,不喜欢的原因多得可以塞满一卡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讨厌自己,是恨之入骨的那种讨厌,以至于我常常这样想,像我这种人凭什么会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越是这么想,双脚就越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动弹不得,只能原地站着,眼看那白光如潮水一般渐渐退去,越来越多的红色像细菌入侵似的占领了整个空间。红色是从床单下面淌出来的,开始是一条小溪没过脚踝,接着顺着我的身体盘旋而上,那黏腻的汁液从指间穿过,从手臂到肩膀,再从脖子一点一点爬上面部,鼻腔里冲进一股血腥的气味,胃部一阵翻搅……我立刻坐起来趴在床边呕吐着,这天早晨,我就是这么醒过来的,第一个闯进视线的东西竟是摆在床边的垃圾桶,刚好避免了宿醉的我弄脏自己的床单。
室温设定为25℃的空调发出嗡嗡的鸣响,我伸直僵硬的胳膊,抓起床头的闹钟,时间显示是凌晨5 点40
分,这个时间可不适合用来做噩梦。好吧,我承认,这样醒来之后的心情真是糟透了!坏心情的原因并不是空调的错,也不是昨晚下肚那些黄汤的错,一半的我冲自己大喊大叫:“你又做了一个噩梦。”另一半的我却不屑地说:“没关系,那只是一个噩梦。”而脱离这两部分意识之外的躯体,可能被刚才真实的梦境给吓傻了,正在浑身发着抖。这种感觉令人沮丧,尽管我这人生性退缩消极,但远不至于胆小懦弱贪生怕死,可我仍旧没办法说服自己不去想梦里那些细枝末节。脖子上这颗混沌的脑袋只记得昨晚我好像狠狠放纵了一把。
推开门走进客厅,茶几上还堆满了空酒瓶,地毯上粘着吃剩的比萨,干掉的芝士看着像硬胶皮一样,我把它们从脚边拎起来,随手甩进地上的啤酒箱子里,右手的骨骼传来一阵刺痛,我定睛看了看,几个指节肿得老高,泛着青紫色,八成是我昨晚把某个浑蛋痛扁一顿留下的纪念。
清障之后,我踢了踢躺在地上的大左,想让他醒醒,他鼻子里发出一阵猪一样的哼哼声,像是没打算把眼皮睁开,他半裸的上身搭着凌乐乐的左臂,我忽然注意到她的手指上文着一朵精巧的雪花,以前和她在一起时,我竟没注意到这么明显的特征。妈的!肯定是她新近文上去的。
沙发上瘫着仰面朝上的安东--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不知他的酒鬼老爸是哪根筋不对,竟给儿子取了一个这么拉风的名字,也难怪他在陌生人前很少提起自己的全名,之前有个选秀节目的评委也曾和我抱有雷同的看法,经她点评的选手也好不到哪里去,似乎是叫“海鸣威”。安东的嘴角挂着一些类似于呕吐物的玩意儿,让人一阵反胃,我走近时发现地上也有一摊,于是恶狠狠地嚷了两句三字经。
我用比萨的包装纸飞快地抹掉那团花花绿绿的东西,再次丢进刚才那个啤酒箱子里。
时间已接近早上六点,我不想新的一天自己的家里还像一个巨型垃圾场,需要赶快把这些家伙扫地出门。
“起来!都给我起来!”我挨个儿踢醒他们。大左睡眼惺忪地看了看我,问道:“几点了?”我没回答他,因为他自己的手机就丢在脚边。凌乐乐和安东也醒了,凌乐乐盘腿打坐在地上,边打哈欠边搓着那只文有雪花图案的手,只有安东还赖在沙发上不起来,两只凹陷的灰蓝色眼睛处于对焦不灵的状态,我想起刚才自己吐在垃圾桶里那摊调色盘一样的玩意儿,猛地上前提起他污迹斑斑的领口:“你给我酒里放什么了?你说过不在我这儿碰那玩意儿的!”
“嘿,哥们儿、哥们儿,别动气。”他抓着我的手,死乞白赖地让我松开他,“就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我就是想帮你放松下心情,要是你不乐意,以后不再碰就是了。”我内心升腾起一股怒火,也许是那场噩梦作祟,也许是因为我推开门看到的这一地狼藉,也许是因为亲眼所见刚刚跟我分手的女人躺在别的男人的臂弯里,而那个男人只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健身教练,几小时前还和我喝着啤酒称兄道弟的,我突然对这一切感到深深的厌恶,我讨厌现在的生活,讨厌这帮狐朋狗友,他们没有一个真心待我,全都只是些酒肉朋友。对,只是酒肉朋友。
我承认自己把所有怒气都撒在了安东的身上,我挥起左手朝着他的右脸就是一拳,因为我现在只有左手灵活,正打在他老爸遗传的高鼻梁上,斑斑点点的血迹顿时喷溅而出,他双手捂住鼻子,眉心拧成一个疙瘩:“你他妈的是疯了吗?”他气急败坏,想要爬起来还手,可他先前整个人是瘫在沙发里的,站起来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实在太过于突然,身体根本借不上力,我也只是随便躲了一下,他便扑了个空。可他似乎并不死心,妄想克制住眩晕在地上站稳,从他迷幻的目光和汗津津的惨白面孔来看,我确定他一定嗑了不少,强劲的药力还在牢牢控制着他。
“你们俩有病吧?”大左在原地站着,但站姿表明他随时准备冲上来把火力全开的我们两个拉开。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安东用手掌抹了一把鼻子下面的血,抄起桌上的啤酒瓶,我也顺手抄起立在鞋柜旁边的棒球棍,那上面还有洋基队A?J?柏奈特的亲笔签名,是一个家住纽约的朋友送我当做纪念的。这下大左不再充当旁观者了,他试图挡在我们俩中间,但又慑于我们各执“凶器”,不敢太过靠近。
“不是来真的吧……”凌乐乐无奈地揉了揉后脑勺,又打了一个哈欠,“至于吗?神经病啊!一大早的……昨晚还没疯够,那就打好了,我看有些人就是心里不痛快,大不了把这儿全给砸了。”她说着站起身用细长的手臂甩了一下沙发上的靠垫。
可能是我的药力也没完全散尽,她此刻的表情在我眼中看来十分放荡,不比楼下洗头房里穿着红色小短裤专靠两条葱白大腿招揽生意的女人好到哪儿去。有一瞬间,我没心没肺地想,究竟为什么会和这个女人好上呢?瘦得没胸没屁股,样子又一般,完全就是一个长裂了的桂纶镁,我以前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回过神来,只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亲手结束它。从来没打过棒球也没认真看过一场棒球赛的我,手里的球棍却像施了魔法似的飞舞起来,砸碎了桌上的啤酒瓶,让这个垃圾场向更加残破的方向迈进,破碎的玻璃渣飞溅出混乱无序的轨迹,我忽然体会到一种快乐,一种只有在欣赏一部黑色喜剧时癫狂而嘲弄的快乐。
大左和凌乐乐吓呆了,安东拿在手上的啤酒瓶只剩下瓶口龇着大嘴,烘托着他脸上戏剧性的表情,转瞬间,他们都成了这出喜剧里表演浮夸的龙套,最后,我用尽身体残余的力气大吼了一声:“滚!都他妈的给老子滚!”话音散尽时,我发觉自己想喊这句话很久了,或许并不只是针对他们而喊的,而是还有别的什么,大有一种武林高手改天换地前振臂一吼的架势。在他们带着震惊的目光忿然离去之后,我从心底涌上来一阵释然。
我又孑然一身了,浑身上下畅快极了。我万分享受这狂欢过后的孤独,把这视作最好的时刻,扔掉球棒瘫倒在沙发上,重重地喘着粗气。我对着电视屏幕映照出的自己的影子,摆摆手用嘴型说了一句“FUCK”。最坏的无非就是,我弄丢了一份原本收入不错,又是我从事的这个行业里人人称羡的工作,又有什么大不了?我今年二十三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这东西,找找总会有的。
手机铃声在这时响起来的,完全陌生的一个号码,接起来,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讲话带着港台腔。
“请问,这里系乔梓聪的家吗?”听到父亲的大名,我立刻回问他有什么事?搬来出租屋之前我就把老房子的电话呼转到了手机上,之所以会这样做,好像冥冥之中就是在等今天这通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回答说:“系这个样子啊,我这里呢,有乔梓聪的一个背包,我是在他的记事簿上查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请问你是乔梓聪的什么人?”(这人似乎是把乔梓冲一概读成乔梓聪。)
“你刚才说什么东西?背包?”我一瞬间有点混乱,赶忙坐直身子,想仔细听清对方说的每一个字,况且他的口音实在难懂。
“噢,对,乔梓聪,系他的背包,你系他的什么人内?”
“我是他儿子,等等,到底怎么回事?”
“系这个样子滴啦……”他又解释道,“本来他呢,系属于另外一个团队的,但我们两个团队呢,之前就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所在的小组都会四处跑的,有人捡到了他的背包,就交到了我手里,可我现在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呀,所以我只能联络你咯。”我彻底被他说的话搞糊涂了,一直在等待父亲消息的我,紧张和不安突然一股脑儿涌了上来。我没空管背包的事:“你刚才说的团队,是指什么意思?能告诉我你在哪儿遇见他的吗?”
“这个真系说来话长了,因为我也已经离开那里回到新嘎坡了。之前呢,是在班达亚齐。”他问我,“你应该知道那里吧?最近新闻上常播粗的嘛。我就系在那里遇上乔梓聪他们团队滴。”
我想回答我知道,但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班达亚齐是印尼某特区的首府,今年春天,那里才刚发生过一场巨大的地震。
“我们系代表新嘎坡到印度尼西亚参与医疗援助的团队,之前遇见乔梓聪所在的团队……唉,后来我们两队人就走散了,但他的背包却阴错阳差地落在我手上了。”
“他还活着吗?”我只是急切地想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不管他在哪里,只要他还活着,什么班达亚齐、苏门答腊,就算他在伊拉克贩卖军火都行。
而对方却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个……我也不能肯定地知道,所以我也不能回答你啦。”他为难地说,“那么,你现在系在哪里啊?我想尽快把他的东西交到你的手上。”
我对这位自称姓陈的先生说了些感谢的话,把详实的地址告诉他,然后电话就挂断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悬在了这条距离遥远的电波上,发出扑哧扑哧的恼人声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