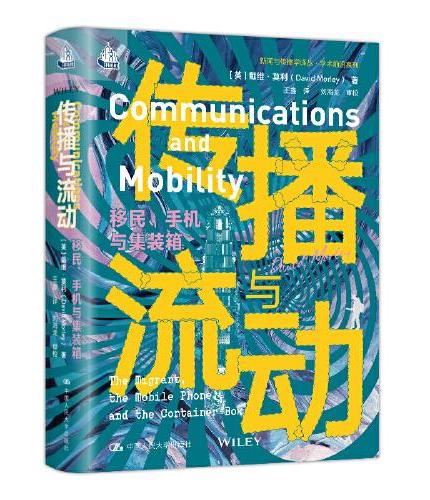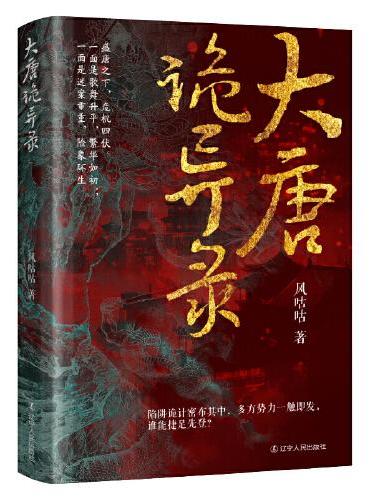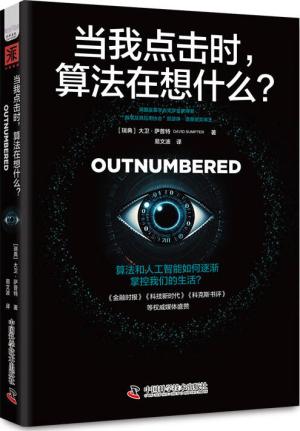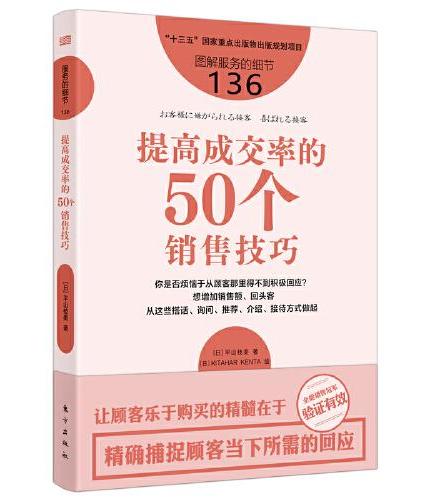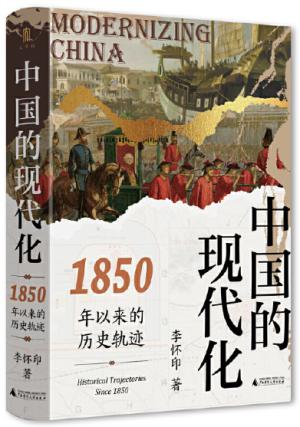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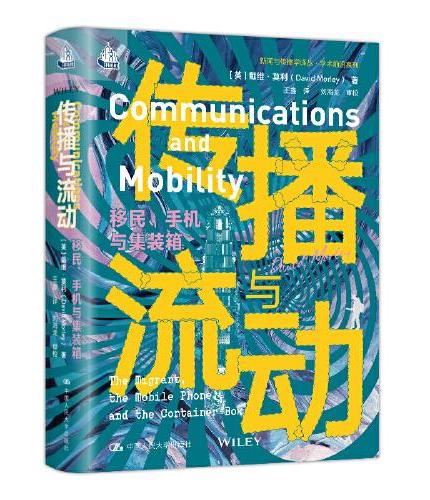
《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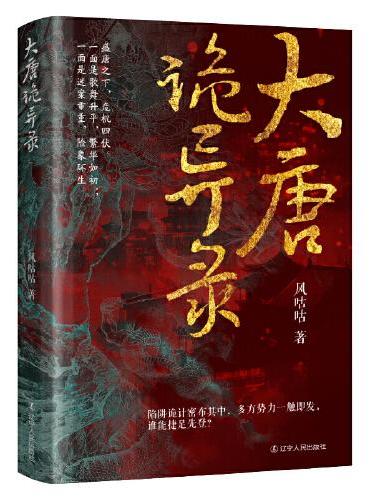
《
大唐诡异录
》
售價:NT$
254.0

《
《证券分析》前传:格雷厄姆投资思想与证券分析方法
》
售價:NT$
6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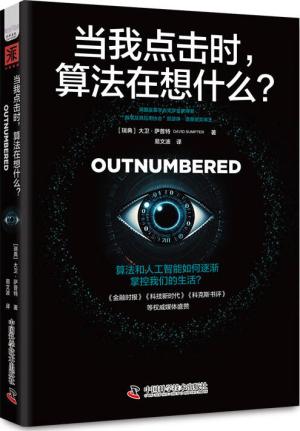
《
当我点击时,算法在想什么?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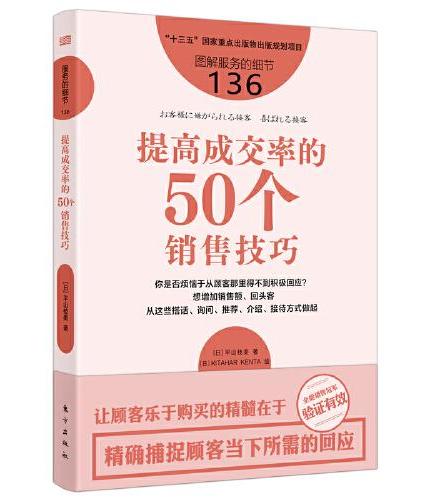
《
服务的细节136:提高成交率的50个销售技巧
》
售價:NT$
296.0

《
变法与党争:大明帝国的衰亡(1500—1644)
》
售價:NT$
4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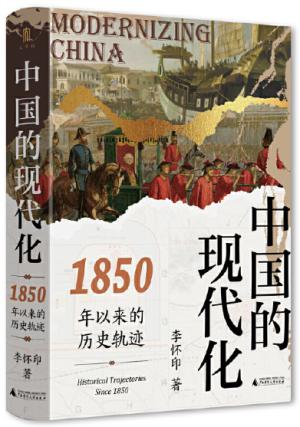
《
大学问·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
》
售價:NT$
490.0

《
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
》
售價:NT$
436.0
|
| 編輯推薦: |
1. 重归纯真年代:一个小姑娘的恋爱冒险,一种底层人的平凡生活。
2. 只有一种经典还不够:读英文,体会经典最完美的魅力。
|
| 內容簡介: |
玛丽姑娘和莫须有太太生活在爱尔兰首都都伯林,她们并不富裕,靠着莫须有太太替人帮佣来维持微薄的生活,生活中唯一的希望是玛丽去美国的舅舅发财回来。虽然穷困,但她们的日常生活并不缺乏情趣。有一天,玛丽玛丽遇到了一位高大的巡警,看上去这就是玛丽姑娘的真命天子,但事情往往不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进行……
小说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但却勾勒出都伯林的城市风貌、民俗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译者之一的徐志摩说作者“没有王尔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纯粹民族性的”。
|
| 關於作者: |
詹姆斯·斯蒂芬斯(1882—1950)爱尔兰诗人、小说家。
徐志摩(1897-1931),中国著名新月派现代诗人,散文家。
沈性仁,(1895—1943),浙江嘉兴人。“五四”时期,1925年她首次将房龙《人类的故事》翻为中文。
|
| 內容試閱:
|
一
玛丽与她的母亲,莫须有太太,住在一所高大的黝黑的屋子的顶上一间小屋子里,在都白林城里的一条后街上。她从小就住在这间屋顶的小房间里。天花板上所有的裂缝,她都知道,裂缝不少,都是奇形怪状的。旧极的糊纸的墙上长着无数霉菌的斑点,她也是熟悉的。她看着这些斑点从灰影子长成黑斑,从小污点长成大霉块,还有墙脚边的破洞,晚上蟑螂虫进出的孔道,她也知道。房间里只有一面玻璃窗,但她要向窗外望时,她得把窗子往上推,因为好几年的垢积已经掩没了玻璃的透明,现在只像是半透光的薄蛎壳了。窗外望得见的也只是隔壁那所屋子顶上的一排烟囱土管,不息的把煤点卷向她的窗子;所以她也不愿意多开窗,因为开窗就得擦脸,用水也得她自己走五层楼梯去提,因此她更不愿意薰黑了脸子多费水。
她的母亲简直的不很洗脸,她以为濯洗不是卫生的,容易擦去脸上本来的光润,并且胰子水不是敛紧了皮肤,就泡起了皱纹。她自己的脸子有地方是太紧,有地方又是太松,玛丽常常想起那松的地方一定是她母亲年轻时擦得太多了,那紧的地方一定是她从来没有洗过的。她想她情愿脸上的皮肤不是全松就是全紧,所以她每次洗脸她就满面的擦一个周到,不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让步。
她的母亲的脸子是又陈又旧的象牙的颜色。她的鼻子是像一只大的强有力的鸟喙,上面的皮张是绷得紧紧的,所以在烛光里,她的鼻子呆顿顿的亮着。她的一双眼是又大又黑像两潭墨水,像鸟眼一样的铄亮。她的头发也是黑的,像最细的丝一样的光滑,放松的时候就直挂了下来,盖在她的象牙色的脸上发亮。她的嘴唇是薄的,差不多没有颜色,她的手是尖形的,敏捷的手,握紧了只见指节,张开了只见指条。
玛丽爱极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爱极了她的女儿,她的爱是一种剧烈的热情,有时发作凶猛的搂抱。每次她的母亲搂住了她,时候稍为长一点,就出眼泪,抱紧了她的女儿一左一右的摇着。她那一把抓得凶极了,可怜的玛丽连气都转不过来;但是她宁可耐着,不愿意妨碍她妈亲热的表情。她倒是在那样搂抱的凶恶中感到几分乐趣,她宁可吃一点小苦的。
她妈每天一早就出去做工,往往不到晚上不回家的。她是个做短工的佣妇,她的工作是洗擦房间与收拾楼梯。她也会得烧饭做菜,有时有针线活计她也做的。她做过最精致的衣服,年轻美丽的姑娘们穿了去跳舞或是去游玩的;她也做上品的白衬衫,那是体面的先生们宴会时穿的;还有花饰的背心为爱时髦的少年们做的,长统的丝袜子跳舞用的——那是从前的事情了,因为她做成好看给别人拿走,她就生气,她往往咒骂到她那里来拿东西的人,有时她发了疯,竟是把做好的鲜艳的衣眼撕烂了,用脚践踏着,口里高声的叫喊。
她时常哭泣因为她是不富。有时她做了工回家的时候,她爱假定她是有钱了的;她就凭空的幻想有某人故了,剩下给她一份大家产,或是她兄弟伯德哥从美洲发了大财回来了,她那时就告诉玛丽明天想买这样,做那样。玛丽也爱那个……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搬家,搬到一所大房子去,背后有花园,园里满是鲜花满是唱歌儿的鸟。屋子的前面是一大块草地,可以拍网球,可以傍着秀气的雅致的年轻人散步,他们有的是俊俏的脸子与雪白的手,他们会说法文,很殷勤的鞠躬,手里拿着的帽子差一点碰着地。她们要用十二个底下人——六个男佣人,六个女佣人——都是很伶俐的,他们每星期拿十先令的工钱,外加膳宿;他们每星期有两晚可以自由,他们的饭也吃得很好的。她们要制备无数的好衣服,穿了在街道上散步的衣服与坐马车兜风的衣服,还有骑马衣与旅行的服装。还要做一件银红丝绸的礼服,镶领是阔条的花边,一件黄酿色缎子的,胸前挂着黄金的项链,一件最细洁的白纱的,腰边插一朵大红的玫瑰。还要黑丝的长袜用红丝线结出古怪的花样,银丝的围巾,有的绣着鲜花与精致的人物。
她妈打算这样那样的时候,她心里就高兴了,但是不久她又哭了,把她的女儿狠劲的搂在胸前摇着,搂得她叫痛。
二
每天早上六点钟,玛丽姑娘爬出了床,起来点旺了炉火。这火却是不容易点着,因为烟囱许久没有打扫过,又没有风可以借力。她们家里又从没有柴条,就把乱纸团成小球儿垫着,把昨夜烧剩的炭屑铺上,再添上一把小煤块算数。有时一会儿火焰就窜了上来,她就快活,但是有时三次四次都点不旺,往往点到六次都有,点着了火,还得使用一点小瓶子里的煤油——几条烂布头浸透了油,放在火里,再用一张报纸围着壁炉的铁格子,火头就旺,一小锅子的水一会儿就可以烧熟;不过这样的引火法容易把油味儿烟进水去,开出来的茶就是一股怪味,除了为省钱再没有人愿意喝的。
莫须有太太爱在床里多偎一会儿。她们屋子里也没有桌子,玛丽就把两杯茶一罐炼乳,一小块的面包放在床上,她们母女俩就是这样吃她们的早点。
早上玛丽一张开眼,她妈就不断的讲话了。她把上一天的事情都背了一遍,又把今天她要去的地方,及可以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都一一的说了。她也打算收拾这间屋子,重新裱糊墙壁,打扫烟囱,填塞鼠穴——一共有三个,一个在火炉格子的左边,还有两个在床底下。玛丽有好几夜只是醒着,听他们的牙齿啃着壁脚。他们的小腿在地板上赛跑。她妈还打算去买一块土耳其线毯铺在地板上,她明知道油布或是席布容易出灰,但是他们没有土耳其毯子好看,也没有那样光滑。她打算着种种的改良,她的女儿也是十二分的赞成。她们要买一个红木抽屉衣柜靠着这边墙上,买一架紫檀大钢琴贴着那边墙上。一架白铜的炉围,火钳火杆也都是铜的,一把烧水用的铜壶,一个烧白薯与煎肉用的小铁盘;玛丽等身大的一幅油画挂在炉架的上面,她母亲的画用金框子装了挂在窗的一面,还要一幅画着一只纽芬兰的大狗偃卧在一只桶里,一只稀小的猎狗爬过来与他做朋友,还要一幅是黑人与白兵打仗的。
她妈一听得隔壁房间出来迟重的脚步声走下楼梯去,她就知道她应该起来了。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六个小孩住着。隔壁门一响,她就跳了起来,快快的穿上衣服,着忙似的逃出了屋子。她妈出了门,玛丽没有事做,往往又上床去睡一两个钟头。睡够了她起来,铺好了床,收拾了房间,走出门上街去闲步,或是圣史蒂芬公园里去坐着。公园里的鸟雀她全认得,有的已经生了小鸟的,有的正怀着小鸟的,有的从没有生过小鸟的——最后的一种大都是雄的,他们自有他们不生小雀儿的道理,玛丽却是懂不得,她只是可怜他们没有孩子,成心多喂他们一些面包屑,算是安慰他们的意思。她爱看那些乳鸭子跟着他们母亲泅水:他们胆子很大,竟会得一直冲到人站着的岸边,使了很大的劲伸出小扁嘴去捡起一点不相干的东西,快活的吞了下去。那只母鸭子稳稳的在她儿女的附近泳着,嘴里低声的向他们唱着种种的警告、指导、埋怨的口号。玛丽心里想那些小鸭子真是聪明,水泳得那么好。她爱他们,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她就学他们的娘低声的唱着口号,但是她也不常试,因为她怕她的口号的意义不对,也许教错了这群孩子,或是与他们的妈教他们的话不合式。
湖上那座桥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太阳的一边,一大群的鸭子竖直了尾梢,头浸没在水里导东西吃,水面上只剩了半个鸭子。有荫的一面好几百的鳗鱼在水里泅着。鳗鱼是顶奇怪的东西,有许多像缎带一样的薄,有些又圆又肥像粗绳子似的。他们像是从不打架的,那小鸭子那样的小,但是大鳗鱼从不欺侮他们,就是有时他们泅水下去他们也不理会。有的鳗鱼游得顶慢,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像是没有事做,又像乡下人进城似的,有的溜得快极了,一霎眼就看不见了。玛丽心里想泅得快的鳗鱼一定是为听得他们的小孩子在哭;她想一个小鱼哭的时候不知道她妈看不看得出他的眼泪,因为水里已经有那么多的水,她又想也许他们一哭就哭出一大块硬硬的,那是很容易看得见的。
看过了鱼,她就到花坛那边去看,有的形状像有棱角的星,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方的。她最爱那星形的花坛,她也爱那圆形,她最不喜那方的。但是她爱所有的花,她常常替花儿编故事。
看过了花,肚子饿了,她就回家去吃午饭。她从葛莱夫登路的夏康内尔路那边回家。她总是从马路右手的走道回家。一路看店铺陈列的窗柜,回头吃过了中饭再出来,她就走左边的走道,照样的一家家看过去,她所以每天都知道城子里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晚上就告诉她妈说孟宁那家窗子里那件西班牙花边滚口的黑绸衫已经换了一件红色的长袍,肩上有折裥,袖口配着爱尔兰花边的;或是永生珠宝铺里那颗定价一百镑的金钢钻已经收进了去,现在摆着的是一盒亮银的胸针与蓝珐琅。
在晚上,她妈领着她到各家戏院的门前去走一转,看进戏院的人与放在路边的戏广告。她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她们就凭着她们方才看过的广告相片来猜想各家戏里的情节,所以她们每晚上床以前总是有很多的话讲的。玛丽在晚上讲话最多,但是她妈早上讲话最多。
三
她妈有时也提起她的婚事,这是还远着,但是总有那么一天的;她说这事还远着倒叫玛丽着急;她知道一个女孩子总得嫁人的,总有那么一天,一个陌生的美丽的男子从一处地方来求婚,等到成了婚,他就同了他的新娘,重新回转他从来的地方,那就是温柔乡。有时候(她一想就想着)他穿了军装,骑在红棕色的马上,他头盔上的缨须在青林里的树叶间飘着。或者他是站在飞快的一只船头上来的,他的黄金的盔甲上反射着烈火似的阳光。或是在一块青草的平原,风一般的快捷,他来了,跑着,跳着,笑着。
一讲到婚事她妈就仔细的品评那新郎的人品,他的了不得的才具,他的更了不得的财产,他的相貌的壮丽,穷人与富人对他一体的敬爱。她也要一件一件的讨论给她女儿的妆奁,将来新郎给她与给女傧相的种种奢侈的礼物,还有新郎家里给这一双新夫妇更值钱的宝贝。照这样的计算,新郎至少是一个爵士、贵族。玛丽就来寻根掘底的盘问一个爵士的身分种种,她妈的答案也是一样的细腻,一样的丰富。
一个爵士出世的时候他的摇篮是银子的,他死的时候他的尸体是放在一个金盒子里,金盒子放在一个橡木的棺材里,橡木棺又放在铅制的外椁里,铅椁又放在一个巨大的石柜里。他的一生只是在逍遥与快乐的旋涡里急转着。他的府第的周围好几里都是软美的青草地与香熟的果子园与啸响的青林,在林子里他不是带了欢笑的同伴打猎,便是伴着他的夫人温柔的散步。他的侍从有好几千,谁都愿意为他尽忠,他的资财的多少是无法计算的,都是堆积在地屋里,这里面低隘的甬道曲折的引到铁壁似的房窖里。
玛丽很愿意嫁给一个爵士。假如她轻盈的在林子里走着,或是独自在海边站着,或是在和风吹着长梗的草堆里躺着的时候,他要是来了,她愿意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跟了他去,从此就爱定了他。但是她不信现在的世界上还有这样如意的事情,她妈也不信。现在的世界!她妈侧着眼看现代的日子,满心只是轻蔑与恚怒。下流、丑陋的日子,下流、丑陋的生活,下流、丑陋的人,她妈说,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她接着又讲她去收拾屋子她去擦楼梯的人家,她那老象牙的脸上就从她漆黑鬓发边泛出火来,她的深沉的黑眼也转动起来,一直变成两块黑玉似的硬性与呆顿,她的手一开一放的,一会儿只见指节,一会儿只见指条。
但是玛丽渐渐的明白了,结婚是实事,不是故事,而且也不知怎的,结婚的一种情趣依旧是黏附着的,虽则她现住的屋子里只见是纷扰的家室,她常走的道上也只见是不出奇的配偶……那些灰色生活的,阴沉性质的人们也还有一点的火星在他们苦窘的经络里冒着烟。六尺深是埋不了人生的情趣的,除非泥土把我们的骨头胶住了,这一点火星总还在那里冒烟,总还可以扇得旺,也许有一天火焰窜了上来,飞度了一乡一镇,还可以温热许多僵缩的人们的冷手哩。
那些男男女女怎样的合成配偶的?她还懂不得那基本的原则,永
远鼓动着男性去会合女性。她还不明白男女性是个生理的差别,她只当是服饰的不同,有胡子与没有胡子的事情;但是她已经开始发见男子的一种特别的兴趣。路上那些急走的或是停逗的陌生人中也许有一个是运定做她的丈夫的。假如有一个男子忽然留住了脚步,上前来向她求婚,她也不会觉得离奇的。她觉得这是男子们唯一的事情,她再不能寻出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世界有了女子要有男子,要是果然有人突然的向她求婚,她便应该怎样的答复他,这倒把玛丽难住了;她也许回答说,“是,多谢你,先生。”因为平常一个男子求人替他做一件事,她总是愿意效劳的。年轻人尤其有一种吸力,她总想不出为什么,有一点子特别的有趣在年轻人的身上;她很愿意去和他们握一次手,究竟怎样的比一个女子不同。她设想就是她让男子打了一下,她也不会得介意的,但是她看了男子行动的强健,她可猜想他们一定可以打得很重——还不是一样让男子打一下的意思,她总觉得脱不了一种可怕的有趣。她有一次无意的问她妈有没有让一个男子打过;她妈一阵子没有开口,忽然大哭起来,玛丽唬了一大跳。她赶快投入了她妈的怀里,让她狠劲的摇着,可怜她哪里懂得她妈突然的伤心,但是她妈却是始终不曾回答玛丽问她的话。
四
每天下午,总有一队巡士从学院警察派出所里排成了又郑重又威严的单行出来。他们走到一处岗位,就有一个巡士站住了,整饬了他的腰带,捻齐了他的胡子,望上街看看,望下街张张,看有刑犯没有,他就站定在那里看管他日常的职务。
在诺沙街与沙福克街交叉过葛莱夫登大街那里,总有一位魁伟的宝货离开了他的队伍站定了,他在路中心高高的矗着,仿佛是一座安全与法律的牌坊,一直要到晚上换班时,方才再与他的同伴合伙。
也许这一个交叉路口要算是都白林城里最有趣的地方。站在这里望开去,葛莱夫登大街上两排辉煌的店铺弧形的一直联到圣史蒂芬公园,尽头处是一座石门,原来叫做浮雪里,本地人重新定名为叛逆门。诺沙街在左,宽敞,洁净,穿度梅里昂方衢,直接黑石与王镇等处及海边。沙福克街在右,不如诺沙街的开朗与爽恺,曲曲的上通圣安得罗的礼拜寺,羞怯似的微触南城市场,低入了乔治街,再过去便是些纷沓的小巷了。交叉口的这一面,葛莱夫登街又延过大学院(在大门口年轻的大学生卖弄着他们烂破的学袍,抽着他们怪相的烟斗),掠着爱尔兰银行,直到栗薇河,河边那条街好胜的本地人硬要叫做夏康内尔街,倔强的外国人,却偏要叫做撒克维尔街。
这里也是全城车辆与行人的交会处,所以总有一位雄伟的巡士先生站着。铛又铛的市街电车到推伦纽洼,到唐耐伯洛克,或到达尔基的,不绝的在转角上飞骋着;集中在梅里昂方衢一带的时髦医生也是马车汽车的满街上乱颠着;大街上店铺里的货车等等也是急急的飞奔着。四点钟左右出来散步的仕女们,各方面来的车辆与行人,自行车与双轮汽油车,电车与汽车,一齐奔辏到那单身的巡士站着的地方,看着他的又严厉又宽和的目光的指挥。赶街车的都是与他熟识的,他的眼角的微瞅是在照会那些脸上红红的口角笑吟吟的马车夫飞过来的眼风,还有那些赶着赚不到钱看相凄凉的街车夫,一脸的紫气与无聊的气概的,他也少不得要招呼的。就是溜踏着的仕女们也避不了他那包罗万象的目光。他的伟大的脑壳不时的点着,他的老练的手指不时的驱挥着有数的靠不住的手脚,他也偶尔闪露着他的宽阔的、洁白的牙齿,应酬着爱嘻哈的少女,或是他相识的妇女,她们就爱他那一下子。
每天下午玛丽吃过了中饭又从家里出来,就到这个最热闹的地方。这位奇伟的巡士先生的样儿她心里爱上了。这还不是一个理想的男子汉,他那样儿多雄壮,多伟大。想像他那狠的粗大拳头使劲的扎下来!
她想像一个英雄打架时的身手,晃着他的大拳,高高的举着,霹雳似的栽下来,什么也挡不住,谁也熬不起——一只遮天的霸王的大手。她也爱瞧着他那两边晃着的大脑袋,他那镇定的骄傲的大乌珠——一双压得住、分得清、断得定的大眼睛。她从不曾准对他的眼光:她看了他的,自己就萎了下去,像一个耗子对着猫儿的神睛萎萎缩缩的躲回了他的鼠洞。她常常躲在一家药房门前的那块石柱旁瞄着他,或是假装要搭电车,站在马路的那一边;她又掩在那家眼镜铺子过去一点的柱子边偷偷的觑了他一眼,赶快又把眼光闪了开去,只算是看街上的车了。她自以为他没有瞧着她,但是什么事也逃不了他的眼。他的事情就是看着管着:他第一次见了她就把她写录在他巡士脑筋里的纪事簿上;他每天都见她,后来他就成心去瞧着她,他乐意她那偷偷的劲儿;有一天她的怕羞的、懦怯的眼光让他的罩住了。他那眼从上面望下来盖住了她——整个的世界,像是全变成了一只大眼——竟像是着了魔,她再也逃不了。
等到她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站在圣史蒂芬公园的池边,全身只是又骇又喜的狂跳。那天晚上她没有走原路回家,她再不敢冒险去步行那伟大的生机体,她绕了一个圈子回家,但是她并没有觉得走远了。
那天晚上她在她妈跟前说话比往夜少。她妈见她少开口,怕她有心事,问她要铜子不要——她脑筋里就是钱。玛丽说没有想什么,她就想睡,她就张开下巴打哈欠——哈欠是装的,答话也没有老实。她上床去也有好一会儿没有睡着。她开了眼对着屋子里阴沉的黑暗尽看,也没有理会她妈凶恶的梦话,她在大声的问睡乡要她醒着的世界里要不到的东西。
五
这是玛丽的模样儿:——她有浅色的头发,很柔也很密;她要一放松就落了下来,简直像水一样的冲了下来,齐着她的腰,有时她散披了在房里走着,发丝很美的弧形似的笼着她的头,逼缩的掩住她的颈凹,宽荡的散掠着她的肩,随着她走路的身段激成各式的浪纹;涌着,萎着,颤着;她的发梢是又柔又缓的像水沫,又亮又光的像纯粹的淡金。在屋子里她不束发的时候多,因为她妈就爱那散披着头发的小姑娘的意思,有时她还要她女儿解了外裳,单穿着白衬裙,更看得年轻。她的头形长得很娇柔,很软和;她把头发全攒在头上的时候,她那娇小的头像是载不住发重似的。她的眼睛是澄清的,灰色的,又温柔,又羞怯的隐在厚重的眼睑下,平常她的眼只看是半开似的,她又常常的看着地,不很放平着眼直瞧;她看人也就只一瞬,轻翻着,轻溜着,轻转着,一会子又沉了下去;还有,她要是对着谁看,她就微微的笑着,像是告罪她自己的卤莽。她有一张小小的白脸,有几点与几处角度很像她母亲的,但她母亲那鸟喙形紧皮的鼻子却是不在玛丽的脸上;她的鼻梁收敛得紧紧的,鼻尖也就只些微的一放,刚够看得见。
她妈就爱那小鼻子,像是害臊,不很敢出头露面似的。现在她们站在她们那面镜子前,镜面有一条大裂缝儿从右手的顶角斜着下来,喝醉了似的,直到左手的底角,还有两块交叉儿的破绽,一上一下的,在镜面的当中。
所以谁要照镜的时候,一个脸子就变成四个古怪的相儿,顶可怕的;耳朵也许蒙着嘴唇,眼睛吊在下巴上诡怪的张着瞧。但是也还有法子照,她们用惯了知道破玻璃的脾气,就是偶然准头错了变了相,也不觉得可怕了。
每回她们娘儿俩并肩儿站着照相,莫须有太太总是仔细的品评镜子里的一双脸子,她点着她自己真正靠得住的鼻子又说她当初丈夫的鼻子也是顶有分量的,她的女儿的鼻子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儿!除非她们上代或是旁支曾经有过小鼻子的种;她就历数着她的姊姊妹妹,一大群的姑母与祖姑母,从往古的坟里翻起历代的祖宗,叫所有死透了的鼻子重新活过来比着瞧。玛丽听着她妈那样科学的研究鼻子,她就张着她的害羞的好奇的眼微微的笑着,像是道歉她那呼吸器官的缺憾,回头她妈就亲她的脸上的精品,赌咒的说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个小鼻子了。
“大鼻子有人合式,”莫须有太太说,“有人可不合式,你要有了一个大的就不合式,我的乖。黑头发的,高身材的,军官先生们,法官,卖药的,他们的鼻子长得大神气;像你这样又小又白的人,可受不了大鼻子。我喜欢我自己的鼻子,”她又接着说,“我做小姑娘的时候在学堂里,同学的女孩子们全笑我的鼻子,可是我总是愿意他的,看熟了别人也就不讨厌了。”
玛丽的手脚,是又瘦小又软弱的,她的手掌比什么东西都软;她的掌上有五个小的、粉红色的肉垫子:从小拇指那里起有一个顶小的垫子,过去一个大一点,再过去更大一点,直到那大拇指底下的那个顶大的,匀匀的排着,看得顶整齐的。她妈有时爱亲这五块小垫子,她扳着一根指头,叫着她的名字,亲了一下嘴,再来第二个,这是玛丽的指头的名字——汤姆塔姆根斯,威利温各尔斯,郎但尼儿,塔西鲍勃推儿,最小弟小弟是的。
她的瘦小的女孩子的身材,现在正在发长到成人的体态,原来髫年的平直的肌肤渐渐的辨认出一半弧的曲线,渐渐的幻成了轻盈的酥肌,至微的起落引起某角度的颤震,隐隐的显示着将次圆满的妙趣。她有时也感觉着这些新来的扰动,她只得益发的矜持她原来无拘束的行动。
她母亲当然是很关心的注意着这渐放的春苞,有时不禁自喜与自傲,但亦往往私自的嗔着她的小姑娘,也不免长成一个大姑娘。她真的愿意玛丽永远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她怕玛丽有一天完全的长成了妇人,那时便许有种种的不便阻碍她们母女间自然的活泼的情景。一个成年的女子也许不再愿意受人看护,不比小女子永远是依人的小鸟;莫须有太太就怕那不愿意,事实上玛丽的确已经感觉到一个苏醒着的肉体与新奇的温暖的戟刺,她妈只当她小孩似的养育与日常慈爱的拥抱渐渐的不能使她满足。她有时私自的想她也来把她搂在她的胸前,一样的温存的摇着,轻唤着宠惜的小语,缓吻着怀里的头顶与半掩的腮弧,但她却不敢尝试,怕惹她妈生气。这一点她妈是不容易让步的,她爱她的姑娘去亲吻她,轻抚着她的手与面,但她却不愿她的女儿来僭试母亲的特权,也从不曾纵容她玩偶的习惯,她是阿妈,玛丽是囡囡,她不肯让步她做娘的身分,即使是偶尔的游戏。
六
玛丽已经十六岁了,但她却不曾有工作;她妈不愿意她的小女儿去尝试劳苦的工役——唯一的职业她能替她想法的,就是帮助她自己佣工的生活。她打算把玛丽送到一家店铺,一家衣服店或是相类的行业,但那个时候也还远着。“况且,”莫须有太太说,“要是我们再等上一年半载,也许有别的运气碰出来。你的舅舅,他到美国去了二十年了,也许会得回来,他要是回来,你就用不着去做事了,乖乖,我也用不着了。再不然过路的人也许看上了你来向你求婚;那都是说不定会来的。”她有无数的计划,她想像无数的偶然,都可以助成她女儿的安乐与光大她自己的尊荣。所以玛丽在她妈出去佣工的时候(她差不多除了星期是每天去的)总是闲着,随她自己爱怎么玩。有时她住在家里不出去。她在楼顶上后背的屋子里缝衣服或是结线,修补被单与毛毡上的破绽,或是念她从开博尔街的公共图书馆里借来的书。但是照例,她收拾了屋子以后,她愿意出门去在街上闲走着,爱上哪儿就哪儿,逛着不曾走过的街道,看着店铺与居民。
有许多人都是面熟的;差不多每天她总在这里或那里看见他们,她对于他们觉得有一种朋友的感情,她常常跟着他们走一小段路;整天的寂寞往往像一种重量似的压在她身上,所以虽然这些面熟陌生的脸子做她远远的伴儿,她也安慰了。她愿意在这人群里打听出几个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是有棕色长胡子的高个儿,他穿着笨重的大氅好像穿着一把铁铲似的;他戴着一副眼镜,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好像永远要发笑;他一路去也是看着店铺,他好像人人都认识。每走几步路便有人停步与他握手,但是这些人从来不开口的,因为这个棕色长胡子的高个儿一见他们便刺刺不休的来一大阵,使他们没有说话的分儿,要是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他便自言自语的咕啰着。到了那种时候他眼睛里看不见一个人,人家都得让开道来让他摇头摆脑的,两眼注视远远的一个地方,迈着大步望前走。有一两次玛丽在他身边经过,听见他独自唱着世界上最悲痛的歌。还有一个人——一个瘦长黑脸的男子——他的样子很年轻,他常自在窃笑;他的两片嘴唇永远没有休息过一分钟,有几次他从玛丽身边走过,她听见他嗡嗡的像只大蜜蜂。他从没有停步同一个人握过手,虽然有许多人向他行礼,他并不理会,自己却窃笑着,轻轻的哼着,放开脚步直望前走。还有第三个人她常常注意的:这人身上的衣服好像已经穿上了许久,一向没有脱下过似的。他有一张长长的苍白脸,一片漆黑的胡须悬挂在一张很美丽的嘴上。他的眼睛很大很无精神,并且不大像人的眼睛;它们会斜着瞟——一种最亲密的,有意的瞟。有的时候他除了走道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却什么都看见。有—次他看了看玛丽,把她吓了一跳,当时她脑中就发生一个奇怪的念头,仿佛这个人她在几百年前曾经认识过,而他也还记得她似的。她心里怕他,可是又喜欢他,因为他的样子很文雅,很——他还有一种样子玛丽想不出一个字来可以形容的,但是这种样子仿佛在许多年以前她曾见过似的。此外还有一个矮小,清秀,苍白脸儿的男子,这人的模样好像他是世上最疲劳的人,他总像心里有心思似的,但是没有旁人那样的古怪。他又像永远在那里倒嚼他的记忆;他看看旁人,似乎都引起他回忆那些久已故去的人们,而对于这些故去的人他只有思念,并不悲悼。他虽在人群之中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有一种冷峭的态度;就是他的笑也是冷峭的,孤高的。他在路上走过,时玛丽看见许多人都拿肘子互相轻轻的一推转过脸来又看了看他,便咬着耳朵唧唧哝哝走去了。
这些人以及许多旁人她差不多每天看见,她常常带着一种朋友的感情去留心他们。别的时候她走到一排站在栗薇河边的码头上,望着基内斯的那些快船吹着气顺着河流而下,与几千白鸥在黑水面上忽起忽落的玩着。后来她又走到凤凰公园,那里有人比赛板球与足球,也有些年轻的男子与姑娘们抛球的,也有孩子们玩着放鹰捉兔的,也有追人的,也有在日光底下跳舞、叫嚷的。她的妈每逢没有工作的日子最欢喜带她去逛凤凰公园。离开了那条又大又白的马路,这条马路上有许多脚踏车,汽车接连不断的,射箭似的飞过,走不上几步便有几条清净的小路,路上阴森森的遮满了大树与荆树的丛林的影子。在这路上你走了半天可以遇不见一个人,你可以随便躺在树荫下的草上或看着日光射在绿草地上与在树林里闪烁。这地方是非常的寂静,住在城内的人初见此地一定很感到惊奇、美丽,并且这也稀奇:在这白日之下举目看不见一人,除了那绿草的随风翻叠,树枝儿的轻轻摇动与蜜蜂、蝴蝶、小鸟的没有声息的飞翔之外没有一点别的动静。
这些东西玛丽看了都爱,但是她妈却爱看孩子们的跳舞,汽车的奔忙,那些身上穿着鲜艳的衣服,手里举着美丽的洋伞的来往的人们与休息日的各色各样的情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