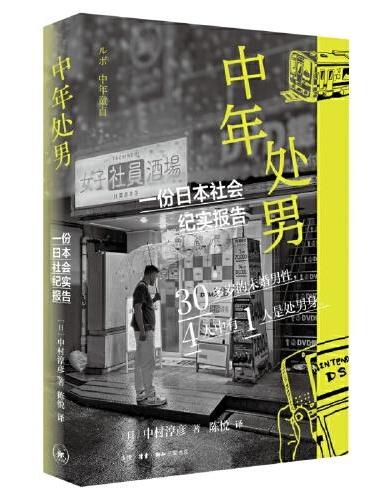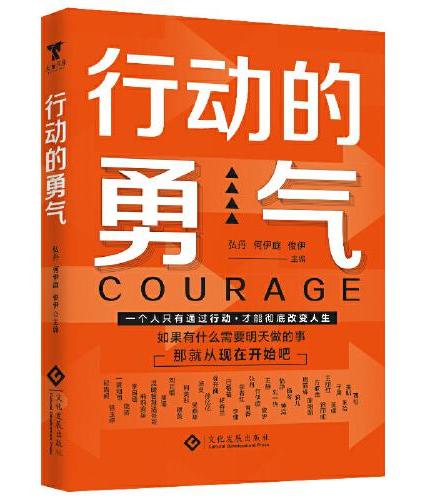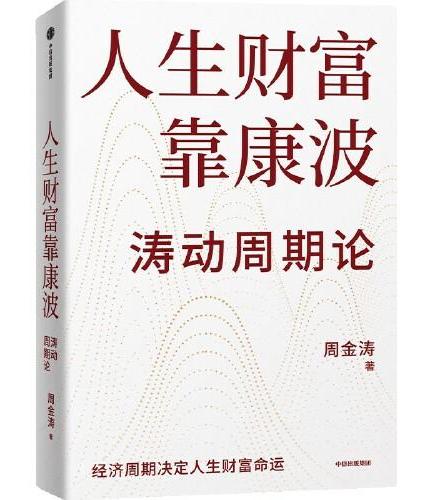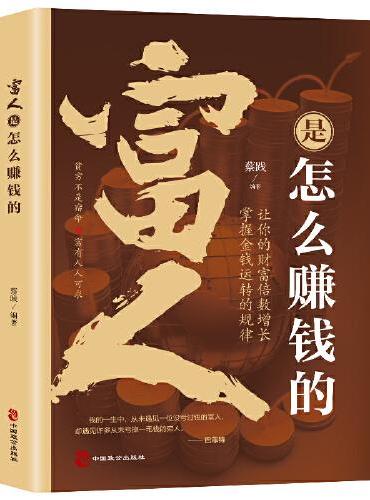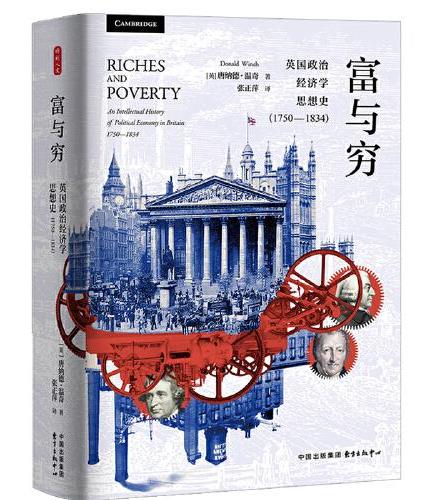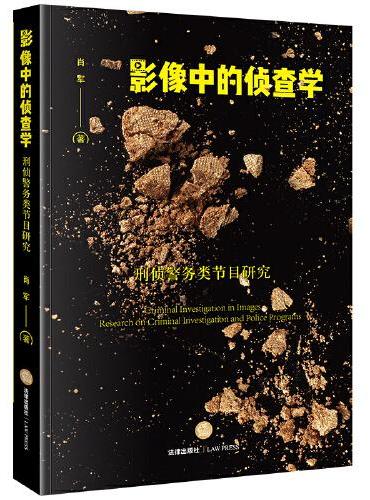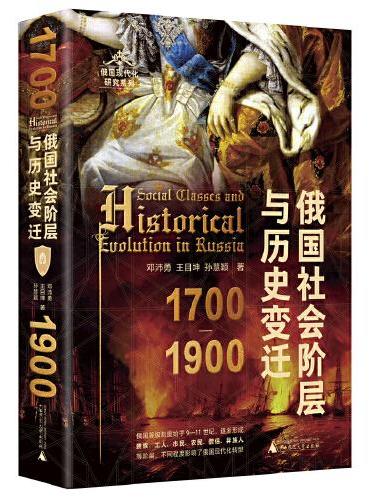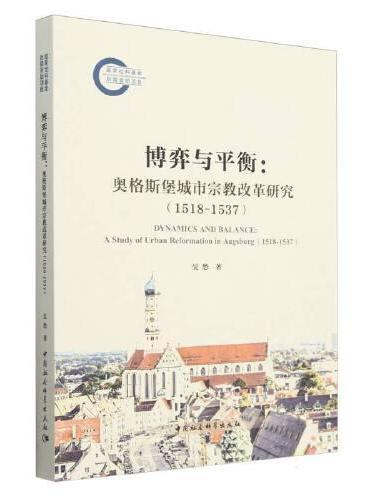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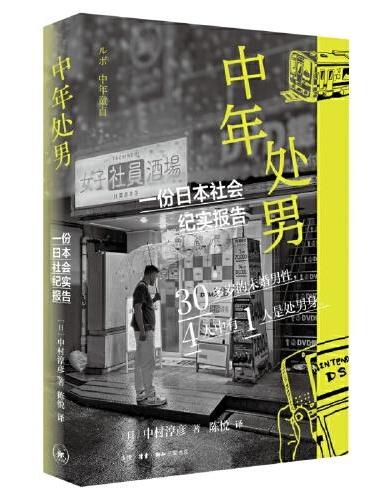
《
中年处男:一份日本社会纪实报告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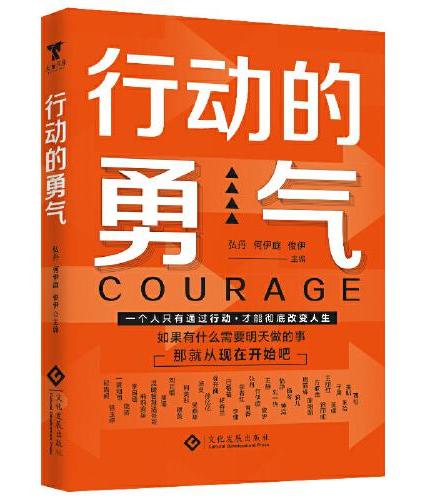
《
行动的勇气,畅销书作家弘丹主编,30余位大咖分享人生高效秘诀。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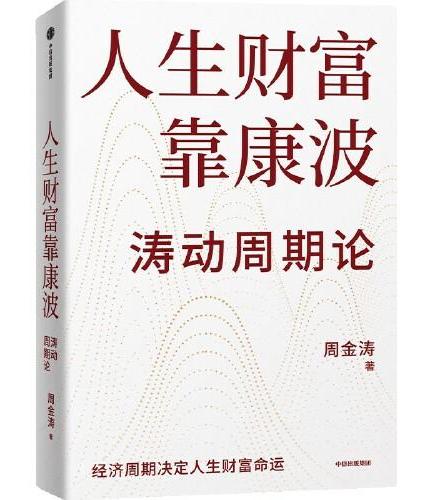
《
人生财富靠康波
》
售價:NT$
5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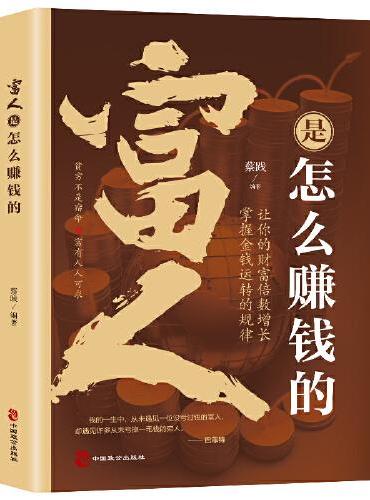
《
富人是怎么赚钱的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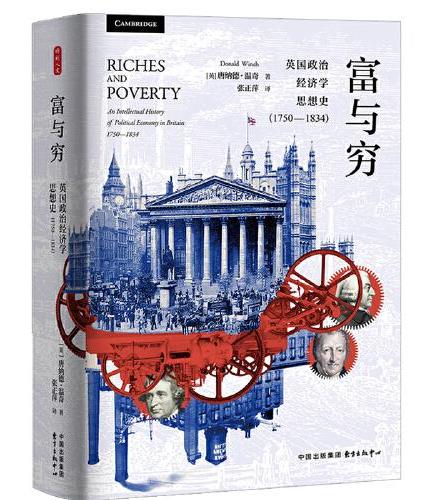
《
时刻人文·富与穷: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750—1834)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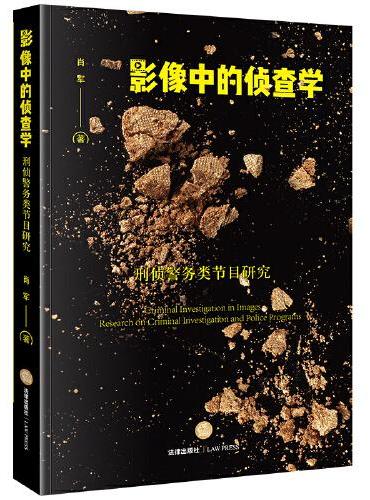
《
影像中的侦查学:刑侦警务类节目研究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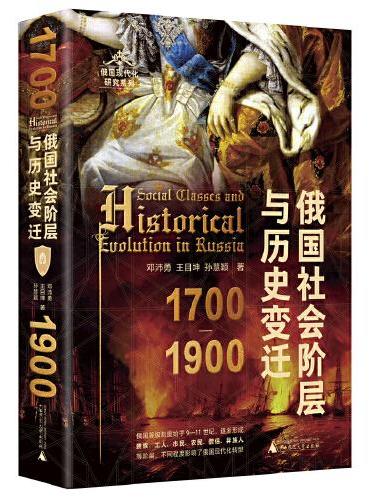
《
俄国社会阶层与历史变迁(1700—1900)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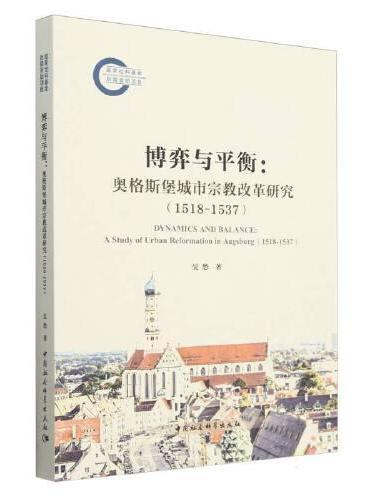
《
博弈与平衡:奥格斯堡城市宗教改革研究(1518-1537)
》
售價:NT$
551.0
|
| 編輯推薦: |
1.
徐志摩说:“曼殊斐尔是我的溺爱。”让天才诗人不能自已的绝妙文字,让多情浪子难以忘怀的文学女性。看最迷人的曼殊斐尔,特别收录徐志摩祭作者的祷文。
2. 曼殊斐尔说:“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平庸。”读英文,体会最原始的天才。
|
| 內容簡介: |
|
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病逝后,徐志摩翻译她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本书收录了《园会》《巴克妈妈的形状》《毒药》《一杯茶》《深夜时》《幸福》《一个理想的家庭》《刮风》等8个短篇,从中可以看出曼殊菲尔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徐志摩的译笔。
|
| 關於作者: |
女作家曼殊斐尔( Katherine
Mansfield),生于新西兰,同时拥有英国国籍,以写短篇小说见长,笔调自然、流畅,在技巧方面综合了多种现代主义手法的表现方法。虽然她在英国成名,其小说背景带有很深的新西兰文化的印迹,被当时的媒介誉为“
新西兰文学花园的一只孔雀”。于1922年7月,在伦敦会见徐志摩,并与他交谈苏联文学和近几年中国文艺运动的趋向。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
|
| 目錄:
|
园会
毒药
巴克妈妈的行状
一杯茶
夜深时
幸福
一个理想的家庭
刮风
曼殊斐尔
The Garden-Party
Poison
Life of Ma Parker
A Cup of Tea
Late at Night
Bliss
An Ideal Family
The Wind Blows
|
| 內容試閱:
|
一杯茶
费蔷媚并不怎样的美。不,你不会得叫她美。好看?呒是的,要是你把她分开来看……可是为什么要拿一个好好的人分开来看,这不太惨了吗?她年纪是轻的,够漂亮,十分的时新,穿衣服讲究极了的,专念最新出的新书博学极了的,上她家去的是一群趣极了的杂凑,社会上顶重要的人物以及……美术家——怪东西,她自己的“发见”,有几个怕得死人的,可也有看得过好玩的。
蔷媚结婚二年了。她有一个蜜甜的孩子,男的。不,不是彼得——叫密仡儿。她的丈夫简直是爱透了她的。他们家有钱,真的有钱,不是就只够舒服过去一类,那听着寒伧,闷劲儿的,像是提起谁家的祖老太爷祖老太太。他们可不,蔷媚要什么东西,她就到巴黎去买,不比你我就知道到彭德街去。她要买花的话,她那车就在黎锦街上那家上等花铺子门前停住了,蔷媚走进铺子去扁着她那眼,带“洋味儿”的看法,口里说:“我要那些那些。那个给我四把。那一瓶子的玫瑰全要。呒,那瓶子也让我带了去吧。不,不要丁香。我恨丁香。那花不是样儿。”铺子里的伙计弯着身子,拿丁香另放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倒像她那话正说对了似的,丁香是真不是样儿。“给我那一球矮个儿的黄水仙。那红的白的也拿着。”她走出铺子上车去的时候,就有一个瘦小的女孩子一颠一颠的跟在背后,抱着一个多大的白纸包的花,像是一个孩子裹在长抱裙里似的……
一个冬天的下午她在寇崇街上一家古董铺里买东西。她喜欢那铺子。他那儿先就清静,不提别的,你去往往可以独占,再兼那铺子里的掌柜,也不知怎么的,就爱伺候她。她一进门儿,他不提有多快活。他抱紧了他自个儿的手;他感激得话都说不出来。恭维,当然。可还是的,这铺子有意思……
“你明白,太太,”他总是用他那恭敬的低音调讲话,“我宝贵我的东西。我宁可留着不卖的,与其卖给不识货的主顾,他们没有那细心,最难得的……”
一边深深的呼着气,他手里拿一小方块的蓝丝绒给展开了,放在玻璃柜上,用他那没血色的指尖儿按着。
今天的是一只小盒子。他替她留着的。他谁都没有给看过的。一只精致的小法瑯盒儿,那釉光真不错,看得就像是在奶酪里焙成的。那盖上雕着一个小人儿站在一株开花的树底下,还有一个更小的小人儿还伸着她那一双手搂着他哪。她的帽子,就够小绣球花的花瓣儿大,挂在一个树枝上;还有绿的飘带。半天里还有一朵粉红的云彩在他们的头顶浮着,像一个探消息的天使。蔷媚把她自己的手从她那长手套里探了出来。她每回看这类东西总是褪了手套的。呒,她很喜欢这个。她爱它;它是个小宝贝。她一定得留了它。她拿那奶光的盒儿翻覆的看,打开了又给关上,她不由的注意到她自个儿的一双手,衬着柜上那块蓝丝绒,不提够多好看。那掌柜的,在他心里那一个不透亮的地基儿,也许竟敢容留同样的感想。因为他手拿着一管铅笔,身子靠在玻璃柜上,他那白得没血色的手指儿心虚虚的向着她那玫瑰色发艳光的爬着,一边他喃喃的说着话:“太太你要是许我点给你看,那小人儿的上身衣上还刻着花哪。”
“有意思!”蔷媚喜欢那些花。这要多少钱呢?有一晌掌柜的像是没有听见。这回她听得他低声的说了。“二十八个金几尼,太太。”
“二十八个几尼。”蔷媚没有给回音。她放下了那小盒儿;她扣上了她的手套。二十八个几尼。就有钱也不能……她愣着了。她一眼瞟着了一把肥肥的水壶,像一只肥肥的母鸡蹲在那掌柜的头上似的,她答话的口音还有点儿迷糊的:“好吧,替我留着——行不行?我想……”
但是那掌柜的已经鞠过躬,表示遵命,意思仿佛是替她留着是他唯一的使命。他愿意,当然,永远替她留着。
那扇谨慎的门咄的关上了。她站在门外的台阶上,看着这冬天的下午。正下着雨,下雨天就跟着昏,黑夜的影子像灰沙似的在半空里洒下来。空气里有一股冷的涩的味儿,新亮上的街灯看着凄惨。对街屋子里的灯光也是这阴瑟瑟的。它们暗暗的亮着像是惆怅什么。街上人匆匆的来往,全躲在他们可恨的伞子底下。蔷媚觉着一阵子古怪的心沉。她拿手筒窝紧了她的胸口;她心想要有那小盒子一起窝着多好。那车当然在那儿。边街就是的。可是她还耽着不动。做人有时候的情景真叫你惊心,就这从屋子里探身出来看着外边的世界,哪儿都是愁,够多难受。你可不能因此就让打失了兴致,你应当跑回家去,吃他一顿特别预备的茶点。但她正想到这儿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瘦的,黑的,鬼影子似的——她哪儿来的?——贴近蔷媚的肘子旁边站着,一个小声音,像是叹气,又像是哭,在说着话:“太太,你许我跟你说一句话吧?”
“跟我说话?”蔷媚转过身子去。她见一个小个儿的破烂的女子睁着一双大眼珠,年纪倒是轻的,不比她自己大,一双冻红的手抓着她的领口,浑身发着抖,像是才从凉水里爬起来似的。
“太——太太,”那声音发愣的叫着,“你能不能给我够吃一杯茶的钱?”
“一杯茶?”听那声音倒是直白老实的;一点也不像化子的口气。“那你一个大子也没有吗?”蔷媚问。
“没有,太太。”她回答。
“多奇怪”蔷媚冲着黄昏的微光直瞧,那女子的眼光也向她瞪着。这不比奇怪还奇怪!蔷媚忽然间觉到这倒是个奇遇。竟像是道施滔奄夫斯基[1]小说里出来的,这黑夜间的相逢。她就带这女子回家去又怎么呢?她就试演演她常常在小说里戏台上看到的一类事情,看他下文怎么来,好不好呢?这准够耸荡的。她仿佛听着她自己事后对她的朋友们说:“我简直的就带了她回家。”这时候她走上一步,对她身旁暗沉沉的人影儿说:“跟我回家吃茶去。”
那女子吓得往后退。她给吓得连哆嗦都停了一阵子。蔷媚伸出一只手去,按着她的臂膀。“我不冤你,”她说,微微的笑着。她觉得她的笑够直爽够和气的。“来吧,为什么不?坐了我车一共回家吃茶去。”
“你——你不能是这个意思,太太。”那女子说,她的声音里有苦痛。
“是的哪,”蔷媚叫着,“我是要你去。你去我欢喜。来你的。”
那女子拿她的手指盖住她的口,眼睁得老大的钉着蔷媚。“你——你不是带我到警察局去?”她愣着说。
“警察局!”蔷媚发笑了,“我为什么要那么恶?不,我就要你作去暖和暖和,乘便听听——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饿慌了的人是容易带走的。小车夫拉开了车门,不一忽儿她们在昏沉的街道上飞似的去了。
“得!”蔷媚说。她觉着得胜了似的,她的手溜进了套手的丝绒带。她眼看着她钩住的小俘虏,心里直想说,“这我可带住你了。”她当然是好意。喔,岂但好意。她意思要做给这女子看,叫她相信——这世界上有的是奇怪的事情——神话里仙母是真碰得到的——有钱人是有心肠的,女人和女人是姊妹。她突然转过身子去,说:“不要害怕。有再说,你有什么可怕的,跟我一同走有什么怕?我们都是女人。就说我的地位比你的好,你就该盼望……”
可是刚巧这时候,她正不知道怎样说完那句话,车子停了,铃子一按,门开了,蔷媚用她那殷勤的姿态,半保护的,简直抱着她似的,把那女子拉进了屋子去。天暖和,柔软,光亮,一种甜香味儿,这在她是享惯了的平常不放在心上,这时候看还有那个怎样的领略。有意思极了的。她像是一个富人家的女孩子在她的奶房里,柜子打开一个又一个,纸盘儿放散一个又一个的。
“来,上楼来,”蔷媚说,急于要开始她的慷慨,“上来到我房间里去。”这来也好救出这可怜的小东西,否则叫下人们钉着看就够受的;她们一边走上楼梯,她心里就打算连金儿都不去按铃叫她,换衣服什么她自个儿来。顶要紧的事情是要做得自然!
“得!”蔷媚第二次又叫了,她们走到了她那宽大的卧房;窗帘全已拉拢了的,壁炉里的火光在她那套精美的水漆家具,金线的坐垫,淡黄的浅蓝的地毯上直晃耀。
那女子就在靠进门那儿站着;她看昏了的样子。可是蔷媚不介意那个。
“来坐下。”她叫,把她那大椅子拉近了火,“这椅子舒泰。来这儿暖和暖和。你一定冷极了。”
“我不敢,太太。”那女子说,她挨着往后退。
“喔,来吧,”——蔷媚跑过去——“你有什么怕的,不要怕,真的。坐下,等我脱下了我的东西我们一同到间壁屋子吃茶舒服去。为什么你怕?”她就轻轻的把那瘦小的人儿半推似的安进了她的深深的摇床。
那女子不作声。她就痴痴的坐着,一双手挂在两边,她的口微微的开着。说实话,她那样儿够蠢的。可是蔷媚她不承认那个。她靠着她的一边,问她:“你脱了你的帽子不好?你的美头发全湿了的。不带帽子舒服得多不是?”
这回她听着一声轻极了的仿佛是“好的,太太”,那顶压扁了的帽子就下来了。
“我再来帮你脱了外套吧。”蔷媚说。
那女子站了起来。可是她一手撑着椅子,就让蔷媚给拉。这可费劲了。她自个儿简直没有动活。她站都站不稳像个小孩,蔷媚的心里不由的想,一个人要旁人帮忙他自己也得稍微,就要稍微,帮衬一点才好,否则事情就为难了。现在她拿这件外套怎么办呢?她给放在地板上,帽子也一起搁着。她正在壁炉架上拿下一枝烟卷来,忽然听得那女子快声的说,音是低的可有点儿怪:“我对不住,太太,可是我要晕了。我得昏了,太太,要是我不吃一点东西。”
“了了不得,我怎么的糊涂!”蔷媚奔过去按铃了。
“茶!马上拿茶来!立刻要点儿白兰地!”
下女来了又去了,可是那女子简直的哭了。“不,我不要白兰地。我从来不喝白兰地,我要的就是一杯茶,太太。”她眼泪都来了。
这阵子是又可怕又有趣的。蔷媚跑在她椅子的一边。
“不要哭,可怜的小东西。”她说。
“别哭。”她拿她的花边手帕给她。她真的心里说不出的感动了。她把她的手臂放在那一对瘦削的鸟样的肩膀上。
这来她才心定了点儿,不怕了,什么都忘了,就知道她们俩都是女人,她咽着说:“我再不能这样儿下去,我受不了这个,我再不能受。我非得自个儿了了完事。我再也受不了了。”
“你用不着的。有我顾着你。再不要哭了。你看你碰着我还不是好事情?我们一忽儿吃茶,你有什么都对我说,我会替你想法子。我答应你。好了,不哭了。怪累的。好了!”
她果然停了,正够蔷媚站起身,茶点就来了。她移过一个桌子来放在她们中间。她这样那样什么都让给那可怜的小人儿吃,所有的夹肉饼,所有的牛油面包,她那茶杯一空就给她倒上,加奶酪,加糖。人家总说糖是滋补的。她自己没有吃;她抽她的烟,又故意眼往一边看,不叫她对面人觉着羞。
真的是,那一顿小点心的效力够奇怪的。茶桌子一挪开,一个新人儿,一个小个儿怯弱的身材,一头发揉着的,黑黑口唇,深的有光的眼,靠在那大椅子里,一种倦慵慵的神情,对壁炉里的火光望着。蔷媚又点上一枝烟;这该是时候谈天了。
“你最后一餐饭是什么时候吃的?”她软软的问。
但正这时候门上的手把转动了。
“蔷媚,我可以进来吗?”是菲立伯。
“当然。”
他进来了。“喔,对不住。”他说,他停住了直望。
“你来吧,不碍,”蔷媚笑着说,“这是我的——我的朋友,密斯——”
“司密司,太太,”倦慵慵的那个说,她这忽儿倒是异常的镇定,也不怕。
“司密司,”蔷媚说,“我们正要谈点儿天哪。”
“喔,是的。”“很好,”说着他的眼瞟着了地板上的外套和帽子。他走过来,背着火站着。“这下半天天时太坏了。”他留神的说,眼睛依然冲着倦慵慵的那个看,看她的手,她的鞋,然后再望着蔷媚。
“可不是,”蔷媚欣欣的说,“下流的天气。”
菲立伯笑了他那媚人的笑。“我方才进来是要,”他说,“你跟我到书房里去一去。你可以吗?密斯司密司许我们不?”
那一对大眼睛挺了起来瞅着他,可是蔷媚替她答了话。“当然她许的。”他们俩一起出房去了。
“我说,”菲立伯到了书房里说,“讲给我听。她是谁?这算什么意思?”
蔷媚,嘻嘻的笑着,身体靠在门上说:“她是我在寇崇街上捡了来的,真的是。她是一个真正的‘捡来货’。她问我要一杯茶的钱,我就带了她回家。”
“可是你想拿她怎么办呢?”
“待她好,”蔷媚快快的说,“待她稀奇的好。顾着她。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们还没有谈哪。可是指点她——看待她——使她觉着——”
“我的乖乖孩子,”菲立伯说,“你够发疯了,你知道。哪儿有这样办法的。”
“我知道你一定这么说,”蔷媚回驳他,“为什么不?我要这么着。那还不够理由?再说,在书上不是常念到这类事情。我决意——”
“可是,”菲立伯慢吞吞的说,割去一枝雪茄的头,“她长得这十二分好看。”
“好看?”蔷媚没有防备他这一来,她脸都红了,“你说她好看?我——我没有想着。”
“真是的!”菲立伯划了一根火柴,“是简直的可爱。再看看去,我的孩子。方才我进你屋的时候我简直的看迷糊了。但是……我想你事情做错了。对不起,乖乖,如其我太粗鲁了或是什么。可是你得按时候让我知道密斯司密司跟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吃前还要看看衣饰杂志哪。”
“你这怪东西!”蔷媚说,她走进了书房,又不回她自己房里去,他走进他的书写间去,在他的书台边坐下了。好看!简直的可爱!看迷糊了!她的心像一个大皮球似的跳着,好看!可爱!她手拉着她那本支票簿。可是不对,支票用不着的,当然。她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了五张镑票看了看,放回了两张,把那三张挤在手掌心里,她走回她卧房去了。
半小时以后菲立伯还在书房里,蔷媚进来了。
“我就来告诉你,”她说,她又靠在门上,望着他,又是她那扁眯着,眼带“洋味儿”的看法,“密斯司密司今晚不跟我们吃饭了。”
菲立伯放下了手里的报。“喔,为什么了?她另有约会?”
蔷媚过来坐在他的腿上。“她一定要走,”她说,“所以我送了那可怜人儿一点儿钱。她要去我也不能勉强她不是?”她软软的又加上一句。
蔷媚方才收拾了她的头发,微微的添深了一点她的眼圈,也戴上了她的珠子。她伸起一双手来,摸着菲立伯的脸。
“你喜欢我不?”她说,她那声音,甜甜的,也有点儿发粗。
“我喜欢你极了,”他说,紧紧的抱住她,“亲我。”
隔了一阵子。
蔷媚迷离的说:“我见一只有趣的小盒儿。要二十八个几尼哪。你许我买不?”
菲立伯在膝盖上颠着她。“许你,你这会花钱的小东西。”他说。
可是那并不是蔷媚要说的话。
“菲立伯,”那低声的说,她拿他的头紧抵着她的胸膛,“我好看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