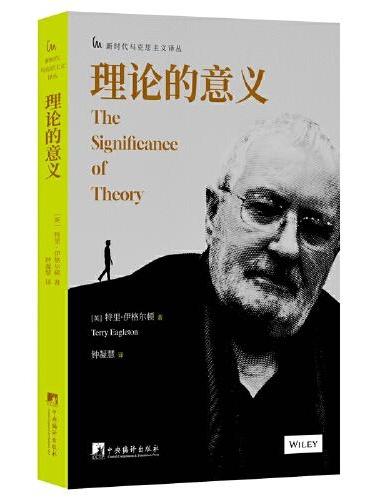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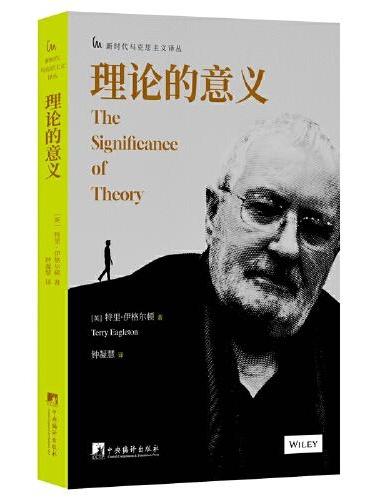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Androi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王玉芹
》
售價:NT$
495.0
|
| 編輯推薦: |
写尽母女间的纠葛和真挚情感;
致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的母亲:对不起!谢谢你!
感动无数读者的深情之作,
献给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她们辛苦养大的子女们。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佐野洋子晚年创作的一部纪实性长篇散文。作者说,此书献给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喜欢过的母亲。在日本出版后反响强烈,有人感动,有人如释重负,还有的人觉得获得了内心的救赎。
这是一部讲述母女之间爱与恨的作品。静子就是佐野洋子的母亲。在作者的笔下,母亲与“我”一生都没有和谐相处过,“我”讨厌母亲,因为她虚荣、自私、冷漠、无情,甚至在小时候虐待“我”。母亲晚年的时候被儿媳妇从家里赶了出来,虽然“我”花费巨额金钱把她送进了设施优良的养老院,但“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一点点安宁,因为从情感上“我”一次也没有喜欢过母亲,“我”成了把母亲丢在弃母山上的人……
作品写出了人性的真实与丰富,对母女之间情感纠葛的描写没有丝毫的掩饰和美化,结尾处对母亲厌恶的冰释、情感的升华,动人心弦,让人感动。
|
| 關於作者: |
|
佐野洋子(1938—2010年),出生于中国北京。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设计系毕业。1967-1968年间赴德国柏林造型大学进修平版画专业。归国后,一边从事设计、插图,一边开始创作图画书。她擅长以水彩和亚克力颜料创作,运用豪迈自由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出画中人物的感情,不论是幽默的,还是温馨的,都能触动读者的心。代表作有《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绅士的雨伞》、《熊爸爸》、《五岁老奶奶去钓鱼》等。除了创作图画书,佐野洋子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写过大量洞悉人性的作品,比如《我不那么想》、《没有神也没有佛》等。2004年,她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以艺术家为对象的紫绶褒章。2009年,她再获严谷小波文艺奖桂冠。
|
| 內容試閱:
|
1
我走进屋子里的时候,母亲正背朝外躺在床上睡着。我把脸凑到跟前去看她,她依然闭着眼,嘴不停地蠕动着。母亲的牙全部掉光了,她那不停蠕动的嘴上出现的皱纹,不禁让人联想到把一块布塞进一个小洞后的情景。嘴还在不停地蠕动着。尽管她一直在睡眠之中,但她焦点涣散的眼神有时也会盯着某处一动不动。
“母亲”----听我这么一叫,她吓得哆嗦了一下,继而用充满恐惧的眼神打量我。“我是洋子啊”----待我说完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始向四处看,等我又说了一遍“我是洋子啊”,她才开始直直地盯着我看。“是洋子吗?哎呀……”,说着就把身子扭过去了,接着她又说了一声“哎呀……”。从这一刻起,在母亲眼里,我已经不是洋子了。也不再是其他任何人。
为了让她心情好一些,我就把带来的东西拿给她看,问她想不想吃,她清楚地说:“想吃”。可吃的时候,那架势就像连盘子也要一并吃掉似的。母亲睡觉的时候,有时听到声响就会睁开眼睛,可今天却只有嘴在不停地蠕动,而不醒来。于是我静静地站在旁边望着她。
过了一会儿,我坐到椅子上继续打量着母亲。她的身子一直裹在干洗完不久硬挺挺的床单和被罩里。十年前母亲住我家里的时候,床单可没有这么整洁。
我连自己的床单一个月也只换两次左右。为此我一直只铺深蓝色或者带红色花纹的床单,因为它们不显脏。换洗被子可是一项繁重劳动,每换一次我就要为自己上年纪了而感慨一番,然后把头钻进被罩和被子中间去,累的浑身是汗。每当此时我都会心生感慨:“真不知道这种活我还能撑着干多久”,“谢天谢地,这种活起码现在我还干的动”。
母亲要是一直住在我家,恐怕就不会是现在这般干净利落的老太太形象了,恐怕也不会像这里一样,把食物捣碎了喂给她吃,她恐怕也就吃不上像这里这般种类丰富的饭菜和甜点了。----这个念头在头脑中闪现的一瞬间,我猛然发觉,其实自己早已抛弃了母亲。
我原本打算静静离开,可还是爬上了母亲的床,即便如此,母亲还是闭着眼睛,身子一动不动,只有嘴,不停地蠕动着。我握着母亲的手,攥几下,摩挲几下,但她始终没把眼睛睁开。视线触及母亲指甲的时候,我一下愣住了,她的指甲显得透明而洁净。母亲曾经身体偏胖,短短的手指头原本是很粗的,可现在怎么会......
直到母亲老糊涂到今天这个样子,我都没有再碰过她的手一下。记得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牵母亲的手,我刚把手放进她的手掌心,她就立刻很不高兴地“切”了一声,然后猛地甩开了我的手。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去拉她的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和母亲紧张的母女关系开始了。
眼前这双手,就是当初粗暴地把我甩在一旁的那双手吗?在我看来,母亲的手应该是结实、胖乎、粗壮而显暗红色的。抚摸着母亲的手,我发现,母亲浑身上下只有指甲上没有皱纹了。如今的这双手又平又薄,骨头上紧紧地贴着一层皮,只要一摩挲,皮就会活动来活动去,可与其说是手上的皮在活动,倒不如说是那些皱纹在四处游窜。我尝试着寻找恰当的比喻去形容,但却始终没有找到。母亲的胳膊原来很粗的,可现在却瘦得只剩皮包骨。说包在骨头上的是皮,其实那是皱纹。而泛着青色的静脉就紧贴着这些皱纹向前延伸开去。
我可怜的母亲!她可就是靠着这双手----自始至终就是这双手----活了一辈子啊!直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眼泪打湿了脸颊,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在回家的车里,我哭个不停。进了家门发现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被窝里哭,可是因为实在停不下来,我就边哭边给小樱打电话。“你怎么了?”“我刚从我母亲那里回来,我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什么事啊?”“我母亲爱说谎。”“说什么谎了?”“她像沙知一样学历造假。”“哈哈,这算什么大事啊?”“可是我不喜欢她这样嘛。一直都是。她收拢着嘴说我是府立第二小学的。其实我上的是私立的女子学校。那所学校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嘛。还有,我们住的地方明明是牛入柳町,可她却只说住在牛入。后来越说越离谱,接着就成住在四谷,最后就成了麦町了。”“哈哈哈。”“还有,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说,母亲你说谎,她就说,你这孩子真可恶,你难道不知道说谎有时能够带来方便的道理吗?然后就扇了我一耳光。”“哦,不会吧。”“她说我和我父亲一个样。”
父亲的手上肉很薄,又平又大。在严冬的北京,当地面结冰的时候,父亲会把我的手握在手里当做手套。然后在他外套的衣兜里握着我的手,一直把我的手捂在兜里面。
我的脚尖冻得没了知觉,疼得我快哭了,我说“脚,脚”,父亲说“蠢货,给我忍着。”但是却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父亲外出的时候他一直拉着我的手。我任何时候都能回想起父亲那平坦而又薄又大的手的感觉。我和母亲则没有一起外出过。
后来连父亲的手也没得牵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忘不了他那双又薄又平的手。那年我十九岁,母亲四十二岁。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最小的妹妹才七岁。因为家里住的是机关宿舍,所以父亲一死我们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
“再后来我长大以后就一直没在她身边。不过我特别讨厌母亲。”“我知道的。”“后来,她七十多岁的时候不是来我家了嘛,不知道因为什么,有一天我批评了她。我那个时候也真够可以的了,竟然把人家的退路给堵上了。”“我能明白。”“我责怪她,为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追求虚荣。母亲哭着说‘可能因为我自卑吧。’”
母亲回了自己的房间。明明是我惹的她,但还是放心不下,过一会儿就打开了母亲的房门,母亲斜着坐在床上,用衬衫的下摆掩着脸,仍然在那里不停地哭着。母亲边哭边说:“你怎么能在别人面前那样说呢?”“别人?那个人和我可是夫妻啊。”我一边说着一边想,是啊,怪我不好,可我还是禁不住觉得奇怪,到这个时候还在顾及着面子呢啊?
母亲在别人家里非常客气,她会老实而高贵地把身子缩成一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父亲死后,她是从自己盖的房子里被唯一的儿子的媳妇给赶出来的。母亲嫁给我父亲之前是在东京长大的,可是那片土地几十年来都是母亲应该待着的地方,母亲已经在那里扎了根。我为母亲的境遇感到可怜。母亲一整天都在给那片土地上的朋友打电话。一个月的电话费竟然高达六万日元。看到发票的时候我就想,难怪呢。十万日元也好,二十万日元也罢,想打就打吧,真是可怜。我非常非常生弟媳妇的气。在我和母亲心情都好的时候就会一起说我弟媳妇的坏话。从中我完全感受到了母亲的万念俱空。可是说谎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你母亲可真了不起。”“就是啊,哇~”“母子之间就是那样。”“可我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啊,真是令人吃惊。你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吗?”“别说了。”“说嘛”“我每周六都会去见她一次,一直如此。后来我就会觉得烦闷,于是就和母亲说,我很忙,不能每周都来看你。母亲说,明白了。然后,过了十天左右,放心不下她,打电话过去一听,声音不对。然后马上就去看她。她发烧发的不是一般的厉害。我马上就带她去了医院。在那种条件下……稍等,我去哪点纸巾过来……”“后来呢?”“后来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她在医院死掉了。她在我去之前身体就很糟糕,可是因为我说了那种话,她就一直忍着来着。”
小樱在电话的另一端抽泣着,我在这边也哭了起来。“……那时你母亲多大岁数?”“八十二岁……”“是吗。不过我更可恨,你特别爱你母亲,不是还向公司请了两个月的假,发疯似地为她摩挲身体,照顾她来着吗?”“可是,如果我没说那种话,她或许……就不会死。”“我呢,虽然现在在反省和哭泣,但是我在母亲说‘可能因为我自卑吧’的时候,心里就舒坦多了。你不觉得我很很过分吗?啊,讨厌,讨厌死了!我也得拿纸巾了。啊,用完了。大家都这样吗?”“你啊,我们还能为此后悔和哭泣呢。有的人对那种事情根本理都不理。”
樱子的情绪好些了,可我挂了电话也没能缓过来,我对母亲说过的话如同泉水一样奔涌出来。
母亲是离开清水到我家的,可我竟然和她吵架,还对她大声喊过“你回去吧!”我从住宅小区的窗户看着母亲。一直盯着她的背影。母亲穿的是一件褐色带花纹的连衣裙,低着头,慢吞吞地走着。那时母亲已经过了五十岁,我简直畜生不如。
我盖着被子哭个不停,可是再怎么哭,罪行也没有因此得到减轻。在养老院母亲的床上,我说过“对不起,对不起”,可是就算我道歉了,又有谁会原谅我呢?我都不会原谅自己。我感觉自己无地自容,狼狈之极,我决定去北轻井泽。把北轻井泽的房子锁上以后马上回来吧。夜里很晚到家的时候,暖气坏了。
在第二天暖气公司的人来之前,我一直呆在了新井先生家。只有夫人在家。
“天气变冷了啊。天一变冷我有时就会想起往事。我上面是两个男孩儿,下面是两个男孩儿,中间我一个女孩儿,正好中间是女孩儿。我是在母亲身体衰弱了以后才去看她的。去了一看,大冷天竟然开着窗户。我说天这么冷怎么能开窗户呢,就把窗户关了。我对嫂子说,窗户开着不冷吗?结果她说‘是婆婆不让关的,她说这样kimiko来的时候能够看见了’。窗户开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等着我来啊。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了,即便是这样她依然想亲眼看着我来。”
新井先生的夫人用双手捂住了眼睛。“您母亲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夫人掰着手指数道:“去年是十三周年忌,我今年七十三岁吧”然后用手指算了一会儿说:“八十五或者八十六吧。差不多是这个岁数,没错。”然后又用手指捂住了眼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