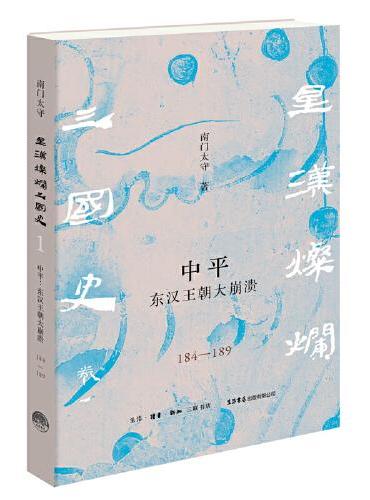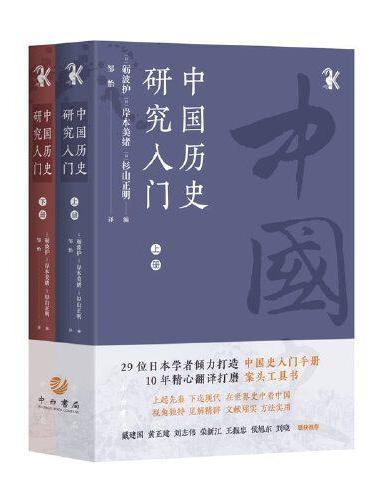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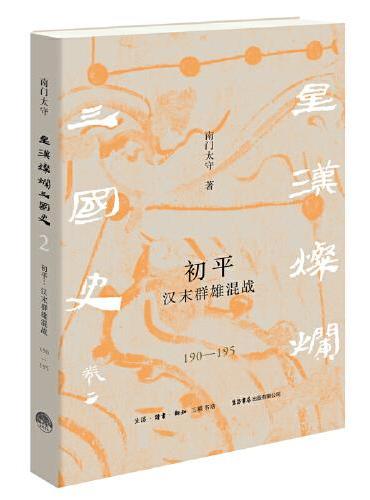
《
初平:汉末群雄混战(190—195)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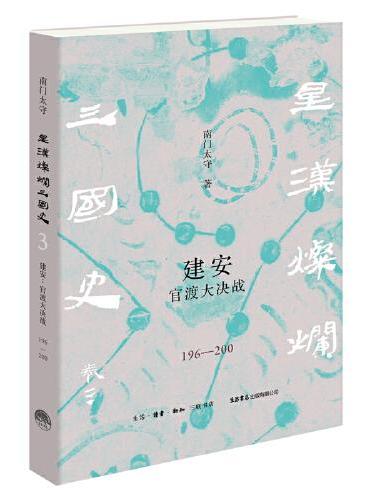
《
建安:官渡大决战(196—200)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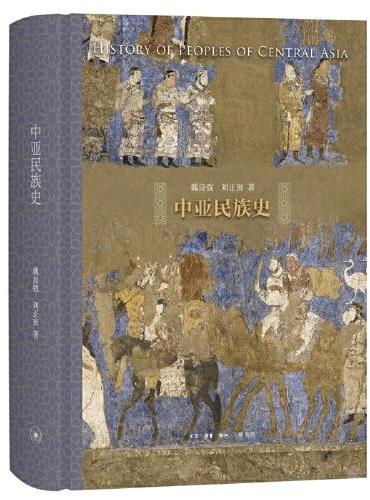
《
中亚民族史
》
售價:NT$
840.0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5912.jpg)
《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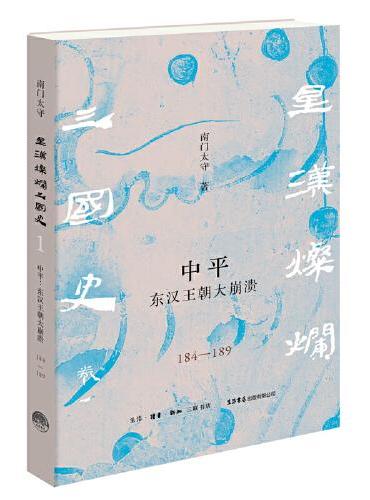
《
中平:东汉王朝大崩溃(184—189)
》
售價:NT$
245.0

《
基于鲲鹏的分布式图分析算法实战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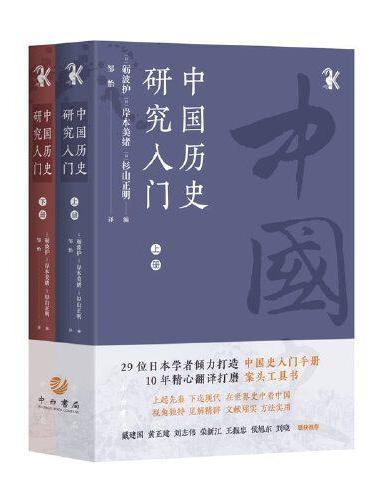
《
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全二册)
》
售價:NT$
1290.0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NT$
299.0
|
| 內容簡介: |
邱妙津长篇小说处女作
震动整个台湾的同性爱情物语
开启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
蒋勋 骆以军 陈雪 推荐
生命地带的边缘,同性情欲的纠结,在冷冷而又无助的人生旷野,倾听邱妙津——
一只寂寞鳄鱼的真挚告白,一曲狂暴热烈的绝望恋歌……
对于这仿佛与生俱来、无法选择更无以更改的同性恋身份,是勇敢面对,还是纠结抗争?直面内心深处的爱和无处放置、无人理解的悲哀到底有多艰难,而再绝望创痛的故事,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刻,都会绽放出令人讶异的温情与美……
“尽管我要再受多大的痛苦与折磨,我还是要述说爱是不灭的。”
《鳄鱼手记》是邱妙津完成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台湾20世纪末大学生迷惘与困顿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全书分为八个章节,其中大部分章节以大学生活为背景,叙述了七个男女主人公的同性、双性恋的情感生活和心路历程,通过解放的性及性别观点,描绘了当时大学生全新的精神世界和得不到认同的感情经历给彼此的成长过程带来的痛苦和收获。其他章节则以一只拟人化鳄鱼的独白,另组合成独立于主要情节之外的寓言,讽刺、影射“鳄鱼╱性异常者”在人类社会孤独、受压迫的命运。这些彼此穿插的叙事线索以复调双声的结构牵动出同一主题的心理及政治层面。
|
| 關於作者: |
震动台湾的一代传奇 用生命创作的天才
以凌厉激烈的才华横空出世,又决绝惨烈地毅然与人世告别
20世纪末台湾文坛最绚烂传奇的女同作家
邱妙津,台湾彰化人,一九六九年生,一九九一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一九九二年赴法国,留学巴黎第八大学心理系,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巴黎自杀身亡,年仅二十六岁。邱妙津多方面的才华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充分显现,曾获得台湾《中央日报》短篇小说文学奖、《联合文学》中篇小说新人奖等,并拍摄有一部三十分钟的十六厘米影片《鬼的狂欢》。
邱妙津的骤然辞世在台湾文坛引起一片惊愕,随即造成一时风潮。同年十月她的首部长篇小说《鳄鱼手记》获得时报文学奖推荐奖,书中的“拉子”、“鳄鱼”等词也成为台湾女同群体袭用的自我称号。翌年遗作《蒙马特遗书》经由友人整理出版,引发全台湾震动,成为台湾女同群体几乎人人必读的经典。
主要文学作品有《鬼的狂欢》《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等。
|
| 目錄:
|
第一手记
第二手记
第三手记
第四手记
第五手记
第六手记
第七手记
第八手记
附录
|
| 內容試閱:
|
我的盲点——序邱妙津简体版作品集(部分)
蒋勋
在文学的阅读上我有我的盲点。
知道是“盲点”,却不愿意改,这是我近于病态的执着或耽溺吧。
年轻的时候,迷恋某些叛逆、颠覆、不遵守世俗羁绊的创作者,耽溺迷恋流浪、忧愁、短促早夭的生命形式。
他们创作着,用文字写诗,用色彩画画,用声音作曲,用身体舞蹈,然而,我看到的,更勿宁是他们的血或泪,是他们全部生命的呕心沥血。
伊冈?席勒(Egon
Shiele)的画,尺幅不大,油画作品也不多,常常是在素描纸上,用冷冷的线,勾画出锐利冷峭的人体轮廓。一点点淡彩,紫或红,都像血斑,蓝灰的抑郁是挥之不去的鬼魅的阴影。
席勒的画里是眼睛张得很大的惊恐的男女,裸体拥抱着,仿佛在世界毁灭的瞬间,寻找彼此身体最后一点体温。
然而,他们平日是无法相爱的。
席勒画里的裸体是自己,是他妹妹,是未成年的少女,瘦削、苍白,没有血色的肉体,褴褛破烂,像是丢在垃圾堆里废弃的玩偶,只剩下叫做“灵魂”的东西,空洞荒凉地看着人间。
人间能够了解他吗?
北京火红的绘画市场能了解席勒吗?
上海光鲜亮丽的艺术家们对席勒会屑于一顾吗?
或许,还是把席勒留给上一个世纪初维也纳的孤独与颓废吧。
他没有活过三十岁,荒凉地看着一次大战,大战结束,他也结束郁郁不得志的一生。
他曾经被控诉,在法庭上要为自己被控告的“败德”“淫猥”辩护。
然而他是无言的,他的答辩只是他的死亡,以及一个世纪以来使无数孤独者热泪盈眶的他的画作吧。
邱妙津也是无言的。
我刚从欧洲回台湾,在一次文学评审作品中读到《鳄鱼手记》,从躺在床上看,到忽然正襟危坐,仿佛看到席勒,鬼魂一样,站在我面前。
我所知道的邱妙津这么少,彰化女中,北一女,台大心理系,巴黎大学博士候选,这些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学历。
我所知道的第二个有关邱妙津的讯息就是她的持刀“自杀”了。
我们可以用“死亡”去答辩这个荒谬的世界吗?
于是,我读到了《蒙马特遗书》。
台湾战后少数让我掩面哭泣的一本书。
……
精彩选摘
第一手记
1
公元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从教务处注册组的窗口领到大学毕业证书,证书太大,用两手抓着,走在校园里掉了两次,一次落在路旁的泥泞,用衣服擦干净,另一次被风吹走,我在后面不好意思地追逐,它的四个角都折到。心里忍住不能偷笑。
“你过来时能不能顺便带一些玩具过来?”鳄鱼说。
“好啊,我带来我亲手缝制的内衣好了。”太宰治说。
“我送给你全世界最华丽的画框,可以吗?”三岛由纪夫说。
“我把我早稻田的毕业证书影印一百份贴在你的厕所。”村上春树说。
就从这里开始。奏乐(选的是《两只老虎》结束时的音效)。不管学生证和图书证没交回,原本真遗失,十九日收到无名氏挂号寄回,变成谎报遗失,真无辜,不得不继续利用证件“方便行事”。也不管考驾照的事了,虽然考了第四次还没考过,但其中可有两次是非人为因素,况且我对外(或是社会)宣称的是两次失败的纪录。不管不管……
把门窗都锁紧,电话拿开,坐下来。这就是写作。写累了,抽两根烟,进浴室洗冷水澡,台风天风狂雨骤,脱掉上半身的衣服,发现没肥皂,赶紧再穿好衣服,到房里拿一块“快乐”香皂,回去继续洗。这是写“畅销”作品。
边听深夜一点的电台,边抹着肥皂,一声轰响,电厂爆炸,周围静寂漆黑,全面停电,没有其他人在,我光着身子出浴室找蜡烛,唯一的打火机临时缺油,将三个小圆柱连身的烛台拿进厨房,中间踢倒电风扇,用瓦斯炉点火,结果铜的烛台烧熔而蜡烛还没点燃。无计可施,打开门走到阳台上乘凉,希望也能看到光着身子走出阳台的其他人类。这是写“严肃”作品。
如果既不畅销又不严肃,那就只好耸动了。一字五角钱。
这是关于毕业证书和写作。
2
从前,我相信每个男人一生中在深处都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原型”,他最爱的就是那个像他“原型”的女人。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深处的“原型”也是关于女人。一个“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冻濒死之际升起最美的幻觉般,潜进我的现实又逸出。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绝美的“原型”,如此相信四年。花去全部对生命最勇敢也最诚实的大学时代,只相信这件事。
如今,不再相信,这件事只变成一幅街头画家的即兴之作,挂在我墙上的小壁画。当我轻飘飘地开始不、再、相、信,我就开始慢慢遗忘,以低廉的价钱变卖满屋珍贵的收藏。也恍然明白,可以把它记下了,记忆之壶马上就要空,恐怕睡个觉起来,连变卖的价目单都会不知塞到哪儿。
像双面胶,背面黏上的是“不信”,同时正面随着黏来“残忍的斧头”。有一天,我如同首次写成自己的名字一样,认识了“残忍”:残忍其实是像仁慈一样,真实地存在这个世界上,恶也和善具有同等的地位,残忍和恶只是自然,它们对这个世界掌握一半的有用和有力。所以关于命运的残忍,我只要更残忍,就会如庖丁解牛。
挥动残忍的斧头——对生命残忍、对自己残忍、对别人残忍。这是符合动物本能、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四位一体的支点。二十二岁逗点。
3
水伶。温州街。法式面包店门口的白长椅。74路公交车。
坐在公交车的尾端,隔着走道,我和水伶分坐两边各缺外侧的位置。十二月的寒气雾湿车内紧闭的窗墙,台北傍晚早已被漆黑吞食的六点,车缓速在和平东路上移行,盆地形的城里上缘,天边交界的底层,熨着纤维状的橙红,环成光耀的色层,被神异性的自然视景所震撼的幸福,流离在窗间,流向车后车流里。
疲惫沉默的人,站满走道,茫然木立的,低头瘫靠座位旁的,隔着乘客间外套的隙缝,我小心地穿望她,以压平激动不带特殊情感的表情。
“你有没有看到窗外?”我修饰我的声音问她。
“嗯。”微弱如羽絮的回声。
一切如抽空声音后,轻轻流荡的画面,我和水伶坐在双人座的密闭车内,车外辉煌的街景、夜晚扭动的人影,华丽而静抑地流过我们两旁的窗玻璃。我们满足,相视微笑,底下盲动着生之黑色脉矿,苦涩不知。
4
一九八七年我摆脱令人诅咒的联考制度,进入大学。在这个城市,人们活着只为了被制成考试和赚钱的罐头,但十八岁的我,在高级罐头工厂考试类的生产线上,也已经被加工了三年,虽然里面全是腐肉。
秋天十月起住进温州街,一家统一超商隔壁的公寓二楼。二房东是一对大学毕业几年的年轻夫妻,他们把四个房间之中,一个临巷有大窗的房间分给我,我对门的另一间租给一对姊妹。年轻夫妻经常在我到客厅看电视时,彼此轻搂着坐靠在咖啡色沙发上,“我们可是大四就结婚的哦。”他们微笑着对我说,但平日两人却绝少说一句话。姊妹整晚都在房间里看另一台电视,经过她们门外传来的是热络的交谈,但对于屋里的其他居民,除非必要,绝不会看一眼,自在地进出,我们仿佛不存在。所以,五个居民,住在四房一厅的一大层屋里,却安静得像“哑巴公寓”。
我独居。昼伏夜出。深夜十二点起床,骑赭红色“捷安特”脚踏车到附近夜市里买些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之类,回到住处边吃边看书,洗澡洗衣服,屋内不再有人声和灯光。写一整夜日记或阅读,着迷于齐克果和叔本华,贪看呻吟灵魂的各类书,也搜集各色“党外”周刊,研究离灵魂最远的政治闹剧的游戏逻辑,它产生的疏离效果,稍稍能缓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点天亮,像见不得光亮的夜鼠,把发烫的脑袋藏到棉被里。
状况佳是如此。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整晚没吃任何一顿,没洗澡,起不了床,连写日记与自己说话、翻几页书获得一点人的声音,都做不到,终日里在棉被里流淌蓝色和红色的眼泪,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没有用。没必要。会伤害自己和犯罪。
家是那张蓝皮的金融卡,没必要回家。大学暂时提供我某种职业,免于被社会和生活责任的框架压垮,只要当成简陋的舞台,上紧发条随着大众敲敲打打,做不卖力会受惩的假面演出,它是制造垃圾的空荡荡建筑物,奇怪的建筑,强迫我的身体走进去却拒绝我的灵魂,并且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更可怕。两个“构造物”,每天如此具体地在那儿,主要构成我地供人辨识,也不断地蠕动着向我索求,但其实抽象名词比不上隔壁的统一超商更构成我。
不看报。不看电视。除必点名的体育课外不上课。不与过往结识的人类做任何联络。不与共同居住的人类说话。唯一说话的时刻是:每天傍晚或中午到辩论社,去做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际练习功课。
太早就知道自己是只天生丽质的孔雀,难自弃,再如何懒惰都要常常梳刷羽毛。因为拥有绚丽的羽毛,经常忍不住要去照众人这面镜子,难以自拔沉迷于孔雀的交际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基本坏癖之一。
但,却是个没有活生生众人的世界。咱们说,要训练自己建造出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要习惯“所谓的世界就是个人”这么样奇怪知觉的我,要在别人所谓的世界面前做淋漓尽致的演出。
因为时间在,要用无聊跑过去。英文说run through,更贴切。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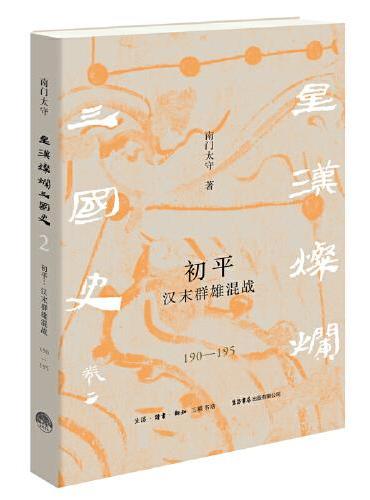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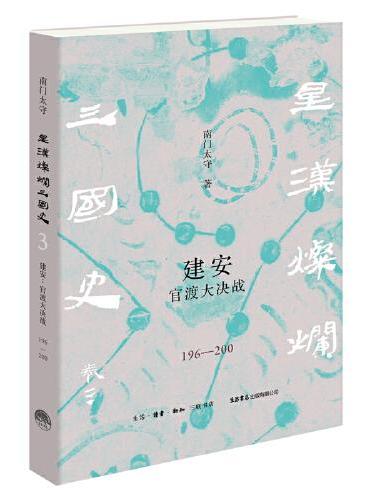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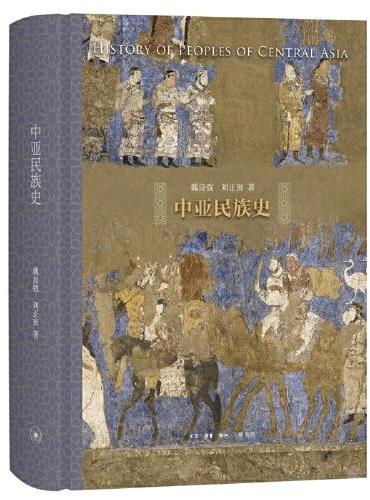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59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