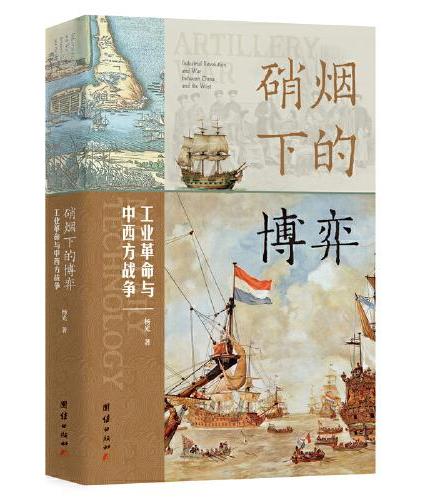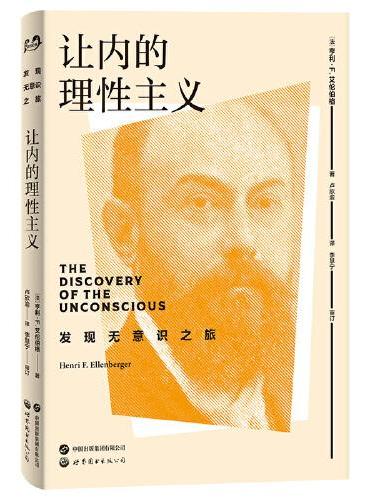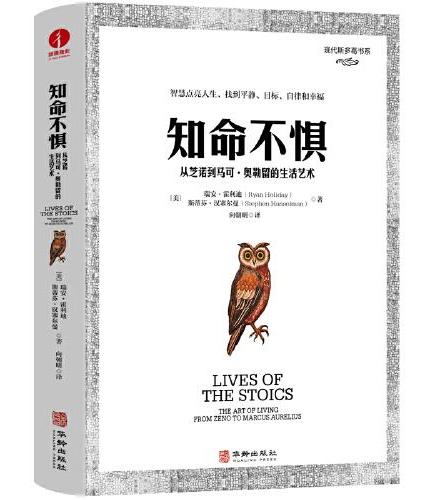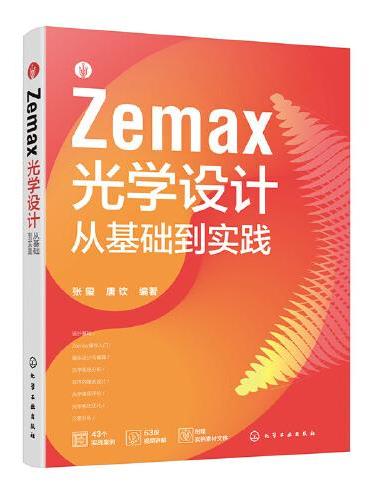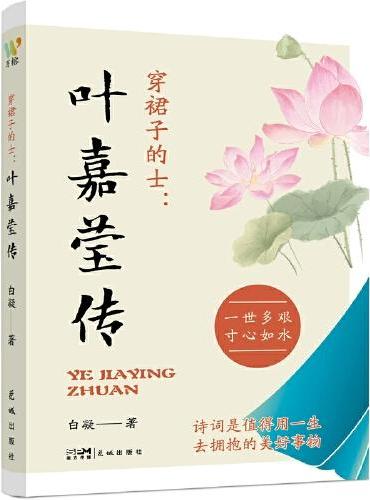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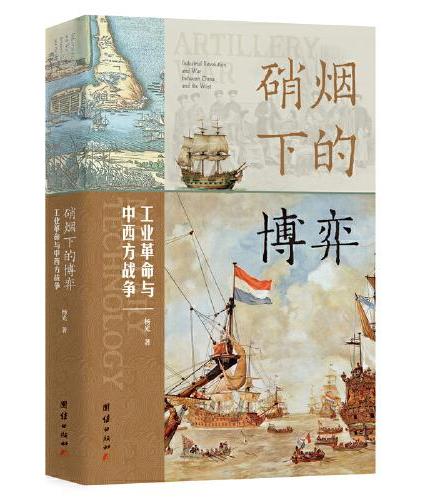
《
硝烟下的博弈:工业革命与中西方战争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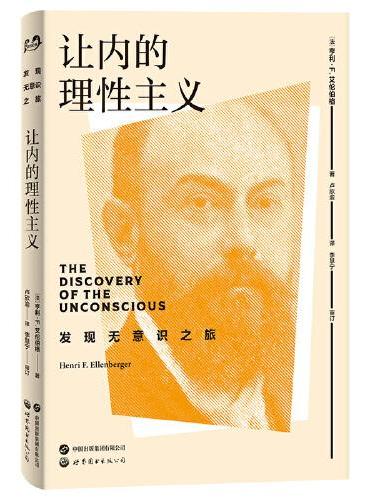
《
让内的理性主义 发现无意识之旅
》
售價:NT$
301.0

《
苏美尔文明(方尖碑)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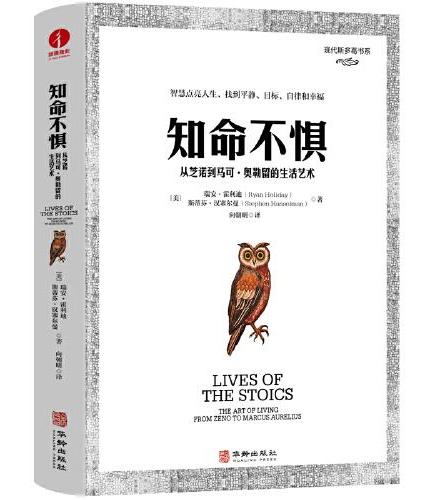
《
知命不惧:从芝诺到马可·奥勒留的生活艺术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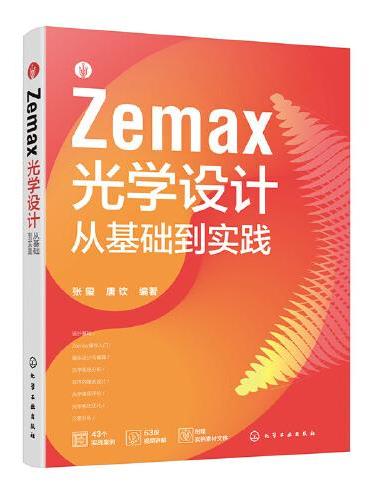
《
Zemax光学设计从基础到实践
》
售價:NT$
602.0

《
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
》
售價:NT$
500.0

《
危局
》
售價:NT$
3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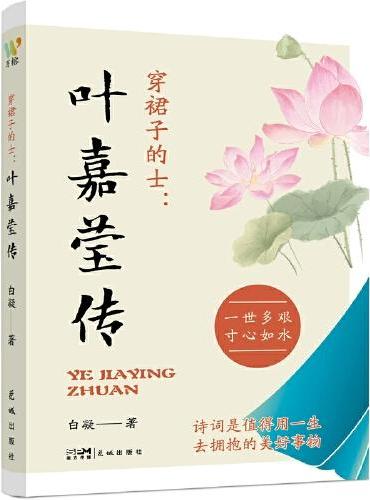
《
穿裙子的士:叶嘉莹传
》
售價:NT$
245.0
|
| 編輯推薦: |
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作家!
“北京娃娃”再次锐叫!义无反顾袒露着“残酷青春”的少女作家——春树全新半自传体小说:欢乐”到底是一场性爱,还是吞云吐雾后的迷幻,抑或是被彻底撕裂的感觉?一部代表着一代人愿望的宣言书!
这是当代中国的《在路上》吗?“北京娃娃”继续在青春的场中疯狂游走。
在这部充满着痛楚与麻木、爱与恨、热情与坍塌的小说中,一群新生代的孩子赤裸着浮出水面,眼神充满着忧怕迟疑和疯狂……
|
| 內容簡介: |
这位义无反顾袒露着“残酷青春”的少女作家,始终在空漠的人海,喧嚣的城市中呐喊着,奔突着。在这本全新半自传体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里,“欢乐”到底是一场性爱,还是吞云吐雾后的迷幻,抑或是被彻底撕裂的感觉?
从14岁的叛逆女生,到国际知名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道出了新生代不为人知的忧郁和暗地里的颤粟……
从一个朋克少年到《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春树用她的奋不顾身,甚至是盲目冲动,创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迹,即以“残酷青春”书写中国新生代的经典,美国人称她是“新激进分子”。
《长达半天的欢乐》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在路上》一群中国年少的凯鲁亚克赤裸着浮出水面,眼眸中充斥着忧郁、迟疑与痴迷。这是一部代表着新新人类愿望的情感白皮书——我们正过着愚蠢的青春,我们乐此不疲!
我们还年轻,我们渴望上路!
|
| 關於作者: |
|
春树,1983年生于北京,2000年从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小说。以“残酷青春”的写作成名,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等,主编《80后诗选》。2004年2月成为美国《Time》的封面人物,2004年9月应邀前往挪威参加国际诗歌节。《北京娃娃》的外文版权已卖至美国、英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芬兰,挪威,日本,以色列,香港,台湾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
| 目錄:
|
前言
第一章 那种感觉叫“麻木”
第二章 像火一样的经历
第三章 听到了留言
第四章 忽然感到冷
第五章 让无力者有力
第六章 长安街少年
第七章 无聊的斗争
第八章 从我眼里流出的是冰雹
第九章 你忘了
第十章 愚蠢的青春
|
| 內容試閱:
|
这个夏天是由认识李小枪开始的。
那是一场演出的结尾处。不,还没有演完我就应该已经认识他了。我就是在那个夏天认识他的。
那天我喝多了,蹲在铁栅栏那里吐。崔晨水跑过来帮忙,他给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一边给我递餐巾纸一边关切地问:春无力,你没事吧? 没事。
在几乎所有的时候我都会说没事。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事,不知道有没有事当然是没事。
我吐得有些神智不清,只知道崔晨水在关心着我,为我着急。看着铁栅栏前面的铁轨,我慢慢浮起一个意味模糊的笑容。
李小枪就是在那时候走向我的。
根据我早已模糊的记忆,我记得李小枪的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啤酒在这里单独写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他先是向崔晨水笑了笑,然后看了看我,对崔晨水而不是我说:“她没事吧?”
由于他的眼里闪动着恰倒好处精明和猎奇的光,我并没有把他的举动理解为关心。
接下来的时间有点像电影片段,而且是定格的那种。演出还没有结束,“乐乐乐”酒吧的门口依然聚集着一堆闲杂人等,我扶着栅栏和崔晨水的肩膀站起身,一阵摇晃。走到“乐乐乐”门口的石头上,坐下去。身边都是不认识的人,以往要是这样我肯定会很尴尬,但今天在酒精的润滑和鼓励下,我已感觉不出太多感觉,体会不出更深的尴尬。
我好像还管人要了一口冰棍吃。在酒精的安慰下,我变得更大胆,敢于做一些不喝酒时不敢做的事。有人举着冰棍站在我前方不远处的铁柱子底下聊天,我没看清他的脸。我走过去,冲着他说道,语速尽量放慢:“
给我吃一口。”他看了我一眼,递给我。我咬下去,傻乐起来。 “干脆都给你了。” “谢谢。”我说。
过了一会,我问崔晨水,那个人是谁。他说叫五五五,是“逆子”的主唱。北京新朋克乐队。那天我穿一件红T恤,左手夹烟,右手拿酒瓶,我的红T恤在灯光下浓得滴血。我变得更自由,在前台自由蹦跳。一切像是在梦游,我像是踩在了云彩里,软绵绵的。就算不时有人撞我的肩膀,说我的烟烫到了他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好心情。或者说,当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时,就顾不得什么心情不心情了。
等等,我觉得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崔晨水和一些朋友去大排挡吃了东西,席间李小枪并不在。但如果他不在,后来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又记得第二天我和崔晨水去了清华大学,还有演出时认识的一个外地大学生。那个外地大学生留着短头发,小个子,眼睛大大的,像年轻的查海生。但第二天我并没有去大学,因为那天下雨了。确切地说雨是从后半夜下起来的,越下越大。后来就是瓢泼大雨。
我们坐着的地方头顶有塑料棚子,但仍然挡不住那场雨。行了,先不提雨了……
那天李小枪应该在场。崔晨水笑着对我说:“春无力,你知道吗?今天所有来看演出的北京朋克都向我打听你是谁。”
“不会吧?怎么了?”李小枪说:“乐乐乐酒吧已经好久没有女孩在撞了,当时我看见你在铁栅栏那里吐,觉得你特别可爱。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认识这个女孩。”
饭桌上的气氛在变化。崔晨水已经不笑了,他有些警惕地看着李小枪,别的人大部分是武汉来的乐手,他们有几支武汉乐队一边吃饭一边注意我和李小枪的动静。我没发现任何不妥,心无旁怠地和他继续聊着——
聊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忘了。雨一直下。
我和李小枪已经有点晕了,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不断地冲他嘻嘻地笑,李小枪拉住我们胳膊,也在笑。我们一边笑着一边接吻,感到兴高采烈。崔晨水气得够怆,他一直暗示我李小枪是个喜欢“戏果儿”的男孩,跟着他是极其短暂的和没谱的。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和一个刚刚还很陌生的小孩儿表示亲昵,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这种感觉真过瘾。何况我也没想和一个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都陆续走了。也许他们有打车回家的钱。只剩下我和李小枪两个人。
屋里已支起摊煮粥,混沌,卖早点。天都亮了。我们分别要了一碗粥。“咱们交朋友吧。”我对李小枪说。 “你还晕着呢现在。”他清醒地说。
“也是,我现在头脑不清醒。”我抱歉地冲他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要不然你当我女朋友吧。”他说,然后飞快接道:“现在我头又晕了。”喝了半碗粥,我们相互凝视一眼:还行,现在应该成了。
我们再次拥抱了一下,确定了现在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刚才酒后的冲动。李小枪把头靠过来,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离开我我就杀了你。我打了一个哆嗦,把这句话当成了一个玩笑话,有点想笑。威胁别人或自己想死一定要别人知道,在我看来都是可笑的表现。我之所以没笑,一是因为此时笑出声来太破坏气氛,有故意搞笑解构的嫌疑;二是李小枪的脸在那一秒钟居然十分严肃,虽然我怀疑他严肃的来由。我随手拿起他挂在脖子上的银链,上边挂着一把刀片。为什么挂刀片?我找出一个话题来问他。
就是,我可以随时去死的意思。
哦。我应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但是觉得他这种“可以随时去死”的想法不错。应该可以实施。不就是一个死嘛!而且是随时的、主动追求的,也就是说,可以把这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年轻人,不死还能干嘛呢?反正大家都处在没什么理想中我还算是有点理想,闲着也是闲着。想想死亡就兴奋——是不是特无知?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我成了李小枪的女朋友,我们俩像突然成立了一个团体似的,都在憧憬以后在一起的自由新生活。显而易见,我们都是对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人,在一起绝对很好玩。
不能在这里再呆下去了。我们到旁边一个杂货店买了一把廉价雨伞,他骑着我的自行车带我回家。我们住得很近,都是海淀区,我万寿路,他五棵松。一听就知道彼此都是军队大院里长大的。路上积满了水,我在他身后打着伞,可是不管用,雨下得那么大,什么伞都不管用了。看着他奋力地在泥水里骑车,我感得一阵新鲜和满足。快到花园桥时我们停车到一车饭馆去接着吃饭。饭馆装修得高大明亮,不禁担心起吃饭的钱来。
可看到李小枪的光头,我又踏实了。不是还有他在吗?有他在我就不用担心了。吃完饭出来时,李小枪脱下脚上被雨浇得湿淋淋的鞋,光脚走出门,一点也不管别人看他的目光。他说这是方便骑车。李小枪长得很瘦,衣服湿淋淋地贴在身上,显得轮廓分明,看上去十分冷酷,有一点新纳粹的样子。我突然觉得他这样子非常好,非常自在。
李小枪带我回到他的家。他家住在一幢稍显破旧的居民楼,楼对面还有几幢同样结构的楼房。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摆满了鸟笼、花盆、晾的衣服,五颜六色,密密麻麻。
似乎从中都能看到他们每天热火朝天、自得其乐的生活。我钻进那幢楼的三号门,感慨道:这儿真他妈的生活化!“可不是嘛,”李小枪边上楼梯边说:“都是一帮小市民,没事儿就聚在一块聊天,谁家干什么都知道,特没劲。哎,我妈可能在家,一会你别忘了喊阿姨。”
我们刚踏到了四层楼梯上,有一扇门就应声而开了,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矮小、穿一身颜色灰暗家居服的中老年妇女探出头来看着我们。“阿姨。”我喊道。
阿姨应了一声,打量了我们一下,把门打开了。 他的房间有些暗。
李小枪哐地锁上屋门,一把把窗帘拉上。整间房间显出一种暗黄色,很舒服的颜色。我一眼看到一架有些旧了的架子鼓。墙上用彩笔写着一些口号,诸如“要做爱,要做战”、“吻你爱人的时候,手不要离枪”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些口号已经没有什么激励人的意思了。它们太旧了。墙上还画着几张画,其中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大脑袋的小孩,看起来有点弱智。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李小枪临摹的几张他喜欢的乐队的唱片封面。因为我曾有过一个画画的男朋友李旗,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对画画的男人没什么好印象。李小枪的画也同样没给我留下好印象。自从离开李旗,我就认为所有画家都是思维飘渺、不现实的动物。李小枪的床尾有一台电视机。床很低,床单和枕头都是那种很旧,洗得有些发白的颜色。外面雨还在下,比刚回来时要小了一些。那是一种翠绿和暗黄结合的颜色。绿的树,黄的是天色。我们好像聊了几句。然后就躺下睡了。醒了时天已经睛了。这时已经下午四、五点了。
外面已经不下雨了。天色是通常夏日特有的透明和金黄色。阳光是暖烘烘的,空气又是清新凉爽的。我们沿着大街走着。树绿得让人想对生活感恩。这是北京海淀西部,到处都是军队大院,不时就能看到穿着军装的军官战士。路过的军队大院门口有军人站岗。有的大院里面还竖着伟人雕象,伟人正在挥手。还有的大院正面进出的地方竖立着红色的牌子,最常见的是“为人民服务”,还有“向雷锋同志学习”等。每当路过这种军队大院时,我和李小枪都觉得心里非常舒服。我们都是那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父母从不同省的农村当兵,后来进城,所以我们能出生在城市,从小和我们一样出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搬家也都是搬到不同的军队大院,每天早上都能听到附近的军人唱歌、跑步。长在军队大院中的孩子通常都比较单纯,不谙世事。
我们到了一家看上去还算比较干净的饭馆,考虑半天,只点了一盘排骨。在等上菜的时候,我们也在彼此打量对方: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身体上熟悉了但精神上还比较陌生。怎么能从肉体过渡到精神是目前我们所要考虑的。对面李小枪的目光比较隐忍,可能在为他没钱感到抱歉。我就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段饭吃得有些索然无趣。在我觉得比较无趣的时候,一般我都会提出回家。可能是第一次吃饭时不浪漫控制了我和李小枪的交往。P2-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