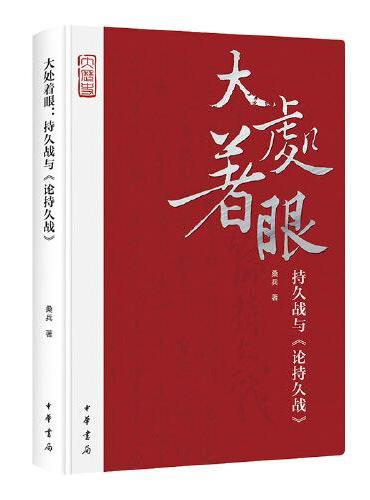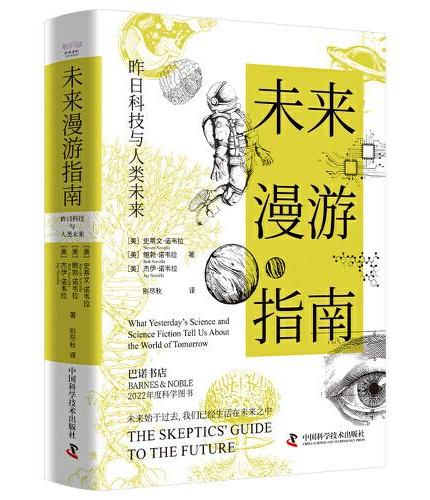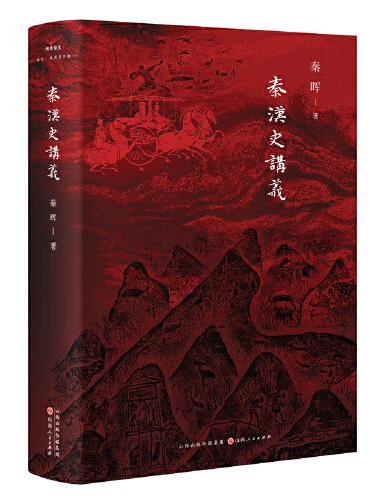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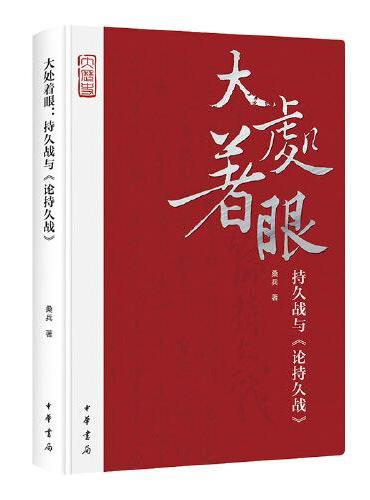
《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
》
售價:NT$
3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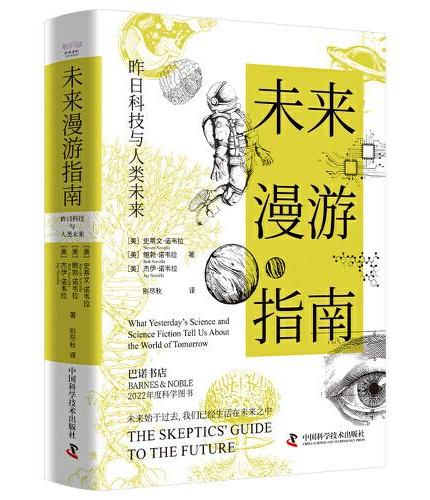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NT$
390.0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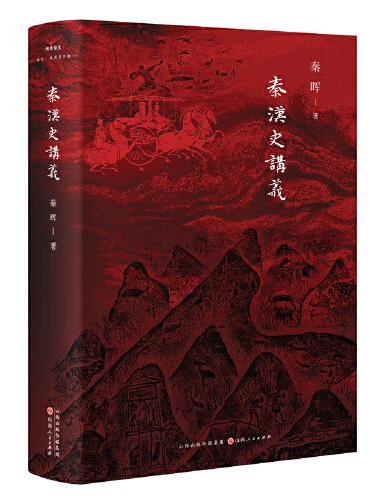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NT$
690.0
|
| 編輯推薦: |
1.横扫美国各大畅销榜单,美国《纽约时报》《书单》《柯克斯书评》《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出版人周刊》《波士顿环球报》《俄勒冈人报》《奥尔巴尼联合时报》《费城询问报》《哈特福德新闻报》《图书馆报》等媒体争相推荐;
2.本书脱胎于这位美国畅销书作家的真实经历,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述了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如何走出悲痛的阴影拥抱新生,刻画深入,故事生动,极具感染力,非常值得阅读;
3.无论是从封面设计还是文字内容都极具文艺味,非常符合当下有购买能力的读者对于文艺书的各类感官要求。
|
| 內容簡介: |
在突然失去了5岁的女儿斯特拉之后,玛丽?巴克斯特一蹶不振,无法阅读,也无法写作。
在母亲的建议之下,她不情愿地加入了一个编织会。她开始尝试用编织来填满自己空虚的时光——而她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举动将会改变她的生活。
编织会的每个女人轮流教给玛丽一种新的编织技巧,与此同时,她们也对玛丽坦白了自己关于失去、爱以及希望的秘密。
最终,在她们一起编织、闲谈的时光里,玛丽敞开心扉,对她们讲述了自己的悲伤故事……
|
| 關於作者: |
安·霍德
美国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著有《红线》《编织会》《远离缅因海岸的地方》等多本畅销小说。
由她所著的回忆录《安慰:穿越悲伤的旅程》,是《纽约时报》编辑2009年度重磅推荐的好书,并被评为2009年最佳非小说读物前十名。
本书《编织会》的故事脱胎于她的回忆录,一上市便受到各方媒体的强力关注,并跻身美国各大畅销榜前列。
|
| 目錄:
|
第1 部
起针
1 玛丽
2 编织会
第 2部
两针平针,两针反针
3 斯嘉丽
4 编织会
第3 部
两针并一针
5 露露
6 编织会
第4 部
袜子
7 爱伦
8 编织会
第 5部
成为好的编织者
9 哈里特
10 编织会
第6 部
坐下来,编织吧!
11 艾丽丝
12 编织会
第7 部
母亲和孩子们
13 贝丝
14 编织会
第8 部
编织
15 罗杰
16 编织会
第9 部
共同的苦难
17 玛米亚
18 编织会
第10 部
收针
19 玛丽
20 编织会
|
| 內容試閱:
|
女儿,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试着想要告诉你。这个故事不会像小象巴巴尔或者艾萝依那些你爱听的童话一样有趣,事实上,这个故事既没有意思,也不够聪明。这只是个简单真实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然而我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你讲述。于是,我拾起了我的编织针,开始编织。每一针就代表一个字母,一行字母拼出一句“我爱你”。我在我织的每一件东西上都会织上“我爱你”。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祈祷,或者说是一种祈愿。我要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听得到。我的女儿,多希望有一天我的故事能够通过这些编织传达给你,多么希望我的爱也能让你感受到。
第1部 _ 起针
编织,每一针都像是在针尖上跳舞。“起
针”在编织里是指织出最初的一段针。一旦你
开始起针,就意味着你准备继续织下去了。
——南希?J . 托马斯 ,伊拉娜?拉比诺维茨
《编织的热情》
1 玛丽
玛丽两手空空地出现在那里。
“我什么都没带。”玛丽说着,还将双臂摊开来,示意里面真的什
么也没有。
站在玛丽面前的女人叫大艾丽丝,但是她身上真没什么东西算得上是“大”的。她身高约五英尺,腰肢纤细,短发银白色,眼睛像是暴风雨来临前天空的颜色。大艾丽丝瘦小的身体倚靠着破旧的木门,面对着玛丽和这个小店。
“这真不是我的风格。”玛丽略带歉意地说。
女人点点头。“我知道,”她说着,向后退了几步,使门敞开得更大一些,“曾经有数不清的人,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跟你说着完全一样的话。”女人的声音很柔和,英式口音。
“好吧!”玛丽应了一声,她也不知道此刻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者该做些什么。现在是九月份了,她的小女儿斯特拉已经音却越来越强烈:医院里的嘈杂声,医生的说话声,还有五岁的斯特拉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妈妈”。有时候,玛丽会想象自己真的听到女儿在大声叫喊着她,而每次,她的心都会不由得缩紧,抽动。
“进来吧!”大艾丽丝说。
玛丽跟在她后面进入店内。艾丽丝穿着一条灰色的粗花呢裙子、一件白色的牛津布衬衫、金色的羊毛衫,还戴着珍珠项链。如果只看上半身,艾丽丝看上去就像个女教师,但向下看,她脚上穿着颜色艳丽的条
纹短袜,拖着双粉色雪尼尔材质的拖鞋,拖鞋的鞋面上还镶着颗用红色的莱茵石做的小樱桃。
“我有痛风,”大艾丽丝抬起一只穿着拖鞋的脚解释道,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就是艾丽丝吧?”
“嗯。”玛丽回答。
玛丽知道自己很容易就会忘记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便签上,那些彩色的纸条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就像是派对上撒下的五彩纸屑。那张写着艾丽丝姓名的纸条,和所有那些写着电话号码、日期以及地址的纸条一样,统统不翼而飞了。还好,店门口就挂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大艾丽丝编织店”,当玛丽看到那个牌子时,她也就想起了艾丽丝这个人。
玛丽停了下来,想确定一下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这些日子以来,她经常会这样,即使是在熟悉的环境里,她也要反复确认自己所在的位置。有时候,她正在自家厨房里,突然就会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环顾四周,像是在清点存货似的。哦,有时她还会自言自语,发现电视是关着的,没有放着《傻瓜猫》;那个斯特拉在黏土时间做的小碗,她精心涂上圆点花纹的碗,此刻也空空的,没有像往常一样盛放着切片黄瓜和堆成小山似的蓝莓;墙上那斯特拉用蜡笔写着“我爱你”的心形剪纸,还有她用彩色美术纸做的风筝,拖着条粉色绸缎的尾巴,此刻就耷拉在那里,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哦,玛丽会再次感叹,再次意识到这
就是她的厨房,这一切就是她现在生活的样子——空洞而悲伤。
艾丽丝的店很小,店里有踩上去嘎吱作响的老旧木地板,还有很多篮子和架子,摆满了毛线。整个屋子都充斥着毛线衫和杉木的味道,还有艾丽丝身上散发出的甜柑橘味。店里有三个房间,这间小屋的不远处摆着个现金出纳机,还有一张老旧的长沙发,沙发上覆盖着粉色和红色花纹的毯子;另一个大一点的屋子里,则有更多的毛线和几把椅子。这些毛线非常漂亮,玛丽一眼就发现了,她跟着艾丽丝从一个屋子
走到另一个屋子的时候,随手触碰着这些毛线,享受着让手指尽可能停留在那些柔软的毛线上的感觉。
“那么,”艾丽丝开口说,“我们就让你从编织围巾开始吧!”她拿起一条编织好的围巾。那是条钴蓝色的围巾,上面还挂着浅蓝色的流苏。“喜欢这条吗?”
“还可以吧!”玛丽说。
“你不喜欢?你在皱眉头。”
“我喜欢,这条很好,只是,我可能做不来。我并不太擅长手工活。小学时我连家政课都不及格,真的。
艾丽丝转向墙壁的另一侧,拿出了一些木质编织针。
“一个十岁的小孩都可以织好那条围巾。”艾丽丝有些不耐烦地说,随后把木质编织针递给了玛丽。
编织针躺在玛丽手中,摸上去很光滑,感觉大而笨拙。玛丽看着艾丽丝走到一个架子前,拿出一些毛线球,有蓝色的、宝石蓝色的,还有淡紫色的。
“你喜欢哪个颜色?”艾丽丝把这些线球摊开在玛丽面前问。
“我想,蓝色的吧,”玛丽犹豫不决地回答,而脑海里却浮现出了斯特拉眼睛里那特别的蓝色。想到这里,玛丽刚想眨眨眼睛,却感觉泪水已经滑了出来。她转过头去,悄悄擦拭掉眼里的泪水。
“嗯,这个是蓝色的。”艾丽丝说,声音多了些温和。艾丽丝指指角落里的一把椅子,椅子上还堆着些胖胖的毛线球。“坐那儿吧!我来教你怎么编织。”
玛丽禁不住笑出声来。“你好有信心啊!”
“两周前,一个女人走进这里,”艾丽丝边说边坐进了一个堆满东西的沙发椅里,抬起双脚架在面前的小脚凳上,脚凳上还盖着条有针绣花边的小毯子,“她之前从没织过任何东西,但她最后还是织出了三条像这样的围巾。就这么简单。”
玛丽驱车行驶了四十英里才来到这家编织店,即使她知道,她家附近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就有一家编织店。就在她行驶在陌生的小路上时,她还觉得自己傻得不可思议,跑那么大老远来编织东西。但是眼下,玛
丽汗津津的手中握着这些令她感觉陌生的编织针,和一个陌生人坐在这里,而这个人对玛丽以及所有发生在玛丽身上的事情都一无所知。玛丽知道,无论如何,这是她眼下应该做的事情。
“这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活结。”艾丽丝说着,举起一长条毛线对着玛丽演示。
“我以前被女童子军踢出去就是因为这个,”玛丽说,“活结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东西。”
“你得先学好家政课,再进女童子军。”艾丽丝啧啧地说,灰色的眼睛里眨巴着淘气的神采。
“事实上,我们是先进女童子军,再学家政课的。”玛丽说。
艾丽丝低声轻笑。“希望这能使你感觉好受些。以前,我很讨厌编织,也压根不想学编织。可现在你看,我有了一家自己的编织店,我教人如何编织。”
玛丽礼貌性地回以微笑。以前,玛丽总是对别人的故事抱有一点小小的兴趣。她常常喜欢听那些伤心的传说、伟大的胜利故事以及一些离奇的生活经历。然而现在,她自己的故事已经取代了所有这些别人的故事。如果她还有必要礼貌地倾听,就像现在这样,这情形就像是在祈求她说点什么,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一样。她一点都不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有些时候,她也曾幻想自己是不是该找个人聊聊自己的故事。
“那么,”玛丽说,“活结是吧?”
“既然你在女童子军和家政课上都不及格,”艾丽丝说,“我就替你起针。另外,如果我站在这里手把手地教你,这是在浪费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因为你很快就会忘记的。”
玛丽并不想费力询问什么是“起针”。艾丽丝就像是个魔术师在演练着手中的小把戏,她拿毛线做了几个圆圈,在手上搓了几下,然后拿起一根针,一排蓝色的线圈就像充满魔力似的像蛇一样盘结在针上。
“我给你起前面的二十二针,然后你自己接下去。”
“哦……嗯。”玛丽有些犹豫地应着。
艾丽丝让玛丽坐到她身边的位置上。
“在这里,”艾丽丝边说边演示,“把毛线像这样裹起来,然后用这根针穿过去。”
第一针后,玛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有一圈线浮在空空的针上。
“好了,”艾丽丝说,“继续吧!”
“我?”玛丽不确定地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怎么做了,对吧?”艾丽丝说。
玛丽深吸一口气,继续。
有一件事玛丽到现在都觉得很奇怪:在斯特拉去世的前一天,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迹象,什么都没有,只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又一个平常日子——她、迪伦,还有斯特拉。他们一家住在旧金山北滩区的时候,有一个邻居,是个叫安吉丽娜的意大利老女人,安吉丽娜总是在头上裹着条黑色的头巾,穿着一身黑色的裙子,脚上蹬着双黑色的厚底鞋。“人们应该知道你是在居丧,”她曾经告诉玛丽,“当你穿一身黑色,人们就会明白了。”玛丽并没有对她指出最近黑色很流行,人人都穿。当安吉丽娜对玛丽说起她丈夫去世前三天所发生的事情时,玛丽不但没有讥笑她,而且听得目不转睛:一只狗在他们的公寓前狂吠,这时候,安吉丽娜迅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并往掌心吐了口唾沫。“我知道死亡就要来了。”她说。几个月前,她的两个邻居死去了。“接着还会有人死去,”安吉丽娜解释道,“会有三个人死去。”安吉丽娜一直在对各种异象唠叨个不停:说她梦到清澈的水,梦到牙齿从嘴里脱落;一只死鸟躺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一只鹅在温暖、静止的空气中跌跌撞撞前行。
但是,玛丽没有感受到任何异象,既没有梦到死去的鸟,也没有看到狂吠的狗。相反,那只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天气不错,斯特拉依然会在早晨喝一瓶牛奶,临睡前也喝一瓶,这可是瞒着她幼儿园朋友的事。迪伦给她带来了牛奶,他俩躲在床上,愉快地吮吸着奶瓶,之后他俩还拥抱在一起。临睡前,玛丽和迪伦读了当天的报纸,斯特拉在看“芝麻街”。
斯特拉早晨醒来之后,他们也知道该起床了。斯特拉只要醒了,她就会开始挠迪伦的胳肢窝。玛丽希望自己可以记起他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早餐的内容,记起他们吃的到底是冻松饼还是肉桂土司,记起他们吃早餐时聊了些什么。然而,那个早晨太平常了,以至于她费尽了力气也无法回忆起那个早晨的种种细节。
她记得斯特拉穿着条纹紧身裤,脚上拖着双带圆点花纹的木屐,还有穿在身上显得过于长的套头针织衫,也是条纹的。她之所以还记得这些是因为斯特拉死去之后,他们从医院回到家里,斯特拉的衣服还皱巴巴地堆在那里,还是她昨晚临睡前脱掉衣服后随手丢弃的状态。而玛丽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拽着这堆衣服,紧紧地凑在鼻子下,用力闻着小斯特拉残留在人间的气息。
那天早晨玛丽正准备送斯特拉去上学,迪伦已先一步离开了。他总是走得比较早,分别在玛丽和斯特拉的额头上亲吻一下后就去上班了。这个时候,斯特拉撅着小嘴,叫嚷着
“爸爸,别走”。玛丽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嫉妒,不过她知道,这也是事实,父母之中,照看孩子最多,接送孩子上下学,为孩子做饭,给孩子洗澡的那个,往往不是最讨孩子喜欢的。
玛丽现在感到很内疚,那天早晨斯特拉又在磨磨蹭蹭的,这令她恼火不已,她为此还对斯特拉大发脾气。斯特拉就喜欢磨蹭、闲逛,她会被任何事情分散注意力,比如找到自己遗失的雨靴,或者把她自己画的烟火挂在冰箱上面。即使玛丽不停地催她,斯特拉也能一边发出嗡嗡的应和声,一边愉快地磨蹭着。跑进车里的时候,她还对妈妈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要迟到了。”那天早晨,玛丽大概也是咕哝了几句,反
正她们经常迟到的。斯特拉大概还“嗯嗯”了几声,随后又嗡嗡地叫嚷着。
那天早晨,玛丽还在幼儿园的咖啡室里和其他母亲一起喝了杯咖啡,分享着她们各自的神奇小孩的各种趣事。之后,玛丽去上班,浪费了她作为母亲最后的宝贵时间,去处理一些无意义的研究和报告。迪伦一如往常地在玛丽下班前打来电话,告诉她晚上自己将会几点到家,询问斯特拉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挂了电话,玛丽就匆忙赶去学校接女儿放学。玛丽坐在车里,张望着学校的大门,直到看到斯特拉那疲倦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小脸出现在视线里,背包的带子都拖到地上了。每当玛丽这样看到女儿斯特拉的时候,她的心就又一次如释重负地吞了回去。
然而,这一天还是和平时有些不同,和斯特拉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玛丽在脑海中反复重演:傍晚时射入厨房的阳光,斯特拉当时正在做她的每周阅读。之后,她们一起点燃烤肉架上的火,斯特拉在鸡肉上淋了些橄榄油,并把门外的桌子、椅子都擦了一遍,然后小心地在每个盘子旁放了餐巾纸。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迪伦刚好走进后院,斯特拉立马扑到爸爸怀里。迪伦咧嘴笑了,愉快地
说:“四月里的烧烤开始啦!”“嗯!”斯特拉兴奋地回应道,“我要在外面吃晚餐喽!”
那天晚上,玛丽将便携式CD机摆在了窗台上,播放着斯特拉最喜欢的舞曲,两个人就光着脚跳起了舞:玛卡瑞娜、小鸡舞,还有林波舞。最后,迪伦也加入了她们,三个人一起又跳又叫,不停地挥舞着手臂。那个美妙的夜晚,长长的月牙高高地挂在天边,如同在为他们祈祷。玛丽一边回忆,一边陷入了沉思。
* * *
斯特拉葬礼的那天早晨,玛丽的母亲打来电话。
“我知道会有很多人陪你,”母亲在电话里说,“我也知道,你能理解我今天早晨赶不过去的原因,最晚一班飞机昨天半夜就起飞了。”
玛丽眉头紧蹙,她简直不敢相信电话里母亲说的话。“你不来了?”她问。到现在为止,她还是无法将自己女儿的名字和“葬礼”或者“死亡”这样的词汇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说出来。
“你会理解的,是吧?”玛丽明显听出电话里母亲的声音中那种恳求的语气。当她还在解释着墨西哥城糟糕的交通,登机口离得多远,海关又是多么复杂的时候,玛丽已静静地挂了电话。
玛丽这一生都对自己的母亲感到失望。她的母亲不是那种会去参加孩子的学校表演或者家长会的母亲,她很少会表扬孩子,但也从不滔滔不绝或者自吹自擂。母亲曾经因为发生在圣米格尔的那场大罢工而错过了玛丽的婚礼,当时她住在那儿,那场罢工使她错过了回美国的航班。
“我会送你一份漂亮的礼物。”母亲说。她也确实这么做了,一周后,一套墨西哥陶器就被送到了玛丽家里,里面一半的碟子都在运送的途中碎掉了。
但在这最最糟糕的时刻,玛丽还是希望母亲能陪在自己身边,用一种安慰的姿态来支持自己,尽管她的母亲至今还从没表现过这种姿态。
玛丽看着教堂里的一张张面孔——她的邻居、她的同事,斯特拉的老师,以及各位亲朋好友——一种失落感顿时涌上胸口,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必须得坐下来,大口吐气。玛丽的母亲真的没来参加外孙女
的葬礼。
她母亲安排送来的花是整个葬礼上最大的一捧,紫色的马蹄莲,多得好像要吞噬掉整个屋子。如果玛丽还有一点儿力气,她会把这些花全部扔掉,连同那华而不实的道歉。然而,她最终只是刻意地忽略了那些花。
斯特拉死后的那个闷热难耐的夏天,玛丽的母亲打来电话。她基本上每周都会打来一次,提供些建议,而玛丽通常根本不和她说话。
“你现在最需要的,”母亲告诉玛丽,“就是去学编织。”
“嗯!”玛丽心不在焉地附和着。
她母亲住在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一个殖民地式样的房子里,那里有一扇明亮的蓝色大门直通庭院,庭院里有喷泉汩汩地流着,还有盛开的粉色花朵。在玛丽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每次经过庭院,她都会停下来喝口那里的泉水。现在,玛丽想到这些才忽然记起,母亲就是从那时开始编织的。有一天,屋子里到处都滚着毛线球,母亲就在厨房的桌子旁,一边研究着各种花式,一边喝着咖啡,咀嚼着薄荷糖。
“我听说,你不能工作,不能思考,也不能阅读。”
母亲说着这些的时候,玛丽哭了起来。最初听到斯特拉的噩耗时,那种清醒的痛几乎将她毁灭,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的痛哭。她的世界,在这之前一直阳光明媚,然而一瞬间就像被炸开了锅一般危机
四伏。商店里摆满了夏天里斯特拉最爱吃的浆果;电梯里总是能听到斯特拉最爱听的歌曲;不管玛丽走到哪里,总能见到一些熟悉的人——一些葬礼后就再没见过的熟人。每当他们见到玛丽,脸上就会露出同情的表情。玛丽真的想要逃离这些人,逃离那些浆果,还有电梯里的音乐,逃离这整个曾经让她和斯特拉感到如此安全的世界。
“编织是大有学问的,”母亲还在说着,“你必须专注其中,但一点儿也不费事。你的手指不停地动着,编织着,而你的大脑也在这同时得到了平静。”
“好的,妈妈,”玛丽终于开口,“我会去了解的。”
挂了电话,她又爬回床上去睡觉了。
从斯特拉出生的那天夜晚开始,玛丽就承诺,她们会是一对非同一般的母女。玛丽将努力成为一个自己从小就期待拥有的母亲,而斯特拉将可以自由地做她自己。对此,玛丽一直遵守着自己的承诺。就算是要耽误自己的工作时间,她也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只为斯特拉的填充玩具做开派对用的帽子。她会允许斯特拉在家里也穿着带有波尔卡圆点条纹的衣服和从商店买来的芭蕾舞短裙,戴着橘黄色的护耳套。
玛丽和斯特拉,她们太像了。她们都有同样棕色的头发,在阳光强烈时或盛夏时节,头发上都有一部分红色的发束会特别显眼。她们的嘴巴相对于细长的脸型,都显得有些宽大,但也正是这张大嘴,使她们拥有迷人的微笑。玛丽的父亲就长着这么一张嘴,玛丽和斯特拉都继承了这一点,但随着父亲逐渐衰老,他的嘴巴也慢慢向下弯了,看上去就像是一张糟糕的画里面那耷拉着的悲伤脸孔。
迪伦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玛丽压根儿不需要他就能造出斯特拉来。
“她跟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说。斯特拉身上唯一一样仅属于她自己的特征,就是那双蓝色的眼睛。迪伦和玛丽的眼睛都是棕色的,然而斯特拉却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其实这双眼睛不无一些玛丽母亲的特征,只是玛丽不愿承认罢了。不管怎样,整体的效果就是,斯特拉是微缩版的玛丽,从头一直到她那双细长的小脚。等斯特拉长大了,她俩穿鞋的尺码说不定都一样。
最有趣的是,有时候,她们都会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斯特拉就会拉着玛丽一起站在衣橱背面的穿衣镜前面,两个人对着镜子一同挤眉弄眼地傻笑。“你和我长得太像了!”斯特拉会自豪地说。而这个时候,玛丽感觉自己的心都膨胀了起来,就如同要从肋骨中爆出来一样。她一直都很好地遵守着自己的承诺。她是一个好母亲,而她的女儿也非常爱她。
当玛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生活总是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严苛至极,她的一切几乎都在母亲的掌控之内。早餐时齐全的食物组合,鞋子和书包都要搭配得当,头发永远被扎成两条整齐的小辫子,紧得玛丽在学校里一直觉得头痛,直到放学回家后松开辫子才会好受些。那时候,她总会坐在一边,畏畏缩缩地摩挲着自己的脑袋。
随着玛丽逐渐长大,她明白了,所有她母亲的规则,所有施加在玛丽身上的秩序,都只是为了掩盖母亲酗酒的事实。每次放学回家,玛丽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做功课,她总是在这时强烈地渴望与母亲在一起。而母亲这时正在做晚餐,一边做饭一边吮吸着杯子里的水。《烹饪的乐趣》静静地立在合成树脂做的烹饪书架上。玛丽觉得非常讽刺,因为这本书竟然是母亲选择的书,而母亲对烹饪和饮食几乎没有任何乐趣。
然而,每天傍晚,玛丽还是坐在厨房的桌边,有时候她会叫母亲帮忙,尽管也并非必需,只是她觉得这样可以有机会亲近母亲罢了。玛丽会在母亲靠近的时候观察她那张美丽的面孔、光滑的皮肤,还有完美挺翘的鼻子、闪亮的金发,每次她都会爱上这个陌生的人。母亲身上的香奈儿5号香水的味道围绕着玛丽,让她觉得有些晕眩。
有些夜晚,母亲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时,父亲就会像童话里的王子抱起睡美人般将母亲抱在怀中,送到床上。“你妈妈工作太累了。”
回来的时候,父亲会这样说。玛丽只能点点头,尽管她完全不明白,除了偶尔打扫卫生,母亲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如此操劳。玛丽上高二的时候,一天晚上正在洗碟子,她将那只杯口沾着母亲玫瑰红唇膏的水杯压在自己的唇下,可以尝到唇膏的蜡味,她轻轻地抿了一口,一股浓烈的伏特加味扑鼻而来。玛丽顿时明白了,所有那些母亲专注做饭的傍晚,所有那些母亲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夜晚,原来都是母亲喝醉了的时候。意识到这些并没有让玛丽吃惊,相反,这解释了所有的一切,唯独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如此漂亮的女人要喝那么多酒。
那个忧伤的夏日,时间无情地流过。玛丽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应该做什么——为斯特拉穿袜子,为斯特拉把三明治上的面包皮切掉,滔滔不绝地聊一项新的艺术活动,催斯特拉上芭蕾舞课……然而现在,玛丽待在家里,拿眼前这无止境的时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玛丽为当地一家标新立异的报社撰写文章,报纸的名字叫《八日一周》,简称《八日》。玛丽主要写些关于电影、餐厅和书籍的评论文章。自从斯特拉死后,玛丽的老板埃迪每周都会给她打电话,布置给她一些小小的工作任务。“就一百字,”他说,“不管是关于什么的,你就写一百字。”办公室经理霍莉会带着自己刚烤好的奶油蛋糕来看玛丽。玛丽老远就瞥见霍莉从她那辆淡蓝色的甲壳虫汽车里走出来,一头淡黄色的金发,眼睛又大又圆。她从车里伸出修长的双腿,双眼含泪地望着玛丽的房子。这个时候,玛丽会假装自己不在家。霍莉通常会连续按十几下门铃才会放弃,把甜点留在门前的台阶上。甜点有时是红糖丝绒蛋糕,有时是香甜的奶油蛋糕,点缀着罐头菠萝,或醉樱桃,或特别甜的椰果。
以前,玛丽通常一周出去几次,有时和丈夫迪伦或自己的女伴们一起,有时和斯特拉一起,要么去尝试一家新的泰国餐厅,要么去看最新上映的法国电影。那时,她的时间被各种事情挤得满满的,各种事情等着她去做、去看、去思考。比如说看书,她总是喜欢同时看两三本,一本摊开在咖啡桌上,一本放在床头,第三本通常是诗集或者短篇小说集,被她塞在包里,每当斯特拉和小朋友们在附近的广场上玩耍的时
候,她都会拿出书来读。
从前,玛丽对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她常常想,普罗维登斯需要一家上好的墨西哥餐厅。她甚至会花好几个小时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武断地得出结论。她会为浪漫喜剧的消亡而担心,她开始喜欢非小说胜过小说。为什么会这样?她经常这样让大脑信马由缰地狂想着。
她是如何对这些无意义的事情拥有如此巨大的热情的呢?现在,她的大脑却无法思考任何事物。她无法理解任何自己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食物的味道就像空气一样,什么也感觉不到。当她吃东西的时候,她会想起斯特拉那本叫《晚安,月亮》的书,想起在玛丽大声念出那些词语之前,斯特拉是怎么说出那些单词的:Goodnight
mush,goodnight
nothing。她几乎感觉自己能听到女儿的声音,但却若隐若现。这时,玛丽会绷紧神经,在空寂的屋子里到处寻找。玛丽想象自己在自学意大利语,想象自己把悲伤写成诗,想象自己在写小说,在小说里,一个孩子幸运地获救了。但是,文字,那个曾经给予她救赎的东西,如今已经抛弃了她。
* * *
“编织的事情进展如何?”几周后,她的母亲又打电话来询问。
那时已是七月份了。
“还没去学呢!”玛丽含糊地回答。
“玛丽,你需要分散注意力。”母亲说。不远处的操场上,玛丽听到有人在说西班牙语。或许她应该改学西班牙语,而不是意大利语。
“别跟我说我需要什么,行不行?”
“好。”母亲无奈地回答。
八月,迪伦给了玛丽一个惊喜,要带她去意大利旅行。安葬斯特拉之后,迪伦立即回到了工作的正轨。迪伦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有很多客户都依赖着他,这令玛丽感到嫉妒。玛丽在家里的工作间——曾经的主卧外的壁橱,现在也慢慢恢复壁橱的原貌了。一些吊唁卡、CD、书、诗集以及一些励志的纪念匾,还有朋友送来的各种东西,现在都堆在玛丽的工作间里。那里还有一整盒的瓷器小天使,那些棕色头发的小天使曾经被认为是代表着斯特拉的,但这些瓷娃娃看起来太假了,对玛丽来说也根本微不足道。此前,斯特拉幼儿园的老师送来了一只鞋盒,里面装满了斯特拉在幼儿园时的作业。那些斯特拉曾经认真写下的数字、单词,精心画的画和练习本,现在都静静地躺在玛丽的工作间里。
“我在想,”迪伦的手中攥着两张机票,仿佛那是他的救命稻草一般,“如果我们打算一直坐在这里哭泣,那我们去意大利哭也是一样的。另外,你不是一直说想学意大利语吗?”
那之后,迪伦的眼睛周围总是一圈红,他瘦了很多,脸上出现了更多皱纹。玛丽记得,迪伦从前也有张长了皱纹的脸,但那些皱纹在他的脸上显得刚刚好,以至于玛丽第一次见到他,就爱上了那些沧桑又有味道的褶皱。然而现在,那些皱纹使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他的眼睛是闪光的——那双棕色的眼睛时而闪着金色和绿色的光,时而随着天气的变化和衣服颜色的变化而呈现出更多的色彩。但最近,这双眼睛一直都是平淡的棕色,那些明亮的绿色和金色已消失殆尽了。
玛丽并不想让迪伦失望,但现在对她来说,即使是英文都很难处理,更别提还要记住意大利语的动词变化和单词了。她唯一可以完整说出的单词是“悲伤”。他怎么会不明白呢?
但这些玛丽都没有说出口,她只是对他说:“我爱你。”是的,她真的爱他,但即使是爱,此时也没有了任何感觉。
他们在一个租来的大农舍里度过了平静的两周,厨师每天清晨会给他们带来新烤的面包卷,并给他们现做意式浓缩咖啡。当他们黄昏时分游玩归来,厨师会为他们奉上一顿丰盛的晚餐。时间平静而悲哀地溜走,生活场景和作息的变换成了一种疗愈。玛丽希望他们回家之后,也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之前的悲伤心境。然而,家只是把他们带回了伤痛的现实,无限哀伤重又袭来。
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玛丽正站着将带回来的橄榄油和细长条的番茄干从包里拿出来,厨房里的电话答录机响起了留言声。
“我叫艾丽丝,是‘大艾丽丝编织店’的店主……”
“什么?编织?”迪伦疑惑地问。
“嘘……”玛丽示意他安静。
“如果你周二早上能早一点过来,我可以亲自教你编织。任何一个周二都可以,十一点之前。到时见。”
“编织?”迪伦半嘲笑地说,“你连纽扣都不会缝。”
玛丽翻了个白眼,说:“妈妈联系的。”
玛丽第二次出现在“大艾丽丝编织店”时,手里的购物袋装着她这一周的功课。自从上周艾丽丝送走她之后,她试着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的编织物。尽管玛丽很不情愿,但她不得不承认,母亲的话是对的,编织能够使她的大脑得到暂时的歇息。每当斯特拉的脸孔浮现在她眼前时,玛丽手上的活就会掉针,或者结了个死结。有一次,她甚至掉了一整段的针,当时她就那样惊恐地看着线像断掉的链子似的掉落到地上。
玛丽并不是不愿意想起斯特拉,她只是不希望自己想得丧失了理智。医院里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回放,常常令玛丽想要发狂尖叫,有时候她也确实如此。编织带来了一种令人镇静的力量。昨天,玛丽去超市购物,看到了新上市的赛克尔梨,小小的,琥珀色的,那曾经是斯特拉的最爱。以往秋季的每一天,玛丽都会给斯特拉的午餐便当中放上两个。现在看到这些美味的赛克尔梨,玛丽感到那盛着痛苦的瓶子像是在她身体里打翻了一样,她赶紧转身离开,全然不顾篮子里刚买的香蕉和帕尔马干酪。坐在车里,玛丽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随后,她在停车场里,拾起针线编织起来,整整编织了一段,才开车回家。
第二次,玛丽站在编织店门前的台阶上等艾丽丝来开门,趁机低头检查了自己的作业。她自己都可以看得出,这一整周她的功课完成得一团糟。编织物的中间有一个大洞,张着大口注视着她。之前,艾丽丝为
她起头的那二十二针,现在已经有原来的两倍大了。有一针被很多毛线塞住了,以至于她没法把另一针插进线孔里。
“真是一团糟啊!”艾丽丝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玛丽注意到艾丽丝的穿着几乎跟上次一样,只换了件绿色的毛线衫,这使得玛丽意识到自己要怎样看待艾丽丝。斯特拉死后,玛丽的体重上升了整整十磅,每天都穿着同一条黑色裤子,因为那条裤子的裤腰部分是松紧带的。尽管秋意渐凉,玛丽还是拖着那双人字拖,因为一想到要找其他的鞋子来穿,就让她感到疲惫不堪。
玛丽扭了扭裸露在外的脚趾头,拿出自己的编织物。
艾丽丝甚至都没等门完全打开,就拽起玛丽的编织物,猛地一拉,整个儿从玛丽手里拽了过来。
玛丽喘着粗气说:“在我的行业里,通过修改可以使文章更好,但从不会像你这样直接按下删除键。”
艾丽丝将门完全打开,玛丽走进编织店。“等着瞧,这是一种解脱。”
“我整个礼拜都在编织那玩意儿。”玛丽还在挣扎。
艾丽丝将毛线扔到她怀里,笑着说:“这可不是为了完成而已,这是编织,讲究的是花纹,是针尖的啪啦声,是缝合每一段针的方式。”
这时,铃声已经响起,提示着下一波客人已经到了,女人们开始拥进艾丽丝的编织店。她们看上去都带着自己编织的半成品毛线衫、袜子和围巾。玛丽看着她们轻抚着毛线,感受着毛线的重量,把毛线对着灯
光以欣赏色彩的变幻。
艾丽丝轻轻拉起玛丽的臂膀,将她带到一个座位上,正是上周二玛丽在编织店里度过最多时间的地方。
“我想,上次那些毛线有点儿太狡猾了。”艾丽丝说。她又递给玛丽一副针线,针上是她重新起的二十二个新针。“这种毛线很有趣,它会自动生成彩色的条纹,所以你织起来就不会那么单调了。”
玛丽还是有些犹豫。
“开始吧!”艾丽丝鼓励她。
随后,艾丽丝看着玛丽织出了完美的两段针。
“就像这样,继续织下去。”艾丽丝说完便走开去帮助其他学员了。
玛丽独自坐在那里专心编织,周围其他学员的声音在她耳边如同轻柔的鸣唱。门铃不时响起,预示着来来去去的人们将在此经过。玛丽专心于手中的毛线,一道紫色的条纹出现了,随后是蓝紫色的,接着又变
成了深蓝色。
等到玛丽感觉到自己背后站了个人时,她吓了一跳。 “你做到了,”艾丽丝说,“现在,回家去,继续织吧!”
玛丽皱了皱眉头说:“但是,要是我又像上次一样弄砸了怎么办?”
“你不会的。”艾丽丝说。
玛丽站在那里,感觉有些得意,又夹杂着些许担忧。
“艾丽丝?”对面房间的一个女人大声叫着,“我要为我的睫毛须毛线围巾起多少针?”
“十五针,”艾丽丝回答。“记得,用第十五号针,每十五针起织。”
这对话在玛丽看来像是另一种语言,让她想起了自己要学意大利语的念头。手中的毛线柔软又可爱,比那些复杂的语法规则要好多了。
“谢谢你,”玛丽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下周还会来。”
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递给艾丽丝一条很大的由多圈毛线织成的围巾。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掉了一针。”女人说着,手指还在薄薄的毛线上搜寻。
“我会替你补好的。”艾丽丝说。
玛丽正准备转身离开,但艾丽丝拽住她的胳膊,示意她先别走。
“周三晚上,”艾丽丝对玛丽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编织会。我想你应该来参加。”
“编织会?”玛丽不禁笑了,“可我还不会编织啊。”
艾丽丝指了指玛丽早晨刚完成的编织活。“那这个是什么?”
“我知道,可是……”
“这些女人你应该见见,她们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有些东西可以提供给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会考虑的。”玛丽说。
“七点,”艾丽丝强调说,“就在这里。”
“谢谢你。”玛丽礼貌地回复。
她当然不会去参加什么编织会的。
下个周二的晚上,玛丽用完了她的第二束毛线。她忽然意识到,此刻躺在自己手中的是一条完整的围巾了,她在想接下来要织什么。围巾的条纹从最初的紫色,一路延续下去,蓝色、绿色、棕色和红色,最后完美地结束在粉色。多么令人激动啊!玛丽欣喜地将围巾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准备展示给迪伦看。
迪伦正坐在床上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玛丽觉得迪伦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点上瘾。
“噔嗒!”玛丽在他面前优美地转了一圈。
“你看看你。”迪伦嘲笑说。
玛丽靠近迪伦,对他展示围巾上一排排整齐的纹理。
“你要像这样把针也戴在身上吗?”他问。
“等我学会了怎么收针就好了,我肯定能学会的。”说着,玛丽紧
挨着迪伦坐下。
“你怎么会去学这种东西?”迪伦轻抚着玛丽的手臂,低声说。
玛丽轻轻闭上了眼睛。
“我参加了一个编织会,”玛丽说,“从明天晚上开始。”
迪伦一把将玛丽揽在怀里。屋子外一片漆黑,屋子里只有电视屏幕的光亮在闪烁。
晚上的编织店看上去与以往有些不同。停车场一片漆黑,小店在天空和大树的映衬下显得更小了。每扇窗户上都挂着盏小小的白灯,像是夜里明亮的星星。玛丽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人围成一个圈坐着,手中拿着针线。玛丽在考虑要不要开车回家去,回到迪伦身边,这时候他一定已经躺在床上看新闻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就好像新闻能告诉他改变一切的东西似的。
玛丽叹了口气,轻轻推开门,她本想一进门就把那条还挂着针的围巾骄傲地围在脖子上。考虑到艾丽丝大吃一惊的表情,她决定还是低调些好。
“找个地方坐下吧!”艾丽丝对玛丽说,“贝丝带来了相当不错的柠檬蛋糕。”
玛丽坐在旧沙发上,身旁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长长的红色头发,高高凸起的颧骨。
“你完成了!”艾丽丝惊喜地看到玛丽刚挂在脖子上的围巾,“嘿!大家注意了,这是玛丽的第一份编织作品。”
屋子里总共就五个女人,加上艾丽丝和玛丽,大家都停下手中的编织活,一同欣赏玛丽的作品,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说她做得多么纯然啊!有的说这围巾的厚度多么匀称,颜色的深度和围巾的长度都刚刚好。玛丽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她还可以和别人谈论这些简单的小事情,同时保留自己的悲伤。在这里她是匿名的,也是安全的。
“你用的是几号针?”站在玛丽对面的女人问。
“十一号。”玛丽很开心,在承受这么多个月的否定之后,她终于听到有人给她肯定的评价了。
“哦,十一号。”女人点点头,转身回去继续织自己的东西去了。
“这个一定很复杂吧?”玛丽对一个正在像表演木偶戏的幕后人一样操纵着四根小针的女人说。
“是袜子,”女人回答,“脚跟那块有些难处理,但其他地方就只是编织而已了。”
“那些针是几号的啊?”玛丽问。“它们看上去好小哦!”
“一号的。”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一号?!”玛丽惊讶了。
“你随时都可以编这个,但现在先让我来教你怎么收针,”艾丽丝不知何时出现在玛丽面前,“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你织点别的东西了,或许再织条围巾?这次你可以学下怎么用反针。”
玛丽解下脖子上的围巾,递给艾丽丝。“暂时不要反针吧!我要在我现有的成功上享受一会儿。”
“我了解。”坐在玛丽身旁的女人附和道。即使玛丽并不喜欢坐在一堆陌生人中的感觉,但她还是立马喜欢上了这个女人。
艾丽丝跪在玛丽身边,手把手地教她如何收针。“像之前一样,先织两针,然后把针穿过这底下,然后拉紧这个环,就这样,看到了吗?”
“把针拉出来?”玛丽尖声叫着,“之前费了那么大力气把它们全塞进去,最后还要拉出来?”
“拉出来。”艾丽丝边说边笑。
玛丽看着一排整齐的收尾线渐渐呈现在眼前。
“现在,你自己来做,我帮你去找些有趣的毛线来。”艾丽丝说。
“根据我学习编织的经验,”一个六十岁左右,留着斑白色波波头的老女人说,“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是织围巾的,那么你就只能织围巾了。如果你开始的时候是织毛衣的,那你才能学会真正的编织。”
女人正编织着毛衣底部的花式,玛丽看着各种颜色的毛线悬在空中被她摆弄得一颤一颤的。或许她说得没错,玛丽想,或许我的余生都会在织围巾。或许我可以开个围巾专卖店,又或许我永远不会走出家门,除了偶尔出去买毛线,其他时间全都待在屋子里不停地织啊织,编织着围巾,织完我的余生。
“干得不错!”红头发女人说。
玛丽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那女人是在跟自己说话,那条已经收完针的围巾,此时就躺在玛丽的大腿上。
“感觉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吗?”不知什么人说了一句,玛丽的心突然怔了一下,宝宝或者孩子,这是玛丽最不想谈论的话题。
“这个比孩子更好玩儿些。”织袜子的女人说。
玛丽并没有抬头,而是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围巾。
“今晚,”艾丽丝就站在玛丽的面前说,“你要学习怎么起针,然后你要用这美丽的毛线为自己织一条围巾。”
感谢这话题的转换,感谢一个新编织任务的开始,感谢手中这毛线的美妙触感,除了点头,玛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红头发的女人对玛丽说。
“我叫玛丽?巴克斯特。”玛丽说。
“你去胭脂面包店吃过东西吗?”艾丽丝问玛丽。
“当然去过,那儿棒极了!”
“嗯,她就是那家店的老板。”
“大多数人都叫我斯嘉丽。”红头发的女人自我介绍说。说完,她拍拍坐在她旁边椅子上的女人,“这是露露,那个是爱伦。”说着,又指指织袜子的那个女人补充道。
玛丽尝试着记住她们,将名字和每个人的脸对上号。斯嘉丽那头红发很显眼,也很好记。露露的黑发顶部,靠近头皮根部是银色的,戴着副嘻哈眼镜,一身黑衣装扮,看上去就好像刚从纽约赶来,途经此地似的。
爱伦的样子使玛丽想起了另一个时代的女人。玛丽猜测爱伦约四十岁,她那脏兮兮的金发带着波浪卷儿一直拖到背后,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红白花式的经典家居服,光着腿穿一条黑色玛丽牛仔裤。她的脸是玛丽母亲曾经说的“马脸”,而她的头似乎在她那又瘦又小的身体的衬托下显得更大了。不管怎么样,整体感觉还不错,所有这些元素结合在这个人身上,竟然也是个性感而纯洁的女性形象。
“我是哈莉特。”那个年长的,头发斑白的女人开口了。说实话,
玛丽觉得她有点阴郁。
哈莉特是个脾气不太好的老太太,玛丽暗自想着。
“还有,这是贝丝,”哈莉特的语气就像贝丝是属于她的一样,“贝丝可以织任何东西,她可神了。看到那个小编织包了吗?她已经快要织完了。贝丝,你什么时候开始编那个的?”
“午饭的时候。”贝丝回答。
“今天中午?!”哈莉特惊讶地说,“她是不是很能干?”
每个人都同意,贝丝是个能干的女人。然而,玛丽看到的是她闪闪发亮的深色头发,很有型地扎成一小缕,披散在脑后;她脸上化了全妆,眼线描得很精细,嘴唇光泽莹润,光泽莹润的嘴唇;她的衣服颜色搭配考
究,就连鞋子看上去都是优良的,带有褶皱的格子呢长裤,琥珀色的耳环,搭配得当的项链。玛丽将这一身精致的打扮看在眼里,心想这是个生活优越的女人。
“你还记得最开始是怎么织的吗?”艾丽丝问玛丽。
“呃……不记得了。”玛丽回答。
“最开始,”艾丽丝继续提醒她,“这次你来起针。”
玛丽看着艾丽丝轻车熟路地摆弄针线,针在她手中玩转得那么轻巧,而玛丽自己照着做的时候,却显得笨手笨脚的。
这一晚的编织会结束,玛丽和陌生的朋友们道别的时候,觉得今晚的两个小时过得真快。不知为什么,这个晚上,有这些陌生女人的陪伴,让玛丽的心情平静了许多。这种安慰和来自她那些闺蜜们的安慰不
一样(迪伦通常叫她的闺蜜为“妈咪朋友”),她的闺蜜们的生活始终围绕着她们各自的小孩打转,而这些女人对玛丽来说则是个谜团。最重要的是,今晚她和她们坐在一起,没有别的,只是编织。
玛丽看着哈莉特和贝丝一起上了一辆车离开,立即陷入沉思:她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是什么使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会如此强烈地袒护贝丝呢?是什么把她俩带到了今晚的编织会呢?
店里的灯暗了,玛丽还站在那里。
“玛丽?”斯嘉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在对着星星许愿吗?”
“哦,你知道,”玛丽说,“我已经不相信那玩意儿了。”
斯嘉丽背靠着玛丽身旁的一辆车,缓缓地点起一根香烟。“我也不信。”
她们一同抬头看着天空,厚厚的乌云飘浮在空中,时而挡住了星光,时而又让它们闪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