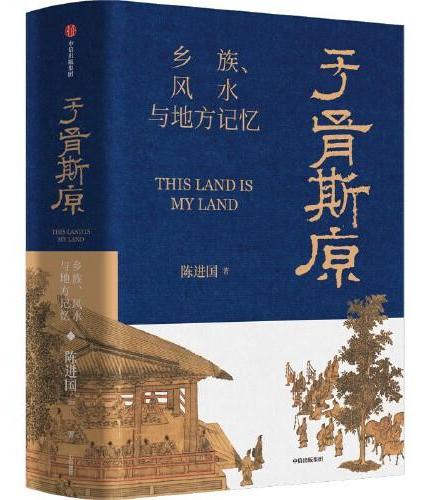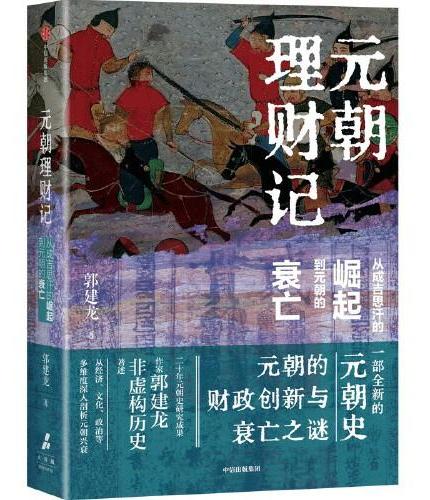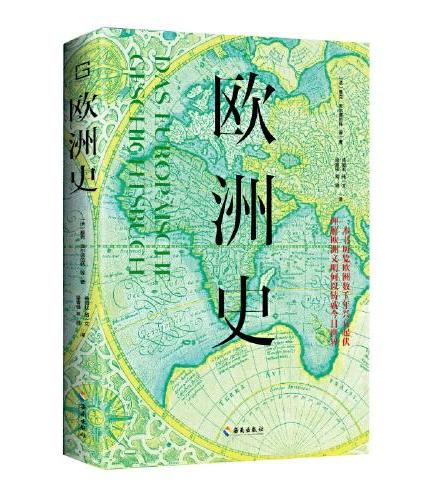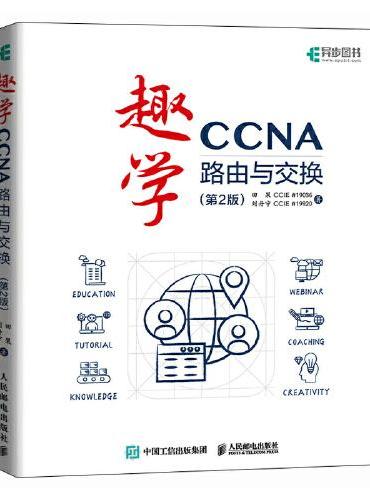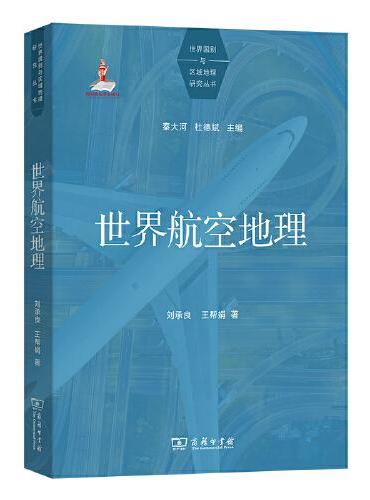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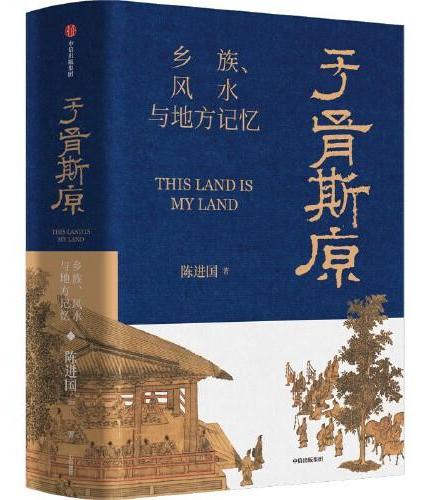
《
于胥斯原 乡族、风水与地方记忆
》
售價:NT$
806.0

《
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
售價:NT$
449.0

《
我真正想要什么?:智慧瑜伽答问/正念系列
》
售價:NT$
2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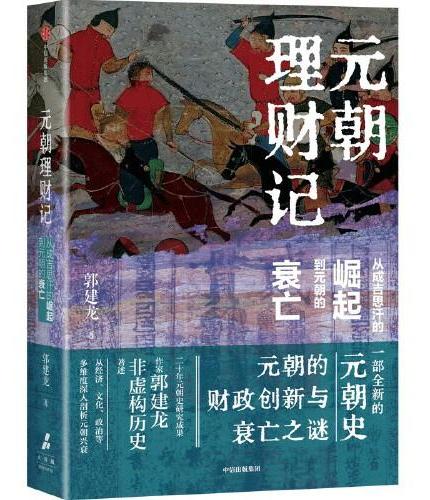
《
元朝理财记 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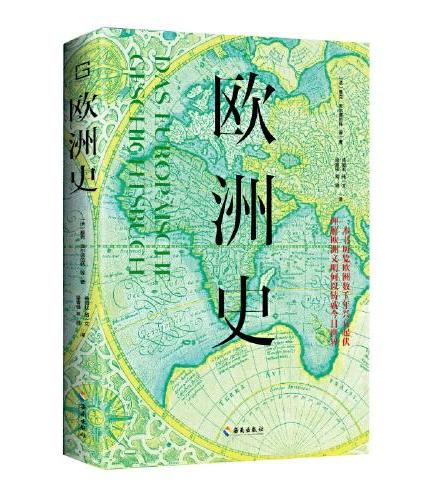
《
欧洲史:一本书历览欧洲数千年兴衰起伏,理解欧洲文明何以铸就今日世界
》
售價:NT$
15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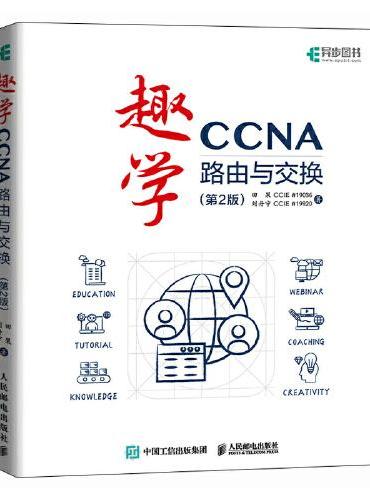
《
趣学CCNA——路由与交换(第2版)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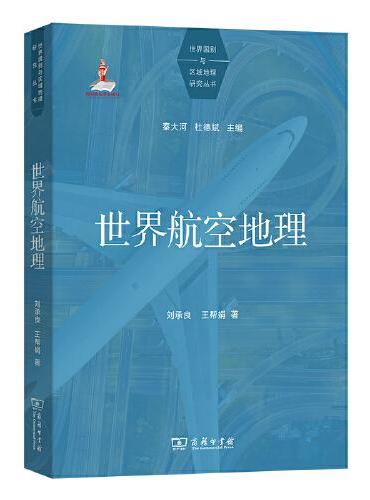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NT$
1112.0

《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
售價:NT$
398.0
|
| 內容簡介: |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社会问题如密集的鼓点不断敲击人们的生活,腐朽的制度席卷人们的良心,懒散的议会,庞杂的统治机构,自满昏聩的资产阶级,金钱的统治力量,人们迷失在这病入膏肓的社会里。
主人公匹普幼年时就成了孤儿,依靠姐姐的抚养长大。但脾气粗暴的姐姐没有给他一点温暖,只有善良的姐夫乔既像父亲又似朋友一样照料着他。匹普长成一个少年时,给乔做了学徒,而他淳朴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像姐夫一样的好铁匠,他从未期盼过要做一个有钱的上等人。可是随着他被引进了贵妇郝薇香的家里,见到高贵骄傲的艾丝黛拉后,匹普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爱上了艾丝黛拉,开始为自己的卑微身份配不上她而痛苦,而想以艾丝黛拉报复男人的郝薇香也在一旁狂热地鼓励匹普追求艾丝黛拉,但艾丝黛拉对匹普忽冷忽热、恣意取笑的态度除了让郝薇香这个对男人充满仇恨的女人心怀快感外,只能让匹普更加怨恨命运的不公,甚至连乔的友谊也不能给他安慰和快乐。
后来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当年匹普在墓地里帮助过的罪犯马格韦契在海外发了财,他要报答匹普,同时实现自己畸形的愿望:用钱打造出一个绅士。于是他暗中出钱让律师贾格斯找到匹普,告诉他“将要继承一大笔财产”,同时还要安排他去伦敦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匹普觉得幸福的大门在他面前敞开了,他从此可以成为上等人,能够以平等的地位追求艾丝黛拉了。
不久后他来到伦敦,立刻着手按自己现有的身份颇有气派地花起钱来,为住房和服饰很费了一番心思。他甚至羞于在伦敦的社交圈子里见到乔。虽然匹普的内心也难免觉得自责,但生活环境的变化主宰了他的价值观和行为。他从一个心地纯朴简单的乡村青年朝向往的上等人的目标努力着。可惜好日子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马格韦契找上门来,向他坦陈了一切,真相于是大白天下,匹普承受了双重的精神打击:一方面锦绣前程刹那间灰飞烟灭,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好期望,另一方面受恩于一个囚犯更让他感到耻辱。大病一场后,匹普回到了现实中,回到他应有的位置上。生活道路上的这段经历和他心理、认识上的渐变过程,充分体现了狄更斯关于环境影响人的观点。
|
| 關於作者: |
|
查尔斯·狄更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大卫·科波菲尔》。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
| 內容試閱:
|
我父亲姓皮利普,我的教名是菲利普,可我年幼时,舌头发不出比“皮普”更长或更清晰的音节。于是,我就自称皮普,别人也开始叫我皮普。
我说父亲姓皮利普,那是根据他的墓碑还有我姐姐——嫁了一个铁匠,成了乔·加杰里夫人——的一面之辞。由于从未见过父亲或是母亲,也没有看到过其中任何一位的肖像因为他们的年代离开拍照片的日子还远着呢,我第一次臆想他们长得什么样时,竟是胡乱地从墓碑开始揣测的。父亲墓碑上的字形,让我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他是个体型方正、身材矮胖、皮肤黝黑的人,长着一头鬈曲的黑发。从墓碑上“及上述者之妻乔治安娜”这几个字的字形,我又得出一个孩子气的结论:母亲脸上长有雀斑,且体弱多病。他们的坟墓边,五个菱形小石碑整齐地排成一列,每个估摸有一英尺半长。要命的是,这竟是为了纪念我的五个小兄弟——在宇宙万物的争斗中,他们过早地放弃了求生的意念。所以我总是一本正经地坚守着这么一个看法:我的兄弟们生来全都四脚朝天,手插裤兜,并且他们再也没有把手抽出来,就和现在躺在墓中的情形相同。
我们家乡地处沼泽区,那儿有一条河流蜿蜒而下,不到二十英里便汇入大海。对周遭事物留下最初那份极为鲜活而又异常清晰的印象的,似乎来自于一个难忘而又阴冷的下午,傍晚时分。自打那一次起,我才闹明白,这一片荨麻遍生的荒凉之地是教堂墓地;教区居民菲利普·皮利普和他的妻子乔治安娜都死了,葬了;他们的婴儿亚历山大、巴塞罗缪、亚伯拉罕、托比亚斯、罗杰也都死了,葬了;教堂墓地前边,黑漆漆的荒地即是一片沼泽,里面堤坝沟渠纵横,土墩小路交错,还零星散布着几只牛,正吃着草;沼泽另一边一浅浅的铅灰色线条,是河流;远方那个狂风呼啸的未开化的巢穴,是大海;面对着这一切越来越恐惧、吓得瑟瑟发抖、呜咽起来的小家伙,是皮普我。
“不许哭!”一记骇人的叫喊声响起,只见从教堂门廊一边的墓地里,腾地蹿出来一个人,“站着别动,你这小鬼,要不然割断你的脖子!”
这是一个可怕的人,穿着一身粗布灰衣,脚上拖着个大铁镣。他头不着帽,裹着破布一条,鞋子破破烂烂的。此人曾在水里泡过,满身烂泥;腿被石头绊得都跛了,还给什么坚硬的东西割破,又让荨麻刺伤,叫荆棘划开了皮;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哆哆嗦嗦的,瞪着两眼愤愤不平地嘟哝着。他一把抓住我的下巴,牙齿在脑间格格打战。
“哦,先生,别割我的脖子。”我惊恐地乞求着,“求求您,别这样,先生。”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快点!”
“我叫皮普,先生。”
“再说一遍。”那人瞪着我,“大声点儿!”
“皮普。皮普,先生。”
“指给我看你住在哪儿。”那人说。“把地方指出来!”
我指向我们村子,它坐落于沿岸的那块平地上,周围矗立着一片赤杨林和截了梢的树林,离教堂有一英里多远。
那人打量了我一会儿,便把我倒栽葱翻了个个儿,这样一来,我口袋里的东西都掉了出来。里面只有一片面包。等到教堂恢复了它的原样——因为他猛地使劲儿把教堂在我面前倒了个向,我看见教堂的尖顶在脚下——话说回来,我是说,等到教堂恢复了它的原样,我已被按坐在一块高高的墓碑上,打着哆嗦,而他却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
“你这小子,”那人舔了舔嘴唇,说道,“脸蛋儿生得好肥啊。”
我相信我的脸蛋是肥嘟嘟的,尽管按年龄来说,我当时身材矮小,也不结实。
“吃不了你的脸蛋就算我该死。”他晃了晃脑袋,威胁我,“不想吃才怪!”
我百般恳求,希望他别吃,一边紧紧抓住那块他把我放在上面的墓碑。一来,让自己坐坐稳,二来,不让自己哭出来。
“喂,看着我!”那人说道,“你母亲呢?”
“在那儿,先生!”我说。
他吃了一惊,立马就逃,一会儿,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
“在那儿,先生!”我涩涩地解释道,“那边写着‘乔治安娜’几个字,那就是我母亲。”
“噢!”他说着跑了回来,“你父亲和她葬在一起吗?”
“是的,先生。”我说,“他也葬在这儿,上边写着‘本教区已故居民’。”
“哈!”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轻声嘀咕道,“要是我好心留着你的小命,你跟谁过?不过,留不留我还没定呢。”
“我的姐姐,先生,就是乔·加杰里夫人——铁匠乔·加杰里的老婆,先生。”
“嗯?铁匠?”他说着往下看自己的腿。
他隐秘地看看自己的腿又看看我,这样来来回回几次后,走近了我坐着的那块墓碑,抓住我的双臂,使劲把我往后揿,那威严有力的目光直射进我的眼球,我万分无助地看着他。
“喂,听着,”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留着你的小命。我问你,你知道锉刀是什么吗?”
“知道,先生。”
“那么你知道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知道,先生。”
他问一个问题,就把我往后揿一点,让我越发感到无助、危在旦夕。
“你给我弄把锉刀,”他又把我往后揿了揿,“再给我弄点吃的。”再一揿,“把两样东西都给我带来。”还是一揿,“否则,挖了你的心和肝。”说完,他照旧把我往后揿。
我怕得要命,头晕目眩的,两只手紧紧抓住他,说:“如果您行行好让我直起身子来,先生,也许我就不会恶心要呕吐了,也许还能更专注地听你说话了。”
他又给我来了个倒栽葱,接着是一个大翻滚,这样一来,我觉得教堂都跃过风标了。然后,他才抓住我的两条胳膊,把我拉到墓碑的顶头,让我直挺挺地坐好,他则继续说着耸人听闻的话:
“明天一早,给我把锉刀和吃的东西带过来,送到那边古炮台,交给我。你做到了,并且不走露一点风声,不透出一丝痕迹,不让人知道你遇见过我这么样一个人,或者遇到了什么人,你才能留着小命。要是做不到,或者有一点点不听我的话,不管这话多么微不足道,我就把你的心和肝都挖出来,烤了吃掉。好了,我可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这你可想而知,有一个小伙子和我藏在一起,和这个小伙子比起来,我可是一个天使了。我说的话他都听得到。他还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会捉小男孩,挖他的心,掏他的肝。小孩子想躲都躲不了。即便他锁上门,躺在暖和的床上,把自己卷进被窝,再用衣服裹住头,想着自己又舒服又安全,但那小伙子还是会轻轻地爬上来,爬上来,撕开小孩的胸口。现在这会儿,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让那小伙子别伤害你,不过我发现,要让他一直不来吃你太难了。喂,你怎么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