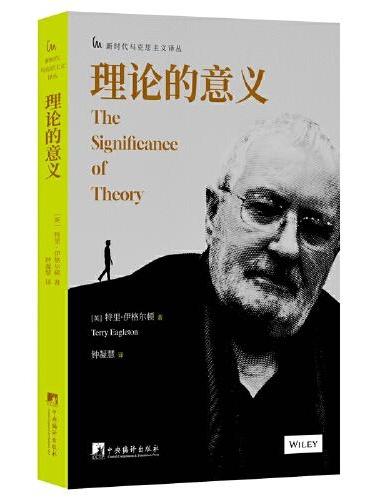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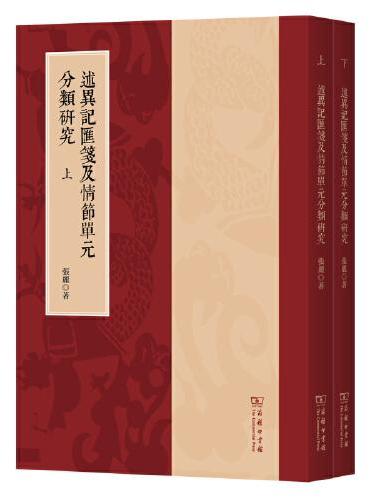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
述异记汇笺及情节单元分类研究(上下册)
》
售價:NT$
4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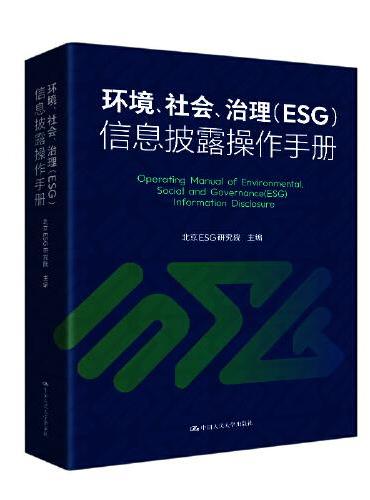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NT$
1190.0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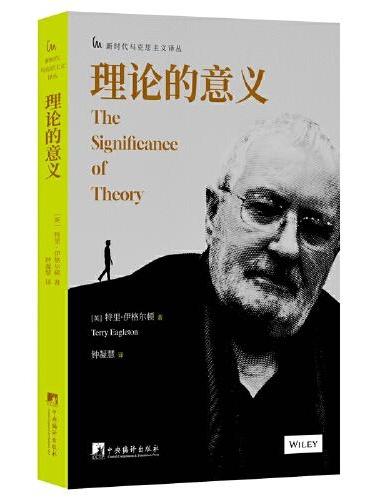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 內容簡介: |
|
本著作系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有关研究员之论文选集。上述外国语文研究中心系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有关文章皆出自中心研究员之手,且此前已在比较重要的刊物发表。
|
| 目錄:
|
序言
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简介
外国文学篇
《哈姆雷特》:演释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
T.S.艾略特与“经典”
荒谬与启蒙的辨证
“Nutting”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
《应和》与“应和论”
罗斯“以色列小说”《夏洛克行动》中内心探索的外化策略
语言学篇
体验人本观视野下的认知符号学
语义合成原则的有效性
象似性原则的准则和象似性的语用性
外语学习者在外语使用中的隐性不地道现象
试谈文本的语文学分析
翻译研究篇
《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
《吉檀迦利》:是创作还是翻译?
傅雷“神似”译论新探
难以逾越的文化失真
雅各岱诗歌译介
语言文化篇
美国与重庆交往的开端: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与重庆
俄罗斯村社共同体与中国宗法家族共同体的文化比较
现代汉语词类体系效度研究
韩国又松大学的发展对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启示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哈姆雷特》:演释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
蓝仁哲
“问题剧”这个术语一般指20 世纪初易卜生及其追随者的剧作,剧中常常以现实主义手法严肃对待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或伦理、心理问题。其实,早在19 世纪末,F. S.
博厄斯在《莎士比亚及其先驱者》一书中便使用了“问题剧”一词,用来描述莎士比亚大致在1590至1604 年间创作的四个剧本:《哈姆雷特》、《特罗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在博厄斯看来,这几部剧都涉及不真实的社会、病态的心理和复杂微妙的良心问题,给人的感觉像是“我们沿着幽暗的没人踩过的小道前进,走到头时既无大喜亦无大悲之感;由于剧中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只觉得大受触动,久久沉浸其中,茫茫然若失。”应该承认,这几部剧的确与莎士比亚其他剧作颇为不同。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博厄斯语焉不详。本文受“问题剧”一语启发,循此思路探讨,旨在说明《哈姆雷特》是一部演绎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
一、重新解读独白名段“To be or not to be”的意蕴
以“To be or not to be”开头的这段著名独白,出现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这时候,哈姆雷特已经装疯大约两个月,搅得丹麦宫廷上下不安。看来,他是借装疯来麻痹窃取了王位的叔父克劳狄斯,以便争取时间兑现他对父亲亡魂许下的复仇诺言。可是,他的心思却是:“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报仇,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像一个下流女人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得的了!”恰巧这时,有一班伶人来宫献艺,他才决定借演戏来试探他的叔父,证实鬼魂透露给他的秘密。可以说,这是他装疯以来朝着复仇目标第一次真正采取行动。到了采取行动的当天,“捕鼠剧”虽然前一天已经布置,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上演,但怎么演法他还要在接下来的第二场里才具体指导,并嘱咐他信赖的朋友霍拉旭在演到相关情节时“全副精神”地盯住他叔父的神情。像平时一样,当他独自一人时又开始沉思起来,自言自语。这一段独白可以视为他装疯以来冥思苦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与将要采取的行动直接有关,甚至是由它引发的,由此可见思考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但他思考的焦点,却是人生中令人困惑的生与死的问题。
长期以来有研究者把这段独白理解为哈姆雷特在权衡“自杀”的利弊。20 世纪初的权威评论家布雷德利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指出:“在这段独白中,哈姆雷特想的根本不是自负的重任。他在权衡自杀的利弊。”前苏联莎评家莫罗佐夫认为,在这里,“哈姆雷特又再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不过,再次萌发这个念头的已是一个成熟的人了”。
梁实秋在翻译该剧的注释里说,这段独白是讲“哈姆雷特蓄意自杀,于第一幕第二景之独白中已有表示”。李赋宁先生对这段独白也持有类似观点,他本来已表明这段独白在“探索生和死的问题,指出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阐述时又说哈姆雷特“焦急地等待着夜晚的来临……在这段无事可做的等待期间,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想到死是一条出路,但是他并未下决心自杀。他权衡着生和死的得失”。
如前所述,要断定这段独白的真正意蕴,弄清它出现的确切时间以及哈姆雷特在这之前是否采取过行动和在此之后将采取什么行动,是非常关键的。布雷德利也注意到了这个关键问题,他在一条注释里特别说明:“‘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以及和奥菲莉亚的会面现在在剧中的位置,看来是莎士比亚经过考虑后才定下来的,因为在第一个四开本中,它们是在伶人们到来之前发生的,而不是在其后,并由此安排了演戏那一场。”莎士比亚“经过考虑后”为什么有意做了这个前后位置的改变呢? 因为正是在伶人们到来之后,哈姆雷特才灵机一动,决定上演一场与父王之死类似的戏来试探和证实叔父的罪恶,首次采取了复仇行动。这恰好说明了莎士比亚的匠心,这样改变之后才能表明独白里“默然忍受”还是“挺身反抗”哪一种行为更高贵的疑问在哈姆雷特心中是确有所指的,是有感而发的。这时并非如布雷德利所断言,“哈姆雷特在这里实际上正处于他两个月前第一段独白时同样的思想状态之中……反映了他惯常的厌世感。”与两个月前那段满怀悲愤的独白相比,亡魂告知的秘密已将哈姆雷特推入苦难的深渊,他接着又遭遇了情人奥菲莉亚的变心,自幼一起长大的朋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忘义,比起两个月前情况已大大变化了。认为哈姆雷特“再次萌发了自杀念头”的莫罗佐夫也发现哈姆雷特“已是一个成熟的人了……我们发现的不是高声叹息,而是‘哪一种行为更高贵’……这样的论断性语言。在这里,我们发现的不是长满莠草的花园,而是比较具体、准确地列举了各种罪恶:‘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几个小时后就要上演决定一切的捕鼠剧《贡扎古之死》,面临这个“挺身反抗”的行动,他情不自禁地思考起与之相对的“默然忍受”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死思辨,既符合哈姆雷特耽于思考的习惯,也符合这一特定时刻所思内容的情理。反过来,在此重大时刻,断定他“在思考着自杀的可能性”,既令人莫名其妙,又会大大削弱这段独白的深刻意义。
至于将这段独白与第一幕第二场那段独白相联,以那段独白提到过“自杀”而推及此时哈姆雷特“蓄意自杀”或“又萌发了自杀的念头”,似乎更缺乏依据。在那段独白的开始,哈姆雷特的确说过:“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自杀的律法!”(14)可是,从前后场景的转换看,这段独白紧接在“随朝听政”之后,哈姆雷特曾当面用双关语对国王表示不满,现在国王和王后退下,只剩他一人,这两句首先爆发出来的话,分明是他满腔愤懑的迸发,表达他刚才违心“上朝”,无可奈何地陪在国王和王后的身旁,简直难堪难受之极:与其出现在那种场合受罪难堪,真不如没有这个形体或者死了的好。这儿提到“自杀”二字,绝非有意自杀,而是抱怨因为有了真神制定的律法不可能去“自杀”。既然不可能去自杀,又怎会一再“萌发自杀的念头” ?
看来,把这段独白理解为在“权衡自杀的利弊”的说法可能不源于剧本别处,而是受了独白中只言片语的表面语义的影响。可是,能凭“生存还是毁灭”、“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的字句,就断定这是在做“自杀”利弊的权衡吗? 有了对全剧和上下文的如实把握,确定了这段独白的语境,其字面含义应当更加显豁。“To be”指现世的“生”,“not to be”即指结束现世生存的“死”,首行“是生还是死,这就是问题”便点明了整段独白的主题。这个“是生还是死”的问题,意味着是“默然忍受”着“生”还是“挺身反抗”(指他将要采取的行动)而“死”。限于篇幅,本文不继续做字句的解读。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哈姆雷特在这段独白里一直使用的是“我们”、“他”、“谁”
等称谓,分明是在泛指一切人。因此,他是站在“人”、“人类”的立场,以“我们”大家的身份在说话。他深刻的人生思辨已经超越了个人,俨然是人类面对生存的意义、生的痛苦、死的疑惧、思与行的矛盾等人生问题的诘问和喟叹。
二、生死问题贯穿全剧
生死问题不仅集中反映在上述独白里,还贯穿于全剧。换句话说,生死问题在剧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悲剧一样,《哈姆雷特》没有遵循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法则,但剧情却是鲜明连贯的。有的莎评家指责《哈姆雷特》的情节“不连贯”,如果不把它视为“复仇剧”或“性格悲剧”,而是看成一部“生死问题”悲剧,就不会有情节不连贯的问题,因为生死问题贯穿了全剧。
全剧以鬼魂出现为开端,第一幕作为说明部分提示我们:大约在两个月前,老国王突然逝世,他的弟弟登上了王位;不出一个月,王后嫁给了新国王。哈姆雷特从求学的威登堡被召回丹麦宫廷,由于父亲突然死去,母亲匆匆改嫁,原先充满理想的单纯王子第一次发现“人世间的一切……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14-15)可见,《哈姆雷特》一剧首先让观众或读者关注的是老国王的死及其死因;毒害老国王这桩罪孽启动了一场灾难,成为全剧的推动因素,将剧情推向纠葛冲突并唤醒哈姆雷特(包括观众和读者)对现世生存和人生际遇的关注。对此,希腊悲剧学者基托也十分明确地指出,第一幕鬼魂出现的“事件给全剧提供了背景,就是说,是全剧的逻辑和动力中心”。他进一步指出:“悲剧的真正基础的结构就在这里,……把这一悲剧看成‘世俗’悲剧,我们是在使用错误的焦距。正确的焦距将把整个情节置于‘自然’和‘老天’的背景下,因为这才是剧作家自己提供的背景。”
随着剧情冲突的展开,哈姆雷特虽然毅然答应了亡魂要报“杀身的仇恨”,却并不采取行动。在整个第二幕里,莎士比亚沿袭复仇剧惯用的装疯手法,这与其说是把复仇者朝复仇行动推,倒不如说给了哈姆雷特一个冷眼旁观、讥评人世的宽松机会,让他一面观察一面思索,着实领略一番人世的苦涩滋味:国家大事可以从宫廷巨变、内忧外患窥知,家庭伦常可以从波洛涅斯一家的情况看个大概,个人际遇则莫过于情人变心、朋友背义。这些情节是在台上演示的,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却活跃在哈姆雷特的心间。因此,在上述那段著名的独白中,他不仅指出人世的苦难是“无涯的”,而且可以一连串地具体罗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63)显而易见,第一、二幕里演示的全是有关人世的际遇和苦难。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幕第三场里借助“捕鼠剧”成功地窥探了仇敌,证实了鬼魂透露的秘密,哈姆雷特在随后去见母亲的路上,偏偏又遇见克劳狄斯跪在地上祈祷“愿一切转祸为福”,本来“正好下手”,他又思考起死后是进天国或地狱的问题来:“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结果,把一个该杀的仇敌放过,而在紧接着的会见母亲的场景中反把躲在帏后偷听的波洛涅斯误杀了。这样,剧情以一生一死达到了冲突的高潮,而这一生一死的背后则突显了“天意”。哈姆雷特说:“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着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成为代天行刑的凶器的使者。”(92)这番表白同时也预示了后面剧情的走向。
收场部分与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形成对照,克劳狄斯当机立断,立即以“保护”
的名义派人把哈姆雷特送往英国,诏令英王将他处死。可是,哈姆雷特死里逃生,又奇迹般地回到了丹麦。然而,他从大难不死的经历中得出了宿命的结论:“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130)而当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与雷欧提斯比剑时,更明白无误地声称:“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在明天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回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137)难怪,他在最后一幕出现在墓地时,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不再装疯,像个大彻大悟的智者,“看透了生命的无常”。他终于明白,唯有死亡才能了结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和苦难,唯有在死亡面前才能人人平等―无论他是显赫一世的亚历山大、恺撒还是一介白丁,无论他是一国之君、国君的弄臣还是狡诈的律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到头来都无非是一具具骷髅而已。剧情的冲突纠葛部分所表明的人生苦难和对死亡的疑惧,可谓由“生”观“死”,而收场部分在超脱死亡之后的达观态度,可谓由“死”观“生”。
最后的悲惨结局同样具有深刻的人生意蕴。哈姆雷特坦然去参加比剑,见到雷欧提斯时主动请求他“原谅”。国王下过毒的酒本是以备万一的最后一招,却先置王后于死地;雷欧提斯涂毒的剑虽然刺中了哈姆雷特,他自己却也死在了毒剑之下。阴谋揭穿后哈姆雷特忍无可忍,这才刺死了国王。四个人倒在了血泊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再次证实了“天意”,回应着剧情高潮时哈姆雷特在波洛涅斯死后的表白。他在临死前的请求―“霍拉旭,我死了,你还活在世上;请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仿佛表明生与死是个首尾相连的圆圈,生时惧死,死时顾生,生生死死将永无穷尽。
三、《哈姆雷特》的悲剧意识
《哈姆雷特》位居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历来是莎剧中上演最频繁、阅读研究最深入者。它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 它震撼人心的悲剧意识究竟是什么?
悲剧之成为悲剧,起码要有一个主人公遭受苦难、最终死亡的故事。《哈姆雷特》包含了这样一个可悲的故事,但它并不是一出有关古代丹麦宫廷政变、王子复仇的历史悲剧,也不是一出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复仇悲剧。莎士比亚借用了丹麦古老的历史题材,但经他改编和创作的《哈姆雷特》,与八世纪丹麦洛亚里克王朝哈姆雷特王子复仇史实大相径庭。莎士比亚大体沿袭了托马斯?基德《西班牙悲剧》的复仇剧模式,但在他笔下复仇并不是《哈姆雷特》表现的主题,它大大超出了复仇悲剧的范畴。
悲剧的感人力量本质上不在于故事的悲惨,而在于悲剧主人公的人格或他遭遇的难题能够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强烈共鸣。主人公应当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人物,悲剧性灾难降落在他身上,由于种种原因,无论他怎样上下求索,左冲右突,都摆脱不了走向死亡的命运。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众多主人公中历来最受评论家的关注,评者大都从哈姆雷特的外部境遇和内在性格这两方面进行分析。批判现实主义论者往往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大而至于文艺复兴时代,小而限于英国伊丽莎白由盛转衰的时期,重视剧本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把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英雄人物、时代精神的代表,赋予他扭转乾坤的重任,并为他经受失败而惋惜,认定那是他脱离人民的历史局限。于是,《哈姆雷特》成了一部“社会悲剧”或“时代悲剧”。
这在前苏联的莎评家中比较常见,而出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原因,类似的批评在我国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也很盛行。然而,一旦将哈姆雷特英雄化,反而会使他疏离读者或观众,产生意想不到的陌生化后果。批评家的论点与读者的实际感受相悖,很难达到批评者的引导愿望。浪漫主义论者则往往围绕哈姆雷特的内在性格大做文章,尽管布雷德利指出:“在18世纪后期以前,几乎没有一个评论家对主人公的性格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兴趣”,性格批评却在19、20世纪的西方蔚然成风。这类评论往往涉及几个最受关注的问题:装疯、忧郁、优柔寡断、延宕、恋母情结、宗教意识等,见解可谓层出不穷。对悲剧主人公性格的探讨无疑是认识主人公的重要途径,以布雷德利为代表的传统批评家都重视主人公的性格,认为“莎士比亚的众多悲剧都表明,剧作家心里的‘主要兴趣’在人物;人物的内在性格决定了自身的行为和命运”。但停留在个人性格的认识上,无论剖析多么入微,见解何等深刻,都难免见树不见林的弊病。当然,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出现以来的后现代批评家不相信语言的功能,把作品与作者的意图割裂开来,不承认文本有任何终极意义,自然谈不上一部悲剧还有什么特定的意蕴。
哈姆雷特不同于莎士比亚笔下的任何其他悲剧主人公,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几乎到了抽象与玄奥的地步。早在19 世纪初,威廉?赫兹利特就称“哈姆雷特只是个名字……这个戏具有一种先知的真理,这是高于历史的真理的。”到了20世纪,基托认为:“围绕着《哈姆雷特》蔓延起来的那种神秘感,暗示着《哈姆雷特》有一种独特的、难于表达的品质,使它不只不同于其他剧作,也不同于其他艺术品,也许莫娜?丽萨除外。”莎学家J . M.罗伯逊认为哈姆雷特“是个谜”;著名演员莎尔维尼甚至声称:“像哈姆雷特这样的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
《哈姆雷特》的神秘独特之处在哪里?哈姆雷特为什么“只是一个名字”,一直“是个谜”?既然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演员为什么争着去演,而且四百年来历演不衰?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它并不是对哈姆雷特这个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否定,相反,这些听来荒唐的评论实则是极高的赞誉。哈姆雷特“只是一个名字”,因为他是莎士比亚塑造的一个超出一般典型意味的人物,他的典型意义不止于他是一位王子而竟有那样险恶的遭遇,或者他在那种境遇里表现出了何种异样的性格特征。
在莎士比亚笔下,他已经成为“人”的缩影、“人生”的缩影;他是人生中“生死烦恼”
的体验者,人生命运的探索者;他成了莎士比亚的一个工具,一个演示品。莎士比亚用他来演示思想―关于人类生与死的思想,人与命运的思想。《哈姆雷特》的真实性印证在每个读者和观众的心间,在那里引起强大的共鸣,让人们深切地感到“我们就是哈姆雷特”,从而观照自己的人生,人生的体验,人生的困惑,面对命运这个斯芬克司式的哑谜。哈姆雷特仿若是人生之谜!《哈姆雷特》要演绎的便是人类生死问题的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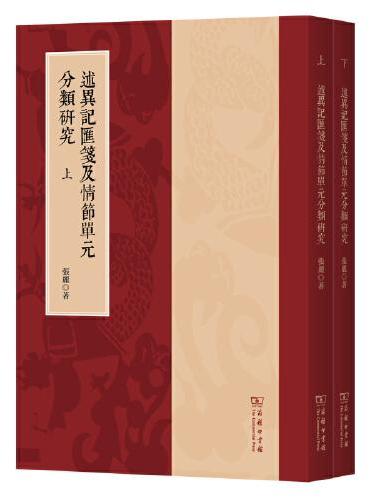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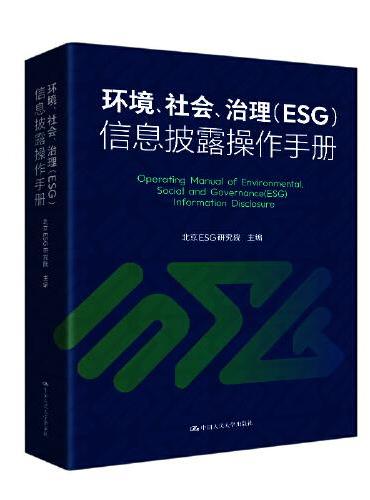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