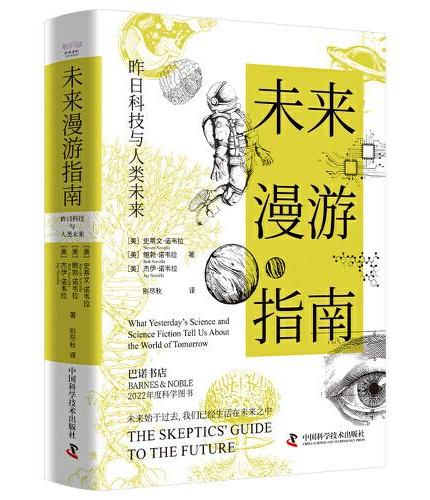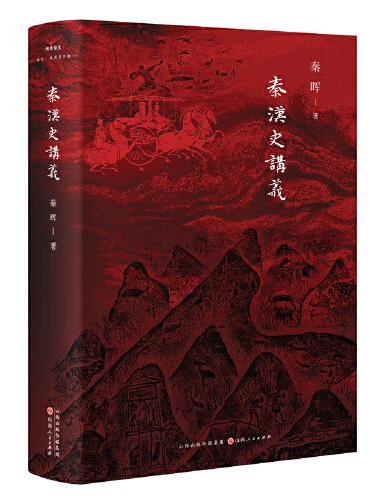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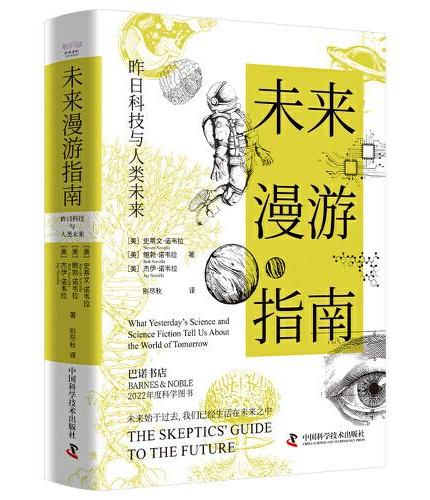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NT$
390.0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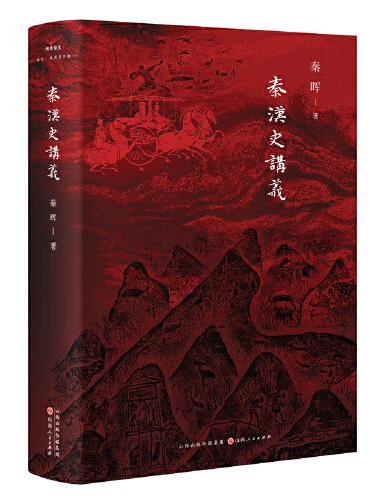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NT$
690.0

《
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售價:NT$
475.0

《
荷马:伊利亚特(英文)-西方人文经典影印21
》
售價:NT$
490.0
|
| 編輯推薦: |
是的,我现在明白爱你其实是很渺小的事情,而后果却堪比伟大。
——罗西 《爱你不是一件伟大的事》
如果一个人口舌不幸失去味觉,胃照样可以幸福地品尝深情。爱一个人就是把最好的留给对方。在生活的万千滋味中,这样的胃消化的是最有温度的幸福;在岁月的长河里,那样布满老茧和裂缝的手无声地牵在一起,就是一道地老天荒的动人风景啊!
——马国福 《有温度的幸福》
“你坐着,我来干。”一句洗尽铅尘的情话,一句浸满人间烟火味的情话,无比的真挚,无限的情意,无数的关切,全都融入了这朴实无华的爱的表白,让美丽在艰难中绽放,让富足在清贫中走来,让美好在平凡中诞生。多么愿意有人能对自己说出这样的情话,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说出这样的情话。
——崔修建 《最美的情话》
|
| 內容簡介: |
没有爱过,没有痛过,没有哭过,没有嬉闹过,没有郑重过,就这样彼此执着,又错过。诗人吉皮乌斯说“趁你活着,别分离。”因为时光在手,肆无忌惮。
本书系《读者》签约作家优秀作品十年纪念珍藏版,十年间,80后人群成长道路上的《读者》优秀作者作品精选,在这些选出的文字里,蕴含了这个时代人的成长脚印,每个人都可能从字里行间,或多或少找寻到当年阅读《读者》的乐趣。
|
| 目錄:
|
凉月满天
这趟列车不到2046
我和老铁的爱恨情仇
麦田守望者
华丽缘
马国福
有温度的幸福
清淡出尘
在尘世里的烦恼开怀
冬夜里落寞的糖葫芦
香透在岁月深处的肉味
包利民
穿不透光阴的爱
广场上弹吉它的弟弟
红尘里的坚守
永远的回程票
周海亮
祝 福
晚报B叠
明亮的天空
铁布衫
姜钦峰
花落无声爱无语
乱世飘零乱世情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
外婆的“四百块”
安宁
盗版碟片里也有梦想扎根
流年里有你天使的笑容
在时光里与你握手言和
崔修建
父亲是“蜘蛛侠”
飘不散的粥香
喀布尔的歌声
90岁的眼,20岁的泪
最美的情话
徐立新
爱是一座静候的小站
沿着树,藤高攀
说好彼此要疼爱
爱隔三道山
黄兴旺
半颗良心
执着的房客
难堪的一躬
父亲的那些秘密
相濡以沫
分一些咖啡给别人
朱成玉
5号病房里的天使
爱,总要拐几个弯儿才来
不要去打扰两株草的相守
嫁给水的蜻蜓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相信玫瑰
范云英
所有的努力都朝向阳光
爱,没有替补
爱,跋涉一万八百秒
朱晖
仇恨不能减轻任何痛苦
在黑暗中点亮一盏小灯
我在表演系92班等着你
贩卖爱心
我只为曾经爱过他而骄傲
梁阁亭
被一美元改变的人生
隐藏在“魔鬼式”教育里的父爱
一个九岁女孩的爱心奇迹
爱过方知情重
人生若只如初见
王飙
生命大智慧,人生大风流
朝圣者的心灵
有些眼神我们终生难忘
心灵的氧气袋
纪广洋
爱到不能爱
涩柿子
菊花枕
没有彼岸的河
罗西
忧郁比忧伤优雅
爱你不是一件伟大的事
婚姻是个安慰奖
那些与时俱进的浪漫
错爱
英涛
父亲的陀螺
没有什么比生命重要
爱心接力能改变什么
不要急于去证明自己
葛闪
暗战
爱情不能潜伏
80枚果子
爱有一双洞彻心扉的眼睛
马德
父亲,是个尊贵的名字
最美的天籁
你是亚马逊的一只蝴蝶
与你的青春擦肩而过
青春里,最好的方向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鲁先圣
这世界需要你
只有你不是为财产而来
亚里斯多德法则
谁都喜欢得到关注
|
| 內容試閱:
|
凉月满天
这趟列车不到2046
文凉月满天
十几年前,土地不像现在这般金贵和僧多粥少。如今即使家在农村,也只一人困守屁帘儿大的一块,上面插花一样间作套种,力求做到地尽其用。而那时候,大片大片的棉田,动辄绵延十几亩。绿油油的棉株,撑开巴掌大的叶子迎风招展,外行人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有内行——包括我一眼看去,就颔首曰:“嗯,该修理了。”
说来惭愧,身为农家子弟,我浇地改不了地畦,打药背不动药筒,去捉虫也能被发育良好、身材丰满肉虫子吓的直冒冷汗,也只有给棉花打尖理杈这点一技之长。棉田一眼望不到边,风飒飒地吹着,脚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手不停地给棉株“掏耳朵”--就是把主力棉枝以外,在腋窝长出来的捣乱的小嫩尖掐掉,不让它们长成不结棉桃的荒枝,争夺养料。“把反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就这意思。这是我最钟爱的一种劳动方式,安静而且舒缓,没事可以四处乱看,看天看地,白云苍狗,晴川历历,芳草萋萋。一大片绿云上浮着一个小小的,穿的确良小花褂的身影。偌大的棉田里,通常只有一个人和我作伴。
家里其他的男人们有更重的活计,浇水、锄地、打药,顶着烈日耕锄犁耙。只有他清秀文弱,就把他留在我身边,一边闲闲地说着话,一边一起给齐腰高的棉花“掏耳朵”。一人占两垄,他干得快,时不时把手伸过来帮我顾一段。正是六月天,抬起头,能看见他脸上的汗。奇怪的是这个人辍学务农已经两年,却怎么晒都晒不黑。17岁的少年,白面、细眼、长身,眼睛里总有一点点忧郁的神情,有点儿招人心疼。家里穷,虽然没让他再上学,但也不舍得让他多吃苦。我是在他家过暑假去的,当然也不会为难我这个客人,于是就把他派来和我一起干这种轻省的活计。
远远地看过去,地头放着他那辆二八加重黑色飞鸽自行车。从家到地里,需要穿过整个村子,走过弯弯曲曲我都绕不清楚的小路。他在后衣架上带着我,我一边坐着,一边拿手指一下下刮他的后背。他就单手掌把,腾出一只手来攥住我的手,惊险地在人们的注视和两旁的庄稼间穿过。
其时我读高二,自命算命先生,学校里正流行看手相。傻丫头们乐意幻想爱情线预示什么样的如意郎君。我想给他看看,他就是不肯,把手攥得紧紧的,怎么掰都掰不开。掰开一根,攥起另一根,掰开另一根,他把我的手也攥住。也不出声打闹,两个人安静地斗法,斗着斗着就到了田里,下地,干活。
要开学了,该回家了。二十多里的乡间土路,曲曲折折,还是他送我。两旁是一人合抱的大杨树,巴掌大的叶子在夏风中哗啦哗啦地唱歌。他停下来,把车子支好,我站一边,莫名其妙,看着他一步步走近,伸出胳膊,抱住我。我个子矮,刚一米五,虽然也17岁,但他却一米七还多。努力抬头,能看见他白皙的脸,还有好看的、红红的、女人一样的嘴唇,细长的眼睛闪闪发亮。他捧起我的脸,叫声:“凤芝”,柔软的吻象蝴蝶,轻轻落在花瓣上……
是的,凤芝。
也是暑假,去住了几天,走的时候他不在。过了几天,再去,他还是不在。一本书凌乱地翻开着,几乎每一页纸的边边沿沿都写满了这两个字:凤芝。凤芝、凤芝……感觉这两个字像长了嘴,发出一声声呼叫,呼叫里是浸透了疼痛的快感。正出神,身后有响动,他像只猫一样轻轻地出现了,就在门边,不说话,静静地看我。他伸出胳膊,一把就把我搂住了。
那天晚上,我宿在西屋,他没走。
外面脸盆大的白月亮照着,他也没睡着,我也没睡着。两个人的衣服都穿得整整齐齐的。闭着眼睛,他吻我,我不张嘴,他也不张嘴,两瓣嘴唇像印模一样贴着——我们都还不懂怎么接吻呢。半睡半醒间,天就一点点亮起来了,鸡开始叫,大人一边咳嗽一边升火。睁开眼睛看他一眼,红脸埋头,他轻轻扳着我的肩膀叫我:“凤芝……”没有誓言,没有许诺,那些不可解的美丽与不能承受的哀痛啊,那些铺满成长小径的忧愁,从此以后,世情似炉,人心如火,再也没有过这样美丽的时刻。
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他是我表哥。我考上大学的第二年,他结婚了。我大学毕业的那年,他添了小宝宝。他抱着脸朝外穿得像个小狗熊的娃娃,迎面走来,站定,细长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叫:“凤芝。”我的心疼了一下。
我是来报喜的。我也要结婚了。他听了,低下头,说:“哦。”
十几年过去,整个世界都变了。农村再也没有大块大块的棉田,整个华北棉田的风光都已不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我的孩子也10岁了。整天穿着职业装来来往往,身心疲惫,人事繁忙。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就把以前的种种渐渐淡忘了。
自从上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和短信,已经习以为常。有一个号码反复发来短信,有时是一个字:“累”;有时是一个字谜,谜面忘记了,谜底倒很容易猜:“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有时是谆谆关怀:“一向可好?”
我回:“请问哪个?”不理我。
“你是谁?”不理我。
“你究竟是谁?”还是不理我。
把电话拨过去,居然一拨就挂,一拨就挂。
不堪其扰,我就托朋友:“你帮我打,看是哪个家伙。骂他一顿。”朋友马上就把电话拨过去了:“听说,你爱乱给人发短信是不是?小子,你再敢这样,我剁了你!”马上电话就打来了:“凤芝,是我。”
“啊!”我没有话。是表哥。他也没有话,在电话里一起一伏地呼吸。相隔太久,也太远了。同事叫我:“老阎,走了,吃饭去。”我抱歉地笑笑,把电话挂了。
有一天回娘家,娘说:“去看看你姨父吧,躺炕上不吃不喝十多天了,估计快那什么了。”
“哦。”我有些自责,好几年没去看望他老人家了。那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从来不生气,也没有邪火。估计除了不让天资聪颖的表哥上学这件事,别的就没做错过什么。
先生骑摩托车带着我,一路上树木“嗖嗖”地往后倒退。进村,我迷了路。大大的水塘不见了,嘎嘎叫的鸭子不见了,空阔的场坪也不见了,那条曲曲折折通到棉田的路踪影全无,到处是房子,还有切割大理石的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我给表哥打电话:“来接我,我在村口,认不得路了。”
两分钟不到,一个人骑着摩托飞快地赶来。我冲他一摆手,两辆摩托相跟着飞快地往冲去。到家,摘掉头盔,表哥看着我,说:“怎么这么瘦了!”
我低头看看:这怎么能叫瘦呢?还是这么珠圆玉润的!
进屋,寒暄,姨爹在炕上躺着打点滴,一家子都在跟前守着。表嫂见我来了,笑着说:“哎呀,也不见你哥,接个电话就疯了样往外跑,原来是把你们接来了……”大家都笑,表嫂什么也不知道,也胸无城府地跟着笑。表哥不笑,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头抽烟,看不见表情。一霎时昨日重现:广大的棉田,强烈的阳光,慢慢走着的两个人。掰不开的手掌,重叠的嘴唇,静静地搂抱着细数月光。Yesterday
once more,啊,Yesterday once more。
我知道我对他的冷落和辜负,我知道他也知道。自从知道是他以后,他给我发短信,我再没回过,有时是半夜两点,电话响两声就挂断,有时是陌生的电话号码,以为是他,一查,远在上海。后来才知道,他给表弟打工,被远派上海,换了号码——还是他。
是他也没用。不冷落能怎样?不辜负,又能怎样呢?难道就为了偿这一世情缘,和他做一些成年人才会做的事吗?此生此世,再也不会有17岁的并肩而行,相向而坐。只能一个驻守,一个远离;一个怀念,一个遗忘;一个来了,另一个转过离去。
《半生缘》里有一句话叫人伤感:“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的,再也回不去了。“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流美人。”那是少年时代的爱情,纯美得无法复制,洁净得不容玷污,让人不忍心再有进一步接触。有些人只适合做朋友,有些人只适合做情人,而有些人什么也不适合做,最合适的就是在心底悄悄藏着,偶尔想起,微微痛过,也就罢了。
王家卫的电影《2046》,是一列开向未来却装满回忆的列车。我只想说,表哥,我们这趟列车,不到2046。
我和老铁的爱恨情仇
文凉月满天
一、 被爹扫地出门
一个男人到底要多行,才算厉害?反正我是见识过厉害男人的。他叫老铁,就是我爹。
我爹,牛眼厚嘴,吃饭有人盛,穿衣有人递,地位至高无上。一走路大脚板咚咚咚震得地皮响,背个盛满凿子刨子的工具箱,走到哪里都像个阎王。大巴掌拍在头上如撞钟一般,耳朵里嗡嗡作响。家里人都怕他,所有村民都服他--三十年前,谁家吃饭不是菜团子搀糠?只有我家是大米白面,最不济也是“皇粮”--黄粮:金黄灿烂的棒子面。我爹是个好木匠,锯板、打材(棺材)、五斗橱方桌大立柜,上手就来。民间有谚曰:“锯子一响,肉碗端上。”
他不喜欢我,当然,我也不喜欢他。
并且,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是老大,一个女娃,底下两个弟弟。他是指着两个儿子给他顶门立户,光宗耀祖的,至于我,白生白养,大了还要赔付嫁妆。读书?要学费?“老子苦扒苦做挣来的钱,不能都叫你打了水漂!”
这时我上初三,大考前夕,老师结伴到我家做说客,磨破嘴皮子,他就是不让我再上学。我娘悄悄推我:“去,给你爹说两句好话,说再也不犟了,他就让你上学了!”我才不。肚里磨牙,恨不得撕碎了他。
到最后老师说了一句话:“老铁,这孩子你甭管了,交给我。花不着你一分钱。”拉起我就走。
这学上不上?老师家里也不宽裕,学费真的要她替我垫?
我一封信写到当地妇联,信中诉尽我爹的罪状,强烈表达了“我想读书”的愿望。
没想到两个星期后,妇联主席亲自带着人来家访,把信拿给我爹看,让我爹成全我的梦想。他蒲扇样的大手捏着4大张信纸,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冲我娘大吼:“你养的好闺女,小崽子个儿没长成就想造反!上学?这辈子都甭想!”
我娘吓得抖抖缩缩,妇联主席看不过眼:“老铁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你不待嫂子好些,不让你女儿上学,我们就把这件事上报县长……”
一句话把他吓住了,粗暴不是愚蠢,发威使蛮他也知道分清对象。扭头进屋,捧出500块钱,啪!摔在桌上:“拿去!给她!老子有俩儿子,还怕没人养老?以后,不许她再进我的门!”
不进就不进,巴不得!
二、 母亲句句是遗言
这就算扫地出门了。读高中,考师专,毕业也不肯回乡,我跟着未婚夫远远到了南疆。
10年间,结婚,生子,得子宫肌瘤,动手术,不死也去半条命。麻醉药渐退,前尘往事一幕幕在脑子里放电影,要不是我爹,我这么一个有家乡的人不会变成在外游荡的野鬼孤魂。
娘来了。面色苍黑,身体瘦弱,气喘吁吁,紧紧捏着我的手。她杀鸡宰鸭,变尽花样,我吃得多,长得快,身体很快恢复了原样。看我好起来,她收拾小包袱要走。临走的头天晚上,她陪着我睡在一张床上,一边咳嗽一边絮絮地跟我说话:“妮子,别恨你爹。你脾气太犟,处处像他。你不知道,他整天教育你两个弟弟,让他们跟你学习……”
我困劲上来,迷迷糊糊地答应:嗯,嗯。
一个月后,一封加急电报拍过来:娘病危,速归!
等我赶回家去,我的娘啊,已经停在灵床上,盖着心头被,又小又黑。她还不到50岁--来照顾我的时候,她就已经是肺癌晚期。二儿一女,再加一个阎王爷,生生地把她早早送进坟墓里。回忆走前那一晚,句句嘱咐我的,原来都是遗言。
我心里刀片划过,鲜血滴落。袅袅升腾的烟雾下,他铜铃大的牛眼里一滴滴泪珠砸进土里。
发送完我娘,我马不停蹄赶了回来。没和我爹说一句话。
光阴滔滔,再隔两岸
然后,小弟就打过电话来了。他一向温柔又懂事,当初我挨打的时候,他不顾自己人小腿短没力气,跑上来拼命抱住我爹的腿,哭着喊:“别打我姐姐,别打我姐姐。”这次他可是来兴师问罪的:“姐,妈没了,咱们都伤心,最伤心的还是咱爹。他自从给你拍过电报,就赶紧上集给你买了一身新衣裳。打算等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交给你。可是你一个字都没跟他说……”
我只觉心里有个地方,软软地疼了一下。
7天长假。我把孩子扔给老公,给弟弟打电话:“告诉爹,我回去。”
大巴车坐了一天一夜,回到家已是星月满天。我爹佝偻着高大的身子,偎在一个破沙发上打盹。我刚把行李一放,他一个激淩惊醒了:“妮子!”
他赶紧站起,腿一软,趔趄两下。我本能要扶,他已站直:“不用,不用。我给你弄饭去。”
转眼5天,又该离别。我提着旅行包,还是当面叫不出一个“爹”字:“我走了,以后,会常来看你……”他正埋头吃饭,筷子抖了一下,头扎得更低:“嗯。”
这次,大弟跟我一起回来,托我给他找工作。
我一个普通教师,能给他找什么工作?让他干保安,他不干,看不起那一个月800块钱;让他当打字员,他更不干,他宁可上网打游戏,也不愿意听别人的使唤。
老公为此和我大打一仗,给了大弟2000块钱,把他打发回家。转眼我老爹的电话就打来了,开口就骂:“老子养大你们3个不容易,你是老大,你不帮你弟谁帮?”
我火撞顶梁:“你养大他们两个,没养大我!早知道你不疼我,当初你还不如就把我溺死,省得如今烦心!”
好容易修补好的裂痕,又撕开一尺宽。光阴滔滔,再隔两岸。
满腹的怨恨,还是被爱打败
从上一次电话上吵架,两不相见又是5年。
一天,大弟打来电话:“姐,回来吧,军军他……”
赶回家去,小弟弟胃出血。可怜我那温柔又可爱的小军弟,婚期已定,还有一个月就要当上幸福的新郎,却死在了医院。
母亲死了,天塌了,小弟弟也死了,地又陷。我爹中年丧妻,老来丧子,饶他强做强,终究是凡人。我恨他当年说话绝情,仍旧不交一言。
安葬完小弟,我精疲力竭,眼泪哭干。已是深夜,我爹主动开口叫我:“妮子,去睡吧。”
勉强抬头去看,家里唯一的大床上铺上新床单,平平展展,一床新被放在上面。他知道我有洁癖,不知道什么时候迈着老腿,忍着幼子丧亡之痛,跑到30里外的小镇上买来新被新床单。旁边摆着新脸盆,脸盆里有热水,冒着袅袅的热气,他说你熏熏眼。哭了一天,怕把眼睛哭坏……
我的天,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
母亲没了,小弟走了,我说你跟我走吧。他说不!“你娘也在这儿,小军也在这儿,我走了,他们找不着家门……”
我的泪,又下来了。
如今,我这个他当年最不肯指望的女儿,给他重新盖了房,刷了墙,按月给他寄钱。我还在这里腾出一间房,往后,就让我们彼此依靠。
本想着恨一辈子的,却没想到当初结那样深的怨,是因为时光在手,肆无忌惮。如今时日无多,彼此珍惜都怕来不及。俄罗斯诗人吉皮乌斯说:“趁你活着,别分离。”果然如此。说到底,满腹的怨恨还是被爱和岁月打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