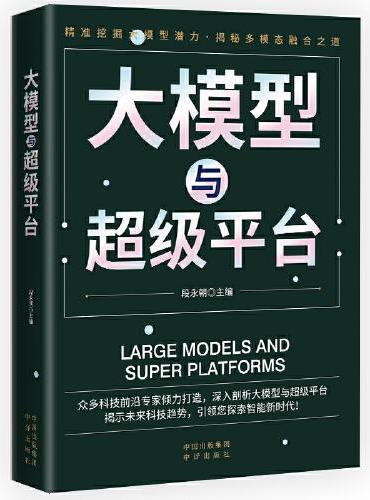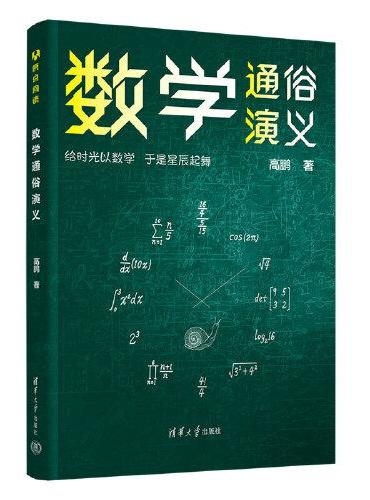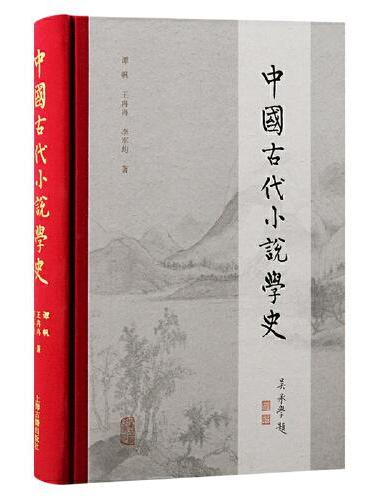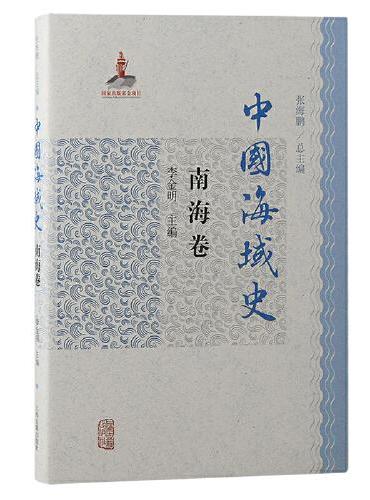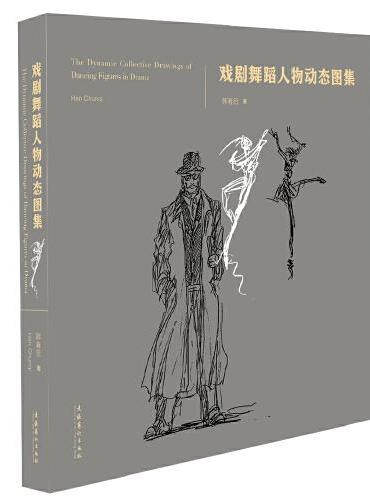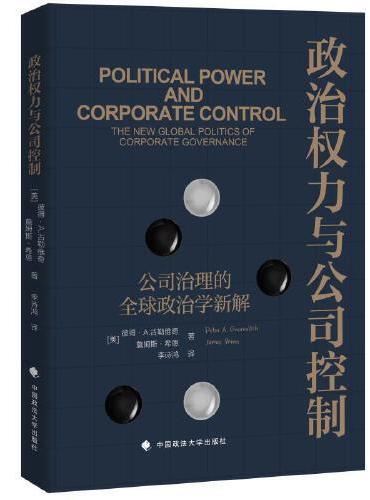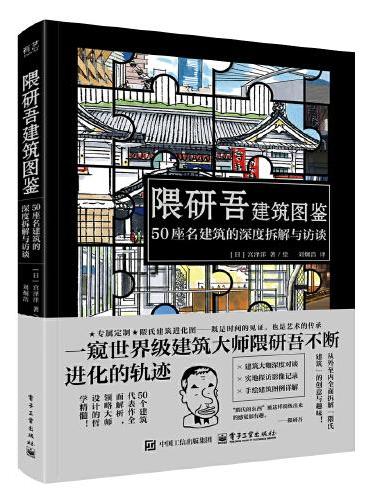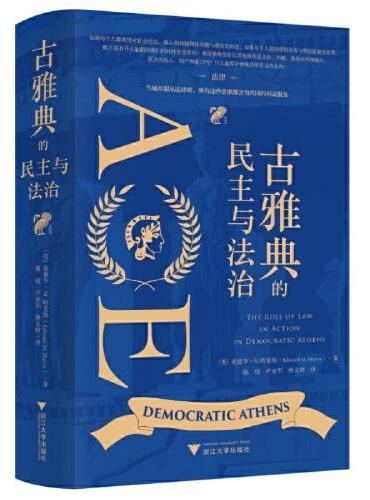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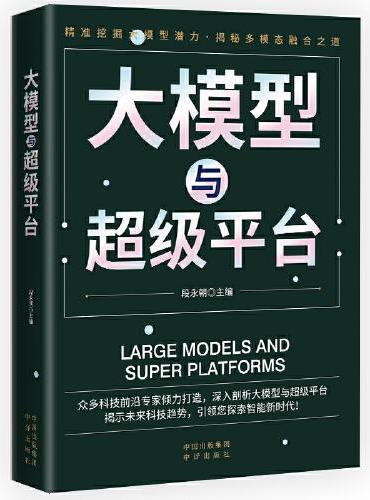
《
大模型与超级平台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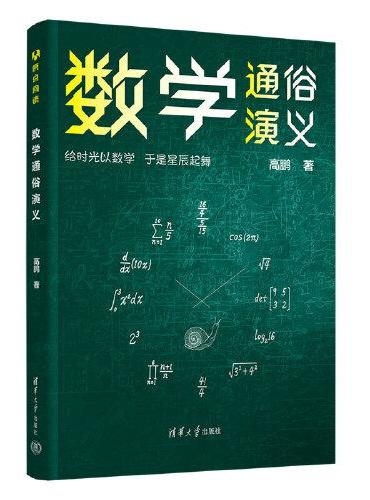
《
数学通俗演义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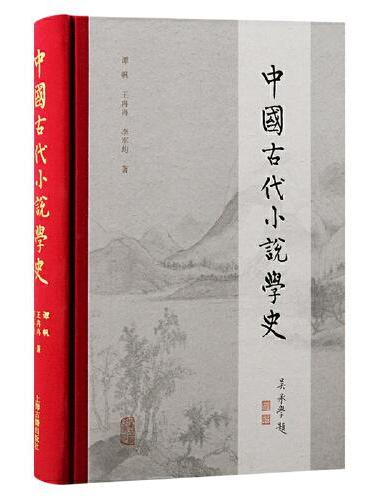
《
中国古代小说学史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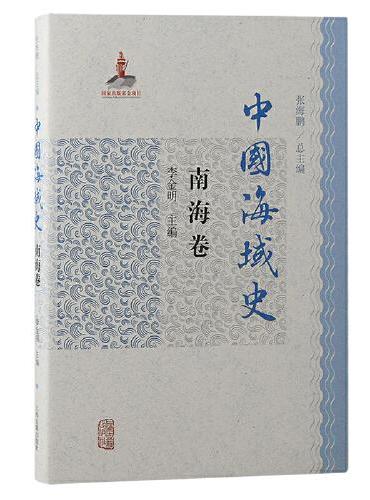
《
中国海域史·南海卷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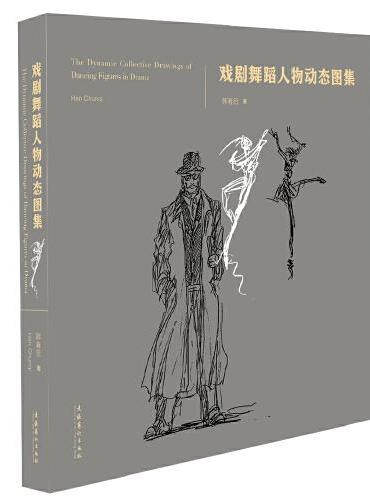
《
戏剧舞蹈人物动态图集(绝美的服装设计和极致的身体动态美感展现)
》
售價:NT$
16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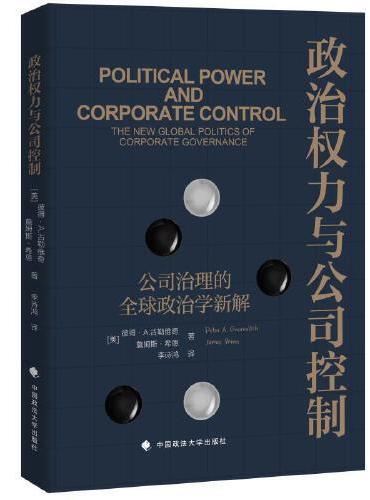
《
政治权力与公司控制 公司治理的全球政治学新解 (美)彼得·A.古勒维奇,(美)詹姆斯·希恩著
》
售價:NT$
5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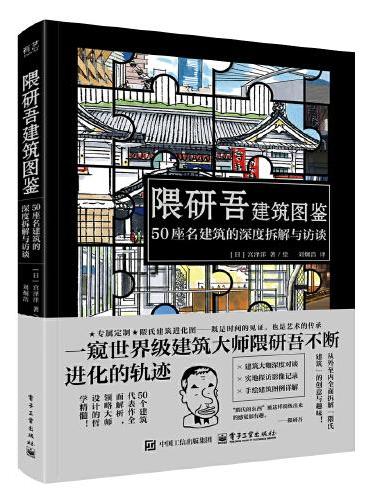
《
隈研吾建筑图鉴 50座名建筑的深度拆解与访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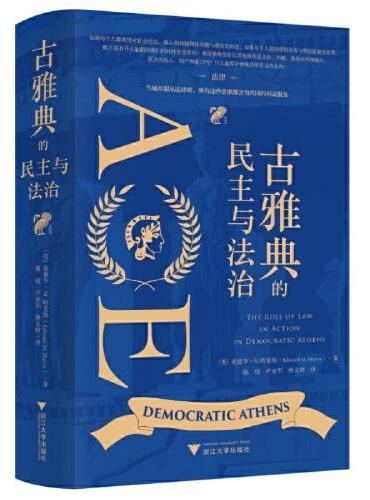
《
古雅典的民主与法治(当城邦服从法律时,所有这些资源都会为共同的利益服务)
》
售價:NT$
551.0
|
| 編輯推薦: |
|
中国小说新制高点,告诉你什么是中国文学里,最牛的文字,这无疑是一个小说天才,在向我们讲述这个时代。
|
| 內容簡介: |
|
小说讲述了“啤酒主义者”的创始人作家狗子,这10年来的生活经历,和对这种生活的反思、反抗。狗子分别客居10座小城,在里面重新发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酒、女人、生命力和思考。
|
| 關於作者: |
狗子,原名贾新栩,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著有《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活去吧》
被誉为最优秀的新生代小说家。
|
| 目錄:
|
写在前面
一.2000 北京
二.2001 廊坊
三.2002 金华
四.2003 东北
五.2003 海拉尔
六.2003 宁德
七.2005 镇江
八.2006 北戴河
九.2007 嘉定
十.2008 崇明岛
|
| 內容試閱:
|
我没有啤酒肚,却有一张啤酒脸。所谓啤酒脸,其实就是喝多了以后,第二天醒来面部浮肿。对我来说,啤酒脸尤为明显,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要胖先胖脸的人。多年来,我的体重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却常听朋友对我说:“你胖了”或“最近怎么好像瘦了”之类的话,前者意味着我已连续喝了多日大酒,后者意味着我近期没怎么喝。
其实都不必连续大酒,有时只需大喝一顿,第二天我就会变成一个胖子,像是一夜之间增重了10斤,其实我知道我大概是长了二两肉,左右腮帮子各一两,加之胖(一声)也就是肿,于是昨日还精瘦干练的我今天就变成了一个满脸横肉二目无神的胖家伙,之所以二目无神,除了酒后易精神低落之外,也因为我对自己恬着张胖脸的这副尊容很是不满,好在这么多年喝下来,我也疲了,不至因一张啤酒脸而不敢见人。
有时这张啤酒脸也会给我带来方便,比如对于那些熟悉我的朋友,我会省掉很多解释的口舌,他们见着恬着张啤酒脸出现的我,上来就会问“昨儿跟谁呀”,也有的端详我一番,然后慢悠悠发问:“昨儿是老弛还是阿坚?”我便如实相告,顺便也满足一下他那一眼看穿的成就感。
在北京,周围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曾有三座大山,阿坚,老弛,黄燎原。黄燎原这座大山已被我推翻了,其实算不得“推翻”,人家是自己移开了。我和黄燎原是发小儿,一度在一起形影不离,但黄燎原不是为混而混,他是要干事情的,要干事情自然就不能成天在我这儿压着……而阿坚老弛则不同,他们认为朋友们成天在一起喝大酒,是第一甚至唯一正经的事,其它都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而这样为混而混的喝大酒,我似乎是最佳人选,敢喝能喝不闹事能接话,没工作没人管得了我,关键是喝起酒来我变得和他们一样虚无,也就是,至少在酒后,我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可说是志同道合,所以他们俩至今仍是我的两座大山,我在北京完全置于这两座大山之下,结果无家无业的我变得比那些上班挣钱养家糊口的朋友还忙。
对于两座大山的说法,两座大山自己均不承认。大山阿坚说自打认识了我,他的诗歌前程基本被毁了,他的诗越写越少越写越水,以至于他后来只会写那些不过脑子的流水账了,现在他连流水账都懒得写了,流水账虽说不动脑子,但字数还摆在那里,现在他只能写提纲了,原本几百行的长诗或中长篇小说,现在到了他手里只变成大约十行的分节目录,他说照这个趋势下一步只能写标题了,最终不立文字。大山老弛则说这些年喝大酒喝得抽筋落枕手脚发麻是常事,有回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竟把腰给扭了,害得他连续一个月天天去医院推拿按摩,他说他担心他的老命迟早毁在我手里。言下之意,二位大山均认为是我在毁他们在欺压他们。
这就是朋友。对此我们倒是有个共识,就是朋友——尤其是好朋友,就是互相毁,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搞不好全插朋友肋上了,谁让离得这么近呢。
阿坚
近一两年,新街口的天川酒馆及周围的胡同成了我和阿坚的单位及游乐场。这之前,我们的“单位”在西四附近的一个拉面馆,但那家拉面馆嫌我们经常只是一个凉菜八瓶啤酒一坐就坐半宿迟迟不愿“下班”,终于烦我们了,开始是脸色不好,这点我们可以不介意,后来一过晚上十点,除了拉面就要什么没什么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阿坚在另一处喝完酒,想在拉面馆里再小坐小酌一番,此时应该还不到十点,小姐说啤酒卖光了,凉菜锁在冰箱里,她没有钥匙,火也封了,阿坚问:有茶吗?来壶茶,我们就坐十分钟。小姐阴着脸说:没有茶。我问:那有白开水吗?喝点水。小姐阴着脸说:没有开水。阿坚问:那有自来水吗?来一壶。小姐没说什么,真给我们上了一壶自来水,两只茶杯。我们各自喝了两杯自来水,抽了根烟,撤了。从此,我们辞别了拉面馆,改在天川上班了。
天川24小时营业,服务态度好,老板娘姿色尚好,40多岁,与阿坚年龄相仿,阿坚跟别人介绍天川时,屡次提到“老板娘很漂亮”。不过老板娘的丈夫是名警察,不过即便老板娘的丈夫不是一名警察,阿坚也绝无非份之想。阿坚之意不在老板娘,在乎啤酒和狐朋狗友之间。当然阿坚给老板娘送过他写的书,给老板娘算过命,夸过老板娘身段好,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想重蹈西四拉面馆之复辙。
时间长了,还真就熟了起来。上至老板娘下至换了几茬的服务员厨子,皆混得厮熟,包括门口卖水果卖烟的小贩,这里的电话就是我们的办公电话,你可能记不清一个朋友的手机号,但你只要记得天川的电话,八成就能找到他,他不在必有认识他的朋友在,我们天天有人在此值班,值夜班。
我们可以坐着喝茶不点菜(当然次数极少),我们每喝6瓶啤酒服务员就会免费送1瓶,我们还赊过一两回帐,阿坚喝多了喜欢舞文弄墨,于是天川酒馆用来写菜单的毛笔墨汁就成了阿坚的醒酒工具……昨夜,阿坚又写了,我记得他在酒馆的电匣箱上写了四个大字:小心玻璃,另加三个叹号和一道闪电。
我们知道天川酒馆服务员的名字正如她们也知道我们的名字。服务员有时也兼秘书,比如她们会在柜台后举着电话朝我们这桌大喊:“阿坚电话!”或“狗子找你的”,有一次阿坚扭着脖子问:“男的女的?”服务员说:“一个男的,叫什么弛的”。阿坚说:“跟他说我正忙,让他过会儿再打”,服务员笑眯眯如实转告,没过多一会儿,老弛半醉着推门进了天川,指着乌烟瘴气的我们一桌说:“你们丫真够贫的。”老弛刚从某海鲜馆吃完喝完,面对我们这一桌家常残羹剩饭,皱了皱眉头,仿佛我们在喝泔水,不过待他狂饮几杯及上了趟厕所之后,便也埋头狂撮了起来。
大约从半年前开始,天川酒馆周边的胡同开始拆迁,拆迁之后遗留下来的一片片废墟成了阿坚的游乐场。从此以后,阿坚每逢喝多了,便要从酒桌上消失,片刻之后,他会抱着些灰砖灰瓦回来,他先是去水池边冲洗,然后堆在地上晾干,然后招呼服务员笔墨伺候,然后在这些砖瓦上题诗题字,然后他将这些题了诗词的砖瓦分送给在座的朋友。
砖是好砖,青灰色,很长,很重,敲起来有金属声,有的砖棱上有细细的凹槽。阿坚说这是清代的。阿坚说可以拿回家当枕头,夏天倍儿凉快,现在我的床下就堆着这样两块砖。
瓦则花样较多,有一般的,有瓦当,有瓦坡,阿坚会对你讲得头头是道,瓦当上有各种花纹,阿坚根据花纹种类将它们分成公母。
还有巨大的方砖,有半个墓碑那么大,一个人免强能抱动,这种砖阿坚专送给开车来的哥们。
一开始,大家觉着新鲜,对阿坚的馈赠均颀然接受,时间长了,众人均有些承受不住,不能每次喝完酒都往家里抱砖吧?尤其是像我这样打车回家的,肯定不能拎着块板砖在街边拦的,掖在怀里也显得形色诡异,只能四处乱找塑料袋,有一次实在没找着合适的塑料袋,我只得脱了外衣把砖裹在里面,下了出租车,我尚需步行5分钟才能到家,那是冬天,我便穿上外衣,拎着块巨大的板砖在夜深人静中满嘴酒气地埋头疾走,好在没碰上巡夜的。
现在,倘阿坚再在酒桌上送砖送瓦,众人一般均不吱声,逼得阿坚没法了,只得愣送:“你把这砖抱回家,我把这酒干了!”弄得这哥们直说:“何必何必,我抱回去就是了。”
我见过阿坚拎着根棍子在这些夜深人静的废墟里翻翻拣拣,有时实在没什么收获,他会打还未搬走的钉子户的主意,找根长杆子直接掀人家的瓦,有一次动静太大,惊动了人家,但可能是作为钉子户心里也发虚吧,那户人家没敢亮灯,只从黑乎乎的小屋里传出一个老爷们圆润的粗嗓:“干什么的?”我和阿坚抹头疾走。后来我们回想那个粗嗓实际上有些外强中干,甚至有些发颤,我想那哥们后半夜八成得失眠,他没准会想:政府不敢跟我玩硬的,莫非要跟我玩什么阴的?
顺便说明一下,阿坚生于50年代,无家无业,爱好写诗和旅行。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他是第一个爬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没有他那些花圈堆不了那么高,历史照片也会黯然失色不少),他还积极参与推翻并焚毁公安机关汽车的群众活动,签于他在这场民主运动中上窜下跳的积极表现,他被青年工人、返城知青、待业青年及一小撮地痞流氓推举为“北京市工人代表”之一,负责与四人帮的黑爪牙进行谈判,据说在谈判中阿坚表现得有理有利有节,无奈这场谈判其实是四人帮的缓兵之计,正当阿坚舌战群儒的时候,几万名拎着棒子的工人民兵正在夜幕掩映下悄悄向天安门广场集结……
作为暴乱分子,阿坚被关了半年。那半年,阿坚对外人缄口不提。有朋友说,阿坚在狱中坚持斗争,既英勇顽强,又灵活多变,保护了自己也掩护了同志,阿坚不愿提那段往事,是出于一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心态;也有朋友说,阿坚在那半年里,写了几十万字的悔过书,其文字功底就是那半年打下的,阿坚不提那场牢狱之灾,实在是羞于提起。反正从此以后,阿坚摆出一副弃政从文的路子,20年来,潜心于诗歌,并且小有成就,成为中国口语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如果朋友们催得不是太急,我经常坐几站公交车到西四,然后步行去新街口。这段路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这条路路窄车多,人也多,平时就很拥挤,又赶上我“上班”的时候通常正是这个城市下班的高峰,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出租车,都慢得像蜗牛爬,有时候堵作一团,喇叭声响作一片,步行的我能看见塞得满满的公交车内人们焦急的目光。
早些年,这条路也曾扩过,不过因为路两边的建筑没动,所以只扩了快行道,自行车道减半,便道减得更厉害,有些地方只有一米来宽,那已经不是什么便道了,分明就是一个宽台阶。这几年机动车恶性膨胀,扩宽的那点快行道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自行车和行人也是只增不减,所以这条路变得越来越拥挤了,尤其是在那一两米宽的便道上,完全可以用“摩肩接踵”这个词,有时我想走快些,便要不时地侧身穿行,这么走容易使我越走越快,甚至干脆小跑起来,似乎阻力越大反而越能焕发我穿越的力量,置身于前后左右各色男女,我时急时缓,穿行其间,谁也不碰,有点疱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意思,简直是越走越上瘾越走越兴奋,经常一阵风一头汗地进了天川,然后气定神闲地一坐,有哥们会说:哦,你最近气色不错,但怎么出汗了?我说:我就是上班心切,怕迟到,一溜小跑来着。
并不总是走得这般兴奋,这般热血沸腾。有时候,因为头一天喝大了,身体极度发虚,内心更是极度发虚,整个人像是没有重量,然而这种失重感与昨夜喝大了之后那种身轻如燕随时都可飞檐走壁的失重感几乎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向下的感觉,有点像身坠无底深渊,因为无底,所以也并不是很恐惧,只是非常不适应这种向下的感觉,而且只能在这种感觉中非常难受地耗着,找不到任何可抓可攥的东西,更不要说找到什么新的途径(哪怕是岔路)能让自己脚踏实地起来。这大概就是所谓崩溃的边缘吧。
天川的上客高峰大致分两波。第一波是晚上6点多到8点多,这一波的食客没什么新鲜的,人员也不固定,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有匆匆填饱肚子的,有各种名目的中小型聚餐。第二波从晚上11点左右开始,来此就餐的有固定的这么几类:一类是从JJ迪厅坐完台的小姐,她们那适应迪厅光线的浓妆在天川的日光灯下显得夸张刺目;一类是公交车司售人员,着天蓝色制报,这种蓝色艳得有些离谱,也很刺目;再有就是警察,来这儿的警察肯定是老板娘丈夫的同事(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她丈夫),这从他们自若的神态就能看出来,他们与老板娘熟到已不用寒暄,他们点菜很少看菜谱,有时不用点菜,他们一坐下,菜很快就上了,我想这是订好了的。他们一来就是七八个,总要拼桌,印象中他们总是进门先去水池洗手,也不知他们刚才干什么了,他们通常吃完就走,然后钻进停在门口的依维柯警车,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剩下的还有出租车司机、牌友、在别处喝大了转场接着喝的醉鬼,以及说不上干什么但一定是形色怪异的青年男女,我说怪异,是指其中经常出现绝对美女和绝对丑女,男人中则经常有长发和光头,相貌平常者几不可见。
阿坚喝多了以后,经常乱点啤酒送给各桌的朋友,有不喝酒的小姐就送可乐。很少给警察送啤酒,主要是这拨警察很少喝酒,而且很可能人家一会儿要执行公务,此时给人家狂送啤酒,想把人家灌晕吗?这不是扰乱社会治安么。有一两次,警察们也喝起了酒,阿坚点了两瓶啤酒让服务员送过去,服务员小姐冲警察们作了个手势,并说“那桌送您的”,警察们略带惊异地回过头来——有情况?我看见一个家伙的手向怀里伸去——这只是我一刹那间的想象,事实是,阿坚迎着警察们的目光将身子板挺得笔直,并且一手高举酒杯,一手高举示意(倒是类似投降状),然后一饮而尽,警察中一个敞着警服扣的老警官也举起杯来,笑眯眯地干了,我对坐在身边的一个姑娘说:这叫警民一家。姑娘小声说:是警匪一家吧?
如果说警察们对阿坚的赠酒只是略显惊讶然后颀然接受的话,那么JJ迪厅的小姐们对此则充满戒备、疑心重重。通常一桌浓妆艳抹埋头暴搓的小姐(她们的吃相大多不雅,让人想起狼吞虎咽、生撕活剥这类词),面对服务员端上来的“那桌大哥送的”啤酒或可乐,先是停了手中的活计,然后齐刷刷扭过头来,有的姑娘嘴中还含着半口菜,她们的神情在一秒钟之内从愣神到疑惑再到尴尬飞速过度,然后其中一个经过些世面的姑娘会硬着头皮说声谢谢,阿坚抬手示意“慢用”,另一只手端起酒杯本想狂饮进一步示意,小姐们却早早收回眼神埋头“慢用”了(她们明显放慢了进食速度,我想她们原本旺盛的胃口被阿坚败了一半),阿坚也只得不咸不淡地自喝一口。
也有比较放得开的小姐,我曾被几个东北大丫头灌晕过;我们还碰到过一个妈咪级的人物,30岁左右,眉毛被拔光后重新纹成一条细线,身材倒是娇小,她的名片上写着某某夜总会领班,她总是后半夜两三点来,并且常带两个女孩,两个女孩长得一般,也不太会打扮,像是初入风尘,与她们狂喝过几回,这姐仨话不多,喝起酒来却着实了得,跟我们一杯一杯对着干,从不推脱,如果后半夜我们还没大醉,但只要碰到这仨女的,则必喝到失忆,所以跟这仨喝酒除了对着干杯没留下别的印像。
女的到底能不能喝?我知道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民间说法:女人天生四两酒,意思是女人能喝;另一种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医学说法,大意是说女人代谢酒精的能力比男人低,这与女人身体中脂肪比例比男人高有关,怎么个有关法我忘了。
现实中的情况当然是,女的不如男的能喝,喝酒的女的比喝酒的男的要少得多。我想这肯定不是女性代谢酒精能力差造成的,差也差不出这样的现状,这显然是文化使然,我们的主流文化是不鼓励妇女喝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些不知主流文化为何物的妇女中间,比如边远山区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们,比如某些少数民族妇女,她们喝起酒来如同家常便饭,我在农村就碰到过喝得醉醺醺的老太太,很可爱。
另一个极端,在那些反主流文化的妇女中间,比如女流氓或所谓艺术女性,在她们这儿,喝酒的比例也徒然增高,写《情人》的那个玛格丽特o杜拉斯算代表人物之一吧,“女人天生四两酒”,说的大概就是这路女侠,男的跟这路女侠喝酒,由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作怪,往往容易不拿人家当回事,你小杯我大杯你一杯我两杯,结果就很容易被她们灌翻,正所谓“喝下了一杯自酿的苦酒”,灌翻之后会想不通,于是只得归结为女人天生就有量,其实细察,她们的酒量也就一般。
还有一种女的,出于工作需要,也能喝,比如上面说到的那姐仨,再比如女秘书,女办公室主任,女处长(当然在座的得有男部长至少男局长)。
跟以上三类女的喝酒,都好办,大不了一醉。难办的是,当某位一向规规矩矩的良家妇女在你面前突然大喝二喝起来,而且怎么都劝不住,这就有点麻烦了,这说明她遇上事了,不是你的事就是你哥们的事。你的事相对好办,也就是等她喝多了听她劈头盖脸一通臭骂,然后摔碟子摔碗,然后嚎啕大哭,然后哇哇大吐,你扛着点就是了,外加受累把卫生搞好。倘若是你哥们的事,而这女的又长得挺好,这时就相对难办,除非你和你哥们都不怕乱甚至喜欢乱,否则一定要顶住,当她对你哥们痛叱时一定别接茬,既不要拧着她的劲狠夸你哥们,这样容易激起她更凶猛的倾诉,当然更不能附合她说这哥们“真不是个东西”;当她说累了也哭累了对你破涕而笑时一定要装作没看见,千万别相视一笑什么的;大不了最终她会投怀送抱,这时您也不必板着面孔跟人家说“请放尊重点”,这太不近人情,此时你一定要学会灵魂出壳,你的手你的肩要像木头一样麻木不仁(像过电一般发麻就糟了),相信她摆弄几下也就没了兴趣。我想也就这三板斧吧,倘若她再过激,那就算你倒霉了,对此我也没想好怎么应对,总之是不能报警的,谁让你丫是个男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