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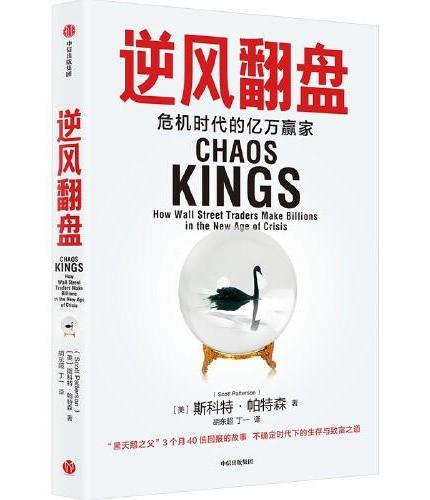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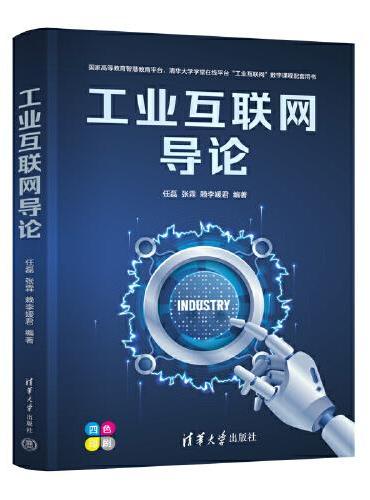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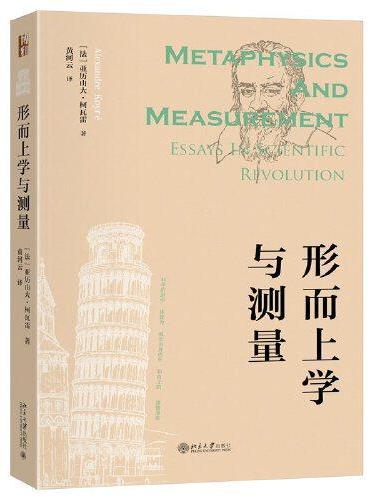
《
形而上学与测量
》
售價:NT$
340.0

《
世界航母、舰载机图鉴 【日】坂本明
》
售價:NT$
340.0

《
量价关系——透视股票涨跌脉络
》
售價:NT$
340.0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
《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
》
售價:NT$
295.0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本书所辑存注释的四十二封书简,大部分是萧红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由日本东京寄回上海和青岛给萧军的,也有几封是她回国后,又去北京,由北京寄到上海的。作者在四十多年后,于故纸堆中发现了这批书简,将它们按年月日作了排序,加以适当的注释,是对其与女作家萧红相识、相处六年间(即上世纪30年代)一段过往心态和历史往事的追忆。
从这批书简的一枝一叶里,也可以大致理解一些这位短命作家基本思想和感情的特点,精神、肉体、生活上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与折磨到了如何境地。为了使这辑书简注释能够更多一些发挥它的文献参考价值,本书在附录中尽可能增加了一些与萧红有关的各方面材料,由于它们也与这批书简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这对于热心研究萧红这位短命作家的作品、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用处。
本书分为四部分:萧红写给萧军(萧红自日本东京寄上海、青岛的35封和自北京寄上海写给萧军的7封书信手稿及注释)、海外的悲悼(萧红所写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书信文章)、萧军写给萧红(萧军自上海寄北京写给萧红的4封书信手稿、注释及诗文)、附录(九篇与女作家萧红有关的各方面材料)。
|
| 關於作者: |
萧军(1907—1988),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刘鸿霖,祖籍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村(现属凌海市)。
他五岁进村学,受私塾启蒙;十八岁入伍当骑兵;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萧军拟组织抗日义勇军,因事机不密险遭不测,事败后潜入哈尔滨,易姓更名,鬻文为生,开始文笔生涯……在此期间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遭伪满通缉而逋迁关内。其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出版后,被誉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称它“是一部很好的书”。历时十余载写就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上下卷,即《过去的年代》)被视为他的代表作。
他是一位多产而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无不涉猎,仅古体诗留存下来的就近千余首。在极度困难的境况下,他也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倾尽毕生的心血。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承上启下者,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萧军晚年所写的《鲁迅先生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开创书信注释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受到学术界好评与关注。
|
| 目錄:
|
萧红写给萧军
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 船上)
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
第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东京)
我们彼此对各自的体性“相知之深”,生活在一起并没什么“矜持”的习惯。
第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东京)
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是并不寂寞的。
第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东京)
后来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化起来:一、早晨六时以前必须起床。二、沿跑道跑步三圈。三、一小时运动后,漱洗,休息,吃早点。四、八时半或九时开始写作。
第五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东京)
我总愿意说一些愉快的事情去影响她,用以冲淡她那种容易感到孤独和寂寞的心情,所以总是说这样好,那样好……免得她大惊小怪,神经过敏,浪费精力来关心我!
第六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东京)
我们这虽然也算是夫妻之间的“情书”,但却看不出有多少地方谈到“情”、谈到“爱”!或者谈到彼此“想念之情”,更多的谈的却只是事务和工作。
第七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东京)
这也就是当时我们的关系和实情。又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关系和实情。
第八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东京)
她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自己的工作的,这也就是很快地熄灭了她的生命之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九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东京)
我估计自己当时不会“漠然视之”,可能马上就写了复信表示祝贺和鼓励!她是需要鼓励的。同时也会对她提出“警告”,当心身体所能容许的限度,免得再故病复发。
第十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 东京)
在我的意念中,过早地睡觉是一种时间的“浪费”!我是很珍惜夜深人寂那一段时间的。
第十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 东京)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由于肚痛好了,写作胜利地完成了,所以她就感到了宁静和“快活”了。
第十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 东京)
她是有矛盾的,但为了自尊,还是隐忍地要坚持原来的计划—住一年,因此我也不便勉强她回来。
第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 东京)
一件作品如此,一个作家也如此,只要人民需要他,他就要被批准,任何排斥,掩没,或假装他不存在的办法……也是无用的。
第十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 东京)
这就是她的脾气,一切事常喜欢从兴趣出发,缺乏一种持久的意志。
第十五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 东京)
一个人的心情一坏下来,对于任何事物全会厌烦的,更何况从事所谓“文学写作”?
第十六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 东京)
这目的是要使对方明白,我不独有钱,而且是有高等文化修养的绅士—那时期能说洋文的就代表是高级知识阶级,这就是那时期作为上海洋场社会的一种可怜和可悲的现实……
第十七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东京)
我通常是接信即复的,首先是回答问题,其次是说些别的,而且要说得多,说得仔细些,“敷衍成篇”,否则又要抱怨、发牢骚了,说我不给她写信。
第十八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东京)
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
第十九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东京)
在任何人,任何国家、社会……在未“笑”别人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笑”一下自己,我看这是有必要的。
第二十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东京)
尽管生活如何折磨我们,但彼此之间还没有失却“童心”,总还要彼此开开玩笑的。
第二十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东京)
她想到“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这“奔波里的人”是指的鲁迅先生。
第二十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东京)
这是给黄河清兄的一封信。
第二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东京)
但她不知道将要有最大的、最沉痛的悲哀在等待来袭击她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
第二十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东京)
她可能在报上(她不懂日文,也许不看日本报纸)得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了吧?也许还不知道。
第二十五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东京)
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
第二十六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东京)
大概许先生把她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全和萧红谈过了,因此她们是彼此较多有所理解的。
第二十七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 东京)
问题还是老问题,我要随着学生们去打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而她却希望我仍然继续做一个“作家”(她也不能算错),但是那时我已经失却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心情了!对于“笔”已经失却了兴趣,渴望是拿起枪!
第二十八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 东京)
古语所谓:“欲哭无泪,欲嘶无声!……”这话是深刻的。流不出眼泪的悲痛才是最深沉的悲痛!
第二十九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东京)
她说我把她一向看得很弱,和我比较起来,无论身体和意志,她确是很“弱”的,在信中她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
第三十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东京)
她又建议我买软枕头了,也发表了“理论”,大概我是没买的,因为我并不头痛。
第三十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东京)
我在那时期是不吸烟的—现在吸了—因此就对吸烟的人有“意见”;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吸烟。
第三十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东京)
幸亏我是个皮粗肉糙、冷暖不拘的人,假如我和她“差不多”,就要生活不下去,为生活所压倒,早就“同归于尽”了。
第三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东京)
回想和她结合的几年来,尽管生活如何艰难困苦,外来的风风雨雨如何恶劣,而“形影不离”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
第三十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 东京)
我和她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后来的永远诀别,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性的悲剧必须演出:共同的基础崩溃了,维系的条件失去了!
第三十五封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东京)
我很敬重他,爱惜他,……并没因为我和萧红分开我们的友情有所损伤或冲淡!
第三十六封信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京)
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件就只剩了以上的三十五封,究竟失落了多少,无法考查了。
第三十七封信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
在一般朋友眼中认为我们“夫妻”之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除开贫穷以外,是幸福的。我们也承认,在比较起一般的夫妇之间来,我们确是幸福的,但也还是各有各的痛苦!
第三十八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北京)
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我希望快来信!
第三十九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 北京)
何况这一次“痛苦”的形成是我自作自受,我无可责备于任何人,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理论”为根据,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
第四十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北京)
假如她用拳头敲我,我也可以任她敲去:第一,她的拳头是敲不疼也敲不坏我的;第二,她也不会认真敲我的。
第四十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 北京)
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第四十二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北京)
这是她从北京寄上海最后一封信了,不久她也就回到了上海。
海外的悲悼
第四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东京)
当她信中问到:“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这时鲁迅先生已经落葬了。这句天真的,孩子气式的问话,不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伤痛啊!这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死了妈妈,她还以为妈妈会再回来呢!
萧军写给萧红
第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上海)
由上海寄北京给萧红的信,我手边还存有四封,附在这里的目的,是可以对照她寄来的信所提的问题是些什么?我是怎样回答的。
第二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 上海)
“小狗熊”这是她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笨而壮健,没有她灵巧,我就叫她“小麻雀”,因为她腿细,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
第三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上海)
这封信可能就是被她讽刺为“讲道理”的信吧。
第四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 上海)
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侧面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节选)
萧军纪萧红诗
附
之一 在西安—聂绀弩回忆萧红
之二 聂绀弩悼萧红词一首,诗四首
之三 萧红生平年表(丁言昭 萧耘)
之四 萧红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丁言昭 萧耘)
之五 第一章 从迁墓说起(陈宝珍)
之六 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王建中)
之七 本书所用参考资料
之八 有关萧红研究的中外文著作资料(萧耘)
之九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的回忆”(骆宾基)
编后赘语
|
| 內容試閱:
|
第十四封信
东京—青岛
(1936年9月10日发,9月15日收到即复)
三郎:
我也给你画张图看看,但这是全屋的半面。我的全屋就是六张席子。你的那张图,别的我倒没有什么,只是那两个小西瓜,非常可爱,你怎么也把它们两个画上了呢?假如有我,我就不是把它吃掉了吗?
尽胡说,修炼什么?没有什么好修炼的。一年之后,才可看书。
今天早晨,发了一信,但不到下午就有书来,也有信来。唐诗,读两首也倒觉不出什(么)好,别的夜来读。
如若在日本住上一年,我想一定没什么长进,死水似的过一年。我也许过不到一年,或几个月就不在这里了。
日文我是不大喜欢学,想学俄文,但日语是要学的。
以上是昨天写的。
今天我去交了学费,买了书,十四号上课,十二点四十分起,四个钟头止,多是相当多,课本就有五六本。全是中国人,那个学校就是给中国人预备的。可不知珂来了没有?
三个月,连书在一起二十一二块钱。本来五号就开课了,但我是错过了的。
现在我打算给奇她们写信,所以不多写了。
祝好。
吟
九月十日
注 释
唐诗总算为她寄了去,但她又没什么兴趣读了,在日本似乎也呆得无味了,还未开始学日文,就对日文产生了不喜欢。俄文,我们在哈尔滨曾同请了一位俄国姑娘学习过,她那时学得比我好,文法练习也作得比我强,很得到先生的称赞!可是一离开哈尔滨,她就连俄文摸也不摸了。这就是她的脾气,一切事常喜欢从兴趣出发,缺乏一种持久的意志。
提到学俄文,顺便写些关于学俄文的小故事在这里。
我们的先生是一位十九岁的俄国姑娘,父亲是一位赶“斗儿车”的老车夫,不大喜欢讲话;母亲是一位很热情的胖老太太,还有一位哥哥,但不和她们住在一起,在感情和思想上,据她说也不很合得来。这人似乎是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
我们曾到她家做过一次客,他们留我们吃午饭,是一餐很地道的、很丰富的俄国饭。我已经吃得很饱了,但那热情的老太太,几乎近于“强迫”地还要我吃,而且用俄语反复地说:
“吃啊!吃啊!青年人应该多多地吃啊!……”
我们的先生叫“佛民娜”(译音,她可能姓“佛民”,“娜”是代表女性的意思),长得并不算美丽,而性格却很活泼愉快,但也很严肃,有时严肃得几乎和她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每星期上三课,每次课一点钟三十分,每月学费十五元,—这应该感激我已故的讲武堂老同学黄之明,是他为我们担负的,我们自己并无这财力!—这还算少收了五元,因为我和萧红学的是同一的课本《俄文津梁》。
使我感动的是,我们这位先生来教一次课,往返要走三十里左右的路程,是完全步行的!而且无论雨、雪、寒、暑……很少有缺课这情况,因此我默默地很敬佩这位先生的吃苦耐劳,负责认真,一贯的意志和精神!……
从外形来看,她并没有什么可惊人的美丽或漂亮的地方。只是个一般的俄国姑娘,身材并不高大,也不显得特殊壮实,相反的和一般俄国姑娘比较起来却倒是显得身材很苗细,然而四肢腰身各部却配合得很匀称;有一个较小的头,脸幅也不宽,但前额很宽广平正,鼻子近于细而略长,鼻头有些尖锐翘出。脸上唯一特异的是那双贴近鼻根的大眼睛、瞳仁和眼白……几乎全是湛蓝的,竟如两泓湛蓝色的小湖,显得是那样深远、安宁而平静。
她能够说俄国式的中国话,讲解课文,教练发音全很认真。有一次我把“印捷以嘎”(俄语“印度鸡”)竟错念成“印度嘎”,于是她大大讥笑了我一场。此后一见面她就管我叫“印度嘎”了。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在要离开哈尔滨的约前两个星期,悄悄告知她,说明我们要离开哈尔滨,俄文不能再学下去了,表示很遗憾!她也显出了一种很依依惜别的样子,因为我们像朋友一般地相处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同时萧红找出了偶然买下的一块米色的软绸准备为我做围巾用的,知道她还能刺花,请她给刺上一点什么,留作纪念。她慷慨地允诺下来了,带走了那软绸。
过了几天,她忽然来了,拿出了那块软绸来,她在绸角上竟斜斜地绣了Индога一行暗绿色粗丝线的俄文字母,同时格格地笑着说:
“拿去,‘印度嘎’!这是你的名字!”
原来她用了俄文字母把“印度嘎”三个音,拼成为一个俄文字了。
一九三五年我和萧红在上海法租界“万氏照相馆”共同照的一张相上,萧红穿了一件暗蓝色开领的“画衣”,还咬了一只烟斗(其实她平时是不吸烟的,当照相时她看到“道具”盒里有一只烟斗,为了好玩就咬在嘴里了。)我则是穿了过去萧红为了我们赴鲁迅先生召请时的“礼服”(黑白格绒布俄国哥萨克农民式长身立领掩襟的大衬衫),腰间还束了一条细皮带,脖子所围的那块米色围巾,上面还清楚照出来Индога俄文字,就是我们那位佛民娜先生给绣作纪念的。
和萧红比较起来,我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了,不独留下的练习作业常出错误,而且常常完成不了,交不上卷,这使我们这位教师真有些愤怒了。她一面称赞着萧红,一面却严厉地批评着我:
“你看,人家(指萧红)学习得多么好,练习做得多好,总是按时完成。看你,总是不用功,花着学费不好好学习,再这样,下次来我就用‘电线杆’(表示粗大)打你!……”
我能向她解释什么呢?她怎能知道我的“苦衷”?第一,我对于外国文的感受能力、记忆能力,……实在太差(这是先天的,生理的);第二,为了维持生活,我要到几处去做家庭教师,夜间还要教授武术,抽出时间还要写文章……时间确是很紧迫,而精神和身体也确是很疲乏,因此学习时精力很难集中—这一点萧红比我优越些。
我正在实验学习读俄文普希金的一首什么诗,有一句“呀,留不留,节Bia……”意思是“我爱你”。一次不知为什么我竟冲口说了出来,我们的教师忽然惊讶地睁起她的一双小蓝湖似的大眼睛,喊着问我:
“你说什吗?你说什吗?”
我看到她似乎在发怒了,我赶忙把这诗集递过去,并指着那首诗解释着说:
“我在试学着读这首诗呀!”
她把诗静静地看了一刻,轻轻地摇了摇头,忽然竟微笑地把诗集还给了我,用一只手指点着说:
“你这学生!真得用‘电线杆’打了……”
这时一片薄薄的红潮浮上了她那平时有些苍白的脸颊上来了,她把脸俯向课本,命令着我:
“快来学习……”
我们“房东”—也是我做家庭教师的“学东”—养着一只黑色的、短腿的不招人爱的狗—其实它不咬人—但是我们的女教师却很怕它,因此每当她离去,为了看管狗,我总要护送她到大门外,有一次我问她“我为你看管狗”这句话用俄语该怎么说?
“呀,思,马达留,稍八克!……”她教给我了。这我明白:“呀”就是俄语的“我”,“思”是个“关系词”,“马达留”是“看”,“稍八克”就是“狗”。我学会了,也念熟了,因此当我一见到她要走了,就抢着说:
“呀,思,马达留,稍八克!……”
有一次,教课时间还未到应该终结的时候,我看到她从桌子边站起来,我以为她可能有事要提前走了,就急忙抢着说:
“呀,思,马达留,稍八克!……”
她竟耸声大笑了,重新又坐到座位上,用一只手指指点着我说:
“你盼望我早点走,好逃学玩去吗?时间还未到,我不走!……”
我有一点窘了,脸上竟发起热来!……
这就是我学习一场俄文到今天还唯一能记住的三句话:
第一句把“印捷以嘎”错读成“印度嘎”。
第二句是“我爱你”!
第三句是“我给你看狗”!
从我们女教师教授我们俄文中,我还记住一个短短的小故事,名称是《两头苍蝇》或《牛与苍蝇》。这可能是俄国大寓言作家克雷洛夫所写的故事:
有一头苍蝇蹲在一只牛的角上,牛要到田里去耕地。半路上遇到从田里耕完了地正在向回家方向走的一头牛,这只牛的角上也蹲着一头苍蝇。
正在去耕地的牛角上的苍蝇向对面回来的牛角上蹲着的苍蝇很谦敬地问候着说:
“午安!姐姐您到哪里去来着?”
对面牛角上的苍蝇,把头一扬,鼻子一翘,傲慢地、粗声地近于申斥地回答着说:
“你没有看到吗?‘我们’这不是刚刚耕了地才回来的吗?……”
“唔!唔!是!是!……对不起!我眼瞎!我……”这问话的苍蝇连连向对方道歉;两头牛却沉默地擦身而过了……
故事本身大体是如此,我只是把它再复述一番,错误之处,由我负责。
我们全知道,真正耕地的是牛,应该不是那头苍蝇吧!
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多少年来无论谈话或作文,记不清曾引用过它若干次了。……这应该是我学习俄文的最大收获,我很感念我们那位女教师。
由于萧红在信中提到学俄文,不禁就使我回忆起我们曾经学过俄文的历史故事,同时也想到了那俄文先生佛民娜……
信中确是附来一张图,是用钢笔速写的,这使我大体上明白了她的居室布置位置;至于我那张图并没有她的好,因为我毫无绘画的才能和素养,不过是“示意”而已,而她是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和素养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于海北楼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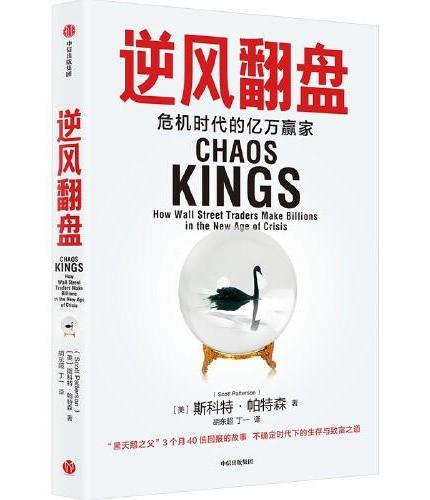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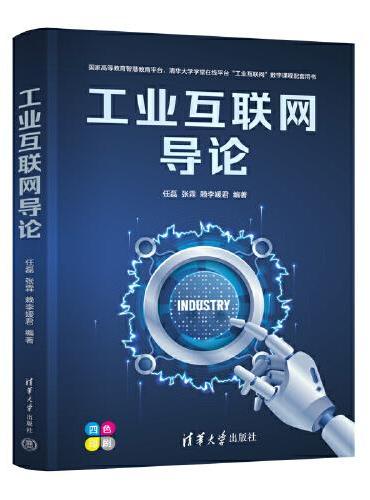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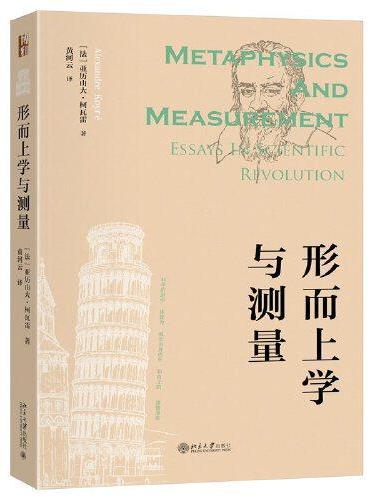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