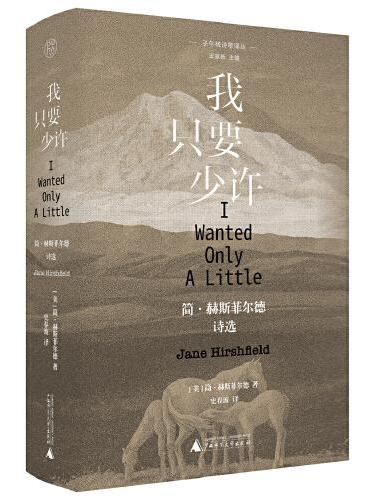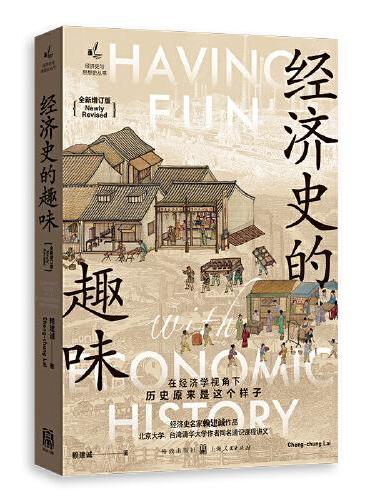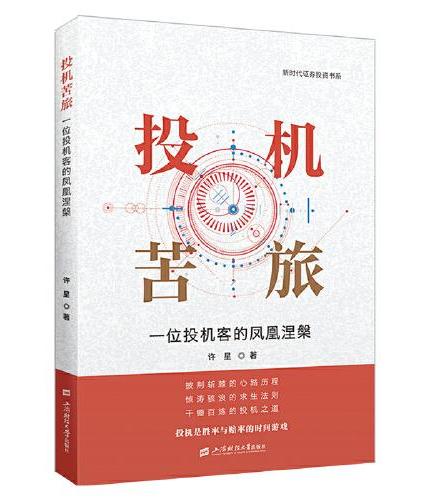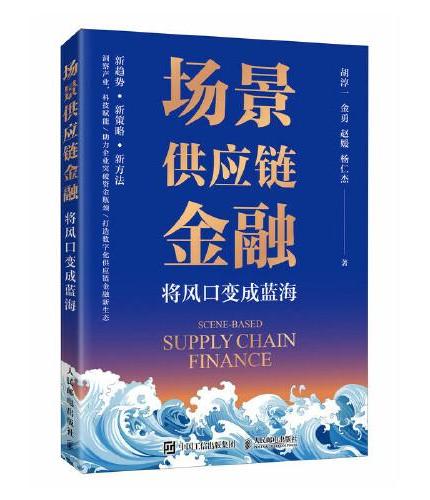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NT$
367.0
《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经济史与思想史丛书)
》 售價:NT$
383.0
《
中国古代鬼神录
》 售價:NT$
866.0
《
投机苦旅:一位投机客的凤凰涅槃
》 售價:NT$
403.0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NT$
316.0
《
日子慢慢向前,事事慢慢如愿
》 售價:NT$
254.0
《
场景供应链金融:将风口变成蓝海
》 售價:NT$
509.0
《
汗青堂丛书146·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家族在东南亚的百年统治
》 售價:NT$
418.0
內容簡介:
《别问我是谁》写了一个男孩的故事:他被叫做小犹太、小吉普赛、斯多普?西夫(Stop!Thief!)、米萨、杰克……他没有父母、没有过去,对自己一无所知。
關於作者:
杰里?史宾尼利(Jerry Spinelli),美国著名作家。作品包括获1991年纽伯瑞金奖的《马尼西亚传奇》(Maniac
目錄
第一部 偷面包的贼
內容試閱
心里想着那块西红柿地和小女孩的眼神,我回到那个后院。她不在那儿了,西红柿也不见了,连最小的绿色的西红柿都没了。但有很多画在纸上的箭头,纸被刺破挂在小树枝上,树枝插在地上。